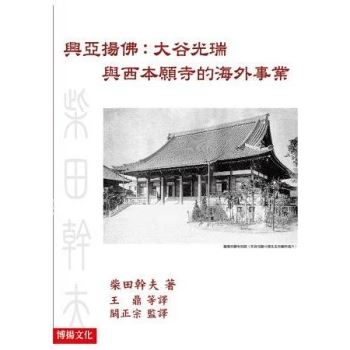緒論
大谷光瑞之研究
序章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足跡遍佈亞洲廣大區域的大谷光瑞(1876-1948)這樣一位日本人的活動,其在亞洲各地以及近代亞洲史之中是處於怎樣的地位?本書以《興亞揚佛:大谷光瑞與西本願寺的海外事業》為題,嘗試去解明大谷光瑞在亞洲各地,其中就中國他的認識又是如何?
大谷光瑞是本願寺•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第22代法主。繼承了宗主•親鸞的法燈和血統於一身,可以說是旁人無法替代的稀有存在。他了無遺憾地活用了他所擁有的宗教權威,從明治後半期到大正初期,不僅站在了巨大真宗教團的高點,同時在亞洲各地區開展廣泛的活動。1914(大正3)年,他因本願寺龐大的負債背景導致的貪污事件而引咎辭去了法主之職,但不可思議的是,他的社會地位卻沒有因此喪失。大谷光瑞在其前本願寺法主的背景下,反而自由地在亞洲各地開展活動。
就像屢屢被強調那樣,大谷光瑞被賦予的特色,或許就是所謂的探尋佛教傳入之跡的「大谷探險隊」(近年新的稱法為:亞洲廣域調查活動)。但是,縱觀大谷光瑞長期開展的各種活動,此探險事業不過為其中的一部而已。因之,在探求大谷光瑞總體形象之時,或許應該與大谷探險隊一起放在他總體活動的比重中來考察。海外開教,尤其是作為清朝開教先驅者的形象,或在辭去法主之職之後,作為一名實業家的形象也有必要一併進行探求。他曾在亞洲各地親自從事絲綢的生產、橡膠園、咖啡園等事業。姑且不論海外開教,就像以營利為目的海外經濟活動那樣,這些都被認為是作為一名宗教者不該有的行為。而上述這些形象至今未被納入研究焦點的原因,或許正在於此吧。借用大谷光瑞的話來說,這些活動包括海外開教,都是在思考「國家之前途」的行為。這是與主導大谷探險隊的大谷光瑞同屬一人的自我認識之根基。
眾所周知,大谷光瑞一直以亞洲佛教徒的領導者自居,其對「國家之前途」抱有很強意識的同時,對本願寺在國家與社會之關係應當發揮的作用也有著深思熟慮。雖然大家只強調他主導的「亞洲廣大區域調查活動」即「大谷光瑞探險隊」,但他的活動不應該僅僅被限定於此,大谷光瑞作為本願寺海外開教先驅者的這個側面,以及近代中日交流史中,其與孫文的之間交流等等是不能忽視的。向來,「大谷探險隊」都被認為是由歐洲各國的中央調查觸發而進行的大谷光瑞個人的特殊探險活動。但是效法明治新政府推動近代化的本願寺的近代化,將「大谷探險隊」看做成日本近代史的問題來研究是幾乎沒有的。同樣,本願寺教團在亞洲地域所開展的一系列活動,也被視為一個巨大的教團的特殊宗教活動,幾乎沒有對其進行體系性以及歷史性的掌握。
最近數年,關於大谷光瑞和大谷探險隊的研究極為活躍。在其去世50年後,由學會誌《東洋史苑》(龍谷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編集了大谷光瑞師五十回忌紀念號,刊載了14篇有關光瑞和其探險隊的論考,引起的學界的矚目,眾所周知。同年,以本願寺為首,在與光瑞有聯繫的場所相繼盛大地舉行了第五十回忌法會和演講會等活動。
受益於第五十回忌的活動,筆者持續對大谷光瑞的研究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即放棄以前「大谷探險隊」一邊倒的研究傾向,研究大谷光瑞在整個亞洲、亦或者在日本國內之中的定位。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作為歷史性存在的大谷光瑞研究已展開。
在明治時代,大谷光瑞嘗親自去證明東方學術的優越地位,在沒有獲得國家援助的情況下,僅憑本願寺自身的力量而開展了中亞探險,這必然是值得稱讚的。但是若是想要掌握光瑞的整體形象,僅僅把光瑞限縮在探險這個活動的話,或許只是管中窺豹而已。時刻都在思考著「國家之前途」的大谷光瑞,與孫文為首的革命黨也有交流,同時也參與制定在上海的都市改造計劃,陳述對於中國的時局強硬的意見等等。因此,我們必須要重新審視在與中國關係中的光瑞的整體形象。大谷光瑞不單單只是宗教家、探險家,時而還發揮著政治家般的作用,同時通曉漢文,善於陶瓷器鑑定、擅長書法,並且是位美食家。若是以一人之力去解密多樣的光瑞,確實困難重重。因此,筆者深感必須組織一支有古代史、近代史或者美術史方面專家共同研究。關於大谷光瑞研究的現狀,過去以研究大谷探險隊關係為中心的自不待言,這數年以筆者為主,展開了對大谷光瑞個人的研究。先驅研究就是高野靜子的《蘇峰與他的時代》(中央公論社,1989年)。高野透過與光瑞有著親交的德富蘇峰(1863-1957)所遺留下來的240封書簡為資料,描述了蘇峰和光瑞之間的關係。尤其在光瑞辭去了本願寺法主之後,蘇峰一直支持著孤獨的光瑞。
再者,一直致力於研究大谷探險隊的隊員,並完美描繪出光瑞像的是白須淨真先生。《被遺忘的明治探險家――渡邊哲信》(中央公論社,1992年),以收錄在大谷探險隊記錄集《新西域記》中的渡邊哲信的《西域旅行日記》為中心,描繪了哲信率領的中亞探險以及他身邊的人物。尤其是對大谷光瑞和哲信出生時明治期本願寺的教育系統,以及關於本願寺輩出的優秀人才的描寫方面,筆者都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由白須先生提出,隨著本願寺的近代化,大谷探險隊也成為了日本近代史領域方面需要重新審視的一個歷史課題。隨後白須先生又在《季刊せいてん》(淨土真宗教學研究所,1996年)雜誌上,以《大谷探險隊與明治時代》為題展開對談。對談所提及的問題不是探險隊,而是對於明治時期的大谷光瑞或者本願寺,如今的重新審視。其後不久,白須先生完成了《大谷探險隊以及那個時代》(勉誠出版,2002年)一書。
此後,描寫同樣是參加第一次探險隊的本多惠隆的生涯的書有《大谷探險隊與本多惠隆》(平凡社,1994年),此書介紹了許多惠隆遺留在所駐錫的德正寺中關於探險隊的相關資料以及照片。
再則,由西澤教夫執筆的《上海へ渡った女たち》(新人物往來社,1996年)正式發行。其中介紹了被選為上海小姐,同時也是大谷光瑞秘書的井上武子,其父親就是大谷探險隊隊員之一井上弘圓。學術以外的一般書籍,也開始提供關於大谷光瑞的話題。
之後,筆者開始了關於大谷光瑞的研究。筆者最初的專門領域是中國近代史,受到中國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的李吉奎教授,以及筆者的恩師之一也就是上海師範大學馬洪林教授的啟示,調查大谷光瑞和孫文之間究何關係。於是筆者查閱《鏡如上人年譜》(鏡如是光瑞的法名)之後,發現有數處記載了其和孫文之間交流的事情。筆者認為,大谷光瑞的目標是以亞洲為中心建立一個大的聯絡網。這個聯絡網,不僅僅限於中國更可以擴大到亞洲全域,當然佛教在其中也起到了樞紐作用。因此,大谷光瑞才積極地推進佛教的海外開教。可是,對華二十一條的要求和五•四運動的高揚,在中國受到軍閥割據及反日運動的激化。在這種狀況下,想要開展新的布教活動並不容易。於是大谷光瑞所關心的,正如小出亨一所指出的,變成了國內外的產業開發構想(小出亨一《大谷光瑞的教育思想與大谷學生》《東洋史苑》50‧51號)以及「大日本帝國的顧問」,大谷光瑞在摸索著自己新的方向。具體來說,就是以臺灣南洋為中心的「橡膠園」、「咖啡園」、「香料農園」等「熱帶農場」以及「大谷光瑞興亞計劃」,還有「歐亞聯絡鐵道計劃」等。大谷光瑞所關心的領域,以北到俄羅斯極東地區、樺太(庫頁島),南到以新加坡為中心的南洋地區、西邊的觸角一直延伸到土耳其。誠然,其中心當然是中國,所以筆者的研究領域也是從俄羅斯一直覆蓋中國、新加坡等地。本論文之所以力陳亞洲廣大區域這個詞彙的理由也是在於此。
與孫文和中國革命軍保持著親近感,而且還不遺餘力的協助在亞洲各地興起的革命運動的光瑞,以及對外方面採取非常強硬的路線的光瑞,這樣一位人物該如何去剖析,或許將會是今後的重大課題之一。
大谷光瑞之研究
序章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足跡遍佈亞洲廣大區域的大谷光瑞(1876-1948)這樣一位日本人的活動,其在亞洲各地以及近代亞洲史之中是處於怎樣的地位?本書以《興亞揚佛:大谷光瑞與西本願寺的海外事業》為題,嘗試去解明大谷光瑞在亞洲各地,其中就中國他的認識又是如何?
大谷光瑞是本願寺•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第22代法主。繼承了宗主•親鸞的法燈和血統於一身,可以說是旁人無法替代的稀有存在。他了無遺憾地活用了他所擁有的宗教權威,從明治後半期到大正初期,不僅站在了巨大真宗教團的高點,同時在亞洲各地區開展廣泛的活動。1914(大正3)年,他因本願寺龐大的負債背景導致的貪污事件而引咎辭去了法主之職,但不可思議的是,他的社會地位卻沒有因此喪失。大谷光瑞在其前本願寺法主的背景下,反而自由地在亞洲各地開展活動。
就像屢屢被強調那樣,大谷光瑞被賦予的特色,或許就是所謂的探尋佛教傳入之跡的「大谷探險隊」(近年新的稱法為:亞洲廣域調查活動)。但是,縱觀大谷光瑞長期開展的各種活動,此探險事業不過為其中的一部而已。因之,在探求大谷光瑞總體形象之時,或許應該與大谷探險隊一起放在他總體活動的比重中來考察。海外開教,尤其是作為清朝開教先驅者的形象,或在辭去法主之職之後,作為一名實業家的形象也有必要一併進行探求。他曾在亞洲各地親自從事絲綢的生產、橡膠園、咖啡園等事業。姑且不論海外開教,就像以營利為目的海外經濟活動那樣,這些都被認為是作為一名宗教者不該有的行為。而上述這些形象至今未被納入研究焦點的原因,或許正在於此吧。借用大谷光瑞的話來說,這些活動包括海外開教,都是在思考「國家之前途」的行為。這是與主導大谷探險隊的大谷光瑞同屬一人的自我認識之根基。
眾所周知,大谷光瑞一直以亞洲佛教徒的領導者自居,其對「國家之前途」抱有很強意識的同時,對本願寺在國家與社會之關係應當發揮的作用也有著深思熟慮。雖然大家只強調他主導的「亞洲廣大區域調查活動」即「大谷光瑞探險隊」,但他的活動不應該僅僅被限定於此,大谷光瑞作為本願寺海外開教先驅者的這個側面,以及近代中日交流史中,其與孫文的之間交流等等是不能忽視的。向來,「大谷探險隊」都被認為是由歐洲各國的中央調查觸發而進行的大谷光瑞個人的特殊探險活動。但是效法明治新政府推動近代化的本願寺的近代化,將「大谷探險隊」看做成日本近代史的問題來研究是幾乎沒有的。同樣,本願寺教團在亞洲地域所開展的一系列活動,也被視為一個巨大的教團的特殊宗教活動,幾乎沒有對其進行體系性以及歷史性的掌握。
最近數年,關於大谷光瑞和大谷探險隊的研究極為活躍。在其去世50年後,由學會誌《東洋史苑》(龍谷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編集了大谷光瑞師五十回忌紀念號,刊載了14篇有關光瑞和其探險隊的論考,引起的學界的矚目,眾所周知。同年,以本願寺為首,在與光瑞有聯繫的場所相繼盛大地舉行了第五十回忌法會和演講會等活動。
受益於第五十回忌的活動,筆者持續對大谷光瑞的研究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即放棄以前「大谷探險隊」一邊倒的研究傾向,研究大谷光瑞在整個亞洲、亦或者在日本國內之中的定位。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作為歷史性存在的大谷光瑞研究已展開。
在明治時代,大谷光瑞嘗親自去證明東方學術的優越地位,在沒有獲得國家援助的情況下,僅憑本願寺自身的力量而開展了中亞探險,這必然是值得稱讚的。但是若是想要掌握光瑞的整體形象,僅僅把光瑞限縮在探險這個活動的話,或許只是管中窺豹而已。時刻都在思考著「國家之前途」的大谷光瑞,與孫文為首的革命黨也有交流,同時也參與制定在上海的都市改造計劃,陳述對於中國的時局強硬的意見等等。因此,我們必須要重新審視在與中國關係中的光瑞的整體形象。大谷光瑞不單單只是宗教家、探險家,時而還發揮著政治家般的作用,同時通曉漢文,善於陶瓷器鑑定、擅長書法,並且是位美食家。若是以一人之力去解密多樣的光瑞,確實困難重重。因此,筆者深感必須組織一支有古代史、近代史或者美術史方面專家共同研究。關於大谷光瑞研究的現狀,過去以研究大谷探險隊關係為中心的自不待言,這數年以筆者為主,展開了對大谷光瑞個人的研究。先驅研究就是高野靜子的《蘇峰與他的時代》(中央公論社,1989年)。高野透過與光瑞有著親交的德富蘇峰(1863-1957)所遺留下來的240封書簡為資料,描述了蘇峰和光瑞之間的關係。尤其在光瑞辭去了本願寺法主之後,蘇峰一直支持著孤獨的光瑞。
再者,一直致力於研究大谷探險隊的隊員,並完美描繪出光瑞像的是白須淨真先生。《被遺忘的明治探險家――渡邊哲信》(中央公論社,1992年),以收錄在大谷探險隊記錄集《新西域記》中的渡邊哲信的《西域旅行日記》為中心,描繪了哲信率領的中亞探險以及他身邊的人物。尤其是對大谷光瑞和哲信出生時明治期本願寺的教育系統,以及關於本願寺輩出的優秀人才的描寫方面,筆者都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由白須先生提出,隨著本願寺的近代化,大谷探險隊也成為了日本近代史領域方面需要重新審視的一個歷史課題。隨後白須先生又在《季刊せいてん》(淨土真宗教學研究所,1996年)雜誌上,以《大谷探險隊與明治時代》為題展開對談。對談所提及的問題不是探險隊,而是對於明治時期的大谷光瑞或者本願寺,如今的重新審視。其後不久,白須先生完成了《大谷探險隊以及那個時代》(勉誠出版,2002年)一書。
此後,描寫同樣是參加第一次探險隊的本多惠隆的生涯的書有《大谷探險隊與本多惠隆》(平凡社,1994年),此書介紹了許多惠隆遺留在所駐錫的德正寺中關於探險隊的相關資料以及照片。
再則,由西澤教夫執筆的《上海へ渡った女たち》(新人物往來社,1996年)正式發行。其中介紹了被選為上海小姐,同時也是大谷光瑞秘書的井上武子,其父親就是大谷探險隊隊員之一井上弘圓。學術以外的一般書籍,也開始提供關於大谷光瑞的話題。
之後,筆者開始了關於大谷光瑞的研究。筆者最初的專門領域是中國近代史,受到中國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的李吉奎教授,以及筆者的恩師之一也就是上海師範大學馬洪林教授的啟示,調查大谷光瑞和孫文之間究何關係。於是筆者查閱《鏡如上人年譜》(鏡如是光瑞的法名)之後,發現有數處記載了其和孫文之間交流的事情。筆者認為,大谷光瑞的目標是以亞洲為中心建立一個大的聯絡網。這個聯絡網,不僅僅限於中國更可以擴大到亞洲全域,當然佛教在其中也起到了樞紐作用。因此,大谷光瑞才積極地推進佛教的海外開教。可是,對華二十一條的要求和五•四運動的高揚,在中國受到軍閥割據及反日運動的激化。在這種狀況下,想要開展新的布教活動並不容易。於是大谷光瑞所關心的,正如小出亨一所指出的,變成了國內外的產業開發構想(小出亨一《大谷光瑞的教育思想與大谷學生》《東洋史苑》50‧51號)以及「大日本帝國的顧問」,大谷光瑞在摸索著自己新的方向。具體來說,就是以臺灣南洋為中心的「橡膠園」、「咖啡園」、「香料農園」等「熱帶農場」以及「大谷光瑞興亞計劃」,還有「歐亞聯絡鐵道計劃」等。大谷光瑞所關心的領域,以北到俄羅斯極東地區、樺太(庫頁島),南到以新加坡為中心的南洋地區、西邊的觸角一直延伸到土耳其。誠然,其中心當然是中國,所以筆者的研究領域也是從俄羅斯一直覆蓋中國、新加坡等地。本論文之所以力陳亞洲廣大區域這個詞彙的理由也是在於此。
與孫文和中國革命軍保持著親近感,而且還不遺餘力的協助在亞洲各地興起的革命運動的光瑞,以及對外方面採取非常強硬的路線的光瑞,這樣一位人物該如何去剖析,或許將會是今後的重大課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