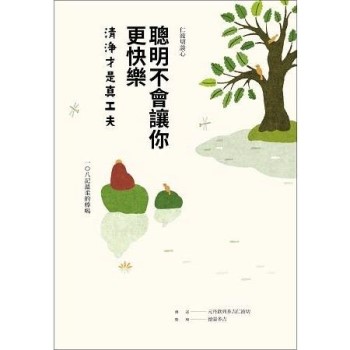叁、別拿輪迴的癮來折磨自己
老師:「人死,為什麼你哭?」
教室裡一片默然。
老師:「因為不是你死!」
台下哄堂大笑。
對錯是一座監獄,
一旦你放開了,監獄就開了。
「人死,為什麼你哭?」這是個好問題;「因為不是你死!」這是個好答案。兩句簡短的話,非常值得大家細細咀嚼。
生死兩頭是件莊嚴的大事。能生而為人,一經父母生下,註定已經是半個贏家,剩下的半個,就看我們自己怎麼去努力。再往更深處去想,當有一天必須告別此生時,你希望自己是怎麼走的?誰來為你掉什麼淚?
我們談的不是輸贏,輸贏需要靠因緣、機緣,這也就是說輸贏需要靠條件和合。但人一輩子都在拼死拼活,贏了就得意,輸了就失意,這似乎也就是人的本性,把這看作了衡量自己來這世間一遭的價值標準。
多少人整天都在為證明自己對、證明別人錯而忙著、堵著,比了一輩子、忙了一輩子、計較了一輩子,結果也氣了一輩子、埋怨了一輩子、庸庸碌碌了一輩子,最終計較的沒計較出什麼、想證明的也沒證明出什麼,埋怨的、氣惱的、心裡不平的,繼續在發生,最後還在比較誰活得比較長。
有人逞了一時之快,輸掉了一輩子;有人贏了上半生,輸掉了下半輩子;有人贏得了報復,卻輸掉了一生;有人贏得了滿堂喝采,卻輸掉了一家人;有人贏得了大樂透,也同時迎來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人比不過人家,又嚥不下自己一口氣,就用上了不正當的手段,甚至毀滅自己。所有那些血淋淋的社會新聞,不都是這樣來的?
書店、媒體、電影、網路,處處都充滿了名人的成功學,陳列了千千萬萬種成功的途徑,鼓舞著人們去爭輸贏,讓人人都以為自己有勝算,拼著一點聰明、一點僥倖也要爭。但人生怎麼定輸贏?什麼是輸?什麼是贏?要輸贏什麼?輸贏又是誰在定?
拿自己一生去跟別人比高低對錯,無非是把自己囚進了一座終身監獄,最終結局無論如何,你都也已經輸了,輸掉了自己的一輩子。唯有放開,一旦你放開了高低對錯,監獄之門就開了。監獄是你造的,是你把自己囚了進去。
肉眼只能幫你看路,
人生要用心量之眼去看。德蒙:我剛踏入社會的時候,有位前輩經常拿一句話鼓勵後輩:「人要服氣,但不能服輸」,說看到別人比自己做得好,你要服氣,服氣才能虛心,但不要服輸,要相信自己付出努力也能做到。上師怎麼看這句話?
仁波切:努力一直都是必須的,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從事什麼樣的職位,每個人都有自己必須擔待的責任,當然要努力。我也非常不贊同人一碰到失敗就退縮,為了鼓勵年輕人要努力,你這位前輩說得好。
但一個人要在俗世的成敗中得意或失意,決定的條件有非常多,其中有兩個極度關鍵,但不是我們看得見的因素,一個叫做因緣,一個就是福報。
有那個福報,一旦因緣成熟,自然就得到條件,你會發現,許多成功的助緣迎面而來,怎麼做就怎麼順。但相反的,如果沒有這份福報,就算你眼看著機會都蜂擁到了門口,但最後總會缺臨門一腳。
所以,人要比什麼?老人家說:「謀是在人,成事在天。」這個天指的其實就是我們的因緣福報,你真要發揮一點企圖心的,是這個,而且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要警覺有這片「天」在為你計成敗。
俗世的成敗就像跨年夜的絢爛煙火,都很短暫,但把日子過好比過新年重要太多了。做人要讓自己活得成功,但不必為追逐成功而活,別拿原本有無限可能的一生去跟煙火一般的成功失敗做賭注,不會划算的。
智商一百八的能夠發明電燈、發現相對論,跟一個智商零蛋的終於摺出一個會飛的紙飛機,你說這兩者的成就誰高誰低?
俗世的成敗,自有俗世的因緣,而我們每個人也都有各自的因緣不同,每個人的立足點、立基點也就不同,所以我說別從各自不同的起跑線出發而去做比較,這麼對待自己只是在處罰自己,這麼對待孩子也就只是折磨孩子而已,如果也這麼看待你的另一半、你的父母兄長,即使這麼折騰成功了,你的家庭極可能也要因此而一敗塗地了。
我不是在叫你看淡,也不是在叫你看開、看破,這個「淡開破」都不是我們這些俗世人說看就可以看得見的。我是在教你看遠、看大,從自己的一生去看眼前這一點,從大輪迴去看我們這一生,很多事情就可以讓你看得比較透、比較寬了。為什麼解脫那麼地難?
因為我們都在不知不覺中上了輪迴的癮。
德蒙:記得還很小的時候,我的祖父就告誡我,不論做什麼事,都要先停一下想想以後,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將來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但千萬不要因為眼前這一下,成為日後終生的遺憾。
進入社會以後,父親也給過一句話:「不要在有情緒的時候做決定。」這個「有情緒」,包括了太高興、太得意、太悲傷或太生氣……。
仁波切:好好地感謝你家裡的這些長輩吧,他們身後可能沒留下什麼傲人的財產給你們,但給了你們最珍貴的錦囊,足以幫你好好地做個對的人,讓你好好過一生。
你的父親和你的祖父分別給你留下的兩句話,聽起來好像不同,但講的其實是同一件事:覺察力和覺知。你要懂得牢牢抓住這兩個錦囊,有意識地在每個待人接物的小細微處拿出來用,日久鐵杵必能磨出繡花針。
人,好像別無選擇地被生下來,別無選擇地生在某個家庭,此後這一生,又好像冥冥中已經為我們寫好了一個劇本,人生只是照這個劇本一幕一幕、一齣一齣無奈地演下去。做人,確實是很辛苦的!但這一切真的都是來自「別無選擇」、冥冥中寫好的嗎?又是誰在寫呢?
幾乎所有人都是不知不覺地在過渡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覺地高興、不知不覺地生氣、不知不覺地憎恨、不知不覺地計較,然後不知不覺地得到或失去、不知不覺地老去,再不知不覺地死去。
世間的一切道理,聽起來都懂,包括佛法所說的貪嗔痴慢疑也都懂,但懂了也就只是懂了,做起來還是不知不覺:貪也不知覺、嗔也不知覺、痴也不知覺、慢也不知覺、疑也不知覺,好壞善惡也都不知覺 —— 就像你不知不覺地吃飯、不知不覺地呼吸、不知不覺的地滑手機,你沒覺知到你吃的每一口飯有多香,覺知不到你還正在一呼一吸有多神奇,就像你沒覺察到你不自覺地又在滑手機,有多麼莫名其妙地上了莫名其妙的癮。
這「癮」就是所有的關鍵字,我們都無所覺知地上了輪迴的許多癮,而且癮頭非常的大,為此而不斷地生與死,不可自拔。
生命的教材隨處都有,
問題是都放在你不喜歡的地方。
每個人都把自己活得很辛苦,但人生真正的問題,實際上都不在於「別無選擇」,而在於「不知不覺」;每個人都在不知不覺地上癮。你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又要滑手機,或許只是感到無聊,你想要從中找樂子、殺時間,美其名為「分享」。但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會讓那麼多的「無聊」來充滿我們的生活?
理論上,文明使得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便利,科技的發展使得我們與人的交流變得彈指可得,無遠弗屆、五彩繽紛,但為什麼我們還是那麼無聊?甚至只感到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無聊?
問題的根源,就在於我們都率真地把自己託付給了別人、給了身外之物,給了這個我們以為充滿快樂、幸福、希望的世界。我們習慣了託付,習慣了寄幾乎所有的希望於我們身外的人事物、習慣了對外求取,逐漸地,「自己」便失去了真實生活的能力,甚至也出賣了「自己」的生存能力。
人與人之間的確有溝通的必要,但一天到晚都忙著跟外界溝通,忙得找不出時間來跟自己溝通,那就非常沒有必要了。放任自己,把出現在我們周遭的每個人都看出了喜歡或討厭,就是看不到自己活得越來越偏狹的由來,更看不到所有這些令你喜歡或討厭的人,給你生命帶來的教材。
你一定也看過不少的動物生態影片,你看那些被圈起來保護的野生動物,等牠被養大了,再把牠野放回去,再如何的猛獸,也要必死無疑。
某種程度來說,我們的「心」、我們「自己」,也就像是這個被圈養、受保護、被豢養的東西,在不知不覺中,早就已經失去了自我求生的本能。但這個失去,卻是我們要來的、求來的。
一切向外求,求來的就是「被圈養」;歸根究柢,是我們自己醉心於此道,求得了「不知不覺」,求得了輪迴,求得了輪迴的圈養。
「自己」是誰?「自己」就是那個醉心於輪迴的「我」;「我」是什麼?「我」就是那個沈溺於身外世界,找不到路回家的「心」。
脫困的方法不在算命而在覺知,
解脫的門戶不在未來而在眼下。
除了一些佛法的閉關課程,我其實很不愛跟大家談業力,因為談業力就像談你與生俱來的基因一樣,總要讓很多人感覺是在潑他們冷水,說你的現在就是你的過去造成的,說你的今生就是你無數個過去世造成的,說業力基因就是已然種下的因,而必然熟成於無可迴避的果,說這就是一切無可改變的苦難的來源,就像家族遺傳不可逆轉的疾病一般。有些人甚至聽得都意志消沈了,感到對生命的無可奈何,感到自己再怎麼努力也無濟於事。去年,我有個機會到亞洲來了一趟,接觸了不下兩千個人,他們大部分都是專程遠道來看我、來找我的,但你不會相信,真正捧心來求佛法、想學佛的人,竟然沒超過三個人。這也就是說,人們最大的關注、最大的興趣,仍在於求俗世,求生活的興隆、回報,仍在求輪迴。
有時候,我甚至感覺佛也不是那麼愛跟大家談業力。我相信,如果只為了創一個欣欣向榮的宗教,他老人家大可每天說說讓人高興的話,再加一點危言聳聽的玄乎乎的道理,告訴大眾如果不給他多燒點好香、不多捐點善款、不多蓋些大廟,就會如何如何倒楣,犯不著每天因果業力的觸人霉頭。但佛還是說了,並且不厭其煩地說。
佛不是個宗教家,不是哪位偉大的神,也不是什麼超級厲害的神秘創教者,「佛」這個字代表「覺悟者」,他發現了解脫生命苦痛的「秘訣」,也發現了原來每個人、每個生命都具備有這種天生的「本能」,因為看到每個人都是那麼無所知覺地深陷在「自己」因為求俗世回報而有的痛苦當中,因此發出大願,無私的去傳授給眾人、給每一位有緣的生命,告訴大家:現世只是業力的現實,要掙脫現實,不在於你對謀求有多努力,而在於你對自己下過多少覺悟的工夫,在每個當下覺知自己的不知不覺。
佛苦口婆心,教我們認清因果,而不是辨識吉凶 —— 他說問題不在吉凶,而在因果;脫困的方法不在算命,而在覺知;解脫的門戶不在未來,就在當下。
最終的抵達就是回到最初;
起點是心,終點也是心。
最終看起來非常遙遠,但實際上就是回到最初 —— 最初就是最終,起點是心,終點也是心;佛法傳授的就是這個,訣竅就在當下。就時間來說,當下在撲面而來的剎那;就空間來說,就在眼下,觸手可及的地方。
起點就是終點,這意味著不管繞多大圈,我們遲早還是得回到那個點,而這也意味著,我們離那個點漸行漸遠,遠得早就互不相識了。
永遠記得珍惜:真正能幫助我們的,始終都在我們的眼前,在我們身邊。很可能,就是我們最感到厭惡的地方,包括自己的家人、自己的配偶、自己的朋友,許多與我們關係最密切的人。關係越深,受苦、受罪、受傷的程度也越深,但許多人都忽略了,這些讓我們自覺受苦、受罪的地方,就正好是我們為自己命運「翻新」最好的地方。因為他們就近在我們的眼前,近在與我們的所有都息息相關,而你無法對這些人、這些事視而不見,他們與你太過緊密了,眼不見為淨是不可能的。但正因為如此,這其中就有了你提煉生命最珍貴的教材。
當一鍋飯開始腐敗的時候,你已經不可能指出到底是從哪一粒米開始的,而你正是這腐敗當中的其中一粒,甚至不會知道腐敗可能就是從你開始的。我們可以理出千百個理由讓自己置身事外,辯說自己的清白,以便數落對方的不是,就是沒看出任何一個理由,讓自己重新回到腐敗當中,為它負上一點應負的責任,或至少回到其中說上一聲道歉。
當關係的腐敗已經發生,我們最該做的,永遠是先讓自己靜心,再回頭去關注這個腐敗,並且記得:我也是這個腐敗當中的一個,腐敗當中沒有清白,所有清白的辯說都是多餘的,都只是傷口上再落下的鹽,只會讓這個腐敗擴大、加深,讓彼此的痛苦和怨恨加劇。一個怨恨的關係絕不會有任何一個人拿得到豁免權,痛苦是雙方共有的,無人能免。
追究誰對誰錯,對一個腐敗的關係絕不會有任何的幫助,而一個愚痴的人,卻總是在事情發生之後,還老在追究源頭的是非。有哪一次證明了誰是誰非了嗎?有哪一次爭執對事態帶來改善了嗎?誰是誰非、誰清白,在你們的關係當中有那麼重要嗎?不用回答我,這些都留給大家去想。
關係中的疼痛,
是緣份帶給我們的機會。
同在一個屋簷下,當一個不如預期的結果發生了,就好好地去對待這個結果,把它當作一個處理的開始,好好地去解一個結。無論追不追究,處理都需要時間,而追究只會再為它多打幾個沒有必要的結,徒勞浪費生命而已,並且是非對錯都已經隨著結果的發生而過去,再拿稍縱即逝的此刻去為爭辯過去花時間,這不是浪費生命的愚痴之舉嗎?
一個親如家人的關係當中,本沒有任何一個是非對錯足以帶來致命的後果,但腐敗會,腐敗對關係有絕對的殺傷力,腐敗會給同一鍋飯的每一粒米帶來悔之莫及的後果,而腐敗卻是從坐視一個小小的變質開始的。當一個不如預期的結果發生時,我建議,先靜下心來,檢查是自己的哪些執念參與了眼前的判斷?不如預期的是事態,還是你的心態?你為此感覺受傷了,究竟是你的什麼在受傷?它傷在你的哪裡?為什麼受傷?
永遠記得:你對事情的反應,其實只是反應了你自己,而你的反應正決定著這個事情的結果,以及這個事態持續的變化,你可以對它一笑置之,你可以把它變成垃圾,你也可以把它變成怨恨。
如果你是一個學習的人,那你應該看見:正是這些苦碰觸到了我們侷限的痛處,讓我們發現了自己存在的這些侷限、這些容易讓我們遭致痛苦的痛點,然後就像循著身體的疼痛點,就不難找到病灶一般,正好給予施治。
對身體的疾病而言,疼痛有它不可替代的診療價值;對我們生命的淬煉而言,心中的苦痛又何嘗不是?關係之中的怨恨,就像身上不治的惡性腫瘤,都是我們坐視疼痛的結果。
讓我再提示一些:關係中的疼痛,本不是事物的本質,而是我們自己的侷限,疼痛就來自這些我們看不見的侷限;疼痛是緣份帶給我們的機會。
今生能成為彼此關係密切的人,尤其是一家人,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我們最需要學習掛在嘴邊的,就是謝謝、對不起。
「愛,就是不用說抱歉」,這都是你說了謝謝、對不起之後的話。好好謝謝,並且珍惜這些為你帶來苦、帶來疼痛的人吧!
修善要從身邊人開始,
度人要從度自己起步。
德蒙:多年前,我曾經在澳門接受一位修行者的指導。那年,我的父親剛剛往生,她告訴我,我的父親現在很好,別為他擔心;「你要不信,我現在就可以讓你看到,你想看嗎?」我想了一想,搖搖頭……。
仁波切:嗯,不看的好,讓老人家好好地上路。他要不好,就算你看了,也幫不上什麼忙,操心而已。生前做的事,比身後重要太多了;幫老人家做做佛事,比幫他做俗事,好太多了。他好,你們一家人都會好。
德蒙:這位修行人告訴我,每一個我們遇見的人,都一定和我們有緣,所以要我謹記,即使只是路上擦肩而過、對望一眼,記得當下就給對方送上一聲「阿彌陀佛」,因為「你們在這一世相遇,可能就只為了還這一眼的緣」。
仁波切:那你謹記了嗎?做了嗎?
德蒙:很慚愧,有想起來就一定做,但經常都沒有想起來……。
仁波切:是,這樣你知道覺知和正念的生起有多不容易了吧?所有能和我們相遇、相見、相處的,都絕非偶然;即使你認為只是個意外,他們過去都和你有過關係,而現在又已經和你有了關係,你們也將在此後牽連著彼此一段路。這一層關係,就是一個因緣,關係越深,意味著這一層因緣也越深;譬如我們的近親。這一段路或長或短,或者愛、或者恨,或者恩、或者怨,但如果你真想過要解脫,你就要真心、正念的去走這一段。
近親包括與我們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的家人、同一個場所工作的同事,以及那些和我們相交密切的朋友,包括或許不稱為朋友但來往頻繁的人。你必須靠著這許多關係來過渡你的此生,這就意味著,這其中每一個因為關係而有的關卡,你都必須要「過」,每一個因緣都需要你花心思、花時間去「度」,而尤其你必須藉著這些來「度」你自己。
佛講的菩提心,是從自己的「度」開始的 —— 你度了你的侷限了嗎?你度了你的煩惱、障礙了嗎?你度了自己的恐懼和不安了嗎?
人只有真心想要度自己以後,才能真實的體會出生命的滋味,並且覺知出苦痛的來源,從這些苦痛了知原來我和眾生、眾生和我,彼此之間是多麼緊密、微妙而奇特,才能夠從中得到真實的智慧,開始體現慈悲心的生起。
沒有這份了知,說要度誰,都只是大話、痴人說夢,只一味把智慧、慈悲當教條強加給別人,一味要求別人的改變和改善,得到符合於我們單向期望的妥協。但妥協不是幫忙、更不是度,你對別人的要求當然也不是。
給自己一次機會吧,整個輪迴只要有這麼一次無怨無悔,這其中的苦就過了;換句話說,就被你自己「度」了。
因緣道上,
錯過一秒便是錯整盤。
許多時候,我眼看著、耳聽著許多人來到我面前,發著對家人的抱怨,說著自己的委屈,說自己已經費盡了多大的心力而依然無解的無力,我心裡最想向他們分解的,就是我以上所說的話。
但我給了建議也沒有多少人能聽得進去,聽了也未必就拿出來用、拿出來實踐,總以為一定還有個更便捷、更俐落,立竿就可見影的方法,所以去做也不過就是兩三天的熱度;熱度一過又不行了,仍然繼續著他四處訴苦、到處燒香、算命卜卦的旅程。當然,我相信我可能也就是他尋求過的第四十八個、第八十四個,而他永遠都難以理解到:問題的根源,始終就只在他一個。凡人都只看到自己的付出,以為自己付出了多少又多少,因此他虧欠於你多少又多少,卻看不到別人的,無視於別人的付出多少又多少。但關係的建立,往往都來自拖欠,沒有拖欠就不會有關係,沒有付出也難以成立關係,只是對方的付出不是你想的、你要的,就像你給對方的付出未必是他想要的一樣。
因緣本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三言兩語的事,它千絲萬縷。但它也就是一個簡單的事,你要覺得它煩、覺得它讓你透不過氣,就快快把它給了了,就是我常說的「善了因緣」,把它給善了了,這條線、這張網就結束了。
不要再等明天、不要再等來生,連下一秒都不要等,你知道一秒能發生多少事?發生多少變化?誰知道錯過一秒,就能錯過多少事?因緣道上,往往也只錯過了一點點,就錯過了一整盤。
德蒙在澳門見到的那位修行人,她要教的,也就是這些。記得要時時刻刻把它拿出來用,別只把它放在腦海裡,讓它只留在溫馨的記憶中;就像是治病求醫,就算你取得了仙丹,你也要實地拿來用,它才會有用。
花開並沒想過要取悅你,
所以它取悅了你。
或許你也在渴求著和諧,你的對方也在渴求著和諧,但為什麼彼此的和諧如此不可得?
和諧是個自然而然的狀態,你也許會說和諧來自互相的包容,但包容仍是個帶有道德性質的思想,自然而然是不需要任何道德、思想、性質去驅動的,就像花要開、水要流、鳥要唱歌,所有自然而然的事都是不假思索的。
真正的智慧和愛,都是不假思索的,它不是來自頭腦的思索,而是心的流露。人與人之間所有的「求」,都來自頭腦,頭腦本來就不是一個善於抵達心的東西,它只是個衡量的工具,它只擅長於評估、擅長於計算、擅長於預測,而人人所求都只是為了實現自己腦中勾勒的藍圖,這就是你所求的和諧、他所求的和諧,如此不可得的原因。
大凡人只要碰上不順心的事,心眼裡就只剩下那個「結」,一股腦的就只想著對付那個「結」。這個順與不順的「心眼」就是頭腦的,自始至終都是經由它評估、計算、預測而有的不平衡。「結」的產生源自頭腦的編織,最後仍交由它指揮做出行動,這個「結」就這麼越打越緊、越打越死了。
老師:「人死,為什麼你哭?」
教室裡一片默然。
老師:「因為不是你死!」
台下哄堂大笑。
對錯是一座監獄,
一旦你放開了,監獄就開了。
「人死,為什麼你哭?」這是個好問題;「因為不是你死!」這是個好答案。兩句簡短的話,非常值得大家細細咀嚼。
生死兩頭是件莊嚴的大事。能生而為人,一經父母生下,註定已經是半個贏家,剩下的半個,就看我們自己怎麼去努力。再往更深處去想,當有一天必須告別此生時,你希望自己是怎麼走的?誰來為你掉什麼淚?
我們談的不是輸贏,輸贏需要靠因緣、機緣,這也就是說輸贏需要靠條件和合。但人一輩子都在拼死拼活,贏了就得意,輸了就失意,這似乎也就是人的本性,把這看作了衡量自己來這世間一遭的價值標準。
多少人整天都在為證明自己對、證明別人錯而忙著、堵著,比了一輩子、忙了一輩子、計較了一輩子,結果也氣了一輩子、埋怨了一輩子、庸庸碌碌了一輩子,最終計較的沒計較出什麼、想證明的也沒證明出什麼,埋怨的、氣惱的、心裡不平的,繼續在發生,最後還在比較誰活得比較長。
有人逞了一時之快,輸掉了一輩子;有人贏了上半生,輸掉了下半輩子;有人贏得了報復,卻輸掉了一生;有人贏得了滿堂喝采,卻輸掉了一家人;有人贏得了大樂透,也同時迎來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人比不過人家,又嚥不下自己一口氣,就用上了不正當的手段,甚至毀滅自己。所有那些血淋淋的社會新聞,不都是這樣來的?
書店、媒體、電影、網路,處處都充滿了名人的成功學,陳列了千千萬萬種成功的途徑,鼓舞著人們去爭輸贏,讓人人都以為自己有勝算,拼著一點聰明、一點僥倖也要爭。但人生怎麼定輸贏?什麼是輸?什麼是贏?要輸贏什麼?輸贏又是誰在定?
拿自己一生去跟別人比高低對錯,無非是把自己囚進了一座終身監獄,最終結局無論如何,你都也已經輸了,輸掉了自己的一輩子。唯有放開,一旦你放開了高低對錯,監獄之門就開了。監獄是你造的,是你把自己囚了進去。
肉眼只能幫你看路,
人生要用心量之眼去看。德蒙:我剛踏入社會的時候,有位前輩經常拿一句話鼓勵後輩:「人要服氣,但不能服輸」,說看到別人比自己做得好,你要服氣,服氣才能虛心,但不要服輸,要相信自己付出努力也能做到。上師怎麼看這句話?
仁波切:努力一直都是必須的,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從事什麼樣的職位,每個人都有自己必須擔待的責任,當然要努力。我也非常不贊同人一碰到失敗就退縮,為了鼓勵年輕人要努力,你這位前輩說得好。
但一個人要在俗世的成敗中得意或失意,決定的條件有非常多,其中有兩個極度關鍵,但不是我們看得見的因素,一個叫做因緣,一個就是福報。
有那個福報,一旦因緣成熟,自然就得到條件,你會發現,許多成功的助緣迎面而來,怎麼做就怎麼順。但相反的,如果沒有這份福報,就算你眼看著機會都蜂擁到了門口,但最後總會缺臨門一腳。
所以,人要比什麼?老人家說:「謀是在人,成事在天。」這個天指的其實就是我們的因緣福報,你真要發揮一點企圖心的,是這個,而且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要警覺有這片「天」在為你計成敗。
俗世的成敗就像跨年夜的絢爛煙火,都很短暫,但把日子過好比過新年重要太多了。做人要讓自己活得成功,但不必為追逐成功而活,別拿原本有無限可能的一生去跟煙火一般的成功失敗做賭注,不會划算的。
智商一百八的能夠發明電燈、發現相對論,跟一個智商零蛋的終於摺出一個會飛的紙飛機,你說這兩者的成就誰高誰低?
俗世的成敗,自有俗世的因緣,而我們每個人也都有各自的因緣不同,每個人的立足點、立基點也就不同,所以我說別從各自不同的起跑線出發而去做比較,這麼對待自己只是在處罰自己,這麼對待孩子也就只是折磨孩子而已,如果也這麼看待你的另一半、你的父母兄長,即使這麼折騰成功了,你的家庭極可能也要因此而一敗塗地了。
我不是在叫你看淡,也不是在叫你看開、看破,這個「淡開破」都不是我們這些俗世人說看就可以看得見的。我是在教你看遠、看大,從自己的一生去看眼前這一點,從大輪迴去看我們這一生,很多事情就可以讓你看得比較透、比較寬了。為什麼解脫那麼地難?
因為我們都在不知不覺中上了輪迴的癮。
德蒙:記得還很小的時候,我的祖父就告誡我,不論做什麼事,都要先停一下想想以後,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將來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但千萬不要因為眼前這一下,成為日後終生的遺憾。
進入社會以後,父親也給過一句話:「不要在有情緒的時候做決定。」這個「有情緒」,包括了太高興、太得意、太悲傷或太生氣……。
仁波切:好好地感謝你家裡的這些長輩吧,他們身後可能沒留下什麼傲人的財產給你們,但給了你們最珍貴的錦囊,足以幫你好好地做個對的人,讓你好好過一生。
你的父親和你的祖父分別給你留下的兩句話,聽起來好像不同,但講的其實是同一件事:覺察力和覺知。你要懂得牢牢抓住這兩個錦囊,有意識地在每個待人接物的小細微處拿出來用,日久鐵杵必能磨出繡花針。
人,好像別無選擇地被生下來,別無選擇地生在某個家庭,此後這一生,又好像冥冥中已經為我們寫好了一個劇本,人生只是照這個劇本一幕一幕、一齣一齣無奈地演下去。做人,確實是很辛苦的!但這一切真的都是來自「別無選擇」、冥冥中寫好的嗎?又是誰在寫呢?
幾乎所有人都是不知不覺地在過渡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覺地高興、不知不覺地生氣、不知不覺地憎恨、不知不覺地計較,然後不知不覺地得到或失去、不知不覺地老去,再不知不覺地死去。
世間的一切道理,聽起來都懂,包括佛法所說的貪嗔痴慢疑也都懂,但懂了也就只是懂了,做起來還是不知不覺:貪也不知覺、嗔也不知覺、痴也不知覺、慢也不知覺、疑也不知覺,好壞善惡也都不知覺 —— 就像你不知不覺地吃飯、不知不覺地呼吸、不知不覺的地滑手機,你沒覺知到你吃的每一口飯有多香,覺知不到你還正在一呼一吸有多神奇,就像你沒覺察到你不自覺地又在滑手機,有多麼莫名其妙地上了莫名其妙的癮。
這「癮」就是所有的關鍵字,我們都無所覺知地上了輪迴的許多癮,而且癮頭非常的大,為此而不斷地生與死,不可自拔。
生命的教材隨處都有,
問題是都放在你不喜歡的地方。
每個人都把自己活得很辛苦,但人生真正的問題,實際上都不在於「別無選擇」,而在於「不知不覺」;每個人都在不知不覺地上癮。你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又要滑手機,或許只是感到無聊,你想要從中找樂子、殺時間,美其名為「分享」。但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會讓那麼多的「無聊」來充滿我們的生活?
理論上,文明使得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便利,科技的發展使得我們與人的交流變得彈指可得,無遠弗屆、五彩繽紛,但為什麼我們還是那麼無聊?甚至只感到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無聊?
問題的根源,就在於我們都率真地把自己託付給了別人、給了身外之物,給了這個我們以為充滿快樂、幸福、希望的世界。我們習慣了託付,習慣了寄幾乎所有的希望於我們身外的人事物、習慣了對外求取,逐漸地,「自己」便失去了真實生活的能力,甚至也出賣了「自己」的生存能力。
人與人之間的確有溝通的必要,但一天到晚都忙著跟外界溝通,忙得找不出時間來跟自己溝通,那就非常沒有必要了。放任自己,把出現在我們周遭的每個人都看出了喜歡或討厭,就是看不到自己活得越來越偏狹的由來,更看不到所有這些令你喜歡或討厭的人,給你生命帶來的教材。
你一定也看過不少的動物生態影片,你看那些被圈起來保護的野生動物,等牠被養大了,再把牠野放回去,再如何的猛獸,也要必死無疑。
某種程度來說,我們的「心」、我們「自己」,也就像是這個被圈養、受保護、被豢養的東西,在不知不覺中,早就已經失去了自我求生的本能。但這個失去,卻是我們要來的、求來的。
一切向外求,求來的就是「被圈養」;歸根究柢,是我們自己醉心於此道,求得了「不知不覺」,求得了輪迴,求得了輪迴的圈養。
「自己」是誰?「自己」就是那個醉心於輪迴的「我」;「我」是什麼?「我」就是那個沈溺於身外世界,找不到路回家的「心」。
脫困的方法不在算命而在覺知,
解脫的門戶不在未來而在眼下。
除了一些佛法的閉關課程,我其實很不愛跟大家談業力,因為談業力就像談你與生俱來的基因一樣,總要讓很多人感覺是在潑他們冷水,說你的現在就是你的過去造成的,說你的今生就是你無數個過去世造成的,說業力基因就是已然種下的因,而必然熟成於無可迴避的果,說這就是一切無可改變的苦難的來源,就像家族遺傳不可逆轉的疾病一般。有些人甚至聽得都意志消沈了,感到對生命的無可奈何,感到自己再怎麼努力也無濟於事。去年,我有個機會到亞洲來了一趟,接觸了不下兩千個人,他們大部分都是專程遠道來看我、來找我的,但你不會相信,真正捧心來求佛法、想學佛的人,竟然沒超過三個人。這也就是說,人們最大的關注、最大的興趣,仍在於求俗世,求生活的興隆、回報,仍在求輪迴。
有時候,我甚至感覺佛也不是那麼愛跟大家談業力。我相信,如果只為了創一個欣欣向榮的宗教,他老人家大可每天說說讓人高興的話,再加一點危言聳聽的玄乎乎的道理,告訴大眾如果不給他多燒點好香、不多捐點善款、不多蓋些大廟,就會如何如何倒楣,犯不著每天因果業力的觸人霉頭。但佛還是說了,並且不厭其煩地說。
佛不是個宗教家,不是哪位偉大的神,也不是什麼超級厲害的神秘創教者,「佛」這個字代表「覺悟者」,他發現了解脫生命苦痛的「秘訣」,也發現了原來每個人、每個生命都具備有這種天生的「本能」,因為看到每個人都是那麼無所知覺地深陷在「自己」因為求俗世回報而有的痛苦當中,因此發出大願,無私的去傳授給眾人、給每一位有緣的生命,告訴大家:現世只是業力的現實,要掙脫現實,不在於你對謀求有多努力,而在於你對自己下過多少覺悟的工夫,在每個當下覺知自己的不知不覺。
佛苦口婆心,教我們認清因果,而不是辨識吉凶 —— 他說問題不在吉凶,而在因果;脫困的方法不在算命,而在覺知;解脫的門戶不在未來,就在當下。
最終的抵達就是回到最初;
起點是心,終點也是心。
最終看起來非常遙遠,但實際上就是回到最初 —— 最初就是最終,起點是心,終點也是心;佛法傳授的就是這個,訣竅就在當下。就時間來說,當下在撲面而來的剎那;就空間來說,就在眼下,觸手可及的地方。
起點就是終點,這意味著不管繞多大圈,我們遲早還是得回到那個點,而這也意味著,我們離那個點漸行漸遠,遠得早就互不相識了。
永遠記得珍惜:真正能幫助我們的,始終都在我們的眼前,在我們身邊。很可能,就是我們最感到厭惡的地方,包括自己的家人、自己的配偶、自己的朋友,許多與我們關係最密切的人。關係越深,受苦、受罪、受傷的程度也越深,但許多人都忽略了,這些讓我們自覺受苦、受罪的地方,就正好是我們為自己命運「翻新」最好的地方。因為他們就近在我們的眼前,近在與我們的所有都息息相關,而你無法對這些人、這些事視而不見,他們與你太過緊密了,眼不見為淨是不可能的。但正因為如此,這其中就有了你提煉生命最珍貴的教材。
當一鍋飯開始腐敗的時候,你已經不可能指出到底是從哪一粒米開始的,而你正是這腐敗當中的其中一粒,甚至不會知道腐敗可能就是從你開始的。我們可以理出千百個理由讓自己置身事外,辯說自己的清白,以便數落對方的不是,就是沒看出任何一個理由,讓自己重新回到腐敗當中,為它負上一點應負的責任,或至少回到其中說上一聲道歉。
當關係的腐敗已經發生,我們最該做的,永遠是先讓自己靜心,再回頭去關注這個腐敗,並且記得:我也是這個腐敗當中的一個,腐敗當中沒有清白,所有清白的辯說都是多餘的,都只是傷口上再落下的鹽,只會讓這個腐敗擴大、加深,讓彼此的痛苦和怨恨加劇。一個怨恨的關係絕不會有任何一個人拿得到豁免權,痛苦是雙方共有的,無人能免。
追究誰對誰錯,對一個腐敗的關係絕不會有任何的幫助,而一個愚痴的人,卻總是在事情發生之後,還老在追究源頭的是非。有哪一次證明了誰是誰非了嗎?有哪一次爭執對事態帶來改善了嗎?誰是誰非、誰清白,在你們的關係當中有那麼重要嗎?不用回答我,這些都留給大家去想。
關係中的疼痛,
是緣份帶給我們的機會。
同在一個屋簷下,當一個不如預期的結果發生了,就好好地去對待這個結果,把它當作一個處理的開始,好好地去解一個結。無論追不追究,處理都需要時間,而追究只會再為它多打幾個沒有必要的結,徒勞浪費生命而已,並且是非對錯都已經隨著結果的發生而過去,再拿稍縱即逝的此刻去為爭辯過去花時間,這不是浪費生命的愚痴之舉嗎?
一個親如家人的關係當中,本沒有任何一個是非對錯足以帶來致命的後果,但腐敗會,腐敗對關係有絕對的殺傷力,腐敗會給同一鍋飯的每一粒米帶來悔之莫及的後果,而腐敗卻是從坐視一個小小的變質開始的。當一個不如預期的結果發生時,我建議,先靜下心來,檢查是自己的哪些執念參與了眼前的判斷?不如預期的是事態,還是你的心態?你為此感覺受傷了,究竟是你的什麼在受傷?它傷在你的哪裡?為什麼受傷?
永遠記得:你對事情的反應,其實只是反應了你自己,而你的反應正決定著這個事情的結果,以及這個事態持續的變化,你可以對它一笑置之,你可以把它變成垃圾,你也可以把它變成怨恨。
如果你是一個學習的人,那你應該看見:正是這些苦碰觸到了我們侷限的痛處,讓我們發現了自己存在的這些侷限、這些容易讓我們遭致痛苦的痛點,然後就像循著身體的疼痛點,就不難找到病灶一般,正好給予施治。
對身體的疾病而言,疼痛有它不可替代的診療價值;對我們生命的淬煉而言,心中的苦痛又何嘗不是?關係之中的怨恨,就像身上不治的惡性腫瘤,都是我們坐視疼痛的結果。
讓我再提示一些:關係中的疼痛,本不是事物的本質,而是我們自己的侷限,疼痛就來自這些我們看不見的侷限;疼痛是緣份帶給我們的機會。
今生能成為彼此關係密切的人,尤其是一家人,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我們最需要學習掛在嘴邊的,就是謝謝、對不起。
「愛,就是不用說抱歉」,這都是你說了謝謝、對不起之後的話。好好謝謝,並且珍惜這些為你帶來苦、帶來疼痛的人吧!
修善要從身邊人開始,
度人要從度自己起步。
德蒙:多年前,我曾經在澳門接受一位修行者的指導。那年,我的父親剛剛往生,她告訴我,我的父親現在很好,別為他擔心;「你要不信,我現在就可以讓你看到,你想看嗎?」我想了一想,搖搖頭……。
仁波切:嗯,不看的好,讓老人家好好地上路。他要不好,就算你看了,也幫不上什麼忙,操心而已。生前做的事,比身後重要太多了;幫老人家做做佛事,比幫他做俗事,好太多了。他好,你們一家人都會好。
德蒙:這位修行人告訴我,每一個我們遇見的人,都一定和我們有緣,所以要我謹記,即使只是路上擦肩而過、對望一眼,記得當下就給對方送上一聲「阿彌陀佛」,因為「你們在這一世相遇,可能就只為了還這一眼的緣」。
仁波切:那你謹記了嗎?做了嗎?
德蒙:很慚愧,有想起來就一定做,但經常都沒有想起來……。
仁波切:是,這樣你知道覺知和正念的生起有多不容易了吧?所有能和我們相遇、相見、相處的,都絕非偶然;即使你認為只是個意外,他們過去都和你有過關係,而現在又已經和你有了關係,你們也將在此後牽連著彼此一段路。這一層關係,就是一個因緣,關係越深,意味著這一層因緣也越深;譬如我們的近親。這一段路或長或短,或者愛、或者恨,或者恩、或者怨,但如果你真想過要解脫,你就要真心、正念的去走這一段。
近親包括與我們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的家人、同一個場所工作的同事,以及那些和我們相交密切的朋友,包括或許不稱為朋友但來往頻繁的人。你必須靠著這許多關係來過渡你的此生,這就意味著,這其中每一個因為關係而有的關卡,你都必須要「過」,每一個因緣都需要你花心思、花時間去「度」,而尤其你必須藉著這些來「度」你自己。
佛講的菩提心,是從自己的「度」開始的 —— 你度了你的侷限了嗎?你度了你的煩惱、障礙了嗎?你度了自己的恐懼和不安了嗎?
人只有真心想要度自己以後,才能真實的體會出生命的滋味,並且覺知出苦痛的來源,從這些苦痛了知原來我和眾生、眾生和我,彼此之間是多麼緊密、微妙而奇特,才能夠從中得到真實的智慧,開始體現慈悲心的生起。
沒有這份了知,說要度誰,都只是大話、痴人說夢,只一味把智慧、慈悲當教條強加給別人,一味要求別人的改變和改善,得到符合於我們單向期望的妥協。但妥協不是幫忙、更不是度,你對別人的要求當然也不是。
給自己一次機會吧,整個輪迴只要有這麼一次無怨無悔,這其中的苦就過了;換句話說,就被你自己「度」了。
因緣道上,
錯過一秒便是錯整盤。
許多時候,我眼看著、耳聽著許多人來到我面前,發著對家人的抱怨,說著自己的委屈,說自己已經費盡了多大的心力而依然無解的無力,我心裡最想向他們分解的,就是我以上所說的話。
但我給了建議也沒有多少人能聽得進去,聽了也未必就拿出來用、拿出來實踐,總以為一定還有個更便捷、更俐落,立竿就可見影的方法,所以去做也不過就是兩三天的熱度;熱度一過又不行了,仍然繼續著他四處訴苦、到處燒香、算命卜卦的旅程。當然,我相信我可能也就是他尋求過的第四十八個、第八十四個,而他永遠都難以理解到:問題的根源,始終就只在他一個。凡人都只看到自己的付出,以為自己付出了多少又多少,因此他虧欠於你多少又多少,卻看不到別人的,無視於別人的付出多少又多少。但關係的建立,往往都來自拖欠,沒有拖欠就不會有關係,沒有付出也難以成立關係,只是對方的付出不是你想的、你要的,就像你給對方的付出未必是他想要的一樣。
因緣本來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三言兩語的事,它千絲萬縷。但它也就是一個簡單的事,你要覺得它煩、覺得它讓你透不過氣,就快快把它給了了,就是我常說的「善了因緣」,把它給善了了,這條線、這張網就結束了。
不要再等明天、不要再等來生,連下一秒都不要等,你知道一秒能發生多少事?發生多少變化?誰知道錯過一秒,就能錯過多少事?因緣道上,往往也只錯過了一點點,就錯過了一整盤。
德蒙在澳門見到的那位修行人,她要教的,也就是這些。記得要時時刻刻把它拿出來用,別只把它放在腦海裡,讓它只留在溫馨的記憶中;就像是治病求醫,就算你取得了仙丹,你也要實地拿來用,它才會有用。
花開並沒想過要取悅你,
所以它取悅了你。
或許你也在渴求著和諧,你的對方也在渴求著和諧,但為什麼彼此的和諧如此不可得?
和諧是個自然而然的狀態,你也許會說和諧來自互相的包容,但包容仍是個帶有道德性質的思想,自然而然是不需要任何道德、思想、性質去驅動的,就像花要開、水要流、鳥要唱歌,所有自然而然的事都是不假思索的。
真正的智慧和愛,都是不假思索的,它不是來自頭腦的思索,而是心的流露。人與人之間所有的「求」,都來自頭腦,頭腦本來就不是一個善於抵達心的東西,它只是個衡量的工具,它只擅長於評估、擅長於計算、擅長於預測,而人人所求都只是為了實現自己腦中勾勒的藍圖,這就是你所求的和諧、他所求的和諧,如此不可得的原因。
大凡人只要碰上不順心的事,心眼裡就只剩下那個「結」,一股腦的就只想著對付那個「結」。這個順與不順的「心眼」就是頭腦的,自始至終都是經由它評估、計算、預測而有的不平衡。「結」的產生源自頭腦的編織,最後仍交由它指揮做出行動,這個「結」就這麼越打越緊、越打越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