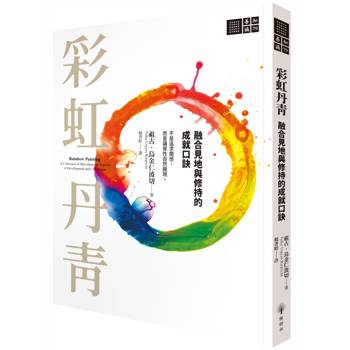大手印、大圓滿、中觀
無論九乘的哪一乘,其見地的要點,除了空性之外,別無其他。每個法乘都是為了要讓行者體證事物的空性,並運用於修行中,且都維護了毫無瑕疵且正確無誤的法要。沒有人會想修行某個自身已知並不完美的道路,因此,各個法乘都主張特定的見地和運用的方法,且此方法乃是真誠且純正的。
依此,不同法乘的見地或取向也有所不同。小乘法教的見地,是從最基本的奢摩他──「止」修開始修持。這是經由不斷以觀照而專注於靜止來達成,最終的成果為成就全然平等捨之境,所有念頭盡皆止息的靜止狀態。
從小乘而上,關於心性真貌的觀念便越來越精細和細微。不過,在所有這些修持當中,要一直持守某個觀念,儘管這個觀念比起我們一般凡念中的觀念來說細微得多。
聲聞乘通常被稱為單一取向。實際上,在佛陀圓寂之後,聲聞乘行者分為十八派別。這十八分支其一,稱為說一切有部的派別在藏地以寺廟的傳承延續,另一者則傳至斯里蘭卡並在其他國家弘揚,其他十六派別都已銷聲匿跡。緣覺乘提及有兩種行者:如鸚鵡般的「群聚型」,以及如犀牛般的「獨身型」。
菩薩乘或稱大乘,具有各種不同的法門,例如三十七道品(三十七佛子行)。也有不同的哲學派別,例如唯識和中觀。這些又各自有許多的分支,以及許多詳盡的分類。大乘法教是藉心智的洞察力來奠定空性的見地,以便「離於四種極端和八種心意造作」。大乘行者主張,此心既非存在、亦非不存在,既非兩者皆是、亦非兩者皆非。最終的主張是,空性乃超越此四種極端(四邊)。這個見地依然留存一些對於空性概念的細微想法或固著。
大手印、大圓滿、中觀的見地之間有任何差異嗎?有時候會說,大手印為根基,中觀為道路,大圓滿則是果熟。這其中是否有差異,端看我們要討論的層面為何。請大家明瞭,中觀並非僅是中觀;你必須界定考量的層面。中觀有著不同的分派,自續派中觀、應成派中觀,以及了義大中觀。
大手印則分為經部大手印、續部大手印,以及精要大手印。經教大手印即是大乘所描述五道十地的次第修持。這和大圓滿絕對不同,因此並非僅稱為大手印,而是經教大手印。續部大手印相應於瑪哈瑜伽和阿努瑜伽,運用「譬喻智」來達到「真實智」。精要大手印則和大圓滿一樣,只是沒有「妥嘎」(Tögal,頓超)。了義大中觀和大圓滿「且卻」(Trekchö,立斷)的見地並無不同。
在大圓滿中,也有不同的層次。光是提到「大圓滿」而不指出我們所談及的特定層面,是不夠的。大圓滿並非一個單一的整體,而是具有四個分支。其一為外在的心部,猶如身體;其二為內在的界部,猶如心臟;其三為祕密的竅訣部,猶如心臟中的脈管;最後是極密的無上部,猶如心臟中的生命能量,生命力的純粹精要。這四個分支有何差異,不都全是大圓滿嗎?大圓滿的外層心部強調心的明性,內層界部強調心的空性,祕密竅訣部則強調兩者合一。極密的無上部教導一切──基、道、果,以及「且卻」和「妥嘎」。最後這個分支,就好像有個人具有完整的五根,任何都不缺。各個法乘最初都是要將真誠純正的見地放入修行,而非錯誤的見地。但若有人從較高層次的法乘來看,就顯得下層法乘的觀點都不完整;這個準則從下而上一直到第八法乘都適用。只要有人從大手印、大圓滿,或究竟中觀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見地看來都具有某些細微的妄念。
見地
關於見地,最重要的是要認識佛性。佛性的梵文是sugata-garbha(善逝藏),藏文為deshek nyingpo。我們必須明瞭,我們要運用於修行的就是這個見地。在九乘的前八乘──聲聞、緣覺和菩薩乘,事部、作部和瑜伽密,瑪哈瑜伽和阿努瑜伽,是以對佛性逐漸加深的觀念,當作牢記在心的參考依據。在此八乘中,佛性的見者或觀者被稱為觀照或細心覺察,以便時刻護守佛性,就好像牧場的人看管好自己的牛群那般。因此在這八乘當中,有兩件事情:佛性和持續的專注以便「不會忘記」。首先應要認出佛性,接下來是保任佛性而毫不散亂。若是觀照離於佛性而分心,修行者便與常人沒有不同。這就是前八乘的通用準則。
藏文對於佛性的譯詞deshek或nyingpo,前者指的是佛陀、一切如來和善逝、覺者,後者則為根本自性。正如牛乳的精要為牛油,諸佛的精要即是了悟的狀態。此佛性正是九乘各乘所要修持的,只是運用於修持的確切方式各不相同,這是因為越往上層,了解的精細程度就會越細微。
各乘從聲聞乘開始,各自有特定的見地、修持和行止。每個法乘都有相同的目的,就是要了解空性;每個法乘也都運用「止」(shamatha,奢摩他)和「觀」(vipashyana,毘婆奢那)的修持。在大乘層次,究竟的「止」和「觀」被稱為「能使如來歡喜的止觀」。儘管所用的名稱相同,在深度上卻遠勝於聲聞乘所修的「止」和「觀﹂。從聲聞乘開始,每個法乘都修持止觀,因此不要以為到了大圓滿的層次, 這兩個就會被忽略或捨棄。相反地,在阿底瑜伽(無上瑜伽)的層次,內在持定於「日巴」(rigpa,本覺)、覺性的無二狀態,即是止的層面;覺醒或能知的性質(覺性),即是觀的層面。我們本來的自性,也稱為覺性的智慧或能知的覺醒(awareness wisdom or cognizant wakefulness),是透過止觀來確認或認出。引述一段著名的陳述:「覺醒之心乃是止觀雙運。」
在此我們必須了解的準則是像這樣的說明:「相同的用詞,更勝一籌的意涵。」止和觀在究竟上並不可分,兩者自然而然地包含於阿底瑜伽中並被加以修持。超凡出世之止,在此意指著確認並安住於真正空性的本身。我們並非僅僅得到空性的觀念,而實際在親身直接體證上,我們確認空性並自然安住於該狀態。自然安住,就是不造作任何人為意想、僅安於空性覺受的真誠之止。觀則是與此狀態不偏不離。
根據一般止觀的方法,要先修止,而後求觀。修止,意指要能有心意靜止的狀態,且接著加以修習。求觀,意指要試著找出觀者是誰;試著指認保持安靜的是何者。兩種修持都顯然相當程度涉及了概念性的思考。唯有在精要大手印和大圓滿中, 才是無有戲論的空性。大圓滿首先就確認空性,毋須加以造作。強調要褪去覺性的外衣而使其赤裸,對空性不予任何方式的攀執。真實而純正的觀,就是心的空性和明性。
大圓滿的獨特所在,就是其見地全然離於各種觀念。這個見地稱為「果地之見」,意指毫無任何概念型態。大圓滿就如寺院的最高頂端,金色的頂嚴;在其之上,除了天空之外無他。大圓滿極密的無上部,就如寺院的金色頂嚴,是九乘的最高頂端。
當我們閱讀佛經,開頭都會有個梵文的經名,其後則是經書的內涵。經書的末尾會提到:「這部稱為某某名稱的佛經於此圓滿。」同樣地,在大圓滿中,一切輪迴與涅槃的現象,都在法身覺性單一界之廣空中完成或圓滿。大圓滿(藏文為dzogchen)總集了完成或圓滿,乃因為其中dzog 的意思是「達成」,換句話說已無進一步的事物;做完了、結束了、完成的。密續中有段話說:「圓滿如一──一切於覺心中圓滿。圓滿如二──輪迴和涅槃的所有現象皆圓滿。」
大圓滿法教可用下述譬喻來描述。當你爬山的時候,只能於同一時間看到某一方向。不過一旦你到達了一切山之王者的須彌山頂端,便能同時間看到四個方向;所有的地方你都看得到。這是因為較低層次法乘的所有特性都包含在較高的見地之中。從較高的見地來看,你將知道較低見地的缺失,就如你能從山頂之巔的有利位置看到所有事物一樣。這並不表示較低層次的法乘會認為他們自己特定的見地是不完整的;反而是各個確信自己特定的見地、修持、行止,以及果熟都是完美的。聲聞乘的十八個派別都相信他們的見地完美無缺,緣覺乘和其他法乘也都是如此。唯有當我們達到了山頂最高之處,才能清楚看見下方的所有事物。
此即為何佛陀會這樣描述九個法乘:「我的教法是一種漸進式的前進,從最開端開始一直到最高層的完美,就像從最低層延伸到最高層的樓梯之階梯,也像是個慢慢長大的新生嬰兒。」
選擇適合自己能力和根器的法教
人們具有不同的能力,傳統上將不同的人分為上、中、下三種根器,每種又各自分為上、中、下三類,因此共有九種不同根器的人們。傳授法教的方式也因這個分類而有所差異。對於上根器者(上士)的上、中、下三種根器來說,上士道為諸佛密意傳,也就是阿底瑜伽、阿努瑜伽、瑪哈瑜伽等三內密的法教。對於中根器者(中士)的上、中、下三種根器來說,中士道為事部、行部和瑜伽部等三外密。對於下根器者(下士)的上、中、下三種根器來說,下士道為聲聞、緣覺、菩薩等三法乘。
會這麼說,並非佛陀的法教在功德上有所不同,以致那些稱為「上上」者是佛陀法教中最好的,而「下下」者就是最糟的法教。佛陀一切的法教都是超凡的。法教有所不同,只是因為人們有所不同。適合於某種特定心智能力的法教,被稱為九乘當中的某一乘。並非佛陀給予了好的和壞的法教,而我們得找出其中好的法教;請明瞭,事情根本不是這樣的。這些法教乃為個別之人善巧地量身打造。佛陀以其全知,能夠曉得來找他的人需要什麼樣的法教才是合宜,並且也以合宜的方式給予法教。舉例來說,當你要找人搬運重物,你要給對方所能夠承受的包裝物品。如果你把小乘法教給予能夠了解無上瑜伽的人,就像把一個微小的包裹交給能用小指就拿得動的強壯大男人,這樣不夠。但若你把最高的金剛乘法教給了某個屬於聲聞乘的行者,就好比將大男人才能扛得動的沉重負擔堆在小孩的肩上,那個小孩就會摔跤,鐵定無法擔當。類似這樣,根據個人能力給予適當法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若是進一步分類,瑪哈瑜伽、阿努瑜伽、阿底瑜伽(三內密)乃為法身佛的三法輪。事部、行部和瑜伽部(三外密)乃為報身佛所宣說的三法輪。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則是化身佛所教導的三法輪。這些法教的傳續分別為諸佛密意傳、持明徵示傳,以及士夫口耳傳。然而所有這些,都是由覺者佛陀所給予的,也就是分別由法身佛、報身佛和化身佛所傳授。
這些法教都是為了要恰巧合宜於我們自己的習性和個別的能力。當我們覺得所受法教適合我們並且能夠理解,我們便能在修習當中快速進展。例如一位菩薩乘的行者領受大乘的法教,便能藉由這些法教而快速進展。
當人們剛開始接觸藏傳佛教,他們或許會認為:「這個宗教好奇怪啊!藏傳佛教充滿了一堆不同的本尊和儀式,有夠古怪!」在其他佛教傳統中長大的人們,其成長方式可能稍有限制。這些人由於並未以較寬廣的角度來完整受教,便相信自己所知的佛法才是佛法,其他地方的都不是。這種態度好似只有一隻手臂的人,或只有一腿或一頭,或只有人類身體的內臟,而其他部分都有缺失:他並非完整的人身。會有這種狹隘的觀點,就是因為未曾完整受教。若是偉大的學者或對佛教整體非常熟知的人,根本不會有這種問題。他將能看到法教的各適其所,而不會落入有限的思考:「大乘或金剛乘有什麼用!聲聞乘就足夠了。為什麼大家不修持聲聞乘就好,其他的法教根本無關緊要。」另外有人可能會想:「大乘法教才是真正的法教,其他的都不算數。」還有的人會說:「金剛乘才是正確的法教,那些像大乘或小乘等較低層次的法教,有什麼用呢?」所有這些態度都是毫無道理的。我們必須具有能夠發揮功能的完整人身。
打個比方,若要建造一座完美的寺院,首先必須要有堅固的基底和適當的基座, 以便讓寺院座落於此。這兩個要素就是小乘法教。沒有基座,便無法建造任何東西。其次,我們需要一個龐大而美好的結構;這就像大乘法教。最後,房子裡面應該不能空無一物,而應該要有佛陀身、口、意的精美代表物;這就好比金剛乘的法教。否則,就像是隨便一個世間的宮殿,一點真正的利益也沒有。類似這樣,我們應該把三大法教的層次組合並融合成修行的單一整體。我們的修行就能像一座完美的寺院,具有適當的基座、莊嚴的建築,並且內含佛陀身、口、意的代表物。這就是將小乘、大乘、金剛乘三層次法教融合為一的方法。
無論九乘的哪一乘,其見地的要點,除了空性之外,別無其他。每個法乘都是為了要讓行者體證事物的空性,並運用於修行中,且都維護了毫無瑕疵且正確無誤的法要。沒有人會想修行某個自身已知並不完美的道路,因此,各個法乘都主張特定的見地和運用的方法,且此方法乃是真誠且純正的。
依此,不同法乘的見地或取向也有所不同。小乘法教的見地,是從最基本的奢摩他──「止」修開始修持。這是經由不斷以觀照而專注於靜止來達成,最終的成果為成就全然平等捨之境,所有念頭盡皆止息的靜止狀態。
從小乘而上,關於心性真貌的觀念便越來越精細和細微。不過,在所有這些修持當中,要一直持守某個觀念,儘管這個觀念比起我們一般凡念中的觀念來說細微得多。
聲聞乘通常被稱為單一取向。實際上,在佛陀圓寂之後,聲聞乘行者分為十八派別。這十八分支其一,稱為說一切有部的派別在藏地以寺廟的傳承延續,另一者則傳至斯里蘭卡並在其他國家弘揚,其他十六派別都已銷聲匿跡。緣覺乘提及有兩種行者:如鸚鵡般的「群聚型」,以及如犀牛般的「獨身型」。
菩薩乘或稱大乘,具有各種不同的法門,例如三十七道品(三十七佛子行)。也有不同的哲學派別,例如唯識和中觀。這些又各自有許多的分支,以及許多詳盡的分類。大乘法教是藉心智的洞察力來奠定空性的見地,以便「離於四種極端和八種心意造作」。大乘行者主張,此心既非存在、亦非不存在,既非兩者皆是、亦非兩者皆非。最終的主張是,空性乃超越此四種極端(四邊)。這個見地依然留存一些對於空性概念的細微想法或固著。
大手印、大圓滿、中觀的見地之間有任何差異嗎?有時候會說,大手印為根基,中觀為道路,大圓滿則是果熟。這其中是否有差異,端看我們要討論的層面為何。請大家明瞭,中觀並非僅是中觀;你必須界定考量的層面。中觀有著不同的分派,自續派中觀、應成派中觀,以及了義大中觀。
大手印則分為經部大手印、續部大手印,以及精要大手印。經教大手印即是大乘所描述五道十地的次第修持。這和大圓滿絕對不同,因此並非僅稱為大手印,而是經教大手印。續部大手印相應於瑪哈瑜伽和阿努瑜伽,運用「譬喻智」來達到「真實智」。精要大手印則和大圓滿一樣,只是沒有「妥嘎」(Tögal,頓超)。了義大中觀和大圓滿「且卻」(Trekchö,立斷)的見地並無不同。
在大圓滿中,也有不同的層次。光是提到「大圓滿」而不指出我們所談及的特定層面,是不夠的。大圓滿並非一個單一的整體,而是具有四個分支。其一為外在的心部,猶如身體;其二為內在的界部,猶如心臟;其三為祕密的竅訣部,猶如心臟中的脈管;最後是極密的無上部,猶如心臟中的生命能量,生命力的純粹精要。這四個分支有何差異,不都全是大圓滿嗎?大圓滿的外層心部強調心的明性,內層界部強調心的空性,祕密竅訣部則強調兩者合一。極密的無上部教導一切──基、道、果,以及「且卻」和「妥嘎」。最後這個分支,就好像有個人具有完整的五根,任何都不缺。各個法乘最初都是要將真誠純正的見地放入修行,而非錯誤的見地。但若有人從較高層次的法乘來看,就顯得下層法乘的觀點都不完整;這個準則從下而上一直到第八法乘都適用。只要有人從大手印、大圓滿,或究竟中觀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見地看來都具有某些細微的妄念。
見地
關於見地,最重要的是要認識佛性。佛性的梵文是sugata-garbha(善逝藏),藏文為deshek nyingpo。我們必須明瞭,我們要運用於修行的就是這個見地。在九乘的前八乘──聲聞、緣覺和菩薩乘,事部、作部和瑜伽密,瑪哈瑜伽和阿努瑜伽,是以對佛性逐漸加深的觀念,當作牢記在心的參考依據。在此八乘中,佛性的見者或觀者被稱為觀照或細心覺察,以便時刻護守佛性,就好像牧場的人看管好自己的牛群那般。因此在這八乘當中,有兩件事情:佛性和持續的專注以便「不會忘記」。首先應要認出佛性,接下來是保任佛性而毫不散亂。若是觀照離於佛性而分心,修行者便與常人沒有不同。這就是前八乘的通用準則。
藏文對於佛性的譯詞deshek或nyingpo,前者指的是佛陀、一切如來和善逝、覺者,後者則為根本自性。正如牛乳的精要為牛油,諸佛的精要即是了悟的狀態。此佛性正是九乘各乘所要修持的,只是運用於修持的確切方式各不相同,這是因為越往上層,了解的精細程度就會越細微。
各乘從聲聞乘開始,各自有特定的見地、修持和行止。每個法乘都有相同的目的,就是要了解空性;每個法乘也都運用「止」(shamatha,奢摩他)和「觀」(vipashyana,毘婆奢那)的修持。在大乘層次,究竟的「止」和「觀」被稱為「能使如來歡喜的止觀」。儘管所用的名稱相同,在深度上卻遠勝於聲聞乘所修的「止」和「觀﹂。從聲聞乘開始,每個法乘都修持止觀,因此不要以為到了大圓滿的層次, 這兩個就會被忽略或捨棄。相反地,在阿底瑜伽(無上瑜伽)的層次,內在持定於「日巴」(rigpa,本覺)、覺性的無二狀態,即是止的層面;覺醒或能知的性質(覺性),即是觀的層面。我們本來的自性,也稱為覺性的智慧或能知的覺醒(awareness wisdom or cognizant wakefulness),是透過止觀來確認或認出。引述一段著名的陳述:「覺醒之心乃是止觀雙運。」
在此我們必須了解的準則是像這樣的說明:「相同的用詞,更勝一籌的意涵。」止和觀在究竟上並不可分,兩者自然而然地包含於阿底瑜伽中並被加以修持。超凡出世之止,在此意指著確認並安住於真正空性的本身。我們並非僅僅得到空性的觀念,而實際在親身直接體證上,我們確認空性並自然安住於該狀態。自然安住,就是不造作任何人為意想、僅安於空性覺受的真誠之止。觀則是與此狀態不偏不離。
根據一般止觀的方法,要先修止,而後求觀。修止,意指要能有心意靜止的狀態,且接著加以修習。求觀,意指要試著找出觀者是誰;試著指認保持安靜的是何者。兩種修持都顯然相當程度涉及了概念性的思考。唯有在精要大手印和大圓滿中, 才是無有戲論的空性。大圓滿首先就確認空性,毋須加以造作。強調要褪去覺性的外衣而使其赤裸,對空性不予任何方式的攀執。真實而純正的觀,就是心的空性和明性。
大圓滿的獨特所在,就是其見地全然離於各種觀念。這個見地稱為「果地之見」,意指毫無任何概念型態。大圓滿就如寺院的最高頂端,金色的頂嚴;在其之上,除了天空之外無他。大圓滿極密的無上部,就如寺院的金色頂嚴,是九乘的最高頂端。
當我們閱讀佛經,開頭都會有個梵文的經名,其後則是經書的內涵。經書的末尾會提到:「這部稱為某某名稱的佛經於此圓滿。」同樣地,在大圓滿中,一切輪迴與涅槃的現象,都在法身覺性單一界之廣空中完成或圓滿。大圓滿(藏文為dzogchen)總集了完成或圓滿,乃因為其中dzog 的意思是「達成」,換句話說已無進一步的事物;做完了、結束了、完成的。密續中有段話說:「圓滿如一──一切於覺心中圓滿。圓滿如二──輪迴和涅槃的所有現象皆圓滿。」
大圓滿法教可用下述譬喻來描述。當你爬山的時候,只能於同一時間看到某一方向。不過一旦你到達了一切山之王者的須彌山頂端,便能同時間看到四個方向;所有的地方你都看得到。這是因為較低層次法乘的所有特性都包含在較高的見地之中。從較高的見地來看,你將知道較低見地的缺失,就如你能從山頂之巔的有利位置看到所有事物一樣。這並不表示較低層次的法乘會認為他們自己特定的見地是不完整的;反而是各個確信自己特定的見地、修持、行止,以及果熟都是完美的。聲聞乘的十八個派別都相信他們的見地完美無缺,緣覺乘和其他法乘也都是如此。唯有當我們達到了山頂最高之處,才能清楚看見下方的所有事物。
此即為何佛陀會這樣描述九個法乘:「我的教法是一種漸進式的前進,從最開端開始一直到最高層的完美,就像從最低層延伸到最高層的樓梯之階梯,也像是個慢慢長大的新生嬰兒。」
選擇適合自己能力和根器的法教
人們具有不同的能力,傳統上將不同的人分為上、中、下三種根器,每種又各自分為上、中、下三類,因此共有九種不同根器的人們。傳授法教的方式也因這個分類而有所差異。對於上根器者(上士)的上、中、下三種根器來說,上士道為諸佛密意傳,也就是阿底瑜伽、阿努瑜伽、瑪哈瑜伽等三內密的法教。對於中根器者(中士)的上、中、下三種根器來說,中士道為事部、行部和瑜伽部等三外密。對於下根器者(下士)的上、中、下三種根器來說,下士道為聲聞、緣覺、菩薩等三法乘。
會這麼說,並非佛陀的法教在功德上有所不同,以致那些稱為「上上」者是佛陀法教中最好的,而「下下」者就是最糟的法教。佛陀一切的法教都是超凡的。法教有所不同,只是因為人們有所不同。適合於某種特定心智能力的法教,被稱為九乘當中的某一乘。並非佛陀給予了好的和壞的法教,而我們得找出其中好的法教;請明瞭,事情根本不是這樣的。這些法教乃為個別之人善巧地量身打造。佛陀以其全知,能夠曉得來找他的人需要什麼樣的法教才是合宜,並且也以合宜的方式給予法教。舉例來說,當你要找人搬運重物,你要給對方所能夠承受的包裝物品。如果你把小乘法教給予能夠了解無上瑜伽的人,就像把一個微小的包裹交給能用小指就拿得動的強壯大男人,這樣不夠。但若你把最高的金剛乘法教給了某個屬於聲聞乘的行者,就好比將大男人才能扛得動的沉重負擔堆在小孩的肩上,那個小孩就會摔跤,鐵定無法擔當。類似這樣,根據個人能力給予適當法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若是進一步分類,瑪哈瑜伽、阿努瑜伽、阿底瑜伽(三內密)乃為法身佛的三法輪。事部、行部和瑜伽部(三外密)乃為報身佛所宣說的三法輪。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則是化身佛所教導的三法輪。這些法教的傳續分別為諸佛密意傳、持明徵示傳,以及士夫口耳傳。然而所有這些,都是由覺者佛陀所給予的,也就是分別由法身佛、報身佛和化身佛所傳授。
這些法教都是為了要恰巧合宜於我們自己的習性和個別的能力。當我們覺得所受法教適合我們並且能夠理解,我們便能在修習當中快速進展。例如一位菩薩乘的行者領受大乘的法教,便能藉由這些法教而快速進展。
當人們剛開始接觸藏傳佛教,他們或許會認為:「這個宗教好奇怪啊!藏傳佛教充滿了一堆不同的本尊和儀式,有夠古怪!」在其他佛教傳統中長大的人們,其成長方式可能稍有限制。這些人由於並未以較寬廣的角度來完整受教,便相信自己所知的佛法才是佛法,其他地方的都不是。這種態度好似只有一隻手臂的人,或只有一腿或一頭,或只有人類身體的內臟,而其他部分都有缺失:他並非完整的人身。會有這種狹隘的觀點,就是因為未曾完整受教。若是偉大的學者或對佛教整體非常熟知的人,根本不會有這種問題。他將能看到法教的各適其所,而不會落入有限的思考:「大乘或金剛乘有什麼用!聲聞乘就足夠了。為什麼大家不修持聲聞乘就好,其他的法教根本無關緊要。」另外有人可能會想:「大乘法教才是真正的法教,其他的都不算數。」還有的人會說:「金剛乘才是正確的法教,那些像大乘或小乘等較低層次的法教,有什麼用呢?」所有這些態度都是毫無道理的。我們必須具有能夠發揮功能的完整人身。
打個比方,若要建造一座完美的寺院,首先必須要有堅固的基底和適當的基座, 以便讓寺院座落於此。這兩個要素就是小乘法教。沒有基座,便無法建造任何東西。其次,我們需要一個龐大而美好的結構;這就像大乘法教。最後,房子裡面應該不能空無一物,而應該要有佛陀身、口、意的精美代表物;這就好比金剛乘的法教。否則,就像是隨便一個世間的宮殿,一點真正的利益也沒有。類似這樣,我們應該把三大法教的層次組合並融合成修行的單一整體。我們的修行就能像一座完美的寺院,具有適當的基座、莊嚴的建築,並且內含佛陀身、口、意的代表物。這就是將小乘、大乘、金剛乘三層次法教融合為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