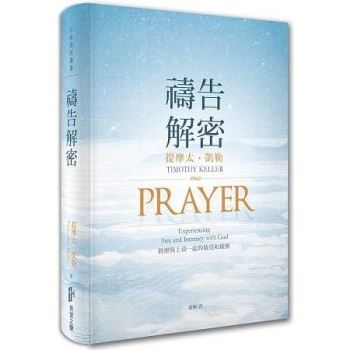「沒人能教我禱告嗎?」
當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 Connor)這位著名的南方作家,二十一歲在愛荷華州學習寫作的時候,她力圖深化她的禱告生活。她非如此不可。
1946 年她開始了手寫禱告日記,她在其中描寫了想成為一位偉大作家的掙扎。「我非常想透過自己所做的事,在世上獲得成功……我對自己的工作很灰心……『平庸』是一個很難用在自己身上的詞……但我非把它丟向自己不可……我甚至沒有一點可誇之處。我很愚蠢,像我所嘲笑的人那樣的愚蠢。」在任何有夢想的藝術家日記裡,都可以看見這一類的說法,但歐康納對這些感受做了一點與眾不同的事是――她為它們禱告。她在此選擇的是一條非常古老的道路,如舊約中的詩篇作者一樣,他們不只是認出、表達和宣洩自己的感受,而且還在上帝的同在中,對它們赤忱地加以處理。歐康納談及自己:
在藝術這方面的努力,我卻未想到您,也沒有感覺到所希望有的愛的激勵。親愛的上帝,我無法按我想要的方式愛祢。祢是我所看見的纖細月牙,我自己則是地球的陰影,使我無法看見月的全貌……我所害怕的,親愛的上帝,就是自己的陰影變得如此之大,以至於擋住了全月;我害怕用那本為虛無的陰影來判斷我自己。我不認識您,上帝,因為我自己擋住了路。
歐康納在這裡所意識到的,就是奧古斯丁在他自己的禱告日記《懺悔錄》(Confession)中所清楚看見的――即,美好的生活取決在重新排序我們的所愛。愛成功過於愛上帝和鄰舍,會使心剛硬,使我們越發不能感受和感知。而更諷刺的是,這也會使我們變成更糟的藝術家。由於歐康納是一位擁有卓越恩賜的作家,卻也可能因此而變得驕傲自戀,所以她唯一的盼望就在於:在禱告中,靈魂的重新轉向。「哦,上帝啊,請讓我頭腦清醒。潔淨它……請幫助我看到事物的深處,找到祢所在的地方。」
她反思了把禱告寫在日記裡的操練,她意識到關於形式的問題。「我很肯定這不太適合做為禱告的直接媒介,禱告甚至不能像這樣先想過――它是即時的。但這樣的形式對即時來說太慢了。」然後還有一個危險是,她寫下來的並不一定真的是禱告,反而是抒發。「我……想把這變成……某種對上帝的讚美。它可能更容易變成心理治療……其底層思想是自我的元素。」但她相信藉著日記,「我的屬靈生活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拋棄了某些青少年的習慣和慣性思維。『要意識到自己有多愚昧』不需要太費事,但是光就這件小事,也得花上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漸漸地明白那荒謬的自我。」歐康納學習到:禱告不只是在獨處中探索自己的主觀性,你是與另一位在一起,而那一位是獨一無二的,上帝是唯一一位你在祂面前會無所遁形的。在祂面前,你會無法避免地用一種新的、獨特的亮光來看待自己。所以,禱告所達致的自我認識,是用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得到的。
貫穿於歐康納整本日記中的,是一種簡單的渴望,渴望真正地學會禱告。她直覺地知道,無論自己在生活中需要做什麼、要成為什麼,禱告都是這一切的關鍵。她不滿足於過去機械式地遵守宗教規條。「我不是要否認我過去一生中所做過的傳統禱告,但我在做的時候並沒有感覺,我的注意力總是不集中;但是用這樣的方式,我每個時刻都有感受,當我想起並把它寫給祢的時候,我能感受到裡面有溫暖的愛在跳動。請不要讓心理學家對此所做的解釋,把它突然地冷卻。」
在一則日記的結尾,她直接就呼喊了:「沒人能教我禱告嗎?」今天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問同樣的問題。有一種必須禱告的感覺――我們不得不禱告。但是,該如何禱告呢?
當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 Connor)這位著名的南方作家,二十一歲在愛荷華州學習寫作的時候,她力圖深化她的禱告生活。她非如此不可。
1946 年她開始了手寫禱告日記,她在其中描寫了想成為一位偉大作家的掙扎。「我非常想透過自己所做的事,在世上獲得成功……我對自己的工作很灰心……『平庸』是一個很難用在自己身上的詞……但我非把它丟向自己不可……我甚至沒有一點可誇之處。我很愚蠢,像我所嘲笑的人那樣的愚蠢。」在任何有夢想的藝術家日記裡,都可以看見這一類的說法,但歐康納對這些感受做了一點與眾不同的事是――她為它們禱告。她在此選擇的是一條非常古老的道路,如舊約中的詩篇作者一樣,他們不只是認出、表達和宣洩自己的感受,而且還在上帝的同在中,對它們赤忱地加以處理。歐康納談及自己:
在藝術這方面的努力,我卻未想到您,也沒有感覺到所希望有的愛的激勵。親愛的上帝,我無法按我想要的方式愛祢。祢是我所看見的纖細月牙,我自己則是地球的陰影,使我無法看見月的全貌……我所害怕的,親愛的上帝,就是自己的陰影變得如此之大,以至於擋住了全月;我害怕用那本為虛無的陰影來判斷我自己。我不認識您,上帝,因為我自己擋住了路。
歐康納在這裡所意識到的,就是奧古斯丁在他自己的禱告日記《懺悔錄》(Confession)中所清楚看見的――即,美好的生活取決在重新排序我們的所愛。愛成功過於愛上帝和鄰舍,會使心剛硬,使我們越發不能感受和感知。而更諷刺的是,這也會使我們變成更糟的藝術家。由於歐康納是一位擁有卓越恩賜的作家,卻也可能因此而變得驕傲自戀,所以她唯一的盼望就在於:在禱告中,靈魂的重新轉向。「哦,上帝啊,請讓我頭腦清醒。潔淨它……請幫助我看到事物的深處,找到祢所在的地方。」
她反思了把禱告寫在日記裡的操練,她意識到關於形式的問題。「我很肯定這不太適合做為禱告的直接媒介,禱告甚至不能像這樣先想過――它是即時的。但這樣的形式對即時來說太慢了。」然後還有一個危險是,她寫下來的並不一定真的是禱告,反而是抒發。「我……想把這變成……某種對上帝的讚美。它可能更容易變成心理治療……其底層思想是自我的元素。」但她相信藉著日記,「我的屬靈生活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拋棄了某些青少年的習慣和慣性思維。『要意識到自己有多愚昧』不需要太費事,但是光就這件小事,也得花上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漸漸地明白那荒謬的自我。」歐康納學習到:禱告不只是在獨處中探索自己的主觀性,你是與另一位在一起,而那一位是獨一無二的,上帝是唯一一位你在祂面前會無所遁形的。在祂面前,你會無法避免地用一種新的、獨特的亮光來看待自己。所以,禱告所達致的自我認識,是用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得到的。
貫穿於歐康納整本日記中的,是一種簡單的渴望,渴望真正地學會禱告。她直覺地知道,無論自己在生活中需要做什麼、要成為什麼,禱告都是這一切的關鍵。她不滿足於過去機械式地遵守宗教規條。「我不是要否認我過去一生中所做過的傳統禱告,但我在做的時候並沒有感覺,我的注意力總是不集中;但是用這樣的方式,我每個時刻都有感受,當我想起並把它寫給祢的時候,我能感受到裡面有溫暖的愛在跳動。請不要讓心理學家對此所做的解釋,把它突然地冷卻。」
在一則日記的結尾,她直接就呼喊了:「沒人能教我禱告嗎?」今天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問同樣的問題。有一種必須禱告的感覺――我們不得不禱告。但是,該如何禱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