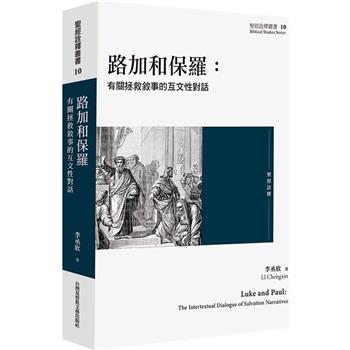第三章 保羅的「拯救敘事」圖景
第一節 保羅拯救敘事的結構
我們將以《羅馬書》為線索,分階段討論保羅思想所呈現的以基督事件為中心的敘事結構,並在此敘事層面上與路加的相關敘事加以比對。在進入《羅馬書》文本分析之前,我們必須首先釐清這個敘事結構的兩個關鍵的整體面貌問題:(a) 在保羅這裡十分重要的「亞當—基督」概念的評估直接影響這人們對其思想圖景的認識,時間性和超越性的矛盾必須加以解決。(b) 其次,保羅提出的模糊時間概念「從亞當到摩西」(羅 5:14)該如何理解?是否與我們在上文所釐定的敘事結構分期衝突呢?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緊密聯繫的。
(一)「亞當—基督」預像
第一階段就是上帝通過摩西向以色列人頒布律法之前的時期,主要涉及亞當的「失樂園」敘事及其與耶穌基督的關係,指涉了《創世記》的部分敘事。正如上文提及,傾向於運用敘事進路解讀保羅思想世界的學者普遍認為保羅在書信中對於「亞當—基督」的「預像」指涉以及由此引發的進一步闡述,是我們討論這一時期的文本基礎。這種所謂「預像」的意涵究竟為何?亞當和基督是一種超越歷史的關係,還是在歷史時空中的關係?回答這些問題成為詢問所謂「從亞當到摩西」內涵的基礎。
對此,N. T. Wright 首先強調從歷史傳統的角度看待「亞當」概念本身所具有的集體性以及它和「以色列」概念之間的關係。他指出在兩約時期(甚至於後來的拉比時期)猶太人關於亞當的神學論述普遍並不像後來基督教神學傳統那樣指涉人類、甚至宇宙整體,而是集中在以色列身上,強調以色列就是上帝拯救計劃的工具,就是一些具有終末傾向的文獻中所論及的「第二亞當」。因此這第二位亞當並非指作為個人的彌賽亞,乃指終末的上帝子民 (eschatological people of God)。在公元前後數百年的危機時刻中,部分猶太人堅信以色列就是亞當的化身,以色列在人類中繼承了上帝在創世過程中賦予亞當的特殊地位,始終位於整個歷史計劃的中心位置。在這種世界圖景中,整個受造世界本以亞當為中心,以色列作為亞當的承繼者處於整個世界的中心,而律法則成為以色列作為上帝子民之存在的中心;外邦異教徒作為以色列的敵人和臣民,則只處於這個同心圓圈的外圍邊緣。這個同心圓圖景支撐著以色列國族復興這一終末期盼。Wright 認為:首先,保羅相信上帝已經把以色列在其拯救計劃中的任務轉移到拿撒勒人耶穌身上,耶穌作為「受膏的王」代表了整個以色列,他一個人成為終末的第二亞當;其次,耶穌及其聚集起來的新群體是天主在其拯救計劃中要重建的真人類 (true humanity),而非那些失去以色列名分的猶太人。由此,保羅的亞當基督論 (Adam-christology) 事實上是以色列基督論 (Israel-christology),詮釋了耶穌被稱為彌賽亞(基督)在保羅心目中的具體歷史含義:耶穌基督以其順服至死扭轉了亞當的悖逆,又以其復活、被舉揚克服了死亡後果,戰勝罪惡權勢,完成了以色列依靠律法所無法完成的事情,滿全了以色列的救恩角色。「亞當—基督」概念被保羅擴展成了「亞當—以色列—基督」三重關係,覆蓋世界歷史的三個時期,具有奠基性意義。
與之相反,Edward Adam 以基督論為中心探討「亞當—基督」概念。他一方面承認可以從敘事角度來看待保羅基督論中對亞當的指涉,但他反對將敘事詮釋進路推及至認為保羅思想具有敘事結構或所謂「救恩史」的觀點。他認為:從內容上而論,保羅的思想氛圍是終末臨近的急切期盼,相信基督的十字架以及「主再來」的終末事件是上帝對歷史的強力介入,這種非連續性才是救恩的本質特徵。其次,保羅書信文本中的敘事結構並非是逐步邁向勝利和成全的漸進歷史發展,而存在以十字架為分水嶺的大轉折,這種轉折超越時空範疇。因此,拯救敘事是出現在保羅書信中的個別文本現象 (textual phenomenon),其產生是源於和《希伯來聖經》敘事的「互文反映」 (intertextual allusions)。值得一提的是,Adam 聯繫加6:15對復活的討論,認為保羅對《創世記》敘事的指涉為他以「新創造」來定義拯救的理念定下基調,人類的救贖是整個宇宙救
贖的一部分。
依照Adam 的立場和整體思路,對「前律法時期」性質和地位的詢問顯然並沒有意義,由於他明確拒絕「救恩史」觀念,進而認為亞當的墮落作為一個事件的意義並非在上帝與人類關係史的時間線中,而是在與基督事件這一中心主題的邏輯連結中,「亞當—基督」預表的意義即在於此。與此立場相近的是Francis Watson,他將林前15:21-22 納入考慮,並認為出現在保羅書信文本中的亞當墮落和基督事件並非處於同一時空層面,亞當只是一個寓意形象,基督不是「第二亞當」。
(二)立體的思想世界圖景
可見,學者在接納保羅書信文本具有敘事結構的前提下,對此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進路,Wright 等人認為保羅思想世界本身具備連續敘事,這一敘事支配了保羅的神學論述;而Adam 和Watson 等人則認為保羅思想中的基督事件並非連續敘事中的其中一個環節,而是傳統敘事的中斷和顛覆,和《創世記》敘事不在一個層面上,因而保羅對亞當事件的指涉不能說明其有一個連續的敘事思想世界。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認為他們的研究和詮釋有一共識:保羅將《創世記》敘事中的亞當事件視為基督事件的處境性前提,這個處境就是人類因悖逆上帝而陷於罪惡和死亡並亟待拯救(羅7:7-25),以色列的敘事和後來的基督事件、基督徒群體敘事等,都套在此前提下論說。
因此,耶穌順服至死(羅5:12-21)以及其復活(林前15:12-28, 加 6:15)這個基督事件主線成為一切基督論闡述的敘事性前提,而這個敘事必須在亞當事件或整個《創世記》敘事的背景中看待,無論兩者是否處於同一思想層面。針對兩派學者對亞當事件與基督事件之關係的不同解讀,
筆者認為這代表了兩種看待保羅思想世界的角度。Adam 和Watson 等人代表的是以神學主題間之邏輯連接為關鍵的網狀思想結構,而Hays、Wright 和Ben 等人代表了以歷史時序為軸心的線性思想結構。前者呈現不同神學主題在保羅書寫信件以及其信仰反思當下的相互關係,這種關係是超越時空的;後者揭示不同神學主題是一系列拯救事件的反映,這些事件在相互銜接的歷史時序中有明確的因果關係,它們扎根於普世人類的歷史世界而非僅是抽象思辨。要更公允地看待保羅的思想世界,一方面要求我們將兩種視角結合起來,以一種立體方式呈現保羅的思想世界。
如果我們將其比喻成一座塔,縱向的角度讓我們看到一個從下到上的層層遞進的層級構造,這是線性的歷史時序,而每一層的房間(思想主題)安排和結構都有所不同;橫向的角度讓我們透視、貫通這個層級結構,看到每一層不同的「房間」之間是如何以樓梯相互連接起來的;而整個塔的中軸棟樑則是上帝的拯救意志(義)以及在其主導下的基督
事件,這貫通了所有的層級和「房間」,處於底層的創世和亞當墮落事件具有非凡意義,「亞當—基督」概念超越單純的預表或寓意的意義。這肯定了在保羅思想的立體結構中歷史時序的優先性,各神學主題的邏輯連接依託於具體的拯救事件及其歷史時序,層層遞進。值得留意的是,羅4:10 關於亞伯拉罕敘事的反問,讓我們肯定相關拯救事件的歷史時序對保羅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簡言之,以歷史時序為基礎的立體視角是我們在這裡以及往後各章節論及保羅思想以及其與《路加福音》、《使
徒行傳》之間關係的基本視野,也是當下討論「從亞當到摩西」含義的前提。
(三)「從亞當到摩西」作為拯救敘事單元?
我們不得不承認,學者們對於保羅所言的「從亞當到摩西」(羅 5:14)這個時間段的具體意涵和性質並沒有共識,對這部分文本的爭論焦點落在律法與罪和死亡的關係上,仿佛關於「從亞當到摩西」的整個討論只是關於律法之於拯救的意義之探討的一個方面而已。無可否認,關於「律法」的意義問題是保羅在整個羅2:17-7:25 中都會涉及的,但是這部分討論的作用實際上是從人類的罪惡處境這一反面角度論證福音的普世性意涵(猶太人和外邦人需要同樣的救恩),其基石仍是羅5:12-21 所呈現的亞當事件。另一方面,關於「亞當—基督」的討論也在《哥林多前書》中出現,其中林前15:17 通過描述基督事件(特指復活)缺席的假設性情況「你們就仍在你們的眾罪裡」(?τι ?στ? ?ν τα?? ?μαρτ?αι? ?μ?ν) 指向了人類的罪惡處境。可見,「亞當—基督」概念在保羅的思想世界中對人類罪惡處境的闡述,具有覆蓋全部時間(從亞當到基督、甚至直到終末)和空間(「不論猶太人還是希臘人」)的普世性意涵,對比之下,「從亞當到摩西」的分期在時間上則具有相對性。它僅僅是保羅為
了方便論述而對整體拯救敘事世界的暫時分野嗎?是否具有更深刻的意涵?
筆者認為,保羅在羅4:1-25 以及加3:6-29 中對《創世記》中亞伯拉罕被上帝呼召事件的指涉,就是對福音普世性意涵的正面確證,使其與亞當事件一起成為「從亞當到摩西」這一「前律法時期」的兩個支點。對保羅來說,亞伯拉罕事件處於人類歷史中的「前律法時期」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與「亞當—基督」概念的普世性意涵緊密相連,原因如下:
保羅通過援引創15:6 在兩處不同的文本處境中指涉亞伯拉罕事件都指向同一主題:「信」和「律法」在「為義」(justification) 中的辯證關係(羅4:3, 9;加 3:6)6 ,全人類都因著對這「信」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承襲其祝福和恩許,通過解構割禮和律法的權威(羅4:10-12;加3:17-20),清晰地呈現其超越猶太人—外邦人二元對立的普世性意涵(羅4:17;加3:28-29)。具體而言,首先,亞伯拉罕事件標示了以色列作為上帝選民的開端,而通過被授予割禮的標記,他在猶太人的傳統敘事中是猶太人—外邦人二元對立的先驅。但保羅卻通過援引創17:5 將承受世界的應許凌駕於割禮和後來的摩西律法,來消解這種二元對立,進而顛覆了猶太人一直以來對亞伯拉罕事件的解讀。這點十分重要!雖然以色列人從其先祖亞伯拉罕開始成為上帝在整個拯救計劃中的特殊族類,但同時也承擔了將救恩擴展到普世的特殊使命,其作為上帝選民的特殊身分是建立在這特殊使命之上的,亞伯拉罕是普世一切藉著「信」而承襲應許之人的原型 (prototype),他與亞當和後來的基督分別有著一正一反的根本聯繫。可見,在保羅思想中「從亞當到摩西」的這段時期,以色列作為選民從人類中被上帝通過對其先祖的呼召區別出來,但在亞當所造成的共同罪惡處境下,他們在救恩上卻並無特權,反而負擔了額外的使命和任務,律法僅是這個使命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種論述中,摩西律法原先在「同心圓」思想圖景中的核心地位被相對化了。保羅藉此將「應許」放在以色列人歷史身分的中心,這既是希望也是普世性的
使命。
綜上,在「從亞當到摩西」這一時期中,「亞當—基督」這個概念所建立起拯救敘事的普世框架,包含了「亞伯拉罕—以色列」這一國族概念的結構,以「應許」作為中心,呈現「亞當—亞伯拉罕—(應許)—以色列—基督」的形式。這是筆者基於羅5:14 對Wright「亞當—以色列—基督」概念的進一步發展。換言之,亞當事件並非保羅之拯救敘事第一階段的唯一內容。亞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的事件是與亞當事件一起成為「從亞當到摩西」這一「前律法時期」的兩個支點。Joseph A. Fitzmyer (1920-2016) 提醒我們留意在羅5:20 和加3:19 中述及律法被「添加」標誌救恩歷史的另一個時代,在這時代中人們在亞當事件造成的普世性罪惡處境基礎上所犯的個人罪行才被視為過犯並記錄在案。因此,James Dunn 等學者稱為「以色列時代」的拯救敘事第二階段似乎並不是於以色列先祖亞伯拉罕被選召時開始的,而是以摩西領受律法和盟約開始的。據此,我們或許能夠解釋為何這段時期的敘事幾乎完全在羅1-8 章中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