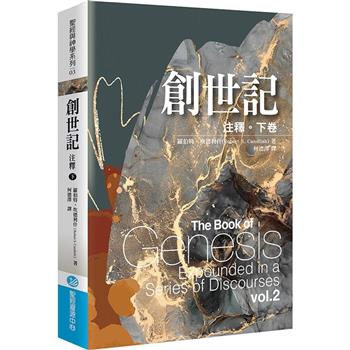關於以掃對他兄弟雅各的心態,上帝所作的見證―以掃充滿苦毒的仇恨並血腥的報復企圖,是對他自身以前的行為最真實的注釋。「以掃因他父親給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裡說:『為我父親居喪的日子近了,到那時候,我要殺我的兄弟雅各。』」(創廿七41)當然,如果以掃確實尋求過真心的悔改,或因真心的悔改而生的哀傷所帶出的任何屬靈的福氣,他就會在上帝面前為自己曾犯過的罪而謙卑,且無論上帝所指定的具體條件為何,都渴望能夠在聖約的祝福上有份。對於自己的弟弟,就不會一直忿忿不平,而是從一開始就應該懷著被神諭所喚醒的情感;尤其是在那位曾經過於偏心的父親也默許的情況下,更應如此。
當然,以掃對雅各懷有這麼致命的仇恨,並且蓄意制定一個兄弟相殘的計畫,這無疑是對以掃那至終「得不著門路」的「悔改」之真實性,提出了確鑿的反面證據。但正如在其他例子中所表明的,這裡也是如此:某些逼迫往往被上帝更有智慧地加以利用而達成善果,從而使教會更加明確地與周邊拜偶像的世界分離。以掃的暴力威脅,成為保護雅各的手段,使他免於和以掃一樣,陷入與不敬虔之人結盟的不幸之中。首先,這使雅各與上帝的交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親近、更隱秘與互信;他被嚴密地包裹在恩典與聖約的關係之中。之後,也使雅各有機會,能建立比以掃娶赫人女子為妻那種情況更理想的婚姻關係(廿六34-35,廿七46)。
雅各從他父親的屋簷下離開,乃是出於他母親的主意。有一個雙重的動機驅動著利百加;她的行為,部分是出於天生情感的推動,部分是因著宗教信仰或屬靈心的引導。她想要拯救雅各免於成為他兄弟怒氣下的犧牲品;同時,她也想要拯救他免於落入類似於他兄弟的罪中。這兩種動機絕不是彼此毫不相容的。讓利百加極為害怕的是:如果雅各死於以掃之手,她必定要經歷雙重的喪子之痛,因為以掃作為殺人犯也將死於報血仇者之手,或者死於上帝親自地「追討流人血之罪」,所以她說:「為什麼一日喪你們二人呢?」(42-45 節)但是除此之外,她還意
識到這個蒙揀選的家庭必須保持聖潔,不應該被異教之風混合玷污。為著這個必要性,她覺得是時候為雅各找一個妻子,好成為所應許之後裔的母親;但不是從當地的女子中尋找,而是從遠方的親戚當中去找,正如自己當初顯然是在他們當中被耶和華選定,而成為以撒的配偶。於是她向丈夫提議說:「我因這赫人的女子連性命都厭煩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為妻,像這些一樣,我活著還有什麼益處呢?」(46 節)因此以撒囑咐小兒子:「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為妻。你起身往巴旦亞蘭去,到你外祖彼土利家裡,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兒中娶一女為妻。」(廿八1、2)有了這項囑咐,並在重新領受父親的祝福之後,雅各就被打發出去了(3-5 節)。
以掃被父母話語當中隱含的責備所刺痛,徒勞地試圖矯正自己的錯誤,結果卻因與被離棄的以實瑪利人建立婚姻聯繫,而使自己罪上加罪。「以掃就曉得他父親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實瑪利那裡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瑪哈拉為妻。她是亞伯拉罕兒子以實瑪利的女兒,尼拜約的妹子。」(8、9 節)而在雅各這邊,在更好的吉兆之下,帶著年邁父親的祝福,以及上帝的引領,雅各開始了孤獨的旅程。當然,他是帶著信心而出發的。
的確,他從家裡離開、獨自踏上天路之旅,當時這些外在的境遇並不能表明或證明他在天上有高階的位份。他是在哥哥的怒氣下倉皇出逃的,獨自一人、且無人隨從照料。當夜幕低垂時,他發現自己沒有居所可以用來遮蔽(連一個枕頭的地方也沒有,附近也沒有可以住的地方),沒有遇到熱情好客的主人準備開門迎客、用鋪好的長榻供客人休息。在穹蒼寬闊的屋簷下,在腳下光禿禿的大地上,雅各只好強顏歡笑地躺臥;遼闊的天空權充他的房間,粗糙的石頭就是他的枕頭之處(10、11 節)。但是那個夜晚註定將成為他人生的一個決定性時刻。
雅各「在伯特利遇見耶和華」(何十二4)。現在是第一次(或者說,至少是第一次明確地),他被主耶和華逮住了,抓個正著。他躺臥在堅硬的、沒有窗簾的長榻上睡著了;但是醒來時卻要成為一個新人,具有新的生命與力量,以及上帝的恩寵和保護的嶄新確據。就是在這裡,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根據我們從歷史的蛛絲馬跡中所能得知的,通過一種不是出於人,而是出於上帝的儀式,雅各正式成為亞伯拉罕之約的繼承人,並且承受了亞伯拉罕家族中那份長子名分之下的祝福(創廿八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