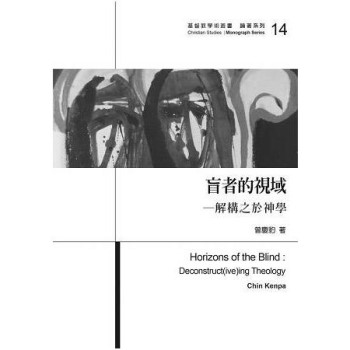第二章:彌賽亞性
一、追尋彌賽亞的足跡
在《災異書寫》(The Writing of Disaster)中,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喚起了一種「猶太彌賽亞精神」的記憶:
如果彌賽亞出現在羅馬城門前那些乞丐和痳瘋病人之中,我們可能會認為他的這種身份正是遮掩了他的來臨,然而,恰恰是這樣他反被人們認出來了。某個人窮追不捨、沒完沒了地追問:「你什麼時候來?」他就在那裡,但沒有來。彌賽亞就在那裡。與他一道,這個人的呼喚也一定會永遠迴響:「到來,到來!」他的出場是沒有什麼擔保的。無論未來和過去(曾經有人也說,彌賽亞已經來過了),他的到來與任何一種在場都不對應……對於「你的到來發生在何時?」這麼一個問題,彌賽亞的回答只能是:「就在今天!」這麼一個回答已經非常令人震驚了:「是的,就在今天!就在現在,永遠現在。」雖然如一種等待的義務一樣,可是卻沒有等待。何時是現在?什麼時候是這個不屬於日常時間……不但不維持日常時間反而要摧毀日常時間的現在?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友愛的政治》(Politics of Friendship)引用過上述這段故事,他毫不違言地承認他從布朗肖的著作中學到了很多關於彌賽亞的東西,這類彌賽亞觀念帶有多少很直接的某種家族特徵有待追究,德希達晚期著作,可謂處處充斥著濃濃的「彌賽亞」氣息。尤其當「哀悼」、「灰燼」、「幽靈書寫」或「解構即正義」的背後,明顯地舞動著一種近似於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虛弱的彌賽亞力量」(weak messianic force)時,加上德希達即不承認、也不否認他與猶太教的關係,正是這種「彌賽亞」思想的結果,這一位「年青的猶太聖者」(Young Jewish Saint)舉手投足都像是Susan A. Handelman所形容的「(猶太教)異端」,或者,他很可能是一種早已遺忘的拉比傳統,一個不曾存在過的《聖經》傳統。在《災異的書寫》中的彌賽亞主義根本不是一般人觀念中的那種彌賽亞主義;它被去語境化,被從歷史或時間的界限之中撕裂開來,也被剝去了一切語言的味道。在討論它之後不久,布朗肖又將彌賽亞描述成「否定性的偏愛,那種抹去了偏愛、也在其中被抹去了的否定:那並不位於要去施為(to do)的事情之列者的中立性——克制,那種不可視作固執、也並不以少數幾個詞來勝過固執的柔和性(gentleness)。」它非常單薄,但卻具有號召力。布朗肖似乎在暗示,如果某人可以被視作一位彌賽亞的話,那是因為他沒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我們進行」期盼的東西,沒有「提供」任何我們並不具有的東西。他教給我們的可能僅僅只是這一點:我們不需要期盼,我們不必如此操心於要去施為的事物,「操心」於作出改變,或者在時間或歷史中進行推進。
布朗肖的彌賽亞並未被捲入要去施為的事情之中,卻以某種特定的方式採取了行動:他帶來了安慰。布朗肖稱他的彌賽亞主義是猶太教的,並且將它與基督教觀念中的某些因素進行了對比,尤其是這一點:基督教的彌賽亞是神聖的,並且是單一的、可識別的存在者。他實質上暗示,通過將彌賽亞神聖化,基督徒壓縮了彌賽亞這個角色,將一切安慰的責任都置於一個場景之下了。布朗肖的彌賽亞「是一個安慰者,公正者之中的最公正者,但卻不能確定他是不是一個人(person)——某個特定的人。當某個評論者說『彌賽亞可能就是我』時,他並不是在提升他自己。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彌賽亞——必定是他,又不是他。」也就是說,那個提供安慰的人就是「我」——是我們中的每一個人。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認識到了窘境,數著眼淚。簡言之,布朗肖的彌賽亞主義並不僅僅被去時間化了(detemporalized),也被去地方化了(delocalized);而且它還作為人類的責任出現。布朗肖提出,期盼一位時間中的、有方所的彌賽亞,就至少是解除了某些進行安慰的義務,因此就是向責任的廢黜靠近。納粹時代的學界曾經別有用心地針對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思想爭論過:「精神分析學是否為一門猶太科學?」;面對於德希達晚期的「宗教轉向」,他的學界友人認真地問到:「解構是否為一門猶太科學?」,尤其當他相當程度地著迷於「彌賽亞性」(messianic)的思想時,對於「到來」、「要來的將來」、「將來臨之物」、「能夠回來的東西」的解構式說詞,成了人們懷疑這位「猶太之子」是否也接受了思想的割禮,流露出了他孩提時的「創傷記憶」。
像奧古斯丁、割禮、懺悔、保羅、祈禱、塔木德、猶太男子晨禱披巾、觸摸耶穌、血,巴別塔、以撒(和/或以實瑪利)的獻祭、祁克果(Kierkegaard),彌賽亞主義、耶路撒冷、神秘主義、索倫姆(Gershom Scholem)、卡巴拉、宗教暴力、基督教普世運動與宗教寬容的界限、獻祭、女人的獻祭和獻祭的核心、倫理、責任和寬恕、終末、約翰啟示錄、上帝之名,等明確的「宗教語詞」,成了晚期德希達大肆談論的關鍵字。這當然已經構成了明顯的「宗教轉向」。
相較於羅森茨維格(Rosenzweig)、布伯(Buber)、列維納斯(Levinas)等人,德希達思想就其整體性而言能否稱為「猶太的」還是一個問題。但在描繪一個「猶太人德希達」的輪廓時,我們首先必須承認,德希達在任何意向性的意義上並非一位「猶太哲學家」(僅就其種族血統而言並不必然決定其哲學形貌);不如說,德希達的思想是由於一種關於效應(而非目的)的潛在原因而成為「猶太的」。正如Gideon Ofrat在The Jewish Derrida選擇了一種佛洛伊德式的視角,形容著「某種猶太文化的暗流中的旋渦,存在於德希達的意識與哲學中」。
一、追尋彌賽亞的足跡
在《災異書寫》(The Writing of Disaster)中,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喚起了一種「猶太彌賽亞精神」的記憶:
如果彌賽亞出現在羅馬城門前那些乞丐和痳瘋病人之中,我們可能會認為他的這種身份正是遮掩了他的來臨,然而,恰恰是這樣他反被人們認出來了。某個人窮追不捨、沒完沒了地追問:「你什麼時候來?」他就在那裡,但沒有來。彌賽亞就在那裡。與他一道,這個人的呼喚也一定會永遠迴響:「到來,到來!」他的出場是沒有什麼擔保的。無論未來和過去(曾經有人也說,彌賽亞已經來過了),他的到來與任何一種在場都不對應……對於「你的到來發生在何時?」這麼一個問題,彌賽亞的回答只能是:「就在今天!」這麼一個回答已經非常令人震驚了:「是的,就在今天!就在現在,永遠現在。」雖然如一種等待的義務一樣,可是卻沒有等待。何時是現在?什麼時候是這個不屬於日常時間……不但不維持日常時間反而要摧毀日常時間的現在?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友愛的政治》(Politics of Friendship)引用過上述這段故事,他毫不違言地承認他從布朗肖的著作中學到了很多關於彌賽亞的東西,這類彌賽亞觀念帶有多少很直接的某種家族特徵有待追究,德希達晚期著作,可謂處處充斥著濃濃的「彌賽亞」氣息。尤其當「哀悼」、「灰燼」、「幽靈書寫」或「解構即正義」的背後,明顯地舞動著一種近似於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虛弱的彌賽亞力量」(weak messianic force)時,加上德希達即不承認、也不否認他與猶太教的關係,正是這種「彌賽亞」思想的結果,這一位「年青的猶太聖者」(Young Jewish Saint)舉手投足都像是Susan A. Handelman所形容的「(猶太教)異端」,或者,他很可能是一種早已遺忘的拉比傳統,一個不曾存在過的《聖經》傳統。在《災異的書寫》中的彌賽亞主義根本不是一般人觀念中的那種彌賽亞主義;它被去語境化,被從歷史或時間的界限之中撕裂開來,也被剝去了一切語言的味道。在討論它之後不久,布朗肖又將彌賽亞描述成「否定性的偏愛,那種抹去了偏愛、也在其中被抹去了的否定:那並不位於要去施為(to do)的事情之列者的中立性——克制,那種不可視作固執、也並不以少數幾個詞來勝過固執的柔和性(gentleness)。」它非常單薄,但卻具有號召力。布朗肖似乎在暗示,如果某人可以被視作一位彌賽亞的話,那是因為他沒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我們進行」期盼的東西,沒有「提供」任何我們並不具有的東西。他教給我們的可能僅僅只是這一點:我們不需要期盼,我們不必如此操心於要去施為的事物,「操心」於作出改變,或者在時間或歷史中進行推進。
布朗肖的彌賽亞並未被捲入要去施為的事情之中,卻以某種特定的方式採取了行動:他帶來了安慰。布朗肖稱他的彌賽亞主義是猶太教的,並且將它與基督教觀念中的某些因素進行了對比,尤其是這一點:基督教的彌賽亞是神聖的,並且是單一的、可識別的存在者。他實質上暗示,通過將彌賽亞神聖化,基督徒壓縮了彌賽亞這個角色,將一切安慰的責任都置於一個場景之下了。布朗肖的彌賽亞「是一個安慰者,公正者之中的最公正者,但卻不能確定他是不是一個人(person)——某個特定的人。當某個評論者說『彌賽亞可能就是我』時,他並不是在提升他自己。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彌賽亞——必定是他,又不是他。」也就是說,那個提供安慰的人就是「我」——是我們中的每一個人。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認識到了窘境,數著眼淚。簡言之,布朗肖的彌賽亞主義並不僅僅被去時間化了(detemporalized),也被去地方化了(delocalized);而且它還作為人類的責任出現。布朗肖提出,期盼一位時間中的、有方所的彌賽亞,就至少是解除了某些進行安慰的義務,因此就是向責任的廢黜靠近。納粹時代的學界曾經別有用心地針對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思想爭論過:「精神分析學是否為一門猶太科學?」;面對於德希達晚期的「宗教轉向」,他的學界友人認真地問到:「解構是否為一門猶太科學?」,尤其當他相當程度地著迷於「彌賽亞性」(messianic)的思想時,對於「到來」、「要來的將來」、「將來臨之物」、「能夠回來的東西」的解構式說詞,成了人們懷疑這位「猶太之子」是否也接受了思想的割禮,流露出了他孩提時的「創傷記憶」。
像奧古斯丁、割禮、懺悔、保羅、祈禱、塔木德、猶太男子晨禱披巾、觸摸耶穌、血,巴別塔、以撒(和/或以實瑪利)的獻祭、祁克果(Kierkegaard),彌賽亞主義、耶路撒冷、神秘主義、索倫姆(Gershom Scholem)、卡巴拉、宗教暴力、基督教普世運動與宗教寬容的界限、獻祭、女人的獻祭和獻祭的核心、倫理、責任和寬恕、終末、約翰啟示錄、上帝之名,等明確的「宗教語詞」,成了晚期德希達大肆談論的關鍵字。這當然已經構成了明顯的「宗教轉向」。
相較於羅森茨維格(Rosenzweig)、布伯(Buber)、列維納斯(Levinas)等人,德希達思想就其整體性而言能否稱為「猶太的」還是一個問題。但在描繪一個「猶太人德希達」的輪廓時,我們首先必須承認,德希達在任何意向性的意義上並非一位「猶太哲學家」(僅就其種族血統而言並不必然決定其哲學形貌);不如說,德希達的思想是由於一種關於效應(而非目的)的潛在原因而成為「猶太的」。正如Gideon Ofrat在The Jewish Derrida選擇了一種佛洛伊德式的視角,形容著「某種猶太文化的暗流中的旋渦,存在於德希達的意識與哲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