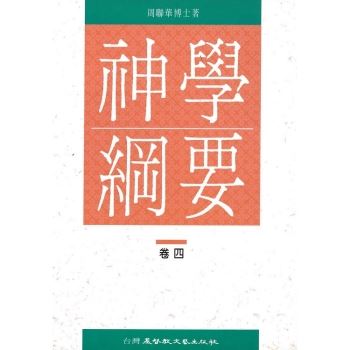第一篇 人 的 起 源
第一章 中國傳說
一個古老民族生存在它的自然環境中,他們在日常生活和大自然的接觸中一定會發生許多關係,這些關係逐漸會「人格化」,因為「人」終究是他們最熟悉的領域。這些自然界的現象及關係再加以宗教化,而初民的想像力又是非常豐富的;這些敘述就成了神話。
壹 神話的重要
在一般國人的心目中,也許是受了傳統儒家的影響,始終沒有給神話正確的地位。雖然在一般老百姓的口頭上、俚語中、戲劇裡、說書中︵包括宣卷、彈詞︶,不斷有神話的內容出現,但是卻沒有真正的地位。如果某人說了一句話,對方說:「這簡直是神話!」那就表示某人說的是一句荒唐得令人難以相信的話。由此可見,一般人對神話的評價。這可能是中了司馬遷的毒,因為他曾對《山海經》││這部近代神話學家像發現寶藏一樣珍貴的古書,給與最不客氣的評語: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總之,他認為「閎大不經」。
其實,神話︵myth︶、傳說︵tradition︶、民間故事︵folklore︶、傳奇︵legend︶都是研究人文科學最重要的古代原始資料。它們雖然並不一樣,各有各的範圍和區別,但對我們的研究,這些分別不頂重要。我們要的是它們的內容。這些資料都反應了初民對大自然︵包括日、月、星辰、山、水、動、植物︶、對自我︵人︶的看法。這些是多麼重要的傳統,可惜這些資料為我國的知識分子所不齒,認為這些是不登大雅之堂、胡說八道的邪說。相反地,它們是研究初民的信仰、思想、心態、感覺等內心境界最好的資料。非常可惜,這些寶貴的資料不被重視而流失了。某些資料一定在民謠山歌之中,而從口頭到文字的階段經過若干「篩選」,再好比那些「純純的」神話色彩相當濃厚的詩歌,因為「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在編輯成為《詩經》的過程中遭淘汰了。
在中國沒有人注意的課題,在日本卻是許多學者研究的中心。在王孝廉所著《中國的神話與傳說》中的附錄「日本學者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所列的日本學者的著作與論文滿滿的佔了四頁的篇幅。 自從大陸開放以後,我們也讀到一些中國有關神話的著作,想不到很具權威的學者李福清竟然是俄國人。 從此看到我國自己不注意的學術領域,外國人反而是權威了。
最近我國在出版界,也有很權威的著作,《神話的智慧》 就是很明顯的一本神學生必讀的課外讀物。當讀到有人把〈創世記〉當作「神話」的時候,至少我們要知道和了解,那作者在說甚麼︵我並沒有說「贊成或反對」我僅說「了解」︶。李亦園先生在為該書作序的時候,曾這麼說:
在一般大眾的觀念裡,神話經常被看為荒誕不經、怪力亂神的作品。……但是,很少人能夠了解,神話其實不是神仙的故事,而是人類自己的故事。人類各民族在神話中所表達的真正主題,……是人類自身的處境,以及他們對自然世界以至於宇宙存在的看法。
我們中國人也有極豐富的神話資料,許多材料很可能因為大人先生們的「道學」而被「扼殺」了。即使碩果僅存的《山海經》也遭遇到不客氣的批評。司馬遷就有所謂「不敢言之」的《山海經》,它是一本了不起的傑作。可惜我們沒有正視它的價值。西諺有一句話說:「從來不會太晚︵never too late︶。」這些神話有著不少的寶藏,因此我們以挖寶的心情來處理它們,成為我們第一章很重要的材料。
貳 人的開始
一、女媧
女媧是一位傳奇的人物;不,她是「神」物。根據《說文》:「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楚辭》中「天問篇」,屈原有「女媧有體,執制匠之。」王逸的注解非常玄,他認為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女媧神話是非常早的,王孝廉認為她還早過盤古的傳說呢!
在三國時代盤古開天闢地的神話出現以前,古代中國最早的開闢神話的神是女媧,及至盤古神話出現了以後,女媧在神話中的地位才逐漸地被盤古取代了。
二、摶土造人
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是早已聞名了,但這不是我們的主題;我們要討論的是「人」。
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與,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為黃土人,貧賤凡庸者人也。
有一位近代人曾寫了一首神話的史詩:
天地開闢之後,大地上已經有了山川草木,有了鳥獸魚蟲,可是沒有人類,世間仍舊荒涼寂寞!行走在這片荒寂地上的大神女媧,心裡感到非常孤獨,這世界好像少了一點生氣,應當添些甚麼,使它更加活潑。
女蝸蹲下身來,抓起一把黃泥滲了水,揉成一個囡囡似的小東西,這東西一放到地上就活了起來蹦蹦跳跳,歡天喜地。他的名字叫作「人」,和飛鳥走獸完全不同身體,雖然渺小,形貌卻像神祇,看來有管理宇宙的能力,女媧心裡非常驚喜。
她對這優美的創造十分滿意,繼續用水揉和著黃泥造成許多男男女女……
女媧已經工作了許久,可是還沒有達到心願,她已弄得疲倦不堪,便順手拉來一條長藤用長藤揮起地上的泥漿,泥漿紛紛落到地面,居然成了呱呱叫著的小人,這方法果然把力氣節省。
地上不久就佈滿了人類的 跡,可是人類的生命都有極限,女媧就教他們男女相配,繁殖後代,人類就這樣一天多過一天。
上述兩段引語:第一段「摶土作人」與《創世記》十分相像,都是用土作原料。在古時文化不相通的時代,這項相通非常有意義。這相似點容後討論︵第三章︶。至於藍先生是一生在香港,雖然是世界公民,仍具濃厚的香港背景,在他筆下的女媧作人,有某些基督教的想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龍的傳人
國內的上海學者王從仁先生的著作《龍││吉祥納福看靈瑞獸》。 在他的前言中,他說:
中華民族古老而悠久的歷史中,此龍是一個最引人注目的象徵物。牠那碩大無比的身軀、雷霆萬鈞的威力、神幻莫測的變化、昂首屈背的雄姿,曾激起中華民族多少動人的想像,點燃起多少崇敬、恐懼、希冀、迷惘等等情感的火花。在牠的身上,凝聚了民族的共同心願,象徵著民族的複雜性格。難怪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
那本書中充滿著龍的神話與傳說,但究竟牠是何種生物?是虛擬的?是實際存在的?有誰看見過?這是二十世紀受過「科學洗禮」的人發的問題;對古人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既然如此,為甚麼台北市「故宮博物院」所展出的「龍之畫像」竟然有數十種之多,而每種又是不同的?這是藝術家的創作?這又是今人問題。一句話,這是傳說中的動物︵legendary animal︶,或是神話中的動物︵mythical animal︶。我希望本書的讀者不要因這句話而成為「絆腳石」,反而加倍地珍惜它,作為我們寶貴的傳統。
在討論「龍的傳人」中無須討論基督徒對「龍」的看法,但為了避免它成為絆腳石,在這裡對「龍」字的翻譯應該有一個交待。根據我人對西方先人學習華文的了解,先從實體的單字開始。很多單字,好比以動物來講,他們可以用實體來定名,如狗、貓、牛、羊等是毫無問題的;然後再進而到那些比較不常見的動物,當時沒有動物園,但是牠們可以用圖片來解決。其他動詞、形容詞、抽象名詞等逐漸發展,不在本文討論之內。問題出在「龍」上:這是一個神話性的動物,我們沒有見過「龍」,西方人也沒有見過dragon;把這兩個神話性的動物湊在一起,無疑是把南北極搞在一起,發生了永遠扯不清的關係,增加了無數不必要的糾紛。我國的「龍」是吉祥動物,集偉大、尊貴於一身;聖經中的「龍」︵dragon的中譯︶是魔鬼的頭,是萬惡之首。其實英文翻dragon的譯者也不知道怎麼翻,所以就把希臘文譯音過來。假如當年我們如法炮製,像譯「撒但」一般,英文譯希臘文的Satan,我們也音譯;我們可把dragon音譯為「屈拉根」之類的名詞,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這類字多得很,例如:Azazel,我們音譯為「阿撒瀉耳」,好極了︵英文:Scapegoat │ AV, Azazel │ NRSV︶,有更多發展空間,現在已知道為一「發怒的神明,魔鬼一流的角色」;另一字英文譯音為Leviathan,也是魔鬼一類的,《和合本》翻成「鱷魚」,《現代本》為「海獸」,註解中有「古代近東傳說中的大怪獸,代表混沌和混亂」的解釋。鱷魚和海獸都不會造成困擾,而龍卻形成了不必要的困擾。我再說,像「阿撒瀉耳」那樣的翻譯就甚麼問題也沒有了。
漢代的畫像磚石中,有很多伏羲、女媧的畫像,下面一幅是在山東嘉祥縣中、東漢武梁祠的畫像磚:
伏羲女媧像
山東嘉祥縣
東漢武梁祠畫像磚
上面的圖畫中,二人上半身是人形,穿長褂,戴冠帽,下半身是蛇型,或龍型。兩條尾巴纏在一起象徵著交尾,更說明了人類的繁衍。這畫面中,男的手拿曲尺,女的手拿圓規,這是木匠的工具;象徵著造天地。某些圖案中,男的手拿太陽,太陽中有金烏;女的手拿月亮,月亮中有蟾蜍。畫中還有小孩,他拉著男女的衣袖,象徵著他們創造人類。
故事大體是這樣的,我說大體,因為各地的傳說各有不同。最早的一對男女是伏羲和女媧,他們成了夫妻以後,女媧生了一條大蛇,伏羲把蛇斬成兩段,就成了天地陰陽;再斬成為四段,分成四季;再斬成為八段,而有四面八方;再斬成為十二段,而有十二地支。再斬,再斬,而有萬物,人也在裡面了。這是漢人的傳統,反不如苗傜地區的邊疆少數民族來得精彩。
很古很古的時代有一個男子,他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有一天,他似乎有預感,天會發生變化,所以他造了一個鐵籠,等待事情的發生。過一會兒,雷聲大作,大雨傾盆。在閃電中一個手持板斧的青臉男子衝進屋來,他是雷公,那男子早有準備,手裡拿了鋼叉,打開鐵門,等待著雷公進來。雷公一闖入鐵籠,他就把門鎖起來。第二天早晨,男子準備到市場去買了作料,回來殺了雷公當菜肴吃。臨走時候再三叮囑兩個小孩,千萬不能給雷公水喝。
那男子走了以後,雷公開始跟孩子講起話來,孩子知道雷公口渴,十分難熬。雷公說:「謝謝你,請你給我一碗水喝。」男孩說:「不行,爸爸說過不可以給你水喝的。」雷公說:「我實在乾死了,請你給我一小杯吧!」男孩說:「爸爸說過不可以的,不能給你水喝。」雷公那時裝出快死的樣子,他說:「那麼就給我幾滴水吧!我快要死了。」女孩比較心軟,她想幾滴水大概沒有問題吧,於是跟哥哥商量。哥哥也覺得幾滴水一定沒有關係的,就給了他。雷公一吃了幾滴水,整個人就改變了,變得非常有精神。
雷公說:「謝啦,我要出來了。」說了這話,只聽到驚天動地的一響,他掙斷了鐵鎖,闖出門來。為了感激兩兄妹,他拔下一顆牙齒,交給孩子,要他們立刻種在地裡,將來無論發生任何變化,可以躲在所結的果子中。過一會兒,爸爸回來了,知道發生的事情,驚慌得不得了,來不及責備他們,即刻準備材料,做一艘大鐵船,等待厄運的來到。同時兩個孩子也知道闖了禍,急急忙忙把牙齒種在地裡。那牙齒一天就開花結果,第二天一早,孩子們看到一個大得無比的葫蘆,他倆鋸掉了葫蘆蓋,看見裡面有無數的牙齒。他們把牙齒挖掉了,剛好夠兄妹爬進去。
第三天狂風暴雨來了。雷公來報仇了。爸爸上了鐵船,孩子們躲進葫蘆。水節節上升,鐵船也跟著上升,直抵天門。父親猛叩天門,希望天老爺能阻止洪水。最後大概天老爺聽了哀求,水不但停止了,也很快退了下去。退得太快了,鐵船碰到地面,跌得粉碎,爸爸也因之喪身。孩子們所坐的葫蘆是軟的,只在地面上跳動了幾下,就不動了。孩子非常高興,他們破「蘆」而出。後來他們成了夫妻,生了一個肉球。他們把肉球包起來;那時天地之間有一個天梯,他兩爬上了天梯,想到天上去玩耍。不料,到了半空,忽然起了一陣大風,小肉塊被吹散了,成了許多小人,這些是他們的兒女。
這是另一個「人的來源」。根據這一傳說,至少伏羲與女媧以前是有人的,但是大水以後的人卻是從他們來的。這些並不重要,神話與傳說不是禁不起理知的考驗,而是不必用理知去思考。至於名字的來源:男的名「伏羲」,是「匏」的意思,也就是葫蘆;女的名「女媧」,是「女葫蘆」的意思。名字的出典太過文縐縐,大概是漢人後加的「傑作」吧。
但是「伏羲龍身,女媧蛇軀」的古代文獻是屢見不鮮的。因此這對龍蛇型的夫妻是傳說中的人類祖先,人也是「龍的傳人」了。
本章註:
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與傳說》,頁274-279,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年月。
李福清,《中國神話故事論集》,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年。
坎伯︵Joseph Cambell︶,《神話的智慧︵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李子寧譯,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年。
同上,頁,李亦園序。
王孝廉,同上,頁。
《淮南子》,「覽冥訓」。
藍海文,《中華史詩││神話與傳說》,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年月。頁-。「摶土作人」引自《風俗通義》,「男女相配」引自同書「女媧禱祠神祈而為女媒,因置婚姻」。
王從仁《龍││吉祥納福看瑞獸》,台灣世界書局,民國年。
王從仁,同前註,頁。
王從仁,同前註,頁。
王從仁,同前註,整篇故事見該書頁-。
第一章 中國傳說
一個古老民族生存在它的自然環境中,他們在日常生活和大自然的接觸中一定會發生許多關係,這些關係逐漸會「人格化」,因為「人」終究是他們最熟悉的領域。這些自然界的現象及關係再加以宗教化,而初民的想像力又是非常豐富的;這些敘述就成了神話。
壹 神話的重要
在一般國人的心目中,也許是受了傳統儒家的影響,始終沒有給神話正確的地位。雖然在一般老百姓的口頭上、俚語中、戲劇裡、說書中︵包括宣卷、彈詞︶,不斷有神話的內容出現,但是卻沒有真正的地位。如果某人說了一句話,對方說:「這簡直是神話!」那就表示某人說的是一句荒唐得令人難以相信的話。由此可見,一般人對神話的評價。這可能是中了司馬遷的毒,因為他曾對《山海經》││這部近代神話學家像發現寶藏一樣珍貴的古書,給與最不客氣的評語: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總之,他認為「閎大不經」。
其實,神話︵myth︶、傳說︵tradition︶、民間故事︵folklore︶、傳奇︵legend︶都是研究人文科學最重要的古代原始資料。它們雖然並不一樣,各有各的範圍和區別,但對我們的研究,這些分別不頂重要。我們要的是它們的內容。這些資料都反應了初民對大自然︵包括日、月、星辰、山、水、動、植物︶、對自我︵人︶的看法。這些是多麼重要的傳統,可惜這些資料為我國的知識分子所不齒,認為這些是不登大雅之堂、胡說八道的邪說。相反地,它們是研究初民的信仰、思想、心態、感覺等內心境界最好的資料。非常可惜,這些寶貴的資料不被重視而流失了。某些資料一定在民謠山歌之中,而從口頭到文字的階段經過若干「篩選」,再好比那些「純純的」神話色彩相當濃厚的詩歌,因為「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在編輯成為《詩經》的過程中遭淘汰了。
在中國沒有人注意的課題,在日本卻是許多學者研究的中心。在王孝廉所著《中國的神話與傳說》中的附錄「日本學者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所列的日本學者的著作與論文滿滿的佔了四頁的篇幅。 自從大陸開放以後,我們也讀到一些中國有關神話的著作,想不到很具權威的學者李福清竟然是俄國人。 從此看到我國自己不注意的學術領域,外國人反而是權威了。
最近我國在出版界,也有很權威的著作,《神話的智慧》 就是很明顯的一本神學生必讀的課外讀物。當讀到有人把〈創世記〉當作「神話」的時候,至少我們要知道和了解,那作者在說甚麼︵我並沒有說「贊成或反對」我僅說「了解」︶。李亦園先生在為該書作序的時候,曾這麼說:
在一般大眾的觀念裡,神話經常被看為荒誕不經、怪力亂神的作品。……但是,很少人能夠了解,神話其實不是神仙的故事,而是人類自己的故事。人類各民族在神話中所表達的真正主題,……是人類自身的處境,以及他們對自然世界以至於宇宙存在的看法。
我們中國人也有極豐富的神話資料,許多材料很可能因為大人先生們的「道學」而被「扼殺」了。即使碩果僅存的《山海經》也遭遇到不客氣的批評。司馬遷就有所謂「不敢言之」的《山海經》,它是一本了不起的傑作。可惜我們沒有正視它的價值。西諺有一句話說:「從來不會太晚︵never too late︶。」這些神話有著不少的寶藏,因此我們以挖寶的心情來處理它們,成為我們第一章很重要的材料。
貳 人的開始
一、女媧
女媧是一位傳奇的人物;不,她是「神」物。根據《說文》:「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楚辭》中「天問篇」,屈原有「女媧有體,執制匠之。」王逸的注解非常玄,他認為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女媧神話是非常早的,王孝廉認為她還早過盤古的傳說呢!
在三國時代盤古開天闢地的神話出現以前,古代中國最早的開闢神話的神是女媧,及至盤古神話出現了以後,女媧在神話中的地位才逐漸地被盤古取代了。
二、摶土造人
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是早已聞名了,但這不是我們的主題;我們要討論的是「人」。
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與,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為黃土人,貧賤凡庸者人也。
有一位近代人曾寫了一首神話的史詩:
天地開闢之後,大地上已經有了山川草木,有了鳥獸魚蟲,可是沒有人類,世間仍舊荒涼寂寞!行走在這片荒寂地上的大神女媧,心裡感到非常孤獨,這世界好像少了一點生氣,應當添些甚麼,使它更加活潑。
女蝸蹲下身來,抓起一把黃泥滲了水,揉成一個囡囡似的小東西,這東西一放到地上就活了起來蹦蹦跳跳,歡天喜地。他的名字叫作「人」,和飛鳥走獸完全不同身體,雖然渺小,形貌卻像神祇,看來有管理宇宙的能力,女媧心裡非常驚喜。
她對這優美的創造十分滿意,繼續用水揉和著黃泥造成許多男男女女……
女媧已經工作了許久,可是還沒有達到心願,她已弄得疲倦不堪,便順手拉來一條長藤用長藤揮起地上的泥漿,泥漿紛紛落到地面,居然成了呱呱叫著的小人,這方法果然把力氣節省。
地上不久就佈滿了人類的 跡,可是人類的生命都有極限,女媧就教他們男女相配,繁殖後代,人類就這樣一天多過一天。
上述兩段引語:第一段「摶土作人」與《創世記》十分相像,都是用土作原料。在古時文化不相通的時代,這項相通非常有意義。這相似點容後討論︵第三章︶。至於藍先生是一生在香港,雖然是世界公民,仍具濃厚的香港背景,在他筆下的女媧作人,有某些基督教的想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龍的傳人
國內的上海學者王從仁先生的著作《龍││吉祥納福看靈瑞獸》。 在他的前言中,他說:
中華民族古老而悠久的歷史中,此龍是一個最引人注目的象徵物。牠那碩大無比的身軀、雷霆萬鈞的威力、神幻莫測的變化、昂首屈背的雄姿,曾激起中華民族多少動人的想像,點燃起多少崇敬、恐懼、希冀、迷惘等等情感的火花。在牠的身上,凝聚了民族的共同心願,象徵著民族的複雜性格。難怪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
那本書中充滿著龍的神話與傳說,但究竟牠是何種生物?是虛擬的?是實際存在的?有誰看見過?這是二十世紀受過「科學洗禮」的人發的問題;對古人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既然如此,為甚麼台北市「故宮博物院」所展出的「龍之畫像」竟然有數十種之多,而每種又是不同的?這是藝術家的創作?這又是今人問題。一句話,這是傳說中的動物︵legendary animal︶,或是神話中的動物︵mythical animal︶。我希望本書的讀者不要因這句話而成為「絆腳石」,反而加倍地珍惜它,作為我們寶貴的傳統。
在討論「龍的傳人」中無須討論基督徒對「龍」的看法,但為了避免它成為絆腳石,在這裡對「龍」字的翻譯應該有一個交待。根據我人對西方先人學習華文的了解,先從實體的單字開始。很多單字,好比以動物來講,他們可以用實體來定名,如狗、貓、牛、羊等是毫無問題的;然後再進而到那些比較不常見的動物,當時沒有動物園,但是牠們可以用圖片來解決。其他動詞、形容詞、抽象名詞等逐漸發展,不在本文討論之內。問題出在「龍」上:這是一個神話性的動物,我們沒有見過「龍」,西方人也沒有見過dragon;把這兩個神話性的動物湊在一起,無疑是把南北極搞在一起,發生了永遠扯不清的關係,增加了無數不必要的糾紛。我國的「龍」是吉祥動物,集偉大、尊貴於一身;聖經中的「龍」︵dragon的中譯︶是魔鬼的頭,是萬惡之首。其實英文翻dragon的譯者也不知道怎麼翻,所以就把希臘文譯音過來。假如當年我們如法炮製,像譯「撒但」一般,英文譯希臘文的Satan,我們也音譯;我們可把dragon音譯為「屈拉根」之類的名詞,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這類字多得很,例如:Azazel,我們音譯為「阿撒瀉耳」,好極了︵英文:Scapegoat │ AV, Azazel │ NRSV︶,有更多發展空間,現在已知道為一「發怒的神明,魔鬼一流的角色」;另一字英文譯音為Leviathan,也是魔鬼一類的,《和合本》翻成「鱷魚」,《現代本》為「海獸」,註解中有「古代近東傳說中的大怪獸,代表混沌和混亂」的解釋。鱷魚和海獸都不會造成困擾,而龍卻形成了不必要的困擾。我再說,像「阿撒瀉耳」那樣的翻譯就甚麼問題也沒有了。
漢代的畫像磚石中,有很多伏羲、女媧的畫像,下面一幅是在山東嘉祥縣中、東漢武梁祠的畫像磚:
伏羲女媧像
山東嘉祥縣
東漢武梁祠畫像磚
上面的圖畫中,二人上半身是人形,穿長褂,戴冠帽,下半身是蛇型,或龍型。兩條尾巴纏在一起象徵著交尾,更說明了人類的繁衍。這畫面中,男的手拿曲尺,女的手拿圓規,這是木匠的工具;象徵著造天地。某些圖案中,男的手拿太陽,太陽中有金烏;女的手拿月亮,月亮中有蟾蜍。畫中還有小孩,他拉著男女的衣袖,象徵著他們創造人類。
故事大體是這樣的,我說大體,因為各地的傳說各有不同。最早的一對男女是伏羲和女媧,他們成了夫妻以後,女媧生了一條大蛇,伏羲把蛇斬成兩段,就成了天地陰陽;再斬成為四段,分成四季;再斬成為八段,而有四面八方;再斬成為十二段,而有十二地支。再斬,再斬,而有萬物,人也在裡面了。這是漢人的傳統,反不如苗傜地區的邊疆少數民族來得精彩。
很古很古的時代有一個男子,他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有一天,他似乎有預感,天會發生變化,所以他造了一個鐵籠,等待事情的發生。過一會兒,雷聲大作,大雨傾盆。在閃電中一個手持板斧的青臉男子衝進屋來,他是雷公,那男子早有準備,手裡拿了鋼叉,打開鐵門,等待著雷公進來。雷公一闖入鐵籠,他就把門鎖起來。第二天早晨,男子準備到市場去買了作料,回來殺了雷公當菜肴吃。臨走時候再三叮囑兩個小孩,千萬不能給雷公水喝。
那男子走了以後,雷公開始跟孩子講起話來,孩子知道雷公口渴,十分難熬。雷公說:「謝謝你,請你給我一碗水喝。」男孩說:「不行,爸爸說過不可以給你水喝的。」雷公說:「我實在乾死了,請你給我一小杯吧!」男孩說:「爸爸說過不可以的,不能給你水喝。」雷公那時裝出快死的樣子,他說:「那麼就給我幾滴水吧!我快要死了。」女孩比較心軟,她想幾滴水大概沒有問題吧,於是跟哥哥商量。哥哥也覺得幾滴水一定沒有關係的,就給了他。雷公一吃了幾滴水,整個人就改變了,變得非常有精神。
雷公說:「謝啦,我要出來了。」說了這話,只聽到驚天動地的一響,他掙斷了鐵鎖,闖出門來。為了感激兩兄妹,他拔下一顆牙齒,交給孩子,要他們立刻種在地裡,將來無論發生任何變化,可以躲在所結的果子中。過一會兒,爸爸回來了,知道發生的事情,驚慌得不得了,來不及責備他們,即刻準備材料,做一艘大鐵船,等待厄運的來到。同時兩個孩子也知道闖了禍,急急忙忙把牙齒種在地裡。那牙齒一天就開花結果,第二天一早,孩子們看到一個大得無比的葫蘆,他倆鋸掉了葫蘆蓋,看見裡面有無數的牙齒。他們把牙齒挖掉了,剛好夠兄妹爬進去。
第三天狂風暴雨來了。雷公來報仇了。爸爸上了鐵船,孩子們躲進葫蘆。水節節上升,鐵船也跟著上升,直抵天門。父親猛叩天門,希望天老爺能阻止洪水。最後大概天老爺聽了哀求,水不但停止了,也很快退了下去。退得太快了,鐵船碰到地面,跌得粉碎,爸爸也因之喪身。孩子們所坐的葫蘆是軟的,只在地面上跳動了幾下,就不動了。孩子非常高興,他們破「蘆」而出。後來他們成了夫妻,生了一個肉球。他們把肉球包起來;那時天地之間有一個天梯,他兩爬上了天梯,想到天上去玩耍。不料,到了半空,忽然起了一陣大風,小肉塊被吹散了,成了許多小人,這些是他們的兒女。
這是另一個「人的來源」。根據這一傳說,至少伏羲與女媧以前是有人的,但是大水以後的人卻是從他們來的。這些並不重要,神話與傳說不是禁不起理知的考驗,而是不必用理知去思考。至於名字的來源:男的名「伏羲」,是「匏」的意思,也就是葫蘆;女的名「女媧」,是「女葫蘆」的意思。名字的出典太過文縐縐,大概是漢人後加的「傑作」吧。
但是「伏羲龍身,女媧蛇軀」的古代文獻是屢見不鮮的。因此這對龍蛇型的夫妻是傳說中的人類祖先,人也是「龍的傳人」了。
本章註:
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與傳說》,頁274-279,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年月。
李福清,《中國神話故事論集》,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年。
坎伯︵Joseph Cambell︶,《神話的智慧︵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李子寧譯,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年。
同上,頁,李亦園序。
王孝廉,同上,頁。
《淮南子》,「覽冥訓」。
藍海文,《中華史詩││神話與傳說》,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年月。頁-。「摶土作人」引自《風俗通義》,「男女相配」引自同書「女媧禱祠神祈而為女媒,因置婚姻」。
王從仁《龍││吉祥納福看瑞獸》,台灣世界書局,民國年。
王從仁,同前註,頁。
王從仁,同前註,頁。
王從仁,同前註,整篇故事見該書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