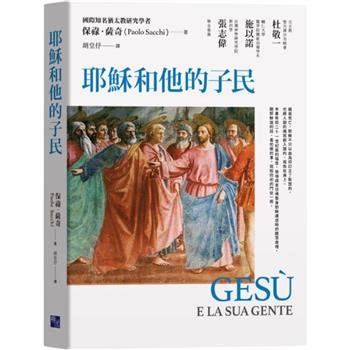第十四章
歷史之外
如同我在自序中說過,歷史性不是促使我重新深讀福音的原因。然而我眼前的耶穌再次走過他的人生,躍然於福音紙上的耶穌。我希望在血肉之軀、和尋常人一樣也吃也喝的耶穌身上,尋找神聖的痕跡,那傳承至今日的我的教會傳統對他所肯定的一切。
耶穌的獨特性,在耶穌赦免罪同時治癒癱子,以及在葡萄園戶的比喻之後,他對自己身分的說明,顯見耶穌對自己是「獨特的」充滿意識。耶穌生平最令我欽佩他的偉大的時刻,是當他在最後晚餐席間說:「這是我的血,盟約之血」。看到那人像梅瑟一樣與天主立盟,以血為印璽的場面,著實令人震驚;只不過這次作為印璽的血不是牛犢的,是他的。血,生命與死亡的意義,只有在希伯來的傳統與文化光照下才能讀取,因為其意義完全體現在此文化中,不過還應當有超越希伯來文化侷限的價值。耶穌應該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才說自己的血要為「大眾」傾流。他的行動為我們應當也有意義,這使我覺得站立在一個奧祕的門檻前,我有部分把握,所以不能拒絕它。像是我能夠領悟的奧祕。
與天主的盟約是在痛苦與死亡中締結,耶穌也接受了死亡和痛苦。對此我感受到一種發自內心、強烈的抗拒,所以我欽佩他,並沉默。我面對的是生命的奧祕,我自己的生命奧祕。
就像是我來到一扇堅實而敞開的窗戶前,窗外是一個遼闊的世界,充滿我無法理解的事與物。與天主立約的耶穌把我放在對現實的理解前,翻轉我理解的方式,不再只依據理性。我的雙腳仍踏在土地上,我的雙眼凝視著痛苦的黑暗之光,痛苦是盟約允許的工具。我不明白,我不了解!我對痛苦的抗拒根深柢固,就像伯多祿對耶穌向自己揭示他的命運時的抗拒一樣。伯多祿不明白,耶穌叫他撒殫,伯多祿仍然不明白。人對痛苦的抗拒是根深柢固的,耶穌在革則瑪尼莊園祈求天主父,放盡一切氣力直到血汗並流,希望免去那苦杯。之後,他接受了。
人繼續抗拒,但是耶穌接受了。「接受」,而不是「忍受」,二者的差異其實不小,如同我一個朋友說的。當耶穌接受的時候,他不再處於以理性判斷的層面,痛苦只是個意外,打亂原本幾何般規律的計劃。耶穌接受存在的實況,在這實況中痛苦有其作用,為存在而生(raisond’être)。當聖保祿領悟到自己的痛苦與耶穌的痛苦有近似的價值,他明白了痛苦是有意義的,所以才能積極地面對痛苦,甚至說出「我很高興」的話。但是我仍留在黑暗中,我的理智持續抗拒這種存在的實況,就像伯多祿,就像革則瑪尼莊園裡的耶穌:人受痛苦不是自然的,雖然存在包含痛苦。我可以感受到自己這句話中的強烈矛盾,但是耶穌因著接受天主父的旨意克服了。痛苦有其作用,但是無法理性條理地解釋,除非把它簡化說成贖罪。雖然這種說法為解釋痛苦的存在更淺顯易懂,卻使得生命成了罪與消罪之間制式衡量的秤台。對此我也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直覺或理性角度看來都不是事實。
需要一個跳躍:一定還有支持生命的存在,即使超乎理性理解的範疇,因為生命是存在的事實。耶穌的事蹟以清晰的方式教人看見,人的理智運作在此範疇幾乎無用武之地。每一個範疇都需要能夠闡釋自己存在的計劃和所屬的分類。生命也必有其所屬範疇。如果我們輕易就能接受理智作用後提供的安全感,和所有生存所需的力量與支援,那麼我們也應當接受生命有我們不了解但肯定存在之處,因為無法從生命中將其抹滅。這是滲透整個存在範疇的渴望,但是我知道在理性主導之下,必使我們在這門檻前止步,讓我們瞥見門檻後的景象一眼,卻無法予以分辨。然而,渴望不會消失。
需要進入盟約中:綑綁盟約的繩索一端握在耶穌手中,另一端是天主父。在這道繩索中,痛苦極具影響力:耶穌的痛苦,全人類的痛苦。這是身處奧祕裡,在當中有穩定與安全感,即使仍缺少絕對的穩定與安全感:那是另一種可以信賴的穩定,另一種安心毋庸掛慮。就像人能夠在水中暢游,唯有當他無懼於水,無意戀棧堅實陸地的時候。
接受痛苦和死亡是耶穌生平最後一個行動。在他的生命裡,一定存在某個原因,允許他即使血汗並流,終究能夠接受,接受「痛苦」這個詞彙的全部意義。耶穌愛了一生。愛,驅動生命的崇高力量,在耶穌一生中扮演重要角色。唯有愛無條件地允許其他存在——對此,人難以理解——這些存在之所是,就是他們存在的理由。我開始明白愛敵人不是一條誡命衍生的新命令。愛,也為了敵人的存在;因為是愛,沒有任何附帶條件,即使是仇恨。耶穌的生命至此成為一個完滿的典型。
為此,耶穌得以無條件地與天主立約,為實現最終目的的盟約。耶穌的經歷再次成為生命的典型:他是進入他立的盟約的第一人!耶穌為當時、現在,及未來的所有人類開闢了一條道路。我們沿著這條道路進入、身處之境,闡釋其究竟的不再是理性智識,而是信仰、希望,與愛。我們身處生命的整全之境,言詞的論辯啞然失聲,生命活潑地躍動著。
這一切都可被察覺、被體驗,雖然我們還能意識到距離的存在,但是人能夠緊緊依附那道維繫人類與天主的繩索。
歷史之外
如同我在自序中說過,歷史性不是促使我重新深讀福音的原因。然而我眼前的耶穌再次走過他的人生,躍然於福音紙上的耶穌。我希望在血肉之軀、和尋常人一樣也吃也喝的耶穌身上,尋找神聖的痕跡,那傳承至今日的我的教會傳統對他所肯定的一切。
耶穌的獨特性,在耶穌赦免罪同時治癒癱子,以及在葡萄園戶的比喻之後,他對自己身分的說明,顯見耶穌對自己是「獨特的」充滿意識。耶穌生平最令我欽佩他的偉大的時刻,是當他在最後晚餐席間說:「這是我的血,盟約之血」。看到那人像梅瑟一樣與天主立盟,以血為印璽的場面,著實令人震驚;只不過這次作為印璽的血不是牛犢的,是他的。血,生命與死亡的意義,只有在希伯來的傳統與文化光照下才能讀取,因為其意義完全體現在此文化中,不過還應當有超越希伯來文化侷限的價值。耶穌應該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才說自己的血要為「大眾」傾流。他的行動為我們應當也有意義,這使我覺得站立在一個奧祕的門檻前,我有部分把握,所以不能拒絕它。像是我能夠領悟的奧祕。
與天主的盟約是在痛苦與死亡中締結,耶穌也接受了死亡和痛苦。對此我感受到一種發自內心、強烈的抗拒,所以我欽佩他,並沉默。我面對的是生命的奧祕,我自己的生命奧祕。
就像是我來到一扇堅實而敞開的窗戶前,窗外是一個遼闊的世界,充滿我無法理解的事與物。與天主立約的耶穌把我放在對現實的理解前,翻轉我理解的方式,不再只依據理性。我的雙腳仍踏在土地上,我的雙眼凝視著痛苦的黑暗之光,痛苦是盟約允許的工具。我不明白,我不了解!我對痛苦的抗拒根深柢固,就像伯多祿對耶穌向自己揭示他的命運時的抗拒一樣。伯多祿不明白,耶穌叫他撒殫,伯多祿仍然不明白。人對痛苦的抗拒是根深柢固的,耶穌在革則瑪尼莊園祈求天主父,放盡一切氣力直到血汗並流,希望免去那苦杯。之後,他接受了。
人繼續抗拒,但是耶穌接受了。「接受」,而不是「忍受」,二者的差異其實不小,如同我一個朋友說的。當耶穌接受的時候,他不再處於以理性判斷的層面,痛苦只是個意外,打亂原本幾何般規律的計劃。耶穌接受存在的實況,在這實況中痛苦有其作用,為存在而生(raisond’être)。當聖保祿領悟到自己的痛苦與耶穌的痛苦有近似的價值,他明白了痛苦是有意義的,所以才能積極地面對痛苦,甚至說出「我很高興」的話。但是我仍留在黑暗中,我的理智持續抗拒這種存在的實況,就像伯多祿,就像革則瑪尼莊園裡的耶穌:人受痛苦不是自然的,雖然存在包含痛苦。我可以感受到自己這句話中的強烈矛盾,但是耶穌因著接受天主父的旨意克服了。痛苦有其作用,但是無法理性條理地解釋,除非把它簡化說成贖罪。雖然這種說法為解釋痛苦的存在更淺顯易懂,卻使得生命成了罪與消罪之間制式衡量的秤台。對此我也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直覺或理性角度看來都不是事實。
需要一個跳躍:一定還有支持生命的存在,即使超乎理性理解的範疇,因為生命是存在的事實。耶穌的事蹟以清晰的方式教人看見,人的理智運作在此範疇幾乎無用武之地。每一個範疇都需要能夠闡釋自己存在的計劃和所屬的分類。生命也必有其所屬範疇。如果我們輕易就能接受理智作用後提供的安全感,和所有生存所需的力量與支援,那麼我們也應當接受生命有我們不了解但肯定存在之處,因為無法從生命中將其抹滅。這是滲透整個存在範疇的渴望,但是我知道在理性主導之下,必使我們在這門檻前止步,讓我們瞥見門檻後的景象一眼,卻無法予以分辨。然而,渴望不會消失。
需要進入盟約中:綑綁盟約的繩索一端握在耶穌手中,另一端是天主父。在這道繩索中,痛苦極具影響力:耶穌的痛苦,全人類的痛苦。這是身處奧祕裡,在當中有穩定與安全感,即使仍缺少絕對的穩定與安全感:那是另一種可以信賴的穩定,另一種安心毋庸掛慮。就像人能夠在水中暢游,唯有當他無懼於水,無意戀棧堅實陸地的時候。
接受痛苦和死亡是耶穌生平最後一個行動。在他的生命裡,一定存在某個原因,允許他即使血汗並流,終究能夠接受,接受「痛苦」這個詞彙的全部意義。耶穌愛了一生。愛,驅動生命的崇高力量,在耶穌一生中扮演重要角色。唯有愛無條件地允許其他存在——對此,人難以理解——這些存在之所是,就是他們存在的理由。我開始明白愛敵人不是一條誡命衍生的新命令。愛,也為了敵人的存在;因為是愛,沒有任何附帶條件,即使是仇恨。耶穌的生命至此成為一個完滿的典型。
為此,耶穌得以無條件地與天主立約,為實現最終目的的盟約。耶穌的經歷再次成為生命的典型:他是進入他立的盟約的第一人!耶穌為當時、現在,及未來的所有人類開闢了一條道路。我們沿著這條道路進入、身處之境,闡釋其究竟的不再是理性智識,而是信仰、希望,與愛。我們身處生命的整全之境,言詞的論辯啞然失聲,生命活潑地躍動著。
這一切都可被察覺、被體驗,雖然我們還能意識到距離的存在,但是人能夠緊緊依附那道維繫人類與天主的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