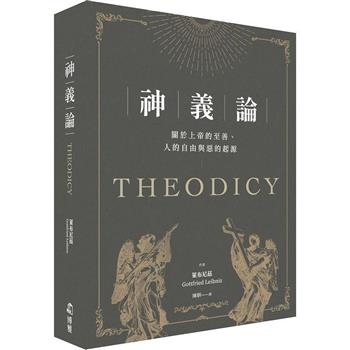前言
我們都曾見過,一般而言,人們都要訴諸於外在形式來表達他們的宗教:可靠的虔誠,即真光和美德,則從來就不是多數人分內的事。人們不應該對此感到驚奇,因為沒有什麼比這更符合人性的弱點了。外在的東西會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但事物的內在本質則要求只有極少數人才能給予這樣恰到好處的考慮。因為真正的虔誠體現在原則和實踐中,宗教的外在形式仿效這些原則和實踐,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禮儀實踐,另一種是信條句式。禮儀類似於高尚的行為,而信條像是真理的影子,而且或多或少接近真光。所有這些外在形式都值得讚揚,如果發明外在形式的那些人能夠使它們恰如其分地維護和表達他們所效法的,諸如宗教儀式、教會戒律、社群規則以及人類的律例典章,這些總會像藩籬一樣圍繞著神聖律,幫助我們遠離邪惡、慣於行善和熟悉美德。這正是摩西和其他優秀的法典擬定者們的目的,也是那些建立宗教秩序的聖賢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這是最純潔、最開明之宗教的神聖創始人耶穌基督的目的。信條句式也同樣如此:只要這些信條的闡述沒有違背包含救贖在內的真理,即便沒有涉及完整的真理,它們也都是有效的。但太頻繁發生的情況卻是:宗教在禮儀上顯得僵化呆板,甚至神聖之光被人的觀點所遮蔽。
在基督宗教創立之前,異教徒們就已經居住在地球上了,他們只有一種外在形式:他們在崇拜中也遵循一些儀式,但他們沒有信仰條文,也從未想過為他們的教義神學建範立式。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所拜的神明是真實的人還是自然力的象徵,猶如太陽、行星和元素一樣。他們的宗教神祕性不在於艱澀難懂的教義,而在於遵守某些祕密儀式;因此那些玷汙者,即那些從一開始就不遵守祕密儀式的人,就被排除在外。這些祕密儀式往往荒謬可笑,為了避免遭到蔑視,有必要將它們隱匿起來。異教徒們很迷信,比如他們吹噓誇大奇蹟,處處充滿神諭、徵兆、怪異、占卜。祭司們發明了用以象徵神明的憤怒或仁慈的靈異現象,而且他們自詡為這些靈異現象的解釋者。這種做法常常透過對人類事件的恐懼和希望來控制人的心智,但幾乎不正視來世生活的偉大盼望,也沒有人願意費心向人們傳授關於上帝和靈魂的真實觀念。
在所有古代族群中,似乎只有希伯來民族對他們自己的宗教擁有公開教義。亞伯拉罕和摩西建立了對獨一上帝的信仰,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泉源,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希伯來人堅信只有上帝才配得上至高無上的實質之稱謂。當看到地球上一小塊區域的居民居然比其他地區的人類更加開明時,人們驚嘆不已。或許其他民族的聖賢有時也說過同樣的話,但他們並沒有那麼幸運能夠找到足夠的追隨者,把教義轉化為律法。儘管如此,摩西並沒有在他的律法中寫入靈魂不朽的教義,這與他的理念是一致的。靈魂不朽的理念先是通過口述傳統而傳授下來,直到耶穌基督揭開靈魂不朽的面紗之前,這個理念並沒有被公開宣告及廣泛接受。雖然耶穌基督無權無勢,但他以律法制定者的全部力量教導人們:不朽的靈魂將進入永恆生命,在那裡他們將接受各自行為所帶來的審判。摩西已經表達了上帝的至大至善的美好概念,這是當今許多文明的民族所認同和讚賞的;但只有耶穌基督充分地證明這些理念的成果,並宣稱神聖的至善和正義在上帝對人類靈魂的設計中展現得完美無缺。
在這裡,我暫不考慮基督教教義的其他觀點,而是就如下一點做些說明:耶穌基督如何把自然宗教轉變為律法,並因此獲得公共教義的權威。他獨自一人完成了歷代哲學家們努力奮鬥卻徒勞無功的事。基督徒們最終在羅馬帝國占了上風,成為地球上大部分已知地區的統治者,聖賢的宗教變成了許多民族的宗教。即便是後來的穆罕默德也沒能背離自然神學的偉大教義:他的追隨者們把這些教義傳播到國外,傳播到亞洲和非洲最偏遠的族群中,甚至傳播到基督宗教尚未傳播到的地方;在許多國家中,他們廢除了那些與上帝的合一性及靈魂不朽的真正教義背道而馳的異教迷信。
耶穌基督完成了始於摩西的工作之後,他祈願上帝不僅僅是我們敬畏和崇拜的對象,也是我們熱愛和獻身的對象,這是顯而易見的。因而祂透過盼望使人幸福,使人在塵世中預先品嘗到未來極樂的滋味。因為沒有什麼比愛一個值得愛的事物更令人愜意歡愉的了。愛是一種精神狀態,它讓我們為我們所愛的對象的完美而欣喜萬分,沒有什麼比上帝更完美,也沒有什麼比在祂裡面更令人喜樂。去愛祂,用靈魂去默觀祂的完美,這其實很容易,因為我們只是在找回深埋於自己心裡的這些思想。上帝的完美就是我們靈魂深處的完美,但祂的完美是無邊無際的;祂是海洋,我們不過是祂恩賜的滄海一粟;在我們裡面,只有一些力量、一點知識、一絲善良;但在上帝裡面,能力、知識和善良皆是完備。秩序、比例、和諧,這些都令人愉悅;繪畫和音樂也是這些實例:上帝是所有秩序;祂總是保持比例的真實性,祂創造宇宙的和諧;一切美都是祂的真光的流溢。
由此可見,真正的虔誠,甚至真正的極樂存在於上帝的愛中,但這愛是如此地甦醒人心,以至於祂的熾熱激情總是伴隨著明悟洞察。這種愛在美善的行為中產生快樂滿足,足以慰藉美德;這種愛將一切與上帝作為中心加以連繫,將人性渡到神性那裡去。因為在履行職責時,當一個人服從理性,他就會遵行最高理性的秩序。一個人把自己的所有意圖都導向共同的善,這就是上帝的榮耀,無其他可媲美。因此,人們會發現,沒有比擁護社群利益更大的個人利益了;一個人透過甘心樂意為人類謀取真正的利益而獲得自我的滿足。一個人無論成功與否,他都會滿足於過往所發生的一切,因為一旦他順從了上帝的旨意,而且深知祂的旨意是最美善的。但在祂透過事件宣告祂的旨意之前,人們必須努力做那些看起來最符合祂命令的事情,如此方可領會祂的旨意。當我們處於這樣的心境時,我們不會因為艱難而沮喪氣餒,我們只會因自己的失誤而懊悔;人們的忘恩負義並不能讓我們溫良的性情懈怠片刻。我們的博愛慈善充滿謙遜和節制,這種慈善之心不會讓我們飛揚跋扈;我們細察自己的缺點,珍惜他人的才華;我們力求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我們必須盡自己所能的做得完美,不可加害於人。沒有仁愛,就沒有虔誠;沒有溫良仁慈,就不可能彰顯出誠摯的敬虔。……
我們都曾見過,一般而言,人們都要訴諸於外在形式來表達他們的宗教:可靠的虔誠,即真光和美德,則從來就不是多數人分內的事。人們不應該對此感到驚奇,因為沒有什麼比這更符合人性的弱點了。外在的東西會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但事物的內在本質則要求只有極少數人才能給予這樣恰到好處的考慮。因為真正的虔誠體現在原則和實踐中,宗教的外在形式仿效這些原則和實踐,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禮儀實踐,另一種是信條句式。禮儀類似於高尚的行為,而信條像是真理的影子,而且或多或少接近真光。所有這些外在形式都值得讚揚,如果發明外在形式的那些人能夠使它們恰如其分地維護和表達他們所效法的,諸如宗教儀式、教會戒律、社群規則以及人類的律例典章,這些總會像藩籬一樣圍繞著神聖律,幫助我們遠離邪惡、慣於行善和熟悉美德。這正是摩西和其他優秀的法典擬定者們的目的,也是那些建立宗教秩序的聖賢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這是最純潔、最開明之宗教的神聖創始人耶穌基督的目的。信條句式也同樣如此:只要這些信條的闡述沒有違背包含救贖在內的真理,即便沒有涉及完整的真理,它們也都是有效的。但太頻繁發生的情況卻是:宗教在禮儀上顯得僵化呆板,甚至神聖之光被人的觀點所遮蔽。
在基督宗教創立之前,異教徒們就已經居住在地球上了,他們只有一種外在形式:他們在崇拜中也遵循一些儀式,但他們沒有信仰條文,也從未想過為他們的教義神學建範立式。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所拜的神明是真實的人還是自然力的象徵,猶如太陽、行星和元素一樣。他們的宗教神祕性不在於艱澀難懂的教義,而在於遵守某些祕密儀式;因此那些玷汙者,即那些從一開始就不遵守祕密儀式的人,就被排除在外。這些祕密儀式往往荒謬可笑,為了避免遭到蔑視,有必要將它們隱匿起來。異教徒們很迷信,比如他們吹噓誇大奇蹟,處處充滿神諭、徵兆、怪異、占卜。祭司們發明了用以象徵神明的憤怒或仁慈的靈異現象,而且他們自詡為這些靈異現象的解釋者。這種做法常常透過對人類事件的恐懼和希望來控制人的心智,但幾乎不正視來世生活的偉大盼望,也沒有人願意費心向人們傳授關於上帝和靈魂的真實觀念。
在所有古代族群中,似乎只有希伯來民族對他們自己的宗教擁有公開教義。亞伯拉罕和摩西建立了對獨一上帝的信仰,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泉源,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希伯來人堅信只有上帝才配得上至高無上的實質之稱謂。當看到地球上一小塊區域的居民居然比其他地區的人類更加開明時,人們驚嘆不已。或許其他民族的聖賢有時也說過同樣的話,但他們並沒有那麼幸運能夠找到足夠的追隨者,把教義轉化為律法。儘管如此,摩西並沒有在他的律法中寫入靈魂不朽的教義,這與他的理念是一致的。靈魂不朽的理念先是通過口述傳統而傳授下來,直到耶穌基督揭開靈魂不朽的面紗之前,這個理念並沒有被公開宣告及廣泛接受。雖然耶穌基督無權無勢,但他以律法制定者的全部力量教導人們:不朽的靈魂將進入永恆生命,在那裡他們將接受各自行為所帶來的審判。摩西已經表達了上帝的至大至善的美好概念,這是當今許多文明的民族所認同和讚賞的;但只有耶穌基督充分地證明這些理念的成果,並宣稱神聖的至善和正義在上帝對人類靈魂的設計中展現得完美無缺。
在這裡,我暫不考慮基督教教義的其他觀點,而是就如下一點做些說明:耶穌基督如何把自然宗教轉變為律法,並因此獲得公共教義的權威。他獨自一人完成了歷代哲學家們努力奮鬥卻徒勞無功的事。基督徒們最終在羅馬帝國占了上風,成為地球上大部分已知地區的統治者,聖賢的宗教變成了許多民族的宗教。即便是後來的穆罕默德也沒能背離自然神學的偉大教義:他的追隨者們把這些教義傳播到國外,傳播到亞洲和非洲最偏遠的族群中,甚至傳播到基督宗教尚未傳播到的地方;在許多國家中,他們廢除了那些與上帝的合一性及靈魂不朽的真正教義背道而馳的異教迷信。
耶穌基督完成了始於摩西的工作之後,他祈願上帝不僅僅是我們敬畏和崇拜的對象,也是我們熱愛和獻身的對象,這是顯而易見的。因而祂透過盼望使人幸福,使人在塵世中預先品嘗到未來極樂的滋味。因為沒有什麼比愛一個值得愛的事物更令人愜意歡愉的了。愛是一種精神狀態,它讓我們為我們所愛的對象的完美而欣喜萬分,沒有什麼比上帝更完美,也沒有什麼比在祂裡面更令人喜樂。去愛祂,用靈魂去默觀祂的完美,這其實很容易,因為我們只是在找回深埋於自己心裡的這些思想。上帝的完美就是我們靈魂深處的完美,但祂的完美是無邊無際的;祂是海洋,我們不過是祂恩賜的滄海一粟;在我們裡面,只有一些力量、一點知識、一絲善良;但在上帝裡面,能力、知識和善良皆是完備。秩序、比例、和諧,這些都令人愉悅;繪畫和音樂也是這些實例:上帝是所有秩序;祂總是保持比例的真實性,祂創造宇宙的和諧;一切美都是祂的真光的流溢。
由此可見,真正的虔誠,甚至真正的極樂存在於上帝的愛中,但這愛是如此地甦醒人心,以至於祂的熾熱激情總是伴隨著明悟洞察。這種愛在美善的行為中產生快樂滿足,足以慰藉美德;這種愛將一切與上帝作為中心加以連繫,將人性渡到神性那裡去。因為在履行職責時,當一個人服從理性,他就會遵行最高理性的秩序。一個人把自己的所有意圖都導向共同的善,這就是上帝的榮耀,無其他可媲美。因此,人們會發現,沒有比擁護社群利益更大的個人利益了;一個人透過甘心樂意為人類謀取真正的利益而獲得自我的滿足。一個人無論成功與否,他都會滿足於過往所發生的一切,因為一旦他順從了上帝的旨意,而且深知祂的旨意是最美善的。但在祂透過事件宣告祂的旨意之前,人們必須努力做那些看起來最符合祂命令的事情,如此方可領會祂的旨意。當我們處於這樣的心境時,我們不會因為艱難而沮喪氣餒,我們只會因自己的失誤而懊悔;人們的忘恩負義並不能讓我們溫良的性情懈怠片刻。我們的博愛慈善充滿謙遜和節制,這種慈善之心不會讓我們飛揚跋扈;我們細察自己的缺點,珍惜他人的才華;我們力求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我們必須盡自己所能的做得完美,不可加害於人。沒有仁愛,就沒有虔誠;沒有溫良仁慈,就不可能彰顯出誠摯的敬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