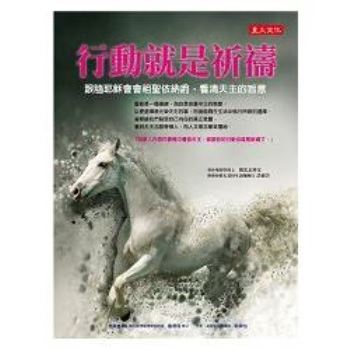著重鍛鍊的靈修方式
《神操》是由以下的一句話開始的:「神操這個名詞,是指任何省察、默想、默觀、口禱、心禱,以及下面要說的其他靈修神工」(神操1),「是為戰勝自己,整理自己的生活,使人不致因任何不正的心情,而決定自己的生活。」(神操21)。後面我會用體操的表達來說明,為何要將這些靈修神工稱為「神操」,由此可知我們要談的不是理論,而是鍛鍊。
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神操的文章,其中發揮了我的老師朱修德神父的一些看法。他認為,神操的重點在於培養一個中立的態度,以便做選擇,而後在生活中執行所做的選擇,因此做神操是為了「準備整理靈魂,驅除邪情,好能認清天主的聖意」(神操1)。當我們提到「認清天主的聖意」時,我們都認為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原因可能出在我們預設的樣本不太對勁。我們會以為天主已經對我的一生預先安排好一個完好的樣子,而我的任務是找到這個藍圖,以便照稿執行。但是我們從依納爵的眾多書信中,看到他在書信的尾端都寫道:「求天主讓我們體驗到祂對我們的旨意,並且忠實的實行它」。因此重要的不是知道,而是體驗。
如何找到天主的旨意?
天主的旨意應該是內在化的,不是在一個客觀的制度下外加給我的。我們不必在我之外尋找天主的旨意。天主在我內發聲,我與天主產生共鳴;祂在我內,這是唯一能找到祂的地方。我尋求的是天主此時此地對我的旨意,假如祂不在我內,假如我不被祂愛,那麼即使意識到天主的旨意,我也會沒什麼感動,或者感覺無能為力。只有當我體驗到,做了我所想的事,而天主會高興,而且我感到自己好像在祂面前站立得住的時候,這樣我才是找到了天主的旨意。
我們選擇的範圍是有限度的,如果用一張A4的紙張來比方,A4紙內的是可以選的各種可能,而這張A4紙的邊緣(界線)就是天主對我們行為的規範,例如十誡。在規範內的都可以執行,例如選擇結婚與否,做什麼行業…等等。另一個比方是,就像我們為了寫字工整而墊在白紙下面的格子墊板,那張有格線的墊板就像是耶穌的言行。我們不太可能和耶穌做一樣的事,因為時代不一樣,情況也大不相同。我們只能體會耶穌的心境,體驗到如果我這樣做,天主是否高興。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將這格子墊板(耶穌的言行)應用在生活中?尤其是我們的善念,常常會受到與之相反的意念的推動,因此,我們需要鍛鍊自己,以反對這些引誘我們遠離善願的意念,以便能碰觸到天主,而在這樣的碰觸中能體驗到祂的旨意。
使徒生活:決定選擇天主對我的召喚
使徒生活是人的生活方法之一,但這樣的生活不是單純的人的選擇(決定)。用依納爵的說法,這應該是一個被選定的決定,先決條件是主的召叫。若按《神操》的主張,一旦人開始做神操,就是有了一個主的召叫。同樣的,會參加基督生活團,也是因為體驗到一個召叫。因此在做神操的過程中,人都要好好的做選擇。
依納爵從蒙召到選擇的經驗
依納爵在悔改之初,對未來並沒有什麼計畫,他只想到耶路撒冷朝聖,用非常刻苦的方式前去。他希望能一輩子活在耶穌所生活過的地方,也在靈修生活上幫別人一點忙,或以言行讓非教友的旅行者獲得一些啟發。然而,令他出乎意料的是,方濟會的省會長取出了教宗的文件,告訴他不可以留在聖地生活,因為有許多安全上的顧慮。在知道無法留在聖地之後,他必須做另一個選擇:回到西班牙。
在他回西班牙的路程中,經過非常複雜的路段,路途遙遠,又遇上西班牙和法國的戰役,兩次被抓,經過千辛萬苦之後,終於回到西班牙。在這趟漫長的路途中,他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思考:他傾向先花一段時間讀書。後來我們從《自述小傳》中知道,這「一段時間」總共是十二年。這件事對後來教會的影響很大。
如果當時方濟會的會長沒有命令依納爵離開聖地,今天就不會有耶穌會的種種一切了。
選擇不是挑揀一個選項
依納爵在《神操》中使用了一個字: election 。這個字和option不同。option的意思是在一些可能性中挑選一個,而election在教會中有很豐富的背景。依納爵故意用了這個字,為了承繼教會內的豐富意涵。在《神操》第一週和第二週的過渡中,祈禱者要做〈耶穌君王的號召〉的默觀,人要答覆天主,若無法對此做答覆,便無法進入選擇,由此可見選擇先於派遣。
我們也從《舊約》的盟約來了解召選這件事。天主選亞巴郎,為了和他訂一個盟約,主召叫梅瑟也是為了藉著他與以色列建立盟約,這個盟約也包括以色列要做一個選擇。若蘇厄講得很清楚:「你們要選擇要侍奉哪一個神。或是你們的祖先在大河那邊所侍奉的神,或是本地的人所侍奉的神。你們要選哪一個呢?至於我,我和我的家人選擇侍奉上主。」一旦選擇了,就進入了愛的盟約。先知們常常是用婚姻關係來表達愛的盟約。如同一對相愛的人選擇了彼此,而建立愛的盟約一樣。做神操的人一旦開始做神操就進入了這個愛的盟約:「我們所願意、所選擇的,只是那更能引我們達到受造目的之事物」(神操23)。
以選擇回應愛的召喚
這個過程自有他辛苦的一面。不是要選擇那些從客觀角度來看是最好的,例如,傳統上認為修道才是最好的一條路。如果正確答案是選擇客觀上看起來最好的一條路,那就沒有什麼好選的了,反正大家都一樣,選那公認最好的就對了。然而我們所說的是:選擇對我此時此刻最好、最能配合天主旨意的。可以說,天主以祂的計畫來召喚我,而我以我的選擇去回應祂,這樣,我和天主之間互相訂立了愛的盟約。
選擇的困難在於權衡自身及生活周圍的情況,要了解自己的個性、考慮周全,做適切的、平衡的決定。不是以一般人眼中最好的目標為首選,不是齊頭式的,而是個別考慮,適合的就是最好的。
目標才是考慮的重點
有些人有聖召,但是生活情況並不允許,他可能需要照顧父母,所以可能是暫時和修會保持連繫,直到父母過世才入會。若是男性遇到類似的情形,他差不多是無法修道了,因為沒有人在五十歲才開始學拉丁文,才開始讀哲學、神學,為了能做神父。此時,可能就是做終身修士了。這樣的選擇不是因為個性,而是生活環境不能配合。因此,選擇時所考慮的不只是當時的情況,而是目標,最後的目標。不是做了這樣的選擇將給我開一條什麼樣的路,而是這條路將通到哪裡?會不會領我到達我受造的目的。
分辨神類
為了選擇生活方式,或為了選擇使徒工作,我們有相同的原則需要遵守,就是應該繼續不斷的分辨,我所做的是否是天主要我做的。我們從教會的歷史中可以看到許多不太理想的情況。哪一個才是耶穌的方法?
君士坦丁皇帝接受基督,因而全國都信了主,但其實這不是好的模式。方濟各.沙勿略去日本,以教宗代表的名義去交涉,想找中央負責人,而後聽到中國,知道中國是皇帝管的,於是想到中國找皇帝,因為只要皇帝接受了信仰,疆域下的人們就全都成了基督徒。這是想用權力來宣講福音,但這不符合福音的樣子。
利瑪竇說他打開了中國福傳的門,這可以接受,因為他和官方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使得福傳工作阻力減少,也許在鄉下就會用貧窮的方式宣講福音,若是如此,這就是一個可以使用的方法。因此從事使徒工作時,需要提防任何和錢、虛榮、權力有關的因素。不要太強調或依賴這些,它們也許在「開門」時可以用,但並不是宣講的方法。這點在《神操》的〈兩旗默想〉中說得很清楚。
我們應該反省的是,我們常常傾向要用比較「有效」的方法從事使徒工作,然而倒底是在哪方面有效力呢?我們常說教會該有「能見度」、「被看見」、「曝光率」,然而「曝光」是為了什麼?為了知名度?虛榮?還是福傳?這真的是耶穌的方法嗎?這一切都需要依靠分辨神類來權衡。
誰在攪動你的情緒?
另外一個要分辨的是頹喪和失望的情緒,也就是神枯。使徒工作也會有神枯,但我們不能因為神枯而停止。在我們的經驗中,每個生活團都經過很深的神枯期,藉著這個神枯卻得到淨化。每個團體都曾經有團員流失,而且流失的量是很可觀的。曾經參加過的成員比留下來的團員大約多五到十倍。這樣的神枯在使徒工作中是免不了的。
我們需要分辨這些失望和頹喪的感覺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主來的,或是從魔鬼來的?也許是善神在提醒我,我正在做什麼不對的事;或是聖神提醒我,耶穌在地上實行最多的美德是忍耐,所以常需要忍耐;或者遇到一個事實,惡神趁機向你說一些喪氣話,讓你失望、放棄。因此要注意的是,究竟是誰在攪動你的情緒?
《神操》是由以下的一句話開始的:「神操這個名詞,是指任何省察、默想、默觀、口禱、心禱,以及下面要說的其他靈修神工」(神操1),「是為戰勝自己,整理自己的生活,使人不致因任何不正的心情,而決定自己的生活。」(神操21)。後面我會用體操的表達來說明,為何要將這些靈修神工稱為「神操」,由此可知我們要談的不是理論,而是鍛鍊。
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神操的文章,其中發揮了我的老師朱修德神父的一些看法。他認為,神操的重點在於培養一個中立的態度,以便做選擇,而後在生活中執行所做的選擇,因此做神操是為了「準備整理靈魂,驅除邪情,好能認清天主的聖意」(神操1)。當我們提到「認清天主的聖意」時,我們都認為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原因可能出在我們預設的樣本不太對勁。我們會以為天主已經對我的一生預先安排好一個完好的樣子,而我的任務是找到這個藍圖,以便照稿執行。但是我們從依納爵的眾多書信中,看到他在書信的尾端都寫道:「求天主讓我們體驗到祂對我們的旨意,並且忠實的實行它」。因此重要的不是知道,而是體驗。
如何找到天主的旨意?
天主的旨意應該是內在化的,不是在一個客觀的制度下外加給我的。我們不必在我之外尋找天主的旨意。天主在我內發聲,我與天主產生共鳴;祂在我內,這是唯一能找到祂的地方。我尋求的是天主此時此地對我的旨意,假如祂不在我內,假如我不被祂愛,那麼即使意識到天主的旨意,我也會沒什麼感動,或者感覺無能為力。只有當我體驗到,做了我所想的事,而天主會高興,而且我感到自己好像在祂面前站立得住的時候,這樣我才是找到了天主的旨意。
我們選擇的範圍是有限度的,如果用一張A4的紙張來比方,A4紙內的是可以選的各種可能,而這張A4紙的邊緣(界線)就是天主對我們行為的規範,例如十誡。在規範內的都可以執行,例如選擇結婚與否,做什麼行業…等等。另一個比方是,就像我們為了寫字工整而墊在白紙下面的格子墊板,那張有格線的墊板就像是耶穌的言行。我們不太可能和耶穌做一樣的事,因為時代不一樣,情況也大不相同。我們只能體會耶穌的心境,體驗到如果我這樣做,天主是否高興。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將這格子墊板(耶穌的言行)應用在生活中?尤其是我們的善念,常常會受到與之相反的意念的推動,因此,我們需要鍛鍊自己,以反對這些引誘我們遠離善願的意念,以便能碰觸到天主,而在這樣的碰觸中能體驗到祂的旨意。
使徒生活:決定選擇天主對我的召喚
使徒生活是人的生活方法之一,但這樣的生活不是單純的人的選擇(決定)。用依納爵的說法,這應該是一個被選定的決定,先決條件是主的召叫。若按《神操》的主張,一旦人開始做神操,就是有了一個主的召叫。同樣的,會參加基督生活團,也是因為體驗到一個召叫。因此在做神操的過程中,人都要好好的做選擇。
依納爵從蒙召到選擇的經驗
依納爵在悔改之初,對未來並沒有什麼計畫,他只想到耶路撒冷朝聖,用非常刻苦的方式前去。他希望能一輩子活在耶穌所生活過的地方,也在靈修生活上幫別人一點忙,或以言行讓非教友的旅行者獲得一些啟發。然而,令他出乎意料的是,方濟會的省會長取出了教宗的文件,告訴他不可以留在聖地生活,因為有許多安全上的顧慮。在知道無法留在聖地之後,他必須做另一個選擇:回到西班牙。
在他回西班牙的路程中,經過非常複雜的路段,路途遙遠,又遇上西班牙和法國的戰役,兩次被抓,經過千辛萬苦之後,終於回到西班牙。在這趟漫長的路途中,他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思考:他傾向先花一段時間讀書。後來我們從《自述小傳》中知道,這「一段時間」總共是十二年。這件事對後來教會的影響很大。
如果當時方濟會的會長沒有命令依納爵離開聖地,今天就不會有耶穌會的種種一切了。
選擇不是挑揀一個選項
依納爵在《神操》中使用了一個字: election 。這個字和option不同。option的意思是在一些可能性中挑選一個,而election在教會中有很豐富的背景。依納爵故意用了這個字,為了承繼教會內的豐富意涵。在《神操》第一週和第二週的過渡中,祈禱者要做〈耶穌君王的號召〉的默觀,人要答覆天主,若無法對此做答覆,便無法進入選擇,由此可見選擇先於派遣。
我們也從《舊約》的盟約來了解召選這件事。天主選亞巴郎,為了和他訂一個盟約,主召叫梅瑟也是為了藉著他與以色列建立盟約,這個盟約也包括以色列要做一個選擇。若蘇厄講得很清楚:「你們要選擇要侍奉哪一個神。或是你們的祖先在大河那邊所侍奉的神,或是本地的人所侍奉的神。你們要選哪一個呢?至於我,我和我的家人選擇侍奉上主。」一旦選擇了,就進入了愛的盟約。先知們常常是用婚姻關係來表達愛的盟約。如同一對相愛的人選擇了彼此,而建立愛的盟約一樣。做神操的人一旦開始做神操就進入了這個愛的盟約:「我們所願意、所選擇的,只是那更能引我們達到受造目的之事物」(神操23)。
以選擇回應愛的召喚
這個過程自有他辛苦的一面。不是要選擇那些從客觀角度來看是最好的,例如,傳統上認為修道才是最好的一條路。如果正確答案是選擇客觀上看起來最好的一條路,那就沒有什麼好選的了,反正大家都一樣,選那公認最好的就對了。然而我們所說的是:選擇對我此時此刻最好、最能配合天主旨意的。可以說,天主以祂的計畫來召喚我,而我以我的選擇去回應祂,這樣,我和天主之間互相訂立了愛的盟約。
選擇的困難在於權衡自身及生活周圍的情況,要了解自己的個性、考慮周全,做適切的、平衡的決定。不是以一般人眼中最好的目標為首選,不是齊頭式的,而是個別考慮,適合的就是最好的。
目標才是考慮的重點
有些人有聖召,但是生活情況並不允許,他可能需要照顧父母,所以可能是暫時和修會保持連繫,直到父母過世才入會。若是男性遇到類似的情形,他差不多是無法修道了,因為沒有人在五十歲才開始學拉丁文,才開始讀哲學、神學,為了能做神父。此時,可能就是做終身修士了。這樣的選擇不是因為個性,而是生活環境不能配合。因此,選擇時所考慮的不只是當時的情況,而是目標,最後的目標。不是做了這樣的選擇將給我開一條什麼樣的路,而是這條路將通到哪裡?會不會領我到達我受造的目的。
分辨神類
為了選擇生活方式,或為了選擇使徒工作,我們有相同的原則需要遵守,就是應該繼續不斷的分辨,我所做的是否是天主要我做的。我們從教會的歷史中可以看到許多不太理想的情況。哪一個才是耶穌的方法?
君士坦丁皇帝接受基督,因而全國都信了主,但其實這不是好的模式。方濟各.沙勿略去日本,以教宗代表的名義去交涉,想找中央負責人,而後聽到中國,知道中國是皇帝管的,於是想到中國找皇帝,因為只要皇帝接受了信仰,疆域下的人們就全都成了基督徒。這是想用權力來宣講福音,但這不符合福音的樣子。
利瑪竇說他打開了中國福傳的門,這可以接受,因為他和官方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使得福傳工作阻力減少,也許在鄉下就會用貧窮的方式宣講福音,若是如此,這就是一個可以使用的方法。因此從事使徒工作時,需要提防任何和錢、虛榮、權力有關的因素。不要太強調或依賴這些,它們也許在「開門」時可以用,但並不是宣講的方法。這點在《神操》的〈兩旗默想〉中說得很清楚。
我們應該反省的是,我們常常傾向要用比較「有效」的方法從事使徒工作,然而倒底是在哪方面有效力呢?我們常說教會該有「能見度」、「被看見」、「曝光率」,然而「曝光」是為了什麼?為了知名度?虛榮?還是福傳?這真的是耶穌的方法嗎?這一切都需要依靠分辨神類來權衡。
誰在攪動你的情緒?
另外一個要分辨的是頹喪和失望的情緒,也就是神枯。使徒工作也會有神枯,但我們不能因為神枯而停止。在我們的經驗中,每個生活團都經過很深的神枯期,藉著這個神枯卻得到淨化。每個團體都曾經有團員流失,而且流失的量是很可觀的。曾經參加過的成員比留下來的團員大約多五到十倍。這樣的神枯在使徒工作中是免不了的。
我們需要分辨這些失望和頹喪的感覺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主來的,或是從魔鬼來的?也許是善神在提醒我,我正在做什麼不對的事;或是聖神提醒我,耶穌在地上實行最多的美德是忍耐,所以常需要忍耐;或者遇到一個事實,惡神趁機向你說一些喪氣話,讓你失望、放棄。因此要注意的是,究竟是誰在攪動你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