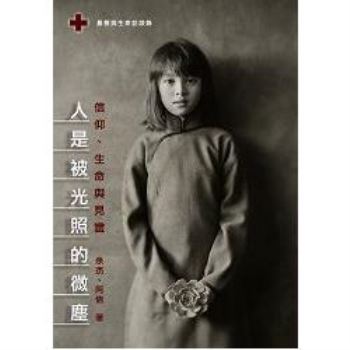基督徒理應成為捍衛人權的先鋒
—基督徒媒體人、人權活動家楊憲宏訪談
楊憲宏簡歷
1953 年生於臺灣彰化縣,資深媒體人、人權活動家,「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創會理事長、臺灣中央廣播電台第五屆常務董事兼《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節目主持人。
楊憲宏自臺北醫學院牙醫學系畢業後,考入臺灣大學醫學研究所,1981 年取得生理學碩士的資格,旋即赴美,進入柏克萊加州大學專攻公共衛生碩士。在臺大唸研究所時,便在《民生報》擔任醫藥版編輯,後轉為專欄組記者;赴美學成歸國後,歷任《聯合報》採訪組副主任、《首都早報》副總編輯、《中時晚報》資深記者室主任、《人間雜誌》總編輯、《首都早報》副總編輯、民間全民電視公司(民視)新聞部經理、三立影視總經理室總顧問、《Taiwan News》總編輯、臺灣數位資訊協會理事、法務部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動小組成員。
作為基督徒和人權活動家,楊憲宏長期關注中國的人權和宗教自由狀況,在電臺節目中常與中國民主人權人士越洋對話,力促臺灣政府和民間聲援中國人權。2011 年5 月14 日,楊憲宏參與創設「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並出任首任理事長。他主張臺灣應用民主人權、自由法治來跟中國大陸交往,強調民主、人權、自由和法治是「臺灣唯一的籌碼」,並倡議「人權標準」應納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談判。
楊憲宏的主要著作有:《走過傷心地:一個記者的公害現場觀察筆記》、《公害政治學:楊憲宏臺灣環境筆記》、《羊入狼群:知識分子的原力與本懷》等。還曾參與多部電視紀錄片的策畫製作。曾獲「曾虛白先生公共服務報導獎 」、「吳三連獎報導文學類」等重要獎項。
採訪緣起
我在北京生活期間,常常接受楊憲宏的越洋電話訪問,有時候電話突然被切斷,再換其他電話,如此者反覆多次。楊憲宏告訴我,這是他採訪中國異議人士時經常遇到的情況,他已視之為家常便飯。
後來,我到臺灣訪問,有機會與楊憲宏會面,並到圓山的央廣總部接受他的採訪。在臺灣的知識分子中,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人本來就不多,像楊憲宏這樣長期地、持之以恆地關注的人更少。因此,我們成了朋友。楊憲宏是一位既可伏案寫作、下筆千言的作家和記者,也是一位奔走呼號、運籌帷幄的社會活動家。基督信仰是他關心人權和自由議題的動力,也是他生命中最深沉厚重的依託,即便在宗教信仰自由的臺灣,像他這樣在公共領域彰顯信仰的基督徒亦寥寥可數。所以,我便產生了訪問他的想法。
2013 年春,我第三次訪問臺灣,並有較長時間的停留。在此期間,我不僅再度赴央廣接受楊憲宏的訪問,也與他約定時間,在誠品書店的咖啡廳中跟他有一段長談。這一次,我與他位置發生了有趣的更替:我成了訪問者,他成了被訪問者;我提問,他回答。這是我們交往的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場景。此後,我們又多次通話和通電郵,補充新的觀點和材料,遂有此篇訪談。
從我媽媽的信仰到我自己的信仰
余杰:楊先生,你採訪過我很多次,今天輪到我來採訪你了。當然,你也接受過很多次訪問,不過,我訪問的重點在於信仰。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基督信仰的?跟你的家族有關嗎?
楊憲宏:是的,在我的家族中,從曾祖父、曾祖母那代人開始就是基督徒。我考察家族的歷史時發現,在十九世紀末,西方宣教士藍大衛來到彰化,跟我的曾祖父那一代人有了接觸,向他們傳福音,他們成了當地最早一批長老會會友。
當時,我們家是當地的一個大家族,開放家庭當作聚會場所,引起其他民間宗教團體的抗議,甚至有人到我家潑大便。可見,當時臺灣對於基督信仰相當排斥。
我查詢彰化基督教醫院的檔案,發現我們家族與這個醫院有十分密切的關係,醫院的土地就是祖父、母他們捐助的,他們在逼迫中持守信仰,並熱心公益事業。
我的祖父名叫楊木,跟賴和同屬一個詩社「應社」。我在《應社詩抄》中發現一張有詩社八個同仁的照片,其中就有祖父在裡面。與賴和一樣,祖父是醫生,也是當地的意見領袖。同時也是基督教傳播的先驅,他認為基督教對臺灣非常需要,臺灣是一個由逃難者組成的社會,逃難者身上根植著一種深深的不安的心態,需要基督信仰來安慰和憐憫。再往上追溯家族的歷史,我們楊氏家族,曾在與陳家的械鬥中,整個家族都被滅族,只剩下一個女孩子,藏在水田沒有死亡。後來,她被葉家帶走,當作童養媳養大。生了孩子以後,葉家把最後一個男孩冠以楊姓,以便讓楊家傳承下去。後來,這一支楊家,絕不跟姓陳的通婚(因為是仇敵),也不能跟姓葉的通婚(因為是近親)。
在當時的生活環境下,信仰顯得異常重要。如果唯讀中國的詩書,人們心中仍然覺得空虛。在時代的動盪不安中,臺灣沒有國家的觀念,只有家族的觀念,差不多算是一個氏族社
會。臺灣人沒有國可以治理,更不用說天下了。
余杰:新教傳教士到臺灣,比到中國大陸早兩百多年。你們家也算是傳教士在臺灣結出的最早的一批「果子」。
楊憲宏:我清楚地記得,小時候跟第二代的藍醫生(藍大弼)見過。他在臺灣長大,父親藍大衛希望他用醫療的方式傳道,等他成年後帶他回倫敦學習四年的醫學。那時,我祖父是彰化的名醫,他義務幫藍大衛出任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等四年後藍大衛回來,再將醫院交給對方。可見,他們之間情深意重。
祖父開醫院時,若有病人沒有錢付診費和藥費,他就答應他們寫張欠條。年底,他派護士或會計,根據借條,一家家地去訪問,看他們有沒有辦法還錢。大部分都收不到錢,於是,過年的時候他就一把火把借據都燒掉了。過年前一個月,是祖父義診的時間。基於基督信仰中十一奉獻的觀念,他利用這段時間無償地為窮人提供服務。
當時,長輩都有穩定的宗教生活。父親和母親固定參加教會的禮拜,也有家庭的禮拜。家庭敬拜的形式,跟一般的禮拜差不多。禮拜是主日,除了主日之外,牧師也會在一個星期內安排時間,到一個個的家庭中探訪,並帶領全家敬拜。家庭敬拜的規模相對小,不一定有鋼琴,大家便清唱讚美詩,還有讀經、禱告等。
小時候,我印象最深的是過耶誕節,那一天我們這些孩子都可以晚睡、甚至可以不回家。一般是晚上十一點到教會集合,我們家有五個孩子,大姐、二姐、大哥、三姐,還有最小的我,我們排著隊,到處敲門,給鄉親們唱聖歌、報佳音。還有一個深刻的童年記憶是,我的爸爸是醫生,同時很熱愛音樂。週末,他教我們五個孩子合唱德國、日本的讚美詩。我們家有一部手搖的留聲機,可以放黑色石英板的唱片。我們邊聽邊唱,有時候是我來搖動留聲機。
我們唱的大多都是聖歌,用台語唱。我母親是日本人,她用日語唱,她讀日文的聖經。大人讀聖經時,我也慢慢跟著讀,感覺到聖經中有一種巨大的力量。我學會了禱告,禱告真的很有用。大人跟我講,很多事情不是我們的智慧能決定的,所有的都要交給上帝我在教會也上主日學課程,聽到幾乎所有的聖經故事。不過,雖然知道這些故事的來龍去脈,但並不明白故事背後的聖經真理。
……(未完)
—基督徒媒體人、人權活動家楊憲宏訪談
楊憲宏簡歷
1953 年生於臺灣彰化縣,資深媒體人、人權活動家,「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創會理事長、臺灣中央廣播電台第五屆常務董事兼《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節目主持人。
楊憲宏自臺北醫學院牙醫學系畢業後,考入臺灣大學醫學研究所,1981 年取得生理學碩士的資格,旋即赴美,進入柏克萊加州大學專攻公共衛生碩士。在臺大唸研究所時,便在《民生報》擔任醫藥版編輯,後轉為專欄組記者;赴美學成歸國後,歷任《聯合報》採訪組副主任、《首都早報》副總編輯、《中時晚報》資深記者室主任、《人間雜誌》總編輯、《首都早報》副總編輯、民間全民電視公司(民視)新聞部經理、三立影視總經理室總顧問、《Taiwan News》總編輯、臺灣數位資訊協會理事、法務部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動小組成員。
作為基督徒和人權活動家,楊憲宏長期關注中國的人權和宗教自由狀況,在電臺節目中常與中國民主人權人士越洋對話,力促臺灣政府和民間聲援中國人權。2011 年5 月14 日,楊憲宏參與創設「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並出任首任理事長。他主張臺灣應用民主人權、自由法治來跟中國大陸交往,強調民主、人權、自由和法治是「臺灣唯一的籌碼」,並倡議「人權標準」應納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談判。
楊憲宏的主要著作有:《走過傷心地:一個記者的公害現場觀察筆記》、《公害政治學:楊憲宏臺灣環境筆記》、《羊入狼群:知識分子的原力與本懷》等。還曾參與多部電視紀錄片的策畫製作。曾獲「曾虛白先生公共服務報導獎 」、「吳三連獎報導文學類」等重要獎項。
採訪緣起
我在北京生活期間,常常接受楊憲宏的越洋電話訪問,有時候電話突然被切斷,再換其他電話,如此者反覆多次。楊憲宏告訴我,這是他採訪中國異議人士時經常遇到的情況,他已視之為家常便飯。
後來,我到臺灣訪問,有機會與楊憲宏會面,並到圓山的央廣總部接受他的採訪。在臺灣的知識分子中,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人本來就不多,像楊憲宏這樣長期地、持之以恆地關注的人更少。因此,我們成了朋友。楊憲宏是一位既可伏案寫作、下筆千言的作家和記者,也是一位奔走呼號、運籌帷幄的社會活動家。基督信仰是他關心人權和自由議題的動力,也是他生命中最深沉厚重的依託,即便在宗教信仰自由的臺灣,像他這樣在公共領域彰顯信仰的基督徒亦寥寥可數。所以,我便產生了訪問他的想法。
2013 年春,我第三次訪問臺灣,並有較長時間的停留。在此期間,我不僅再度赴央廣接受楊憲宏的訪問,也與他約定時間,在誠品書店的咖啡廳中跟他有一段長談。這一次,我與他位置發生了有趣的更替:我成了訪問者,他成了被訪問者;我提問,他回答。這是我們交往的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場景。此後,我們又多次通話和通電郵,補充新的觀點和材料,遂有此篇訪談。
從我媽媽的信仰到我自己的信仰
余杰:楊先生,你採訪過我很多次,今天輪到我來採訪你了。當然,你也接受過很多次訪問,不過,我訪問的重點在於信仰。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基督信仰的?跟你的家族有關嗎?
楊憲宏:是的,在我的家族中,從曾祖父、曾祖母那代人開始就是基督徒。我考察家族的歷史時發現,在十九世紀末,西方宣教士藍大衛來到彰化,跟我的曾祖父那一代人有了接觸,向他們傳福音,他們成了當地最早一批長老會會友。
當時,我們家是當地的一個大家族,開放家庭當作聚會場所,引起其他民間宗教團體的抗議,甚至有人到我家潑大便。可見,當時臺灣對於基督信仰相當排斥。
我查詢彰化基督教醫院的檔案,發現我們家族與這個醫院有十分密切的關係,醫院的土地就是祖父、母他們捐助的,他們在逼迫中持守信仰,並熱心公益事業。
我的祖父名叫楊木,跟賴和同屬一個詩社「應社」。我在《應社詩抄》中發現一張有詩社八個同仁的照片,其中就有祖父在裡面。與賴和一樣,祖父是醫生,也是當地的意見領袖。同時也是基督教傳播的先驅,他認為基督教對臺灣非常需要,臺灣是一個由逃難者組成的社會,逃難者身上根植著一種深深的不安的心態,需要基督信仰來安慰和憐憫。再往上追溯家族的歷史,我們楊氏家族,曾在與陳家的械鬥中,整個家族都被滅族,只剩下一個女孩子,藏在水田沒有死亡。後來,她被葉家帶走,當作童養媳養大。生了孩子以後,葉家把最後一個男孩冠以楊姓,以便讓楊家傳承下去。後來,這一支楊家,絕不跟姓陳的通婚(因為是仇敵),也不能跟姓葉的通婚(因為是近親)。
在當時的生活環境下,信仰顯得異常重要。如果唯讀中國的詩書,人們心中仍然覺得空虛。在時代的動盪不安中,臺灣沒有國家的觀念,只有家族的觀念,差不多算是一個氏族社
會。臺灣人沒有國可以治理,更不用說天下了。
余杰:新教傳教士到臺灣,比到中國大陸早兩百多年。你們家也算是傳教士在臺灣結出的最早的一批「果子」。
楊憲宏:我清楚地記得,小時候跟第二代的藍醫生(藍大弼)見過。他在臺灣長大,父親藍大衛希望他用醫療的方式傳道,等他成年後帶他回倫敦學習四年的醫學。那時,我祖父是彰化的名醫,他義務幫藍大衛出任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等四年後藍大衛回來,再將醫院交給對方。可見,他們之間情深意重。
祖父開醫院時,若有病人沒有錢付診費和藥費,他就答應他們寫張欠條。年底,他派護士或會計,根據借條,一家家地去訪問,看他們有沒有辦法還錢。大部分都收不到錢,於是,過年的時候他就一把火把借據都燒掉了。過年前一個月,是祖父義診的時間。基於基督信仰中十一奉獻的觀念,他利用這段時間無償地為窮人提供服務。
當時,長輩都有穩定的宗教生活。父親和母親固定參加教會的禮拜,也有家庭的禮拜。家庭敬拜的形式,跟一般的禮拜差不多。禮拜是主日,除了主日之外,牧師也會在一個星期內安排時間,到一個個的家庭中探訪,並帶領全家敬拜。家庭敬拜的規模相對小,不一定有鋼琴,大家便清唱讚美詩,還有讀經、禱告等。
小時候,我印象最深的是過耶誕節,那一天我們這些孩子都可以晚睡、甚至可以不回家。一般是晚上十一點到教會集合,我們家有五個孩子,大姐、二姐、大哥、三姐,還有最小的我,我們排著隊,到處敲門,給鄉親們唱聖歌、報佳音。還有一個深刻的童年記憶是,我的爸爸是醫生,同時很熱愛音樂。週末,他教我們五個孩子合唱德國、日本的讚美詩。我們家有一部手搖的留聲機,可以放黑色石英板的唱片。我們邊聽邊唱,有時候是我來搖動留聲機。
我們唱的大多都是聖歌,用台語唱。我母親是日本人,她用日語唱,她讀日文的聖經。大人讀聖經時,我也慢慢跟著讀,感覺到聖經中有一種巨大的力量。我學會了禱告,禱告真的很有用。大人跟我講,很多事情不是我們的智慧能決定的,所有的都要交給上帝我在教會也上主日學課程,聽到幾乎所有的聖經故事。不過,雖然知道這些故事的來龍去脈,但並不明白故事背後的聖經真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