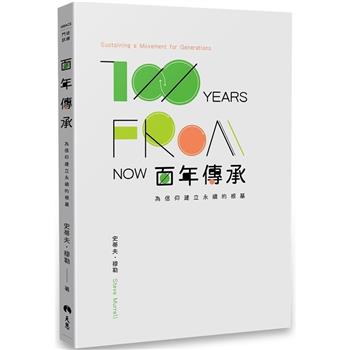Chapter
09╱ 聖經與護照
The Bible and the Passport
上帝只有一個兒子,
祂卻使祂成了宣教士。
大衛.李文斯頓
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
馬可福音16:15b
萬民教會的存在是為了榮耀神,在萬民中建立以基督為中心、被聖靈充滿,且承擔社會責任的教會和校園事工。目前,我們還沒有在每個國家都建立教會,但我們終究會實現這個目標,每一次,都是從一位宣教士,和一個國家開始。
1980年春天,當時我才二十歲,就讀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企業管理系,當時我的職業規劃是去亞洲闖出一番天地。同一年,我和幾位朋友報名參加了亞特蘭大的某個週末學生宣教特會。我已經忘了誰是講員,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句經文:「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見詩2:8)
剛分享完信息,他就邀請在場的學生都跪下禱告,向神求一個國家。當我們跪下、臉伏於地的時候,講員繼續說:「現在向神求你的產業,求神給你一個國家。」
我不知道別人當時做了什麼,但我照著所聽見的去做了,我向神求一個國家。在那神聖的靜默時刻,我想我聽見神開口說:「緬甸」。
伴隨著舒緩的音樂、零落的啜泣聲和靜默的禱告,講員繼續說到:「你們當中有人將成為宣教士,到神放在你心中的國家去,你會住在那地,直到離世。有些人會成為某個國家的禱告宣教士,有些人會成為某個國家的財務宣教士。」
我從來沒聽說過「禱告宣教士」或「財務宣教士」,我只知道,神好像把緬甸放在我的心中。「我應該輟學去緬甸嗎?天哪!我該怎麼跟我爸媽交代?」
這時,講員解釋說:我們沒有要輟學,直接買機票飛去異國。但他希望我們在這個學期剩下的八週中,為神放在我們心中的國家懇切禱告。我照做了。八週後,「緬甸」還是留在我的心中。我一個緬甸人也不認識,但在為他們禱告了幾個月之後,我愛上了他們。這就是禱告的功效!
二十年後,也就是1999年,我和我十二歲的兒子乘坐從馬尼拉飛往緬甸的航班,去拜訪新建立的仰光萬民教會。在為緬甸人禱告多年後,終於有機會拜訪這個國家的感覺十分奇妙。我們菲律賓宣教士的工作成績十分優秀,短短幾年內,牧養管理教會的接力棒,就被交到幾位年輕有為的緬甸領袖手中,他們將這個教會提升到新的層次,也協助在鄰近的寮國建立萬民教會。
一本聖經、一本護照
雖然我不太清楚我和底波拉究竟是如何明白的,但是,當我們降落在馬尼拉,成為「意外的宣教士」時,我們就知道,我們正在建立的教會,會是一間差派宣教士的教會。
第一眼看下來,這群菲律賓學生是最不可能去列國宣教的人,很多人甚至連飛機都沒坐過。只有少數曾離開呂宋島的馬尼拉,去外地探險。沒有人有護照,更別說簽證了。但是神喜歡「揀選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見林前1:27)。用「愚拙」和「軟弱」來形容當時的我們,簡直再合適不過。
為了幫助學生們稍微有一點世界觀,我們將一張來自《國家地理雜誌》的破舊世界地圖,釘在陰暗、骯髒的地下室會堂牆上。大多數學生都在天主教環境中長大,進入教堂時都習慣用手沾一點聖水。我們這裡沒有聖水,而是創造了新的教會傳統:讓學生們按手在世界地圖上,按照詩篇二章8節來為列
國禱告—「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當學生們順著台階,走進地下室敬拜神時(這經常會讓我想起,初代教會的基督徒也常常在地下墓穴裡敬拜神),他們會為中國、俄羅斯、印度、伊朗、以色列和美國禱告,尤其是加州和佛羅里達,就是迪士尼樂園和另一間迪士尼樂園的所在地。
我們知道,從開始就對新教會和新信徒傳遞世界宣教的異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我們讓「世界宣教」成為初信造就課程的中心。菲律賓學生一信主,我們就帶他讀馬太福音的最後一章,向他們解釋何為「大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首先,我們要把「權柄」說清楚:「從此刻起,耶穌就是你生命最終的權柄。祂擁有所有的權柄,而你沒有。祂說什麼,你就做什麼。不抱怨,也不討價還價。『所有的權柄』意味著祂是主。明白了嗎?」當我們把「權柄」說清楚之後,我們接著講下一點。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我們繼續引導新信徒:「為了成為一名好基督徒,你需要兩樣東西:聖經和護照。你需要聖經來認識神,每天最重要的是要讀神的話。你還需要護照,這樣就可以順服神的呼召。如果你要『使萬民作主門徒』,則會需要護照,才能到其他國家。如果你是認真要做耶穌的門徒,那麼,今天就去買一本聖經,然後趕快去申請護照。」我們真的就這樣告訴新信徒,猜猜發生了什麼?這些貧困的菲律賓學生都有護照了!而且護照上的海關章一個接一個地增加。一開始,我們派了一個短宣隊去印尼,然後去了日本,再去了中國,這幾個短宣隊的人幾週後都回來了。最後,我們差派出去的隊伍好幾年都沒有回來,先是孟加拉,再來是俄羅斯、拉托維亞、泰國、越南、緬甸、阿富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西班牙和其他許多國家。
我們必須走進列國,因為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死在十架上,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見啟5:9)。使徒約翰在他年老時,曾看見天堂的異象,他看到「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見啟7:9)。如果天堂中的人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那麼,就必須有人先去「各國各族各民各方」傳福音、帶門徒、建立教會。
如今的「萬民」是什麼意思?
當剩下的十一位門徒聽到大使命—「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時,他們就將福音帶到當時世上所知最遠的地方。教會歷史告訴我們,彼得去了羅馬,馬太去了衣索比亞,巴多羅買去了土耳其和亞美尼亞,安得烈去了希臘,多馬去了印度,猶大去了伊朗。為了去這些遙遠的地方傳福音,他們有的步行,有
的坐船,有的騎駱駝。對當時的人來說,這就是「萬民」。那麼,對我們來說,現在「萬民」意味著什麼呢?
目前地球上住著超過七十億人。除非你主修數學,否則,對你來說七十億會是個很難理解的數字。對於我們當中某些有數學障礙的人來說,我們可以把世界想像成只有十個人的村落,這個村莊中有一個非洲人、一個歐洲人、一個拉丁美洲人、一個北美人和六個亞洲人。這六個亞洲人中有兩個中國人、兩個印度人、一個中東人和另一個亞洲人(菲律賓人、寮國人、泰國人或其他亞裔)。
在這個村莊中,有四個人擁有收音機,兩個人有車,村莊裡有一部電話和一台電腦。有兩個人住得比較寬敞,四個人有安全的水可以喝,一個人比較胖(可能是北美人),五個人正在挨餓,五個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兩美元。每一年的最後,會有一個人死去,兩個人出生,這個村子的總人口會增加到十一
人。
現在,讓我們回到現實生活中的七十億人口,目前的宗教分佈是這樣的:有二十億人—32%,會在填問卷時勾選自己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的各種宗派,以及廣義上被稱為「基督教」的其他群體。這些人當中,有的是全心全意跟隨耶穌的門徒,有的則有名無實。有十三億人—22%是穆斯林。和基督徒很像,有的人是虔誠的穆斯林,而有的沒有那麼虔誠。有九億人—15%是沒有信仰的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和懷疑論者。有八億人—14%是印度教徒。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宗教如猶太教、錫克教或部落宗教占了10%的人口。有四億人—7%是佛教徒。現在的世界看起來是這樣的。
要有人去
就目前來看,地球上基督徒最少的十二個國家是:阿富汗、阿爾及利亞、孟加拉、不丹、柬埔寨、伊朗、尼泊爾、索馬利亞、泰國、土耳其、突尼西亞和葉門。這些國家中,信耶穌基督的人連1%都不到。我寫這個章節的時候,萬民教會的同工已經在這十二個國家當中的七個建立教會。這很棒,但誰願意去另外五個國家呢?誰願意背上十字架跟隨耶穌,去往阿爾及利亞、不丹、索馬利亞、突尼西亞和葉門呢?
慈善家兼宣教士威廉.波頓(第十六章會更多提到他的故事)對「宣教動員」提出見解。他常常用這段反問句來闡明他的觀點:「如果有十個人扛著一根木棍,九個人扛著輕的一端,一個人舉著重的另一端,那麼,你會幫忙扛哪一端?」那些世上未曾聽過福音的穆斯林、印度教和佛教國家顯然代表著世界宣教中「重的一端」,而且很少有人去扛這個重擔。
目前,萬民教會在六十五個國家都有植堂,但誰願意去開拓另外的一百三十一個國家呢?誰願意去舉起「重的一端」?誰願意去北非的摩洛哥、利比亞和馬利?誰願意去南美的智利、巴拉圭和烏拉圭?誰願意去東非的肯亞、盧安達和衣索比亞?誰願意去歐洲的挪威、羅馬尼亞和義大利?誰願意去中亞
的哈薩克、塔吉克和烏茲別克?也許我們都需要跪下來,向神求一個國家。但是,在我們這樣做之前,我們應當借鑒摩拉維亞兄弟會創始人欽岑多夫的態度,他曾說:
「我只有一種熱情,就是為祂,單單為祂。
世界就是禾場,禾場就是世界。從此以後,
那個我要為基督贏得靈魂的國家,就是我的家鄉。」
但如果千千萬萬的人開始走向列國,那麼光是機票就需要花不少錢。
要有人供應
「爸,我們有個好主意!」我三個兒子的臉上因著喜樂發出光來。
「夥計們,有什麼好主意?」
「今年聖誕節,我們應該一起去美國。然後就可以打雪仗了。」
我的孩子都在熱帶地區長大,所以他們總是盼望能有個白色聖誕,是美國版的皚皚白雪,而不是白色的沙灘。他們在菲律賓美麗的沙灘上度過了許多白色耶誕節。但現在,他們盼望著冰天雪地的白色。
「這個主意很有意思,」我回答,試著用一個有創意的說法讓他們知道這不太可能。「但是,會有個問題。」
「爸,什麼問題?」他們異口同聲,身體前傾,仿佛正有雪花飛舞在他們眼前一般。
「親戚們住的密西西比或喬治亞不會下雪。」
「沒關係,我們也可以去加拿大!」
「好吧,事實上,那會有另一個問題,得有人付錢啊!」從某種角度來說,在我與兒子們對話的那一刻,我們都學到了一個功課:就是美夢常常被拮据的現實碾碎。
這對他們來說,這真的是個好主意。跳上飛機,在美國待幾天,從寵愛他們的祖父母、叔叔阿姨和表兄弟手上收到成堆的禮物。然後去加拿大,扔扔雪球。一週後回馬尼拉。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是有個問題,這個老問題就是—錢。想出美好的聖誕度假計畫很容易,但付不付得起卻是個難題。需要有人計算成本、擔起責任、付錢。如果我們想進入更多國家,差派更多宣教士,那麼我們就需要花更多的錢。
我不建議任何人,像我們1984年那樣「毫無準備、身無分文」地出去,但我也不希望人只是坐在那裡什麼都不做,一直等待所有的財物支援出現。有的時候,如果我們想要進入列國,就必須要採取勇敢、犧牲的信心跨越過去。史蒂夫.艾迪生(Steve Addison)在他著名的《改變世界的運動》8 一書中
描述了信心的作用:
教會歷史並不是由家財萬貫、資源綽綽的個人和
機構組成,而是由與永生神相遇並以信心回應的弟兄
姊妹所組成。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心靈願意,但錢包軟弱
近期,我與一位知名的宣教領袖聊天,我們談到彼此都對建立宣教差派型教會充滿熱情。我們為著許多門徒願意走出去而喜樂,但也為著少有教會願意差派宣教感到哀傷。
宣教資金缺乏是個全球性問題,對其他宗教來說也不罕見。在許多國家,不計其數的信徒抓住大使命這個異象,他們準備好要去列國傳福音。但,就像我回答兒子的聖誕度假計畫一樣,有一個問題:需要有人買單!世界宣教的工價是昂貴的。
兩千年前,使徒保羅問: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 (羅10:14-15)
我想在保羅的提問清單後再加幾個問題:如果沒人奉獻,何來差派?如果教會不拿出宣教基金,他們該如何買機票?如果牧師沒有在教會預算中將世界宣教基金視為優先,宣教士從哪裡獲得財務支援呢?
除了很重要的錢以外,要完成大使命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要有人禱告
每個信仰的人都知道禱告很重要,但我們要為什麼禱告?耶穌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祂希望我們把下列事項放在禱告清單中:「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見可11:17)不要忽略最後的「萬國」兩個字。我知道我們都會為朋友和家人禱告,但我們會為列國中的宣教士禱告嗎?
1888年1月19日,歷史上著名的諾克斯教堂被擠得水泄不通,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興奮的味道。一位年輕人和他剛結婚的新娘,在差派到非洲某個稱為「白人墳墓」的宣教禾場前,他們在母會發表最後一次演講:
「我們夫妻對前往那個地方有種奇怪的恐懼感。」年輕人冷靜地說,引用了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經典的繩索比喻:「彷彿我們將要進入一個洞窟,但我們願意承擔風險,只要你們—我們的母會承諾會抓住繩子的另一端。」
這對勇敢的夫妻明白,他們正在從事一份危險的工作。他們知道這樣做的風險很高,他們無法獨自完成,他們需要請求幫助。在那激勵人心又充滿恩膏的時刻,會眾給予了英雄般的回應。在場的每個人都承諾會為他們的宣教士禱告,我相信他們是真心的。
不幸的是,所謂「真心」到了前線就止步不前。
兩年內,這位宣教士的妻子和新生的孩子被葬在非洲的「白人墳墓」裡。當這位年經的宣教士也染上致命的高熱時,他知道自己命在旦夕,於是決定重返加拿大。他一踏上故土,就立刻去參加週三晚上諾克斯教堂的禱告會。他坐在後排,沒有人注意到他回來了。當禱告會按部就班地行進到尾聲時,他
走到台前,開口說話。人們震驚地看著這位形容枯槁、破碎不堪的年輕人開口說:
「我是你們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我的妻子和孩子永遠長眠在非洲,我重返家鄉,準備死在這裡。今天晚上,我焦急地聽著你們的禱告,希望你們會提到宣教士,信守你們的承諾為宣教士禱告,但你們沒有!你們為一切和自己或教會有關的事禱告,卻忘了為宣教士禱告。我現在知道為什麼我的宣教沒有成功。因為你們沒能抓住繩子的這一端!」
母會沒有為他禱告,真的是他失去妻兒的原因嗎?「抓住繩子的另一端」是一個嚴肅的承諾,尤其是在前往滿懷敵意的領地傳福音的時候。
我相信,每個人都曾承諾為那些放棄一切跟隨基督的人抓住繩子的另一端。他們的順服將他們帶到遠離家鄉又危險重重的地方。他們盡了自己的本分,那我們呢?我們有沒有忠心地抓住繩子的另一端呢?
經歷神同在最好的方法
兩年前,我正在享受一個寧靜祥和的聖誕早晨。有別於兒子還年幼時的瘋狂、喧鬧與歡笑,外頭的雪花緩緩落下,我正在讀使徒行傳,思想「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見太1:23)
你是否曾覺得離神很遠,好像以馬內利的神不與你親近?我們都有這個時候。使徒行傳二十三章11節說:「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為什麼祂站在保羅身邊,但我們卻經常覺得祂離我們很遠?
也許是我們在安全舒適的生活中太久了,我們不覺得自己需要祂時刻親近我們。保羅的一生既不安全也不舒適,他每天都需要神靠近他,他才能活下去。是什麼使神站立在保羅身邊?「爭論越來越激烈,千夫長怕保羅會被他們(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扯碎了,就派人把他從人群中救出來,帶回軍營。」
(見徒23:10,現代中文譯本)
你想經歷神與你親近嗎?很簡單。走出你的舒適圈,行出使命,跨出信心的步伐,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宗教人士會想殺你,但神會與你靠近。
09╱ 聖經與護照
The Bible and the Passport
上帝只有一個兒子,
祂卻使祂成了宣教士。
大衛.李文斯頓
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
馬可福音16:15b
萬民教會的存在是為了榮耀神,在萬民中建立以基督為中心、被聖靈充滿,且承擔社會責任的教會和校園事工。目前,我們還沒有在每個國家都建立教會,但我們終究會實現這個目標,每一次,都是從一位宣教士,和一個國家開始。
1980年春天,當時我才二十歲,就讀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的企業管理系,當時我的職業規劃是去亞洲闖出一番天地。同一年,我和幾位朋友報名參加了亞特蘭大的某個週末學生宣教特會。我已經忘了誰是講員,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句經文:「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見詩2:8)
剛分享完信息,他就邀請在場的學生都跪下禱告,向神求一個國家。當我們跪下、臉伏於地的時候,講員繼續說:「現在向神求你的產業,求神給你一個國家。」
我不知道別人當時做了什麼,但我照著所聽見的去做了,我向神求一個國家。在那神聖的靜默時刻,我想我聽見神開口說:「緬甸」。
伴隨著舒緩的音樂、零落的啜泣聲和靜默的禱告,講員繼續說到:「你們當中有人將成為宣教士,到神放在你心中的國家去,你會住在那地,直到離世。有些人會成為某個國家的禱告宣教士,有些人會成為某個國家的財務宣教士。」
我從來沒聽說過「禱告宣教士」或「財務宣教士」,我只知道,神好像把緬甸放在我的心中。「我應該輟學去緬甸嗎?天哪!我該怎麼跟我爸媽交代?」
這時,講員解釋說:我們沒有要輟學,直接買機票飛去異國。但他希望我們在這個學期剩下的八週中,為神放在我們心中的國家懇切禱告。我照做了。八週後,「緬甸」還是留在我的心中。我一個緬甸人也不認識,但在為他們禱告了幾個月之後,我愛上了他們。這就是禱告的功效!
二十年後,也就是1999年,我和我十二歲的兒子乘坐從馬尼拉飛往緬甸的航班,去拜訪新建立的仰光萬民教會。在為緬甸人禱告多年後,終於有機會拜訪這個國家的感覺十分奇妙。我們菲律賓宣教士的工作成績十分優秀,短短幾年內,牧養管理教會的接力棒,就被交到幾位年輕有為的緬甸領袖手中,他們將這個教會提升到新的層次,也協助在鄰近的寮國建立萬民教會。
一本聖經、一本護照
雖然我不太清楚我和底波拉究竟是如何明白的,但是,當我們降落在馬尼拉,成為「意外的宣教士」時,我們就知道,我們正在建立的教會,會是一間差派宣教士的教會。
第一眼看下來,這群菲律賓學生是最不可能去列國宣教的人,很多人甚至連飛機都沒坐過。只有少數曾離開呂宋島的馬尼拉,去外地探險。沒有人有護照,更別說簽證了。但是神喜歡「揀選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見林前1:27)。用「愚拙」和「軟弱」來形容當時的我們,簡直再合適不過。
為了幫助學生們稍微有一點世界觀,我們將一張來自《國家地理雜誌》的破舊世界地圖,釘在陰暗、骯髒的地下室會堂牆上。大多數學生都在天主教環境中長大,進入教堂時都習慣用手沾一點聖水。我們這裡沒有聖水,而是創造了新的教會傳統:讓學生們按手在世界地圖上,按照詩篇二章8節來為列
國禱告—「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當學生們順著台階,走進地下室敬拜神時(這經常會讓我想起,初代教會的基督徒也常常在地下墓穴裡敬拜神),他們會為中國、俄羅斯、印度、伊朗、以色列和美國禱告,尤其是加州和佛羅里達,就是迪士尼樂園和另一間迪士尼樂園的所在地。
我們知道,從開始就對新教會和新信徒傳遞世界宣教的異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我們讓「世界宣教」成為初信造就課程的中心。菲律賓學生一信主,我們就帶他讀馬太福音的最後一章,向他們解釋何為「大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首先,我們要把「權柄」說清楚:「從此刻起,耶穌就是你生命最終的權柄。祂擁有所有的權柄,而你沒有。祂說什麼,你就做什麼。不抱怨,也不討價還價。『所有的權柄』意味著祂是主。明白了嗎?」當我們把「權柄」說清楚之後,我們接著講下一點。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我們繼續引導新信徒:「為了成為一名好基督徒,你需要兩樣東西:聖經和護照。你需要聖經來認識神,每天最重要的是要讀神的話。你還需要護照,這樣就可以順服神的呼召。如果你要『使萬民作主門徒』,則會需要護照,才能到其他國家。如果你是認真要做耶穌的門徒,那麼,今天就去買一本聖經,然後趕快去申請護照。」我們真的就這樣告訴新信徒,猜猜發生了什麼?這些貧困的菲律賓學生都有護照了!而且護照上的海關章一個接一個地增加。一開始,我們派了一個短宣隊去印尼,然後去了日本,再去了中國,這幾個短宣隊的人幾週後都回來了。最後,我們差派出去的隊伍好幾年都沒有回來,先是孟加拉,再來是俄羅斯、拉托維亞、泰國、越南、緬甸、阿富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西班牙和其他許多國家。
我們必須走進列國,因為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死在十架上,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見啟5:9)。使徒約翰在他年老時,曾看見天堂的異象,他看到「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見啟7:9)。如果天堂中的人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那麼,就必須有人先去「各國各族各民各方」傳福音、帶門徒、建立教會。
如今的「萬民」是什麼意思?
當剩下的十一位門徒聽到大使命—「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時,他們就將福音帶到當時世上所知最遠的地方。教會歷史告訴我們,彼得去了羅馬,馬太去了衣索比亞,巴多羅買去了土耳其和亞美尼亞,安得烈去了希臘,多馬去了印度,猶大去了伊朗。為了去這些遙遠的地方傳福音,他們有的步行,有
的坐船,有的騎駱駝。對當時的人來說,這就是「萬民」。那麼,對我們來說,現在「萬民」意味著什麼呢?
目前地球上住著超過七十億人。除非你主修數學,否則,對你來說七十億會是個很難理解的數字。對於我們當中某些有數學障礙的人來說,我們可以把世界想像成只有十個人的村落,這個村莊中有一個非洲人、一個歐洲人、一個拉丁美洲人、一個北美人和六個亞洲人。這六個亞洲人中有兩個中國人、兩個印度人、一個中東人和另一個亞洲人(菲律賓人、寮國人、泰國人或其他亞裔)。
在這個村莊中,有四個人擁有收音機,兩個人有車,村莊裡有一部電話和一台電腦。有兩個人住得比較寬敞,四個人有安全的水可以喝,一個人比較胖(可能是北美人),五個人正在挨餓,五個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兩美元。每一年的最後,會有一個人死去,兩個人出生,這個村子的總人口會增加到十一
人。
現在,讓我們回到現實生活中的七十億人口,目前的宗教分佈是這樣的:有二十億人—32%,會在填問卷時勾選自己是「基督徒」,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的各種宗派,以及廣義上被稱為「基督教」的其他群體。這些人當中,有的是全心全意跟隨耶穌的門徒,有的則有名無實。有十三億人—22%是穆斯林。和基督徒很像,有的人是虔誠的穆斯林,而有的沒有那麼虔誠。有九億人—15%是沒有信仰的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和懷疑論者。有八億人—14%是印度教徒。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宗教如猶太教、錫克教或部落宗教占了10%的人口。有四億人—7%是佛教徒。現在的世界看起來是這樣的。
要有人去
就目前來看,地球上基督徒最少的十二個國家是:阿富汗、阿爾及利亞、孟加拉、不丹、柬埔寨、伊朗、尼泊爾、索馬利亞、泰國、土耳其、突尼西亞和葉門。這些國家中,信耶穌基督的人連1%都不到。我寫這個章節的時候,萬民教會的同工已經在這十二個國家當中的七個建立教會。這很棒,但誰願意去另外五個國家呢?誰願意背上十字架跟隨耶穌,去往阿爾及利亞、不丹、索馬利亞、突尼西亞和葉門呢?
慈善家兼宣教士威廉.波頓(第十六章會更多提到他的故事)對「宣教動員」提出見解。他常常用這段反問句來闡明他的觀點:「如果有十個人扛著一根木棍,九個人扛著輕的一端,一個人舉著重的另一端,那麼,你會幫忙扛哪一端?」那些世上未曾聽過福音的穆斯林、印度教和佛教國家顯然代表著世界宣教中「重的一端」,而且很少有人去扛這個重擔。
目前,萬民教會在六十五個國家都有植堂,但誰願意去開拓另外的一百三十一個國家呢?誰願意去舉起「重的一端」?誰願意去北非的摩洛哥、利比亞和馬利?誰願意去南美的智利、巴拉圭和烏拉圭?誰願意去東非的肯亞、盧安達和衣索比亞?誰願意去歐洲的挪威、羅馬尼亞和義大利?誰願意去中亞
的哈薩克、塔吉克和烏茲別克?也許我們都需要跪下來,向神求一個國家。但是,在我們這樣做之前,我們應當借鑒摩拉維亞兄弟會創始人欽岑多夫的態度,他曾說:
「我只有一種熱情,就是為祂,單單為祂。
世界就是禾場,禾場就是世界。從此以後,
那個我要為基督贏得靈魂的國家,就是我的家鄉。」
但如果千千萬萬的人開始走向列國,那麼光是機票就需要花不少錢。
要有人供應
「爸,我們有個好主意!」我三個兒子的臉上因著喜樂發出光來。
「夥計們,有什麼好主意?」
「今年聖誕節,我們應該一起去美國。然後就可以打雪仗了。」
我的孩子都在熱帶地區長大,所以他們總是盼望能有個白色聖誕,是美國版的皚皚白雪,而不是白色的沙灘。他們在菲律賓美麗的沙灘上度過了許多白色耶誕節。但現在,他們盼望著冰天雪地的白色。
「這個主意很有意思,」我回答,試著用一個有創意的說法讓他們知道這不太可能。「但是,會有個問題。」
「爸,什麼問題?」他們異口同聲,身體前傾,仿佛正有雪花飛舞在他們眼前一般。
「親戚們住的密西西比或喬治亞不會下雪。」
「沒關係,我們也可以去加拿大!」
「好吧,事實上,那會有另一個問題,得有人付錢啊!」從某種角度來說,在我與兒子們對話的那一刻,我們都學到了一個功課:就是美夢常常被拮据的現實碾碎。
這對他們來說,這真的是個好主意。跳上飛機,在美國待幾天,從寵愛他們的祖父母、叔叔阿姨和表兄弟手上收到成堆的禮物。然後去加拿大,扔扔雪球。一週後回馬尼拉。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是有個問題,這個老問題就是—錢。想出美好的聖誕度假計畫很容易,但付不付得起卻是個難題。需要有人計算成本、擔起責任、付錢。如果我們想進入更多國家,差派更多宣教士,那麼我們就需要花更多的錢。
我不建議任何人,像我們1984年那樣「毫無準備、身無分文」地出去,但我也不希望人只是坐在那裡什麼都不做,一直等待所有的財物支援出現。有的時候,如果我們想要進入列國,就必須要採取勇敢、犧牲的信心跨越過去。史蒂夫.艾迪生(Steve Addison)在他著名的《改變世界的運動》8 一書中
描述了信心的作用:
教會歷史並不是由家財萬貫、資源綽綽的個人和
機構組成,而是由與永生神相遇並以信心回應的弟兄
姊妹所組成。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心靈願意,但錢包軟弱
近期,我與一位知名的宣教領袖聊天,我們談到彼此都對建立宣教差派型教會充滿熱情。我們為著許多門徒願意走出去而喜樂,但也為著少有教會願意差派宣教感到哀傷。
宣教資金缺乏是個全球性問題,對其他宗教來說也不罕見。在許多國家,不計其數的信徒抓住大使命這個異象,他們準備好要去列國傳福音。但,就像我回答兒子的聖誕度假計畫一樣,有一個問題:需要有人買單!世界宣教的工價是昂貴的。
兩千年前,使徒保羅問: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 (羅10:14-15)
我想在保羅的提問清單後再加幾個問題:如果沒人奉獻,何來差派?如果教會不拿出宣教基金,他們該如何買機票?如果牧師沒有在教會預算中將世界宣教基金視為優先,宣教士從哪裡獲得財務支援呢?
除了很重要的錢以外,要完成大使命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要有人禱告
每個信仰的人都知道禱告很重要,但我們要為什麼禱告?耶穌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祂希望我們把下列事項放在禱告清單中:「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見可11:17)不要忽略最後的「萬國」兩個字。我知道我們都會為朋友和家人禱告,但我們會為列國中的宣教士禱告嗎?
1888年1月19日,歷史上著名的諾克斯教堂被擠得水泄不通,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興奮的味道。一位年輕人和他剛結婚的新娘,在差派到非洲某個稱為「白人墳墓」的宣教禾場前,他們在母會發表最後一次演講:
「我們夫妻對前往那個地方有種奇怪的恐懼感。」年輕人冷靜地說,引用了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經典的繩索比喻:「彷彿我們將要進入一個洞窟,但我們願意承擔風險,只要你們—我們的母會承諾會抓住繩子的另一端。」
這對勇敢的夫妻明白,他們正在從事一份危險的工作。他們知道這樣做的風險很高,他們無法獨自完成,他們需要請求幫助。在那激勵人心又充滿恩膏的時刻,會眾給予了英雄般的回應。在場的每個人都承諾會為他們的宣教士禱告,我相信他們是真心的。
不幸的是,所謂「真心」到了前線就止步不前。
兩年內,這位宣教士的妻子和新生的孩子被葬在非洲的「白人墳墓」裡。當這位年經的宣教士也染上致命的高熱時,他知道自己命在旦夕,於是決定重返加拿大。他一踏上故土,就立刻去參加週三晚上諾克斯教堂的禱告會。他坐在後排,沒有人注意到他回來了。當禱告會按部就班地行進到尾聲時,他
走到台前,開口說話。人們震驚地看著這位形容枯槁、破碎不堪的年輕人開口說:
「我是你們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我的妻子和孩子永遠長眠在非洲,我重返家鄉,準備死在這裡。今天晚上,我焦急地聽著你們的禱告,希望你們會提到宣教士,信守你們的承諾為宣教士禱告,但你們沒有!你們為一切和自己或教會有關的事禱告,卻忘了為宣教士禱告。我現在知道為什麼我的宣教沒有成功。因為你們沒能抓住繩子的這一端!」
母會沒有為他禱告,真的是他失去妻兒的原因嗎?「抓住繩子的另一端」是一個嚴肅的承諾,尤其是在前往滿懷敵意的領地傳福音的時候。
我相信,每個人都曾承諾為那些放棄一切跟隨基督的人抓住繩子的另一端。他們的順服將他們帶到遠離家鄉又危險重重的地方。他們盡了自己的本分,那我們呢?我們有沒有忠心地抓住繩子的另一端呢?
經歷神同在最好的方法
兩年前,我正在享受一個寧靜祥和的聖誕早晨。有別於兒子還年幼時的瘋狂、喧鬧與歡笑,外頭的雪花緩緩落下,我正在讀使徒行傳,思想「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見太1:23)
你是否曾覺得離神很遠,好像以馬內利的神不與你親近?我們都有這個時候。使徒行傳二十三章11節說:「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為什麼祂站在保羅身邊,但我們卻經常覺得祂離我們很遠?
也許是我們在安全舒適的生活中太久了,我們不覺得自己需要祂時刻親近我們。保羅的一生既不安全也不舒適,他每天都需要神靠近他,他才能活下去。是什麼使神站立在保羅身邊?「爭論越來越激烈,千夫長怕保羅會被他們(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扯碎了,就派人把他從人群中救出來,帶回軍營。」
(見徒23:10,現代中文譯本)
你想經歷神與你親近嗎?很簡單。走出你的舒適圈,行出使命,跨出信心的步伐,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宗教人士會想殺你,但神會與你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