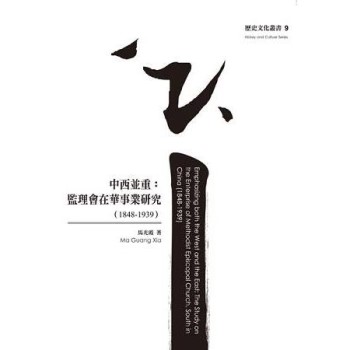林樂知是美國監理會傳教士,1860 年被派來華傳教,但隨後爆發的美國內戰切斷了他與母會的聯繫,使其在經濟上陷於嚴重困境。為擺脫危機,他開始從事世俗活動,其特殊的世俗工作,不僅解了燃眉之急,還為其結交中國的士和官提供了便利,更使其傳教思路也因之發生變化,由「直接佈道」向「自由佈道」方式轉化,同時注重自上而下的方式,走上層路線。
王立新曾對基督教傳教方法有這樣的總結,縱觀整個19 世紀,基督教來華傳教士主要有基要派和自由派兩種不同的傳教政策,絕大多數傳教士採取傳統的「直接佈道」方法,即宣講教義、巡迴佈道和散發宗教印刷品。 這種「直接佈道」的方法正是基要派宣導的傳教方法,它注重「個人得救」,即不分貴賤、尊卑和階級,每一個人的靈魂都在上帝面前平等,都應得到「救恩」;它還特別強調一切教義的絕對性,對本土文化表現出一種全不妥協的態度。 然而這種通過用純粹的基督教教義來拯救個人靈魂的側重卻使得傳教士在傳道之時不自覺地疏離了傳統文化的代表—士大夫階層,而將佈道對象主要集中於普通大眾,尤其是一些貧苦百姓。因而這種方法又被稱為「自下而上」的傳教方法。早期監理會來華傳教士也是採取這種傳教政策,堅持基督教教義的純粹性,主要通過在教堂佈道、露天佈道,沿街散發傳單和小冊子,創辦義務學校收留貧窮子弟,培養當地傳道等手段開展傳教活動。
林樂知在來華之初,也是沿用前輩傳教士的傳教經驗,採用「直接傳道」的政策,遵循「面」和「量」的原則,擴大傳教範圍,建立更多的教堂,爭取更多的信徒。因此,林樂知在學習漢語之外,就到四鄉佈道,如1861 年就曾到南翔傳教。 然而,林樂知在從事中國現代化的文化活動中,其思想逐漸被「現代化」,其傳教政策也逐漸從傳統方式走向自由多元的轉化。林樂知及其上海「文化圈」
以藍柏為代表的監理會傳教士在以蘇州為中心的內地城鎮逐步建立起了以當地助手為聯繫紐帶的傳教網路,而上海的林樂知在為擺脫經濟危機而從事世俗活動的過程中,以教習、翻譯和編輯等職業為紐帶構建了不同於以往的以文化為突出特點的交遊網路,形成了以士紳為主體包括高級官員和一些有上進心的青年學者、西方自由派傳教士及部分中國信徒在內的文化圈。這種交遊網路如同無形的神助之手,使林樂知日後的教會事業順利展開,也使林樂知在中國近代化的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林樂知憑藉著一些上海的友人如丁韙良(W. A. P. Martin, 1827–1916)、傅蘭雅及偉烈亞力等介紹結識了一些上海的官紳,這其中就有上海道台應寶時及廣方言館館長馮桂芬等。1864 年2 月24 日,林樂知收到上海廣方言館的邀請函,這可以看作是林樂知與中國政府正式打交道的開始;1871 年後進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進一步擴大了其交遊圈;自1868 年他創辦《教會新報》到1874 年改為《萬國公報》後,其輻射圈更為擴大。那麼他究竟是怎樣與他們交往的呢,下面對此做一考察。1. 官員,如馮桂芬和郭嵩燾。據貝奈特考證,林樂知和馮桂芬的友誼一直持續到馮桂芬去世。馮桂芬(1809–1874)是晚清著名思想家,1864 年後任李鴻章的幕僚,尤其是關於蘇州及其周邊行政事務的顧問,曾任上海廣方言館館長。太平天國運動期間馮桂芬駐上海,林樂知每週與其會談一次,而馮遷往蘇州96 後,林樂知與其每月討論一次。林樂知認為馮桂芬是許多較開明學者中的一個,他向林樂知解釋中國的事情是怎樣和為何這樣,而由於其角色,林樂知也與他討論各種各樣的西方政策, 發展及其態度。另如郭嵩燾,他是19 世紀第一位中國駐外公使,1876 年離華前與林樂知相遇,當時林樂知贈予他一本《中西關係略論》, 這本書分析了中國目前的國際地位,它曾刊行在1875–1876 年的《萬國公報》期刊上。1878 年,林樂知在倫敦與郭再次相逢時,郭告訴林樂知:「當我剛接受中國駐英大使這份工作時一無所知,但幸運的是我有你的書作指導。」馮桂芬和郭嵩燾是晚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視西學及西政等方面的內容,從上面林樂知與兩人的交往看,他主要以「西政」為載體搭起了與晚清改革派官員的聯繫橋樑。
2. 廣方言館學生,如嚴良勳、席淦、汪鳳藻、王遠焜、王文秀等, 與學生的交往,除了課堂上的交流,他還帶領學生參觀法租界的煤氣燈廠,現代化的麵粉廠,參觀江南製造局的機器車間, 這種方式一方面讓學生在學外語的同時學到了一些科學知識,另一方面也密切了與學生的交流。與學生的這種交往,是潛移默化的,後來學生的工作經歷也驗證了林樂知的預測,他們有不少擔任了政府的官職,有的在國內任職,還有的在國外任過公使和領事。1903 年一位19 世紀70 年代上海廣方言館的學生還給林樂知寫信說他在福建的汀州任高官。 後來出使過德國的H. E. Yang也曾是林樂知的學生。
林樂知與學生的交往可看作是他以「西學導師」的身份切入,同時這種身份的建構對其傳教士身份的彰顯無疑是一道美麗的光環。3. 翻譯館同事,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員,可考的有59人,其中外國學者9 人,中國學者50人, 比如徐壽、華蘅芳及徐建寅等。從下表可看出與林樂知直接打交道的學者有嚴良勳、李鳳苞、鄭昌棪、瞿昂來、蔡錫齡、趙元益等,他們在一起合作譯書。林樂知及其中國助手翻譯了大批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其軍事科學等方面的大批西學作品,其中內容較多的還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內容。顯然在此林樂知與中國學者的交往是以「西學」、「西藝」為媒介的。
林樂知不僅通過上述管道建立了與官員及文人學者的聯繫,而且還因其特殊的貢獻,獲得了名義上的「官銜」。1876 年被清政府賞封五品銜。
報刊社交圈
以藍柏等為代表的早期監理會傳教士在文字方面主要著力於出版一些宗教宣傳品及其用上海方言編成的福音小冊子, 而且其面向的對象是下層民眾;以林樂知為代表的傳教士則由於特殊的編輯和翻譯經歷,在文字方面主要從事翻譯和報刊工作,其面向的對象已逐漸向上層社會擴展。下面主要探討林樂知自己創辦的報刊《教會新報》或《萬國公報》及其聯繫網。
《教會新報》的宗旨為「傳教」與「聯絡信徒」,主要是為基督徒設計的, 刊載的也主要是基督教的內容。隨著林樂與中國士紳交往的深入,林樂知逐步意識到知識份子的力量, 因此1874 年從301 期開始,《教會新報》改名為《萬國公報》(Globe Magazine),「林樂知想使它成為教會性質不明顯,中國知識份子也不很反感的一份報紙」,且「本刊是為推廣與泰西各國有關的地理、歷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學、藝術、工業及一般進步知識的期刊」,這樣「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賞識,並可以入名門閨秀之精鑒,且可以助大商富賈之利益, 更可以佐各匠農工之取資,益人實非淺鮮,豈徒《新報》雲爾哉!」因此,《萬國公報》不僅以教徒為對象,而且跳出教會圈子,以中國上流階層和知識份子等為對象,淡化宗教色彩和添加世俗內容,使得讀者群及其影響進一步擴大。該報刊不僅依賴於讀者,也依賴於撰稿人,有的還是讀者兼撰稿人。林樂知開始聘用兩名助手:一位負責宗教內容, 另一位則負責新聞內容由以上資料可以看出,當時報刊的擴散面之廣,不僅地域跨越中西,而且作者也涵蓋中西,形成了兩大作者圈:一是以中國基督徒為中心。二是以傳教士為主的外國人交遊圈,主要是當時在華的西方傳教士。據貝奈特統計:向該報撰稿的西方人大多是傳教士:如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丁韙良、艾約瑟、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慕維廉、花之安(Ernst Faber)、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藍柏、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倪維斯(John L. Nevius)、楊格非(Griffith John)、理一視(Jonathan Lees)、湛約翰(John Chalmers)、潘慎文等。另外,傅蘭雅博士和德貞醫生(Dr. John Dudgeon) 也為雜誌撰過文。西方作者既撰寫世俗文稿也有宗教主題的文章。
在江南製造局的廣方言館和翻譯館中,林樂知就結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外國人朋友,只不過在公報這兒,這個圈子的範圍進一步擴大了。其實,中國學者早就注意到了晚清時期中國傳教士內部形成的這個圈子,比如梁元生就認為這是以廣學會為中心、《萬國公報》為喉舌的自由派傳教士圈,這群人翻譯過不少西學書籍,並發表過有關維新變法的言論。這群志同道合的傳教士們擁有一個共同的交流平臺和社交圈,而且他們交往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中國的「士」。也正是由於他們的聯合行動,中國近代化的舞臺上才留下了他們忙碌的身影和中國學者對傳教士不同評價的聲音,他們甚至被稱為「西儒」。
買辦商人與中西書院
1881 年林樂知擔任監理會中國教區長,並創建中西書院。他批評當時差會所經營的學校,認為「學生來自中國較為低下並毫無希望的階層」,而林樂知的工作經歷,使他看到了結交「士」和「官」的好處,從而使他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辦學思路。他將中西書院的招生對象指向「上層社會」,當時學校初招學生200 餘人,據林樂知稱,「除一人外,所有學生皆來自上海最優秀的家庭,並且代表了中國社會幾乎所有的階層。」中西書院先後建成的有三處校址:第一分院、第二分院和大書院。按其規制,學生先在分院修讀二年,始進大書院就讀。後來,二分院歸併大書院,1884 年後,中西書院實際上就只有上海昆山路中西大書院一處院址了。對於建設費用,當時「按林樂知與監理會所定之條款,差會承擔購置校舍地皮, 支付外籍教師薪水的費用,餘者皆從當地籌措,自1881 年夏起,林樂知向滬上中外人士籌集資金,迄1882 年底,中西書院已獲足夠『支付兩年的開辦費用』」,這其中「美國本公會撥洋四萬餘元,中朝李傅相、王總戎、邵唐諸觀察暨中西官紳商富慨分鶴俸、惠賜洋蚨。」1883年,「又蒙粵東徐君雨之觀察慨讓虹口空地三十六畝,業也備價購就」,由是觀之,林樂知與徐潤的交情已非同一般。中西書院的舉辦也離不開上海一些文人的支持。如王韜、沈毓桂等,他們都曾作過該校的監院,而沈毓桂和林樂知的合作可以看作是中西融合的典範。
中外人士對中西書院創辦的讚譽也可旁證他們的支持態度。如李鴻章曾致函林樂知,稱其為「影響久遠之偉大創舉, 比任何事都重要」,丁韙良、傅蘭雅等對此也極表讚揚。可以說,中西書院的成功創辦,得益於林樂知在上海的世俗經歷, 更離不開他與當地社會上流人士所建立的人脈網絡,這裏面集結著他曾交往過,或者支持他的官員、文人、傳教士,還鏈結了當地的買辦階層,他們所提供的人力和物力支持為其日後的教會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小結
1848–1885 年是監理會在華各項事業的奠基階段,1886 年中華年議會成立,監理會在華各項工作有綱例可循,逐步趨向正規發展。在此階段由於藍柏、潘慎文等主要以直接傳道為主,在蘇州、南翔等內地城市開展佈道工作,並通過開辦學校培養當地助手,為教會儲備了大批領袖人才;此階段也是林樂知「改直接佈道為間接佈道,走上層路線」傳教思路的形成, 上海中西書院的成功舉辦及其《教會新報》到《萬國公報》的轉變也正好踐行了林樂知的這些思想。正是由於藍柏和林樂知不同的傳教思路,才使得監理會在以蘇州為代表的內陸城市及以上海為代表的口岸城市所開展的教會事業兼具傳統和現代的特徵,其傳教對象也覆蓋邊緣與主流。如林樂知初來華時,沿循傳統的佈道方法,傳教對象多以來自於社會底層的社會邊緣人物為主,到1875 年,信徒的情況還是「當地每年的捐款數從10–15 美元不等,許多信徒太窮以致捐不出什麼東西」。而在林樂知從事世俗工作,尤其是從事政府工作之後,他的交往圈逐漸滲入到主流社會中的上層人物之中,隨之構建了包括官員、文人、紳商、買辦階層等中上層人士在內的交遊網路。其傳教思路一改傳統風格,由「直接佈道」改為「間接佈道」,並且「兼合中西」、「走上層路線」。中西書院學生的積極報名及社會各階層的踴躍捐款即可看作是林樂知及其事業楔入主流社會的成功嘗試。
同時,通過林樂知的世俗實踐及傳教思路的變化,可以看出林樂知是被中國「啟蒙」後才開始「啟蒙」活動的,也可以說他在從事中國近代化的活動中「被近代化」,才開始擴大教會事業進而加入「使中國近代化」的活動行列。而林樂知的交往圈從邊緣階層到主流階層,由教內人士擴至教外人士的過程,也是其「被啟蒙」到「再啟蒙」過程的反應,它包括從最初的「傳播基督教」到「傳播西學加基督教」的轉變。而「被啟蒙」與「再啟蒙」內容的矛盾,也註定了林樂知「基督教救中國」的願望不會實現。 (節錄自本書第三章「以傳教士為主體的早期宣教」)
王立新曾對基督教傳教方法有這樣的總結,縱觀整個19 世紀,基督教來華傳教士主要有基要派和自由派兩種不同的傳教政策,絕大多數傳教士採取傳統的「直接佈道」方法,即宣講教義、巡迴佈道和散發宗教印刷品。 這種「直接佈道」的方法正是基要派宣導的傳教方法,它注重「個人得救」,即不分貴賤、尊卑和階級,每一個人的靈魂都在上帝面前平等,都應得到「救恩」;它還特別強調一切教義的絕對性,對本土文化表現出一種全不妥協的態度。 然而這種通過用純粹的基督教教義來拯救個人靈魂的側重卻使得傳教士在傳道之時不自覺地疏離了傳統文化的代表—士大夫階層,而將佈道對象主要集中於普通大眾,尤其是一些貧苦百姓。因而這種方法又被稱為「自下而上」的傳教方法。早期監理會來華傳教士也是採取這種傳教政策,堅持基督教教義的純粹性,主要通過在教堂佈道、露天佈道,沿街散發傳單和小冊子,創辦義務學校收留貧窮子弟,培養當地傳道等手段開展傳教活動。
林樂知在來華之初,也是沿用前輩傳教士的傳教經驗,採用「直接傳道」的政策,遵循「面」和「量」的原則,擴大傳教範圍,建立更多的教堂,爭取更多的信徒。因此,林樂知在學習漢語之外,就到四鄉佈道,如1861 年就曾到南翔傳教。 然而,林樂知在從事中國現代化的文化活動中,其思想逐漸被「現代化」,其傳教政策也逐漸從傳統方式走向自由多元的轉化。林樂知及其上海「文化圈」
以藍柏為代表的監理會傳教士在以蘇州為中心的內地城鎮逐步建立起了以當地助手為聯繫紐帶的傳教網路,而上海的林樂知在為擺脫經濟危機而從事世俗活動的過程中,以教習、翻譯和編輯等職業為紐帶構建了不同於以往的以文化為突出特點的交遊網路,形成了以士紳為主體包括高級官員和一些有上進心的青年學者、西方自由派傳教士及部分中國信徒在內的文化圈。這種交遊網路如同無形的神助之手,使林樂知日後的教會事業順利展開,也使林樂知在中國近代化的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林樂知憑藉著一些上海的友人如丁韙良(W. A. P. Martin, 1827–1916)、傅蘭雅及偉烈亞力等介紹結識了一些上海的官紳,這其中就有上海道台應寶時及廣方言館館長馮桂芬等。1864 年2 月24 日,林樂知收到上海廣方言館的邀請函,這可以看作是林樂知與中國政府正式打交道的開始;1871 年後進入江南製造局翻譯館,進一步擴大了其交遊圈;自1868 年他創辦《教會新報》到1874 年改為《萬國公報》後,其輻射圈更為擴大。那麼他究竟是怎樣與他們交往的呢,下面對此做一考察。1. 官員,如馮桂芬和郭嵩燾。據貝奈特考證,林樂知和馮桂芬的友誼一直持續到馮桂芬去世。馮桂芬(1809–1874)是晚清著名思想家,1864 年後任李鴻章的幕僚,尤其是關於蘇州及其周邊行政事務的顧問,曾任上海廣方言館館長。太平天國運動期間馮桂芬駐上海,林樂知每週與其會談一次,而馮遷往蘇州96 後,林樂知與其每月討論一次。林樂知認為馮桂芬是許多較開明學者中的一個,他向林樂知解釋中國的事情是怎樣和為何這樣,而由於其角色,林樂知也與他討論各種各樣的西方政策, 發展及其態度。另如郭嵩燾,他是19 世紀第一位中國駐外公使,1876 年離華前與林樂知相遇,當時林樂知贈予他一本《中西關係略論》, 這本書分析了中國目前的國際地位,它曾刊行在1875–1876 年的《萬國公報》期刊上。1878 年,林樂知在倫敦與郭再次相逢時,郭告訴林樂知:「當我剛接受中國駐英大使這份工作時一無所知,但幸運的是我有你的書作指導。」馮桂芬和郭嵩燾是晚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視西學及西政等方面的內容,從上面林樂知與兩人的交往看,他主要以「西政」為載體搭起了與晚清改革派官員的聯繫橋樑。
2. 廣方言館學生,如嚴良勳、席淦、汪鳳藻、王遠焜、王文秀等, 與學生的交往,除了課堂上的交流,他還帶領學生參觀法租界的煤氣燈廠,現代化的麵粉廠,參觀江南製造局的機器車間, 這種方式一方面讓學生在學外語的同時學到了一些科學知識,另一方面也密切了與學生的交流。與學生的這種交往,是潛移默化的,後來學生的工作經歷也驗證了林樂知的預測,他們有不少擔任了政府的官職,有的在國內任職,還有的在國外任過公使和領事。1903 年一位19 世紀70 年代上海廣方言館的學生還給林樂知寫信說他在福建的汀州任高官。 後來出使過德國的H. E. Yang也曾是林樂知的學生。
林樂知與學生的交往可看作是他以「西學導師」的身份切入,同時這種身份的建構對其傳教士身份的彰顯無疑是一道美麗的光環。3. 翻譯館同事,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員,可考的有59人,其中外國學者9 人,中國學者50人, 比如徐壽、華蘅芳及徐建寅等。從下表可看出與林樂知直接打交道的學者有嚴良勳、李鳳苞、鄭昌棪、瞿昂來、蔡錫齡、趙元益等,他們在一起合作譯書。林樂知及其中國助手翻譯了大批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其軍事科學等方面的大批西學作品,其中內容較多的還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內容。顯然在此林樂知與中國學者的交往是以「西學」、「西藝」為媒介的。
林樂知不僅通過上述管道建立了與官員及文人學者的聯繫,而且還因其特殊的貢獻,獲得了名義上的「官銜」。1876 年被清政府賞封五品銜。
報刊社交圈
以藍柏等為代表的早期監理會傳教士在文字方面主要著力於出版一些宗教宣傳品及其用上海方言編成的福音小冊子, 而且其面向的對象是下層民眾;以林樂知為代表的傳教士則由於特殊的編輯和翻譯經歷,在文字方面主要從事翻譯和報刊工作,其面向的對象已逐漸向上層社會擴展。下面主要探討林樂知自己創辦的報刊《教會新報》或《萬國公報》及其聯繫網。
《教會新報》的宗旨為「傳教」與「聯絡信徒」,主要是為基督徒設計的, 刊載的也主要是基督教的內容。隨著林樂與中國士紳交往的深入,林樂知逐步意識到知識份子的力量, 因此1874 年從301 期開始,《教會新報》改名為《萬國公報》(Globe Magazine),「林樂知想使它成為教會性質不明顯,中國知識份子也不很反感的一份報紙」,且「本刊是為推廣與泰西各國有關的地理、歷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學、藝術、工業及一般進步知識的期刊」,這樣「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賞識,並可以入名門閨秀之精鑒,且可以助大商富賈之利益, 更可以佐各匠農工之取資,益人實非淺鮮,豈徒《新報》雲爾哉!」因此,《萬國公報》不僅以教徒為對象,而且跳出教會圈子,以中國上流階層和知識份子等為對象,淡化宗教色彩和添加世俗內容,使得讀者群及其影響進一步擴大。該報刊不僅依賴於讀者,也依賴於撰稿人,有的還是讀者兼撰稿人。林樂知開始聘用兩名助手:一位負責宗教內容, 另一位則負責新聞內容由以上資料可以看出,當時報刊的擴散面之廣,不僅地域跨越中西,而且作者也涵蓋中西,形成了兩大作者圈:一是以中國基督徒為中心。二是以傳教士為主的外國人交遊圈,主要是當時在華的西方傳教士。據貝奈特統計:向該報撰稿的西方人大多是傳教士:如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丁韙良、艾約瑟、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慕維廉、花之安(Ernst Faber)、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藍柏、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倪維斯(John L. Nevius)、楊格非(Griffith John)、理一視(Jonathan Lees)、湛約翰(John Chalmers)、潘慎文等。另外,傅蘭雅博士和德貞醫生(Dr. John Dudgeon) 也為雜誌撰過文。西方作者既撰寫世俗文稿也有宗教主題的文章。
在江南製造局的廣方言館和翻譯館中,林樂知就結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外國人朋友,只不過在公報這兒,這個圈子的範圍進一步擴大了。其實,中國學者早就注意到了晚清時期中國傳教士內部形成的這個圈子,比如梁元生就認為這是以廣學會為中心、《萬國公報》為喉舌的自由派傳教士圈,這群人翻譯過不少西學書籍,並發表過有關維新變法的言論。這群志同道合的傳教士們擁有一個共同的交流平臺和社交圈,而且他們交往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中國的「士」。也正是由於他們的聯合行動,中國近代化的舞臺上才留下了他們忙碌的身影和中國學者對傳教士不同評價的聲音,他們甚至被稱為「西儒」。
買辦商人與中西書院
1881 年林樂知擔任監理會中國教區長,並創建中西書院。他批評當時差會所經營的學校,認為「學生來自中國較為低下並毫無希望的階層」,而林樂知的工作經歷,使他看到了結交「士」和「官」的好處,從而使他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辦學思路。他將中西書院的招生對象指向「上層社會」,當時學校初招學生200 餘人,據林樂知稱,「除一人外,所有學生皆來自上海最優秀的家庭,並且代表了中國社會幾乎所有的階層。」中西書院先後建成的有三處校址:第一分院、第二分院和大書院。按其規制,學生先在分院修讀二年,始進大書院就讀。後來,二分院歸併大書院,1884 年後,中西書院實際上就只有上海昆山路中西大書院一處院址了。對於建設費用,當時「按林樂知與監理會所定之條款,差會承擔購置校舍地皮, 支付外籍教師薪水的費用,餘者皆從當地籌措,自1881 年夏起,林樂知向滬上中外人士籌集資金,迄1882 年底,中西書院已獲足夠『支付兩年的開辦費用』」,這其中「美國本公會撥洋四萬餘元,中朝李傅相、王總戎、邵唐諸觀察暨中西官紳商富慨分鶴俸、惠賜洋蚨。」1883年,「又蒙粵東徐君雨之觀察慨讓虹口空地三十六畝,業也備價購就」,由是觀之,林樂知與徐潤的交情已非同一般。中西書院的舉辦也離不開上海一些文人的支持。如王韜、沈毓桂等,他們都曾作過該校的監院,而沈毓桂和林樂知的合作可以看作是中西融合的典範。
中外人士對中西書院創辦的讚譽也可旁證他們的支持態度。如李鴻章曾致函林樂知,稱其為「影響久遠之偉大創舉, 比任何事都重要」,丁韙良、傅蘭雅等對此也極表讚揚。可以說,中西書院的成功創辦,得益於林樂知在上海的世俗經歷, 更離不開他與當地社會上流人士所建立的人脈網絡,這裏面集結著他曾交往過,或者支持他的官員、文人、傳教士,還鏈結了當地的買辦階層,他們所提供的人力和物力支持為其日後的教會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小結
1848–1885 年是監理會在華各項事業的奠基階段,1886 年中華年議會成立,監理會在華各項工作有綱例可循,逐步趨向正規發展。在此階段由於藍柏、潘慎文等主要以直接傳道為主,在蘇州、南翔等內地城市開展佈道工作,並通過開辦學校培養當地助手,為教會儲備了大批領袖人才;此階段也是林樂知「改直接佈道為間接佈道,走上層路線」傳教思路的形成, 上海中西書院的成功舉辦及其《教會新報》到《萬國公報》的轉變也正好踐行了林樂知的這些思想。正是由於藍柏和林樂知不同的傳教思路,才使得監理會在以蘇州為代表的內陸城市及以上海為代表的口岸城市所開展的教會事業兼具傳統和現代的特徵,其傳教對象也覆蓋邊緣與主流。如林樂知初來華時,沿循傳統的佈道方法,傳教對象多以來自於社會底層的社會邊緣人物為主,到1875 年,信徒的情況還是「當地每年的捐款數從10–15 美元不等,許多信徒太窮以致捐不出什麼東西」。而在林樂知從事世俗工作,尤其是從事政府工作之後,他的交往圈逐漸滲入到主流社會中的上層人物之中,隨之構建了包括官員、文人、紳商、買辦階層等中上層人士在內的交遊網路。其傳教思路一改傳統風格,由「直接佈道」改為「間接佈道」,並且「兼合中西」、「走上層路線」。中西書院學生的積極報名及社會各階層的踴躍捐款即可看作是林樂知及其事業楔入主流社會的成功嘗試。
同時,通過林樂知的世俗實踐及傳教思路的變化,可以看出林樂知是被中國「啟蒙」後才開始「啟蒙」活動的,也可以說他在從事中國近代化的活動中「被近代化」,才開始擴大教會事業進而加入「使中國近代化」的活動行列。而林樂知的交往圈從邊緣階層到主流階層,由教內人士擴至教外人士的過程,也是其「被啟蒙」到「再啟蒙」過程的反應,它包括從最初的「傳播基督教」到「傳播西學加基督教」的轉變。而「被啟蒙」與「再啟蒙」內容的矛盾,也註定了林樂知「基督教救中國」的願望不會實現。 (節錄自本書第三章「以傳教士為主體的早期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