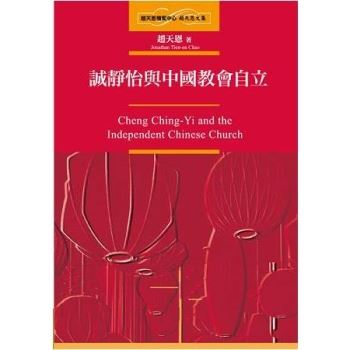在誠靜怡思維成形的這些年間,他可能領悟到:隨著中國的本色化進程需要建立一個聯合的中國教會。1890年代的維新運動和排外的民族主義,特別是義和團運動,肯定使他意識到同時具備中國人與基督徒雙重身分的張力。理一視似乎對誠靜怡具有相當重要的個人影響,因為在後來的歲月裡,在成熟的誠靜怡身上能夠清楚地看到理一視的品格特徵。理一視被視為一位性格直率和純樸高尚的人。在人們的眼中,他也是一位性情中人,氣度寬宏。他具有開放的心態和寬廣的眼界。作為一名基督徒,他虔誠、全心奉獻給上帝,並具有超凡魅力、執著、信仰堅定。作為一名傳教士,理一視熱情而又堅定,並且熱愛傳揚福音。他有洞察時代徵兆的遠見,並以作為人們的領路人而聞名。72 後來,這些性格特徵在誠靜怡身上都是顯而易見的。另一種來自理一視的影響體現在誠靜怡對處境的關懷,以及對發展適應中國情勢的教會事工的種種方法的關注。理一視欣賞儒家教育,即使他並不完全贊同儒家教育的內容。他試圖抵制將西方制度性基督教作全面的移植。理一視對福音佈道的熱情也在誠靜怡身上留下了痕跡,這一點可以從追溯他後來的事奉生涯中看出來。73
誠靜怡於1900 年5 月從天津的神學院畢業。在同班的四名同學之中,他排名第一。首先他被派往倫敦會位於天津和北京之間的一個傳教站事奉。74 然而,義和團運動的爆發阻止了他在畢業後返回北京,這致使他未能就任這一新的職位。到了五月底,義和團運動已經從直隸與山東的邊界區域開始往北,向天津和北京擴散。運動鋒鏑之處,義和團焚燒、掠奪和殘害中國信徒,並且常常綁架婦女信徒。75
在北京的英國傳教士於6月7日接到命令要他們躲進英國使館,但是英國公使竇納樂(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1852-1915)卻全然拒絕為中國基督徒提供保護。石牧師(Rev. J. Stonehouse)描述了倫敦會信徒們的驚恐:
因為我們是基督徒,我們將被我們自己的同胞殺害。你們的政府和我們的政府都不保護我們,我們的處境真是可憐。76幸運的是,美國公理會(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願意接納他們進入他們的駐所,該駐所由二十五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守衛。6 月13 日,義和團進入北京,傍晚,他們在搶掠之後縱火燒毀倫敦會的東城傳教站。6 月20 日,德國公使克林德(C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在臨近東城傳教站的哈德門(今崇文門)遇害。這一事件造成了恐慌,所有的外國公使和傳教士連同中國信徒湧進了英國使館,因為這是唯一有防禦能力的駐地。77 連同誠靜怡的家人一起躲進英國使館避難的倫敦會信徒有180 名,可是在當時,誠靜怡並不知道他們是生是死。78
到6 月20 日,清政府開始與義和團合作,在自己的指揮下組織義和團,開始圍攻英國使館。該使館由400名士兵在傳教士和中國信徒的幫助下苦苦堅守,這些傳教士和中國信徒提供了主要的勞力。次日,清政府向八國聯軍宣戰。79 圍攻持續了八個星期,直到8月14日營救的部隊趕到,危機才得以解除。隨後,誠靜怡擔任了八國聯軍在北京的翻譯員和擔架手。80
倫敦會在華北的損失非常慘重。東城教會損失了過半數的教友。81 西城傳教站的156名教友中有46名遇害,其中包括傳道人及其家屬,另外還有27名失蹤。在位於義和團起源地附近的冀州(Chichou),有2名傳道人,9名執事,200名信徒遇害。在冀州北邊的燕山(Yenshan),當地的傳道人,女傳道和80名信徒被殺害並拋入火海。82 根據倫敦會的記錄,義和團通常會先掠奪差會駐地和信徒的家,並綁架年輕婦女;之後,他們將信徒斬首、剜腸或分屍;最後,他們有時會縱火焚燒信徒的房屋,並將屍首拋入火海。但總體而言,大多數基督徒寧可死,也不肯放棄他們的信仰。83 當時十九歲的誠靜怡後來參加了在北京的市民救濟工作,義和團的暴行、殉教者對信仰的堅定,肯定讓他深深體會到作為一名基督徒要付的代價。然而,有資料顯示,在此之前,就如他在義和團事件中的表現,誠靜怡認同的是傳教士及其政府的立場。由此看來傳教士通過教育而馴化的計劃看來是成功的。
79 Martin, pp. 85, 93-94; Tan, p. 96.
80 Kepler, p. 35.81 1899年,東城教會224名教會會友中,成年信徒有197人,但到了1900年,僅僅只剩107名,其中35名為成年信徒。AR (1902), p. 93.
82 George Owen, “Martyrdom in North China,” Chronicle (1901), p. 61. 對倫敦會災難的其他描述,見Chronicle (1901), pp. 6-7; A. D. Peill, “Out of Great Tribulation: How Our Christians Died in North China,” Chronicle (1902), pp. 86-87.
83 W. Hopkyn Rees, “Massacre and Pillage in Chi Chou,” Chronicle (Feb. 1901), pp. 39-40.
誠靜怡於1900 年5 月從天津的神學院畢業。在同班的四名同學之中,他排名第一。首先他被派往倫敦會位於天津和北京之間的一個傳教站事奉。74 然而,義和團運動的爆發阻止了他在畢業後返回北京,這致使他未能就任這一新的職位。到了五月底,義和團運動已經從直隸與山東的邊界區域開始往北,向天津和北京擴散。運動鋒鏑之處,義和團焚燒、掠奪和殘害中國信徒,並且常常綁架婦女信徒。75
在北京的英國傳教士於6月7日接到命令要他們躲進英國使館,但是英國公使竇納樂(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1852-1915)卻全然拒絕為中國基督徒提供保護。石牧師(Rev. J. Stonehouse)描述了倫敦會信徒們的驚恐:
因為我們是基督徒,我們將被我們自己的同胞殺害。你們的政府和我們的政府都不保護我們,我們的處境真是可憐。76幸運的是,美國公理會(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願意接納他們進入他們的駐所,該駐所由二十五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守衛。6 月13 日,義和團進入北京,傍晚,他們在搶掠之後縱火燒毀倫敦會的東城傳教站。6 月20 日,德國公使克林德(C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在臨近東城傳教站的哈德門(今崇文門)遇害。這一事件造成了恐慌,所有的外國公使和傳教士連同中國信徒湧進了英國使館,因為這是唯一有防禦能力的駐地。77 連同誠靜怡的家人一起躲進英國使館避難的倫敦會信徒有180 名,可是在當時,誠靜怡並不知道他們是生是死。78
到6 月20 日,清政府開始與義和團合作,在自己的指揮下組織義和團,開始圍攻英國使館。該使館由400名士兵在傳教士和中國信徒的幫助下苦苦堅守,這些傳教士和中國信徒提供了主要的勞力。次日,清政府向八國聯軍宣戰。79 圍攻持續了八個星期,直到8月14日營救的部隊趕到,危機才得以解除。隨後,誠靜怡擔任了八國聯軍在北京的翻譯員和擔架手。80
倫敦會在華北的損失非常慘重。東城教會損失了過半數的教友。81 西城傳教站的156名教友中有46名遇害,其中包括傳道人及其家屬,另外還有27名失蹤。在位於義和團起源地附近的冀州(Chichou),有2名傳道人,9名執事,200名信徒遇害。在冀州北邊的燕山(Yenshan),當地的傳道人,女傳道和80名信徒被殺害並拋入火海。82 根據倫敦會的記錄,義和團通常會先掠奪差會駐地和信徒的家,並綁架年輕婦女;之後,他們將信徒斬首、剜腸或分屍;最後,他們有時會縱火焚燒信徒的房屋,並將屍首拋入火海。但總體而言,大多數基督徒寧可死,也不肯放棄他們的信仰。83 當時十九歲的誠靜怡後來參加了在北京的市民救濟工作,義和團的暴行、殉教者對信仰的堅定,肯定讓他深深體會到作為一名基督徒要付的代價。然而,有資料顯示,在此之前,就如他在義和團事件中的表現,誠靜怡認同的是傳教士及其政府的立場。由此看來傳教士通過教育而馴化的計劃看來是成功的。
79 Martin, pp. 85, 93-94; Tan, p. 96.
80 Kepler, p. 35.81 1899年,東城教會224名教會會友中,成年信徒有197人,但到了1900年,僅僅只剩107名,其中35名為成年信徒。AR (1902), p. 93.
82 George Owen, “Martyrdom in North China,” Chronicle (1901), p. 61. 對倫敦會災難的其他描述,見Chronicle (1901), pp. 6-7; A. D. Peill, “Out of Great Tribulation: How Our Christians Died in North China,” Chronicle (1902), pp. 86-87.
83 W. Hopkyn Rees, “Massacre and Pillage in Chi Chou,” Chronicle (Feb. 1901), pp. 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