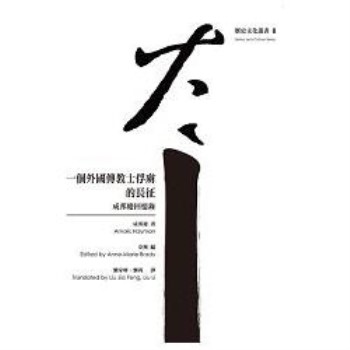譯者前言
劉家峰
目前所見關於紅軍長征的歷史敍述中,最具史料價值的文獻應該是《紅軍長征記》,這是一本由眾多親歷者回憶錄編纂而成的作品。這些回憶錄都是在長征結束不久完成,沒有後來的思想路線鬥爭等條條框框的限制,因而被當代史家高華看作「最真實的長征記憶」。
然而,在長征親歷者的歷史敍述中,有兩位內地會傳教士的回憶錄值得特別留意,分別是來自瑞士的薄復禮(Rudolf Alfred Bosshardt,1897–1993)和來自紐西蘭的成邦慶(Arnolis Hayman,1890–1971)。他們在1934年10月1日和2日在貴州被蕭克領導的紅六軍團扣押,後跟隨紅軍長征長達一年多。薄復禮的回憶錄於1936年11月在英國出版。成邦慶的回憶錄稍晚於薄復禮完成,但卻一直湮沒無聞,直到2003年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安琳教授(Anne-Marie Brady)在澳大利亞發現原稿,整理後於2010年在美國出版,書名直譯為《長征路上的一位外國傳教士——內地會成邦慶回憶錄》。
成邦慶回憶錄並不長,譯成中文不足九萬字,但內容豐富,有他們被俘、談判與釋放的經過,也有關於紅軍戰鬥、行軍的艱難及途中的政治宣傳等,當然更多內容是關於長征途中的日常生活細節。這部回憶錄對我們長征史、黨史研究都是不可多得的史料,筆者覺得有必要把這部回憶錄介紹給國內學術界。如果把這部回憶錄跟以前的長征敍述做一比較,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其價值。下面就此再稍加鋪陳。
首先,從回憶錄的主題來看,正如蕭克評論薄復禮回憶錄的價值一樣,成邦慶回憶錄的重要性在於他忠實地「記錄了紅軍長征的一個側面」。蕭克認為歷史是多方面的,中國工農紅軍的歷史也不例外,也是一個多側面的。他提醒研究者不要只「喜歡看它的正面,不想看它的側面,更不敢看它的背面」。薄復禮、成邦慶回憶錄正是這樣一部反映紅軍長征「側面」、「背面」的著作,這對我們今天全面理解當時紅軍長征的艱難複雜歷程無疑具有重要的補充作用。
其次,從敍述的內容主體看,以往長征敍述的主體集中在中央紅軍,而紅二、紅四方面軍以及紅二十五軍的長征則很少涉及,而成邦慶(包括薄復禮)回憶錄所敍述的主體恰好是紅二方面軍(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合編而成)。成邦慶跟隨紅軍的413天,正好是紅六軍團第一次長征的過程。該回憶錄對復原紅二方面軍的長征歷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再次,成邦慶回憶錄的重要價值還在於它對於長征途中日常生活的描述。他所敍述的這段長征,有激烈的戰鬥和行軍的驚險,但更多是日常生活的細節。他的敍述通常都是不加修飾,直抒胸臆,頗具個人化色彩,大大彌補了以前長征敍述中有關日常生活細節的不足,讓讀者如同置身歷史現場。
當然,還須提及一點,即讀者在閱讀成邦慶(包括薄復禮)的回憶錄時要注意,這兩部作品本意是用長征這段經歷來感恩上帝、為上帝做見證的證道作品,並非是要弘揚紅軍的長征精神。這點從他們原有的書名即可看出。薄復禮著作的第一本書英文書名是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直譯是《抑制之手——為基督在華被俘》,第二本書原名是The Guiding Hand: Captivity and Answered Prayer in China,直譯是《舵手:在華被俘與神的回應》,成邦慶的回憶錄原來有個題目Who Shall Separate? 直譯為《誰能隔絕?》,這些題目都頗具基督教意味,語句直接出自《聖經》。我們在閱讀、使用這些著作時要注意當時寫作的特定語境。還有,本書主人公對紅軍長征的個別敍述與我們今天的認識有所不同,可能還有一些對紅軍的不實之詞,但出於保存史料、求實求真的目的,翻譯出版時不做任何刪改,這點請讀者閱讀使用時多加注意。
本書涉及湘鄂黔川等省的地名,譯者儘量回譯到當時的名稱,並注明現在的地名。凡不確定的地名,括弧內都附有原英文名稱。所涉及的人名,凡有查到外國人自取的漢名,一律用其漢名,沒有漢名或查不到的則直接音譯。本書所引用的聖經經文,譯者採用了國內通行的和合本翻譯。本書註腳,部分是原編者所加,部分是譯者所加,凡譯者所加注釋,後面都標有「譯者注」。(節錄自本書譯者前言)
劉家峰
目前所見關於紅軍長征的歷史敍述中,最具史料價值的文獻應該是《紅軍長征記》,這是一本由眾多親歷者回憶錄編纂而成的作品。這些回憶錄都是在長征結束不久完成,沒有後來的思想路線鬥爭等條條框框的限制,因而被當代史家高華看作「最真實的長征記憶」。
然而,在長征親歷者的歷史敍述中,有兩位內地會傳教士的回憶錄值得特別留意,分別是來自瑞士的薄復禮(Rudolf Alfred Bosshardt,1897–1993)和來自紐西蘭的成邦慶(Arnolis Hayman,1890–1971)。他們在1934年10月1日和2日在貴州被蕭克領導的紅六軍團扣押,後跟隨紅軍長征長達一年多。薄復禮的回憶錄於1936年11月在英國出版。成邦慶的回憶錄稍晚於薄復禮完成,但卻一直湮沒無聞,直到2003年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安琳教授(Anne-Marie Brady)在澳大利亞發現原稿,整理後於2010年在美國出版,書名直譯為《長征路上的一位外國傳教士——內地會成邦慶回憶錄》。
成邦慶回憶錄並不長,譯成中文不足九萬字,但內容豐富,有他們被俘、談判與釋放的經過,也有關於紅軍戰鬥、行軍的艱難及途中的政治宣傳等,當然更多內容是關於長征途中的日常生活細節。這部回憶錄對我們長征史、黨史研究都是不可多得的史料,筆者覺得有必要把這部回憶錄介紹給國內學術界。如果把這部回憶錄跟以前的長征敍述做一比較,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其價值。下面就此再稍加鋪陳。
首先,從回憶錄的主題來看,正如蕭克評論薄復禮回憶錄的價值一樣,成邦慶回憶錄的重要性在於他忠實地「記錄了紅軍長征的一個側面」。蕭克認為歷史是多方面的,中國工農紅軍的歷史也不例外,也是一個多側面的。他提醒研究者不要只「喜歡看它的正面,不想看它的側面,更不敢看它的背面」。薄復禮、成邦慶回憶錄正是這樣一部反映紅軍長征「側面」、「背面」的著作,這對我們今天全面理解當時紅軍長征的艱難複雜歷程無疑具有重要的補充作用。
其次,從敍述的內容主體看,以往長征敍述的主體集中在中央紅軍,而紅二、紅四方面軍以及紅二十五軍的長征則很少涉及,而成邦慶(包括薄復禮)回憶錄所敍述的主體恰好是紅二方面軍(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合編而成)。成邦慶跟隨紅軍的413天,正好是紅六軍團第一次長征的過程。該回憶錄對復原紅二方面軍的長征歷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再次,成邦慶回憶錄的重要價值還在於它對於長征途中日常生活的描述。他所敍述的這段長征,有激烈的戰鬥和行軍的驚險,但更多是日常生活的細節。他的敍述通常都是不加修飾,直抒胸臆,頗具個人化色彩,大大彌補了以前長征敍述中有關日常生活細節的不足,讓讀者如同置身歷史現場。
當然,還須提及一點,即讀者在閱讀成邦慶(包括薄復禮)的回憶錄時要注意,這兩部作品本意是用長征這段經歷來感恩上帝、為上帝做見證的證道作品,並非是要弘揚紅軍的長征精神。這點從他們原有的書名即可看出。薄復禮著作的第一本書英文書名是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直譯是《抑制之手——為基督在華被俘》,第二本書原名是The Guiding Hand: Captivity and Answered Prayer in China,直譯是《舵手:在華被俘與神的回應》,成邦慶的回憶錄原來有個題目Who Shall Separate? 直譯為《誰能隔絕?》,這些題目都頗具基督教意味,語句直接出自《聖經》。我們在閱讀、使用這些著作時要注意當時寫作的特定語境。還有,本書主人公對紅軍長征的個別敍述與我們今天的認識有所不同,可能還有一些對紅軍的不實之詞,但出於保存史料、求實求真的目的,翻譯出版時不做任何刪改,這點請讀者閱讀使用時多加注意。
本書涉及湘鄂黔川等省的地名,譯者儘量回譯到當時的名稱,並注明現在的地名。凡不確定的地名,括弧內都附有原英文名稱。所涉及的人名,凡有查到外國人自取的漢名,一律用其漢名,沒有漢名或查不到的則直接音譯。本書所引用的聖經經文,譯者採用了國內通行的和合本翻譯。本書註腳,部分是原編者所加,部分是譯者所加,凡譯者所加注釋,後面都標有「譯者注」。(節錄自本書譯者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