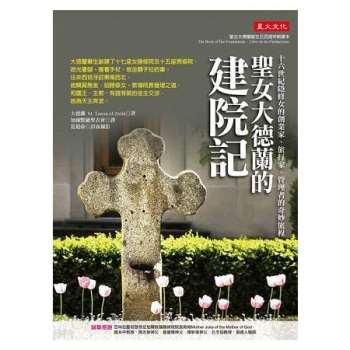大德蘭的旅行紀實
那時(一五七五年四月),碩士神父,熱羅尼莫.古嵐清會士,來貝雅斯看我,我們從未謀面,雖然我極渴望會見他;是的,我們有時信件往返。當我獲悉他在這裡,令我感到欣喜至極,因為一些對他很好的傳聞,使我非常渴望會見他。然而,當我開始與他交談,我的喜樂非常非常的大,因為.按照他之令我滿意,我覺得那些對我稱讚他的人,其實是不認識他的。
在此期間,送來了卡拉瓦卡的建院許可證書,但卻與我要求的宗旨不符;因此,必須再呈送到宮廷,因為我已寫信給那些建院恩人,如果缺少某項特殊的申請,絕不可建院,所以,必須再呈請宮廷。要在那裡等這麼久,使我覺得相當難受,我想要返回卡斯提,然而,由於熱羅尼莫會士神父在那裡,那修院屬他管理,他是整個卡斯提會省的代理(省會長),沒有他的許可,什麼都不能做;所以我和他談這事。
他認為,一旦我離開,卡拉瓦卡的建院也會不了了之,同時,去塞維亞建院,則是獻給天主的很大服事,他認為這是非常容易的事,因為已經有些人向他這麼請求,他們非常能幹又很富有,馬上就會有房子;還有,塞維亞的總主教這麼恩待本修會,他相信,在那裡建院,會獻給天主很大的服事;於是,他安排去卡拉瓦卡的院長和修女,轉往塞維亞。我,雖然極力推辭,不要在安大路西亞建立我們的隱修院,由於我看到那是長上的決定,我立刻順從,雖然我已經決定要建立另一座新院,甚至也有一些非常重大的理由,不要去塞維亞。
立刻著手準備上路,因為天氣開始酷熱起來,宗座代理古嵐清神父,那時正蒙教廷大使召見,我們動身前往塞維亞,我的好友伴是:胡利安.亞味拉神父、安東尼奧.凱堂及一位赤足會士,陪伴我們上路。我們乘坐在遮蔽得很好的馬車上,這是我們旅行的模式,當我們住進旅店時,我們修女住在一個房間,無論那房間好或不好,只要有就住進,有位修女在門口處,接收我們需要的物品,甚至和我們同來的友伴,也不許進入房間內。雖然我們快速趕路,抵達塞維亞時,已是一五七五年五月廿六日、聖三主日前的星期四,一路上受盡猛烈的酷暑;因為,雖然沒有在午休時間行路,修女們,我對妳們說,由於陽光直射馬車,進到馬車內,彷彿進入煉獄一般。有時我想的是在地獄裡,有時則認為是做了些什麼(即為天主忍受酷暑),為天主而忍受,路途中,那些修女滿懷高興和喜樂。因為和我同行的六位修女是這樣的修女,我覺得,我敢和她們一起去土耳其人的地方,而且,她們是剛毅的,或者,更好說,我們的上主賦予她們剛毅,願意為祂受苦,因為這是她們的渴望,也是談話的主題,她們是祈禱和克苦的精修者,由於她們必須留守在這麼遠的地方,我盡力安排的修女,是我認為最適當的人選。
聖神降臨前,有一天,天主給她們一個相當大的磨難,就是我發了高燒。我相信她們對天主的呼喊,足以使我的病況不再惡化;發這樣的高燒,不繼續惡化,是我一輩子從未有過的事。事情是這樣的,我好像在昏睡,不省人事。
她們把水灑在我的臉上,可是太陽這麼熾熱,所以也得不到什麼清涼。
我不想對妳們略而不談,在此困境中,我們居住的壞旅店:給我們的是一間空無片瓦的小房間,沒有窗子,如果把門打開,房間內滿是陽光。要知道,那裡的陽光可不像在卡斯提,是極累人的。她們讓我躺在一張床上,我覺得,更好是把我放在地面上;因為這個床到處凹凸不平,我不知怎能躺在上面,因為彷彿在尖銳的石頭上,生病真是不得了的事啊!健康時,樣樣都容易忍受。最後,我決定,更好是我起身,我們離開那裡,我覺得在田野忍受太陽,比在那個小房間裡更好。處在地獄中的可憐人,會是何等光景呢?他們的處境必是永遠不變!雖然接踵而至的磨難,看來好像有些減輕。臨於我的遭遇是,在某處有個非常強烈的痛苦,然而在別處,又遭逢另一個這麼大的痛苦,我覺得好像因改變而減輕(其實並沒有!);這裡就是像這樣。按我所記得的,看到自己生病,我並不覺得痛苦;修女們忍受的痛苦遠超過我。應是上主的保祐,我發的高燒沒有持續到次日。之前不久,我不知道是不是兩天前,我們碰到另一件事,使我們陷於窘境,那時我們正乘船渡過瓜達爾幾微河;到了馬車要過河時,不可能用繩索直接過河,必須在河中轉彎,雖然用繩索轉彎,多少也有些幫助;然而,不巧的是繩索鬆脫,或是說,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帶馬車的小船,既沒有繩索,也沒有槳。看到渡船夫如此焦急,我對他深感同情,遠超過對危險的掛慮。我們(指修女們)在祈禱。其他的人則是高聲喊叫。
正好有個紳士,他在附近的城堡上望見我們,深表同情,派人來幫助,因為在那時,繩索還不是完全鬆脫,我們的兄弟(指同行的男士)正用盡全力,拉住繩索;但是,水的衝力這麼猛烈,有的人竟然撲倒在地上。渡船夫的一個兒子,實在引起我深切的虔敬之情,使我永遠難忘;我看他大約是十或十一歲,由於看見爸爸在困苦中,他那樣辛勞地工作,這使我讚美我們的上主。然而,至尊陛下總是以憐憫給予磨難,這裡就是這樣;這隻小船恰好擱淺在沙地上,那是一處水不多的地方,因此能予以補救。因為夜晚已到,如果不是有城堡來的人帶領,我們真不知要如何繼續上路。
我並沒有想要敘述這些事,因為這是一些不甚重要的事,我已說了相當多路上不好的遭遇。我之詳述這事,是受人的堅持請求。對我而言,比所說的這些還要大的磨難是,聖神降臨節後的第二天發生的。我們趕在早晨抵達哥多華,去望彌撒而不會被人看見。當我們要過橋時,馬車需要有地方官發給的通行證才能通過。在這裡等了兩個多小時,因為地方官還沒有起床,也吸引了許多人過來,想要知道誰來到這裡。我們對這事並不在意,因為馬車遮掩得很好,他們不能看見什麼。通行證終於到了,我們的馬車卻通不過橋門;必須鋸掉它們,或說,我不知道是什麼,這樣,又用了一段時間。最後,我們抵達聖堂,胡利安.亞味拉神父主持彌撒,聖堂內充滿了人:因為,這聖堂是奉獻給聖神的,我們卻不知道這事,所以,舉行的是極隆重的慶節,也有證道。當我看見這樣,覺得非常難過,我認為,還是我們離開,不要望彌撒,比進去當中,引來這麼多的騷動要好得多了。胡利安.亞味拉神父卻不以為然,由於他是神學家,我們都得順從他的意見;其他的同伴或許會順從我的主意,那可能是個不好的意見,雖然我不知道,是否我只信賴自己的看法。我們在聖堂的附近下馬車,雖然如此,沒有人能看得見我們的面容,因為我們的臉上經常戴著大紗,看見我們戴著大紗,穿著白色粗羊毛斗篷,還有腳上穿著麻繩編織的涼鞋,這些已足夠引起騷動,真的就是這樣一團騷亂。必是這驚嚇使得我的高燒完全退去;的確,這對我和所有的人,都是好大的驚嚇。
開始進入聖堂時,一位友善的好人走近我,幫助我們隔開人群。我懇求他帶我們到一間祈禱室。他這麼做了,且把祈禱室的門關上,陪伴我們,直到我們離開聖堂。不多幾天後,他來塞維亞,對我們修會的一位神父說,為了所做的那件好事,他覺得天主賞報了他,使他得到,或說給他,一大筆資產,這是他早已忘記的。女兒們,我對妳們說,雖然妳們可能認為這算不了什麼,對我來說,卻是曾經歷的糟糕時刻之一,因為人群的喧鬧,彷彿是一群鬥牛進入聖堂。所以,我等不及要離開那地方;由於附近沒有可午休的地方,我們在一座橋下休息。
五月廿六日,我們到達塞維亞,來到瑪利安諾神父為我們租好的房子,這是他已經告知的事,我想一切都已辦妥:因為,如我說的,總主教多麼恩待赤足會士,他有時寫信給我,表示對我疼愛有加。但這都不足以使我避免相當大的磨難,因為是天主願意如此的。總主教非常反對建立單靠施捨、守貧的女隱修院,他是有道理的。這是難處,或更好說,為完成建院的工作,是益處;因為,如果在上路之前,對總主教說了建立的是守貧隱院這事,我肯定他不會同意。因為代理神父和瑪利安諾神父(我的來到也帶給他極大欣喜)確定至極,由於我的來到,他們為總主教做了極大的服務,所以,之前並沒有對他說這事;如我說的,想到要是他們這麼做,可能會犯下許多的錯誤。因為在建立其他的隱修院時,我首先謀求的是當地主教的許可,如神聖大公會議(即特利騰大公會議)所命令的;這裡,我們不只認為總主教一定給許可,如我說的,還認定是給他的一個大服事,也真是這樣,不過,這是後來才應驗的;沒有一次的建院,上主願意我沒有許多艱難的:有時是這樣,有時是那樣。
那時(一五七五年四月),碩士神父,熱羅尼莫.古嵐清會士,來貝雅斯看我,我們從未謀面,雖然我極渴望會見他;是的,我們有時信件往返。當我獲悉他在這裡,令我感到欣喜至極,因為一些對他很好的傳聞,使我非常渴望會見他。然而,當我開始與他交談,我的喜樂非常非常的大,因為.按照他之令我滿意,我覺得那些對我稱讚他的人,其實是不認識他的。
在此期間,送來了卡拉瓦卡的建院許可證書,但卻與我要求的宗旨不符;因此,必須再呈送到宮廷,因為我已寫信給那些建院恩人,如果缺少某項特殊的申請,絕不可建院,所以,必須再呈請宮廷。要在那裡等這麼久,使我覺得相當難受,我想要返回卡斯提,然而,由於熱羅尼莫會士神父在那裡,那修院屬他管理,他是整個卡斯提會省的代理(省會長),沒有他的許可,什麼都不能做;所以我和他談這事。
他認為,一旦我離開,卡拉瓦卡的建院也會不了了之,同時,去塞維亞建院,則是獻給天主的很大服事,他認為這是非常容易的事,因為已經有些人向他這麼請求,他們非常能幹又很富有,馬上就會有房子;還有,塞維亞的總主教這麼恩待本修會,他相信,在那裡建院,會獻給天主很大的服事;於是,他安排去卡拉瓦卡的院長和修女,轉往塞維亞。我,雖然極力推辭,不要在安大路西亞建立我們的隱修院,由於我看到那是長上的決定,我立刻順從,雖然我已經決定要建立另一座新院,甚至也有一些非常重大的理由,不要去塞維亞。
立刻著手準備上路,因為天氣開始酷熱起來,宗座代理古嵐清神父,那時正蒙教廷大使召見,我們動身前往塞維亞,我的好友伴是:胡利安.亞味拉神父、安東尼奧.凱堂及一位赤足會士,陪伴我們上路。我們乘坐在遮蔽得很好的馬車上,這是我們旅行的模式,當我們住進旅店時,我們修女住在一個房間,無論那房間好或不好,只要有就住進,有位修女在門口處,接收我們需要的物品,甚至和我們同來的友伴,也不許進入房間內。雖然我們快速趕路,抵達塞維亞時,已是一五七五年五月廿六日、聖三主日前的星期四,一路上受盡猛烈的酷暑;因為,雖然沒有在午休時間行路,修女們,我對妳們說,由於陽光直射馬車,進到馬車內,彷彿進入煉獄一般。有時我想的是在地獄裡,有時則認為是做了些什麼(即為天主忍受酷暑),為天主而忍受,路途中,那些修女滿懷高興和喜樂。因為和我同行的六位修女是這樣的修女,我覺得,我敢和她們一起去土耳其人的地方,而且,她們是剛毅的,或者,更好說,我們的上主賦予她們剛毅,願意為祂受苦,因為這是她們的渴望,也是談話的主題,她們是祈禱和克苦的精修者,由於她們必須留守在這麼遠的地方,我盡力安排的修女,是我認為最適當的人選。
聖神降臨前,有一天,天主給她們一個相當大的磨難,就是我發了高燒。我相信她們對天主的呼喊,足以使我的病況不再惡化;發這樣的高燒,不繼續惡化,是我一輩子從未有過的事。事情是這樣的,我好像在昏睡,不省人事。
她們把水灑在我的臉上,可是太陽這麼熾熱,所以也得不到什麼清涼。
我不想對妳們略而不談,在此困境中,我們居住的壞旅店:給我們的是一間空無片瓦的小房間,沒有窗子,如果把門打開,房間內滿是陽光。要知道,那裡的陽光可不像在卡斯提,是極累人的。她們讓我躺在一張床上,我覺得,更好是把我放在地面上;因為這個床到處凹凸不平,我不知怎能躺在上面,因為彷彿在尖銳的石頭上,生病真是不得了的事啊!健康時,樣樣都容易忍受。最後,我決定,更好是我起身,我們離開那裡,我覺得在田野忍受太陽,比在那個小房間裡更好。處在地獄中的可憐人,會是何等光景呢?他們的處境必是永遠不變!雖然接踵而至的磨難,看來好像有些減輕。臨於我的遭遇是,在某處有個非常強烈的痛苦,然而在別處,又遭逢另一個這麼大的痛苦,我覺得好像因改變而減輕(其實並沒有!);這裡就是像這樣。按我所記得的,看到自己生病,我並不覺得痛苦;修女們忍受的痛苦遠超過我。應是上主的保祐,我發的高燒沒有持續到次日。之前不久,我不知道是不是兩天前,我們碰到另一件事,使我們陷於窘境,那時我們正乘船渡過瓜達爾幾微河;到了馬車要過河時,不可能用繩索直接過河,必須在河中轉彎,雖然用繩索轉彎,多少也有些幫助;然而,不巧的是繩索鬆脫,或是說,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帶馬車的小船,既沒有繩索,也沒有槳。看到渡船夫如此焦急,我對他深感同情,遠超過對危險的掛慮。我們(指修女們)在祈禱。其他的人則是高聲喊叫。
正好有個紳士,他在附近的城堡上望見我們,深表同情,派人來幫助,因為在那時,繩索還不是完全鬆脫,我們的兄弟(指同行的男士)正用盡全力,拉住繩索;但是,水的衝力這麼猛烈,有的人竟然撲倒在地上。渡船夫的一個兒子,實在引起我深切的虔敬之情,使我永遠難忘;我看他大約是十或十一歲,由於看見爸爸在困苦中,他那樣辛勞地工作,這使我讚美我們的上主。然而,至尊陛下總是以憐憫給予磨難,這裡就是這樣;這隻小船恰好擱淺在沙地上,那是一處水不多的地方,因此能予以補救。因為夜晚已到,如果不是有城堡來的人帶領,我們真不知要如何繼續上路。
我並沒有想要敘述這些事,因為這是一些不甚重要的事,我已說了相當多路上不好的遭遇。我之詳述這事,是受人的堅持請求。對我而言,比所說的這些還要大的磨難是,聖神降臨節後的第二天發生的。我們趕在早晨抵達哥多華,去望彌撒而不會被人看見。當我們要過橋時,馬車需要有地方官發給的通行證才能通過。在這裡等了兩個多小時,因為地方官還沒有起床,也吸引了許多人過來,想要知道誰來到這裡。我們對這事並不在意,因為馬車遮掩得很好,他們不能看見什麼。通行證終於到了,我們的馬車卻通不過橋門;必須鋸掉它們,或說,我不知道是什麼,這樣,又用了一段時間。最後,我們抵達聖堂,胡利安.亞味拉神父主持彌撒,聖堂內充滿了人:因為,這聖堂是奉獻給聖神的,我們卻不知道這事,所以,舉行的是極隆重的慶節,也有證道。當我看見這樣,覺得非常難過,我認為,還是我們離開,不要望彌撒,比進去當中,引來這麼多的騷動要好得多了。胡利安.亞味拉神父卻不以為然,由於他是神學家,我們都得順從他的意見;其他的同伴或許會順從我的主意,那可能是個不好的意見,雖然我不知道,是否我只信賴自己的看法。我們在聖堂的附近下馬車,雖然如此,沒有人能看得見我們的面容,因為我們的臉上經常戴著大紗,看見我們戴著大紗,穿著白色粗羊毛斗篷,還有腳上穿著麻繩編織的涼鞋,這些已足夠引起騷動,真的就是這樣一團騷亂。必是這驚嚇使得我的高燒完全退去;的確,這對我和所有的人,都是好大的驚嚇。
開始進入聖堂時,一位友善的好人走近我,幫助我們隔開人群。我懇求他帶我們到一間祈禱室。他這麼做了,且把祈禱室的門關上,陪伴我們,直到我們離開聖堂。不多幾天後,他來塞維亞,對我們修會的一位神父說,為了所做的那件好事,他覺得天主賞報了他,使他得到,或說給他,一大筆資產,這是他早已忘記的。女兒們,我對妳們說,雖然妳們可能認為這算不了什麼,對我來說,卻是曾經歷的糟糕時刻之一,因為人群的喧鬧,彷彿是一群鬥牛進入聖堂。所以,我等不及要離開那地方;由於附近沒有可午休的地方,我們在一座橋下休息。
五月廿六日,我們到達塞維亞,來到瑪利安諾神父為我們租好的房子,這是他已經告知的事,我想一切都已辦妥:因為,如我說的,總主教多麼恩待赤足會士,他有時寫信給我,表示對我疼愛有加。但這都不足以使我避免相當大的磨難,因為是天主願意如此的。總主教非常反對建立單靠施捨、守貧的女隱修院,他是有道理的。這是難處,或更好說,為完成建院的工作,是益處;因為,如果在上路之前,對總主教說了建立的是守貧隱院這事,我肯定他不會同意。因為代理神父和瑪利安諾神父(我的來到也帶給他極大欣喜)確定至極,由於我的來到,他們為總主教做了極大的服務,所以,之前並沒有對他說這事;如我說的,想到要是他們這麼做,可能會犯下許多的錯誤。因為在建立其他的隱修院時,我首先謀求的是當地主教的許可,如神聖大公會議(即特利騰大公會議)所命令的;這裡,我們不只認為總主教一定給許可,如我說的,還認定是給他的一個大服事,也真是這樣,不過,這是後來才應驗的;沒有一次的建院,上主願意我沒有許多艱難的:有時是這樣,有時是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