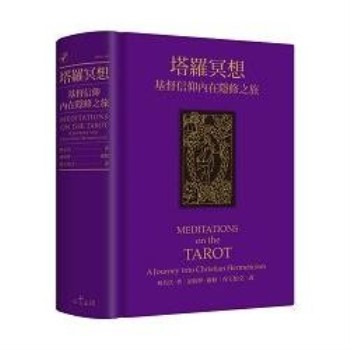第一封信:魔法師
風隨意吹動,
你聽見它的聲音,
卻不知道它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也都是這樣。——《約翰福音》第3 章,第8 節
祕密地進入這愉悅的暗夜,
眼前空無一物,
連應當看見的也沒出現,
雖然缺少別的光和指引,
藏在我心底的那個東西依舊燃燒著。——聖十字若望
親愛的不知名朋友:
第一段主耶穌的話語如同鑰匙一樣開啟了「魔法師」的門,而「魔法師」又是進入其他大阿卡納之門的鑰匙,因此我特別選它作為第一封信的開場白。接著我引述了聖十字若望(St. John of the Cross)在《靈魂之歌》(Songs of the Soul)裡的一段詩句,原因是它能喚醒心靈深處的東西,而這正是第一張以及後續所有大阿卡納的主旨。
所謂的大阿卡納其實是可信的、被印證過的象徵系統;人們可以藉由它們所蘊含的「魔法、心智、精神及道德的作用力」,激發出嶄新的想法、概念、觀點和渴望,因此你必須採取比探究或解釋更深的方式來體認它們。你必須處在一種深觀狀態,而且得一直探究下去,才能發揮它們的作用力。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塔羅冥想,心底隱密的部分會變得活躍而有所收穫。聖十字若望所謂的「暗夜」,指的就是回到內在這個隱密部分。這項工作只能在獨處情況下達成,所以比較適合隱居生活。
大阿卡納既不是寓言也不是祕密。寓言是運用象徵性故事來表達抽象道理,祕密則是蓄意隱藏某些事實、程序、手法或原理,以免別人因理解而開始付諸練習。大阿卡納兼具了隱藏和揭露的功能,關鍵就在於冥想能進展到多深。事實上,它們揭露的並不是什麼刻意隱藏的祕密,而是必須有真實體悟才能獲益的奧祕。它們必須活躍地存在於意識甚至潛意識裡,這樣我們才有條件發現新的事物、開創新的想法、孕育新的藝術創作。簡言之,大阿卡納豐富了我們在靈性生活領域的創作,它是一種激發心靈與精神成長的「酵母」或「酵素」,它的圖像則是傳達這些「酵母」或「酵素」的媒介——當然,領受者的心智與道德都必須做好準備,也就是尚未罹患最嚴重的靈性病:驕矜自滿。如果說奧祕比祕密更崇高,那麼神祕又更超越了奧祕。神祕的密契體驗不只是激發心靈成長的酵素,更可以說是一件生死大事。處在密契體驗裡,一切心理與精神的動機都會改變,也就是意識產生了徹底蛻變。教會的七件聖事(the seven sacraments of the Church)就是從同一道神祕淨光放射出來的七彩光芒,而進入這淨光便是「重生」,也是耶穌啟發尼哥德慕(Nicodemus)的那個深夜裡所談到的「神聖啟蒙」(The Great Initiation)。
如果將「神聖啟蒙」理解為「重生」或「進入神祕淨光」,我們就會明白主耶穌指的是沒有任何人能夠為人啟蒙。只有上界的主宰可以為人帶來永恆的神聖啟蒙。我們的指引者在天上,地上接觸到的都只是祂的學子;學子們之所以認出對方,是因為「彼此相愛」(《約翰福音》第13 章,第35節)。除了那唯一的啟蒙者之外,世上沒有任何人可以做我們的主人。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世間永遠有一些精神導師會繼續傳授他們的教誨和祕密知識,讓學生變成所謂的「入門者」——但這一切都跟神聖啟蒙無關。
基於此理,關懷人類的隱修士是不會擅自為別人做這件事的。真正的隱修士不會自稱為他人的「大師」或「啟蒙師」,因為每個人都是彼此教學相長的靈修夥伴。若要舉例,應該找不到比聖安東尼(St. Anthony the Great,又譯聖安當)的為人處事更佳的典範:他以最真摯的心去對待他所探訪的虔誠信徒,在每個人身上他都能發現自認不足的熱情和自制力。從某個人身上他觀察到和藹,從另一個人身上他看到祈禱時的認真;他學習他們的平和與仁慈,留意他們如何徹夜禱告、研讀聖經;他讚嘆某人的堅忍毅力,欽佩另一個人能夠斷食和席地而臥;他也仔細觀察他們的溫順和節制;在所有人的身上他都看到了對主耶穌的忠誠皈依,以及彼此之間的愛。他滿載而歸後,回復到節制慾望的生活,將這些人身上的美德全心實踐出來。(St. Athanasius, The life of Saint Anthony, ch. 4; trsl. R. T. Meyer, Westminster, 1950, p. 21)
隱修士必須有相同的自我要求態度,特別是在各種知識與科學的研習上面——自然科學、歷史、語言、哲學、神學、象徵系統及聖傳等。總地來說,隱修士要通曉的就是「學習的藝術」,但是在其中引領和激發我們的,卻是如酵素般的大阿卡納。換句話說,大阿卡納如同一所完整的、全面的、無價的學院,能夠供人冥思、做學問以及拓展性靈——一所和「學習的藝術」有關的研習院。親愛的朋友,基督隱修之道(Christian Hermeticism)沒有任何意圖與宗教或正宗科學競爭。如果想在其中發現「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哲學」或「真正的科學」,那就是找錯了方向。基督隱修士扮演的角色並不是大師而是服務者。他們無法佯稱(這麼做是幼稚的)自己的作為超越虔信者的真誠、科學家的卓越成就,或是藝術天才的傑作。隱修士不會謹守任何學術祕密,他們和所有人一樣尚未發現治癌藥方。如果發現新的藥方卻不讓世人知道,那真是太荒謬了。若是有專家發明了治癌良藥,他們將會在第一時間向這位人類的恩人致上最大敬意。
同樣地,隱修士也不吝於讚揚像亞西西的聖方濟(Francis of Assisi)這樣的「顯教」派信仰者。他們很清楚所有的虔誠信徒都有潛力成為聖方濟。只要是虔信者、科學家或藝術家,無論男女都是優秀的學習對象。這樣的隱修者不會自認是更優越、更虔誠、更精通或更有能力的人。他們不會以自己認同的密教取代現存的顯教、以特定的科學觀點取代現有的科學理論,也不會以某種藝術派別取代昨日或今日的主流藝術。他們的知識不具備任何現實利益,也不帶有凌駕於現有的宗教、科學或藝術之上的超越性。他們擁有的僅僅是與人分享的精神,但這份精神的使命究竟是什麼?守護它有什麼意義?我想拿以下的例子來說明。
親愛的朋友,你們知道法國、德國、英國和其他國家有許多人——特別是作家——都在傳佈所謂「雙教會」的理念。雙教會指的就是彼得與約翰的宗派,也被稱為聖彼德和聖約翰世代。教義內容是關於彼得世代的終止可能即將來臨,亦即超越彼得世代所象徵的教宗政治,由最後晚餐上靠在主耶穌胸前聆聽其心跳聲的約翰精神取代。換言之,彼得的「顯教派」(exoteric church)將讓位給約翰的「密教派」(esotericchurch),這意味著終極解脫的教義會被發揚光大。約翰雖然自願跟隨彼得這位十二門徒中的領袖,卻不願成為彼得過世後的繼承人。這位聆聽過耶穌心跳聲的愛徒,自始至終都代表耶穌的心,而且一向是它的守護者。基於此理,他一直不肯扮演教會領導的角色。由於心臟的使命不是要取代腦子,所以約翰的使命也不是要取代彼得。「心」當然是身體與靈魂的守護者,但是在一個完整的有機體中,「腦子」才是主宰,負責做出決策及指揮,為組織找到達成任務方式的方式。約翰的使命是維護教會的活力與精神直到基督再現。這就是他不要求任何教會職位的原因。他活化這個結構卻不指導它的作為。
隱修之道,現存的隱修傳統,一直守護著純正文化的共通精神。我再強調一次,隱修士一直聆聽著人類精神層面的心跳聲。他們不可能不守護宗教、科學及藝術的精髓。在上述這些領域裡他們沒有任何特權,其中的聖者、真正的科學家或藝術天才都是他們的學長。他們願意為這些領域裡的神祕心跳而存在—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受到約翰的啟發,他們無法佯稱自己是上述領域或政治組織的領袖,但也不會錯過為人類的精神泉源注入活力的機會—與天主教的聖餐式有著類似的意義。隱修之道是——也僅僅是——一種具有活化功能的「酵素」,它激勵著人類在心靈成長的有機過程中產生「發酵」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隱修之道是一種密修法門,也是密契重生或神聖啟蒙之前要做的功課。
現在讓我們回到第一張大阿卡納。這張卡的內容是什麼呢?
一名年輕男子戴著一頂雙曲線大帽子,站在一張小桌子後面。桌面上有一個黃色瓶子,三個黃色小圓璧,另外有四個紅色圓璧被分成兩疊,還有一個紅色杯子和兩顆骰子,一把出鞘的刀最後是可以容納桌上所有物件的黃色袋子。這名男子是魔法師,他右邊的手握著一根棍子,另一手拿著一個黃色的球狀物(從讀者的方向來看)。雖然雙手都握有物件,他臉上的表情卻泰然自若,沒有任何緊張、用力或慌亂的樣子。他的動作是如此輕鬆自然—看起來就像是在玩遊戲而非認真工作。他沒有留意手上的動作,眼睛也是看著別處的。塔羅一系列的象徵符號或揭露奧祕的啟示,就是從這張魔法師卡展開了序幕,而它代表的居然是一個玩雜耍的人,真是令人驚訝!這該如何解釋呢?
這張大阿卡納背後的奧義和個人的實修狀態及心靈真相有關,也是其他二十一張大阿卡納的根基。如果不去理解箇中意涵(認知和實修上),面對其他的大阿卡納勢必不得其門而入。它是「奧祕中的奧祕」,揭露了進入這所心靈研習院必須具備的認識和意願。簡單地說,實修的第一個基本法則就是:學習不用力的專注;把工作轉化為遊戲;讓你願意承受的軛變得不費力,讓你背負的擔子變得輕鬆。這段忠告、指示甚至可以說是訓誡,不論你對它的感受是什麼,都必須認真對待,因為主耶穌說過:「我的軛是容易負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第 11 章,第30節)。
若想參透「積極卻放鬆」、「努力但不用力」的含義,就必須分別檢視一下上述的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學習不用力的專注,這在實修和認知上究竟意味著什麼?專注指的就是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小的範圍內(德國著名劇作家席勒(Schiller)曾說過,若想有所成就或渴望擁有一技之長,「必須學會安靜而持續地集中注意力在一個點上面。」)無論在任何領域這都是成功的關鍵。現代教育學和心理治療,不同的祈禱方式和靈修宗派—方濟會、加爾默羅會、道明會和耶穌會—包括各種類型的玄學,甚至是古老的印度瑜伽,在這一點上都有相同的見解。帕坦伽利(Patanjali)透過《瑜伽經》(Yoga Sutra)介紹了瑜伽修練的精髓和理論,其中的第一句話就是入門之鑰或首要祕訣:
藉由克制力讓腦子停止活動。
換句話說,這是一門培養專注力的心靈藝術。腦子裡的思維或想像是一種自動化作用,和專注力恰好相反。人只有處在平靜無念的狀態,擺脫了思維和想像的自動化作用,才可能真正專注。因此,「靜默」(to be silent)是在發展「真知」(to know)、「意志」(to will) 與「膽識」(to dare) 之前必須進行的修煉。基於此理,畢達哥拉斯派(Pythagorean school)也規定初學者或「傾聽者」必須禁語五年。只有精通了靜默的藝術、擁有專注力之後,學生才可以開口說話。不再信口開河,不再被思維或想像牽制,內外都祥和寧靜,而且有能力覺知話語的內涵,學生才擁有說話的「權力」。特拉普修士(Trappist monks)在避靜時所採取的禁語練習,也都遵循著「藉由克制力讓腦子停止活動」、「透過專注來擺脫思維和想像的自動化作用」。
雖然如此,專注還可以細分成兩種;一種是不感興趣的專注,另一種則是感興趣的專注。前者是藉由意志力來擺脫束縛人心的激情、迷戀或執著。後者則是被激情、迷戀或執著掌控而產生的。完全沉浸於祈禱的僧侶和被激怒的公牛都是專注的,但前者是處於寧靜的默觀狀態,後者則是被憤怒沖昏了頭。強烈的激情當然也是一種高度專注的表現,所以某些貪吃的老饕、對金錢吝嗇的人或傲慢自負的人,偶爾也能達到相當程度的專注,但牽動他們的並非專注力而是執念。
正確的專注乃自在地處於清明安祥狀態,先決條件是抽離而淡定的意志,因為意志所處的狀態決定了專注的程度。基於此理,瑜伽的持戒(遵守五種道德規範)與精進(遵守五種節慾準則),通常是在身體鍛鍊(呼吸與體位法)之前進行的,而專注力的修練又可分為等持、靜慮、三摩地(或是專注、冥想、默觀)。
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St. Teresa of Avila)都不厭其煩地重覆告誡信徒,唯有淨化後的意志力才能為靈性祈禱帶來專注力。你的意志力如果被迷惑,就算再努力也無法專注。意志本身如果不投入到靜默裡,你那「不斷活動的腦子」是無法靜止的。只有靜下來的意志能夠讓思維和想像安歇。因此所有卓越的克己修行者都是精通專注這門藝術的大師。這些道理相當清晰易懂,但我們要討論的並不是一般所指的專注,而是不用力的專注。這究竟是什麼呢?請觀察一位走高空繩索的人,你會發現他是全神貫注的,因為不這麼做他肯定掉落地面。他賭上了自己的性命,只有全神貫注才能保命。但是你認為他會一直思索或揣度自己要做的動作嗎?你覺得他會不斷臆測或設想著在繩索上移動的每一步嗎?
這麼做他一定會立刻摔下來。若是不想摔下來,他就必須排除思維或想像之類的大腦活動,這樣才有機會發揮早已熟悉的技藝。當他在表演特技時,身體的自律神經本有的智慧——呼吸與循環系統的配合——必須取代頭腦的活動。從理智和想像的角度來看走繩索的特技,簡直就像聖德宜(St. Dionysius)(註1) 展現的奇蹟。聖德宜是高盧人中的第一位傳教士,也是巴黎的第一位主教,傳統上人們經常將他和聖保羅的門徒亞略巴古的丟尼修(St.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註2)混淆成同一人:聖德宜坦白承認了對三位一體的信仰,在墨丘利(Mercury)的雕像前被斬首。據說他被斬首後身體筆直地站立起來,用雙手捧起被砍下的頭顱;在一位天使和一道光的引領下走了兩英里路,從蒙馬特到達另一個他自己選擇的、也是天意安排的休憩之處。他就在那裡安息了。(Jacobus de Voragine, Legenda aurea; trsl. G. Ryan and H. Ripperger, The Golden Legend, New York, 1948, pp. 620-621)
風隨意吹動,
你聽見它的聲音,
卻不知道它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也都是這樣。——《約翰福音》第3 章,第8 節
祕密地進入這愉悅的暗夜,
眼前空無一物,
連應當看見的也沒出現,
雖然缺少別的光和指引,
藏在我心底的那個東西依舊燃燒著。——聖十字若望
親愛的不知名朋友:
第一段主耶穌的話語如同鑰匙一樣開啟了「魔法師」的門,而「魔法師」又是進入其他大阿卡納之門的鑰匙,因此我特別選它作為第一封信的開場白。接著我引述了聖十字若望(St. John of the Cross)在《靈魂之歌》(Songs of the Soul)裡的一段詩句,原因是它能喚醒心靈深處的東西,而這正是第一張以及後續所有大阿卡納的主旨。
所謂的大阿卡納其實是可信的、被印證過的象徵系統;人們可以藉由它們所蘊含的「魔法、心智、精神及道德的作用力」,激發出嶄新的想法、概念、觀點和渴望,因此你必須採取比探究或解釋更深的方式來體認它們。你必須處在一種深觀狀態,而且得一直探究下去,才能發揮它們的作用力。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塔羅冥想,心底隱密的部分會變得活躍而有所收穫。聖十字若望所謂的「暗夜」,指的就是回到內在這個隱密部分。這項工作只能在獨處情況下達成,所以比較適合隱居生活。
大阿卡納既不是寓言也不是祕密。寓言是運用象徵性故事來表達抽象道理,祕密則是蓄意隱藏某些事實、程序、手法或原理,以免別人因理解而開始付諸練習。大阿卡納兼具了隱藏和揭露的功能,關鍵就在於冥想能進展到多深。事實上,它們揭露的並不是什麼刻意隱藏的祕密,而是必須有真實體悟才能獲益的奧祕。它們必須活躍地存在於意識甚至潛意識裡,這樣我們才有條件發現新的事物、開創新的想法、孕育新的藝術創作。簡言之,大阿卡納豐富了我們在靈性生活領域的創作,它是一種激發心靈與精神成長的「酵母」或「酵素」,它的圖像則是傳達這些「酵母」或「酵素」的媒介——當然,領受者的心智與道德都必須做好準備,也就是尚未罹患最嚴重的靈性病:驕矜自滿。如果說奧祕比祕密更崇高,那麼神祕又更超越了奧祕。神祕的密契體驗不只是激發心靈成長的酵素,更可以說是一件生死大事。處在密契體驗裡,一切心理與精神的動機都會改變,也就是意識產生了徹底蛻變。教會的七件聖事(the seven sacraments of the Church)就是從同一道神祕淨光放射出來的七彩光芒,而進入這淨光便是「重生」,也是耶穌啟發尼哥德慕(Nicodemus)的那個深夜裡所談到的「神聖啟蒙」(The Great Initiation)。
如果將「神聖啟蒙」理解為「重生」或「進入神祕淨光」,我們就會明白主耶穌指的是沒有任何人能夠為人啟蒙。只有上界的主宰可以為人帶來永恆的神聖啟蒙。我們的指引者在天上,地上接觸到的都只是祂的學子;學子們之所以認出對方,是因為「彼此相愛」(《約翰福音》第13 章,第35節)。除了那唯一的啟蒙者之外,世上沒有任何人可以做我們的主人。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世間永遠有一些精神導師會繼續傳授他們的教誨和祕密知識,讓學生變成所謂的「入門者」——但這一切都跟神聖啟蒙無關。
基於此理,關懷人類的隱修士是不會擅自為別人做這件事的。真正的隱修士不會自稱為他人的「大師」或「啟蒙師」,因為每個人都是彼此教學相長的靈修夥伴。若要舉例,應該找不到比聖安東尼(St. Anthony the Great,又譯聖安當)的為人處事更佳的典範:他以最真摯的心去對待他所探訪的虔誠信徒,在每個人身上他都能發現自認不足的熱情和自制力。從某個人身上他觀察到和藹,從另一個人身上他看到祈禱時的認真;他學習他們的平和與仁慈,留意他們如何徹夜禱告、研讀聖經;他讚嘆某人的堅忍毅力,欽佩另一個人能夠斷食和席地而臥;他也仔細觀察他們的溫順和節制;在所有人的身上他都看到了對主耶穌的忠誠皈依,以及彼此之間的愛。他滿載而歸後,回復到節制慾望的生活,將這些人身上的美德全心實踐出來。(St. Athanasius, The life of Saint Anthony, ch. 4; trsl. R. T. Meyer, Westminster, 1950, p. 21)
隱修士必須有相同的自我要求態度,特別是在各種知識與科學的研習上面——自然科學、歷史、語言、哲學、神學、象徵系統及聖傳等。總地來說,隱修士要通曉的就是「學習的藝術」,但是在其中引領和激發我們的,卻是如酵素般的大阿卡納。換句話說,大阿卡納如同一所完整的、全面的、無價的學院,能夠供人冥思、做學問以及拓展性靈——一所和「學習的藝術」有關的研習院。親愛的朋友,基督隱修之道(Christian Hermeticism)沒有任何意圖與宗教或正宗科學競爭。如果想在其中發現「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哲學」或「真正的科學」,那就是找錯了方向。基督隱修士扮演的角色並不是大師而是服務者。他們無法佯稱(這麼做是幼稚的)自己的作為超越虔信者的真誠、科學家的卓越成就,或是藝術天才的傑作。隱修士不會謹守任何學術祕密,他們和所有人一樣尚未發現治癌藥方。如果發現新的藥方卻不讓世人知道,那真是太荒謬了。若是有專家發明了治癌良藥,他們將會在第一時間向這位人類的恩人致上最大敬意。
同樣地,隱修士也不吝於讚揚像亞西西的聖方濟(Francis of Assisi)這樣的「顯教」派信仰者。他們很清楚所有的虔誠信徒都有潛力成為聖方濟。只要是虔信者、科學家或藝術家,無論男女都是優秀的學習對象。這樣的隱修者不會自認是更優越、更虔誠、更精通或更有能力的人。他們不會以自己認同的密教取代現存的顯教、以特定的科學觀點取代現有的科學理論,也不會以某種藝術派別取代昨日或今日的主流藝術。他們的知識不具備任何現實利益,也不帶有凌駕於現有的宗教、科學或藝術之上的超越性。他們擁有的僅僅是與人分享的精神,但這份精神的使命究竟是什麼?守護它有什麼意義?我想拿以下的例子來說明。
親愛的朋友,你們知道法國、德國、英國和其他國家有許多人——特別是作家——都在傳佈所謂「雙教會」的理念。雙教會指的就是彼得與約翰的宗派,也被稱為聖彼德和聖約翰世代。教義內容是關於彼得世代的終止可能即將來臨,亦即超越彼得世代所象徵的教宗政治,由最後晚餐上靠在主耶穌胸前聆聽其心跳聲的約翰精神取代。換言之,彼得的「顯教派」(exoteric church)將讓位給約翰的「密教派」(esotericchurch),這意味著終極解脫的教義會被發揚光大。約翰雖然自願跟隨彼得這位十二門徒中的領袖,卻不願成為彼得過世後的繼承人。這位聆聽過耶穌心跳聲的愛徒,自始至終都代表耶穌的心,而且一向是它的守護者。基於此理,他一直不肯扮演教會領導的角色。由於心臟的使命不是要取代腦子,所以約翰的使命也不是要取代彼得。「心」當然是身體與靈魂的守護者,但是在一個完整的有機體中,「腦子」才是主宰,負責做出決策及指揮,為組織找到達成任務方式的方式。約翰的使命是維護教會的活力與精神直到基督再現。這就是他不要求任何教會職位的原因。他活化這個結構卻不指導它的作為。
隱修之道,現存的隱修傳統,一直守護著純正文化的共通精神。我再強調一次,隱修士一直聆聽著人類精神層面的心跳聲。他們不可能不守護宗教、科學及藝術的精髓。在上述這些領域裡他們沒有任何特權,其中的聖者、真正的科學家或藝術天才都是他們的學長。他們願意為這些領域裡的神祕心跳而存在—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受到約翰的啟發,他們無法佯稱自己是上述領域或政治組織的領袖,但也不會錯過為人類的精神泉源注入活力的機會—與天主教的聖餐式有著類似的意義。隱修之道是——也僅僅是——一種具有活化功能的「酵素」,它激勵著人類在心靈成長的有機過程中產生「發酵」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隱修之道是一種密修法門,也是密契重生或神聖啟蒙之前要做的功課。
現在讓我們回到第一張大阿卡納。這張卡的內容是什麼呢?
一名年輕男子戴著一頂雙曲線大帽子,站在一張小桌子後面。桌面上有一個黃色瓶子,三個黃色小圓璧,另外有四個紅色圓璧被分成兩疊,還有一個紅色杯子和兩顆骰子,一把出鞘的刀最後是可以容納桌上所有物件的黃色袋子。這名男子是魔法師,他右邊的手握著一根棍子,另一手拿著一個黃色的球狀物(從讀者的方向來看)。雖然雙手都握有物件,他臉上的表情卻泰然自若,沒有任何緊張、用力或慌亂的樣子。他的動作是如此輕鬆自然—看起來就像是在玩遊戲而非認真工作。他沒有留意手上的動作,眼睛也是看著別處的。塔羅一系列的象徵符號或揭露奧祕的啟示,就是從這張魔法師卡展開了序幕,而它代表的居然是一個玩雜耍的人,真是令人驚訝!這該如何解釋呢?
這張大阿卡納背後的奧義和個人的實修狀態及心靈真相有關,也是其他二十一張大阿卡納的根基。如果不去理解箇中意涵(認知和實修上),面對其他的大阿卡納勢必不得其門而入。它是「奧祕中的奧祕」,揭露了進入這所心靈研習院必須具備的認識和意願。簡單地說,實修的第一個基本法則就是:學習不用力的專注;把工作轉化為遊戲;讓你願意承受的軛變得不費力,讓你背負的擔子變得輕鬆。這段忠告、指示甚至可以說是訓誡,不論你對它的感受是什麼,都必須認真對待,因為主耶穌說過:「我的軛是容易負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第 11 章,第30節)。
若想參透「積極卻放鬆」、「努力但不用力」的含義,就必須分別檢視一下上述的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學習不用力的專注,這在實修和認知上究竟意味著什麼?專注指的就是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小的範圍內(德國著名劇作家席勒(Schiller)曾說過,若想有所成就或渴望擁有一技之長,「必須學會安靜而持續地集中注意力在一個點上面。」)無論在任何領域這都是成功的關鍵。現代教育學和心理治療,不同的祈禱方式和靈修宗派—方濟會、加爾默羅會、道明會和耶穌會—包括各種類型的玄學,甚至是古老的印度瑜伽,在這一點上都有相同的見解。帕坦伽利(Patanjali)透過《瑜伽經》(Yoga Sutra)介紹了瑜伽修練的精髓和理論,其中的第一句話就是入門之鑰或首要祕訣:
藉由克制力讓腦子停止活動。
換句話說,這是一門培養專注力的心靈藝術。腦子裡的思維或想像是一種自動化作用,和專注力恰好相反。人只有處在平靜無念的狀態,擺脫了思維和想像的自動化作用,才可能真正專注。因此,「靜默」(to be silent)是在發展「真知」(to know)、「意志」(to will) 與「膽識」(to dare) 之前必須進行的修煉。基於此理,畢達哥拉斯派(Pythagorean school)也規定初學者或「傾聽者」必須禁語五年。只有精通了靜默的藝術、擁有專注力之後,學生才可以開口說話。不再信口開河,不再被思維或想像牽制,內外都祥和寧靜,而且有能力覺知話語的內涵,學生才擁有說話的「權力」。特拉普修士(Trappist monks)在避靜時所採取的禁語練習,也都遵循著「藉由克制力讓腦子停止活動」、「透過專注來擺脫思維和想像的自動化作用」。
雖然如此,專注還可以細分成兩種;一種是不感興趣的專注,另一種則是感興趣的專注。前者是藉由意志力來擺脫束縛人心的激情、迷戀或執著。後者則是被激情、迷戀或執著掌控而產生的。完全沉浸於祈禱的僧侶和被激怒的公牛都是專注的,但前者是處於寧靜的默觀狀態,後者則是被憤怒沖昏了頭。強烈的激情當然也是一種高度專注的表現,所以某些貪吃的老饕、對金錢吝嗇的人或傲慢自負的人,偶爾也能達到相當程度的專注,但牽動他們的並非專注力而是執念。
正確的專注乃自在地處於清明安祥狀態,先決條件是抽離而淡定的意志,因為意志所處的狀態決定了專注的程度。基於此理,瑜伽的持戒(遵守五種道德規範)與精進(遵守五種節慾準則),通常是在身體鍛鍊(呼吸與體位法)之前進行的,而專注力的修練又可分為等持、靜慮、三摩地(或是專注、冥想、默觀)。
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St. Teresa of Avila)都不厭其煩地重覆告誡信徒,唯有淨化後的意志力才能為靈性祈禱帶來專注力。你的意志力如果被迷惑,就算再努力也無法專注。意志本身如果不投入到靜默裡,你那「不斷活動的腦子」是無法靜止的。只有靜下來的意志能夠讓思維和想像安歇。因此所有卓越的克己修行者都是精通專注這門藝術的大師。這些道理相當清晰易懂,但我們要討論的並不是一般所指的專注,而是不用力的專注。這究竟是什麼呢?請觀察一位走高空繩索的人,你會發現他是全神貫注的,因為不這麼做他肯定掉落地面。他賭上了自己的性命,只有全神貫注才能保命。但是你認為他會一直思索或揣度自己要做的動作嗎?你覺得他會不斷臆測或設想著在繩索上移動的每一步嗎?
這麼做他一定會立刻摔下來。若是不想摔下來,他就必須排除思維或想像之類的大腦活動,這樣才有機會發揮早已熟悉的技藝。當他在表演特技時,身體的自律神經本有的智慧——呼吸與循環系統的配合——必須取代頭腦的活動。從理智和想像的角度來看走繩索的特技,簡直就像聖德宜(St. Dionysius)(註1) 展現的奇蹟。聖德宜是高盧人中的第一位傳教士,也是巴黎的第一位主教,傳統上人們經常將他和聖保羅的門徒亞略巴古的丟尼修(St.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註2)混淆成同一人:聖德宜坦白承認了對三位一體的信仰,在墨丘利(Mercury)的雕像前被斬首。據說他被斬首後身體筆直地站立起來,用雙手捧起被砍下的頭顱;在一位天使和一道光的引領下走了兩英里路,從蒙馬特到達另一個他自己選擇的、也是天意安排的休憩之處。他就在那裡安息了。(Jacobus de Voragine, Legenda aurea; trsl. G. Ryan and H. Ripperger, The Golden Legend, New York, 1948, pp. 62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