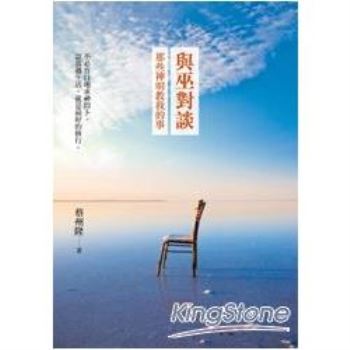信使
「媽!媽!快過來一下!」
伴隨著我緊急又加一點慌張的驚呼聲,媽媽快步地走到門前的院子裡。
「啊!怎麼會這樣?!」
只見門前原本堆放雜物的地方,出現一個深度及直徑皆約五十公分的地洞,裡面盤雜著將近四、五十條斑斕的小蛇。真的不誇張,紅、綠、褐、白、黃鮮豔之至。每條小蛇的身長差不多有三十公分,牠們都昂起頭來,吐出舌頭,似乎也在看著我們。
這是在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這一天所發生的事。回想起當年,二十六歲的我還滿陽光的。那時候我才剛結束掉經營了兩年的電子加工廠,打算好好地再做一些進修。而門前堆放著那些捨不得扔掉的物品常是我的眼中釘,所以我才會心血來潮地去整理它們,也因此發現了這一窩小蛇。
當時,對拜拜一向虔誠的母親,非常擔心周遭鄰居發現後會將牠們撲殺,畢竟住宅區發現一窩蛇可是大事一樁,所以趕緊對我們發出警告:
「噓!小聲點!」
接著,她轉身進屋拿出了金紙和香過來。說也奇怪,就在母親對牠們祭拜的同時,一窩小蛇一轉眼間全不見了。
自認為受過科學教育的我,當然不信這一套,趕緊對地洞做一番探查,我相信地洞一定有其他的通道。
不過,我老媽可不這麼想,她認為這些蛇是「修行者」,躲在靈氣好的地方從事修行,發現牠們已經是一種不敬的過錯,不可以再打擾牠們,所以急忙對我說:
「不要再看了,趕緊把它蓋好。」
我只好找塊木板把地洞蓋上,然後再鋪上泥土,結束了這場「探索」之旅。
徵兆
我怎麼也沒料到,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種徵兆,這窩小蛇也許就是我的「信使」,因為當我發現了牠們之後,一輩子的光陰歲月也隨之改變,從一個對未來充滿憧憬,深懷信心的普通年輕人,變成了「與神共舞」的神職人員,在那之前,這是我完全無法想像的事。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當初沒有翻出這一窩小蛇,我的人生是不是會有另一個不一樣的歷程?
畢生難忘的一日
人生中不時會有因為某些事件發生,而轉變了自己一生的經歷,這也就是人生的轉捩點。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這一天,不但是令我畢生難忘的一日,也絕對是改變我一生命運的重要轉捩點。因為在這一天,我突然從一個懵懂的年輕人,變成了轉達天地意旨的「乩童」。
在二十六歲之前,如果你問我什麼是「乩童」,我會告訴你:「乩童是一種迷信、陋俗,他們沒什麼知識,只懂得詐財騙色。」相信我,在台灣,這是對乩童的一種普遍社會形象認知。對於乩童有這種負面印象的不只是我,而是其來有自的。
清代官方就曾對乩童活動頒發禁令,稱乩童為不法之徒。日治時期也將乩童活動列為違警行為,是一種需要受拘役處分的活動。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乩童並不因為中華民國憲法保障宗教自由而得以不受限制,相反地,政府單位對乩童做了更多的規範。一九四八年,政府將乩童列為查禁民間不良習俗的對象,需要強制轉業。在一九六三年的「台灣省改善民間習俗辦法」中,直接以神棍一詞來稱呼乩童。一九七六年,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台灣省分會改善禮俗推行要點」中,將乩童列為是極應杜絕的一個迷信現象。傳播媒體在那個時期,理所當然地配合政府立場,所做的報導中,也常以「神棍」來稱呼乩童,並且伴隨著「迷信」、「陋俗」、「傷風敗俗」、「詐財騙色」等字眼出現。因此,乩童往往成為「改善民間陋俗」中的一環,變成了擾亂社會秩序的一種不良信仰。
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又自詡是個念過書的年輕人,接受、相信這些訊息是很自然的事,對這種「妖言惑眾」的人物,怎麼會有好印象?因此二十六歲前,我非但不會去接觸乩童,甚至對於接觸乩童的人也非常不以為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一天,我突然起駕了。
北極玄天上帝
吃完晚飯後,白天發現的那一窩小蛇自然成了家人聊天的話題。就在大家聊得正起勁時,坐在電視機前的我,在事先沒有任何徵兆下,突然一瞬間全身僵硬而不能動彈,只感覺到一股非常冰冷的氣,自尾椎緩慢地向上走。那一種冷,比在寒冬中跳入冰水池中還冷,加上全身上下不能活動,這時候我只能咬緊牙關強忍著。當這股寒氣走到了頭頂正中時,我突然能動了,但是動的方式與目的,卻不再是我的意識所能控制的。值得慶幸的是寒氣不見了,只是我全身依然不由自主地顫抖。這前後可能只有經歷了幾分鐘,但是在我的感覺裡卻像過了幾個鐘頭那麼久。
接著,我踏著只有在歌仔戲中才能看到的步伐,緩慢地走向家裡的神桌前。當時父親還未返家,母親帶著我的兄弟姐妹、妻子等家中所有大小成員,亦步亦趨地緊跟著我走向佛案。到了案桌旁後,我的手很自然地在桌上書寫出:
「本座乃北極玄天上帝是也。」
這時候,我只感覺腦中轟轟作響,一連串的疑問突然湧現:
「我是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不會吧,我竟然起駕了?!北極玄天上帝到底是誰?是不是真有這個神明?」
是真的,那個時候我甚至不知道有「北極玄天上帝」這號神明。在這些疑問還沒有機會獲得解答時,祂退了,而我也癱了。
雖然祂不再操控我的身體,我卻清楚地感覺到,祂還在我的身體中,只是祂不用這個身體,而我也用不了。
「好像睡了……」
「要不要叫他起來?」
「讓他再躺一下吧!」
──「我沒有睡著,只是沒辦法動。」儘管耳朵聽到了家人們的對談,然而我就是無法用自己的意識來活動這個身體,甚至連眼皮都動不了。不過這時候心情卻非常寧靜,不再有激動的想法,倒像是滿陶醉在這種感覺中的。
也許是真的陶醉其中了,我完全沒有感受到時間的存在,只覺得好像沒過多久,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震怒地大罵:
「這是在幹什麼?躺成這樣能看嗎?!」
原來是爸回來了。事後我才知道,台灣的臨終禮儀是把即將往生的人送到佛案前躺下,由親人圍繞在旁送行。我當時的情況就類似這樣的儀式,因此父親才會如此地憤怒。但他不是十一點才會到家嗎?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難道我已經躺了那麼久?!
宮主不信,孰信?
沒有時間讓我再多想,祂又使我這個身體動了起來。站起來之後,祂再度走到佛案前,在桌上清楚地寫著:
「請宮主過來。」
我又是一頭霧水:老爸變成宮主了?那這裡不就真的成為宮壇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家裡面沒人懂這個,這樣下去還了得?
父親當然不來這套,不過他好像也是茫然而不知所以。母親趕緊上前對父親說:
「好像是真的,過去看看嘛!」
父親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來到佛案旁。
這時候,祂朝著父親的額頭伸出手指,父親很不高興地揮手遮擋,只見祂一轉身在案桌上一拍,也不見有多麼用力,卻將桌子拍得非常響亮,使得在場的所有瞬間都鴉雀無聲。然後祂又在案桌上寫下:
「吾將在此興宮濟世,宮主不信,孰信?」
大哥看了寫在桌上的字跡,轉述給父親聽了之後,父親彷彿是震懾於玄天上帝的威嚴,將信就信地站在那裡,不再開口。
祂再度伸手指向父親的額頭,似乎在額上畫了一道符。奇蹟出現了,隨著祂的書符,老爸也「起駕」了!看著父親不由自主地顫抖,口中發出如同小孩子的叫聲,並且蹭著一隻腳,這連我也看懂了,一定是「三太子」!
老爸起駕後,便朝著玄天上帝打躬敬禮,只見祂將手一揮,三太子便很規矩地退到一旁站立。接著祂轉過身在桌上寫著:
「太子降臨,速速接駕。」
「怎麼會這樣?」家裡大大小小的成員,這時只能比誰的嘴巴張得大。
然而事情還未了,接著祂請我大哥來到跟前,依樣畫葫蘆,只見大哥瞬間板起面孔,右手虛撚長髯,形態威武。
「嗯!關公!絕對錯不了。」
同樣地,玄天上帝將手一揮,祂也走到另一旁站定。
如果你們認為這樣就結束了,那就錯了。就在大夥兒對關聖帝君接駕禮拜的同時,玄天上帝又請我大姐及二姐上前,一樣的動作,一樣的過程,結果也一樣──天上聖母上了我大姐的身,瑤池金母上了我二姐的身,四尊神分列兩側,玄天上帝位居其中,可以想見那時候的聲勢有多麼壯觀。在一個從未接觸宮廟活動的家庭中,有五個成員在同一時間,毫無準備地成為乩童,那種震驚真的是無法以言語表達!全家人除了年幼的小孩外,母親、我的妻子、兩個弟弟和一位妹妹都對當前的情況不知如何應對。
這時候,玄天上帝一改威嚴的神情,用極柔和的態度在案桌上寫下:
「吾在此處,興宮濟世,今日點將,汝,不必擔心。」
「不過家裡沒有人懂這些呢!」母親虔誠地回答。
玄天上帝又寫:
「凡有作為,必將自然,道聽塗說,不可任信,興宮之務,吾,自有裁策。」
母親急著問:
「這樣我們應該怎麼做?」
玄天上帝指著自己的額頭,接著寫:
「交代吾兒,戌時訓乩,子時靜坐,一應諸事,自有安排,未言之事,不可強為,日常生活,不必變易,謹言慎行,善矣。」
交代了這麼幾句話後,祂一一走到各個神駕前,依然在祂們額頭上書符,使其「退駕」。然後在自己的額頭上做一樣的動作,好像也是讓自己「退駕」。果然,我總算可以依自己的意志活動身體了。從晚上七點一直到凌晨一點,我終於領悟到,能夠自由使用自己的身體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不過還是不對,我感覺到體內有一股蠢蠢欲動的力量,需要我用盡全部的意志力才能壓抑它、抵抗它。
「是不是起駕之後的後遺症?」
我懷疑地問「大家」──當然是有起駕的人。但是看他們神情自若,沒有任何不舒服的樣子,只有我需要咬緊牙關,盡全力去抵抗體內的一股力量,因為我感覺到只要一放鬆,祂又會馬上上身。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了將近三年,甚至一直到現在,只要身旁有其他「靈」存在,這種感覺就會自然產生。它很難透過言語傳述。我清楚地感覺到,全身上下的神經都充滿了另一種能量訊息,我需要與這種訊息抗衡,才能以自我的意識來活動自己。
那種感覺就像自己雖然眼盲,但是一樣可以確實認知身旁的事物。我可以清楚感覺到祂們的存在,只是無法用眼睛看見祂們。這個衝擊對我而言是非比尋常的,二十六年來對生命的認知,突然變成了一種無知,對前程的追求,變成了一個笑話。
「祂們到底是什麼?祂們真的是神嗎?神不是一種精神的信仰而已嗎?祂們怎麼能那麼確實地存在?」
一連串的問題使我下定了決心,我要瞭解祂們,也因此開始了我往後的「乩童」人生。
「媽!媽!快過來一下!」
伴隨著我緊急又加一點慌張的驚呼聲,媽媽快步地走到門前的院子裡。
「啊!怎麼會這樣?!」
只見門前原本堆放雜物的地方,出現一個深度及直徑皆約五十公分的地洞,裡面盤雜著將近四、五十條斑斕的小蛇。真的不誇張,紅、綠、褐、白、黃鮮豔之至。每條小蛇的身長差不多有三十公分,牠們都昂起頭來,吐出舌頭,似乎也在看著我們。
這是在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這一天所發生的事。回想起當年,二十六歲的我還滿陽光的。那時候我才剛結束掉經營了兩年的電子加工廠,打算好好地再做一些進修。而門前堆放著那些捨不得扔掉的物品常是我的眼中釘,所以我才會心血來潮地去整理它們,也因此發現了這一窩小蛇。
當時,對拜拜一向虔誠的母親,非常擔心周遭鄰居發現後會將牠們撲殺,畢竟住宅區發現一窩蛇可是大事一樁,所以趕緊對我們發出警告:
「噓!小聲點!」
接著,她轉身進屋拿出了金紙和香過來。說也奇怪,就在母親對牠們祭拜的同時,一窩小蛇一轉眼間全不見了。
自認為受過科學教育的我,當然不信這一套,趕緊對地洞做一番探查,我相信地洞一定有其他的通道。
不過,我老媽可不這麼想,她認為這些蛇是「修行者」,躲在靈氣好的地方從事修行,發現牠們已經是一種不敬的過錯,不可以再打擾牠們,所以急忙對我說:
「不要再看了,趕緊把它蓋好。」
我只好找塊木板把地洞蓋上,然後再鋪上泥土,結束了這場「探索」之旅。
徵兆
我怎麼也沒料到,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種徵兆,這窩小蛇也許就是我的「信使」,因為當我發現了牠們之後,一輩子的光陰歲月也隨之改變,從一個對未來充滿憧憬,深懷信心的普通年輕人,變成了「與神共舞」的神職人員,在那之前,這是我完全無法想像的事。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當初沒有翻出這一窩小蛇,我的人生是不是會有另一個不一樣的歷程?
畢生難忘的一日
人生中不時會有因為某些事件發生,而轉變了自己一生的經歷,這也就是人生的轉捩點。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這一天,不但是令我畢生難忘的一日,也絕對是改變我一生命運的重要轉捩點。因為在這一天,我突然從一個懵懂的年輕人,變成了轉達天地意旨的「乩童」。
在二十六歲之前,如果你問我什麼是「乩童」,我會告訴你:「乩童是一種迷信、陋俗,他們沒什麼知識,只懂得詐財騙色。」相信我,在台灣,這是對乩童的一種普遍社會形象認知。對於乩童有這種負面印象的不只是我,而是其來有自的。
清代官方就曾對乩童活動頒發禁令,稱乩童為不法之徒。日治時期也將乩童活動列為違警行為,是一種需要受拘役處分的活動。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乩童並不因為中華民國憲法保障宗教自由而得以不受限制,相反地,政府單位對乩童做了更多的規範。一九四八年,政府將乩童列為查禁民間不良習俗的對象,需要強制轉業。在一九六三年的「台灣省改善民間習俗辦法」中,直接以神棍一詞來稱呼乩童。一九七六年,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台灣省分會改善禮俗推行要點」中,將乩童列為是極應杜絕的一個迷信現象。傳播媒體在那個時期,理所當然地配合政府立場,所做的報導中,也常以「神棍」來稱呼乩童,並且伴隨著「迷信」、「陋俗」、「傷風敗俗」、「詐財騙色」等字眼出現。因此,乩童往往成為「改善民間陋俗」中的一環,變成了擾亂社會秩序的一種不良信仰。
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又自詡是個念過書的年輕人,接受、相信這些訊息是很自然的事,對這種「妖言惑眾」的人物,怎麼會有好印象?因此二十六歲前,我非但不會去接觸乩童,甚至對於接觸乩童的人也非常不以為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一天,我突然起駕了。
北極玄天上帝
吃完晚飯後,白天發現的那一窩小蛇自然成了家人聊天的話題。就在大家聊得正起勁時,坐在電視機前的我,在事先沒有任何徵兆下,突然一瞬間全身僵硬而不能動彈,只感覺到一股非常冰冷的氣,自尾椎緩慢地向上走。那一種冷,比在寒冬中跳入冰水池中還冷,加上全身上下不能活動,這時候我只能咬緊牙關強忍著。當這股寒氣走到了頭頂正中時,我突然能動了,但是動的方式與目的,卻不再是我的意識所能控制的。值得慶幸的是寒氣不見了,只是我全身依然不由自主地顫抖。這前後可能只有經歷了幾分鐘,但是在我的感覺裡卻像過了幾個鐘頭那麼久。
接著,我踏著只有在歌仔戲中才能看到的步伐,緩慢地走向家裡的神桌前。當時父親還未返家,母親帶著我的兄弟姐妹、妻子等家中所有大小成員,亦步亦趨地緊跟著我走向佛案。到了案桌旁後,我的手很自然地在桌上書寫出:
「本座乃北極玄天上帝是也。」
這時候,我只感覺腦中轟轟作響,一連串的疑問突然湧現:
「我是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不會吧,我竟然起駕了?!北極玄天上帝到底是誰?是不是真有這個神明?」
是真的,那個時候我甚至不知道有「北極玄天上帝」這號神明。在這些疑問還沒有機會獲得解答時,祂退了,而我也癱了。
雖然祂不再操控我的身體,我卻清楚地感覺到,祂還在我的身體中,只是祂不用這個身體,而我也用不了。
「好像睡了……」
「要不要叫他起來?」
「讓他再躺一下吧!」
──「我沒有睡著,只是沒辦法動。」儘管耳朵聽到了家人們的對談,然而我就是無法用自己的意識來活動這個身體,甚至連眼皮都動不了。不過這時候心情卻非常寧靜,不再有激動的想法,倒像是滿陶醉在這種感覺中的。
也許是真的陶醉其中了,我完全沒有感受到時間的存在,只覺得好像沒過多久,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震怒地大罵:
「這是在幹什麼?躺成這樣能看嗎?!」
原來是爸回來了。事後我才知道,台灣的臨終禮儀是把即將往生的人送到佛案前躺下,由親人圍繞在旁送行。我當時的情況就類似這樣的儀式,因此父親才會如此地憤怒。但他不是十一點才會到家嗎?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難道我已經躺了那麼久?!
宮主不信,孰信?
沒有時間讓我再多想,祂又使我這個身體動了起來。站起來之後,祂再度走到佛案前,在桌上清楚地寫著:
「請宮主過來。」
我又是一頭霧水:老爸變成宮主了?那這裡不就真的成為宮壇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家裡面沒人懂這個,這樣下去還了得?
父親當然不來這套,不過他好像也是茫然而不知所以。母親趕緊上前對父親說:
「好像是真的,過去看看嘛!」
父親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來到佛案旁。
這時候,祂朝著父親的額頭伸出手指,父親很不高興地揮手遮擋,只見祂一轉身在案桌上一拍,也不見有多麼用力,卻將桌子拍得非常響亮,使得在場的所有瞬間都鴉雀無聲。然後祂又在案桌上寫下:
「吾將在此興宮濟世,宮主不信,孰信?」
大哥看了寫在桌上的字跡,轉述給父親聽了之後,父親彷彿是震懾於玄天上帝的威嚴,將信就信地站在那裡,不再開口。
祂再度伸手指向父親的額頭,似乎在額上畫了一道符。奇蹟出現了,隨著祂的書符,老爸也「起駕」了!看著父親不由自主地顫抖,口中發出如同小孩子的叫聲,並且蹭著一隻腳,這連我也看懂了,一定是「三太子」!
老爸起駕後,便朝著玄天上帝打躬敬禮,只見祂將手一揮,三太子便很規矩地退到一旁站立。接著祂轉過身在桌上寫著:
「太子降臨,速速接駕。」
「怎麼會這樣?」家裡大大小小的成員,這時只能比誰的嘴巴張得大。
然而事情還未了,接著祂請我大哥來到跟前,依樣畫葫蘆,只見大哥瞬間板起面孔,右手虛撚長髯,形態威武。
「嗯!關公!絕對錯不了。」
同樣地,玄天上帝將手一揮,祂也走到另一旁站定。
如果你們認為這樣就結束了,那就錯了。就在大夥兒對關聖帝君接駕禮拜的同時,玄天上帝又請我大姐及二姐上前,一樣的動作,一樣的過程,結果也一樣──天上聖母上了我大姐的身,瑤池金母上了我二姐的身,四尊神分列兩側,玄天上帝位居其中,可以想見那時候的聲勢有多麼壯觀。在一個從未接觸宮廟活動的家庭中,有五個成員在同一時間,毫無準備地成為乩童,那種震驚真的是無法以言語表達!全家人除了年幼的小孩外,母親、我的妻子、兩個弟弟和一位妹妹都對當前的情況不知如何應對。
這時候,玄天上帝一改威嚴的神情,用極柔和的態度在案桌上寫下:
「吾在此處,興宮濟世,今日點將,汝,不必擔心。」
「不過家裡沒有人懂這些呢!」母親虔誠地回答。
玄天上帝又寫:
「凡有作為,必將自然,道聽塗說,不可任信,興宮之務,吾,自有裁策。」
母親急著問:
「這樣我們應該怎麼做?」
玄天上帝指著自己的額頭,接著寫:
「交代吾兒,戌時訓乩,子時靜坐,一應諸事,自有安排,未言之事,不可強為,日常生活,不必變易,謹言慎行,善矣。」
交代了這麼幾句話後,祂一一走到各個神駕前,依然在祂們額頭上書符,使其「退駕」。然後在自己的額頭上做一樣的動作,好像也是讓自己「退駕」。果然,我總算可以依自己的意志活動身體了。從晚上七點一直到凌晨一點,我終於領悟到,能夠自由使用自己的身體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不過還是不對,我感覺到體內有一股蠢蠢欲動的力量,需要我用盡全部的意志力才能壓抑它、抵抗它。
「是不是起駕之後的後遺症?」
我懷疑地問「大家」──當然是有起駕的人。但是看他們神情自若,沒有任何不舒服的樣子,只有我需要咬緊牙關,盡全力去抵抗體內的一股力量,因為我感覺到只要一放鬆,祂又會馬上上身。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了將近三年,甚至一直到現在,只要身旁有其他「靈」存在,這種感覺就會自然產生。它很難透過言語傳述。我清楚地感覺到,全身上下的神經都充滿了另一種能量訊息,我需要與這種訊息抗衡,才能以自我的意識來活動自己。
那種感覺就像自己雖然眼盲,但是一樣可以確實認知身旁的事物。我可以清楚感覺到祂們的存在,只是無法用眼睛看見祂們。這個衝擊對我而言是非比尋常的,二十六年來對生命的認知,突然變成了一種無知,對前程的追求,變成了一個笑話。
「祂們到底是什麼?祂們真的是神嗎?神不是一種精神的信仰而已嗎?祂們怎麼能那麼確實地存在?」
一連串的問題使我下定了決心,我要瞭解祂們,也因此開始了我往後的「乩童」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