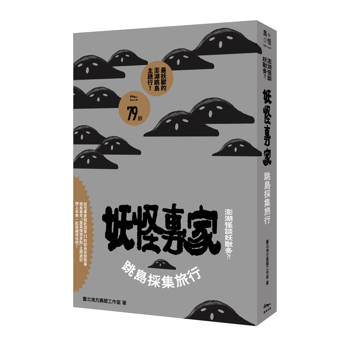〈風坑豬母精——殞命女子的化身〉
文:青悠
(內文)
用來貶低女性的「母豬」一詞,一直含有性羞辱的意思。西嶼豬母精故事中的公媳矛盾,即使不往最醜惡的方向解讀,也是冒犯身體界線而產生的衝突。
在澎湖的最後一天,我和工作室夥伴決定要去「風坑」看看。根據《臺灣地名辭書》,風坑位於「羊山」與「東埔」之間,是這兩個丘陵間的低地,地形就像是山的鞍部一樣,因為地低,剛好成為氣流的通道,因此才被稱作風坑。這一帶自清代以來是重要的軍事據點,留下不少堡壘、砲台等軍事設施,雖然現在已無駐軍,但遺留下的建築物經過整理,已規劃成了軍事文化園區,有空走上一趟,多少能遙想當年屬於軍事基地的肅穆氣氛。
不過我們要去風坑尋訪的故事「西嶼豬母精」,倒是與軍營無關。
《澎湖民間傳說故事》中有二則西嶼「豬母精」的故事,其中一則情節頗為詳盡,說是有位女子從大池嫁到了外垵村,因外垵村捕魚為業,下水捕魚難免打溼衣服,但早年經濟情況不佳,哪有那麼多衣服能換呢?於是家中公公總是不穿衣服,女子見此很不習慣,因此都躲在房間不敢出來。公公遂認為這女子不做家事卻待在房裡偷懶,很是不諒解,生氣地責罵她。女子覺得委屈,就對丈夫說要回娘家,走在路上愈想愈難過,最後連娘家都沒有回,就在風坑這個地方自殺了。過了好幾天,娘家與夫家都不見人,覺得奇怪,出來尋找,才終於在樹叢中發現女子的屍體。怪事不久後就發生了:埋葬那名女子之後,風坑附近一到傍晚就會出現一隻大豬母,遇到路人便會追逐啃咬,令人既困擾又害怕。
雖然沒有人親眼見到女子化為豬母精的過程,不過民間自有解釋:大家都說屍體沾到露水就會變成精怪,在外數天的女子屍體想必已歷經幾次露水洗禮了,變成豬母精也是合情合理吧——於是乎女子殞命的「風坑」,就成了妖怪「豬母精」誕生的地點。
風坑「原生」妖怪?
我們確認了大致地點,打算先前往「風坑口」——也就是風坑近海的那一邊,再往陸地方向走,於是在Google地圖選定了一條小路路口後,便騎著機車奔馳過去。到了目的地那條小路路口,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條連鋪面都沒有的紅土路。那時是夏末,土路兩旁的的銀合歡林樹葉茂密,枝條雖沒有完全遮蔽天光,仍然使土路添上一分神祕的未知感。
這附近不是熱門觀光景點,我們停車,走上無人的土路,多少有點忐忑,走一陣子後便萌生了退意。不過勸退我們的倒不是不安的心情,而是蚊蟲與蛛網,我們沒預料到會直直走進大自然的懷抱,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顯得狼狽不堪,到半路我們稍稍商量了一下,還是決定回頭。一方面實在是不敵蚊蟲,另一方面,那時突然想到:如果想要好好觀察風坑的地形,到一旁的高處往下望也是一個選擇吧?
我們將目標轉向建於羊山之上的西堡壘。在外圍舊營區的廣場處停了車,我們循著指標,走上了大榕樹旁的水泥路,往丘陵頂上的堡壘前進。比起剛才,這段水泥路可親了許多,兩旁有些榕樹,偶爾外展的枝葉搭出拱門狀的遮蔭,走在其中不怕熱昏了頭,只是銀合歡依舊過於茂盛,否則道路左側應該能眺望海洋才對。
路不長,走約五分鐘便抵達了西堡壘,只是我們無暇細看設施,匆匆走過,便找起往上的樓梯,就最終來到了一座金屬製的穹頂觀測所,從此處瞭望,總算能將附近的環境盡收眼底——
結果卻不如想像中海闊天空。主要原因仍是茂盛的銀合歡遮蔽了不少視野,即使登上觀測所的平台,仍然要踮著腳才能看到遠方。
我們還是努力拍了些照片。從此處看得見下凹的地形,西堡壘所在的羊山與對面的丘陵圍出了一塊谷地,又在臨海的那一側開了個偏窄的缺口。谷地裡可見幾座剛剛才經過的軍事建築,除此之外不少地方仍遍布雜樹,宛如一塊未經開發的荒野。其實這也在預料之中,畢竟附近沒有居民定居的聚落,長久以來又都是封閉的軍事據點,當然也就不會有太多人的痕跡。
總之植被蒼翠,海水湛藍,我們在上頭靜靜欣賞了一陣的自然風景,權作休息,一會兒就離開羊山,繼續下一個行程。風坑並不是什麼壯闊的景點,甚至有點像是刻板印象裡鬼魅橫行的野地,讓人卻步,然而風坑真的妖氣橫生嗎?可能不然。事實上,儘管豬母精在風坑出沒,但牠也許並不能算是真的在風坑誕生的妖怪。
豬母精的#metoo
工作室後來曾討論過「豬母精」、「豬母鬼」這種妖怪。除卻真由母豬變成的豬母精不談,那些女性死後化成的豬母精,怎麼想都有一點奇怪。除了上述出現在風坑的豬母精,《澎湖民間傳說故事》另一則較簡單的故事,情節是女子受不了村人閒話,投海自盡,死後變成豬母鬼作弄路人;而雲林流傳一則更慘烈的豬母精故事,說的是一名女子遭受性暴力後死去,死後化作豬母鬼向加害人之一索命。奇怪的地方在於,人受委屈而死後找仇人報復的故事其實頗常見,許多女鬼索命的故事更是流傳甚廣。既然人死成鬼就能復仇了,偏偏選擇變作豬母的形象來作弄人,總覺得有點多此一舉。
工作室夥伴對此提出了有點恐怖的猜想。「性」在傳統社會中是諱莫如深的話題,而用來貶低女性的「母豬」一詞,則一直含有性羞辱的意思。西嶼豬母精故事中的公媳矛盾,即使不往最醜惡的方向解讀,也是冒犯身體界線而產生的衝突,在女子死去後,村人隨即傳言她變成了「豬母精」;而雲林採集的那則故事雖講明了性暴力事件,然而生了病的加害人原本不明所以,是直到求神問卜後才被診斷為「豬母鬼」纏身——
這簡直是對性的避諱加上譴責受害者的心理在雙重作祟啊。
若是夥伴的猜想為真,這些含冤而死的女性,直到死後仍被貶低蔑稱,實在太讓人不寒而慄了。
諷刺的是,西嶼豬母精故事還有後話。因為豬母精會追逐行人,大家感到畏懼,入夜後都不敢經過風坑。有位學過法術的土水師,自恃有點功力,不把豬母精放在眼裡,卻被豬母精追趕,一路逃到受王爺廟庇護的鄰村才逃過一劫,他心有不甘,隔天白天先設下了八卦陣當作陷阱,夜晚引豬母精走到陣中。豬母精也果真受困,在八卦陣裡逃不出來,最終等到天亮時被陽光照到,化為煙消散了。
妖怪被消滅,看似迎來了圓滿大結局。只是我總想,應該見光死的或許並不是豬母精,而是那些更加陰暗幽微的,製造出豬母精的意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