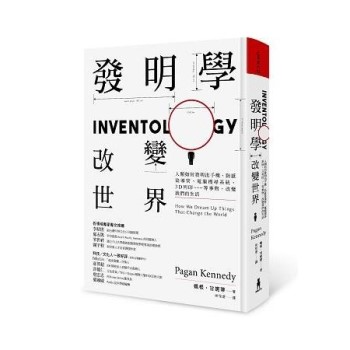第六章 戴著護目鏡看數據
一群新興科學家——生物資訊學專家——重新對偶然力產生興趣。他們希望能加速及「策畫」他們的運氣,方法就是用電腦搜尋過去成千上萬的實驗數據,偵測沒人預期的關連……
醫學史上有個福至心靈、偶然發現的著名故事,和起先被稱為 UK-92480 的藥有關。最初,這個藥物的設計是幫助心絞痛病人打通血管之用。但研究人員在志願者身上進行測試時,他們發現,呃,一些令人興奮的事情:男性志願者回報說,他們出現驚人的勃起現象。「當時在輝瑞藥廠的我們,對於這個副作用都沒想太多。」負責臨床實驗的發明家依安.奧斯特羅(IanOsterloh)說。但等結果回來時,「我們決定追蹤這些報告,看看會把我們帶到哪裡去。」結果發明了一砲而紅、名叫「威而鋼」(Viagra)的熱門新藥,而整個發現事件則為「快樂的意外」這名詞帶來全新的意義。
二十世紀許多重要藥物的發現過程都很類似——研究人員原本在尋覓這個、最後卻發現了那個。成功總是難以捉摸得讓人抓狂,也昂貴得可怕;企業可能集中幾百位科學家的力氣在一個目標上,結果一無所得。於是幾十年前大藥廠開始追逐他們稱為「目標搜尋」或「理性設計」的做法。他們不再等待靈光一閃、福至心靈的一刻,而是理性分析,找到新發現,例如首先分辨出可能引起某種疾病的是哪些蛋白,然後嘗試用生物工程的方法,製造可以影響這些蛋白的化合物。
二○一三年,一群研究人員在《臨床與實驗藥理》
(Clinical & Experimental Pharmacology)期刊發表了一篇論文,指出近年來精神科新藥的發現速度緩慢,可謂乏善可陳。他們提出一個疑問:為什麼一九五○、六○年代的科學家,雖然使用的工具頗為原始,卻能夠發展出讓人眼睛一亮、有助醫治精神障礙的各種新方法?又為了甚麼,從那時起發現的速度快速下跌?「關鍵和重要的是需釐清楚,到底是哪些因素使得藥物發展好像陷入窒息狀態,」他們寫道,「至少有一位聲譽崇隆的專家,將目前的停滯不前歸咎於偶然力的式微。」
這篇論文的作者群辨識出一連串他們稱之為「反偶然力」的因素,認為這些因素可能影響了藥物的發展。他們指出,今天多家藥廠都刻意避開興之所至的嘗試和實驗,而擁抱比較「理性」的研究方式,包括「挑出那些根據基礎研究和理論」看來很有價值的「化合物來進行臨床試驗」。換句話說,你要在草堆裡找一根針,但又不願意仔細搜索整堆草,而只去看你相信埋藏了針的部分。這些作者宣稱,這種鎖定目標的做法可能減少了「快樂的意外」發生的機率。他們又說,在今天忙碌不堪的醫院裡,由於醫師花在觀察和聆聽病人的時間愈來愈少,他們從飽受病魔折磨的人身上學習的機會也減少了。
也許,製藥公司花幾百億美元老想著避開白忙一場的研究計畫,結果真正錯失的卻是意料之外、令人驚喜的發現。就像笑話中在路燈下手腳並用趴在地上找東西那個人——他在黑暗處搞丟了鑰匙,卻決定到光線比較好的地方來找尋。
不過就在這幾年,一群新興科學家——生物資訊學
(bioinformatics)專家——重新對偶然力產生興趣。他們希望能加速及「策畫」他們的運氣,方法就是用電腦搜尋過去成千上萬的實驗數據,偵測沒人預期的關連。理論上這做法會幫助他們注意到某些現象,獲得像將 UK-92480 轉變為威而鋼的寶貴靈感,只不過他們能夠做得更快也更便宜而已。二○一三年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報告估計,由於新方法能巨幅降低藥物的研發成本,因此在美國的醫療保健市場中,資料探勘技巧可能相當於一千億美元的產值——而且是每年的產值!
根據生物技術顧問公司 CBT Advisors 執行長斯帝夫.迪克曼(Steve Dickman)的說法:「過不了多久,比起大數據在財務預測或選擇最快捷交通路線上的應用,大數據在發現新藥和醫療保健中扮演的角色,將不遑多讓。」
但這方法真的那麼管用嗎?這問題可真比大數據還要大:迫使我們正視人類想像力的本質,思考我們探索未知的真正心態。
埋藏在基因中的謎團
正當我努力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偶然聽到一則故事,正充分反映出目前最潮的偶然力,可以如何和老舊偵探手法相輔相成,做出重大突破。故事的主人翁是名為莫里.羅賓遜(MurrayRobinson)的藥學家以及他的哥哥凱利(Kelly)。凱利的身體裡藏著一個謎。揭開這個謎的第一個線索來自一位臨床醫師,她對病人的細心觀察加上神準的第六感,一步步將她帶到這個問題上。可是,謎題中較複雜的細節,還是要靠基因定序或數據分析等工具方能解開。這些工具讓研究人員又快又準地探尋未知的世界,而這甚至在十年前仍未能做到。
一九七○年莫里只有八歲大時,跟哥哥同住一個房間。晚上熄燈以後,兩個小孩仍會小聲談話,回憶白天的不凡經歷。大人說凱利「慢」,因為他有學習障礙,但是莫里覺得哥哥很快、很吵也很好笑。凱利排隊買冰淇淋時會擠到最前面去;手舞足蹈,講好笑的屁笑話。在肅穆安靜的博物館內,凱利會指著一個希臘雕像大喊:「噢,天哪,這女生沒穿衣服耶!」戲院裡黑暗一片,他大叫:「嘿,各位,我們來玩大風吹吧!」然後就是對電子產品的著迷:你得將手電筒和電晶體收音機收好,否則凱利會把它拆開,讓電線和電池散落一地。凱利很古怪,但莫里就是喜歡他的多姿多采。多年以後,莫里才明白,所有的奇怪言行,都是數據點。
快轉到一九九○年代。此時莫里已經是生技公司安進(Amgen)一個研究團隊的主管,負責研發癌症新藥。「基因體的時代才剛開始。」莫里說,「因此我們抓住這個機會,全力投入。」安進添置了先進的DNA定序儀器,莫里和他的團隊開始收集跟癌症有關的基因。「那時候,大數據開始在生物學嶄露頭角,我們很清楚,必須發明新的方法來解讀和理解這些數據。我花很多時間跟數學家學習,如何將基因數據整理出個道理來。」
數據點之間的關聯,有時可以靜靜藏在那裡幾百年,直到某人找到正確的點,將它們連起來。但線索並不是在我們接觸不到的「遙遠彼端」,而是就在我們身邊,不過我們毫無警覺。
一九九八年,莫里正在跟有如暴風雪鋪天蓋地而來的數據拚搏,突然接到媽媽的電話。她剛剛讓凱利做了個新近發現的「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Smith-Magenis Syndrome,SMS)的檢查。而雖然莫里是基因體定序的專家,直到那一刻,他從未想過凱利的行為可能源自基因突變。
那一天,莫里使用安進的醫療系統搜尋數據庫,追查出每一篇研究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的論文。「我讀到一篇論文,那裡列出這個症候群的所有特徵─喜歡社交、有幽默感、咬自己的手、發脾氣,」莫里回憶說,「每一項好像都在形容凱利。再看下去,看到讓我最震驚的事。它說大部分有這種突變狀況的人都對電子產品著迷。我下巴立刻掉了下來。」那些過往時光——他哥哥為了看看電開關或遙控器裡面有甚麼而將它們拆爛——一下全回來了。重新認知哥哥凱利的「性格」,讓他十分掙扎。凱利的熱情、迷戀,甚至他的幽默感,竟然都肇因於基因裡頭的小小錯誤?(凱利的外觀也受到基因影響:眉毛濃密、嘴唇形狀像愛神邱比特的弓,手指粗粗短短的。)
一直以來,莫里覺得他哥哥性格很特別,獨一無二,但結果原來凱利屬於一個散布全球的族群,一個隱形的家族,而且他們全都極為相似。莫里至今仍覺得很驚訝,自己手上有最新式的基因定序機器,卻從未懷疑過,哥哥的稀奇古怪也許可用基因突變來解釋。
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的發現過程十分老派,換句話說,經由仔細觀察和絕佳運氣。一九八一年,丹佛市一家醫院裡的遺傳諮詢師安.史密斯(Ann Smith)在檢查一名嬰兒時,注意到小孩的心臟和上唇出現缺陷。幾個月後,她碰到另一名徵狀幾乎完全一樣的嬰兒。循著自己的第六感,史密斯懷疑兩者有關聯,於是分析了兩個小孩的基因物質,發現兩人的第十七號染色體都缺了一些東西。起先史密斯相信自己只不過發現了一個已被發現過的現象,因此她翻找文獻,企圖尋找研究報告來證實自己的觀察。結果發現從來沒有人發表過關於這個基因缺失的論文。
過沒多久,史密斯開始跟基因科學家艾倫.馬吉利氏(Ellen Magenis)合作,尋找和檢驗一出生就帶著罕見的第十七號染色體缺陷的小孩子。到了一九八○年代末,這個毛病已經有個名字,就是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以紀念兩位證明這個問題的女性。這時候,研究人員已發現了幾十位具有這種基因缺失的人,將他們的共同特徵整理出一個長長的清單。
當初史密斯誤打誤撞遇到這個神祕事件時,她不知道這是個謎,並沒有刻意尋求突破。相反地,好像是那個發現找上她,運氣則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大約二萬五千人當中,才會有一個人出生時帶著這種基因缺陷,而史密斯極湊巧地在幾個月之間遇到兩個案例。如果兩名小孩年齡差很多,她或者也不會注意到兩人相似之處,這又是另一個巧合。然而,史密斯似乎具有某些特異能力,能見人之所未見。她只不過抓住兩個案例,但把兩點連起來,就看出其中規律。在第五章,我們學到有一種人叫「超級偶遇者」,他們特別會注意到規律和發現新事物。史密斯無疑符合超級偶遇者的資格。她簡直是「直覺的威力+仔細觀察+不知疲倦的尋找真相」的活廣告,是個偶然力達人。
二○○九年,莫里和凱利抵達維珍尼亞州勒士頓市的凱悅飯店。在這之前,他們從未遇到過任何一個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的同路人。可是等他們一走進研討會會場的大門,圍繞著他們的幾十個小孩子——和幾個大人——全都手指粗硬、濃眉、行動蹣跚,皆因為基因裡的小小缺陷。
研討會期間,凱利對圍繞在他腳邊走來走去的史密斯—馬吉利氏小孩興趣不大,而立刻走到會場前方檢查麥克風,檢查電線如何連接,他對小工具的癡迷始終如一。同時,莫里則不停跟其他人握手,研究他們的名片。他十分興奮,因有此機會跟相關科學家討論,看有哪些可能治療他哥哥的方法。這時候,專家已斷定,單單缺了一個基因(RAT1),就會形成大部分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的問題。未能斷定的是其他大問題:基因如何運作?它在身體裡都在幹嘛?「我跟醫師、臨床醫師還有遺傳學家都談過了,」莫里說,「叫我震驚的是,想要在分子的層次理解根本原因,連專家都感到無助。於是我想:『我好像可以做點甚麼。』我明白,必須找到方法,弄清楚基因如何運作。」莫里說:「那會是我們這行的下一個重大議題。於是,由於我哥哥的關係,也由於我一直在研究癌症,我決定要建立一些研究工具,好解讀基因的運作。」雖然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從一個小缺陷開始,它的效應卻觸及其他基因,將他們或開或關,而引致悲劇。莫里想看看有沒有辦法利用大數據技巧來找出更多。
這種技巧仍然很新穎,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名稱。有人稱之為「乾巴巴生物學」,其他人較喜歡「生物資訊學」的說法,還有一些人說這是「矽中生物學」。(譯注:所謂「in silico」[在矽之中]的說法意思是「在電腦上進行或透過電腦模擬」)而最後這個說法自有其深意,關係到我們如何投資未來。「每一天,龐大的資訊量(關於基因的、蛋白的、藥物的或疾病的)全都被倒到網路上。換句話說,這是極為大量的新資訊,大部分未經分析,」莫里告訴我說,「所有的資訊都靜靜躺在那裡,開放給任何想分析資料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些資訊,做出巨大發現。」
為了研究 RAT1 這個基因,理解它為哥哥身體帶來的浩劫,莫里成立了一個團隊。「我找了一些寫程式的人,將一大堆數據放在北卡的一個伺服器,然後我們就『玩』各種演算法,用數學方式將各基因的關連找出來。」他說。他們在數據中找到一些規律。似乎史密斯—馬吉利氏缺陷會破壞DNA在細胞裡的存放方式,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一個基因斷掉,居然會影響從睡眠模式到手指形狀等所有事情了。
他們就這樣在公開的數據庫裡東敲西弄。莫里在數以千計的實驗和研究報告中看到許多可能性,因而十分興奮。跟其他很多科學家一樣,他相信,這種資料探勘的做法可讓我們找到使用藥物的新方法。正確的演算法也許能將某種疾病造成的基因問題和藥物的作用配對,找到對策。「與其在實驗室等待『快樂的意外』出現,你也許可以在數據裡找到它。也許你可以說:『嘿,這種藥試過用來醫治風濕,不太管用,但它好像很適合拿來對付高血壓呢。』」莫里解釋。
這些日子,隨著生物資訊學的蓬勃發展,大家希望能夠用成本更低的方式來「碰」到重大發現。比方,面對如山的數據,只要拿著合適的工具,也許你只消花一個下午,就能夠搜尋並分析幾千個隨機找到的數據了。
莫里也把自己的未來押寶在上面了。二○一三年,他創立了一家名為 Molquant 的公司,目標正是要揪出躲藏在大數據裡的真知灼見,將之轉化為藥物以及診斷工具。
刻意製造出來的偶然?
阿圖.布特(Atul Butte)是位生物醫學家兼創業家,且是加州舊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計算健康科學院(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Health Sciences)的領導人。他更是大數據技巧的狂熱推動者。二○一四年一個研討會中,布特從口袋中掏出一塊基因晶片(gene chip,又名DNA微陣列[DNA microarray]),在觀眾面前揮舞。它看來不怎麼樣——一塊餅乾大小的四方型塑膠而已。不過,他說,這片小東西改變了我們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舉個例子,研究人員使用這塊晶片的時候,例如研究某種藥物如何影響血壓時,這晶片同時也取得了這藥物如何與DNA內各基因互動的大量數據。二○○二年,許多醫學期刊開始要求科學家將這些跟基因表現相關的數據全部上傳到公共數據庫,儘管該篇論文可能只提到這批數據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事實上,著那些多出來的數據(研究過程中順便收集到的數據)現在數量多到必須用「拍位元組」(petabytes,或千兆位元組)來計量了。(一拍位元組大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內總資訊量的四倍之多。)
這是為什麼有些研究人員,比如布特,全心擁抱這個新策略:他們不迴避未知,而是想辦法快速整理爬梳,在未知中探索,利用合適的演算法,搜尋全球頂尖實驗室累積的龐大實驗數據——頂尖研究人員做過數以千計的實驗,蒐集下來的數據卻可能從來沒人利用過。
這些數據將會大幅改變我們的能力,讓我們得以替原本熟悉的藥物找到新用途。本章一開頭,我們看到為了心絞痛研發的新藥,結果在治療勃起障礙上出乎意料的有效,但那個發現還需要有個「快樂的意外」來促成。「歷史上,幫舊藥發現新用途通常都牽涉到偶然的機運。」二○一五年一篇論文寫道。但作者指出,今天我們有可能加速快樂意外的發生率,方法是找出疾病狀態的規律和型態(例如基因表現),將之和藥物的作用相配對。網飛(Netflix)就透過分析用戶偏好,預測哪些人會喜歡某部新電影;臉書也藉由挖掘用戶的人際網絡,研究如何上廣告;現在同樣的數據分析被用在藥物學了。
布特和他的團隊早已開始在這些公開數據庫挖寶,為舊藥找新用途。他們透過演算法,發現鹽酸伊米胺(imipramine,自一九五○年代即存在的一種抗憂鬱藥物)對於小細胞肺癌可能有醫療功效。於是布特團隊用小鼠來測試這理論。而正如布特所希望的,鹽酸伊米胺的確有助於縮小實驗鼠的癌腫瘤。他們將結果刊登在《癌症發現》期刊中。「我們的研究顯示生物資訊學的威力強大,能極快速地為已獲美國食物藥品管理局(FDA)批准過的藥物重新定位……治療[患有小細胞肺癌的]病人,之前數十年來,都沒有一套有系統、有效的治療方法。」他們寫道。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整個流程進行的速度:研究人員從抓出線索到臨床試驗大約只花了兩年。要是必須等待偶然的機遇,可能得等個幾十年,才能將各個點串連起來。
布特告訴我,演算法提醒他其他還有許多可能的機會,包括或許可利用找到的型態,開發出能提早偵測病情的診斷工具:「我們正在檢視胰臟癌、皮膚病變、潰瘍性結腸炎等情況。新近的計畫是早產,或者說研究為什麼嬰兒會過早誕生。我們用的是由『出生缺陷基金會』(March of Dimes)資助的開放資料庫。」透過資料探勘,他的團隊找到幾種蛋白,可作為提醒是否有「先兆子癇」(preeclampsia,又稱妊娠毒血症)的問題。這是產婦及未出生嬰兒可能遇到的一大威脅。由於這些生物標記的發現,他們建立起一套早期檢測系統,在本書出版的二○一六年,這些檢測方法也許已可供大眾使用。整個過程進展飛快,從資料探勘到產品設計只不過花了兩年左右。
「開放資料跟世界上任何其他物品都很不一樣,它不像石油,不像土地,也不像空氣,更不像水。資料可重新補充,人人都可取而用之。只要你將每個數據組跟不同的東西比較配對,而且問對問題,你就可以找到新發現。」布特這樣告訴我。如果你把「breast cancer」(乳癌)這幾個字打進一些資料庫,你會找到數以千計、來自乳癌腫瘤的基因序列,由於資訊取得是如此容易,任何高中生都可以用這些數據來做研究。布特告訴我,杜克大學有個名為布麗坦妮.文歌(Brittany Wenger)的大學生,她還在念中學的時候,就曾經使用開放數據,描畫出惡性乳癌的分布地圖。在第十六章,我們會遇到另一位青少年,他則是利用網上數據庫發展出胰臟癌的早期偵測方法。
對布特而言,從數據得到的發現實在太多了,他有時會覺得不堪負荷。「我們真的需要多些人來參與。事情太多了,單靠我做不完。」而當然,等到更多人加入尋找新藥後,機緣湊巧的意外發現機率也會相應提高許多。
車庫中崛起的新藥發明家?
我們在前幾章看到,由於今天大家都能接觸到便宜的研發工具,因此愈來愈多人加入產品設計的行列。今天,我們差不多都有管道找到工具(例如3D印表機)來製作原型,但在一九八○年代,只有一小撮頂尖工程師才有機會接觸到這類工具。這種趨勢,為產品設計這行業帶來一批新的人才和新點子。例如第三章曾經提到的發明家法雷伊,就有能力獨立經營工作室,管控自己的生產流程,同時仰賴背後的群眾支持者。
如果期望同樣的趨勢也會吹到製藥界,那麼,就必須給有興趣的新世代人才提供工具和資金。但直到目前為止,離這種理想狀況還頗為遙遠。製藥界仍是門戶緊閉的團體,侷限於少數研究人員的參與,他們擁有實驗室,能接觸到病理樣本、病人,以及最重要的——龐大資金。加速藥物開發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創造其他人也負擔得起的研發工具,容許成千上萬的人才都能成為製藥業者。
目前我們就是往這方向邁進。
第一個讓我注意到這驚人發展的人是布特:許多研發藥物所需要的設施,皆可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正如車庫發明家可以找工廠合作生產,目前,車庫生技發明家也可以聘請實驗室或其他相關服務,來協助證明藥物真的有效。
在傳統的製藥體系,研發人員必須準備幾百萬美元的資金,在附屬的實驗室進行動物試驗。現在則可在網路上找到其他解決管道。你可以透過名為 Assay Depot 的網站聘請研究人員,替你將設計好的藥物在大鼠、小鼠、生物組織或細胞上進行研究測試。你可以明確指定要用哪一種狀態的小鼠來試驗你的化合物,這些小鼠可能經過基因改造後變得過肥,罹患肺癌、白血病,或處於其他狀態之中。你也可以聘請和 Assay Depot 有合作關係的實驗室創造出你的「設計師小鼠」,來進行你的試驗。因此,任何人只要拿著信用卡,就能買到實驗的許多步驟,有如一般產品設計師直接跟中國某家工廠下訂單買零件。
布特早已開始使用 Assay Depot 來測試藥物的功效。只要點幾下滑鼠,用信用卡付費,他就聘請了好幾家聲譽良好實驗室裡的專家,來測試他的候選藥物。布特估計,使用這種方式,一整套測驗的花費(包含他自己的人力)約為七萬五千美元,開發新藥時,從開始到結束的成本則可減到約十五萬美元。這樣的研發成本已降至小公司都負擔得起的範圍,包括布特自己的新創事業NuMedii 公司在內。
布特告訴我,連組織樣本也可以在網上購買。「樣本主人(病人)的個人資料已全清除掉,重新包裝好,等待有需要的研究人員。因此尋求樣本來做實驗已不是最困難的一部分,特別是針對比較一般的病症而言,」他說,「其實你可以從網路開始。」
真的,我找到一家名為「先進組織服務」(Advanced Tissue Services)的公司,宣稱可「為你提供細胞、人體組織及生物檢體」。這網站沒有購物車的功能,但承諾「可根據你開列的需求,提供新鮮的組織。」
有些創業家很可能已開始想辦法將這類服務連結整合為生技公司。到時大型製藥公司發現自己將面對一大群小公司的競爭。
「在矽谷,我們已很習慣毛頭小子在家裡車庫或校內宿舍創立令人驚訝、價值奇高的公司,」布特說,「那麼,你為何不能在某個車庫創立下一家基因科技公司(Genentech)呢?」
我提醒他,由於他擁有博士外加醫學學位,且在大學任教,安排人體臨床實驗當然比較容易,從車庫起家的毛頭小子沒有類似的人脈可運用。
「現在還不能,」他回應說,「但未來為何不能呢?」
二○一四年,曾協助創立 Airbnb 等公司的著名創投育成公司 Y Combinator(簡稱YC公司)宣布,他們將開始投資製藥公司。
Y C的其中一個創投標的 Transcriptic 打算提供的服務,是讓任何人皆可租用機器人來進行自動化的實驗。「創立 Transcriptic 時,我們的目標是為生命科學界提供網路業享有的結構性優勢,這樣一來,兩個博士後傢伙只要拿著一部手提電腦,坐在咖啡廳裡,就可以經營製藥公司,而無須花幾百萬美元買儀器或租地方設立實驗室,」創辦人馬克斯.何達克(Max Hodak)在二○一五年一篇部落格文章裡寫道,可是,「要說清楚,我們目前還未走到那地步。」
目前,醫藥研發正面臨開始鬆綁的階段,一如「優步」(Uber)面對各種官司和挫折,可出租實驗室也會面臨類似問題,但看來大勢所趨,某些藥物難以避免地將在手提電腦上產生。事實上,生物創客已開始進入這個行業了。
醫學的金礦
不過,美國克里夫蘭醫療中心(Cleveland Clinic)的血液學兼腫瘤科專家尤根.桑塔拉拉札(Yogen Saunthararajah)仍然對於「有計畫的偶然事件」存疑。過去十多年,他持續進行臨床試驗,試圖尋找更好的血癌療法;且於二○一五年有突破性發現,結果發表在《臨床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前文提過的史密斯是個超級偶遇者,桑塔拉拉札和史密斯很像,費盡心力治療病人,聆聽他們談話,全心奉獻於發現的藝術。但他告訴我,他對於從如山的數據中找出規律,接著依靠遠端進行的實驗來決定一切的做法,十分懷疑不信任。
桑塔拉拉札參與血癌病人的生活,事實上參與甚深,對於傳統化療的恐怖副作用也深感痛苦——體力衰竭、掉頭髮、沮喪、嘔吐,甚至死亡。十多年前他就開始疑惑,是否可以使用低劑量、無毒、FDA核准的藥物「地西他濱」(decitabine),輔以還未經FDA批准的「四氫尿苷」(tetrahydrouridine),來代替傳統的化療程序。他希望找到更有效的治療方案,讓病患接受治療時可以不必犧牲生活品質。他的理論是,只要這兩種藥物的分量配合得當,或許可啟動癌細胞內的一組指令,讓癌細胞「長大」為無害的血液細胞,最後死去。這樣一來,藥物幾乎不會影響到健康的細胞,換句話說,不會構成什麼副作用。
二○一五年,他和他的同事報告說,已在二十五位血癌病人身上測試過這套方法,接近一半的病人血細胞計數出現進步,表示他們的身體確實開始抗癌。考量到那些病患原已處於末期階段,而且對其他藥物毫無反應,這個結果特別令人興奮。同樣重要的是,病患差不多沒有經歷伴隨化療而來的可怕副作用。
為了取得這些成果,桑塔拉拉札和他的團隊可是花了很多年不斷摸索,仔細反覆測試、檢驗他們的理論。他強調,藥物研發需要同時深入研究病人和科學。捷徑極少行得通。「套一句被引用到爛、但極為正確的話,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如果我們真的想征服疾病,取得進展,就需要在分子層次充分理解一連串的因果關係,」他說,「機器人無法揭示其間的機制,這些真理,需要如藝術般的技巧,需要愛,還需要大量經費以及多年的努力。運用人類的聰明才智和熱忱努力不懈地解決問題,不會成為新聞,但這才是做事情的王道。」
可是,我們必須在人類和機器人之中擇一嗎?理想的方案應該是同時動用兩種新治療方法。目前,許多有天分的研究人員正致力於找尋聰明的方法,結合巧妙設計下的偶然力和傳統的直覺力,加速突破的誕生。
畢竟,那些花四十億美元的藥物已彷彿是上個世代的老古董了,就像那些百萬美元電腦或兩千美元的手提計算機。無疑地,網際網路在移除障礙,讓行外人拿到工具,得以挑戰權威。已經發生的是,新創公司或獨立發明家開始進入藥物研發的領域,試驗新方法。千萬別忘記,那以「拍」來計算的位元組,簡直是還未被探勘的新大陸,可能藏著醫治疾病的線索。「那些數據是被冰封的知識,需要某人用熱力將它溶化,讓知識破冰而出。」布特告訴我。冰封的數據王國也許就是醫學的金礦。
一路走來,科學家繼續發展新科技,讓我們搜尋數據庫,也搜尋我們的周遭環境,找尋救命藥物。例如,基因定序的工具有助於找出池中藻類、泥土甚至人體腸子裡潛藏著的寶藏;又或者是幾十年前還不為人知的微生物,其實是藥物的來源。換句話說,曾經看來不值一提的,原來包含著巨大的價值。在下一章,我們會跳到神奇的垃圾箱,看看為什麼發明家認為,看似無用的廢物竟是那麼充滿啟發性和靈感。
一群新興科學家——生物資訊學專家——重新對偶然力產生興趣。他們希望能加速及「策畫」他們的運氣,方法就是用電腦搜尋過去成千上萬的實驗數據,偵測沒人預期的關連……
醫學史上有個福至心靈、偶然發現的著名故事,和起先被稱為 UK-92480 的藥有關。最初,這個藥物的設計是幫助心絞痛病人打通血管之用。但研究人員在志願者身上進行測試時,他們發現,呃,一些令人興奮的事情:男性志願者回報說,他們出現驚人的勃起現象。「當時在輝瑞藥廠的我們,對於這個副作用都沒想太多。」負責臨床實驗的發明家依安.奧斯特羅(IanOsterloh)說。但等結果回來時,「我們決定追蹤這些報告,看看會把我們帶到哪裡去。」結果發明了一砲而紅、名叫「威而鋼」(Viagra)的熱門新藥,而整個發現事件則為「快樂的意外」這名詞帶來全新的意義。
二十世紀許多重要藥物的發現過程都很類似——研究人員原本在尋覓這個、最後卻發現了那個。成功總是難以捉摸得讓人抓狂,也昂貴得可怕;企業可能集中幾百位科學家的力氣在一個目標上,結果一無所得。於是幾十年前大藥廠開始追逐他們稱為「目標搜尋」或「理性設計」的做法。他們不再等待靈光一閃、福至心靈的一刻,而是理性分析,找到新發現,例如首先分辨出可能引起某種疾病的是哪些蛋白,然後嘗試用生物工程的方法,製造可以影響這些蛋白的化合物。
二○一三年,一群研究人員在《臨床與實驗藥理》
(Clinical & Experimental Pharmacology)期刊發表了一篇論文,指出近年來精神科新藥的發現速度緩慢,可謂乏善可陳。他們提出一個疑問:為什麼一九五○、六○年代的科學家,雖然使用的工具頗為原始,卻能夠發展出讓人眼睛一亮、有助醫治精神障礙的各種新方法?又為了甚麼,從那時起發現的速度快速下跌?「關鍵和重要的是需釐清楚,到底是哪些因素使得藥物發展好像陷入窒息狀態,」他們寫道,「至少有一位聲譽崇隆的專家,將目前的停滯不前歸咎於偶然力的式微。」
這篇論文的作者群辨識出一連串他們稱之為「反偶然力」的因素,認為這些因素可能影響了藥物的發展。他們指出,今天多家藥廠都刻意避開興之所至的嘗試和實驗,而擁抱比較「理性」的研究方式,包括「挑出那些根據基礎研究和理論」看來很有價值的「化合物來進行臨床試驗」。換句話說,你要在草堆裡找一根針,但又不願意仔細搜索整堆草,而只去看你相信埋藏了針的部分。這些作者宣稱,這種鎖定目標的做法可能減少了「快樂的意外」發生的機率。他們又說,在今天忙碌不堪的醫院裡,由於醫師花在觀察和聆聽病人的時間愈來愈少,他們從飽受病魔折磨的人身上學習的機會也減少了。
也許,製藥公司花幾百億美元老想著避開白忙一場的研究計畫,結果真正錯失的卻是意料之外、令人驚喜的發現。就像笑話中在路燈下手腳並用趴在地上找東西那個人——他在黑暗處搞丟了鑰匙,卻決定到光線比較好的地方來找尋。
不過就在這幾年,一群新興科學家——生物資訊學
(bioinformatics)專家——重新對偶然力產生興趣。他們希望能加速及「策畫」他們的運氣,方法就是用電腦搜尋過去成千上萬的實驗數據,偵測沒人預期的關連。理論上這做法會幫助他們注意到某些現象,獲得像將 UK-92480 轉變為威而鋼的寶貴靈感,只不過他們能夠做得更快也更便宜而已。二○一三年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報告估計,由於新方法能巨幅降低藥物的研發成本,因此在美國的醫療保健市場中,資料探勘技巧可能相當於一千億美元的產值——而且是每年的產值!
根據生物技術顧問公司 CBT Advisors 執行長斯帝夫.迪克曼(Steve Dickman)的說法:「過不了多久,比起大數據在財務預測或選擇最快捷交通路線上的應用,大數據在發現新藥和醫療保健中扮演的角色,將不遑多讓。」
但這方法真的那麼管用嗎?這問題可真比大數據還要大:迫使我們正視人類想像力的本質,思考我們探索未知的真正心態。
埋藏在基因中的謎團
正當我努力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偶然聽到一則故事,正充分反映出目前最潮的偶然力,可以如何和老舊偵探手法相輔相成,做出重大突破。故事的主人翁是名為莫里.羅賓遜(MurrayRobinson)的藥學家以及他的哥哥凱利(Kelly)。凱利的身體裡藏著一個謎。揭開這個謎的第一個線索來自一位臨床醫師,她對病人的細心觀察加上神準的第六感,一步步將她帶到這個問題上。可是,謎題中較複雜的細節,還是要靠基因定序或數據分析等工具方能解開。這些工具讓研究人員又快又準地探尋未知的世界,而這甚至在十年前仍未能做到。
一九七○年莫里只有八歲大時,跟哥哥同住一個房間。晚上熄燈以後,兩個小孩仍會小聲談話,回憶白天的不凡經歷。大人說凱利「慢」,因為他有學習障礙,但是莫里覺得哥哥很快、很吵也很好笑。凱利排隊買冰淇淋時會擠到最前面去;手舞足蹈,講好笑的屁笑話。在肅穆安靜的博物館內,凱利會指著一個希臘雕像大喊:「噢,天哪,這女生沒穿衣服耶!」戲院裡黑暗一片,他大叫:「嘿,各位,我們來玩大風吹吧!」然後就是對電子產品的著迷:你得將手電筒和電晶體收音機收好,否則凱利會把它拆開,讓電線和電池散落一地。凱利很古怪,但莫里就是喜歡他的多姿多采。多年以後,莫里才明白,所有的奇怪言行,都是數據點。
快轉到一九九○年代。此時莫里已經是生技公司安進(Amgen)一個研究團隊的主管,負責研發癌症新藥。「基因體的時代才剛開始。」莫里說,「因此我們抓住這個機會,全力投入。」安進添置了先進的DNA定序儀器,莫里和他的團隊開始收集跟癌症有關的基因。「那時候,大數據開始在生物學嶄露頭角,我們很清楚,必須發明新的方法來解讀和理解這些數據。我花很多時間跟數學家學習,如何將基因數據整理出個道理來。」
數據點之間的關聯,有時可以靜靜藏在那裡幾百年,直到某人找到正確的點,將它們連起來。但線索並不是在我們接觸不到的「遙遠彼端」,而是就在我們身邊,不過我們毫無警覺。
一九九八年,莫里正在跟有如暴風雪鋪天蓋地而來的數據拚搏,突然接到媽媽的電話。她剛剛讓凱利做了個新近發現的「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Smith-Magenis Syndrome,SMS)的檢查。而雖然莫里是基因體定序的專家,直到那一刻,他從未想過凱利的行為可能源自基因突變。
那一天,莫里使用安進的醫療系統搜尋數據庫,追查出每一篇研究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的論文。「我讀到一篇論文,那裡列出這個症候群的所有特徵─喜歡社交、有幽默感、咬自己的手、發脾氣,」莫里回憶說,「每一項好像都在形容凱利。再看下去,看到讓我最震驚的事。它說大部分有這種突變狀況的人都對電子產品著迷。我下巴立刻掉了下來。」那些過往時光——他哥哥為了看看電開關或遙控器裡面有甚麼而將它們拆爛——一下全回來了。重新認知哥哥凱利的「性格」,讓他十分掙扎。凱利的熱情、迷戀,甚至他的幽默感,竟然都肇因於基因裡頭的小小錯誤?(凱利的外觀也受到基因影響:眉毛濃密、嘴唇形狀像愛神邱比特的弓,手指粗粗短短的。)
一直以來,莫里覺得他哥哥性格很特別,獨一無二,但結果原來凱利屬於一個散布全球的族群,一個隱形的家族,而且他們全都極為相似。莫里至今仍覺得很驚訝,自己手上有最新式的基因定序機器,卻從未懷疑過,哥哥的稀奇古怪也許可用基因突變來解釋。
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的發現過程十分老派,換句話說,經由仔細觀察和絕佳運氣。一九八一年,丹佛市一家醫院裡的遺傳諮詢師安.史密斯(Ann Smith)在檢查一名嬰兒時,注意到小孩的心臟和上唇出現缺陷。幾個月後,她碰到另一名徵狀幾乎完全一樣的嬰兒。循著自己的第六感,史密斯懷疑兩者有關聯,於是分析了兩個小孩的基因物質,發現兩人的第十七號染色體都缺了一些東西。起先史密斯相信自己只不過發現了一個已被發現過的現象,因此她翻找文獻,企圖尋找研究報告來證實自己的觀察。結果發現從來沒有人發表過關於這個基因缺失的論文。
過沒多久,史密斯開始跟基因科學家艾倫.馬吉利氏(Ellen Magenis)合作,尋找和檢驗一出生就帶著罕見的第十七號染色體缺陷的小孩子。到了一九八○年代末,這個毛病已經有個名字,就是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以紀念兩位證明這個問題的女性。這時候,研究人員已發現了幾十位具有這種基因缺失的人,將他們的共同特徵整理出一個長長的清單。
當初史密斯誤打誤撞遇到這個神祕事件時,她不知道這是個謎,並沒有刻意尋求突破。相反地,好像是那個發現找上她,運氣則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大約二萬五千人當中,才會有一個人出生時帶著這種基因缺陷,而史密斯極湊巧地在幾個月之間遇到兩個案例。如果兩名小孩年齡差很多,她或者也不會注意到兩人相似之處,這又是另一個巧合。然而,史密斯似乎具有某些特異能力,能見人之所未見。她只不過抓住兩個案例,但把兩點連起來,就看出其中規律。在第五章,我們學到有一種人叫「超級偶遇者」,他們特別會注意到規律和發現新事物。史密斯無疑符合超級偶遇者的資格。她簡直是「直覺的威力+仔細觀察+不知疲倦的尋找真相」的活廣告,是個偶然力達人。
二○○九年,莫里和凱利抵達維珍尼亞州勒士頓市的凱悅飯店。在這之前,他們從未遇到過任何一個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的同路人。可是等他們一走進研討會會場的大門,圍繞著他們的幾十個小孩子——和幾個大人——全都手指粗硬、濃眉、行動蹣跚,皆因為基因裡的小小缺陷。
研討會期間,凱利對圍繞在他腳邊走來走去的史密斯—馬吉利氏小孩興趣不大,而立刻走到會場前方檢查麥克風,檢查電線如何連接,他對小工具的癡迷始終如一。同時,莫里則不停跟其他人握手,研究他們的名片。他十分興奮,因有此機會跟相關科學家討論,看有哪些可能治療他哥哥的方法。這時候,專家已斷定,單單缺了一個基因(RAT1),就會形成大部分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的問題。未能斷定的是其他大問題:基因如何運作?它在身體裡都在幹嘛?「我跟醫師、臨床醫師還有遺傳學家都談過了,」莫里說,「叫我震驚的是,想要在分子的層次理解根本原因,連專家都感到無助。於是我想:『我好像可以做點甚麼。』我明白,必須找到方法,弄清楚基因如何運作。」莫里說:「那會是我們這行的下一個重大議題。於是,由於我哥哥的關係,也由於我一直在研究癌症,我決定要建立一些研究工具,好解讀基因的運作。」雖然史密斯—馬吉利氏症候群從一個小缺陷開始,它的效應卻觸及其他基因,將他們或開或關,而引致悲劇。莫里想看看有沒有辦法利用大數據技巧來找出更多。
這種技巧仍然很新穎,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名稱。有人稱之為「乾巴巴生物學」,其他人較喜歡「生物資訊學」的說法,還有一些人說這是「矽中生物學」。(譯注:所謂「in silico」[在矽之中]的說法意思是「在電腦上進行或透過電腦模擬」)而最後這個說法自有其深意,關係到我們如何投資未來。「每一天,龐大的資訊量(關於基因的、蛋白的、藥物的或疾病的)全都被倒到網路上。換句話說,這是極為大量的新資訊,大部分未經分析,」莫里告訴我說,「所有的資訊都靜靜躺在那裡,開放給任何想分析資料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這些資訊,做出巨大發現。」
為了研究 RAT1 這個基因,理解它為哥哥身體帶來的浩劫,莫里成立了一個團隊。「我找了一些寫程式的人,將一大堆數據放在北卡的一個伺服器,然後我們就『玩』各種演算法,用數學方式將各基因的關連找出來。」他說。他們在數據中找到一些規律。似乎史密斯—馬吉利氏缺陷會破壞DNA在細胞裡的存放方式,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一個基因斷掉,居然會影響從睡眠模式到手指形狀等所有事情了。
他們就這樣在公開的數據庫裡東敲西弄。莫里在數以千計的實驗和研究報告中看到許多可能性,因而十分興奮。跟其他很多科學家一樣,他相信,這種資料探勘的做法可讓我們找到使用藥物的新方法。正確的演算法也許能將某種疾病造成的基因問題和藥物的作用配對,找到對策。「與其在實驗室等待『快樂的意外』出現,你也許可以在數據裡找到它。也許你可以說:『嘿,這種藥試過用來醫治風濕,不太管用,但它好像很適合拿來對付高血壓呢。』」莫里解釋。
這些日子,隨著生物資訊學的蓬勃發展,大家希望能夠用成本更低的方式來「碰」到重大發現。比方,面對如山的數據,只要拿著合適的工具,也許你只消花一個下午,就能夠搜尋並分析幾千個隨機找到的數據了。
莫里也把自己的未來押寶在上面了。二○一三年,他創立了一家名為 Molquant 的公司,目標正是要揪出躲藏在大數據裡的真知灼見,將之轉化為藥物以及診斷工具。
刻意製造出來的偶然?
阿圖.布特(Atul Butte)是位生物醫學家兼創業家,且是加州舊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計算健康科學院(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Health Sciences)的領導人。他更是大數據技巧的狂熱推動者。二○一四年一個研討會中,布特從口袋中掏出一塊基因晶片(gene chip,又名DNA微陣列[DNA microarray]),在觀眾面前揮舞。它看來不怎麼樣——一塊餅乾大小的四方型塑膠而已。不過,他說,這片小東西改變了我們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舉個例子,研究人員使用這塊晶片的時候,例如研究某種藥物如何影響血壓時,這晶片同時也取得了這藥物如何與DNA內各基因互動的大量數據。二○○二年,許多醫學期刊開始要求科學家將這些跟基因表現相關的數據全部上傳到公共數據庫,儘管該篇論文可能只提到這批數據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事實上,著那些多出來的數據(研究過程中順便收集到的數據)現在數量多到必須用「拍位元組」(petabytes,或千兆位元組)來計量了。(一拍位元組大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內總資訊量的四倍之多。)
這是為什麼有些研究人員,比如布特,全心擁抱這個新策略:他們不迴避未知,而是想辦法快速整理爬梳,在未知中探索,利用合適的演算法,搜尋全球頂尖實驗室累積的龐大實驗數據——頂尖研究人員做過數以千計的實驗,蒐集下來的數據卻可能從來沒人利用過。
這些數據將會大幅改變我們的能力,讓我們得以替原本熟悉的藥物找到新用途。本章一開頭,我們看到為了心絞痛研發的新藥,結果在治療勃起障礙上出乎意料的有效,但那個發現還需要有個「快樂的意外」來促成。「歷史上,幫舊藥發現新用途通常都牽涉到偶然的機運。」二○一五年一篇論文寫道。但作者指出,今天我們有可能加速快樂意外的發生率,方法是找出疾病狀態的規律和型態(例如基因表現),將之和藥物的作用相配對。網飛(Netflix)就透過分析用戶偏好,預測哪些人會喜歡某部新電影;臉書也藉由挖掘用戶的人際網絡,研究如何上廣告;現在同樣的數據分析被用在藥物學了。
布特和他的團隊早已開始在這些公開數據庫挖寶,為舊藥找新用途。他們透過演算法,發現鹽酸伊米胺(imipramine,自一九五○年代即存在的一種抗憂鬱藥物)對於小細胞肺癌可能有醫療功效。於是布特團隊用小鼠來測試這理論。而正如布特所希望的,鹽酸伊米胺的確有助於縮小實驗鼠的癌腫瘤。他們將結果刊登在《癌症發現》期刊中。「我們的研究顯示生物資訊學的威力強大,能極快速地為已獲美國食物藥品管理局(FDA)批准過的藥物重新定位……治療[患有小細胞肺癌的]病人,之前數十年來,都沒有一套有系統、有效的治療方法。」他們寫道。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整個流程進行的速度:研究人員從抓出線索到臨床試驗大約只花了兩年。要是必須等待偶然的機遇,可能得等個幾十年,才能將各個點串連起來。
布特告訴我,演算法提醒他其他還有許多可能的機會,包括或許可利用找到的型態,開發出能提早偵測病情的診斷工具:「我們正在檢視胰臟癌、皮膚病變、潰瘍性結腸炎等情況。新近的計畫是早產,或者說研究為什麼嬰兒會過早誕生。我們用的是由『出生缺陷基金會』(March of Dimes)資助的開放資料庫。」透過資料探勘,他的團隊找到幾種蛋白,可作為提醒是否有「先兆子癇」(preeclampsia,又稱妊娠毒血症)的問題。這是產婦及未出生嬰兒可能遇到的一大威脅。由於這些生物標記的發現,他們建立起一套早期檢測系統,在本書出版的二○一六年,這些檢測方法也許已可供大眾使用。整個過程進展飛快,從資料探勘到產品設計只不過花了兩年左右。
「開放資料跟世界上任何其他物品都很不一樣,它不像石油,不像土地,也不像空氣,更不像水。資料可重新補充,人人都可取而用之。只要你將每個數據組跟不同的東西比較配對,而且問對問題,你就可以找到新發現。」布特這樣告訴我。如果你把「breast cancer」(乳癌)這幾個字打進一些資料庫,你會找到數以千計、來自乳癌腫瘤的基因序列,由於資訊取得是如此容易,任何高中生都可以用這些數據來做研究。布特告訴我,杜克大學有個名為布麗坦妮.文歌(Brittany Wenger)的大學生,她還在念中學的時候,就曾經使用開放數據,描畫出惡性乳癌的分布地圖。在第十六章,我們會遇到另一位青少年,他則是利用網上數據庫發展出胰臟癌的早期偵測方法。
對布特而言,從數據得到的發現實在太多了,他有時會覺得不堪負荷。「我們真的需要多些人來參與。事情太多了,單靠我做不完。」而當然,等到更多人加入尋找新藥後,機緣湊巧的意外發現機率也會相應提高許多。
車庫中崛起的新藥發明家?
我們在前幾章看到,由於今天大家都能接觸到便宜的研發工具,因此愈來愈多人加入產品設計的行列。今天,我們差不多都有管道找到工具(例如3D印表機)來製作原型,但在一九八○年代,只有一小撮頂尖工程師才有機會接觸到這類工具。這種趨勢,為產品設計這行業帶來一批新的人才和新點子。例如第三章曾經提到的發明家法雷伊,就有能力獨立經營工作室,管控自己的生產流程,同時仰賴背後的群眾支持者。
如果期望同樣的趨勢也會吹到製藥界,那麼,就必須給有興趣的新世代人才提供工具和資金。但直到目前為止,離這種理想狀況還頗為遙遠。製藥界仍是門戶緊閉的團體,侷限於少數研究人員的參與,他們擁有實驗室,能接觸到病理樣本、病人,以及最重要的——龐大資金。加速藥物開發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創造其他人也負擔得起的研發工具,容許成千上萬的人才都能成為製藥業者。
目前我們就是往這方向邁進。
第一個讓我注意到這驚人發展的人是布特:許多研發藥物所需要的設施,皆可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正如車庫發明家可以找工廠合作生產,目前,車庫生技發明家也可以聘請實驗室或其他相關服務,來協助證明藥物真的有效。
在傳統的製藥體系,研發人員必須準備幾百萬美元的資金,在附屬的實驗室進行動物試驗。現在則可在網路上找到其他解決管道。你可以透過名為 Assay Depot 的網站聘請研究人員,替你將設計好的藥物在大鼠、小鼠、生物組織或細胞上進行研究測試。你可以明確指定要用哪一種狀態的小鼠來試驗你的化合物,這些小鼠可能經過基因改造後變得過肥,罹患肺癌、白血病,或處於其他狀態之中。你也可以聘請和 Assay Depot 有合作關係的實驗室創造出你的「設計師小鼠」,來進行你的試驗。因此,任何人只要拿著信用卡,就能買到實驗的許多步驟,有如一般產品設計師直接跟中國某家工廠下訂單買零件。
布特早已開始使用 Assay Depot 來測試藥物的功效。只要點幾下滑鼠,用信用卡付費,他就聘請了好幾家聲譽良好實驗室裡的專家,來測試他的候選藥物。布特估計,使用這種方式,一整套測驗的花費(包含他自己的人力)約為七萬五千美元,開發新藥時,從開始到結束的成本則可減到約十五萬美元。這樣的研發成本已降至小公司都負擔得起的範圍,包括布特自己的新創事業NuMedii 公司在內。
布特告訴我,連組織樣本也可以在網上購買。「樣本主人(病人)的個人資料已全清除掉,重新包裝好,等待有需要的研究人員。因此尋求樣本來做實驗已不是最困難的一部分,特別是針對比較一般的病症而言,」他說,「其實你可以從網路開始。」
真的,我找到一家名為「先進組織服務」(Advanced Tissue Services)的公司,宣稱可「為你提供細胞、人體組織及生物檢體」。這網站沒有購物車的功能,但承諾「可根據你開列的需求,提供新鮮的組織。」
有些創業家很可能已開始想辦法將這類服務連結整合為生技公司。到時大型製藥公司發現自己將面對一大群小公司的競爭。
「在矽谷,我們已很習慣毛頭小子在家裡車庫或校內宿舍創立令人驚訝、價值奇高的公司,」布特說,「那麼,你為何不能在某個車庫創立下一家基因科技公司(Genentech)呢?」
我提醒他,由於他擁有博士外加醫學學位,且在大學任教,安排人體臨床實驗當然比較容易,從車庫起家的毛頭小子沒有類似的人脈可運用。
「現在還不能,」他回應說,「但未來為何不能呢?」
二○一四年,曾協助創立 Airbnb 等公司的著名創投育成公司 Y Combinator(簡稱YC公司)宣布,他們將開始投資製藥公司。
Y C的其中一個創投標的 Transcriptic 打算提供的服務,是讓任何人皆可租用機器人來進行自動化的實驗。「創立 Transcriptic 時,我們的目標是為生命科學界提供網路業享有的結構性優勢,這樣一來,兩個博士後傢伙只要拿著一部手提電腦,坐在咖啡廳裡,就可以經營製藥公司,而無須花幾百萬美元買儀器或租地方設立實驗室,」創辦人馬克斯.何達克(Max Hodak)在二○一五年一篇部落格文章裡寫道,可是,「要說清楚,我們目前還未走到那地步。」
目前,醫藥研發正面臨開始鬆綁的階段,一如「優步」(Uber)面對各種官司和挫折,可出租實驗室也會面臨類似問題,但看來大勢所趨,某些藥物難以避免地將在手提電腦上產生。事實上,生物創客已開始進入這個行業了。
醫學的金礦
不過,美國克里夫蘭醫療中心(Cleveland Clinic)的血液學兼腫瘤科專家尤根.桑塔拉拉札(Yogen Saunthararajah)仍然對於「有計畫的偶然事件」存疑。過去十多年,他持續進行臨床試驗,試圖尋找更好的血癌療法;且於二○一五年有突破性發現,結果發表在《臨床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前文提過的史密斯是個超級偶遇者,桑塔拉拉札和史密斯很像,費盡心力治療病人,聆聽他們談話,全心奉獻於發現的藝術。但他告訴我,他對於從如山的數據中找出規律,接著依靠遠端進行的實驗來決定一切的做法,十分懷疑不信任。
桑塔拉拉札參與血癌病人的生活,事實上參與甚深,對於傳統化療的恐怖副作用也深感痛苦——體力衰竭、掉頭髮、沮喪、嘔吐,甚至死亡。十多年前他就開始疑惑,是否可以使用低劑量、無毒、FDA核准的藥物「地西他濱」(decitabine),輔以還未經FDA批准的「四氫尿苷」(tetrahydrouridine),來代替傳統的化療程序。他希望找到更有效的治療方案,讓病患接受治療時可以不必犧牲生活品質。他的理論是,只要這兩種藥物的分量配合得當,或許可啟動癌細胞內的一組指令,讓癌細胞「長大」為無害的血液細胞,最後死去。這樣一來,藥物幾乎不會影響到健康的細胞,換句話說,不會構成什麼副作用。
二○一五年,他和他的同事報告說,已在二十五位血癌病人身上測試過這套方法,接近一半的病人血細胞計數出現進步,表示他們的身體確實開始抗癌。考量到那些病患原已處於末期階段,而且對其他藥物毫無反應,這個結果特別令人興奮。同樣重要的是,病患差不多沒有經歷伴隨化療而來的可怕副作用。
為了取得這些成果,桑塔拉拉札和他的團隊可是花了很多年不斷摸索,仔細反覆測試、檢驗他們的理論。他強調,藥物研發需要同時深入研究病人和科學。捷徑極少行得通。「套一句被引用到爛、但極為正確的話,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如果我們真的想征服疾病,取得進展,就需要在分子層次充分理解一連串的因果關係,」他說,「機器人無法揭示其間的機制,這些真理,需要如藝術般的技巧,需要愛,還需要大量經費以及多年的努力。運用人類的聰明才智和熱忱努力不懈地解決問題,不會成為新聞,但這才是做事情的王道。」
可是,我們必須在人類和機器人之中擇一嗎?理想的方案應該是同時動用兩種新治療方法。目前,許多有天分的研究人員正致力於找尋聰明的方法,結合巧妙設計下的偶然力和傳統的直覺力,加速突破的誕生。
畢竟,那些花四十億美元的藥物已彷彿是上個世代的老古董了,就像那些百萬美元電腦或兩千美元的手提計算機。無疑地,網際網路在移除障礙,讓行外人拿到工具,得以挑戰權威。已經發生的是,新創公司或獨立發明家開始進入藥物研發的領域,試驗新方法。千萬別忘記,那以「拍」來計算的位元組,簡直是還未被探勘的新大陸,可能藏著醫治疾病的線索。「那些數據是被冰封的知識,需要某人用熱力將它溶化,讓知識破冰而出。」布特告訴我。冰封的數據王國也許就是醫學的金礦。
一路走來,科學家繼續發展新科技,讓我們搜尋數據庫,也搜尋我們的周遭環境,找尋救命藥物。例如,基因定序的工具有助於找出池中藻類、泥土甚至人體腸子裡潛藏著的寶藏;又或者是幾十年前還不為人知的微生物,其實是藥物的來源。換句話說,曾經看來不值一提的,原來包含著巨大的價值。在下一章,我們會跳到神奇的垃圾箱,看看為什麼發明家認為,看似無用的廢物竟是那麼充滿啟發性和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