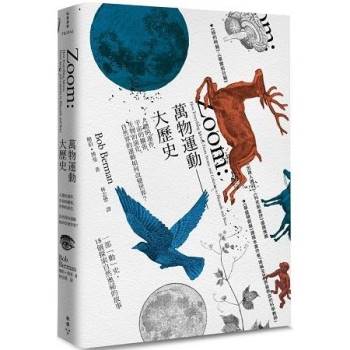人的大腦有偏見。我們天生就是會去注意突發動作。
當我們呆望窗外,想著要繳多少稅,如果突然有什麼風吹草動打破這寧靜時刻,馬上便會抓住我們的目光。比方說,兔子從灌木叢裡衝出來。這個場景裡可能早就有數不清的東西在慢速移動——毛毛蟲、樹枝微微晃動、雲影變幻——但我們不會去注意。真丟臉。雖然我們會注意突如其來的快動作,但地球上慢速緩步、匍匐行進的物體,對我們生活的影響遠大於兔子的衝刺。
我們對速度的偏見,最晚打從有書寫文字就開始了。儘管古時候的生活步調遠比今天悠閒,但古代的重要文獻資料也表現出對「慢」興趣缺缺。沒錯,大家都知道,太陽下山的地方與它黎明首次現身處差了180度。農業社會在乎麥子有沒有長得更高,但重要的是最後的結果。他們不知道、不然就是不在乎玉米一天長高2.5公分,一種難以察覺、連鐘的時針都比它快上20倍的動作。
◎快移慢動大驚奇
我們全都是受縛於自身經驗的囚徒,而人類的運動便是我們名之曰快或慢的標準。速度最快的真實人物至今仍在世:牙買加的波特(Usain Bolt)。他在2009年柏林世錦賽的百米賽跑中跑出9秒58,相當於每小時37公里的速度。這是人類只憑自己雙腿最快的行進速度。彷彿要證明這不只是曇花一現的僥倖,他在2012年倫敦奧運時把所有競爭者全甩在後頭,跑出幾乎分毫不差的速度。
當然,沒有人能長時間維持這樣的速度。1.6公里的最快速度為3分43秒13,相當於每小時25.8公里。馬拉松跑者所達到的最佳紀錄平均為每小時20公里。我們衡量動物快或慢,是根據「牠們能不能從後面趕上我們」這個古代重要課題。
但我們此刻所要探索的,是比快普遍得多的懶散。說到懶散,那些三蹄哺乳類不應揹上一無是處的名聲。樹獺即使有充分動機,每小時也只走0.1公里。就像電影《西城故事》裡的Ice唱的:「腳步輕,聲音小,輕鬆把事辦」;單單1.6公里,最興奮的樹獺需要一整天漫長夏日才能走完。連大海龜慢慢跑都比牠快25%。速度感知這種事有點微妙。某物只要在短時間內移動相當於自己身體長度的距離,我們就認為它快。舉例來說,旗魚每秒游10倍自體長度的距離,因而被認為非常快速。但即將降落的波音747客機一秒內只能飛越「1倍」自體長度:70公尺。它因為自身的巨大而在視覺上吃了虧。從遠處看,下降中的大型噴射機看似幾乎沒在動,那是因為它要花整整一秒才能完全離開現在的位置。但實際上,它移動得比旗魚快4倍。
現在來想想細菌。已知細菌有半數能夠自己前進,通常是靠著揮動其鞭毛——看起來像尾巴的螺旋狀長附肢。細菌慢不慢?在某種意義上,是慢。最快的細菌每秒能跨越一根人髮粗細的距離。我們應該要覺得印象深刻嗎?
不過,把鏡頭拉近來看,這種運動就變得不同凡響。首先,這種細菌每秒移動了100倍自體長度的距離,有些能做到200倍的自體長度。按其相對大小,細菌游得比魚快20倍,這等於短跑運動員突破音速障礙一樣。
而且,所行經的距離快速增加。微生物每小時可移動0.3、0.6公尺,難怪疾病會傳播。
其他令人害怕的運動也隨時在我們家中出現。例如空氣中的灰塵,許多灰塵的組成成分是細小的死皮碎片。注意看陽光穿過窗戶射進來的光線,你家裡無所不在的浮塵便會變得明顯。畢竟,單就其本身而論,光線是看不見的。在家裡,只有當光線擊中數不清的慢速飄浮粒子時,我們才看見光線。在非常潮濕的情況下,微細的水滴捕捉到光,但乾燥的空氣中都是灰塵。
乍看之下,懸浮微粒好像哪兒都不去。這些粒子隨著最微弱的氣流或上或下地移動。但要是讓房間空著——比如說晚上,那時候沒有人會去動任何東西——那麼這種死皮和其他碎屑會以每小時2.5公分的速率下降。那些到處亂竄的細菌都比這快10倍。有誰曾想過我們的家是這麼令人毛骨悚然?
在可見領域內,我們身邊的慢速運動典型就是我們的指甲。還有頭髮。
指甲每兩個月長0.6公分,這是頭髮生長速率的一半。如果我們像牛頓和愛因斯坦那樣忘了與理髮師有約,便會發現自己的頭髮每年長15公分。但指甲的變動方式很有趣。比較長的那幾根手指,指甲長得比較快速,小指指甲的進展拖拖拉拉。腳指甲的生長速率只有手指甲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說,它們以這種速率生長,除非你喜歡赤腳走路,這會刺激生長。手指甲也對刺激有反應,這就是為什麼打字員和電腦上癮的人有比其他人長得都快的指甲。或許,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作家當中有這麼多人喜歡咬指甲。
指甲在夏天長得比較快、男性長得比較快、不抽菸的人長得比較快,還有懷孕的人長得比較快。但指甲在你死後就完全不長。死後傳說開始流傳,大概是因為一個人過世兩天之內,和死掉的手指相連的皮膚會往回縮,露出更多的指甲。
◎這個動個不停的世界
地球上慢速運動最戲劇化的例子,大概是地球本身吧。洞穴裡的鐘乳石和石筍,一般而言是以每五百年2.5公分的速率延長。相較之下,山則相當快速;它們——隨便啦,就說是喜馬拉雅山好了——每年把自己推高個5公分。
2006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山脈隆起到最大高度,一般來說只需要兩百萬年左右。聖母峰自從第一次測量以來,長高之多已到可以測量出來的程度。某些活動只會越來越困難。
事實上,你自己也在移動,即便是癱在沙發上看電視的時候。所有陸塊都在移動,帶著你和你的電視西移,如果你住在美國的話。你可以躺在床上高唱:「加州,我來了!」但一年1.3公分,你最好把你的綜合堅果帶著。
我們人類對事物的度量與分類有強迫症,但談到速度,我們發現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終止點:最低速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跑得比「停止」還慢。但要找出有哪一種東西看不到有任何層級的運動,卻驚人困難。
如果我們仔細看,連睡覺中的樹獺也有細微的動靜。牠在呼吸,而且牠的原子抖得可凶了。但很酷的是,我們發現,某物越冷,其原子就動得越慢,所以真正的無運動是意味著達到無限冷的狀態。在地球上最冷颼颼的地方(南極,1983年在那裡記錄到冷冰冰的攝氏零下89度),還是有很多的原子運動。原子只有到了攝氏零下273.15度才停止運動,那就是「絕對零度」。19世紀中葉,脾氣雖壞但才華洋溢的愛爾蘭裔英籍科學家克爾文爵士(Lord Kelvin)最先確認這一點,而應用日廣的克氏溫標便是他的身後崇榮;這套溫標將其零度定在這個事關重大的點(而不是像瑞典天文學家攝爾修斯﹝Anders Celsius﹞定在水的冰點,或是鹵冰融泥的溫度,這是波蘭物理學家華倫海特﹝Daniel Fahrenheit﹞選定為其溫標起點之處)。
◎動個不停的你
「抱歉,我現在在忙,」你對朋友這麼說。
這話說得真對,你的身體像銀河系一樣忙。
即使在我們休息和作白日夢的時候,體內活動也未停止。其中有些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脈搏、自己的心跳、自己的胸腔正在吐氣。也許還有我們的肚子咕咕響個幾下,其他就沒什麼了。像這樣僅限於對少數幾種體內運動有知覺是件好事。大自然放我們一馬,免於被皮膚底下正在上演、多到數不清的戲碼給煩死了。
但現在讓我們來知覺看看吧,即使只是為了理解青少女畫眼線時那種微妙又巨大的複雜性。
我們或許可以先來思考一下思考這回事。大腦當然是我們神經系統的冠頂之珠、最高主宰。(會不會就是大腦在此刻吹響它的號角,讓我寫下這段話?)大腦有八百五十億神經元細胞,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腦豪擁一百五十「兆」神經突觸。這些是它的電性連結、它的可能性,這個數目比銀河系恆星之數大上近千倍。
大腦神經元數目大得驚人。以每秒一個的速率來數的話,得花上三千兩百年。但大腦神經突觸,或是它的電性連結,數量之多更是令人難以置信。那一百五十兆沒花上三百萬年是數不完的。事情還沒完呢,接著想到的是每個細胞可以有多少種彼此連結的方式。講到這裡,我們就必須用到階乘了。這東西很酷。且說,我們想知道書架上的4本書可以有多少種排列方式。簡單:你把4×3×2——唸作「四的階乘」,寫成4!——乘起來,就能找出有多少可能,也就是24種。但要是你有10本書呢?還是簡單:是10!,或是10×9×8×7×6×5×4×3×2,那是——準備好了嗎?——3,628,800種不同的方式。想像一下:從4個項目到10個,可能的排列方式從24種增加到360萬種!總結:可能性總是比我們周遭的事物數量還多,多到一發不可收拾、多到令人抓狂。如果每一個神經元或大腦細胞和你顱骨內其他任何一個神經元都可以連結,其組合數會是850億的階乘。這個數裡頭的0多到可以填滿地球上所有的書還有剩,而這只是0而已——只是記數法,不是實際的數目。記住,每次你光是加上六個0,不管在此之前的數有多大,你所表式的量都比它還要大上100萬倍。大腦連結的可能性超乎同一顆大腦的理解能力。
這種複雜構造全都在一團看似了無生氣的1.4公斤重起司裡,大小約與1400cc引擎的活塞相同。因為顱骨內沒有肌肉,也因為大腦的密度比水大不了多少,所以看起來的確像是一團爛糊糊、不起眼的東西。然而,大腦的賦動能力完全隱藏了起來。使它活躍有生氣的,是它無休無止的電性活動。肉眼不可見的火花四處飛躍,每個神經元都以大約100毫伏(1毫伏為千分之一伏特)在運作。十分之一伏特非常夠用了:這個運作基體比一顆AAA電池還小。即使你把大腦全部的能源消耗量加起來,也只不過23瓦特(一個人每天消耗2400卡)。儘管如此,只占人體質量2%的大腦,還是用掉人體能源的20%這麼一大塊。大腦是耗能大戶,沒有斷電裝置,電流持續不斷地流動著。
◎我決定還是大腦決定?
關於這種電性活動最早的線索來自義大利醫生賈法尼(Luigi Galvani),他在1791年發表青蛙的神經電刺激研究成果。如果是電使得肌肉收縮,那麼這就是大腦完成其指令的必要方法!隔年,他的義大利同胞、博物學家法布羅尼(Giovanni Valentino Mattia Fabbroni)指出,這種電性神經活動一定會動用到化學物質。八年後的1800年,當義大利物理學家伏特(Alessandro Volta)發明濕式電池,這整個想法聲勢大漲。這種電池是以自我閉合的方式產生電力並加以儲存——大腦有沒有可能同樣如此?
當然,大腦比這複雜多了。當1906年的諾貝爾醫學獎頒給義大利病理學家高爾基(Camillo Golgi)和西班牙病理學家拉蒙—卡哈爾(Santiago Ramón y Cajal),獎勵他們在神經系統組織研究上的突破,也不過是標識出探索這個迷宮構造的先驅腳步。而即使到了今天,這個構造仍然遠比人體其他部分神祕得多。但至少在那一刻,我們掌握到指揮肌肉運動的機制。電通過銅線是以96%的光速行進,進了神經纖維就沒這種好事了。我們人體的神經元有好幾種不同的種類和功能,但沒有一種能讓電流流動得像在電動開罐器中那般迅捷,連1%都沒有。不過,我們顯然不需要靠這種光速認知能力,便能在日常心智表現上有出色成績,像是把垃圾放進袋子裡。我們實際上只有每秒約120公尺的最大運作速率,比光速的百萬分之一還少,就已經快到夠把這差事給搞定了。
我們很快地做個實驗,就能明顯看出這一點。閉上你的眼睛,然後舉起一隻手快速地四面揮舞——在頭頂上揮、往旁邊揮、隨便揮。你每一分每一秒、隨時都清楚那隻手到底在哪兒,無論你的手變換位置的速度有多快。你對手掌位置的即刻察覺能力證明,神經電訊號到達大腦的速度極快,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唯有「即時」資訊才派得上用場。事實上,那些脈衝訊號每小時前進400公里。
這是神經對必要內容的傳送速度。但怎麼樣才算得上「必要」?幸好,你不必針對大腦接收到的所有感覺、肌肉、壓力、疼痛和其他訊號,就其相對重要性排優先順位。這件事甚至在你離開子宮之前便已經安排、設計、透過基因內建好了。朋友興高采烈但粗心大意的手勢就要戳到你的眼睛?你馬上一邊眨眼、一邊閃避。吃東西時叉子最好別刺到自己?你的手指和嘴唇傳來的位置訊號當下就整合起來。某次露營過夜之旅,你赤腳走出帳篷,踩到一個可疑的物體,感覺起來是一坨像蛇一樣的可怕東西,你在剎那間猛力把腿拉起來。這些反射動作都是神經以每小時400公里的速度在下命令。
但現在用你的腳趾踢東西,請記住是什麼時候踢到。要過幾秒鐘才會感覺到痛。那是因為疼痛訊號的行進是沿著不同的線路,以每小時只有4.8公里或每秒0.6公尺的低順位速度。傳遞壞消息不用急。
那思考呢?這類訊號以介於兩者之間的速度出現,既不是最快、也不是最慢。這些訊號以每小時112公里滑行、分進,通過大腦皮質層。這個過程的速度夠快,所以你可以在另一套電路系統——你的本我、你的自我感知——獲知之前做完決定。2006年,晚近的研究者、美國神經生理學家利貝特(Benjamin Libet)及其研究團隊要求志願受試者,在他們想好要舉起哪隻手臂的當下按下按鈕,然後立刻抬起正確的那隻手臂。驚人的事情來了。盯著實驗對象腦波的研究人員在志願受試者弄清楚自己的選擇之前十秒,就能有把握地分辨出受試者做了哪一種決定!
換句話說,大腦的電性活動會自動進行,像胰臟或肝臟一樣。大腦自主做出決定,我們要稍晚一點才明白決定了什麼。
我們可能對選擇這件事有一種主觀的認知。我們可能會說:「我決定今晚要吃中國菜,不吃義大利菜。」但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發揮自由意志,大腦藉由自發的電性連結自行做了決定。要如何把這個活動控制得比對自己腎臟運作的掌控更好,我們沒人有一丁點的概念(好,如果你對此不以為然,聲稱能夠自己做選擇且這些決定並非自動產生,那麼你應該要知道,你這個想法本身甚至在你起心動念去想、去說之前,就已經自行形成)。
這些或快、或慢、不快不慢的電脈衝和突觸連結,全都連續不斷地發生,而且早上的步調最快。只有在燈光熄滅時才得以休息:當我們睡著時,大腦運轉程度降低很多。
二十二歲至二十七歲之間達到高峰後就開始萎縮的神經系統活動,當然是體內其他無數運動的控制系統。而我們感知最明確的,當然是呼吸和心跳。
當我們呆望窗外,想著要繳多少稅,如果突然有什麼風吹草動打破這寧靜時刻,馬上便會抓住我們的目光。比方說,兔子從灌木叢裡衝出來。這個場景裡可能早就有數不清的東西在慢速移動——毛毛蟲、樹枝微微晃動、雲影變幻——但我們不會去注意。真丟臉。雖然我們會注意突如其來的快動作,但地球上慢速緩步、匍匐行進的物體,對我們生活的影響遠大於兔子的衝刺。
我們對速度的偏見,最晚打從有書寫文字就開始了。儘管古時候的生活步調遠比今天悠閒,但古代的重要文獻資料也表現出對「慢」興趣缺缺。沒錯,大家都知道,太陽下山的地方與它黎明首次現身處差了180度。農業社會在乎麥子有沒有長得更高,但重要的是最後的結果。他們不知道、不然就是不在乎玉米一天長高2.5公分,一種難以察覺、連鐘的時針都比它快上20倍的動作。
◎快移慢動大驚奇
我們全都是受縛於自身經驗的囚徒,而人類的運動便是我們名之曰快或慢的標準。速度最快的真實人物至今仍在世:牙買加的波特(Usain Bolt)。他在2009年柏林世錦賽的百米賽跑中跑出9秒58,相當於每小時37公里的速度。這是人類只憑自己雙腿最快的行進速度。彷彿要證明這不只是曇花一現的僥倖,他在2012年倫敦奧運時把所有競爭者全甩在後頭,跑出幾乎分毫不差的速度。
當然,沒有人能長時間維持這樣的速度。1.6公里的最快速度為3分43秒13,相當於每小時25.8公里。馬拉松跑者所達到的最佳紀錄平均為每小時20公里。我們衡量動物快或慢,是根據「牠們能不能從後面趕上我們」這個古代重要課題。
但我們此刻所要探索的,是比快普遍得多的懶散。說到懶散,那些三蹄哺乳類不應揹上一無是處的名聲。樹獺即使有充分動機,每小時也只走0.1公里。就像電影《西城故事》裡的Ice唱的:「腳步輕,聲音小,輕鬆把事辦」;單單1.6公里,最興奮的樹獺需要一整天漫長夏日才能走完。連大海龜慢慢跑都比牠快25%。速度感知這種事有點微妙。某物只要在短時間內移動相當於自己身體長度的距離,我們就認為它快。舉例來說,旗魚每秒游10倍自體長度的距離,因而被認為非常快速。但即將降落的波音747客機一秒內只能飛越「1倍」自體長度:70公尺。它因為自身的巨大而在視覺上吃了虧。從遠處看,下降中的大型噴射機看似幾乎沒在動,那是因為它要花整整一秒才能完全離開現在的位置。但實際上,它移動得比旗魚快4倍。
現在來想想細菌。已知細菌有半數能夠自己前進,通常是靠著揮動其鞭毛——看起來像尾巴的螺旋狀長附肢。細菌慢不慢?在某種意義上,是慢。最快的細菌每秒能跨越一根人髮粗細的距離。我們應該要覺得印象深刻嗎?
不過,把鏡頭拉近來看,這種運動就變得不同凡響。首先,這種細菌每秒移動了100倍自體長度的距離,有些能做到200倍的自體長度。按其相對大小,細菌游得比魚快20倍,這等於短跑運動員突破音速障礙一樣。
而且,所行經的距離快速增加。微生物每小時可移動0.3、0.6公尺,難怪疾病會傳播。
其他令人害怕的運動也隨時在我們家中出現。例如空氣中的灰塵,許多灰塵的組成成分是細小的死皮碎片。注意看陽光穿過窗戶射進來的光線,你家裡無所不在的浮塵便會變得明顯。畢竟,單就其本身而論,光線是看不見的。在家裡,只有當光線擊中數不清的慢速飄浮粒子時,我們才看見光線。在非常潮濕的情況下,微細的水滴捕捉到光,但乾燥的空氣中都是灰塵。
乍看之下,懸浮微粒好像哪兒都不去。這些粒子隨著最微弱的氣流或上或下地移動。但要是讓房間空著——比如說晚上,那時候沒有人會去動任何東西——那麼這種死皮和其他碎屑會以每小時2.5公分的速率下降。那些到處亂竄的細菌都比這快10倍。有誰曾想過我們的家是這麼令人毛骨悚然?
在可見領域內,我們身邊的慢速運動典型就是我們的指甲。還有頭髮。
指甲每兩個月長0.6公分,這是頭髮生長速率的一半。如果我們像牛頓和愛因斯坦那樣忘了與理髮師有約,便會發現自己的頭髮每年長15公分。但指甲的變動方式很有趣。比較長的那幾根手指,指甲長得比較快速,小指指甲的進展拖拖拉拉。腳指甲的生長速率只有手指甲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說,它們以這種速率生長,除非你喜歡赤腳走路,這會刺激生長。手指甲也對刺激有反應,這就是為什麼打字員和電腦上癮的人有比其他人長得都快的指甲。或許,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作家當中有這麼多人喜歡咬指甲。
指甲在夏天長得比較快、男性長得比較快、不抽菸的人長得比較快,還有懷孕的人長得比較快。但指甲在你死後就完全不長。死後傳說開始流傳,大概是因為一個人過世兩天之內,和死掉的手指相連的皮膚會往回縮,露出更多的指甲。
◎這個動個不停的世界
地球上慢速運動最戲劇化的例子,大概是地球本身吧。洞穴裡的鐘乳石和石筍,一般而言是以每五百年2.5公分的速率延長。相較之下,山則相當快速;它們——隨便啦,就說是喜馬拉雅山好了——每年把自己推高個5公分。
2006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山脈隆起到最大高度,一般來說只需要兩百萬年左右。聖母峰自從第一次測量以來,長高之多已到可以測量出來的程度。某些活動只會越來越困難。
事實上,你自己也在移動,即便是癱在沙發上看電視的時候。所有陸塊都在移動,帶著你和你的電視西移,如果你住在美國的話。你可以躺在床上高唱:「加州,我來了!」但一年1.3公分,你最好把你的綜合堅果帶著。
我們人類對事物的度量與分類有強迫症,但談到速度,我們發現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終止點:最低速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跑得比「停止」還慢。但要找出有哪一種東西看不到有任何層級的運動,卻驚人困難。
如果我們仔細看,連睡覺中的樹獺也有細微的動靜。牠在呼吸,而且牠的原子抖得可凶了。但很酷的是,我們發現,某物越冷,其原子就動得越慢,所以真正的無運動是意味著達到無限冷的狀態。在地球上最冷颼颼的地方(南極,1983年在那裡記錄到冷冰冰的攝氏零下89度),還是有很多的原子運動。原子只有到了攝氏零下273.15度才停止運動,那就是「絕對零度」。19世紀中葉,脾氣雖壞但才華洋溢的愛爾蘭裔英籍科學家克爾文爵士(Lord Kelvin)最先確認這一點,而應用日廣的克氏溫標便是他的身後崇榮;這套溫標將其零度定在這個事關重大的點(而不是像瑞典天文學家攝爾修斯﹝Anders Celsius﹞定在水的冰點,或是鹵冰融泥的溫度,這是波蘭物理學家華倫海特﹝Daniel Fahrenheit﹞選定為其溫標起點之處)。
◎動個不停的你
「抱歉,我現在在忙,」你對朋友這麼說。
這話說得真對,你的身體像銀河系一樣忙。
即使在我們休息和作白日夢的時候,體內活動也未停止。其中有些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脈搏、自己的心跳、自己的胸腔正在吐氣。也許還有我們的肚子咕咕響個幾下,其他就沒什麼了。像這樣僅限於對少數幾種體內運動有知覺是件好事。大自然放我們一馬,免於被皮膚底下正在上演、多到數不清的戲碼給煩死了。
但現在讓我們來知覺看看吧,即使只是為了理解青少女畫眼線時那種微妙又巨大的複雜性。
我們或許可以先來思考一下思考這回事。大腦當然是我們神經系統的冠頂之珠、最高主宰。(會不會就是大腦在此刻吹響它的號角,讓我寫下這段話?)大腦有八百五十億神經元細胞,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腦豪擁一百五十「兆」神經突觸。這些是它的電性連結、它的可能性,這個數目比銀河系恆星之數大上近千倍。
大腦神經元數目大得驚人。以每秒一個的速率來數的話,得花上三千兩百年。但大腦神經突觸,或是它的電性連結,數量之多更是令人難以置信。那一百五十兆沒花上三百萬年是數不完的。事情還沒完呢,接著想到的是每個細胞可以有多少種彼此連結的方式。講到這裡,我們就必須用到階乘了。這東西很酷。且說,我們想知道書架上的4本書可以有多少種排列方式。簡單:你把4×3×2——唸作「四的階乘」,寫成4!——乘起來,就能找出有多少可能,也就是24種。但要是你有10本書呢?還是簡單:是10!,或是10×9×8×7×6×5×4×3×2,那是——準備好了嗎?——3,628,800種不同的方式。想像一下:從4個項目到10個,可能的排列方式從24種增加到360萬種!總結:可能性總是比我們周遭的事物數量還多,多到一發不可收拾、多到令人抓狂。如果每一個神經元或大腦細胞和你顱骨內其他任何一個神經元都可以連結,其組合數會是850億的階乘。這個數裡頭的0多到可以填滿地球上所有的書還有剩,而這只是0而已——只是記數法,不是實際的數目。記住,每次你光是加上六個0,不管在此之前的數有多大,你所表式的量都比它還要大上100萬倍。大腦連結的可能性超乎同一顆大腦的理解能力。
這種複雜構造全都在一團看似了無生氣的1.4公斤重起司裡,大小約與1400cc引擎的活塞相同。因為顱骨內沒有肌肉,也因為大腦的密度比水大不了多少,所以看起來的確像是一團爛糊糊、不起眼的東西。然而,大腦的賦動能力完全隱藏了起來。使它活躍有生氣的,是它無休無止的電性活動。肉眼不可見的火花四處飛躍,每個神經元都以大約100毫伏(1毫伏為千分之一伏特)在運作。十分之一伏特非常夠用了:這個運作基體比一顆AAA電池還小。即使你把大腦全部的能源消耗量加起來,也只不過23瓦特(一個人每天消耗2400卡)。儘管如此,只占人體質量2%的大腦,還是用掉人體能源的20%這麼一大塊。大腦是耗能大戶,沒有斷電裝置,電流持續不斷地流動著。
◎我決定還是大腦決定?
關於這種電性活動最早的線索來自義大利醫生賈法尼(Luigi Galvani),他在1791年發表青蛙的神經電刺激研究成果。如果是電使得肌肉收縮,那麼這就是大腦完成其指令的必要方法!隔年,他的義大利同胞、博物學家法布羅尼(Giovanni Valentino Mattia Fabbroni)指出,這種電性神經活動一定會動用到化學物質。八年後的1800年,當義大利物理學家伏特(Alessandro Volta)發明濕式電池,這整個想法聲勢大漲。這種電池是以自我閉合的方式產生電力並加以儲存——大腦有沒有可能同樣如此?
當然,大腦比這複雜多了。當1906年的諾貝爾醫學獎頒給義大利病理學家高爾基(Camillo Golgi)和西班牙病理學家拉蒙—卡哈爾(Santiago Ramón y Cajal),獎勵他們在神經系統組織研究上的突破,也不過是標識出探索這個迷宮構造的先驅腳步。而即使到了今天,這個構造仍然遠比人體其他部分神祕得多。但至少在那一刻,我們掌握到指揮肌肉運動的機制。電通過銅線是以96%的光速行進,進了神經纖維就沒這種好事了。我們人體的神經元有好幾種不同的種類和功能,但沒有一種能讓電流流動得像在電動開罐器中那般迅捷,連1%都沒有。不過,我們顯然不需要靠這種光速認知能力,便能在日常心智表現上有出色成績,像是把垃圾放進袋子裡。我們實際上只有每秒約120公尺的最大運作速率,比光速的百萬分之一還少,就已經快到夠把這差事給搞定了。
我們很快地做個實驗,就能明顯看出這一點。閉上你的眼睛,然後舉起一隻手快速地四面揮舞——在頭頂上揮、往旁邊揮、隨便揮。你每一分每一秒、隨時都清楚那隻手到底在哪兒,無論你的手變換位置的速度有多快。你對手掌位置的即刻察覺能力證明,神經電訊號到達大腦的速度極快,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唯有「即時」資訊才派得上用場。事實上,那些脈衝訊號每小時前進400公里。
這是神經對必要內容的傳送速度。但怎麼樣才算得上「必要」?幸好,你不必針對大腦接收到的所有感覺、肌肉、壓力、疼痛和其他訊號,就其相對重要性排優先順位。這件事甚至在你離開子宮之前便已經安排、設計、透過基因內建好了。朋友興高采烈但粗心大意的手勢就要戳到你的眼睛?你馬上一邊眨眼、一邊閃避。吃東西時叉子最好別刺到自己?你的手指和嘴唇傳來的位置訊號當下就整合起來。某次露營過夜之旅,你赤腳走出帳篷,踩到一個可疑的物體,感覺起來是一坨像蛇一樣的可怕東西,你在剎那間猛力把腿拉起來。這些反射動作都是神經以每小時400公里的速度在下命令。
但現在用你的腳趾踢東西,請記住是什麼時候踢到。要過幾秒鐘才會感覺到痛。那是因為疼痛訊號的行進是沿著不同的線路,以每小時只有4.8公里或每秒0.6公尺的低順位速度。傳遞壞消息不用急。
那思考呢?這類訊號以介於兩者之間的速度出現,既不是最快、也不是最慢。這些訊號以每小時112公里滑行、分進,通過大腦皮質層。這個過程的速度夠快,所以你可以在另一套電路系統——你的本我、你的自我感知——獲知之前做完決定。2006年,晚近的研究者、美國神經生理學家利貝特(Benjamin Libet)及其研究團隊要求志願受試者,在他們想好要舉起哪隻手臂的當下按下按鈕,然後立刻抬起正確的那隻手臂。驚人的事情來了。盯著實驗對象腦波的研究人員在志願受試者弄清楚自己的選擇之前十秒,就能有把握地分辨出受試者做了哪一種決定!
換句話說,大腦的電性活動會自動進行,像胰臟或肝臟一樣。大腦自主做出決定,我們要稍晚一點才明白決定了什麼。
我們可能對選擇這件事有一種主觀的認知。我們可能會說:「我決定今晚要吃中國菜,不吃義大利菜。」但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發揮自由意志,大腦藉由自發的電性連結自行做了決定。要如何把這個活動控制得比對自己腎臟運作的掌控更好,我們沒人有一丁點的概念(好,如果你對此不以為然,聲稱能夠自己做選擇且這些決定並非自動產生,那麼你應該要知道,你這個想法本身甚至在你起心動念去想、去說之前,就已經自行形成)。
這些或快、或慢、不快不慢的電脈衝和突觸連結,全都連續不斷地發生,而且早上的步調最快。只有在燈光熄滅時才得以休息:當我們睡著時,大腦運轉程度降低很多。
二十二歲至二十七歲之間達到高峰後就開始萎縮的神經系統活動,當然是體內其他無數運動的控制系統。而我們感知最明確的,當然是呼吸和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