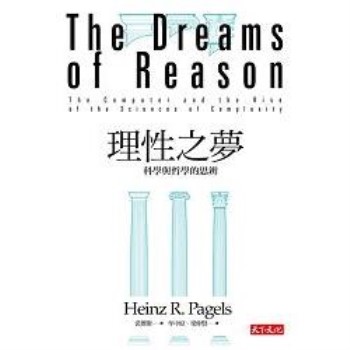在本書中,我探討科學的領域和人類理性的極限。科學提供對真實世界的理性觀點,這觀點將宇宙視為有秩序,無論活的或死的,都看成按規則運行的物質世界。這是極有力的觀點,嚴謹且簡潔,但卻對人類最關心的問題出奇沉默。
科學能讓我們知其然,卻無法知其所以然。
政治、法律、藝術和宗教,則提供對真實世界的其他觀點,從第一人稱立場出發,根據的是實用或美學的理性原則。正如幾世紀以前義大利哲學家維科所指出的,這個真實世界(文明與文化的世界)才是我們真正能掌握的,因為這個世界是我們而非上帝所創造的。
創造的瞬間、失望的深淵
也有完全非理性的觀點,無關規則、無關判斷,但往往能在瞬間撕破日常生活的外衣,而讓我們看到真實感情的部分。理性好像是蛋的脆殼,常在危機時破裂,讓我們看到裡面軟弱的部分。這些危機可以是創造的時刻,也可能是失望的深淵—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周遭的世界改變,我們的想法和價值觀也隨之起了變化。
偉大的量子物理學家鮑立(Wolfgang Pauli)是極端的理性主義者,他病重臨終前,便遭逢這樣的危機。荷蘭宗教史學家奎斯培(Gilles Quispel)曾告訴我以下的故事。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有一次派奎斯培遠赴埃及, 買一本「靈知主義」(Gnosticism)的古典經文(後來就叫榮格抄本)。多年後,奎斯培應榮格之邀,做了一系列有關靈知主義的演講。鮑立那時正和榮格合作,寫一篇談「共時性」的論文(探討恰巧同時發生且意義上相關的事件),就來聽演講並參加餐會。奎斯培坐在鮑立旁邊,談話內容十分引人入勝。突然鮑立改變話題,激動問道:「你相信有人類性格的神嗎?」奎斯培嚇了一跳,閃過了這個話題。後來他才知道鮑立瀕臨死亡,正尋找他生命更深一層的意義,此過程使他重新確認他的猶太祖先和傳統。
在那一場關於靈知主義的演講之後,鮑立走向奎斯培,言辭沉重說道:「這神—靈知主義的神,我可以接受。我永遠無法接受有人類性格的神,不可能有這種能忍受人類痛苦的神。」幾個月後,他過世了,他已見到了信仰的神:耶路撒冷的神,而非希臘的理性之神。
1960 年代末,我在亞洲旅行,途中在印度加爾各答的統計研究所演講。我在巿內停留數天,獨自閒逛人滿為患的街道。加爾各答是個赤貧的城巿,街上漂泊著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的人。我雖然看到貧窮,卻也同時看到井然有序且快活的生活,共存於不可言喻的痛苦中,那是個日常生活和宗教不可分的世界。這場景也讓我憤怒,因為我認為社會改革、教育及行政措施,可以減少許多如此悲慘的景況。
有一天,我獨自走過貧民區一條人跡罕至的巷子。路上有一大堆垃圾,我正要通過時,注意到垃圾中有些動靜,像是隻好大的狗,但我知道那區域不可能有狗。不管是什麼,他突然進入我眼前。他像個大蜘蛛般移動,有個人頭但沒有四肢,他朝我古怪的笑。我嚇了一大跳,急忙向後跑。當我後退時,聽到身後有人聲,一種無法描述的美妙歌聲唱著讚頌大自在天(Shiva,印度神話中象徵破壞的神)的歌,歌頌生存之美。如電擊般,我轉身看到那蜘蛛人唱著,從那極度悲慘的軀體發出超凡的歌聲。那時,我恍然大悟,剛剛拒絕以人道對待那個人,是我得到的教訓。我感到羞恥,發誓以後不能忘記以人道待人,我和那蜘蛛人是有連繫的。
情感危機之後的新價值觀
當為生存而奮鬥,當智識的成分之外還有情緒的成分時,學習會最有效率。情緒不一定是負面的,柏拉圖認為真正的教育必含有情慾的成分。我們的感情生活不受理性拘束(雖然也可以用理性來檢視它),在感情最濃密之處,我們知道沒有規則可以遵循,引導我們安抵彼岸。這是創造的機會,我們常會在情感危機之後,學到新的規則和價值觀。
危機可能來自混亂及不確定,此時總是有危險,不知不覺中陷入智識、政治、科學或宗教上的基本教義派。其特徵是能找到絕對的堅信(堅信階級鬥爭、科學的絕對或聖經的絕對),像是一個找到堅石為立足點的人。但它實在是人類智識上的末期病狀:一切發展已停止,成長所需的不確定和風險都已消除。我們需要分辨這種基本教義派想法,和有道德理念之人的真實信念。前者是把個人內在的信仰投射到外在世界,而以為同樣理所當然,則世界(而非個人)變成是確定的。而信念的本質是把個人信仰當成純粹的內部事物,個人的主觀部分並不一定屬客觀世界。所以,我們的信念可以是很堅強,但它會演變和成長。因為它並不是視為磐石般的外在實體,而是個人創造性的一部分。人類感情既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包括創造、實現或毀滅的潛力如此雄厚,那麼脆弱的理性又怎能規範我們的生活?尤其當面對互相衝突的價值觀時,光靠理性是不夠的,那些價值觀往往取決於我們的國籍、文化、種族、年齡和性別。
進一步而言,極力想了解自然和心靈的複雜科學,能提供我們什麼洞識呢?信仰的巨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雖理性推動他的運動,但他曾說「去他的理性」。阿奎奈(Thomas Aquinas)把理性看成是人內在神性的表現,但他知道信仰是「底線」。高耶親眼目睹啟蒙時代的理性之夢,轉變成猙獰的拿破崙戰爭。
理性的殿堂
追究起來,理性的殿堂是否只不過是為那無意識的、原始的感覺服務呢?還是它是領航員?簡言之,第三人稱的觀點如何能啟發第一人稱的存在熱情?
首要的重點,是科學發現提供了我們對宇宙物質世界的了解。至少,我們的信念和哲學觀要與它不衝突,雖然不一定要植基於它。若你採的信念直接與科學事實矛盾,你就冒了很大的險。長遠而言,採這種信念無助於個人或群體的生存。
雖然根深柢固的信念不能和科學矛盾,但它也不能只奠基於科學,尤其以宗教信仰為然。天主教長久以來曾以托勒密的地心宇宙觀為其信仰支柱。當哥白尼推翻該宇宙觀,教會便感到它的信念受到威脅。衝突的發生,肇因於科學發現總是暫時的,而信仰卻追求永恆。如果信仰植基於科學,當科學對實體的想法改變時,它會顛覆信仰。
今天,西方有些人著迷於東方宗教,他們說現代量子論和東方宗教比較吻合。這樣把物理和宗教之間做聯繫是非常膚淺的,完全不能與科學理念或宗教洞識的深度相提並論。東方宗教信徒聲稱冥思狀態和量子場有關,這種說法往好處想是一個錯誤,往壞處想可就是欺詐。想要把自然科學,直接和主觀的心靈狀態聯繫是相當可笑的。從錯誤事實中,不可能產生正確的道德理念。新的複雜科學讓我們知道,如何從簡單規則中產生複雜結果,我們描述的許多電腦模型便是基於這種想法。我們的一些道德行為看來十分複雜,但它們可能源自可以了解的簡單元素。科學無法做價值判斷,但它卻能幫助我們了解。
我不知道有沒有行為合乎倫理的電腦模型存在,但有許多經濟行為的電腦模型,詳究起來頗能發人深省。一個特性是它們往往與直覺相反。我記得有些經濟學家朋友曾問我一些問題,如做某件事是否會導致利率上升。雖然我竭盡所能推測,但是答對和答錯的機率幾乎各半。因為我忽視某些因素,正確答案就往往與直覺相反。
科學能讓我們知其然,卻無法知其所以然。
政治、法律、藝術和宗教,則提供對真實世界的其他觀點,從第一人稱立場出發,根據的是實用或美學的理性原則。正如幾世紀以前義大利哲學家維科所指出的,這個真實世界(文明與文化的世界)才是我們真正能掌握的,因為這個世界是我們而非上帝所創造的。
創造的瞬間、失望的深淵
也有完全非理性的觀點,無關規則、無關判斷,但往往能在瞬間撕破日常生活的外衣,而讓我們看到真實感情的部分。理性好像是蛋的脆殼,常在危機時破裂,讓我們看到裡面軟弱的部分。這些危機可以是創造的時刻,也可能是失望的深淵—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周遭的世界改變,我們的想法和價值觀也隨之起了變化。
偉大的量子物理學家鮑立(Wolfgang Pauli)是極端的理性主義者,他病重臨終前,便遭逢這樣的危機。荷蘭宗教史學家奎斯培(Gilles Quispel)曾告訴我以下的故事。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有一次派奎斯培遠赴埃及, 買一本「靈知主義」(Gnosticism)的古典經文(後來就叫榮格抄本)。多年後,奎斯培應榮格之邀,做了一系列有關靈知主義的演講。鮑立那時正和榮格合作,寫一篇談「共時性」的論文(探討恰巧同時發生且意義上相關的事件),就來聽演講並參加餐會。奎斯培坐在鮑立旁邊,談話內容十分引人入勝。突然鮑立改變話題,激動問道:「你相信有人類性格的神嗎?」奎斯培嚇了一跳,閃過了這個話題。後來他才知道鮑立瀕臨死亡,正尋找他生命更深一層的意義,此過程使他重新確認他的猶太祖先和傳統。
在那一場關於靈知主義的演講之後,鮑立走向奎斯培,言辭沉重說道:「這神—靈知主義的神,我可以接受。我永遠無法接受有人類性格的神,不可能有這種能忍受人類痛苦的神。」幾個月後,他過世了,他已見到了信仰的神:耶路撒冷的神,而非希臘的理性之神。
1960 年代末,我在亞洲旅行,途中在印度加爾各答的統計研究所演講。我在巿內停留數天,獨自閒逛人滿為患的街道。加爾各答是個赤貧的城巿,街上漂泊著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的人。我雖然看到貧窮,卻也同時看到井然有序且快活的生活,共存於不可言喻的痛苦中,那是個日常生活和宗教不可分的世界。這場景也讓我憤怒,因為我認為社會改革、教育及行政措施,可以減少許多如此悲慘的景況。
有一天,我獨自走過貧民區一條人跡罕至的巷子。路上有一大堆垃圾,我正要通過時,注意到垃圾中有些動靜,像是隻好大的狗,但我知道那區域不可能有狗。不管是什麼,他突然進入我眼前。他像個大蜘蛛般移動,有個人頭但沒有四肢,他朝我古怪的笑。我嚇了一大跳,急忙向後跑。當我後退時,聽到身後有人聲,一種無法描述的美妙歌聲唱著讚頌大自在天(Shiva,印度神話中象徵破壞的神)的歌,歌頌生存之美。如電擊般,我轉身看到那蜘蛛人唱著,從那極度悲慘的軀體發出超凡的歌聲。那時,我恍然大悟,剛剛拒絕以人道對待那個人,是我得到的教訓。我感到羞恥,發誓以後不能忘記以人道待人,我和那蜘蛛人是有連繫的。
情感危機之後的新價值觀
當為生存而奮鬥,當智識的成分之外還有情緒的成分時,學習會最有效率。情緒不一定是負面的,柏拉圖認為真正的教育必含有情慾的成分。我們的感情生活不受理性拘束(雖然也可以用理性來檢視它),在感情最濃密之處,我們知道沒有規則可以遵循,引導我們安抵彼岸。這是創造的機會,我們常會在情感危機之後,學到新的規則和價值觀。
危機可能來自混亂及不確定,此時總是有危險,不知不覺中陷入智識、政治、科學或宗教上的基本教義派。其特徵是能找到絕對的堅信(堅信階級鬥爭、科學的絕對或聖經的絕對),像是一個找到堅石為立足點的人。但它實在是人類智識上的末期病狀:一切發展已停止,成長所需的不確定和風險都已消除。我們需要分辨這種基本教義派想法,和有道德理念之人的真實信念。前者是把個人內在的信仰投射到外在世界,而以為同樣理所當然,則世界(而非個人)變成是確定的。而信念的本質是把個人信仰當成純粹的內部事物,個人的主觀部分並不一定屬客觀世界。所以,我們的信念可以是很堅強,但它會演變和成長。因為它並不是視為磐石般的外在實體,而是個人創造性的一部分。人類感情既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包括創造、實現或毀滅的潛力如此雄厚,那麼脆弱的理性又怎能規範我們的生活?尤其當面對互相衝突的價值觀時,光靠理性是不夠的,那些價值觀往往取決於我們的國籍、文化、種族、年齡和性別。
進一步而言,極力想了解自然和心靈的複雜科學,能提供我們什麼洞識呢?信仰的巨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雖理性推動他的運動,但他曾說「去他的理性」。阿奎奈(Thomas Aquinas)把理性看成是人內在神性的表現,但他知道信仰是「底線」。高耶親眼目睹啟蒙時代的理性之夢,轉變成猙獰的拿破崙戰爭。
理性的殿堂
追究起來,理性的殿堂是否只不過是為那無意識的、原始的感覺服務呢?還是它是領航員?簡言之,第三人稱的觀點如何能啟發第一人稱的存在熱情?
首要的重點,是科學發現提供了我們對宇宙物質世界的了解。至少,我們的信念和哲學觀要與它不衝突,雖然不一定要植基於它。若你採的信念直接與科學事實矛盾,你就冒了很大的險。長遠而言,採這種信念無助於個人或群體的生存。
雖然根深柢固的信念不能和科學矛盾,但它也不能只奠基於科學,尤其以宗教信仰為然。天主教長久以來曾以托勒密的地心宇宙觀為其信仰支柱。當哥白尼推翻該宇宙觀,教會便感到它的信念受到威脅。衝突的發生,肇因於科學發現總是暫時的,而信仰卻追求永恆。如果信仰植基於科學,當科學對實體的想法改變時,它會顛覆信仰。
今天,西方有些人著迷於東方宗教,他們說現代量子論和東方宗教比較吻合。這樣把物理和宗教之間做聯繫是非常膚淺的,完全不能與科學理念或宗教洞識的深度相提並論。東方宗教信徒聲稱冥思狀態和量子場有關,這種說法往好處想是一個錯誤,往壞處想可就是欺詐。想要把自然科學,直接和主觀的心靈狀態聯繫是相當可笑的。從錯誤事實中,不可能產生正確的道德理念。新的複雜科學讓我們知道,如何從簡單規則中產生複雜結果,我們描述的許多電腦模型便是基於這種想法。我們的一些道德行為看來十分複雜,但它們可能源自可以了解的簡單元素。科學無法做價值判斷,但它卻能幫助我們了解。
我不知道有沒有行為合乎倫理的電腦模型存在,但有許多經濟行為的電腦模型,詳究起來頗能發人深省。一個特性是它們往往與直覺相反。我記得有些經濟學家朋友曾問我一些問題,如做某件事是否會導致利率上升。雖然我竭盡所能推測,但是答對和答錯的機率幾乎各半。因為我忽視某些因素,正確答案就往往與直覺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