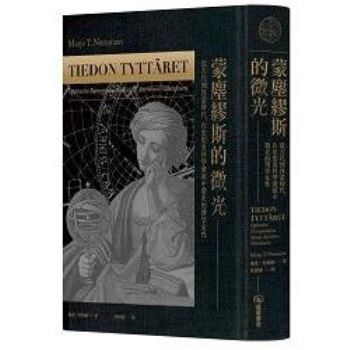緒論
在科學領域上的考古、權力遊戲及性別角色
二○○七年夏天,在一份日報上有篇短文,是有關某個死於三千五百年前之女性,引起我的注意。古埃及唯一的女法老王哈特謝普蘇特,有好幾天成為世界各地報紙專欄的焦點。根據她的DNA和牙齒,在開羅考古博物館內的木乃伊之中,有一尊被鑑定出就是這位博學的女統治者。在寫本書的過程中,她的故事具有偉大的象徵意義:死了很久且遭忘卻的女性,從遺忘中浮現。
在《蒙塵繆斯的微光》一書中,我介紹從古代,經啟蒙運動,到十九世紀初期的博學女性。透過她們,檢視最早女性的學習傳統,以及在歐洲科學史中女性所扮演的各種角色。我聚焦於現代科學出現之前,也就是早於居里夫人(一八六七~一九三四)很久的時期,當時自然科學依舊與哲學緊密聯繫在一起,而且還被稱做「自然哲學」。在哲學和科學中佔主導地位的,正是那些富裕又有閒的人。社會地位和性別,決定了一個人是否被視為有能力運用他的智力,以及是否有資格出現在學術論壇上──譬如創立於中世紀的大學和後來創立於十七世紀的科學學會。
直到最近數十年為止,在學習的舞台上,男性一向扮演著關鍵角色。在古代,自然哲學被歸屬自由人的領域;然而在中世紀,乃屬於學者和教士;至於現代,則屬於紳士。除了繆斯的角色以外,還有什麼可讓女性利用的嗎?首先,為什麼我們應該對博學婦女、科學的考古、古代科學三者的歷史感到興趣?女性「最後」成功地在傳統上由男人佔盡優勢的領域中為她們自己清掃出空間,而且今天她們也積極參與了我們從科學來理解現實世界的過程。可是,這樣就足夠了嗎?
針對長期慢慢改變的文化結構──諸如科學、權力、性別的合流──進行研究,是很重要的,因為它能夠幫助我們了解,為何連結於這個三位一體(科學、權力、性別)的文化概念及實踐難以被辨認和改變。它們的根,在時間上,可以回溯至數千年以前,而且至今仍以某些形式在西方文化中繼續發揮其影響力。它們已深深嵌入我們的日常思考和社會結構裏,同時因為它們是如此地不證自明,所以已經變得幾乎視而不見了。研究舊世代博學婦女的生活與工作,對於今日的科學姐妹們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她們呼籲女性之間相互對話。根據哲學家薩拉‧海伊納瑪的說法,「為了讓一個知性的傳統出現,寫作及做研究的女性必須連接彼此的思想和言辭。女性光讀她們當代的教科書是不夠的,她們必須──在她們的思想和寫作中──從那些不再出現的女性所做的工作中取得一個立場。最重要的是,她們必須能夠辨認她們的前任者,也就是那些如今已不存在,卻留下她們的著述給後人的女性。」[4]當我們決定了在過去什麼是重要和值得研究的事物之後,我們同時也獲得機會去思索我們這個時代的價值。由歷史學家照在過去的聚光燈,對著兩個方向:在探查過去時,我們也把光線灑在我們目前的地方。過去有可能引導出另一種的未來。開發一種歷史的隨機感,有助於了解過去的動態本質、與其相關的各種力量,以及各種人類的欲望和心願──這些經常互不相容。雖說歷史總是從勝利者的角度撰寫,但失敗者也參與了這些事件,而且對它們產生影響。在研究科學史和思想史中,辨認出勝利者和失敗者,其實不難。
過去,與其說它不是一座讓歷史學家可以從它雕刻出歷史「真相」的冰山,倒不如說它是一個開啟了縱橫交錯的小徑、地層、坳坑、死巷等無盡排列的巨大洞穴。歷史學家每一次都只能從這個巨大的實體中,選擇窄窄的一片而已。這聚光燈所照射的過去,都是選擇性的。然而一個新的翻轉,經常出現在目前的這一小片上,而且還會無止境地繼續下去。我們必須甘心於解釋零零落落的軌跡,甘心於跟隨差勁的,甚至彼此衝突的一些引導。
不過,解讀往往傾向凝聚出「真相」,如果它們以足夠的頻率重複出現的話。像這種根據事實而來的歷史「真相」,會形成一種歷史的學說、規則、指導路線,進而引領歷史的研究。依照思想史和學術的傳統學說,在歐洲科學史方面,女性還不卓越,因此,研究她們是無意義的。雖然在研究方面並未明講,但是從歷史書籍的索引來看就很明顯──沒有引用婦女的著作。可是,當西方科學的基礎奠定於古希臘時,當謄寫和研究古書開始於修道院和中世紀的大學之時,當自然哲學在文藝復興時期移入王侯宮廷以及在十七世紀移入科學學會及貴族沙龍的時候,難道都沒有女性參與過嗎?固然「正式的」學術位子,譬如大學與科學學會,把女性排除在外,但是她們有許多人仍然成功地獲得教育,也成功地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參與了科學的追求。
超過三千五百年的一段時間,我所研究的女性在許多學術領域工作──哲學、神學、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學、自然史、醫學──她們以獨立的科學家、不可替代的助手,以及男性家族成員(父親、兄弟、丈夫)的同事,發揮自身的影響力。她們計畫、金援、指揮科學探險。她們出版和翻譯科學書籍,並充當科學的傑出贊助人。她們經常是科學的推廣人和科學性文學的讀者。如果我們想要聽歷史的複音,那我們就必須傾聽這些婦女的故事。根據仍普遍存在於通俗科學史裏的舊學說而寫出來的歷史當中,依然強調科學的線性發展。那些儘管遇到障礙和挫折,仍朝向知識和真相奮鬥,因而被提升至天才地位的男主角們──個人科學家──被置於這些故事的中心。不過,當解構此種印象之後,卻可看出,從來就沒有一個人能夠獨自,亦即在完全與他人隔離的情況下,從事發明或工作。科學在與他人對話中發展,並且在不同的方向、討論上,與先前的研究、學者、捐助者、大眾形成互動。這些團體經常存在著。少數博學之人在當時便已出名。就像在生活的其他領域一樣,某些人要到下一個世代才會被提升到主角地位,其他人則被忘掉。即使科學也並非直線前進,相反地,新的理念和創新往往經由衝突而產生,因為既存的概念和理念受到挑戰之故。新科學並未遵從佔主導地位的真理,反而向它挑戰。因此,很明顯地,科學史與其說是以連續敘事的方式,無寧說是以欲望、心願、權力關係、理念、創新等不斷縱橫交錯、相互碰撞的方式流動著。在表面的統一之下,存在著一個幾乎令人窒息的多樣性。
一九六○年代,美國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孔恩(一九二二~一九九六)在他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科學史的既定敘述提出質疑。他最先使用「概念模式」來描寫科學裏的成規,這些成規決定了研究的主題、如何指導研究工作、如何制定科學問題、如何解讀研究發現、誰有資格介紹它們。他質疑科學的線型發展,而且他提出模式轉變或革命──透過它們,進步才得以達成──的概念,以取代連續性。在後來的著作中,他也強調,科學進步的偉大故事,只能根據事實重新建構。
根據大約從公元前三百年起到十七世紀為止,一直佔上風的亞里斯多德學派之科學理想的說法,世上所有不可或缺的知識,在古代期間都已經被發現了。在中世紀,學者的任務僅僅在於陳述某個現象乃符合傳承下來的智慧,並且組織它,同時相互比較亞里斯多德的各種解釋罷了。對亞里斯多德學派的科學理想發生懷疑,最早發生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然而新的科學模式決不會立刻完全取代既存的概念和實踐。科學革命變成了「進化」,亦即一個緩慢的過程,在其中仍有些理念被保存和發展,而其他的逐漸衰亡。這整個革命性概念,是歷史的;在不同的背景下,它改變和承擔不同的意義。現代科學概念的出現延續了至少三百年,所以舊的和新的觀念、概念、技術、工藝,並存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如果爭論說,從古代到十七世紀,煉金師和占星師用來解釋、感知宇宙及其力量的方法是不科學的話,事實上,這件事本身就是時代錯誤和違反歷史的。按照我們目前的科學概念,他們的方法無疑是不科學的;煉金師和占星師既沒有想過,也沒根據現代的科學概念來做。普遍存在的科學模式──孔恩稱它為一般科學──不但解釋了這個世界,而且維持了主流的解釋。固然新的知性、概念性、技術性的工具,可以逐漸駁倒這個對於世界的舊解釋,並且創造出一個新的,可是,舊的和新的模式並不相稱。對活在數百年前的科學家而言,立足於當前知識的西方科學和我們的生活方式,或許很簡陋。當我們想了解過去的人如何感受他們自己的世界時,即使我們無法完全融入他們的時代,但我們必須試著站在他們自己的規則基礎上進行評估。
當我們認識,並且承認,我們的性別概念是歷史的產物,而且性別的社會尺度和永久的分類一樣,都是不自然之時,我們將成功地從束縛著以往歷史學的兩件緊身衣中解放出來。只不過數十年前,「婦女史」和「性別史」仍處於混亂中,事實上,在一般歷史的研究中,尚不為人知。近年來,這種情況發生了幸運又戲劇性的轉變。
婦女史的主要目標,通常在於提昇與婦女的經驗及領域相關的實況,這一點還未被早期的歷史著作注意到。與此同時,還有種願望想讓人們看見,並質疑基於性別之規範、價值以及內建於文化中的等級制度。此外,還有人提出說,透過婦女史,婦女實際上被人以一種新的方式將她們邊緣化。女性學者和她們的研究被巧妙地貶至她們自己的領域中,而且她們無法跳脫這個領域而去破壞其他的研究。
女性史學家特別指責早期的歷史著作,因為它們完全排除了婦女和許多社會邊緣群體,譬如小孩、年長者、窮人等。有些歷史學家在他們的研究中,就只把女性描寫成男性──父權運作下的──的犧牲者,這樣的誇大令他們自己也感到汗顏。固然女性曾經是這種權力運作下的犧牲者,但是社會地位及財富,也會影響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社會地位低的男性,也會成為社會階級高的女性在其權力運用下的馬前卒。
目前的性別史強調,「兩」性的區分源自主流的文化概念、社會價值、習慣。越多強勢的階級將權威施加在弱者身上,這樣的關係比它第一眼所呈現出來的就越為複雜。依賴所屬性別而享受到的權威,是從涉及到的所有人員的互動中產生並被維持的。它們並非永恆的,必須經過不斷再協商,而這個協商的過程,則決定了佔主導的現實及真相之界線何在。這條界線,同時畫在心靈的假想現實與在四周環境中的物理現實之上。然而革命不就是將舊界線抹去,再劃定新界線而已。不論社會或科學革命,都是這樣。
在科學領域上的考古、權力遊戲及性別角色
二○○七年夏天,在一份日報上有篇短文,是有關某個死於三千五百年前之女性,引起我的注意。古埃及唯一的女法老王哈特謝普蘇特,有好幾天成為世界各地報紙專欄的焦點。根據她的DNA和牙齒,在開羅考古博物館內的木乃伊之中,有一尊被鑑定出就是這位博學的女統治者。在寫本書的過程中,她的故事具有偉大的象徵意義:死了很久且遭忘卻的女性,從遺忘中浮現。
在《蒙塵繆斯的微光》一書中,我介紹從古代,經啟蒙運動,到十九世紀初期的博學女性。透過她們,檢視最早女性的學習傳統,以及在歐洲科學史中女性所扮演的各種角色。我聚焦於現代科學出現之前,也就是早於居里夫人(一八六七~一九三四)很久的時期,當時自然科學依舊與哲學緊密聯繫在一起,而且還被稱做「自然哲學」。在哲學和科學中佔主導地位的,正是那些富裕又有閒的人。社會地位和性別,決定了一個人是否被視為有能力運用他的智力,以及是否有資格出現在學術論壇上──譬如創立於中世紀的大學和後來創立於十七世紀的科學學會。
直到最近數十年為止,在學習的舞台上,男性一向扮演著關鍵角色。在古代,自然哲學被歸屬自由人的領域;然而在中世紀,乃屬於學者和教士;至於現代,則屬於紳士。除了繆斯的角色以外,還有什麼可讓女性利用的嗎?首先,為什麼我們應該對博學婦女、科學的考古、古代科學三者的歷史感到興趣?女性「最後」成功地在傳統上由男人佔盡優勢的領域中為她們自己清掃出空間,而且今天她們也積極參與了我們從科學來理解現實世界的過程。可是,這樣就足夠了嗎?
針對長期慢慢改變的文化結構──諸如科學、權力、性別的合流──進行研究,是很重要的,因為它能夠幫助我們了解,為何連結於這個三位一體(科學、權力、性別)的文化概念及實踐難以被辨認和改變。它們的根,在時間上,可以回溯至數千年以前,而且至今仍以某些形式在西方文化中繼續發揮其影響力。它們已深深嵌入我們的日常思考和社會結構裏,同時因為它們是如此地不證自明,所以已經變得幾乎視而不見了。研究舊世代博學婦女的生活與工作,對於今日的科學姐妹們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她們呼籲女性之間相互對話。根據哲學家薩拉‧海伊納瑪的說法,「為了讓一個知性的傳統出現,寫作及做研究的女性必須連接彼此的思想和言辭。女性光讀她們當代的教科書是不夠的,她們必須──在她們的思想和寫作中──從那些不再出現的女性所做的工作中取得一個立場。最重要的是,她們必須能夠辨認她們的前任者,也就是那些如今已不存在,卻留下她們的著述給後人的女性。」[4]當我們決定了在過去什麼是重要和值得研究的事物之後,我們同時也獲得機會去思索我們這個時代的價值。由歷史學家照在過去的聚光燈,對著兩個方向:在探查過去時,我們也把光線灑在我們目前的地方。過去有可能引導出另一種的未來。開發一種歷史的隨機感,有助於了解過去的動態本質、與其相關的各種力量,以及各種人類的欲望和心願──這些經常互不相容。雖說歷史總是從勝利者的角度撰寫,但失敗者也參與了這些事件,而且對它們產生影響。在研究科學史和思想史中,辨認出勝利者和失敗者,其實不難。
過去,與其說它不是一座讓歷史學家可以從它雕刻出歷史「真相」的冰山,倒不如說它是一個開啟了縱橫交錯的小徑、地層、坳坑、死巷等無盡排列的巨大洞穴。歷史學家每一次都只能從這個巨大的實體中,選擇窄窄的一片而已。這聚光燈所照射的過去,都是選擇性的。然而一個新的翻轉,經常出現在目前的這一小片上,而且還會無止境地繼續下去。我們必須甘心於解釋零零落落的軌跡,甘心於跟隨差勁的,甚至彼此衝突的一些引導。
不過,解讀往往傾向凝聚出「真相」,如果它們以足夠的頻率重複出現的話。像這種根據事實而來的歷史「真相」,會形成一種歷史的學說、規則、指導路線,進而引領歷史的研究。依照思想史和學術的傳統學說,在歐洲科學史方面,女性還不卓越,因此,研究她們是無意義的。雖然在研究方面並未明講,但是從歷史書籍的索引來看就很明顯──沒有引用婦女的著作。可是,當西方科學的基礎奠定於古希臘時,當謄寫和研究古書開始於修道院和中世紀的大學之時,當自然哲學在文藝復興時期移入王侯宮廷以及在十七世紀移入科學學會及貴族沙龍的時候,難道都沒有女性參與過嗎?固然「正式的」學術位子,譬如大學與科學學會,把女性排除在外,但是她們有許多人仍然成功地獲得教育,也成功地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參與了科學的追求。
超過三千五百年的一段時間,我所研究的女性在許多學術領域工作──哲學、神學、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學、自然史、醫學──她們以獨立的科學家、不可替代的助手,以及男性家族成員(父親、兄弟、丈夫)的同事,發揮自身的影響力。她們計畫、金援、指揮科學探險。她們出版和翻譯科學書籍,並充當科學的傑出贊助人。她們經常是科學的推廣人和科學性文學的讀者。如果我們想要聽歷史的複音,那我們就必須傾聽這些婦女的故事。根據仍普遍存在於通俗科學史裏的舊學說而寫出來的歷史當中,依然強調科學的線性發展。那些儘管遇到障礙和挫折,仍朝向知識和真相奮鬥,因而被提升至天才地位的男主角們──個人科學家──被置於這些故事的中心。不過,當解構此種印象之後,卻可看出,從來就沒有一個人能夠獨自,亦即在完全與他人隔離的情況下,從事發明或工作。科學在與他人對話中發展,並且在不同的方向、討論上,與先前的研究、學者、捐助者、大眾形成互動。這些團體經常存在著。少數博學之人在當時便已出名。就像在生活的其他領域一樣,某些人要到下一個世代才會被提升到主角地位,其他人則被忘掉。即使科學也並非直線前進,相反地,新的理念和創新往往經由衝突而產生,因為既存的概念和理念受到挑戰之故。新科學並未遵從佔主導地位的真理,反而向它挑戰。因此,很明顯地,科學史與其說是以連續敘事的方式,無寧說是以欲望、心願、權力關係、理念、創新等不斷縱橫交錯、相互碰撞的方式流動著。在表面的統一之下,存在著一個幾乎令人窒息的多樣性。
一九六○年代,美國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孔恩(一九二二~一九九六)在他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科學史的既定敘述提出質疑。他最先使用「概念模式」來描寫科學裏的成規,這些成規決定了研究的主題、如何指導研究工作、如何制定科學問題、如何解讀研究發現、誰有資格介紹它們。他質疑科學的線型發展,而且他提出模式轉變或革命──透過它們,進步才得以達成──的概念,以取代連續性。在後來的著作中,他也強調,科學進步的偉大故事,只能根據事實重新建構。
根據大約從公元前三百年起到十七世紀為止,一直佔上風的亞里斯多德學派之科學理想的說法,世上所有不可或缺的知識,在古代期間都已經被發現了。在中世紀,學者的任務僅僅在於陳述某個現象乃符合傳承下來的智慧,並且組織它,同時相互比較亞里斯多德的各種解釋罷了。對亞里斯多德學派的科學理想發生懷疑,最早發生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然而新的科學模式決不會立刻完全取代既存的概念和實踐。科學革命變成了「進化」,亦即一個緩慢的過程,在其中仍有些理念被保存和發展,而其他的逐漸衰亡。這整個革命性概念,是歷史的;在不同的背景下,它改變和承擔不同的意義。現代科學概念的出現延續了至少三百年,所以舊的和新的觀念、概念、技術、工藝,並存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如果爭論說,從古代到十七世紀,煉金師和占星師用來解釋、感知宇宙及其力量的方法是不科學的話,事實上,這件事本身就是時代錯誤和違反歷史的。按照我們目前的科學概念,他們的方法無疑是不科學的;煉金師和占星師既沒有想過,也沒根據現代的科學概念來做。普遍存在的科學模式──孔恩稱它為一般科學──不但解釋了這個世界,而且維持了主流的解釋。固然新的知性、概念性、技術性的工具,可以逐漸駁倒這個對於世界的舊解釋,並且創造出一個新的,可是,舊的和新的模式並不相稱。對活在數百年前的科學家而言,立足於當前知識的西方科學和我們的生活方式,或許很簡陋。當我們想了解過去的人如何感受他們自己的世界時,即使我們無法完全融入他們的時代,但我們必須試著站在他們自己的規則基礎上進行評估。
當我們認識,並且承認,我們的性別概念是歷史的產物,而且性別的社會尺度和永久的分類一樣,都是不自然之時,我們將成功地從束縛著以往歷史學的兩件緊身衣中解放出來。只不過數十年前,「婦女史」和「性別史」仍處於混亂中,事實上,在一般歷史的研究中,尚不為人知。近年來,這種情況發生了幸運又戲劇性的轉變。
婦女史的主要目標,通常在於提昇與婦女的經驗及領域相關的實況,這一點還未被早期的歷史著作注意到。與此同時,還有種願望想讓人們看見,並質疑基於性別之規範、價值以及內建於文化中的等級制度。此外,還有人提出說,透過婦女史,婦女實際上被人以一種新的方式將她們邊緣化。女性學者和她們的研究被巧妙地貶至她們自己的領域中,而且她們無法跳脫這個領域而去破壞其他的研究。
女性史學家特別指責早期的歷史著作,因為它們完全排除了婦女和許多社會邊緣群體,譬如小孩、年長者、窮人等。有些歷史學家在他們的研究中,就只把女性描寫成男性──父權運作下的──的犧牲者,這樣的誇大令他們自己也感到汗顏。固然女性曾經是這種權力運作下的犧牲者,但是社會地位及財富,也會影響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社會地位低的男性,也會成為社會階級高的女性在其權力運用下的馬前卒。
目前的性別史強調,「兩」性的區分源自主流的文化概念、社會價值、習慣。越多強勢的階級將權威施加在弱者身上,這樣的關係比它第一眼所呈現出來的就越為複雜。依賴所屬性別而享受到的權威,是從涉及到的所有人員的互動中產生並被維持的。它們並非永恆的,必須經過不斷再協商,而這個協商的過程,則決定了佔主導的現實及真相之界線何在。這條界線,同時畫在心靈的假想現實與在四周環境中的物理現實之上。然而革命不就是將舊界線抹去,再劃定新界線而已。不論社會或科學革命,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