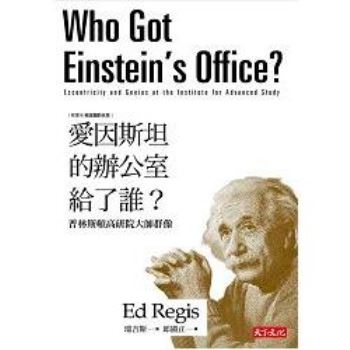「你正在寫一本有關本院的書?好,那或許你可以告訴我⋯⋯」塔布斯(Rob Tubbs)說道。塔布斯是高研院的短期訪問學者,是超越數論(transcendental number theory)領域的青年數學家。結束訪談後,他隨手把辦公室的門帶上並上鎖,與我一起步出辦公室。
「我們很多人皆對此傳聞耳熟能詳,就是愛氏辭世以後,他們就將其辦公室原封不動的保存著,一直到現在,是⋯⋯是真的嗎?」
嗯!這是個好問題。每個人第一次踏入高研院,都會很自然的做此假設。愛因斯坦就是在這兒渡過了二十幾個寒暑⋯⋯愛因斯坦,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唯一一位老少皆知,家喻戶曉的科學家,任誰都能脫口說出他的大名;這樣的人,他的辦公室難道不值得保存嗎?⋯⋯就連他的腦子都一樣,此刻正懸浮在一罐甲醛溶液中,置於密蘇里州威斯頓市哈維(Thomas Harvey)醫生的辦公室內。當然他們應該把愛氏的辦公室關閉,甚至原封不動的永久保存下來,就像一個凍結時間的膠囊,否則的話,簡直就是對他的人格、成就的一種⋯⋯褻瀆、冒犯、汙辱。畢竟,有誰夠資格在那兒工作?誰能套上他的鞋子(像灰姑娘的鞋子)?誰又敢坐在同一間辦公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假如他知道這間辦公室就是愛因斯坦以前工作的聖地?
「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究竟在哪裡呢?」塔布斯疑惑的問道。
曠世奇才
愛因斯坦未進高等研究院前,早已經是風靡全球的人物了。1919年,當天文學家證實了他的預測,光線會受太陽的重力偏折時,舉世為他如痴如狂。新生兒命名、香菸品牌都用上愛氏的名字。倫敦智慧女神(London Palladium)劇場邀請他去參與演出三週,酬勞隨便他開。兩位德國教授合作拍製了「相對論影片」在大西洋兩岸同時放映。愛氏拜訪英國生物學家霍登(J. B. S. Haldane),並於他家中過夜時,霍登的女兒才看了此人一眼,即暈死過去。新聞界更將愛氏的理論,捧為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就,而愛氏本人則為有史以來最傑出、最優秀的人。
畢竟,他真是新秩序的發言人。光有重量、空間是彎的、宇宙有四維空間。人們愛死他了,雖然對他講的東西毫無概念,可是又有什麼關係?他是這些理論的創始者,真正懂得的人,是眾人的英雄,新的彌賽亞,第一位真正的飽學之士,是廣闊無邊物理宇宙的最高元帥。愛氏備受尊崇,然而他本人卻極謙虛、和藹,不懂人家為何要大驚小怪。至少他待人很民主,一視同仁,愛氏說:「我和每個人的說話方式都一樣。不論對方是清潔工還是大學校長。」當然,如果要吹毛吹疵的話,還是可以發現一些例外⋯⋯比方有次他寄了一篇論文給《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審核,編輯竟敢退回論文要求重寫。哇!這下可好了!那位可憐的編輯只不過克盡本分,將文章送交審稿委員評閱而已,但這卻不見容於愛因斯坦,並終身視《物理評論》為拒絕往來戶。這說明了什麼呢?這位曠世物理奇才,終究自我中心:如果某項見解是高研院首席科學巨星肯定的,那就是健全而完整的點子,絕不容許別人有絲毫質疑。
在凡人眼中,愛氏可能是謙卑的天才,只是從來不穿襪子(至少還穿了鞋子)。但是在那柏拉圖的天空,可又另當別論了。這個人絕對的高傲自信,令人咋舌;他自認可以徹底了解整個宇宙的奧祕—沒有漏網之魚,大至最龐大的星系,小至最微小的夸克;他認為自己無所不通,而且可以找出一組簡單原則,即是跨越兩個極端,涵蓋大、小宇宙的統一場論(unified field theory)。他怎麼做呢?純靠推理,完全符合了柏拉圖天空的優良傳統。當那些迴旋加速器(cyclotron)工程師使勁撞擊他們的王國,天文學家架出碩大的高倍望遠鏡,朝著億萬光年外的浩瀚、冰冷星際瞭望的時候,愛因斯坦則將自己關在斗室裡,放下窗簾,然後,以他特有的口吻說:「我要想一下。」他寫下幾行潦潦草草的方程式,做做頭腦體操,仔細瞧瞧!他很快的就把一切搞定了。只靠冥想⋯⋯沒有機器,沒有儀器設備。
曾經有人問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他的實驗室設在哪裡?愛氏微微一笑,從胸前的口袋中摸出一枝鋼筆,說:「在這裡!」
三顧茅廬
1932年冬,傅列克斯納遠赴加州尋找新研究院的合適成員。名叫摩根的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建議傅氏去和愛因斯坦碰個面,愛氏正巧在那兒客座。相談之下,愛氏很喜歡高等研究院的構想,頗有相見恨晚的感慨,當時愛氏仍是柏林大學的教授,但在德國的處境每況愈下。1920年時,蹦出了一個反愛因斯坦的聯盟,自稱是「日耳曼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出錢資助任何肯出面反對「猶太物理」,特別是什麼「相對論」那檔子事的人。1920年8月24日,這個愛氏稱之為「反相對論有限公司」的組織,贊助了一場在柏林愛樂廳舉行的會議。愛氏本人也參加了那場會議,卻當場哭笑不得,因為對方的攻訐實在是荒謬絕倫。
這些亞利安物理學家煞有介事的恣意攻訐,而愛氏則人在屋簷下,忍受了他們十年的無理取鬧。1931年前夕,「反相對論公司」出版了一本書《一百位作家反愛因斯坦》(100 Authors Against Einstein)後,他就決意離開德國,永不再回來,因此對傅氏所言側耳傾聽。兩人沿著加州理工教職員俱樂部的長廊來來回回走了數趟,討論行將在普林斯頓成立的新研究中心。愛氏要求與傅氏擇期再敘,兩人便約定在1932年的春季班開始時再見面,屆時他們二人都會在英國的牛津。
5月一個美麗的週六早晨,晴空萬里,小鳥輕啼,傅氏和愛氏二人穿越基督教堂前的草坪,緩步微吟,宛如兩個體面的牛津教授。傅氏開門見山,直陳來意:「愛因斯坦教授,在下不揣冒昧,願在新研究院內提供您一個職缺,倘若閣下經過深思熟慮,覺得本院有幸能提供您珍視的機會,本院將竭誠期待您的大駕光臨。」
愛因斯坦有點心動,但一如往常,不願倉促行事。畢竟,全世界如耶路撒冷、馬德里、巴黎、萊登和牛津等地的知名大學,都爭相虛位以待,提供教授、研究員和各式各樣榮譽職位給他—只要他肯大駕光臨,能使學校蓬蓽生輝,幾乎是任何要求都行。早在1927年,他已經回絕過普林斯頓一次,不過事過境遷,或許該是拜訪新大陸的時候了。
「你今年夏天會在德國嗎?」愛氏問道。
翌月,傅氏飛抵德國卡普特(Caputh),在下午三點於寒風細雨中邁步進入愛氏的鄉居,直到深夜十一點才離去。此行他獲得了夢寐以求的答案,因為愛氏的回答是:「我心如火焰,熱切期待這一刻來臨!」就在1932年6月4日,愛因斯坦成為了高等研究院第一位教授。一夕之間,傅氏夢中的研究院,有了全新的意義和展望,就像上帝親自臨幸傅氏在普林斯頓的新家一樣。當然還有一些問題待解決:愛因斯坦的薪水、再加上愛氏同僚梅爾(Walther Mayer)的去留問題。愛氏要求年薪三千美元。他問傅氏:「數目再少些,可以應付生活所需嗎?」傅氏回答:「不行,那樣不夠!」
最後「薪事」以年薪一萬美元定案,愛氏也欣然同意;至於梅爾的聘約則延期再議。愛氏通常都避免與其他人共事—他以前常這麼說:「我是一匹只披單轡的馬」。不過事實上,他曾和奧地利數學家梅爾合寫過幾篇論文,而且兩人亦有共同的夢想,要完成統一場論。此外,愛氏考慮到,如果分派一些較為例行的計算工作給助手,自己就可專注於較為抽象而創新的推理。綜合這些原因,他肯定梅爾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傅氏原則上同意延請梅爾入院,但不是以他的名義,給他獨立的聘約,只同意他擔任愛氏的助理。梅爾畢竟並不真正符合該院人才延攬的標準;他曾出過一本有關非歐幾何方面的書,但也是他唯一的成名作,不管愛氏如何器重他,為他冠上教授頭銜,對研究院的聲望並沒有實質的幫助。可是,愛氏卻很堅持,並於1933年春寫信給傅氏說,除非院方聘請梅爾,否則全部協議一筆勾銷。愛氏寫道:「不瞞您說,我會深感遺憾,如果梅爾寶貴的合作權遭剝奪,沒有他在院中鼎力相助,甚至會妨礙了我的工作推展。」因此,傅氏終於聘請了梅爾。
摘自《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物理教宗──愛因斯坦〉
「我們很多人皆對此傳聞耳熟能詳,就是愛氏辭世以後,他們就將其辦公室原封不動的保存著,一直到現在,是⋯⋯是真的嗎?」
嗯!這是個好問題。每個人第一次踏入高研院,都會很自然的做此假設。愛因斯坦就是在這兒渡過了二十幾個寒暑⋯⋯愛因斯坦,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唯一一位老少皆知,家喻戶曉的科學家,任誰都能脫口說出他的大名;這樣的人,他的辦公室難道不值得保存嗎?⋯⋯就連他的腦子都一樣,此刻正懸浮在一罐甲醛溶液中,置於密蘇里州威斯頓市哈維(Thomas Harvey)醫生的辦公室內。當然他們應該把愛氏的辦公室關閉,甚至原封不動的永久保存下來,就像一個凍結時間的膠囊,否則的話,簡直就是對他的人格、成就的一種⋯⋯褻瀆、冒犯、汙辱。畢竟,有誰夠資格在那兒工作?誰能套上他的鞋子(像灰姑娘的鞋子)?誰又敢坐在同一間辦公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假如他知道這間辦公室就是愛因斯坦以前工作的聖地?
「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究竟在哪裡呢?」塔布斯疑惑的問道。
曠世奇才
愛因斯坦未進高等研究院前,早已經是風靡全球的人物了。1919年,當天文學家證實了他的預測,光線會受太陽的重力偏折時,舉世為他如痴如狂。新生兒命名、香菸品牌都用上愛氏的名字。倫敦智慧女神(London Palladium)劇場邀請他去參與演出三週,酬勞隨便他開。兩位德國教授合作拍製了「相對論影片」在大西洋兩岸同時放映。愛氏拜訪英國生物學家霍登(J. B. S. Haldane),並於他家中過夜時,霍登的女兒才看了此人一眼,即暈死過去。新聞界更將愛氏的理論,捧為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就,而愛氏本人則為有史以來最傑出、最優秀的人。
畢竟,他真是新秩序的發言人。光有重量、空間是彎的、宇宙有四維空間。人們愛死他了,雖然對他講的東西毫無概念,可是又有什麼關係?他是這些理論的創始者,真正懂得的人,是眾人的英雄,新的彌賽亞,第一位真正的飽學之士,是廣闊無邊物理宇宙的最高元帥。愛氏備受尊崇,然而他本人卻極謙虛、和藹,不懂人家為何要大驚小怪。至少他待人很民主,一視同仁,愛氏說:「我和每個人的說話方式都一樣。不論對方是清潔工還是大學校長。」當然,如果要吹毛吹疵的話,還是可以發現一些例外⋯⋯比方有次他寄了一篇論文給《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審核,編輯竟敢退回論文要求重寫。哇!這下可好了!那位可憐的編輯只不過克盡本分,將文章送交審稿委員評閱而已,但這卻不見容於愛因斯坦,並終身視《物理評論》為拒絕往來戶。這說明了什麼呢?這位曠世物理奇才,終究自我中心:如果某項見解是高研院首席科學巨星肯定的,那就是健全而完整的點子,絕不容許別人有絲毫質疑。
在凡人眼中,愛氏可能是謙卑的天才,只是從來不穿襪子(至少還穿了鞋子)。但是在那柏拉圖的天空,可又另當別論了。這個人絕對的高傲自信,令人咋舌;他自認可以徹底了解整個宇宙的奧祕—沒有漏網之魚,大至最龐大的星系,小至最微小的夸克;他認為自己無所不通,而且可以找出一組簡單原則,即是跨越兩個極端,涵蓋大、小宇宙的統一場論(unified field theory)。他怎麼做呢?純靠推理,完全符合了柏拉圖天空的優良傳統。當那些迴旋加速器(cyclotron)工程師使勁撞擊他們的王國,天文學家架出碩大的高倍望遠鏡,朝著億萬光年外的浩瀚、冰冷星際瞭望的時候,愛因斯坦則將自己關在斗室裡,放下窗簾,然後,以他特有的口吻說:「我要想一下。」他寫下幾行潦潦草草的方程式,做做頭腦體操,仔細瞧瞧!他很快的就把一切搞定了。只靠冥想⋯⋯沒有機器,沒有儀器設備。
曾經有人問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他的實驗室設在哪裡?愛氏微微一笑,從胸前的口袋中摸出一枝鋼筆,說:「在這裡!」
三顧茅廬
1932年冬,傅列克斯納遠赴加州尋找新研究院的合適成員。名叫摩根的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建議傅氏去和愛因斯坦碰個面,愛氏正巧在那兒客座。相談之下,愛氏很喜歡高等研究院的構想,頗有相見恨晚的感慨,當時愛氏仍是柏林大學的教授,但在德國的處境每況愈下。1920年時,蹦出了一個反愛因斯坦的聯盟,自稱是「日耳曼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出錢資助任何肯出面反對「猶太物理」,特別是什麼「相對論」那檔子事的人。1920年8月24日,這個愛氏稱之為「反相對論有限公司」的組織,贊助了一場在柏林愛樂廳舉行的會議。愛氏本人也參加了那場會議,卻當場哭笑不得,因為對方的攻訐實在是荒謬絕倫。
這些亞利安物理學家煞有介事的恣意攻訐,而愛氏則人在屋簷下,忍受了他們十年的無理取鬧。1931年前夕,「反相對論公司」出版了一本書《一百位作家反愛因斯坦》(100 Authors Against Einstein)後,他就決意離開德國,永不再回來,因此對傅氏所言側耳傾聽。兩人沿著加州理工教職員俱樂部的長廊來來回回走了數趟,討論行將在普林斯頓成立的新研究中心。愛氏要求與傅氏擇期再敘,兩人便約定在1932年的春季班開始時再見面,屆時他們二人都會在英國的牛津。
5月一個美麗的週六早晨,晴空萬里,小鳥輕啼,傅氏和愛氏二人穿越基督教堂前的草坪,緩步微吟,宛如兩個體面的牛津教授。傅氏開門見山,直陳來意:「愛因斯坦教授,在下不揣冒昧,願在新研究院內提供您一個職缺,倘若閣下經過深思熟慮,覺得本院有幸能提供您珍視的機會,本院將竭誠期待您的大駕光臨。」
愛因斯坦有點心動,但一如往常,不願倉促行事。畢竟,全世界如耶路撒冷、馬德里、巴黎、萊登和牛津等地的知名大學,都爭相虛位以待,提供教授、研究員和各式各樣榮譽職位給他—只要他肯大駕光臨,能使學校蓬蓽生輝,幾乎是任何要求都行。早在1927年,他已經回絕過普林斯頓一次,不過事過境遷,或許該是拜訪新大陸的時候了。
「你今年夏天會在德國嗎?」愛氏問道。
翌月,傅氏飛抵德國卡普特(Caputh),在下午三點於寒風細雨中邁步進入愛氏的鄉居,直到深夜十一點才離去。此行他獲得了夢寐以求的答案,因為愛氏的回答是:「我心如火焰,熱切期待這一刻來臨!」就在1932年6月4日,愛因斯坦成為了高等研究院第一位教授。一夕之間,傅氏夢中的研究院,有了全新的意義和展望,就像上帝親自臨幸傅氏在普林斯頓的新家一樣。當然還有一些問題待解決:愛因斯坦的薪水、再加上愛氏同僚梅爾(Walther Mayer)的去留問題。愛氏要求年薪三千美元。他問傅氏:「數目再少些,可以應付生活所需嗎?」傅氏回答:「不行,那樣不夠!」
最後「薪事」以年薪一萬美元定案,愛氏也欣然同意;至於梅爾的聘約則延期再議。愛氏通常都避免與其他人共事—他以前常這麼說:「我是一匹只披單轡的馬」。不過事實上,他曾和奧地利數學家梅爾合寫過幾篇論文,而且兩人亦有共同的夢想,要完成統一場論。此外,愛氏考慮到,如果分派一些較為例行的計算工作給助手,自己就可專注於較為抽象而創新的推理。綜合這些原因,他肯定梅爾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傅氏原則上同意延請梅爾入院,但不是以他的名義,給他獨立的聘約,只同意他擔任愛氏的助理。梅爾畢竟並不真正符合該院人才延攬的標準;他曾出過一本有關非歐幾何方面的書,但也是他唯一的成名作,不管愛氏如何器重他,為他冠上教授頭銜,對研究院的聲望並沒有實質的幫助。可是,愛氏卻很堅持,並於1933年春寫信給傅氏說,除非院方聘請梅爾,否則全部協議一筆勾銷。愛氏寫道:「不瞞您說,我會深感遺憾,如果梅爾寶貴的合作權遭剝奪,沒有他在院中鼎力相助,甚至會妨礙了我的工作推展。」因此,傅氏終於聘請了梅爾。
摘自《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物理教宗──愛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