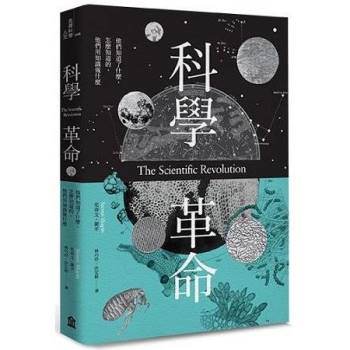自然與目的:科學世界裡的祕境
這本描述科學革命之作有個一以貫之的主題,就是現代論實作者對於以目的論來詮釋自然現象(也就是把自然效果的目的當成是它的成因)的猜疑,甚至是強烈的排斥;從伽利略與霍布斯對於亞里斯多德學派「自然位置」的批評開始,到梅森以機械論取代「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主義」,再到波以耳對於用哲學性的語言使用「自然定律」的慎重。我們可能會想要下一個簡化的結論,認為這個主題捕捉了科學革命的「本質」,或至少是機械論自然哲學的本質:機械論詮釋就這樣取代目的論詮釋,而現代性就此形成。
但是之前的篇幅卻正好說明了,這樣的結論是不正確的。非常多的十七世紀實作者意識到機械論的詮釋範圍是有限的。自然哲學家的言語可能是機械論的,擱置了所有的目的性,但即便如此,能夠以機械論加以詮釋的,也不見得就等同於世界上的所有現象。其他的實作者雖然也同樣折服於機械論的詮釋價值,卻不認為自然哲學家在提供關於世界的敘述時會有這樣的限制。一方面,笛卡兒設想了一個上帝可能創造的假想世界,一個完全禁得起機械論詮釋的世界:這就是自然哲學家需要去解釋的世界。另一方面,如波以耳及雷(John Ray)這些作家的關切則在於,追尋上帝在祂所真正創造的世界中的意圖及設計。這就是為何他們覺得,當自然界中的證據夠清楚,以目的性來詮釋世界,在哲學上是合宜的。構成「自然神學」基石的設計論證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一個目的論詮釋:它以神聖的意圖來解釋自然構造如何適應其功能。這些在詮釋策略上的差異反映出了,關於「什麼是自然哲學家與自然史學家的正經事」之不同看法。所有的實作者可能會原則上同意,改革後的自然知識應該要消除疑慮、確保正確的信念,並保障維持道德秩序所需的基礎;但他們對於該如何架構自然研究,使其適於從事這些任務上則意見分歧。對部分哲學家來說,對自然的認知裡會有一個適當的位置留給非機械論及目的論詮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該說機械論是「不完全的」,因為這可能影射了自然哲學家的工作只有提供機械論詮釋,無論那是何種自然現象,或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這樣的詮釋。比方說,波以耳便為最終成因的哲學適當性提供了一個深思熟慮的辯護,特別是在(但不完全是)詮釋生命體時:「我們所知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動物的身體結構可能是最適合以最終成因來加以解釋的。」生命結構的高度複雜性,加上其結構明顯地適應其功能,這些都迫使我們相信存在著一位「理性的管理者」。我們或許可以說,複雜及適應是藉由機械方法而發生的,但卻無法說它們的出現與具知性的設計無關。
到了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牛頓爵士(Sir Isaac Newton),他有時被稱頌是將機械論哲學帶到完美境界的哲學家,表達了其對於全面提供機械論詮釋的哲學感到不耐。如第一章所示,牛頓並不願意指明重力的機械論成因,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他關於磁力、電力,以及生命現象的處理方法。是誰決定自然哲學的工作定義就是提供明確的機械論成因說明?如果這是自然現象所顯明的,為什麼不使用吸引力或排斥力這種「主動的力」?這樣做不必然就是回到亞里斯多德學派,或文藝復興時期神祕論的談法:「我所探討的這些原理,並不是那種由特定事物歸結來的神祕特性,而是自然的普遍定律,事物因此形成;藉由現象,它們的真實得以顯現,雖然它們成因尚未被發現。這些是明顯的特質,只有其成因才是神祕的。」這不是哲學,而是在我們的感知及智力尚無法確切發現成因假說時,「捏造出」(或以想像調製出)的假說,即使(特別)是那些機械論成因的假說。牛頓寫道,「關於物體,我們能看見的只有其特徵及顏色,能聽到的只有聲音,能碰觸到的只有外部表面,能聞到的只有氣味,能嚐到的只有滋味;但物體內部的物質並不是我們的感知或我們心靈的內省所能瞭解的。」如果其他的實作者將適當的自然哲學等同於提供機械論說明,在此,牛頓則表明了他滿足於自然最終的不可解。應該要認清,知性的適當侷限。自然哲學會是塊堅固而確定的岩石,但其四周則為巨大的神祕海洋所環繞。前述的討論透露出,在十七世紀的現代論者中,笛卡兒一直是最積極樂觀的機械論成因詮釋提供者,因此與波以耳及牛頓這樣的哲學家成對比;要瞭解笛卡兒在機械論上的野心,他如何看待生命現象(包括人體之運作)是最好的途徑。藉此我們將可以同時深入瞭解,那用來說明人類及人類經驗在現代自然定位的機械論架構,其說明的侷限,以及架構所可能產生的後果。
第一章曾簡單地介紹了,笛卡兒將人類身體解釋為一座「雕像,一座泥塑的機器」。他有意將人類身體的運作全部放在機械論哲學的架構下處理:食物的消化、吸收與排泄;血液的構成,以及它經由靜脈與動脈的移動;呼吸的動作與功能;以及「反射動作」的模式7。當然,構成人體的機械「在組成上是無可匹敵的完美」,勝過那些人類工匠的手藝,儘管如此,那仍舊是一台機器。如此,要解釋人體的運作就可以套用風靡現代早期貴族社會之精巧自動機的說明:擁有隱藏的彈簧、齒輪、輪子,可移動身軀的,甚至還可以發聲的塑像。要承認是機械成因推動這些自動機械之運動毫無困難(畢竟,這是人類所造的),對笛卡兒來說,要以類似的機械論語彙來解釋動物身體的各個面向也同樣沒問題。在笛卡兒看來,物質機械論足以解釋關於猴子或蜜蜂的一切。
然而,對於人類來說,機械論能說明的範圍就侷限得多。對笛卡兒來說,解釋人類身體不同於解釋人類,因為光是從身體構造以及動作並無法完全說明人類的一切。我們並不覺得自己是機器,而笛卡兒也同意我們並不是機器。我們可感受自己運用意志、擁有目的、因著目的移動身體、擁有知覺、進行道德判斷、從事思考及推理(也就是說,會思考),並會用語言表達思考的結論;這些都是笛卡兒認為機械或動物無法做的事情。人類之所以擁有這些特質並從事這些行為,是由於人類的二元本質:若只考慮其身體,那當然就只與物質的移動相關,但他們還擁有心靈,而心靈的現象最終是無法用物質的移動加以解釋。這個世界本身包含了兩種不同性質的領域,物質的與心靈的。唯有在人類身上,這兩個領域才會互相交會。人類是上帝生命造物中唯一具有「理性靈魂」的。這靈魂是上帝給予的特殊天賦,將人類連結至其創造者,也將笛卡兒哲學連結至聖經。每一個人類靈魂都是由上帝特別打造;它是不朽的;不同於物質、不占空間,也無法分割。於是,這個十七世紀最具雄心的機械論詮釋計畫,最後也終歸於神祕。
這神祕所關切的,是心靈與物質如何在人類架構中會合。我們可以找到一些類似這種神祕結合的例子,像是石頭與重力的結合,手指與手的結合,同一身體裡不同組織的結合等等;但到最後,發生在人類身上心靈與物質的結合才是最根本的,也因此是無法分析的概念。如果說,心靈不占據空間,那它到底在哪裡?這兩個領域在何處相會?這裡,笛卡兒的確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正如同所有的知覺及感覺都必須同時是思考的作用物,因此我們所要找的,是一個位於大腦內部中央,一個非左右對稱的小器官(圖30)。那便是小小的松果體,「想像與常識棲身之所」,確實的「靈魂的所在地」。體積微小且僅為周遭血管所支撐的松果體,非常適於從事傳遞心靈與身體的動作。這最終的神祕很恰當地落腳在一個點上。
笛卡兒將他的機械論詮釋計畫推展到可能的極限,最後卻結束於一個位於其機械論哲學範圍之外的概念上,這個概念看來甚至違反了一些他最關切的原理。人類的獨特性來自於,分別位於機械論架構內外之概念的神祕交會。人類擁有具目的性的心靈,而且最後到底還是這個心靈移動了物質。就像你翻開這本書的同時,便顯示了心靈在自然中的角色。如同機械論同時受到宗教敏感度以及人類生活經驗所限,對於人類中心主義的拒否(如第一章所提)也因為機械論無法完全解釋「什麼是人類」而受限。如我們所見,其他自然哲學家們在劃定機械論詮釋範圍的界線時,都較笛卡兒來得小心謹慎;而笛卡兒的說法也常遭受質疑,被謠傳為會危害教會所認可的人類的精神本質,及其與上帝間的獨特關係。然而笛卡兒野心勃勃的機械論計畫並未否定人類在自然世界中所占據的獨特中心位置,只是提供了另一個語法來理解之。神祕的人類本質所身處的那個小點,也就是人類中心主義繼續存在的地方。人類在自然中的特殊位置,既是問題的解答,也是個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科學革命留給它文化繼承人的遺產。
這本描述科學革命之作有個一以貫之的主題,就是現代論實作者對於以目的論來詮釋自然現象(也就是把自然效果的目的當成是它的成因)的猜疑,甚至是強烈的排斥;從伽利略與霍布斯對於亞里斯多德學派「自然位置」的批評開始,到梅森以機械論取代「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主義」,再到波以耳對於用哲學性的語言使用「自然定律」的慎重。我們可能會想要下一個簡化的結論,認為這個主題捕捉了科學革命的「本質」,或至少是機械論自然哲學的本質:機械論詮釋就這樣取代目的論詮釋,而現代性就此形成。
但是之前的篇幅卻正好說明了,這樣的結論是不正確的。非常多的十七世紀實作者意識到機械論的詮釋範圍是有限的。自然哲學家的言語可能是機械論的,擱置了所有的目的性,但即便如此,能夠以機械論加以詮釋的,也不見得就等同於世界上的所有現象。其他的實作者雖然也同樣折服於機械論的詮釋價值,卻不認為自然哲學家在提供關於世界的敘述時會有這樣的限制。一方面,笛卡兒設想了一個上帝可能創造的假想世界,一個完全禁得起機械論詮釋的世界:這就是自然哲學家需要去解釋的世界。另一方面,如波以耳及雷(John Ray)這些作家的關切則在於,追尋上帝在祂所真正創造的世界中的意圖及設計。這就是為何他們覺得,當自然界中的證據夠清楚,以目的性來詮釋世界,在哲學上是合宜的。構成「自然神學」基石的設計論證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一個目的論詮釋:它以神聖的意圖來解釋自然構造如何適應其功能。這些在詮釋策略上的差異反映出了,關於「什麼是自然哲學家與自然史學家的正經事」之不同看法。所有的實作者可能會原則上同意,改革後的自然知識應該要消除疑慮、確保正確的信念,並保障維持道德秩序所需的基礎;但他們對於該如何架構自然研究,使其適於從事這些任務上則意見分歧。對部分哲學家來說,對自然的認知裡會有一個適當的位置留給非機械論及目的論詮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該說機械論是「不完全的」,因為這可能影射了自然哲學家的工作只有提供機械論詮釋,無論那是何種自然現象,或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這樣的詮釋。比方說,波以耳便為最終成因的哲學適當性提供了一個深思熟慮的辯護,特別是在(但不完全是)詮釋生命體時:「我們所知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動物的身體結構可能是最適合以最終成因來加以解釋的。」生命結構的高度複雜性,加上其結構明顯地適應其功能,這些都迫使我們相信存在著一位「理性的管理者」。我們或許可以說,複雜及適應是藉由機械方法而發生的,但卻無法說它們的出現與具知性的設計無關。
到了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牛頓爵士(Sir Isaac Newton),他有時被稱頌是將機械論哲學帶到完美境界的哲學家,表達了其對於全面提供機械論詮釋的哲學感到不耐。如第一章所示,牛頓並不願意指明重力的機械論成因,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他關於磁力、電力,以及生命現象的處理方法。是誰決定自然哲學的工作定義就是提供明確的機械論成因說明?如果這是自然現象所顯明的,為什麼不使用吸引力或排斥力這種「主動的力」?這樣做不必然就是回到亞里斯多德學派,或文藝復興時期神祕論的談法:「我所探討的這些原理,並不是那種由特定事物歸結來的神祕特性,而是自然的普遍定律,事物因此形成;藉由現象,它們的真實得以顯現,雖然它們成因尚未被發現。這些是明顯的特質,只有其成因才是神祕的。」這不是哲學,而是在我們的感知及智力尚無法確切發現成因假說時,「捏造出」(或以想像調製出)的假說,即使(特別)是那些機械論成因的假說。牛頓寫道,「關於物體,我們能看見的只有其特徵及顏色,能聽到的只有聲音,能碰觸到的只有外部表面,能聞到的只有氣味,能嚐到的只有滋味;但物體內部的物質並不是我們的感知或我們心靈的內省所能瞭解的。」如果其他的實作者將適當的自然哲學等同於提供機械論說明,在此,牛頓則表明了他滿足於自然最終的不可解。應該要認清,知性的適當侷限。自然哲學會是塊堅固而確定的岩石,但其四周則為巨大的神祕海洋所環繞。前述的討論透露出,在十七世紀的現代論者中,笛卡兒一直是最積極樂觀的機械論成因詮釋提供者,因此與波以耳及牛頓這樣的哲學家成對比;要瞭解笛卡兒在機械論上的野心,他如何看待生命現象(包括人體之運作)是最好的途徑。藉此我們將可以同時深入瞭解,那用來說明人類及人類經驗在現代自然定位的機械論架構,其說明的侷限,以及架構所可能產生的後果。
第一章曾簡單地介紹了,笛卡兒將人類身體解釋為一座「雕像,一座泥塑的機器」。他有意將人類身體的運作全部放在機械論哲學的架構下處理:食物的消化、吸收與排泄;血液的構成,以及它經由靜脈與動脈的移動;呼吸的動作與功能;以及「反射動作」的模式7。當然,構成人體的機械「在組成上是無可匹敵的完美」,勝過那些人類工匠的手藝,儘管如此,那仍舊是一台機器。如此,要解釋人體的運作就可以套用風靡現代早期貴族社會之精巧自動機的說明:擁有隱藏的彈簧、齒輪、輪子,可移動身軀的,甚至還可以發聲的塑像。要承認是機械成因推動這些自動機械之運動毫無困難(畢竟,這是人類所造的),對笛卡兒來說,要以類似的機械論語彙來解釋動物身體的各個面向也同樣沒問題。在笛卡兒看來,物質機械論足以解釋關於猴子或蜜蜂的一切。
然而,對於人類來說,機械論能說明的範圍就侷限得多。對笛卡兒來說,解釋人類身體不同於解釋人類,因為光是從身體構造以及動作並無法完全說明人類的一切。我們並不覺得自己是機器,而笛卡兒也同意我們並不是機器。我們可感受自己運用意志、擁有目的、因著目的移動身體、擁有知覺、進行道德判斷、從事思考及推理(也就是說,會思考),並會用語言表達思考的結論;這些都是笛卡兒認為機械或動物無法做的事情。人類之所以擁有這些特質並從事這些行為,是由於人類的二元本質:若只考慮其身體,那當然就只與物質的移動相關,但他們還擁有心靈,而心靈的現象最終是無法用物質的移動加以解釋。這個世界本身包含了兩種不同性質的領域,物質的與心靈的。唯有在人類身上,這兩個領域才會互相交會。人類是上帝生命造物中唯一具有「理性靈魂」的。這靈魂是上帝給予的特殊天賦,將人類連結至其創造者,也將笛卡兒哲學連結至聖經。每一個人類靈魂都是由上帝特別打造;它是不朽的;不同於物質、不占空間,也無法分割。於是,這個十七世紀最具雄心的機械論詮釋計畫,最後也終歸於神祕。
這神祕所關切的,是心靈與物質如何在人類架構中會合。我們可以找到一些類似這種神祕結合的例子,像是石頭與重力的結合,手指與手的結合,同一身體裡不同組織的結合等等;但到最後,發生在人類身上心靈與物質的結合才是最根本的,也因此是無法分析的概念。如果說,心靈不占據空間,那它到底在哪裡?這兩個領域在何處相會?這裡,笛卡兒的確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正如同所有的知覺及感覺都必須同時是思考的作用物,因此我們所要找的,是一個位於大腦內部中央,一個非左右對稱的小器官(圖30)。那便是小小的松果體,「想像與常識棲身之所」,確實的「靈魂的所在地」。體積微小且僅為周遭血管所支撐的松果體,非常適於從事傳遞心靈與身體的動作。這最終的神祕很恰當地落腳在一個點上。
笛卡兒將他的機械論詮釋計畫推展到可能的極限,最後卻結束於一個位於其機械論哲學範圍之外的概念上,這個概念看來甚至違反了一些他最關切的原理。人類的獨特性來自於,分別位於機械論架構內外之概念的神祕交會。人類擁有具目的性的心靈,而且最後到底還是這個心靈移動了物質。就像你翻開這本書的同時,便顯示了心靈在自然中的角色。如同機械論同時受到宗教敏感度以及人類生活經驗所限,對於人類中心主義的拒否(如第一章所提)也因為機械論無法完全解釋「什麼是人類」而受限。如我們所見,其他自然哲學家們在劃定機械論詮釋範圍的界線時,都較笛卡兒來得小心謹慎;而笛卡兒的說法也常遭受質疑,被謠傳為會危害教會所認可的人類的精神本質,及其與上帝間的獨特關係。然而笛卡兒野心勃勃的機械論計畫並未否定人類在自然世界中所占據的獨特中心位置,只是提供了另一個語法來理解之。神祕的人類本質所身處的那個小點,也就是人類中心主義繼續存在的地方。人類在自然中的特殊位置,既是問題的解答,也是個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科學革命留給它文化繼承人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