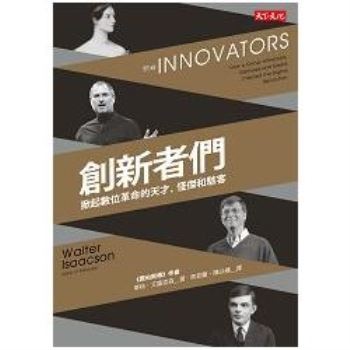《勒夫雷斯伯爵夫人愛達》
詩意的科學
1833 年 5 月 1 日,芳齡十七的愛達.拜倫(Ada Byron)參加宮廷宴會,和其他年輕女孩一起被引見給英國皇室認識。愛達生性敏感,個性獨立,家人原本很擔心她能否進退合宜,結果根據她母親的說法,愛達的表現「算是中規中矩,差強人意」。當晚愛達見到的王公貴族中包括威靈頓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她很欣賞他率直的作風。至於高齡七十九的法國大使塔列朗(Telleyrand),愛達覺得他像「老猴子」。
身為英國著名詩人拜倫的唯一婚生子女,愛達遺傳了父親的浪漫,母親為了調和她的浪漫天性,特別請家庭教師來教她數學。她那叛逆不羈的想像力,加上對數字的迷戀,讓她愛上了這門「詩意的科學」。在許多人眼中(包括她父親在內),浪漫時期的純淨感性與工業革命掀起的科技狂熱,其實相互衝突。但愛達置身於兩個時代的交叉口,卻感到怡然自得。
難怪愛達雖然在富麗堂皇的宮廷中初次踏入社交界,卻對幾個星期後的另一場盛會更為印象深刻。她在那次盛會中見到了巴貝奇(Charles Babbage)。喪偶的巴貝奇是數學和科學奇才,當時四十一歲,是倫敦社交圈名人。「愛達對星期三聚會的喜愛,勝過其他上流社會的豪華宴會。」愛達的母親對朋友表示:「她在那兒會碰到幾個科學界人士—包括巴貝奇,她喜歡和他在一起。」
巴貝奇每週舉辦熱鬧有趣的沙龍,邀請近三百位賓客參加,身穿燕尾服的紳士、披著華麗織錦的淑女,和作家、工業家、詩人、演員、政治家、探險家、植物學家,以及其他「科學家」(這是巴貝奇的朋友剛創造的名詞)共聚一堂。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指出,巴貝奇成功的把科學家引進上流社會,從而「確立了科學在社會上的地位。」
聚會當晚,他們通常會跳舞、閱讀、玩遊戲、聆聽演講,同時品嘗各種美食,包括海鮮、肉類、異國飲料和冰品。女士在台上玩角色扮演,穿上戲服重現名畫中的情景。天文學家架好望遠鏡,研究人員展示他們的電磁發明,巴貝奇則搬出機械娃娃供賓客賞玩。聚會的焦點是巴貝奇展示他的差分機(Difference Engine)部分模型,這也是他舉辦聚會的原因之一。差分機是巴貝奇在家中打造的巨大機械式計算機。巴貝奇總是以戲劇化的方式展示差分機,他會在差分機計算數字時轉動曲柄,然後等觀眾開始覺得無聊時,開始顯示機器如何根據輸入的指令,突然改變型態。對差分機特別感興趣的人會受邀穿過庭院,到過去是馬廄的地方親眼見識巴貝奇正在打造的完整機器。
大家對於能解開多項式函數的巴貝奇差分機各有不同觀感。威靈頓公爵認為,將軍上戰場前或許可利用差分機來分析可能面臨的各項變數。愛達的母親拜倫夫人則對這部「思考機器」大為讚歎。至於愛達(她後來有一段名言,指出機器永遠無法真正思考),根據一起出席展示會的朋友所言:「拜倫小姐雖然年輕,卻了解機器的運作,而且看出新發明的絕美之處。」
由於熱愛數學與詩,愛達得以看到計算機蘊含的美。浪漫科學時代的特色是對新發明和新發現展現高度熱情,愛達正是最佳範例。霍姆斯(Richard Holmes)在《奇蹟年代》(The Age of Wonder)中寫道,這個時期「為科學工作注入強烈的想像力與熱情。許多人對科學發現有強烈(甚至魯莽)的執著,驅動了科學發展。」簡言之,這個時代和我們的時代頗為相似,工業革命的發展,包括蒸汽機、紡織機和電報的發明,改變了十九世紀的面貌,正如同數位革命(電腦、微晶片和網路)改變了我們的時代一樣。這兩個時代都有一群能結合想像力、熱情和神奇科技的創新者,創造出愛達口中的「詩意的科學」,以及二十世紀詩人布羅提根(RichardBrautigan)所謂「深情優雅的機器」。世界第一枚電晶體
電腦雖然誕生,卻沒能立刻掀起巨浪、啟動革命,原因是最初的電腦仍需仰賴昂貴、脆弱又耗電的巨大真空管來運作,成本十分高昂,唯有企業、研究型大學和軍方才負擔得起。真正的數位時代(電子裝置滲透到生活的每個層面)其實要等到 1947 年 12 月 16 日午後才發端。當天在美國新澤西州默里丘(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兩位科學家用小條金箔、一小片半導體材料和扭曲的迴紋針,把他們的巧妙設計組裝成功,只要把幾個東西擺弄到正確位置,就可以放大電流,也可以把電流開開關關。新裝置很快命名為「電晶體」,就好比蒸汽機啟動工業革命,電晶體也對數位時代帶來重大衝擊。
電晶體誕生後,各種創新發明紛至沓來,新科技能夠把數百萬個電晶體蝕刻在小小的微晶片上,換句話說,比 ENIAC 強大數千倍的資訊處理能力,從此可藏身於火箭鼻錐、筆記型電腦、掌上型計算機和音樂播放器,以及能和網路世界任何節點交流資訊或共享娛樂的手持裝置之中。
三位對科技懷抱強烈熱情的工作伙伴(他們的個性既互補,也相互衝突)後來都名垂千史,被譽為電晶體的發明人,這三人是技巧熟練的實驗高手布拉頓(Walter Brattain)、量子理論學家巴丁(John Bardeen),以及三人之中最熱情執著(後來因此成為悲劇人物)的固態物理學家蕭克利(William Shockley)。
但是,這齣戲裡還有一個要角,重要性和任何發明家不相上下:三人所任職的貝爾實驗室。電晶體的發明並非單憑少數天才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綜合了各種不同才能後的成果。由於電晶體的本質使然,研究小組必須結合對量子現象有敏銳直覺的材料科學家、善於在矽中摻入雜質的專家,以及熟練的實驗高手、工業化學家、製造專家和靈巧的工匠。
貝爾實驗室—創新的搖籃
貝爾實驗室真空管部門的主管名叫凱利(Mervin Kelly),是個能幹的密蘇里人,凱利最初在密蘇里礦業學院研習冶金,後來成為芝加哥大學教授密立坎(Robert Millikan)的門生,並獲得物理博士學位。雖然他設計的水冷卻系統提高了真空管的可靠性,但他也明白,真空管絕對不可能成為高效率的放大器和開關。1936 年,凱利被拔擢為貝爾實驗室的研究主任,首要之務就是設法找出替代方案。
凱利的偉大洞見在於,貝爾實驗室過去雖然是實務工程的技術重鎮,但也應聚焦於原本屬於大學範疇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研究。於是,他開始積極獵才,網羅美國最出色的年輕物理學博士,希望把創新變成組織的常態,而不是袖手旁觀,只靠古怪的天才躲在車庫和閣樓裡獨自鑽研。
「貝爾實驗室開始思考發明的關鍵究竟繫於個人天分,還是仰賴團隊合作,」歷史學家葛特納(Jon Gertner)在關於貝爾實驗室的著作《創意工廠》(The Idea Factory)中寫道。答案是兩者皆是。
無論對貝爾實驗室或對數位時代整體而言,創新的關鍵都在於,必須了解培養個別天才和提倡團隊合作並不衝突,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遊戲。的確,在數位時代,兩種方式可以並行不悖。有創意的天才(莫渠利、蕭克利、賈伯斯等)想到的創新構想,必須仰賴和他們緊密合作的工程師(艾科特、布拉頓、沃茲尼克等)把概念變成新發明。然後技術專才和創業家組成團隊,合力把新發明變成實際產品。像這樣的生態系統如果缺了一角,偉大的概念很可能淪為泡影,最後只能塵封在歷史中,愛荷華州立大學的阿塔納索夫或在倫敦自家後院小棚子裡的巴貝奇,情況就是如此。偉大的團隊如果缺乏高瞻遠矚、滿懷熱情的夢想家,創新的火花也會慢慢熄滅,例如莫渠利和艾科特離開後的賓大團隊、馮諾伊曼求去後的普林斯頓、或蕭克利離開後的貝爾實驗室。
詩意的科學
1833 年 5 月 1 日,芳齡十七的愛達.拜倫(Ada Byron)參加宮廷宴會,和其他年輕女孩一起被引見給英國皇室認識。愛達生性敏感,個性獨立,家人原本很擔心她能否進退合宜,結果根據她母親的說法,愛達的表現「算是中規中矩,差強人意」。當晚愛達見到的王公貴族中包括威靈頓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她很欣賞他率直的作風。至於高齡七十九的法國大使塔列朗(Telleyrand),愛達覺得他像「老猴子」。
身為英國著名詩人拜倫的唯一婚生子女,愛達遺傳了父親的浪漫,母親為了調和她的浪漫天性,特別請家庭教師來教她數學。她那叛逆不羈的想像力,加上對數字的迷戀,讓她愛上了這門「詩意的科學」。在許多人眼中(包括她父親在內),浪漫時期的純淨感性與工業革命掀起的科技狂熱,其實相互衝突。但愛達置身於兩個時代的交叉口,卻感到怡然自得。
難怪愛達雖然在富麗堂皇的宮廷中初次踏入社交界,卻對幾個星期後的另一場盛會更為印象深刻。她在那次盛會中見到了巴貝奇(Charles Babbage)。喪偶的巴貝奇是數學和科學奇才,當時四十一歲,是倫敦社交圈名人。「愛達對星期三聚會的喜愛,勝過其他上流社會的豪華宴會。」愛達的母親對朋友表示:「她在那兒會碰到幾個科學界人士—包括巴貝奇,她喜歡和他在一起。」
巴貝奇每週舉辦熱鬧有趣的沙龍,邀請近三百位賓客參加,身穿燕尾服的紳士、披著華麗織錦的淑女,和作家、工業家、詩人、演員、政治家、探險家、植物學家,以及其他「科學家」(這是巴貝奇的朋友剛創造的名詞)共聚一堂。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指出,巴貝奇成功的把科學家引進上流社會,從而「確立了科學在社會上的地位。」
聚會當晚,他們通常會跳舞、閱讀、玩遊戲、聆聽演講,同時品嘗各種美食,包括海鮮、肉類、異國飲料和冰品。女士在台上玩角色扮演,穿上戲服重現名畫中的情景。天文學家架好望遠鏡,研究人員展示他們的電磁發明,巴貝奇則搬出機械娃娃供賓客賞玩。聚會的焦點是巴貝奇展示他的差分機(Difference Engine)部分模型,這也是他舉辦聚會的原因之一。差分機是巴貝奇在家中打造的巨大機械式計算機。巴貝奇總是以戲劇化的方式展示差分機,他會在差分機計算數字時轉動曲柄,然後等觀眾開始覺得無聊時,開始顯示機器如何根據輸入的指令,突然改變型態。對差分機特別感興趣的人會受邀穿過庭院,到過去是馬廄的地方親眼見識巴貝奇正在打造的完整機器。
大家對於能解開多項式函數的巴貝奇差分機各有不同觀感。威靈頓公爵認為,將軍上戰場前或許可利用差分機來分析可能面臨的各項變數。愛達的母親拜倫夫人則對這部「思考機器」大為讚歎。至於愛達(她後來有一段名言,指出機器永遠無法真正思考),根據一起出席展示會的朋友所言:「拜倫小姐雖然年輕,卻了解機器的運作,而且看出新發明的絕美之處。」
由於熱愛數學與詩,愛達得以看到計算機蘊含的美。浪漫科學時代的特色是對新發明和新發現展現高度熱情,愛達正是最佳範例。霍姆斯(Richard Holmes)在《奇蹟年代》(The Age of Wonder)中寫道,這個時期「為科學工作注入強烈的想像力與熱情。許多人對科學發現有強烈(甚至魯莽)的執著,驅動了科學發展。」簡言之,這個時代和我們的時代頗為相似,工業革命的發展,包括蒸汽機、紡織機和電報的發明,改變了十九世紀的面貌,正如同數位革命(電腦、微晶片和網路)改變了我們的時代一樣。這兩個時代都有一群能結合想像力、熱情和神奇科技的創新者,創造出愛達口中的「詩意的科學」,以及二十世紀詩人布羅提根(RichardBrautigan)所謂「深情優雅的機器」。世界第一枚電晶體
電腦雖然誕生,卻沒能立刻掀起巨浪、啟動革命,原因是最初的電腦仍需仰賴昂貴、脆弱又耗電的巨大真空管來運作,成本十分高昂,唯有企業、研究型大學和軍方才負擔得起。真正的數位時代(電子裝置滲透到生活的每個層面)其實要等到 1947 年 12 月 16 日午後才發端。當天在美國新澤西州默里丘(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兩位科學家用小條金箔、一小片半導體材料和扭曲的迴紋針,把他們的巧妙設計組裝成功,只要把幾個東西擺弄到正確位置,就可以放大電流,也可以把電流開開關關。新裝置很快命名為「電晶體」,就好比蒸汽機啟動工業革命,電晶體也對數位時代帶來重大衝擊。
電晶體誕生後,各種創新發明紛至沓來,新科技能夠把數百萬個電晶體蝕刻在小小的微晶片上,換句話說,比 ENIAC 強大數千倍的資訊處理能力,從此可藏身於火箭鼻錐、筆記型電腦、掌上型計算機和音樂播放器,以及能和網路世界任何節點交流資訊或共享娛樂的手持裝置之中。
三位對科技懷抱強烈熱情的工作伙伴(他們的個性既互補,也相互衝突)後來都名垂千史,被譽為電晶體的發明人,這三人是技巧熟練的實驗高手布拉頓(Walter Brattain)、量子理論學家巴丁(John Bardeen),以及三人之中最熱情執著(後來因此成為悲劇人物)的固態物理學家蕭克利(William Shockley)。
但是,這齣戲裡還有一個要角,重要性和任何發明家不相上下:三人所任職的貝爾實驗室。電晶體的發明並非單憑少數天才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綜合了各種不同才能後的成果。由於電晶體的本質使然,研究小組必須結合對量子現象有敏銳直覺的材料科學家、善於在矽中摻入雜質的專家,以及熟練的實驗高手、工業化學家、製造專家和靈巧的工匠。
貝爾實驗室—創新的搖籃
貝爾實驗室真空管部門的主管名叫凱利(Mervin Kelly),是個能幹的密蘇里人,凱利最初在密蘇里礦業學院研習冶金,後來成為芝加哥大學教授密立坎(Robert Millikan)的門生,並獲得物理博士學位。雖然他設計的水冷卻系統提高了真空管的可靠性,但他也明白,真空管絕對不可能成為高效率的放大器和開關。1936 年,凱利被拔擢為貝爾實驗室的研究主任,首要之務就是設法找出替代方案。
凱利的偉大洞見在於,貝爾實驗室過去雖然是實務工程的技術重鎮,但也應聚焦於原本屬於大學範疇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研究。於是,他開始積極獵才,網羅美國最出色的年輕物理學博士,希望把創新變成組織的常態,而不是袖手旁觀,只靠古怪的天才躲在車庫和閣樓裡獨自鑽研。
「貝爾實驗室開始思考發明的關鍵究竟繫於個人天分,還是仰賴團隊合作,」歷史學家葛特納(Jon Gertner)在關於貝爾實驗室的著作《創意工廠》(The Idea Factory)中寫道。答案是兩者皆是。
無論對貝爾實驗室或對數位時代整體而言,創新的關鍵都在於,必須了解培養個別天才和提倡團隊合作並不衝突,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遊戲。的確,在數位時代,兩種方式可以並行不悖。有創意的天才(莫渠利、蕭克利、賈伯斯等)想到的創新構想,必須仰賴和他們緊密合作的工程師(艾科特、布拉頓、沃茲尼克等)把概念變成新發明。然後技術專才和創業家組成團隊,合力把新發明變成實際產品。像這樣的生態系統如果缺了一角,偉大的概念很可能淪為泡影,最後只能塵封在歷史中,愛荷華州立大學的阿塔納索夫或在倫敦自家後院小棚子裡的巴貝奇,情況就是如此。偉大的團隊如果缺乏高瞻遠矚、滿懷熱情的夢想家,創新的火花也會慢慢熄滅,例如莫渠利和艾科特離開後的賓大團隊、馮諾伊曼求去後的普林斯頓、或蕭克利離開後的貝爾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