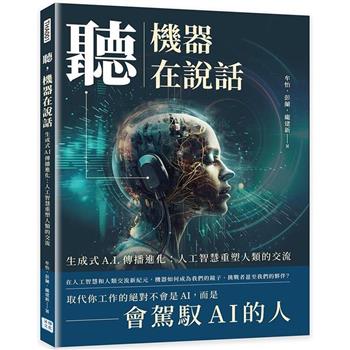從雪莉.特克爾的《群體性孤獨》到約翰.塞爾的「中文房間」論證,無不昭顯著人工智慧/機器人陪伴的真實的謊言。其出發點在於信源的「真實性」。然而信源沒有意識沒有生命,我們就可以否認傳播效果的真實性嗎?陪伴效應,我們當根據因還是當根據果?
群體性孤獨?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教授是享譽世界的社會心理學家,在人與技術關係領域具有很高的聲望。這位被稱為網路文化領域的「瑪格麗特.米德」的學者的每一本書都會引發熱議。從進入社會科學領域伊始,我把她的每一本著作都奉為經典,反覆研讀。2012年,特克爾教授的《群體性孤獨》(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出版後,又一次引發廣泛的討論。在TED 論壇上,她拋出了這樣的質疑:「我們在開發機器人。它們被稱作社交機器人,專門被用來陪伴老人、孩子和我們。我們失去陪伴對方的信心到了如此的地步了嗎?」(We are developing robots. They call them sociable robots, they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be companions, to the elderly, to our children, to us. Have we so lost confidence that we will be there for each other?)
然而,我與特克爾教授在人與技術關係上的觀點卻有很大的分歧。我確信在她書中的論據詳實而有力,但我卻每每得到與之相反的結論。在她1985年的《第二個自我》(The Second Self)裡,她質疑同為MIT 同事的人工智慧先驅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的「非心理學」開發人工智慧心智的方法。到了1995年的《虛擬化身》(Life on the Screen),她進一步指出電腦對人類獨特性的侵犯。2012年的《群體性孤獨》不過是對這一質疑的進一步延伸。至於2015年新發表的《重拾交談》(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則是徹底吹響了討伐人機交流、奪回人機交流陣地的號角。
這樣的觀點代表著目睹人類生活慢慢被技術蠶食後的無奈與反抗,而這樣的觀點我們並不陌生。比如,雪莉.特克爾將兒童與社交機器人的親密關係歸因於兒童某些方面的缺失:「兒童的依戀並不簡單取決於機器人能夠做些什麼,而在於兒童缺失了什麼。在這場實驗中,許多兒童似乎缺失了他們最重要的東西:父母的關注,以及『認為自己很重要』的意識。兒童把機器人想像成他們生活中失去的那些人的替代者……我們向機器人索取什麼,就代表我們需要什麼。」(克特爾,2014,pp.96-97)
真實的謊言
我與特克爾教授在人與技術關係觀點上的分歧固然帶有年齡、文化、個人經歷的烙印,更有意思的是,這也折射出心理學與傳播學兩個學科的差異。作為一名接受過心理分析訓練的心理學家,特克爾教授的出發點在於信源的「真實性」:人類感受到快樂是真實的,因為腦內分泌的多巴胺是真實可測的;我們能對其他人的痛苦經歷感同身受,是因為激發我們共鳴的經歷是真實的。「真實性意味著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因經歷相似而與他人產生情感共鳴的能力,因為人類以相同的方式出生、擁有家人、品味失去家人的痛苦和死亡的真義。而機器人,即使再精密複雜,顯然也難以企及。」(2014, p.7)
然而信源的「真實性」本身不就是一個偽命題嗎?我們可以因為巧克力帶來的多巴胺不是真實的愛人帶來的就拒絕承認巧克力能改善我們的情緒嗎?
我在美國念博士的時候,一位美國同學對電影表演很感興趣。他的一個研究項目就是把大腦功能與表演風格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戲劇表演中有兩個流派:一個是表現派,強調演員表演時將鑽研出的人物性格準確地如一面鏡子一樣重現在舞台上;而另一派是體驗派,主張演員把自己的情感融入表演,表演時或多或少感受到應該表現出的情緒。前者強調對角色的反覆揣摩,用心模仿,進而冷靜判斷。用這一派的祖師爺19世紀法國演員哥格蘭的觀點來說,就是「藝術不是合一,而是表現」。而後者則要求演員聽命於自己的感受,需要流淚時,立馬能表現出自己的傷心記憶,需要大笑時,自己的歡樂記憶噴湧而出。所以演員在每一次演出時都會真正產生人物的熱情。而眾所周知,人的感性控制主要依靠右腦,而左腦則掌控理性。反映在臉部上,被右腦控制的左邊臉會比右邊臉表情更動人。如果體驗派的表演者體驗的是真實的情感,而表現派表演者只是透過理性控制自己的身體,那麼前者表演中更多的是動用右腦,左臉的表情會更豐富,後者則運用左腦居多,右臉的表情會更豐富一些。
於是這位同學把好萊塢演員中典型的兩派演員做出各種表情的照片找出來,用圖像處理軟體把他們的左臉和右臉切割之後再鏡像,生成一堆完全對稱的大頭照,然後讓受試者判斷每張照片反映出來的情感。結果倒是不讓人意外:左臉鏡像反映出的情緒比右臉鏡像的情緒更準確,更真實。
然而,即使在知道這個結論之後,我們依然會對表現派演員的表演樂在其中。我們會因為他們展現出的憂傷快樂僅僅是運用理性的手段動用了臉部的幾塊肌肉造成的便嗤之以鼻嗎?顯然不會。
從達爾文開始,到19世紀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再到當代的心理學家們,一個共同的觀點就是:人類不僅僅是因為開心才會微笑,因為沮喪而皺眉頭;相反的因果關係依然成立,那就是:我們做出微笑的表情後,我們便會覺得高興,我們皺眉之後便會覺得不開心。這就是著名的臉部回饋假設(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 Kleinke, Peterson, Rutledge, 1998)。難道我們會因為讓我們喜悅的不是愛人的擁抱、同人的讚許、家人的肯定,而僅僅是我們讓自己的嘴角上揚,就否定了這種喜悅的真實嗎?
信任與移情
人類上萬年的進化過程中,謹慎一直是被推崇的品質,即使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哈利波特第二部《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中金妮的父親曾給過金妮一個警告:「不要相信任何會自己思考的東西,除非你能看到是什麼在操縱它的大腦。」這樣對陌生智慧不信任的觀點古而有之。中國西周匠人偃師獻給周穆王的能歌善舞的機器人「能倡者」因為「勾引挑逗」王之美人,引得龍顏大怒。偃師只得剖開機器人,演示其「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的五臟六腑,才博得周穆王的信任。
因為對機器智慧的不熟悉,人們對它自然也不敢抱以信任。更重要的是,對機器,我們沒法實現移情。移情(empathy),指一種情感從一個人向他人轉移的模糊過程,是同情心以及情感共鳴的前提。例如,我們看到別人流淚,自己也會難過;看到別人手舞足蹈,自己也會興奮起來。不僅在生命體中如此,微觀世界中的「量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現象也被多次證實。
然而,不少人相信,只有人才能真正的關心他人,與之發生情感共鳴。然而,我們似乎誇大了人的這一功能。當別人握著你的手給予你安慰的時候,很可能他只是例行公事,而非真的感同身受。這樣例行公事的行為與程式編制出的行為有何區別?如果我們一定要區分這兩者的差別,未免犯了信源至上的錯誤。如果我們從資訊接收方來看,只要對方表露得不露痕跡,接收方是感受不到區別的。這樣看來,程式的欺騙行為和人類的作秀行為從傳播效果上而言的確殊途同歸。
讓我們回到著名的圖靈測試:如果機器能騙得了人認為它是人,那麼它就具有智慧。換言之,機器如果表現得智慧,我們便認為它是智慧的。雖然約翰.塞爾(John Searle)著名的「中文房間」論證(the Chinese room argument)指出機器智慧的欺騙性,然而只是取得了在質疑信源上的成功,卻未對交流的效果帶來實質性的挑戰。如果我們能夠接受「表現出的」智慧,為什麼就不能接受「表現出的」關心,「表現出的」信任呢?
群體性孤獨?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教授是享譽世界的社會心理學家,在人與技術關係領域具有很高的聲望。這位被稱為網路文化領域的「瑪格麗特.米德」的學者的每一本書都會引發熱議。從進入社會科學領域伊始,我把她的每一本著作都奉為經典,反覆研讀。2012年,特克爾教授的《群體性孤獨》(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出版後,又一次引發廣泛的討論。在TED 論壇上,她拋出了這樣的質疑:「我們在開發機器人。它們被稱作社交機器人,專門被用來陪伴老人、孩子和我們。我們失去陪伴對方的信心到了如此的地步了嗎?」(We are developing robots. They call them sociable robots, they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be companions, to the elderly, to our children, to us. Have we so lost confidence that we will be there for each other?)
然而,我與特克爾教授在人與技術關係上的觀點卻有很大的分歧。我確信在她書中的論據詳實而有力,但我卻每每得到與之相反的結論。在她1985年的《第二個自我》(The Second Self)裡,她質疑同為MIT 同事的人工智慧先驅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的「非心理學」開發人工智慧心智的方法。到了1995年的《虛擬化身》(Life on the Screen),她進一步指出電腦對人類獨特性的侵犯。2012年的《群體性孤獨》不過是對這一質疑的進一步延伸。至於2015年新發表的《重拾交談》(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則是徹底吹響了討伐人機交流、奪回人機交流陣地的號角。
這樣的觀點代表著目睹人類生活慢慢被技術蠶食後的無奈與反抗,而這樣的觀點我們並不陌生。比如,雪莉.特克爾將兒童與社交機器人的親密關係歸因於兒童某些方面的缺失:「兒童的依戀並不簡單取決於機器人能夠做些什麼,而在於兒童缺失了什麼。在這場實驗中,許多兒童似乎缺失了他們最重要的東西:父母的關注,以及『認為自己很重要』的意識。兒童把機器人想像成他們生活中失去的那些人的替代者……我們向機器人索取什麼,就代表我們需要什麼。」(克特爾,2014,pp.96-97)
真實的謊言
我與特克爾教授在人與技術關係觀點上的分歧固然帶有年齡、文化、個人經歷的烙印,更有意思的是,這也折射出心理學與傳播學兩個學科的差異。作為一名接受過心理分析訓練的心理學家,特克爾教授的出發點在於信源的「真實性」:人類感受到快樂是真實的,因為腦內分泌的多巴胺是真實可測的;我們能對其他人的痛苦經歷感同身受,是因為激發我們共鳴的經歷是真實的。「真實性意味著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因經歷相似而與他人產生情感共鳴的能力,因為人類以相同的方式出生、擁有家人、品味失去家人的痛苦和死亡的真義。而機器人,即使再精密複雜,顯然也難以企及。」(2014, p.7)
然而信源的「真實性」本身不就是一個偽命題嗎?我們可以因為巧克力帶來的多巴胺不是真實的愛人帶來的就拒絕承認巧克力能改善我們的情緒嗎?
我在美國念博士的時候,一位美國同學對電影表演很感興趣。他的一個研究項目就是把大腦功能與表演風格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戲劇表演中有兩個流派:一個是表現派,強調演員表演時將鑽研出的人物性格準確地如一面鏡子一樣重現在舞台上;而另一派是體驗派,主張演員把自己的情感融入表演,表演時或多或少感受到應該表現出的情緒。前者強調對角色的反覆揣摩,用心模仿,進而冷靜判斷。用這一派的祖師爺19世紀法國演員哥格蘭的觀點來說,就是「藝術不是合一,而是表現」。而後者則要求演員聽命於自己的感受,需要流淚時,立馬能表現出自己的傷心記憶,需要大笑時,自己的歡樂記憶噴湧而出。所以演員在每一次演出時都會真正產生人物的熱情。而眾所周知,人的感性控制主要依靠右腦,而左腦則掌控理性。反映在臉部上,被右腦控制的左邊臉會比右邊臉表情更動人。如果體驗派的表演者體驗的是真實的情感,而表現派表演者只是透過理性控制自己的身體,那麼前者表演中更多的是動用右腦,左臉的表情會更豐富,後者則運用左腦居多,右臉的表情會更豐富一些。
於是這位同學把好萊塢演員中典型的兩派演員做出各種表情的照片找出來,用圖像處理軟體把他們的左臉和右臉切割之後再鏡像,生成一堆完全對稱的大頭照,然後讓受試者判斷每張照片反映出來的情感。結果倒是不讓人意外:左臉鏡像反映出的情緒比右臉鏡像的情緒更準確,更真實。
然而,即使在知道這個結論之後,我們依然會對表現派演員的表演樂在其中。我們會因為他們展現出的憂傷快樂僅僅是運用理性的手段動用了臉部的幾塊肌肉造成的便嗤之以鼻嗎?顯然不會。
從達爾文開始,到19世紀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再到當代的心理學家們,一個共同的觀點就是:人類不僅僅是因為開心才會微笑,因為沮喪而皺眉頭;相反的因果關係依然成立,那就是:我們做出微笑的表情後,我們便會覺得高興,我們皺眉之後便會覺得不開心。這就是著名的臉部回饋假設(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 Kleinke, Peterson, Rutledge, 1998)。難道我們會因為讓我們喜悅的不是愛人的擁抱、同人的讚許、家人的肯定,而僅僅是我們讓自己的嘴角上揚,就否定了這種喜悅的真實嗎?
信任與移情
人類上萬年的進化過程中,謹慎一直是被推崇的品質,即使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哈利波特第二部《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中金妮的父親曾給過金妮一個警告:「不要相信任何會自己思考的東西,除非你能看到是什麼在操縱它的大腦。」這樣對陌生智慧不信任的觀點古而有之。中國西周匠人偃師獻給周穆王的能歌善舞的機器人「能倡者」因為「勾引挑逗」王之美人,引得龍顏大怒。偃師只得剖開機器人,演示其「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的五臟六腑,才博得周穆王的信任。
因為對機器智慧的不熟悉,人們對它自然也不敢抱以信任。更重要的是,對機器,我們沒法實現移情。移情(empathy),指一種情感從一個人向他人轉移的模糊過程,是同情心以及情感共鳴的前提。例如,我們看到別人流淚,自己也會難過;看到別人手舞足蹈,自己也會興奮起來。不僅在生命體中如此,微觀世界中的「量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現象也被多次證實。
然而,不少人相信,只有人才能真正的關心他人,與之發生情感共鳴。然而,我們似乎誇大了人的這一功能。當別人握著你的手給予你安慰的時候,很可能他只是例行公事,而非真的感同身受。這樣例行公事的行為與程式編制出的行為有何區別?如果我們一定要區分這兩者的差別,未免犯了信源至上的錯誤。如果我們從資訊接收方來看,只要對方表露得不露痕跡,接收方是感受不到區別的。這樣看來,程式的欺騙行為和人類的作秀行為從傳播效果上而言的確殊途同歸。
讓我們回到著名的圖靈測試:如果機器能騙得了人認為它是人,那麼它就具有智慧。換言之,機器如果表現得智慧,我們便認為它是智慧的。雖然約翰.塞爾(John Searle)著名的「中文房間」論證(the Chinese room argument)指出機器智慧的欺騙性,然而只是取得了在質疑信源上的成功,卻未對交流的效果帶來實質性的挑戰。如果我們能夠接受「表現出的」智慧,為什麼就不能接受「表現出的」關心,「表現出的」信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