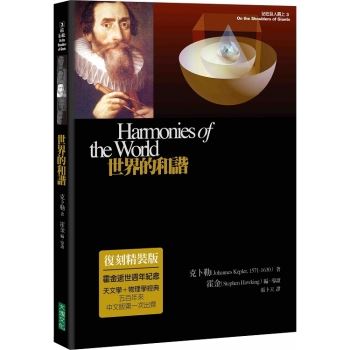【內文試閱】
第五卷:論天體運動完美的和諧以及由此得到的離心率、半徑和週期的起源
依據目前最為完善的天文學學說所建立的模型,以及業已取代托勒密、並被公認為正確的哥白尼和第谷•布拉赫的假說。
我正在進行一次神聖的討論,這是一首獻給上帝這位造物主的真正頌歌。我以為,虔誠不在於用大批公牛作犧牲給祂獻祭,也不在於用數不清的香料和肉桂給祂焚香,而在於首先自己領會祂的智慧是如何之高,能力是如何之大,善是如何之寬廣,然後再把這些傳授給別人。因為希望盡其所能為應當增色的東西增光添彩,而不去忌妒它的閃光之處,我把這看做至善之象徵;探尋一切可能使他美奐絕倫的東西,我把這看做非凡智慧之表現;履行他所頒佈的一切事務,我把這看作不可抗拒之偉力。
——蓋倫,《論人體各部分的用處》,第三卷
序言
關於這個發現,我二十二年前發現天球之間存在著五種正多面體時就曾預言過;在我見到托勒密的《和聲學》(Harmonica)之前就已經堅信不移了;遠在我對此確信無疑以前,我曾以本書第五卷的標題向我的朋友允諾過;十六年前,我曾在一本出版的著作中堅持要對它進行研究。為了這個發現,我已把我一生中最好的歲月獻給了天文學事業,為此,我曾拜訪過第谷•布拉赫,並選擇在布拉格定居。最後,至高至善的上帝開啟了我的心靈,激起了我強烈的渴望,延續了我的生命,增強了我精神的力量,還惠允兩位慷慨仁慈的皇帝以及上奧地利地區的長官們滿足了我其餘的要求。我想說的是,當我在天文學領域完成了足夠多的工作之後,我終於撥雲見日,發現它甚至比我曾經預期的還要真實:連同第三卷中所闡明的一切,和諧的全部本質都可以在天體運動中找到,而且它所呈現出來的並不是我頭腦中曾經設想的那種模式(這還不是最令我興奮的),而是一種非常完美的迥然不同的方式。正當重建天體運動這項極為艱苦繁複的工作使我進退維谷之時,閱讀托勒密的《和聲學》極大地增強了我對這項工作的興趣和熱情。這本書是以抄本的形式寄給我的,寄送人是巴伐利亞的總督約翰•格奧格•赫瓦特(John George Herward)先生,一個為推進哲學而生的學識淵博的人。出人意料的是,我驚奇地發現,這本書的幾乎整個第三卷在一五○○年前就已經討論了天體的和諧。不過在那個時候,天文學還遠沒有成熟,托勒密通過一種不幸的嘗試,可能已經使人陷入了絕望。他就像西塞羅(Cicero)筆下的西庇阿(Scipio),似乎講述了一個令人愜意的畢達哥拉斯之夢,卻沒有對哲學有所助益。然而醜陋的古代哲學竟能與時隔十五個世紀的我的想法完全一致,這極大地增強了我把這項工作繼續下去的力量。那麼多人的作用為何?事物的真正本 正是通過不同時代的不同闡釋者才把自身揭示給人類的。兩個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對自然的思索當中的人,竟對世界的形構有著同樣的想法,這種觀念上的一致正是上帝的點化(套用一句希伯來人的慣用語),因為他們並沒有互為對方的嚮導。從十八個月前透進來的第一縷曙光,到三個月前的一天的豁然開朗,再到幾天前思想中那顆明澈的太陽開始盡放光芒,我始終勇往直前,百折不回。我要縱情享受那神聖的狂喜,以坦誠的告白盡情嘲弄人類:我竊取了埃及人的金瓶,卻用它們在遠離埃及疆界的地方給我的上帝築就了一座聖所。如果你們寬恕我,我將感到欣慰;如果你們申斥我,我將默默忍受。總之書是寫成了,骰子已經擲下去了,人們是現在讀它,還是將來子孫後代讀它,這都無關緊要。既然上帝為了他的研究者已經等了六千年,那就讓它為讀者等上一百年吧。
在開始探討這些問題以前,我想先請讀者銘記蒂邁歐(Timaeus)這位異教哲學家在開始討論同樣問題時所提出的勸誡。基督徒應當帶著極大的讚美之情去學習這段話,而如果他們沒有遵照這些話去做,那就應當感到羞愧。這段話是這樣的:
蘇格拉底,凡是稍微有一點頭腦的人,在每件事情開始的時候總要求助於神,無論這件事情是大是小;我們也不例外,如果我們不是完全喪失理智的話,要想討論宇宙的本性,考察它的起源,或者要是沒有起源的話,它是如何存在的,我們當然也必須向男女眾神求助,祈求我們所說的話首先能夠得到諸神的首肯,其次也能為你所接受。
第五卷:論天體運動完美的和諧以及由此得到的離心率、半徑和週期的起源
依據目前最為完善的天文學學說所建立的模型,以及業已取代托勒密、並被公認為正確的哥白尼和第谷•布拉赫的假說。
我正在進行一次神聖的討論,這是一首獻給上帝這位造物主的真正頌歌。我以為,虔誠不在於用大批公牛作犧牲給祂獻祭,也不在於用數不清的香料和肉桂給祂焚香,而在於首先自己領會祂的智慧是如何之高,能力是如何之大,善是如何之寬廣,然後再把這些傳授給別人。因為希望盡其所能為應當增色的東西增光添彩,而不去忌妒它的閃光之處,我把這看做至善之象徵;探尋一切可能使他美奐絕倫的東西,我把這看做非凡智慧之表現;履行他所頒佈的一切事務,我把這看作不可抗拒之偉力。
——蓋倫,《論人體各部分的用處》,第三卷
序言
關於這個發現,我二十二年前發現天球之間存在著五種正多面體時就曾預言過;在我見到托勒密的《和聲學》(Harmonica)之前就已經堅信不移了;遠在我對此確信無疑以前,我曾以本書第五卷的標題向我的朋友允諾過;十六年前,我曾在一本出版的著作中堅持要對它進行研究。為了這個發現,我已把我一生中最好的歲月獻給了天文學事業,為此,我曾拜訪過第谷•布拉赫,並選擇在布拉格定居。最後,至高至善的上帝開啟了我的心靈,激起了我強烈的渴望,延續了我的生命,增強了我精神的力量,還惠允兩位慷慨仁慈的皇帝以及上奧地利地區的長官們滿足了我其餘的要求。我想說的是,當我在天文學領域完成了足夠多的工作之後,我終於撥雲見日,發現它甚至比我曾經預期的還要真實:連同第三卷中所闡明的一切,和諧的全部本質都可以在天體運動中找到,而且它所呈現出來的並不是我頭腦中曾經設想的那種模式(這還不是最令我興奮的),而是一種非常完美的迥然不同的方式。正當重建天體運動這項極為艱苦繁複的工作使我進退維谷之時,閱讀托勒密的《和聲學》極大地增強了我對這項工作的興趣和熱情。這本書是以抄本的形式寄給我的,寄送人是巴伐利亞的總督約翰•格奧格•赫瓦特(John George Herward)先生,一個為推進哲學而生的學識淵博的人。出人意料的是,我驚奇地發現,這本書的幾乎整個第三卷在一五○○年前就已經討論了天體的和諧。不過在那個時候,天文學還遠沒有成熟,托勒密通過一種不幸的嘗試,可能已經使人陷入了絕望。他就像西塞羅(Cicero)筆下的西庇阿(Scipio),似乎講述了一個令人愜意的畢達哥拉斯之夢,卻沒有對哲學有所助益。然而醜陋的古代哲學竟能與時隔十五個世紀的我的想法完全一致,這極大地增強了我把這項工作繼續下去的力量。那麼多人的作用為何?事物的真正本 正是通過不同時代的不同闡釋者才把自身揭示給人類的。兩個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對自然的思索當中的人,竟對世界的形構有著同樣的想法,這種觀念上的一致正是上帝的點化(套用一句希伯來人的慣用語),因為他們並沒有互為對方的嚮導。從十八個月前透進來的第一縷曙光,到三個月前的一天的豁然開朗,再到幾天前思想中那顆明澈的太陽開始盡放光芒,我始終勇往直前,百折不回。我要縱情享受那神聖的狂喜,以坦誠的告白盡情嘲弄人類:我竊取了埃及人的金瓶,卻用它們在遠離埃及疆界的地方給我的上帝築就了一座聖所。如果你們寬恕我,我將感到欣慰;如果你們申斥我,我將默默忍受。總之書是寫成了,骰子已經擲下去了,人們是現在讀它,還是將來子孫後代讀它,這都無關緊要。既然上帝為了他的研究者已經等了六千年,那就讓它為讀者等上一百年吧。
在開始探討這些問題以前,我想先請讀者銘記蒂邁歐(Timaeus)這位異教哲學家在開始討論同樣問題時所提出的勸誡。基督徒應當帶著極大的讚美之情去學習這段話,而如果他們沒有遵照這些話去做,那就應當感到羞愧。這段話是這樣的:
蘇格拉底,凡是稍微有一點頭腦的人,在每件事情開始的時候總要求助於神,無論這件事情是大是小;我們也不例外,如果我們不是完全喪失理智的話,要想討論宇宙的本性,考察它的起源,或者要是沒有起源的話,它是如何存在的,我們當然也必須向男女眾神求助,祈求我們所說的話首先能夠得到諸神的首肯,其次也能為你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