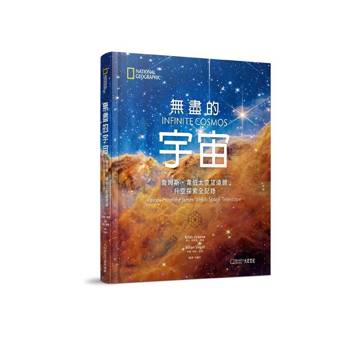序
史上最深邃的追尋
布萊恩・格林
Brian Greene
2010年的6月溫暖宜人,我站在紐約市閃爍的天際線包圍之下,被一件人類智慧的巨作深深吸引。太陽在砲臺公園(Battery Park)灑下金色的光芒時,我被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的全尺寸模型深深迷住了。這場世界科學祭(World Science Festival)的活動,吸引了許多充滿好奇心的人和天文愛好者前來探索人類知識的極限。一位年輕學生問了一個問題,讓我有點吃驚:「所以這就是我們要用來理解人類為什麼存在的方法嗎?」我面帶微笑,被這個突如其來的直率說法嚇了一跳:他一語道破了敬畏與科學的關連,而這正是我再熟悉不過的。正如這位學生所感覺到的,當時距離發射還有十幾年的韋伯太空望遠鏡,不僅預期將窺見遙遠的宇宙,同時也和所有志向遠大的挑戰一樣,將如同舉起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的本質。韋伯的計畫,展現了我們打算以何等的深度和廣度來了解自己和這個實在界的決心。
幾年後,我在位於馬里蘭州綠帶城(Greenbelt)的戈達德太空飛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擔任客座,當時韋伯望遠鏡就在這裡進行組裝。我看著團隊小心翼翼地移動兩片韋伯的六角形鍍金鏡面,為接下來一系列的測試做準備。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整部望遠鏡被封入巨大的消音室當中,接受強度大到足以致命的聲波震動測試,以確保望遠鏡能夠在發射過程中安然無恙。身為一名理論學家,我要面對的物理挑戰頂多就是偶爾弄斷鉛筆,或是罹患輕微的腕隧道症候群。至於設計一臺擁有大量活動零件的儀器,再仔細組裝成史上最強大的望遠鏡之一,而且企圖把這一整套精巧脆弱的器材裝到一架火箭上,發射到150萬公里外的太空,在那裡完成部署並正常運作──執行這樣的任務所需要的毅力簡直是史詩級的。
這樣一場英勇行動由資深專案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約翰・馬瑟(John Mather)領導,匯集數千名專業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專案經理人和外部人員的努力,於 2021 年耶誕節第一次面對真實的考驗。望遠鏡被小心地裝在亞利安5號火箭中,矗立在法屬圭亞那庫魯(Kourou)的發射臺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團隊成員屏息以待,25 年的籌備工作終於來到最後倒數十秒。引擎轟然作響,火箭升空,在那場完美的發射中,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把兩代天文學家的希望和夢想帶上了天際。
全世界的觀眾都鬆了一口氣,但參與計畫的人員很快又開始屏息了。按照計劃,接下來的六個月將會充滿各種焦慮。若亞利安5號發射軌跡不準確,望遠鏡需要多少燃料來修正?亞利安5號的裝載艙裡像摺紙一樣摺起來、跟網球場一樣大的遮陽罩,能在太空中順利展開嗎?望遠鏡能否適應僅受到少量陽光照射的寒冷環境?與地球通訊的系統是否能依計畫運作?這些只是望遠鏡可能失敗的眾多環節之一。
那麼,結果如何呢?
除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小故障在所難免之外,韋伯望遠鏡在整個過程達到預期中的最高標準,已經準備好要觀測更遙遠的宇宙與更久遠的過去了。
望遠鏡
光的速度是非常龐大的數值,快到能在一秒內繞地球七圈以上。即使如此,因為宇宙的尺度也非常龐大,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最遙遠天體,其實是早在幾十億年前就發出來的光。因此,我們捕捉並且分析這些光時,是在直接觀察不但極為遙遠、也是極為久遠的宇宙景象。這正是光的奇妙之處,也是像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JWST)這樣的儀器的能力所在。
無論是地球上的物體,還是遙遠的天體,它們產生或反射的光都會朝各個方向傳播。用量子物理的術語來說,物體上的每一個點都會發出許多光子,也就是一個個小小的能量包。望遠鏡能攔截到的光子愈多,物體上的每一個點看起來就愈亮,因此望遠鏡的設計重點之一,就是盡可能收集最多的光子。這個方法其實非常直觀:望遠鏡的鏡片愈大,收集到的光子數量就愈多。對於像 JWST 這類使用反射鏡來收集光子的望遠鏡而言,鏡面的面積愈大,能捕捉的光子也愈多。
哈伯太空望遠鏡(Hubble Space Telescope)的主鏡直徑為 2.4 公尺,總集光面積約為 4.5 平方公尺。而 JWST 的主鏡由 18 片六角形鏡面組成,每片鏡面直徑約為 1.3 公尺,總集光面積約 25 平方公尺——差不多是哈伯的六倍。這表示JWST接收到的光子中,大約有85%沒辦法被哈伯望遠鏡的鏡面捕捉到,由此可以說明JWST的集光能力為什麼強這麼多。
地面望遠鏡少了發射升空的難題,所以可以建造得更大,但它們在觀測時會受到地球上相對溫暖且紊亂的大氣層的干擾與扭曲。這一點對JWST要觀測的各種波長範圍尤其嚴重,也因此JWST被設計成必須部署在深遠的太空中,比月球的距離要遠得多。我來解釋一下。
雖然光速是固定的,但光的振動性質卻不是。光是一種波,科學家早在 19 世紀就已經了解到,波動愈慢,光就愈偏向紅色。因為光速不變,波動愈慢表示波長(光在每個波動所走的距離)愈長,而波長愈長,光的顏色就愈紅。人眼能偵測的光波範圍非常有限——從紅色到紫色——這恰好也是太陽發出的最強波段。在數百萬年的演化過程中,眼睛對白天能量最強的光波 (即可見光)最敏感的那些人,得以在無止境的生存競爭中獲勝。
然而,適合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眼,並未在觀測宇宙結構方面經過最佳化。各種天體發射或反射的波長範圍,往往超出了人眼能偵測的範圍。JWST 就是專門設計來偵測紅外線(波長比紅光還長,是人眼看不到的光),這一點對於研究早期宇宙和遙遠的恆星形成區尤其重要。此外,JWST 上的全套儀器不只能建構天體影像,還能像稜鏡一樣,把收集到的光分解成各種波長,也就是光譜,這對於分析光源的組成細節非常重要。
JWST 包含四個主要的探測儀器:近紅外線相機(NIRCam),這是觀測近紅外光(波長比可見光中的紅光稍長一點)的成像儀;近紅外線光譜儀(NIRSpec),同樣用來觀測近紅外光波段,但能把光分解成光譜;精細導星感測器/近紅外線相機和無縫光譜儀(FGS/NIRISS),這是望遠鏡的精密導星系統,也具備成像與光譜的功能;中紅外線儀器(MIRI),這是用於偵測紅外線波段的中段範圍的成像與光譜儀。
我們往往把紅外光與「熱」聯想在一起,因為溫暖的物體會發出這種肉眼看不到的輻射。這也是 JWST 在設計上的關鍵考量因素。為了避免受到自身熱輻射的干擾,望遠鏡必須保持在極冷的狀態。該怎麼保持?設計團隊採用了兩個互補的方法:第一,為 JWST 裝上一個巨大的遮陽罩,由五層金屬化塑膠膜所組成,能有效反射太陽光,並幫助望遠鏡散熱。第二,把 JWST 放置在一個非常特定的軌道上,這是最早由18 世紀數學家歐拉與拉格朗日計算出來的軌道,能讓望遠鏡穩定地維持在幾乎不變的環境條件中。我就不讓讀者看那些數學公式了(雖然一個程度不錯的高中生就能算出來),但可以用幾句話說明一下基本原理:對望遠鏡這樣相對小的物體來說,太陽與地球的重力會在幾個特定軌道上達成平衡,使望遠鏡穩定地維持在軌道上。這些特殊的位置中,有一個叫做第二拉格朗日點(L2),距離地球約 150 萬公里,JWST 就駐點在這裡。
更準確地說,JWST 並不是「位於」 L2 點,而是在L2點周圍繞行。這個繞行軌道可以讓望遠鏡避開地球和月球的陰影,讓太陽能板持續接收到陽光,而遮陽罩也能恆常地維持在極低溫的觀測條件下。這樣穩定的環境是望遠鏡能正常運作的必要條件,同時也因為它的一切移動都是由太陽和地球的重力引導,望遠鏡需要用到的燃料很少,而得以延長工作壽命。
然而,這個遠距離軌道也有缺點。如果望遠鏡離地球太遠,要是出了差錯就不可能派人前往維修。你可能記得,哈伯望遠鏡剛發射不久,科學家發現主鏡出了狀況(鏡片表面研磨弧度有偏差,大約是頭髮厚度的 1/50),會嚴重影響成像品質。1993 年,奮進號太空梭把太空人送到哈伯,修正了光學問題。但哈伯的軌道離地球僅約 525 公里,和將近 150 萬公里遠的JWST比起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倘若未來出現問題,就只能從地球進行遠端排解了。
史上最深邃的追尋
布萊恩・格林
Brian Greene
2010年的6月溫暖宜人,我站在紐約市閃爍的天際線包圍之下,被一件人類智慧的巨作深深吸引。太陽在砲臺公園(Battery Park)灑下金色的光芒時,我被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的全尺寸模型深深迷住了。這場世界科學祭(World Science Festival)的活動,吸引了許多充滿好奇心的人和天文愛好者前來探索人類知識的極限。一位年輕學生問了一個問題,讓我有點吃驚:「所以這就是我們要用來理解人類為什麼存在的方法嗎?」我面帶微笑,被這個突如其來的直率說法嚇了一跳:他一語道破了敬畏與科學的關連,而這正是我再熟悉不過的。正如這位學生所感覺到的,當時距離發射還有十幾年的韋伯太空望遠鏡,不僅預期將窺見遙遠的宇宙,同時也和所有志向遠大的挑戰一樣,將如同舉起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的本質。韋伯的計畫,展現了我們打算以何等的深度和廣度來了解自己和這個實在界的決心。
幾年後,我在位於馬里蘭州綠帶城(Greenbelt)的戈達德太空飛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擔任客座,當時韋伯望遠鏡就在這裡進行組裝。我看著團隊小心翼翼地移動兩片韋伯的六角形鍍金鏡面,為接下來一系列的測試做準備。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整部望遠鏡被封入巨大的消音室當中,接受強度大到足以致命的聲波震動測試,以確保望遠鏡能夠在發射過程中安然無恙。身為一名理論學家,我要面對的物理挑戰頂多就是偶爾弄斷鉛筆,或是罹患輕微的腕隧道症候群。至於設計一臺擁有大量活動零件的儀器,再仔細組裝成史上最強大的望遠鏡之一,而且企圖把這一整套精巧脆弱的器材裝到一架火箭上,發射到150萬公里外的太空,在那裡完成部署並正常運作──執行這樣的任務所需要的毅力簡直是史詩級的。
這樣一場英勇行動由資深專案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約翰・馬瑟(John Mather)領導,匯集數千名專業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專案經理人和外部人員的努力,於 2021 年耶誕節第一次面對真實的考驗。望遠鏡被小心地裝在亞利安5號火箭中,矗立在法屬圭亞那庫魯(Kourou)的發射臺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團隊成員屏息以待,25 年的籌備工作終於來到最後倒數十秒。引擎轟然作響,火箭升空,在那場完美的發射中,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把兩代天文學家的希望和夢想帶上了天際。
全世界的觀眾都鬆了一口氣,但參與計畫的人員很快又開始屏息了。按照計劃,接下來的六個月將會充滿各種焦慮。若亞利安5號發射軌跡不準確,望遠鏡需要多少燃料來修正?亞利安5號的裝載艙裡像摺紙一樣摺起來、跟網球場一樣大的遮陽罩,能在太空中順利展開嗎?望遠鏡能否適應僅受到少量陽光照射的寒冷環境?與地球通訊的系統是否能依計畫運作?這些只是望遠鏡可能失敗的眾多環節之一。
那麼,結果如何呢?
除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小故障在所難免之外,韋伯望遠鏡在整個過程達到預期中的最高標準,已經準備好要觀測更遙遠的宇宙與更久遠的過去了。
望遠鏡
光的速度是非常龐大的數值,快到能在一秒內繞地球七圈以上。即使如此,因為宇宙的尺度也非常龐大,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最遙遠天體,其實是早在幾十億年前就發出來的光。因此,我們捕捉並且分析這些光時,是在直接觀察不但極為遙遠、也是極為久遠的宇宙景象。這正是光的奇妙之處,也是像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JWST)這樣的儀器的能力所在。
無論是地球上的物體,還是遙遠的天體,它們產生或反射的光都會朝各個方向傳播。用量子物理的術語來說,物體上的每一個點都會發出許多光子,也就是一個個小小的能量包。望遠鏡能攔截到的光子愈多,物體上的每一個點看起來就愈亮,因此望遠鏡的設計重點之一,就是盡可能收集最多的光子。這個方法其實非常直觀:望遠鏡的鏡片愈大,收集到的光子數量就愈多。對於像 JWST 這類使用反射鏡來收集光子的望遠鏡而言,鏡面的面積愈大,能捕捉的光子也愈多。
哈伯太空望遠鏡(Hubble Space Telescope)的主鏡直徑為 2.4 公尺,總集光面積約為 4.5 平方公尺。而 JWST 的主鏡由 18 片六角形鏡面組成,每片鏡面直徑約為 1.3 公尺,總集光面積約 25 平方公尺——差不多是哈伯的六倍。這表示JWST接收到的光子中,大約有85%沒辦法被哈伯望遠鏡的鏡面捕捉到,由此可以說明JWST的集光能力為什麼強這麼多。
地面望遠鏡少了發射升空的難題,所以可以建造得更大,但它們在觀測時會受到地球上相對溫暖且紊亂的大氣層的干擾與扭曲。這一點對JWST要觀測的各種波長範圍尤其嚴重,也因此JWST被設計成必須部署在深遠的太空中,比月球的距離要遠得多。我來解釋一下。
雖然光速是固定的,但光的振動性質卻不是。光是一種波,科學家早在 19 世紀就已經了解到,波動愈慢,光就愈偏向紅色。因為光速不變,波動愈慢表示波長(光在每個波動所走的距離)愈長,而波長愈長,光的顏色就愈紅。人眼能偵測的光波範圍非常有限——從紅色到紫色——這恰好也是太陽發出的最強波段。在數百萬年的演化過程中,眼睛對白天能量最強的光波 (即可見光)最敏感的那些人,得以在無止境的生存競爭中獲勝。
然而,適合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眼,並未在觀測宇宙結構方面經過最佳化。各種天體發射或反射的波長範圍,往往超出了人眼能偵測的範圍。JWST 就是專門設計來偵測紅外線(波長比紅光還長,是人眼看不到的光),這一點對於研究早期宇宙和遙遠的恆星形成區尤其重要。此外,JWST 上的全套儀器不只能建構天體影像,還能像稜鏡一樣,把收集到的光分解成各種波長,也就是光譜,這對於分析光源的組成細節非常重要。
JWST 包含四個主要的探測儀器:近紅外線相機(NIRCam),這是觀測近紅外光(波長比可見光中的紅光稍長一點)的成像儀;近紅外線光譜儀(NIRSpec),同樣用來觀測近紅外光波段,但能把光分解成光譜;精細導星感測器/近紅外線相機和無縫光譜儀(FGS/NIRISS),這是望遠鏡的精密導星系統,也具備成像與光譜的功能;中紅外線儀器(MIRI),這是用於偵測紅外線波段的中段範圍的成像與光譜儀。
我們往往把紅外光與「熱」聯想在一起,因為溫暖的物體會發出這種肉眼看不到的輻射。這也是 JWST 在設計上的關鍵考量因素。為了避免受到自身熱輻射的干擾,望遠鏡必須保持在極冷的狀態。該怎麼保持?設計團隊採用了兩個互補的方法:第一,為 JWST 裝上一個巨大的遮陽罩,由五層金屬化塑膠膜所組成,能有效反射太陽光,並幫助望遠鏡散熱。第二,把 JWST 放置在一個非常特定的軌道上,這是最早由18 世紀數學家歐拉與拉格朗日計算出來的軌道,能讓望遠鏡穩定地維持在幾乎不變的環境條件中。我就不讓讀者看那些數學公式了(雖然一個程度不錯的高中生就能算出來),但可以用幾句話說明一下基本原理:對望遠鏡這樣相對小的物體來說,太陽與地球的重力會在幾個特定軌道上達成平衡,使望遠鏡穩定地維持在軌道上。這些特殊的位置中,有一個叫做第二拉格朗日點(L2),距離地球約 150 萬公里,JWST 就駐點在這裡。
更準確地說,JWST 並不是「位於」 L2 點,而是在L2點周圍繞行。這個繞行軌道可以讓望遠鏡避開地球和月球的陰影,讓太陽能板持續接收到陽光,而遮陽罩也能恆常地維持在極低溫的觀測條件下。這樣穩定的環境是望遠鏡能正常運作的必要條件,同時也因為它的一切移動都是由太陽和地球的重力引導,望遠鏡需要用到的燃料很少,而得以延長工作壽命。
然而,這個遠距離軌道也有缺點。如果望遠鏡離地球太遠,要是出了差錯就不可能派人前往維修。你可能記得,哈伯望遠鏡剛發射不久,科學家發現主鏡出了狀況(鏡片表面研磨弧度有偏差,大約是頭髮厚度的 1/50),會嚴重影響成像品質。1993 年,奮進號太空梭把太空人送到哈伯,修正了光學問題。但哈伯的軌道離地球僅約 525 公里,和將近 150 萬公里遠的JWST比起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倘若未來出現問題,就只能從地球進行遠端排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