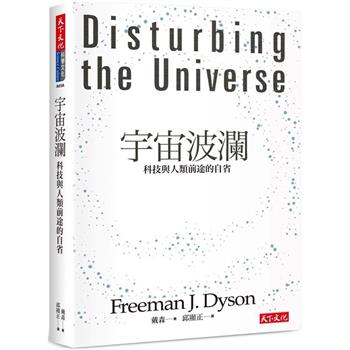轟炸致勝說
懷頓基地可以說是戰時軍事基地醜陋的代表,一窪又一窪的水坑、一座又一座的軍營,倉庫裡堆滿了炸彈,還有一大堆破損不堪、不值得修理的裝備。連續兩個月,83中隊每個晚上都出勤,只要天氣不是糟到完全無法飛行,就會載滿炸彈去轟炸柏林。但平均每一次任務會損失一架飛機,而每架蘭開斯特轟炸機上,都載有七名機員。
轟炸機指揮部那年冬天集中火力,把作戰能量推到極致,對柏林展開疲勞轟炸;因為在英美盟軍主力開進歐洲之前,這是給與德國戰時經濟致命一擊的最後機會了。那些駕著蘭開斯特轟炸機的少年軍,所被告知的是:柏林這一仗是大戰勝負所繫,而盟軍正節節勝利。
我不清楚他們當中有多少人相信這番說法,我只知道他們聽到的都是騙人的!截至1944年1月,我方都節節失利。我曾經看過轟炸成果的報告,圖表顯示炸彈散布範圍極廣,而我們損失的轟炸機數量亦急遽上升—我們這種持續性的攻擊根本沒能左右戰局!沒錯,柏林市區裡有各種重要的軍事工業與指揮中心,問題是,轟炸機指揮部沒有試圖找出這些重要工業或行政中心的個別所在,以施行定點轟炸;只是像西北雨一樣投下燃燒彈,只求火力集中攻擊市區的某一地帶,再加上小部分高爆炸藥的轟炸,來阻撓消防隊滅火。其實這種一成不變的攻擊方法,人家只要重點加強防守即可,重要的工廠加派消防隊保護,在最短時間內,把落於危險地帶的燃燒彈大火撲滅;至於一般民眾和商店就任其焚燒。所以常見的是,轟炸機指揮部「摧毀」了一座城市,但是幾週以後的照相偵察結果顯示,那些工廠仍然在大火過後的殘垣斷瓦中照常生產。
大戰當中,轟炸機指揮部的燃燒攻勢只有兩次獲致出奇的成功。第一次是1943年7月在漢堡,我們在一處人口稠密的地區製造了許多火災,以致串聯成一場「火暴」(fire storm)—火焰像颱風過境,所經之處都夷為平地,燒死了四萬多人。我們任何一次攻擊所造成的摧毀效果,都不及火暴功效的十分之一;如果我們要在柏林戰場贏得有意義的軍事勝利,就得在那裡製造火暴。很明顯的,若有巨大火暴燒過柏林的話,必定可以實現那群轟炸機指揮部創辦人的夢想—他們的口號是「空戰致勝」;但是,到了1944年1月,我知道這已是不可能實現的了。火暴要出現,轟炸機必須能超級準確的命中目標,並且沒有地面防禦的干擾。可是,我們天天疲勞轟炸的結果,柏林仍是一天強似一天,炸彈的攻擊則愈來愈零散。我到懷頓基地一年之後,也就是德國遭盟軍圍勦,開始搖搖欲墜的時候,才又成功引發另一次的火暴,那是在1945年2月的德勒斯登。
推翻官方說法
我以民間科學家的身分奉派到轟炸機指揮總部,士別三日,我早已不是昔日那位宇宙合一教的吳下阿蒙。我隸屬於作業研究部門下的小組,負責擔任總司令的科學參謀,專門從事統計研究,任務是要找出,飛行人員的經驗和飛機遭擊落的機率之間是否有關聯。
指揮部有一個信念,並且對機員一再耳提面命,同時官方的傳播媒體也一再對大眾灌輸這個觀念—機員經驗愈豐富,出勤後生還的機率愈高。機員聽到的精神教育是:一旦熬過了頭五次或頭十次的勤務,你就會抓到訣竅,得以更快發現德軍的夜行戰鬥機,自然就更有圓滿達成任務並生還的把握。毫無疑問的,這個信念對提升少年軍的士氣有莫大的幫助。況且,中隊長又都是些身經百戰的生還者,更是打從心底相信他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完全是因為個人的純熟技術與堅強意志所致,而非單靠運氣。他們說的或許沒錯,在大戰初期,經驗豐富的飛行員的確存活率高出許多。我奉派到轟炸機指揮部之前,作業研究部曾進行研究,證實了存活率與經驗成正相關的官方說法,而這項研究結果也廣受各方接納。
很不幸,當我重複上述研究,比對更周密的統計資料時,我發現實情完全改觀。我的分析是根據完整的紀錄,審慎刪除一些可疑關聯造成的誤導,例如:新手常被委派低難度的任務。結果很明顯,機員折損率與經驗成負相關的關係在1942年成立,但到1944年已不復存在。當然還是有許多案例顯示:經驗老到的機員,英雄式的將受重創的飛機飛回家;而在類似的情境下,新手可能已人機俱焚了。然而,這些案例並不能動搖統計結果—經驗生疏或嫻熟,對生存的貢獻根本看不出來。譬如在1916年索母河戰役(Battle of Somme)中,機員一旦陷入德軍機關槍的火網,不論是菜鳥還是老鳥,一律獲得平等對待,也就是遭徹底殲滅!
經驗與傷亡率無關的發現,照理說,應該已經讓指揮部有所警惕,並且嘉獎我們發現新的結果。在作業研究部,我們找到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嫻熟的經驗,也無法保證轟炸機員能平安回來,而且我們也確信這個理論正確無誤。理論的名稱叫「頂射砲」(Upward-Firing Gun)。每架蘭開斯特轟炸機除駕駛艙的三名機員外,尚配屬四名機員持續不斷對空搜索,找尋戰鬥機的行蹤:中座是導航員和炸彈瞄準員;另外兩名砲手,一名在機尾,一名在中上部位的砲塔。機身的正下方雖是個盲點,但配備傳統前射機砲的戰鬥機,不可能從正下方仰攻轟炸機並將之擊落,因為尚未接近就早被發現了。
但是,德軍的戰鬥機有愈來愈多不再配備傳統武器,而是架設砲口垂直向上的大砲,利用簡單的潛望鏡偵察瞄準器,飛行員可以悄悄飛到轟炸機的正下方,仔細瞄準後射擊。德軍戰鬥機飛行員只要小心別被轟炸機爆裂的大型碎片擊中就好了。
缺乏道德素養?
由於83中隊是歷史最悠久的前導機中隊,隊中經驗老到的機員比例也較其他中隊高出許多。正常的中隊勤務分配下,一名機員服役時,大約要出三十次任務。在大戰的中期,損失率大約4%。換句話說,一名機員在正常服役年限下,十中有三仍會存活。至於簽下雙役(double tour)的前導機員,則須出勤六十次。那麼退役時,大約十一名當中,只有一名可以存活。在1943年至1944年的冬天,因為密集轟炸柏林,損失率更是遠高於平均值,活著退役的人也就更少了。
我從總司令部來到懷頓基地,考察各種戰鬥機反制雷達的運作情形。雷達功能仍很正常,只是沒有什麼用,因為它們無法分辨出戰鬥機和轟炸機。此行另外一個目的,是蒐集有助於我們研究經驗與損失率相關性的資訊。我滿心指望可以和一些有經驗的機員交談,蒐集第一手印象,並稍微體會一下柏林夜戰的實況。
可是不久後,情勢即明朗化,機員和平民旁觀者之間,根本不可能有什麼深刻的交談,尤其存活率這個話題在此間已是一大禁忌。整個空軍官僚的傳統想法,就是要官兵想都不要去想死傷人數多寡的問題,因為想太多容易造成精神崩潰;而若有官兵和其他同僚談到這些話題,對中隊的訓練更是一大威脅。所以指揮部裡任何討論到存活率的文件,統統受到嚴密的監視,以防流到中隊部。中隊的傳統信條是:「不問原因何在,只求實踐履行,為國犧牲」。
中隊部倒沒有禁止官兵和我交談,官兵們高興和我說什麼、說多少都可以。但是他們能對我說什麼?我又能告訴他們什麼?我們彼此間彷彿有一條鴻溝相隔,他們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年紀和我相若,然而他們已經出生入死三十幾趟,幸運的話,後面還能碰上另外三十幾趟。我則完全不同,我沒有經歷過這種生死交關,以後也不會經歷。他們知道(我也曉得他們知道)我是那種接受學院教育的孩子,戰時可以受派前往一些輕鬆的、沒什麼危險的單位。同是二十歲,命運卻有如此天淵之別的二個年輕人,能談些什麼重要的事情,不想可知。
摘自《宇宙波瀾》〈少年十字軍〉
懷頓基地可以說是戰時軍事基地醜陋的代表,一窪又一窪的水坑、一座又一座的軍營,倉庫裡堆滿了炸彈,還有一大堆破損不堪、不值得修理的裝備。連續兩個月,83中隊每個晚上都出勤,只要天氣不是糟到完全無法飛行,就會載滿炸彈去轟炸柏林。但平均每一次任務會損失一架飛機,而每架蘭開斯特轟炸機上,都載有七名機員。
轟炸機指揮部那年冬天集中火力,把作戰能量推到極致,對柏林展開疲勞轟炸;因為在英美盟軍主力開進歐洲之前,這是給與德國戰時經濟致命一擊的最後機會了。那些駕著蘭開斯特轟炸機的少年軍,所被告知的是:柏林這一仗是大戰勝負所繫,而盟軍正節節勝利。
我不清楚他們當中有多少人相信這番說法,我只知道他們聽到的都是騙人的!截至1944年1月,我方都節節失利。我曾經看過轟炸成果的報告,圖表顯示炸彈散布範圍極廣,而我們損失的轟炸機數量亦急遽上升—我們這種持續性的攻擊根本沒能左右戰局!沒錯,柏林市區裡有各種重要的軍事工業與指揮中心,問題是,轟炸機指揮部沒有試圖找出這些重要工業或行政中心的個別所在,以施行定點轟炸;只是像西北雨一樣投下燃燒彈,只求火力集中攻擊市區的某一地帶,再加上小部分高爆炸藥的轟炸,來阻撓消防隊滅火。其實這種一成不變的攻擊方法,人家只要重點加強防守即可,重要的工廠加派消防隊保護,在最短時間內,把落於危險地帶的燃燒彈大火撲滅;至於一般民眾和商店就任其焚燒。所以常見的是,轟炸機指揮部「摧毀」了一座城市,但是幾週以後的照相偵察結果顯示,那些工廠仍然在大火過後的殘垣斷瓦中照常生產。
大戰當中,轟炸機指揮部的燃燒攻勢只有兩次獲致出奇的成功。第一次是1943年7月在漢堡,我們在一處人口稠密的地區製造了許多火災,以致串聯成一場「火暴」(fire storm)—火焰像颱風過境,所經之處都夷為平地,燒死了四萬多人。我們任何一次攻擊所造成的摧毀效果,都不及火暴功效的十分之一;如果我們要在柏林戰場贏得有意義的軍事勝利,就得在那裡製造火暴。很明顯的,若有巨大火暴燒過柏林的話,必定可以實現那群轟炸機指揮部創辦人的夢想—他們的口號是「空戰致勝」;但是,到了1944年1月,我知道這已是不可能實現的了。火暴要出現,轟炸機必須能超級準確的命中目標,並且沒有地面防禦的干擾。可是,我們天天疲勞轟炸的結果,柏林仍是一天強似一天,炸彈的攻擊則愈來愈零散。我到懷頓基地一年之後,也就是德國遭盟軍圍勦,開始搖搖欲墜的時候,才又成功引發另一次的火暴,那是在1945年2月的德勒斯登。
推翻官方說法
我以民間科學家的身分奉派到轟炸機指揮總部,士別三日,我早已不是昔日那位宇宙合一教的吳下阿蒙。我隸屬於作業研究部門下的小組,負責擔任總司令的科學參謀,專門從事統計研究,任務是要找出,飛行人員的經驗和飛機遭擊落的機率之間是否有關聯。
指揮部有一個信念,並且對機員一再耳提面命,同時官方的傳播媒體也一再對大眾灌輸這個觀念—機員經驗愈豐富,出勤後生還的機率愈高。機員聽到的精神教育是:一旦熬過了頭五次或頭十次的勤務,你就會抓到訣竅,得以更快發現德軍的夜行戰鬥機,自然就更有圓滿達成任務並生還的把握。毫無疑問的,這個信念對提升少年軍的士氣有莫大的幫助。況且,中隊長又都是些身經百戰的生還者,更是打從心底相信他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完全是因為個人的純熟技術與堅強意志所致,而非單靠運氣。他們說的或許沒錯,在大戰初期,經驗豐富的飛行員的確存活率高出許多。我奉派到轟炸機指揮部之前,作業研究部曾進行研究,證實了存活率與經驗成正相關的官方說法,而這項研究結果也廣受各方接納。
很不幸,當我重複上述研究,比對更周密的統計資料時,我發現實情完全改觀。我的分析是根據完整的紀錄,審慎刪除一些可疑關聯造成的誤導,例如:新手常被委派低難度的任務。結果很明顯,機員折損率與經驗成負相關的關係在1942年成立,但到1944年已不復存在。當然還是有許多案例顯示:經驗老到的機員,英雄式的將受重創的飛機飛回家;而在類似的情境下,新手可能已人機俱焚了。然而,這些案例並不能動搖統計結果—經驗生疏或嫻熟,對生存的貢獻根本看不出來。譬如在1916年索母河戰役(Battle of Somme)中,機員一旦陷入德軍機關槍的火網,不論是菜鳥還是老鳥,一律獲得平等對待,也就是遭徹底殲滅!
經驗與傷亡率無關的發現,照理說,應該已經讓指揮部有所警惕,並且嘉獎我們發現新的結果。在作業研究部,我們找到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嫻熟的經驗,也無法保證轟炸機員能平安回來,而且我們也確信這個理論正確無誤。理論的名稱叫「頂射砲」(Upward-Firing Gun)。每架蘭開斯特轟炸機除駕駛艙的三名機員外,尚配屬四名機員持續不斷對空搜索,找尋戰鬥機的行蹤:中座是導航員和炸彈瞄準員;另外兩名砲手,一名在機尾,一名在中上部位的砲塔。機身的正下方雖是個盲點,但配備傳統前射機砲的戰鬥機,不可能從正下方仰攻轟炸機並將之擊落,因為尚未接近就早被發現了。
但是,德軍的戰鬥機有愈來愈多不再配備傳統武器,而是架設砲口垂直向上的大砲,利用簡單的潛望鏡偵察瞄準器,飛行員可以悄悄飛到轟炸機的正下方,仔細瞄準後射擊。德軍戰鬥機飛行員只要小心別被轟炸機爆裂的大型碎片擊中就好了。
缺乏道德素養?
由於83中隊是歷史最悠久的前導機中隊,隊中經驗老到的機員比例也較其他中隊高出許多。正常的中隊勤務分配下,一名機員服役時,大約要出三十次任務。在大戰的中期,損失率大約4%。換句話說,一名機員在正常服役年限下,十中有三仍會存活。至於簽下雙役(double tour)的前導機員,則須出勤六十次。那麼退役時,大約十一名當中,只有一名可以存活。在1943年至1944年的冬天,因為密集轟炸柏林,損失率更是遠高於平均值,活著退役的人也就更少了。
我從總司令部來到懷頓基地,考察各種戰鬥機反制雷達的運作情形。雷達功能仍很正常,只是沒有什麼用,因為它們無法分辨出戰鬥機和轟炸機。此行另外一個目的,是蒐集有助於我們研究經驗與損失率相關性的資訊。我滿心指望可以和一些有經驗的機員交談,蒐集第一手印象,並稍微體會一下柏林夜戰的實況。
可是不久後,情勢即明朗化,機員和平民旁觀者之間,根本不可能有什麼深刻的交談,尤其存活率這個話題在此間已是一大禁忌。整個空軍官僚的傳統想法,就是要官兵想都不要去想死傷人數多寡的問題,因為想太多容易造成精神崩潰;而若有官兵和其他同僚談到這些話題,對中隊的訓練更是一大威脅。所以指揮部裡任何討論到存活率的文件,統統受到嚴密的監視,以防流到中隊部。中隊的傳統信條是:「不問原因何在,只求實踐履行,為國犧牲」。
中隊部倒沒有禁止官兵和我交談,官兵們高興和我說什麼、說多少都可以。但是他們能對我說什麼?我又能告訴他們什麼?我們彼此間彷彿有一條鴻溝相隔,他們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年紀和我相若,然而他們已經出生入死三十幾趟,幸運的話,後面還能碰上另外三十幾趟。我則完全不同,我沒有經歷過這種生死交關,以後也不會經歷。他們知道(我也曉得他們知道)我是那種接受學院教育的孩子,戰時可以受派前往一些輕鬆的、沒什麼危險的單位。同是二十歲,命運卻有如此天淵之別的二個年輕人,能談些什麼重要的事情,不想可知。
摘自《宇宙波瀾》〈少年十字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