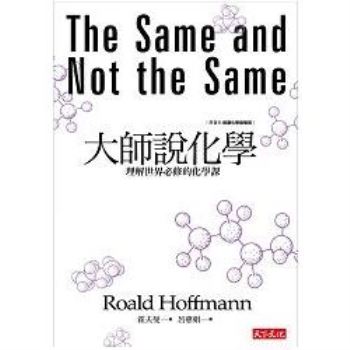第2 章 你是誰?
化學家在面對任何新樣品,譬如:以天價從月球表面帶回的塵土、從街上買回的不純麻藥、從一千隻蟑螂腺體中抽出的長生不老藥,第一個問題總是:「我得到的是什麼?」這個疑問可能比一般人想像的還複雜;因為在現實世界裡,沒有一種物質是純的。你仔細觀察周遭最純的物質,譬如矽晶片、精糖或藥物,你會發現這所謂的「純物質」中,存有百萬分之若干的物質,是你或許不想知道的雜質。
其實物質都不純,尤其是天然物,一般來說,天然物比合成物更不純。的確如此。葡萄酒中已經鑑定出大約九百種揮發性芳香成分;品酒專家能辨識出著名的德國莫色耳(Moselle)葡萄酒,即是由於它的混合成分(當然是指天然化合物,還有別的嗎?)別具特殊風味與香氣。令人好奇的是,雖然酒的成分是可定量的化學物,但它的風味與香氣,卻始終令化學家捉摸不清,還得倚賴味覺和嗅覺靈敏的品酒師,才能把正確的酒挑出來。
為什麼天然物不純呢?因為生物是很複雜的,它們是演化的產物。你需要上千個化學反應和無數的化學物,才能使葡萄樹或你的身體運作。並且,大自然是不斷嘗試的修補匠,確保動植物存活的運行法則,是祂數百萬年以來隨機實驗的結果。因而,生命織錦上的每一處,都呈現出繽紛撩亂的分子形狀與色彩。我們眼前任何運作中的事物,都是歷經彼此的揀選,再由大自然的生存實驗錘鍊成形的。
因此,我們真正要問的不再是「這是什麼?」而是「這裡面有多少這東西?」我們把物質的組成成分分開來看,每一成分就是一種化合物;它們是穩定黏結在一起的原子群,而這樣一群原子就叫做分子。純化合物是指由完全相同的分子聚集而成的物質。每種化合物的性質都不同,就像糖和鹽,兩者都是能溶於水的白色結晶體,但是我們可以輕易利用其他的物理、化學或生物性質來區別它們。
把物質的成分分離出來後,我們要鑑定這些化合物的結構。對化學家而言,結構的意義是指:純化合物中含有哪些原子,這些原子如何相互連接,以及它們在空間中如何排列。讓我們先從物質的分離開始探討吧!我恰巧也是礦物蒐藏者;次頁的圖2.1顯示的是自然界形成礦物的一種方式。這是長在長刃狀重晶石上的淡紫色螢石,這塊標本採自德國黑森林區。如果你的一生能像地質年代那麼長久,在某些條件下,你會發現物質自然相互分離,螢石晶體就是這樣形成的。這種現象就稱為部分結晶。不過,大多數化學家無法等上數千年之久。如果僅歷時五年(差不多是取得博士學位所需的時間),或許還能等等看。所以人類需要較快速的技術,因此有人發明了各種儀器來分離物質。
第43 章 為什麼科學家不宜治國?
如果你傾聽科學家私底下的隨興閒聊,會聽到一些八卦消息,例如某人將搬遷到某處去的傳聞、及大嘆研究經費取得不易等等。但換個場合,他們會聲稱科學的理性,並且照例表示反對政客,有時還會對於有點「軟性」的藝術和人文話題,表現出不屑的態度。他們認為只要把科學的理性思維應用於治國,全世界的問題和爭議或許就此一掃而空了。
這些言談可視為科學家自私的兄弟情,我們在此先不談。其他有大半的談話內容,透露出原始而有瑕疵的世界觀,一種把文化與政治系統橫切的謬誤見解。然而我們不確定柏拉圖是否會同意由這些庸俗的科學家來擔任哲學家皇帝,這是把柏拉圖一些單純信念套用在假設為合理的事物上,裝扮出現代模樣。
現代科學是西歐一項成功的社會發明,而且這項成功著實令人不可思議;它是能有效獲取世界上各種可靠知識,並用來改造世界的大事業。居於這樁事業核心的是:對大自然和我們關心的現象,做仔細的觀察。例如科學家會去探尋使泰爾紫呈現顏色的分子,或是探究如何修改這個分子,以達到更鮮亮的紫色或藍色。
在科學家的世界,複雜的事物都經過分解而簡化。這和把事物數學化的過程一樣,也就是所謂的分析(當然不是指化學上的)。無論是在發現或創造的過程中,科學家通常會先設定研究範圍,以便從中獲得複雜和令人驚訝的結果。而且無疑的,在這種範圍裡,分析法是可行的。科學家從分析當中獲得「泰爾紫中所含的染料,有特定結構」的解答,所以「被關起來的貓熊繁殖能力受限」也必有原因。科學家承認,能觀察到的因素或作用,或許是由好多個因素造成的;但是不管這些因素有多複雜,總有受過完善訓練的聰明科學家能把它分析、解開;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再以全世界共通的語言(不流利的英語)相互交換訊息。
讓我們把這個小心構築的科學家世界,和情緒上偶然的實際表現,或人類的風俗習慣互做對比。試問,年輕人的竊盜習慣可有唯一的原因?為什麼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或在前南斯拉夫,會出現手足相殘的情形?浪漫的愛情可有什麼邏輯?我們是否應有分秒不差的行動時程表?
我們發現,外面的世界有許多事物很難用簡化的(或甚至是複雜的)科學分析來處理。這個世界、我們的生活,事實上都傾向於透過倫理與道德的辯論,來取得正義與同情。清楚陳述問題的癥結、變通辦法和後果是有用的,就像在有時漫無目標的爭論中,會出現道德立場的對話,而人們可以藉此痛快吐露真言。正是這種宣洩,使參與式民主政治得以運作。科學家宣稱任何問題都有合理的解答;但事實上,個人和社會的問題並不能用科學家主張的方式解決。
在我的經驗裡,科學家多傾向於凡事應有和平理性的主張。因為在他們的研究工作上,仔細分析的方式行得通;而且他們對我們生存的世界充滿的複雜性,感到迷惑甚至傷心,所以他們天真的追求一種夢想,相信人類的紊亂情感和所有行動,都是受某些理性原則監控,而這些原則仍有待發現。
令人好奇的是,想必會遭科學排擠的宗教,竟然也提出類似的(但讓我很不滿意的)世界觀。科學家傾向用黑與白來看待這世界,希望那些在真實生活裡無時無刻不闖入我們意識中的灰色地帶,消失不見。而且,只要真實世界裡的實行者和製造者(其中最糟的那些,我們稱為政客),肯聽從我們的想法,這個世界就會朝正途發展。
不過,邇來我們已親眼目睹一個支持科學家或技術官僚來經營世界的夢想破滅了,那就是「馬克思主義」。不管它征服的是哪種文化(蘇俄、中國或古巴),馬克思主義不僅證明了它在經濟上行不通,也證明了它會導致無盡的腐敗貪婪,證明它已誘使公正社會的基礎核心墮落。科學家並不喜歡聽到這種論調,但是馬克思主義確實是「科學」的社會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擬出了一種信仰,這種信仰預言了某種社會科學的到臨。他們的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將無止境的進步與發展」的神話為動力,而由人類以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來改造社會,鑄造夢幻國度。
這麼說來,要是科學家不去治理這個世界,那該立身何處呢?就我看來,科學家最好不要從政,但是仍然致力與聞政治。如此,他們就會受到激發,發出理性之聲,對大眾提出睿智的忠告,並對日漸不合理的做法施以反擊。他們的能力恰好能扮演好這種角色。但是若由科學家掌權,我認為科學家那種以為只有自己才具備理性的傲慢態度,很可能導致他們不自覺的逾越分際。
我曉得我把實際的情形誇大了。其實,如果要說科學家有什麼不對,應該是他們對於政治參與得不夠。一旦他們走入政治舞台,也許並不比其他從事政治的人好到哪裡,但也壞不到哪裡。舉例來說,法國有科學家和工程師從政的傳統,例如從拉札爾.卡諾(Lazare Carnot)和他的孫子沙第.卡諾(Sadi Carnot,熱力學第二定律創始人)一直到我的博士後研究生德瓦蓋(Alain Devaquet,曾任法國教育部長)。再說,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的缺點或成就,也不該歸因於她的化學學士學位。
第45 章 化學教育
對我而言,農藥「阿拉爾」的論戰具有使人謙卑,以及教育的和訓示的意義。它是一個機會教育,而不是讓我們趁機去反對環境學家。我就從中學習到一些化學,我也從印度的博帕爾事故中學到一些,我還打算從下一個化學災難中再學習一些。因為,當知識伴隨某些重要事物(像是災難、人的遺體,甚至是淫穢可恥的事物)出現時,人們的心智才會打開。所以,就教育的意義來說,我們可以從發生的事中獲得知識。
這麼一談,我們已經進入教育的話題。我認為教育是民主政治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其實,我對科學文盲的關心,並非著眼於它限制了我們人類勢力的基礎,或是對我們在全球經濟競爭力上的影響;我感到憂心的,在於它代表教育失敗。我有以下兩點說明。首先,要是我們不了解周遭世界運作(尤其是人類製造添加的東西)的基本道理,就會被疏離於環境之外。無知所導致的疏離,會使人貧乏,使我們感到無能為力也沒有行動力。要是不了解這個世界,我們可能會發明出神祕的事物和新的神祇,就好像很久以前人們對閃電和日月食,以及聖愛爾摩之火(St. Elmo’s fire)和火山的硫黃噴發現象,發展出的傳奇說法。
我憂慮的第二點是,對化學的無知會增添民主政治進展的阻礙。我深信一個必然的事實,那就是必須授權「一般人」來做決定,決定遺傳工程或廢物棄置地點,決定哪些工廠是危險的或安全的,或決定是哪種藥會上癮、藥品應不應該管制等事務。公民可以要求專家對他們解釋利弊,說明有哪些選擇、利益和可能的風險。但是卻不能授權專家做決定;只有人民和人民代表才有權決定。此外,人民還有一項責任,那就是他們必須學習足夠的化學知識,有能力去抗拒化學專家充滿誘惑的說辭,因為這些專家可能聯合起來支持不法活動。
接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建立小學和中學程度的化學課程,使之普及於社會大眾;同時還要訓練和嘉獎教授這些課程的老師。這些化學課程必然要忠於主題的思想核心,也必須是具有吸引力、能促進思考和引發興趣與好奇心。教育的目標主要應該放在非主修科學的學生和有學識的公民身上,而不是對專攻化學的人講授。我相信專攻化學的這些年輕人,會出現新的化學家和聰明的物質改革者;但是,除非我們教導他們的朋友和鄰居(那百分之九十九的非化學家)化學家做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事,否則那百分之一的化學界新星和改革者,也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
(摘自本書第2章、第43章、第45章)
化學家在面對任何新樣品,譬如:以天價從月球表面帶回的塵土、從街上買回的不純麻藥、從一千隻蟑螂腺體中抽出的長生不老藥,第一個問題總是:「我得到的是什麼?」這個疑問可能比一般人想像的還複雜;因為在現實世界裡,沒有一種物質是純的。你仔細觀察周遭最純的物質,譬如矽晶片、精糖或藥物,你會發現這所謂的「純物質」中,存有百萬分之若干的物質,是你或許不想知道的雜質。
其實物質都不純,尤其是天然物,一般來說,天然物比合成物更不純。的確如此。葡萄酒中已經鑑定出大約九百種揮發性芳香成分;品酒專家能辨識出著名的德國莫色耳(Moselle)葡萄酒,即是由於它的混合成分(當然是指天然化合物,還有別的嗎?)別具特殊風味與香氣。令人好奇的是,雖然酒的成分是可定量的化學物,但它的風味與香氣,卻始終令化學家捉摸不清,還得倚賴味覺和嗅覺靈敏的品酒師,才能把正確的酒挑出來。
為什麼天然物不純呢?因為生物是很複雜的,它們是演化的產物。你需要上千個化學反應和無數的化學物,才能使葡萄樹或你的身體運作。並且,大自然是不斷嘗試的修補匠,確保動植物存活的運行法則,是祂數百萬年以來隨機實驗的結果。因而,生命織錦上的每一處,都呈現出繽紛撩亂的分子形狀與色彩。我們眼前任何運作中的事物,都是歷經彼此的揀選,再由大自然的生存實驗錘鍊成形的。
因此,我們真正要問的不再是「這是什麼?」而是「這裡面有多少這東西?」我們把物質的組成成分分開來看,每一成分就是一種化合物;它們是穩定黏結在一起的原子群,而這樣一群原子就叫做分子。純化合物是指由完全相同的分子聚集而成的物質。每種化合物的性質都不同,就像糖和鹽,兩者都是能溶於水的白色結晶體,但是我們可以輕易利用其他的物理、化學或生物性質來區別它們。
把物質的成分分離出來後,我們要鑑定這些化合物的結構。對化學家而言,結構的意義是指:純化合物中含有哪些原子,這些原子如何相互連接,以及它們在空間中如何排列。讓我們先從物質的分離開始探討吧!我恰巧也是礦物蒐藏者;次頁的圖2.1顯示的是自然界形成礦物的一種方式。這是長在長刃狀重晶石上的淡紫色螢石,這塊標本採自德國黑森林區。如果你的一生能像地質年代那麼長久,在某些條件下,你會發現物質自然相互分離,螢石晶體就是這樣形成的。這種現象就稱為部分結晶。不過,大多數化學家無法等上數千年之久。如果僅歷時五年(差不多是取得博士學位所需的時間),或許還能等等看。所以人類需要較快速的技術,因此有人發明了各種儀器來分離物質。
第43 章 為什麼科學家不宜治國?
如果你傾聽科學家私底下的隨興閒聊,會聽到一些八卦消息,例如某人將搬遷到某處去的傳聞、及大嘆研究經費取得不易等等。但換個場合,他們會聲稱科學的理性,並且照例表示反對政客,有時還會對於有點「軟性」的藝術和人文話題,表現出不屑的態度。他們認為只要把科學的理性思維應用於治國,全世界的問題和爭議或許就此一掃而空了。
這些言談可視為科學家自私的兄弟情,我們在此先不談。其他有大半的談話內容,透露出原始而有瑕疵的世界觀,一種把文化與政治系統橫切的謬誤見解。然而我們不確定柏拉圖是否會同意由這些庸俗的科學家來擔任哲學家皇帝,這是把柏拉圖一些單純信念套用在假設為合理的事物上,裝扮出現代模樣。
現代科學是西歐一項成功的社會發明,而且這項成功著實令人不可思議;它是能有效獲取世界上各種可靠知識,並用來改造世界的大事業。居於這樁事業核心的是:對大自然和我們關心的現象,做仔細的觀察。例如科學家會去探尋使泰爾紫呈現顏色的分子,或是探究如何修改這個分子,以達到更鮮亮的紫色或藍色。
在科學家的世界,複雜的事物都經過分解而簡化。這和把事物數學化的過程一樣,也就是所謂的分析(當然不是指化學上的)。無論是在發現或創造的過程中,科學家通常會先設定研究範圍,以便從中獲得複雜和令人驚訝的結果。而且無疑的,在這種範圍裡,分析法是可行的。科學家從分析當中獲得「泰爾紫中所含的染料,有特定結構」的解答,所以「被關起來的貓熊繁殖能力受限」也必有原因。科學家承認,能觀察到的因素或作用,或許是由好多個因素造成的;但是不管這些因素有多複雜,總有受過完善訓練的聰明科學家能把它分析、解開;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再以全世界共通的語言(不流利的英語)相互交換訊息。
讓我們把這個小心構築的科學家世界,和情緒上偶然的實際表現,或人類的風俗習慣互做對比。試問,年輕人的竊盜習慣可有唯一的原因?為什麼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或在前南斯拉夫,會出現手足相殘的情形?浪漫的愛情可有什麼邏輯?我們是否應有分秒不差的行動時程表?
我們發現,外面的世界有許多事物很難用簡化的(或甚至是複雜的)科學分析來處理。這個世界、我們的生活,事實上都傾向於透過倫理與道德的辯論,來取得正義與同情。清楚陳述問題的癥結、變通辦法和後果是有用的,就像在有時漫無目標的爭論中,會出現道德立場的對話,而人們可以藉此痛快吐露真言。正是這種宣洩,使參與式民主政治得以運作。科學家宣稱任何問題都有合理的解答;但事實上,個人和社會的問題並不能用科學家主張的方式解決。
在我的經驗裡,科學家多傾向於凡事應有和平理性的主張。因為在他們的研究工作上,仔細分析的方式行得通;而且他們對我們生存的世界充滿的複雜性,感到迷惑甚至傷心,所以他們天真的追求一種夢想,相信人類的紊亂情感和所有行動,都是受某些理性原則監控,而這些原則仍有待發現。
令人好奇的是,想必會遭科學排擠的宗教,竟然也提出類似的(但讓我很不滿意的)世界觀。科學家傾向用黑與白來看待這世界,希望那些在真實生活裡無時無刻不闖入我們意識中的灰色地帶,消失不見。而且,只要真實世界裡的實行者和製造者(其中最糟的那些,我們稱為政客),肯聽從我們的想法,這個世界就會朝正途發展。
不過,邇來我們已親眼目睹一個支持科學家或技術官僚來經營世界的夢想破滅了,那就是「馬克思主義」。不管它征服的是哪種文化(蘇俄、中國或古巴),馬克思主義不僅證明了它在經濟上行不通,也證明了它會導致無盡的腐敗貪婪,證明它已誘使公正社會的基礎核心墮落。科學家並不喜歡聽到這種論調,但是馬克思主義確實是「科學」的社會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擬出了一種信仰,這種信仰預言了某種社會科學的到臨。他們的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將無止境的進步與發展」的神話為動力,而由人類以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來改造社會,鑄造夢幻國度。
這麼說來,要是科學家不去治理這個世界,那該立身何處呢?就我看來,科學家最好不要從政,但是仍然致力與聞政治。如此,他們就會受到激發,發出理性之聲,對大眾提出睿智的忠告,並對日漸不合理的做法施以反擊。他們的能力恰好能扮演好這種角色。但是若由科學家掌權,我認為科學家那種以為只有自己才具備理性的傲慢態度,很可能導致他們不自覺的逾越分際。
我曉得我把實際的情形誇大了。其實,如果要說科學家有什麼不對,應該是他們對於政治參與得不夠。一旦他們走入政治舞台,也許並不比其他從事政治的人好到哪裡,但也壞不到哪裡。舉例來說,法國有科學家和工程師從政的傳統,例如從拉札爾.卡諾(Lazare Carnot)和他的孫子沙第.卡諾(Sadi Carnot,熱力學第二定律創始人)一直到我的博士後研究生德瓦蓋(Alain Devaquet,曾任法國教育部長)。再說,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的缺點或成就,也不該歸因於她的化學學士學位。
第45 章 化學教育
對我而言,農藥「阿拉爾」的論戰具有使人謙卑,以及教育的和訓示的意義。它是一個機會教育,而不是讓我們趁機去反對環境學家。我就從中學習到一些化學,我也從印度的博帕爾事故中學到一些,我還打算從下一個化學災難中再學習一些。因為,當知識伴隨某些重要事物(像是災難、人的遺體,甚至是淫穢可恥的事物)出現時,人們的心智才會打開。所以,就教育的意義來說,我們可以從發生的事中獲得知識。
這麼一談,我們已經進入教育的話題。我認為教育是民主政治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其實,我對科學文盲的關心,並非著眼於它限制了我們人類勢力的基礎,或是對我們在全球經濟競爭力上的影響;我感到憂心的,在於它代表教育失敗。我有以下兩點說明。首先,要是我們不了解周遭世界運作(尤其是人類製造添加的東西)的基本道理,就會被疏離於環境之外。無知所導致的疏離,會使人貧乏,使我們感到無能為力也沒有行動力。要是不了解這個世界,我們可能會發明出神祕的事物和新的神祇,就好像很久以前人們對閃電和日月食,以及聖愛爾摩之火(St. Elmo’s fire)和火山的硫黃噴發現象,發展出的傳奇說法。
我憂慮的第二點是,對化學的無知會增添民主政治進展的阻礙。我深信一個必然的事實,那就是必須授權「一般人」來做決定,決定遺傳工程或廢物棄置地點,決定哪些工廠是危險的或安全的,或決定是哪種藥會上癮、藥品應不應該管制等事務。公民可以要求專家對他們解釋利弊,說明有哪些選擇、利益和可能的風險。但是卻不能授權專家做決定;只有人民和人民代表才有權決定。此外,人民還有一項責任,那就是他們必須學習足夠的化學知識,有能力去抗拒化學專家充滿誘惑的說辭,因為這些專家可能聯合起來支持不法活動。
接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建立小學和中學程度的化學課程,使之普及於社會大眾;同時還要訓練和嘉獎教授這些課程的老師。這些化學課程必然要忠於主題的思想核心,也必須是具有吸引力、能促進思考和引發興趣與好奇心。教育的目標主要應該放在非主修科學的學生和有學識的公民身上,而不是對專攻化學的人講授。我相信專攻化學的這些年輕人,會出現新的化學家和聰明的物質改革者;但是,除非我們教導他們的朋友和鄰居(那百分之九十九的非化學家)化學家做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事,否則那百分之一的化學界新星和改革者,也無法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
(摘自本書第2章、第43章、第4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