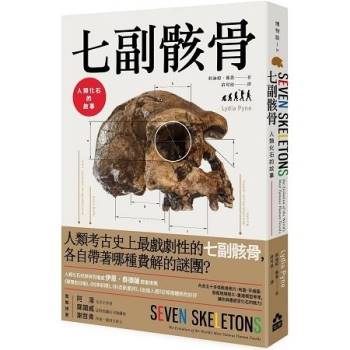第三章 湯恩幼兒:民族英雄的興起(節錄)
「我感到無比興奮且激動。在這堆石頭最頂端的一定是顱骨內部的腦膜。即使它只是任何一種猿類的大腦腦膜化石,它也會被列為一項偉大的發現,因為這種東西以前從未曾有人提過。」雷蒙.達特在一九五九年的回憶錄《失落環節的冒險》(Adventures with the Missing Link,暫譯)中這麼寫著。
「湯恩幼兒」這個引人注目的化石頭骨是在一九二四年發現的,而這本回憶錄卻是在化石出土超過三十五年後才出版。「但我一看就知道,自己捧著的可不是一般的類人頭骨。我很肯定,它是人類學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我想到達爾文那個沒什麼人相信的理論,他說人類的祖先可能住在非洲,我會是幫他發現理論中『失落環節』的那個人嗎?」
在二十世紀初,因為爪哇人(於一八九一年)、幾個尼安德塔人(例如拉沙佩勒老人)和英國皮爾當人的發現,古人類學的學術焦點牢牢鎖定在東南亞和歐洲──換句話說,就是沒有非洲。然而,雷蒙.達特卻在古人類學熱門地點幾千哩外的南非約翰尼斯堡進行研究。但達特是對的:他發現的化石是「人類學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今日,湯恩幼兒身為第一個南方古猿非洲種(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又名非洲南猿),對科學研究十分重要,自然是享有盛名;但它之所以聲名遠播,更因為它是個絕佳範例,說明了一個原始人的成名過程與科學、歷史密不可分。
*
一九二四年一月,年輕的澳洲解剖學家達特,正要展開他在約翰尼斯堡的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的職業生涯,該校要他負責創設醫學與解剖系。早先,達特是在英國神經解剖學家格拉夫頓.艾略特.史密斯爵士的指導下,於倫敦研究神經解剖學,為期兩年。在倫敦的學業結束時,因為拿到了獎學金,所以著名解剖學家亞瑟.基斯爵士說服達特去申請約翰尼斯堡的新職缺。雖然達特對前往南非、遠離倫敦科學界的前景感到畏懼,但他成功申請到這個職位,並且暗自打算未來某個時間點一定要再回到倫敦。(基斯後來是這樣形容達特的:「確實是我推薦他去那裡任職的,不過現在,我可以無所顧忌地承認,當初我其實有點不安。他的聰明才智和想像力都是無庸置疑的;真正讓我害怕的是他的輕浮態度、對大眾公認的看法不屑一顧,還有他那非傳統的觀點。」)達特抵達金山大學後,開始建立學術課程和該院的醫學學程。在他其中一門頗受歡迎的課程中,他要求學生外出收集化石,並將自己找到的標本和其他現存的骨頭相互比較,藉以學習如何辨認出自己發現了什麼。達特鼓勵學生為課程收集化石珍奇,因此這些動物化石很快都匯集至教室的實驗室。一九二四年早期,達特唯一的女學生約瑟芬.薩爾曼斯(Josephine Salmons)在她朋友工作的巴克斯頓石灰採石場,看到主任的桌上用一個很奇特的化石當紙鎮。(有個略為不同的說法是,該化石展示在家庭的壁爐上,引起了薩爾曼斯的興趣。)她可以看出這個化石屬於某種靈長類,並猜測它應該有更深層的演化重要性,而不只是一個古玩,所以她問採石場主任能不能讓她的指導老師雷蒙.達特教授看一看。達特評估這化石可能是非常古老的獼猴,或是已經絕種的狒狒。
發現這化石屬於靈長類,讓達特和他的學生極度興奮,因為這代表南非化石紀錄裡可能還有其他的靈長類。身為研究人腦結構和演化的解剖學家,達特渴望收集到更多標本,好了解靈長類大腦的早期演化狀況。他請薩爾曼斯告訴石灰採石場的人,自己對那裡挖出的任何化石都非常感興趣,甚至提議要提供小額獎金給找到有趣標本的工人。北方石灰公司(Northern Lime Company)的董事史拜爾先生(A. E. Spiers)本身也是化石奇玩的業餘愛好者和收藏家,他一口答應集中保管這些化石,但拒絕達特提供的金錢回饋。因此,巴克斯頓採石場的主管伊佐德先生(E. G. Izod)開始著手收集更多工人找到的有趣化石。多虧了當地豐富的石灰岩地質,化石藏量非常豐富。
那年秋天,從那座石灰採石場收集到的化石,全都運送到了住在約翰尼斯堡的達特手上。一九二四年十月,達特收到採石場寄來的一箱化石,那天他和妻子正要主持一場婚禮,而且達特是伴郎。達特的妻子朵菈對送達的箱子一點好感都沒有。他在自傳中描述了朵菈的反應:「我猜這些就是你期待已久的化石。但它們為什麼偏偏要在今天送達?現在,雷蒙,賓客們很快就會陸續抵達了,所以你要等到婚禮結束、大家離開後,才能栽進那堆殘骸裡。我知道這些化石對你來說有多重要,但請留到明天再處理。」但達特把賓客的事擱在一邊,馬上開始翻看箱子內的化石,身上還穿著全套正式的愛德華式禮服。他看到了小小一顆讓他熱血沸騰的靈長類頭部化石。他完全被這個發現迷住了:「我的內心激動萬分……我站在陰暗處,像個守財奴貪婪地抱著金子般,把腦膜(化石)捧在手心,腦中飛快閃過各種念頭。」婚禮還是或多或少將他的注意力拉回儀式中,那位生氣的新郎正在等著達特履行他身為伴郎的職責。達特回憶道:「新郎扯了扯我的袖子,打斷了我愉快的白日夢,『我的老天,雷蒙』,他努力忍住自己的緊張語氣:『你得馬上穿好衣服,不然我得找別人當伴郎了,新娘車馬上就要到了。』我心不甘情不願地將石頭放回盒子裡,不過那顆顱內腦膜以及與其相連的石頭,我則是拿去鎖在衣櫃裡。」
達特的同事揚格博士(Dr. Young)則對化石的發現過程提供了另一個略有不同的版本。在一九二五年《約翰尼斯堡星報》(Johannesburg Star)的訪談中,揚格描述在湯恩採石場(Taung quarry)引爆數次後,他抵達現場,發現岩石中露出那枚「失落環節」化石的臉,旁邊還有部分頭骨──這兩個化石能完美契合在一起。揚格宣稱自己小心地整理了該發現,並且在返回約翰尼斯堡後,將化石交給達特。揚格博士的說法除了在這場訪談中出現之外,一直沒有太多人引述,不過達特一九二五年於《自然》期刊發表此化石時,確實曾感謝揚格教授和薩爾曼斯小姐協助找到化石。
為了從堅硬的角礫石灰岩中分離出顱骨和下顎骨等化石,達特偷拿了幾對妻子的棒針,將頂端磨尖,做成可以精確挑離化石周圍岩石的工具。接下來的三個月,達特利用每一個空檔,耐心地剝離顱骨上的脈石。在聖誕節前兩天,岩石中出現了一張兒童的臉。達特寫道:「我懷疑在一九二四年的聖誕節,有沒有別的父母對他們的小孩,比我對我的湯恩(原文照錄)寶寶更加驕傲。」
他馬上為它命名為「湯恩幼兒」,這是達特夫婦的化石孩子。第四章 北京人:掉進古代黑洞的奇異案例(節錄)
因為北京人的故事缺乏一個令人滿意的解答,許多人相信化石還在某個地方等待著人們重新發現,這些信徒幾十年來也不停搜索。
一九七二年,來自芝加哥的美國金融家兼慈善家克里斯多夫.雅努斯(Christopher Janus),也加入了北京人的故事。雅努斯對引起公憤這種事很熟悉,因為他曾買下希特勒的豪華轎車,還開著到處跑。他還在一九五○年繼承了一座棉花園和「五十個埃及舞女」,並命令這些人做雜耍表演;惱怒的埃及大使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跟他解釋蓄奴在埃及是非法的行為,並竭力和雅努斯保持距離,在他們眼中,他根本是個政治麻瘋病人。雅努斯就像是個從黑色電影中走出來的角色(他的名字也很像),他決定在北京人的故事中,寫下屬於自己的篇章。
當中國在一九七二年再次對西方開放時,他和第一群得到許可的美國人一起造訪中國,途中,化石失蹤的故事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充滿活力的個性,非常適合追求對歷史的愛好及對文化的興趣。雅努斯沒受過人類學訓練,他承認到北京人博物館參觀前,從來沒聽過北京人化石,但他覺得自己被周口店北京人博物館吳博士選中,要找出這些化石的下落,並將它們還給中國。在雅努斯的故事中,歸還北京人化石變成他個人的使命。雅努斯回到美國後,很快就著手尋找失蹤的標本──他放出風聲,若有人能提供化石下落的資訊,他將提供五千美元做為獎勵。
他的書《尋找北京人》(The Search for Peking Man)充滿了各種謎團和陰謀──祕密會議、隱祕的暗示和國際陰謀。此書的前兩章描述這些化石的遺失過程,並以生動的細節描述赫爾曼.戴維斯博士(Herman Davis)怎麼拿這些箱子當撲克桌。根據雅努斯的「研究」,戴維斯甚至在日軍入侵基地時,利用化石盒來穩定他的機槍。因為雅努斯的緣故,出現了許多莫名其妙的人,他們都想在北京人的可能命運中軋上一角:有些人聲稱知道它在哪裡,另一些人聲稱他們擁有那些遺留物。例如,居住在美國的華僑安德魯.施(Andrew Sze)聲稱化石在臺灣,而他最好的朋友知道確切的位置。
雅努斯搜尋行動的最高潮是,他與一名宣稱曾在亡夫的海軍陸戰隊軍用提箱中看到化石的女人偷偷會面──她說自己在丈夫結束二次世界大戰的派駐生涯後,將化石帶回來了。雅努斯在一個春日午後,去帝國大廈的頂樓見了那個女人;她說,她會戴著太陽眼鏡,讓他能認出她來。在屋頂上,她給了他一張像是化石的模糊照片,然後就徹底失聯。(雅努斯請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哈利.夏皮羅〔Harry Shapiro〕鑑定照片中是否真的是那些化石,但哈利.夏皮羅對於照片中的物質是什麼感到非常懷疑。這張有問題的照片不僅非常模糊,而且還失焦。)雅努斯號稱自己對化石的搜索行動還在持續當中,雖然相當不可能,但他說,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為了國家利益」,答應要協助他找出化石在哪裡。
雅努斯追尋北京人的行動,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嘎然而止,因為他遭聯邦陪審團起訴三十七條詐欺罪。根據檢察官的指控,他因這些骨頭的國際搜尋行動而累積到的詐騙金額,已經高達六十四萬美元,其中包括五十二萬的銀行貸款和十二萬來自投資者資助搜尋計畫、製作影片的錢;大多數資金都流入了雅努斯的個人帳戶。在《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對雅努斯的採訪中,他堅持所有借來的錢都是要用在搜尋化石和規劃拍片上的。雅努斯遭到起訴後,還曾暗示聯邦政府若對他採取行動,會毀了中美關係。雅努斯告訴記者:「整件事不只是在尋找北京人而已,它還涉及與中國的某些關係,不能搬上檯面,那是我們和聯邦政府正在進行的計畫。」
陪審團的結論是,雅努斯並未嚴肅認真地尋找北京人或是拍攝影片,除此之外,大家也找不到他借來的錢大部分到哪裡去了。《尋找北京人》的共同作者威廉.布拉什勒(William Brashler)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採訪中說:「他會說,『我把自己看成是哈里遜.福特』,他馬上找我投資電影。你很難不喜歡他,但他一隻手搭著你的肩膀,另一隻手就在掏你的錢包。」
最終,雅努斯承認了兩項詐欺罪名。有些人像雅努斯這樣,他們找到露骨手段,強將自己插入北京人故事中;其他人像克萊兒.塔什簡(Claire Taschdjian),則是用一種更微妙的方式參與北京人的傳說,她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技師,也是最後一個看到化石的人,她還寫了一個有關化石失蹤的虛構故事:《北京人失蹤了》(The Peking Man is Missing)。(這本書用最寬容的角度來說,是本譁眾取寵的書──由可笑的簡單情節組合而成的呆板散文。)但化石遺失時,塔什簡是北京實驗室的祕書,也是最後一批實際看到化石的人之一,因此在歷史的巧合下,使得她所寫的任何評論,包括她寫的任何東西,都讓人感覺是整個事件的大揭祕,能夠引起轟動。一九七五年一月,原版的《檀島警騎》(Hawaii Five-O)影集中,〈爭論的焦點〉(Bones of Contention)這集演出了史提夫.麥加雷(Steve McGarrett;劇中主角)的團隊如何追蹤「世界最古老的人口失蹤案」;他們在夏威夷的軍事儲藏庫找到北京人的遺留物。追獵、寶藏和謎團激發的興奮感,是這個虛構故事的動力,而且它非常煽情,直接影響我們如何思考北京人的故事。這些化石的名聲現在取決於圍繞著它的謎團和陰謀;那麼,我們為此化石創造並重複的故事,最終也只能像化石一般變成傳奇。
就連近在二○○六年七月,北京房山區政府也宣布重啟對化石的搜索。四位周口店遺址的博物館委員,開始在全中國尋找化石下落的線索。他們的搜索熱線甚至被刊登在當地報紙上;那年秋天,委員會宣布總共找到六十三條線索。許多報紙引述其中一名委員會成員的說法,有四個線索看來「特別有希望」。線索一:有位「一百二十一歲的老人」是孫中山共和政府的高官,他說他清楚知道化石在哪裡。線索二:西北甘肅省有位「老教授」在訪問日本期間,曾在東京軍事法庭檔案中,找到一個美軍公開的證詞。線索三:一位來自北京的劉先生,說自己認識一位「老革命」,他曾擁有一顆頭骨。線索四:另一個北京男子說,他父親曾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有天他從醫院帶了顆頭顱回家,將它埋在鄰居的院子裡。
這些線索全都落空了。
「我感到無比興奮且激動。在這堆石頭最頂端的一定是顱骨內部的腦膜。即使它只是任何一種猿類的大腦腦膜化石,它也會被列為一項偉大的發現,因為這種東西以前從未曾有人提過。」雷蒙.達特在一九五九年的回憶錄《失落環節的冒險》(Adventures with the Missing Link,暫譯)中這麼寫著。
「湯恩幼兒」這個引人注目的化石頭骨是在一九二四年發現的,而這本回憶錄卻是在化石出土超過三十五年後才出版。「但我一看就知道,自己捧著的可不是一般的類人頭骨。我很肯定,它是人類學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我想到達爾文那個沒什麼人相信的理論,他說人類的祖先可能住在非洲,我會是幫他發現理論中『失落環節』的那個人嗎?」
在二十世紀初,因為爪哇人(於一八九一年)、幾個尼安德塔人(例如拉沙佩勒老人)和英國皮爾當人的發現,古人類學的學術焦點牢牢鎖定在東南亞和歐洲──換句話說,就是沒有非洲。然而,雷蒙.達特卻在古人類學熱門地點幾千哩外的南非約翰尼斯堡進行研究。但達特是對的:他發現的化石是「人類學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今日,湯恩幼兒身為第一個南方古猿非洲種(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又名非洲南猿),對科學研究十分重要,自然是享有盛名;但它之所以聲名遠播,更因為它是個絕佳範例,說明了一個原始人的成名過程與科學、歷史密不可分。
*
一九二四年一月,年輕的澳洲解剖學家達特,正要展開他在約翰尼斯堡的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的職業生涯,該校要他負責創設醫學與解剖系。早先,達特是在英國神經解剖學家格拉夫頓.艾略特.史密斯爵士的指導下,於倫敦研究神經解剖學,為期兩年。在倫敦的學業結束時,因為拿到了獎學金,所以著名解剖學家亞瑟.基斯爵士說服達特去申請約翰尼斯堡的新職缺。雖然達特對前往南非、遠離倫敦科學界的前景感到畏懼,但他成功申請到這個職位,並且暗自打算未來某個時間點一定要再回到倫敦。(基斯後來是這樣形容達特的:「確實是我推薦他去那裡任職的,不過現在,我可以無所顧忌地承認,當初我其實有點不安。他的聰明才智和想像力都是無庸置疑的;真正讓我害怕的是他的輕浮態度、對大眾公認的看法不屑一顧,還有他那非傳統的觀點。」)達特抵達金山大學後,開始建立學術課程和該院的醫學學程。在他其中一門頗受歡迎的課程中,他要求學生外出收集化石,並將自己找到的標本和其他現存的骨頭相互比較,藉以學習如何辨認出自己發現了什麼。達特鼓勵學生為課程收集化石珍奇,因此這些動物化石很快都匯集至教室的實驗室。一九二四年早期,達特唯一的女學生約瑟芬.薩爾曼斯(Josephine Salmons)在她朋友工作的巴克斯頓石灰採石場,看到主任的桌上用一個很奇特的化石當紙鎮。(有個略為不同的說法是,該化石展示在家庭的壁爐上,引起了薩爾曼斯的興趣。)她可以看出這個化石屬於某種靈長類,並猜測它應該有更深層的演化重要性,而不只是一個古玩,所以她問採石場主任能不能讓她的指導老師雷蒙.達特教授看一看。達特評估這化石可能是非常古老的獼猴,或是已經絕種的狒狒。
發現這化石屬於靈長類,讓達特和他的學生極度興奮,因為這代表南非化石紀錄裡可能還有其他的靈長類。身為研究人腦結構和演化的解剖學家,達特渴望收集到更多標本,好了解靈長類大腦的早期演化狀況。他請薩爾曼斯告訴石灰採石場的人,自己對那裡挖出的任何化石都非常感興趣,甚至提議要提供小額獎金給找到有趣標本的工人。北方石灰公司(Northern Lime Company)的董事史拜爾先生(A. E. Spiers)本身也是化石奇玩的業餘愛好者和收藏家,他一口答應集中保管這些化石,但拒絕達特提供的金錢回饋。因此,巴克斯頓採石場的主管伊佐德先生(E. G. Izod)開始著手收集更多工人找到的有趣化石。多虧了當地豐富的石灰岩地質,化石藏量非常豐富。
那年秋天,從那座石灰採石場收集到的化石,全都運送到了住在約翰尼斯堡的達特手上。一九二四年十月,達特收到採石場寄來的一箱化石,那天他和妻子正要主持一場婚禮,而且達特是伴郎。達特的妻子朵菈對送達的箱子一點好感都沒有。他在自傳中描述了朵菈的反應:「我猜這些就是你期待已久的化石。但它們為什麼偏偏要在今天送達?現在,雷蒙,賓客們很快就會陸續抵達了,所以你要等到婚禮結束、大家離開後,才能栽進那堆殘骸裡。我知道這些化石對你來說有多重要,但請留到明天再處理。」但達特把賓客的事擱在一邊,馬上開始翻看箱子內的化石,身上還穿著全套正式的愛德華式禮服。他看到了小小一顆讓他熱血沸騰的靈長類頭部化石。他完全被這個發現迷住了:「我的內心激動萬分……我站在陰暗處,像個守財奴貪婪地抱著金子般,把腦膜(化石)捧在手心,腦中飛快閃過各種念頭。」婚禮還是或多或少將他的注意力拉回儀式中,那位生氣的新郎正在等著達特履行他身為伴郎的職責。達特回憶道:「新郎扯了扯我的袖子,打斷了我愉快的白日夢,『我的老天,雷蒙』,他努力忍住自己的緊張語氣:『你得馬上穿好衣服,不然我得找別人當伴郎了,新娘車馬上就要到了。』我心不甘情不願地將石頭放回盒子裡,不過那顆顱內腦膜以及與其相連的石頭,我則是拿去鎖在衣櫃裡。」
達特的同事揚格博士(Dr. Young)則對化石的發現過程提供了另一個略有不同的版本。在一九二五年《約翰尼斯堡星報》(Johannesburg Star)的訪談中,揚格描述在湯恩採石場(Taung quarry)引爆數次後,他抵達現場,發現岩石中露出那枚「失落環節」化石的臉,旁邊還有部分頭骨──這兩個化石能完美契合在一起。揚格宣稱自己小心地整理了該發現,並且在返回約翰尼斯堡後,將化石交給達特。揚格博士的說法除了在這場訪談中出現之外,一直沒有太多人引述,不過達特一九二五年於《自然》期刊發表此化石時,確實曾感謝揚格教授和薩爾曼斯小姐協助找到化石。
為了從堅硬的角礫石灰岩中分離出顱骨和下顎骨等化石,達特偷拿了幾對妻子的棒針,將頂端磨尖,做成可以精確挑離化石周圍岩石的工具。接下來的三個月,達特利用每一個空檔,耐心地剝離顱骨上的脈石。在聖誕節前兩天,岩石中出現了一張兒童的臉。達特寫道:「我懷疑在一九二四年的聖誕節,有沒有別的父母對他們的小孩,比我對我的湯恩(原文照錄)寶寶更加驕傲。」
他馬上為它命名為「湯恩幼兒」,這是達特夫婦的化石孩子。第四章 北京人:掉進古代黑洞的奇異案例(節錄)
因為北京人的故事缺乏一個令人滿意的解答,許多人相信化石還在某個地方等待著人們重新發現,這些信徒幾十年來也不停搜索。
一九七二年,來自芝加哥的美國金融家兼慈善家克里斯多夫.雅努斯(Christopher Janus),也加入了北京人的故事。雅努斯對引起公憤這種事很熟悉,因為他曾買下希特勒的豪華轎車,還開著到處跑。他還在一九五○年繼承了一座棉花園和「五十個埃及舞女」,並命令這些人做雜耍表演;惱怒的埃及大使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跟他解釋蓄奴在埃及是非法的行為,並竭力和雅努斯保持距離,在他們眼中,他根本是個政治麻瘋病人。雅努斯就像是個從黑色電影中走出來的角色(他的名字也很像),他決定在北京人的故事中,寫下屬於自己的篇章。
當中國在一九七二年再次對西方開放時,他和第一群得到許可的美國人一起造訪中國,途中,化石失蹤的故事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充滿活力的個性,非常適合追求對歷史的愛好及對文化的興趣。雅努斯沒受過人類學訓練,他承認到北京人博物館參觀前,從來沒聽過北京人化石,但他覺得自己被周口店北京人博物館吳博士選中,要找出這些化石的下落,並將它們還給中國。在雅努斯的故事中,歸還北京人化石變成他個人的使命。雅努斯回到美國後,很快就著手尋找失蹤的標本──他放出風聲,若有人能提供化石下落的資訊,他將提供五千美元做為獎勵。
他的書《尋找北京人》(The Search for Peking Man)充滿了各種謎團和陰謀──祕密會議、隱祕的暗示和國際陰謀。此書的前兩章描述這些化石的遺失過程,並以生動的細節描述赫爾曼.戴維斯博士(Herman Davis)怎麼拿這些箱子當撲克桌。根據雅努斯的「研究」,戴維斯甚至在日軍入侵基地時,利用化石盒來穩定他的機槍。因為雅努斯的緣故,出現了許多莫名其妙的人,他們都想在北京人的可能命運中軋上一角:有些人聲稱知道它在哪裡,另一些人聲稱他們擁有那些遺留物。例如,居住在美國的華僑安德魯.施(Andrew Sze)聲稱化石在臺灣,而他最好的朋友知道確切的位置。
雅努斯搜尋行動的最高潮是,他與一名宣稱曾在亡夫的海軍陸戰隊軍用提箱中看到化石的女人偷偷會面──她說自己在丈夫結束二次世界大戰的派駐生涯後,將化石帶回來了。雅努斯在一個春日午後,去帝國大廈的頂樓見了那個女人;她說,她會戴著太陽眼鏡,讓他能認出她來。在屋頂上,她給了他一張像是化石的模糊照片,然後就徹底失聯。(雅努斯請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哈利.夏皮羅〔Harry Shapiro〕鑑定照片中是否真的是那些化石,但哈利.夏皮羅對於照片中的物質是什麼感到非常懷疑。這張有問題的照片不僅非常模糊,而且還失焦。)雅努斯號稱自己對化石的搜索行動還在持續當中,雖然相當不可能,但他說,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情局「為了國家利益」,答應要協助他找出化石在哪裡。
雅努斯追尋北京人的行動,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嘎然而止,因為他遭聯邦陪審團起訴三十七條詐欺罪。根據檢察官的指控,他因這些骨頭的國際搜尋行動而累積到的詐騙金額,已經高達六十四萬美元,其中包括五十二萬的銀行貸款和十二萬來自投資者資助搜尋計畫、製作影片的錢;大多數資金都流入了雅努斯的個人帳戶。在《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對雅努斯的採訪中,他堅持所有借來的錢都是要用在搜尋化石和規劃拍片上的。雅努斯遭到起訴後,還曾暗示聯邦政府若對他採取行動,會毀了中美關係。雅努斯告訴記者:「整件事不只是在尋找北京人而已,它還涉及與中國的某些關係,不能搬上檯面,那是我們和聯邦政府正在進行的計畫。」
陪審團的結論是,雅努斯並未嚴肅認真地尋找北京人或是拍攝影片,除此之外,大家也找不到他借來的錢大部分到哪裡去了。《尋找北京人》的共同作者威廉.布拉什勒(William Brashler)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採訪中說:「他會說,『我把自己看成是哈里遜.福特』,他馬上找我投資電影。你很難不喜歡他,但他一隻手搭著你的肩膀,另一隻手就在掏你的錢包。」
最終,雅努斯承認了兩項詐欺罪名。有些人像雅努斯這樣,他們找到露骨手段,強將自己插入北京人故事中;其他人像克萊兒.塔什簡(Claire Taschdjian),則是用一種更微妙的方式參與北京人的傳說,她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技師,也是最後一個看到化石的人,她還寫了一個有關化石失蹤的虛構故事:《北京人失蹤了》(The Peking Man is Missing)。(這本書用最寬容的角度來說,是本譁眾取寵的書──由可笑的簡單情節組合而成的呆板散文。)但化石遺失時,塔什簡是北京實驗室的祕書,也是最後一批實際看到化石的人之一,因此在歷史的巧合下,使得她所寫的任何評論,包括她寫的任何東西,都讓人感覺是整個事件的大揭祕,能夠引起轟動。一九七五年一月,原版的《檀島警騎》(Hawaii Five-O)影集中,〈爭論的焦點〉(Bones of Contention)這集演出了史提夫.麥加雷(Steve McGarrett;劇中主角)的團隊如何追蹤「世界最古老的人口失蹤案」;他們在夏威夷的軍事儲藏庫找到北京人的遺留物。追獵、寶藏和謎團激發的興奮感,是這個虛構故事的動力,而且它非常煽情,直接影響我們如何思考北京人的故事。這些化石的名聲現在取決於圍繞著它的謎團和陰謀;那麼,我們為此化石創造並重複的故事,最終也只能像化石一般變成傳奇。
就連近在二○○六年七月,北京房山區政府也宣布重啟對化石的搜索。四位周口店遺址的博物館委員,開始在全中國尋找化石下落的線索。他們的搜索熱線甚至被刊登在當地報紙上;那年秋天,委員會宣布總共找到六十三條線索。許多報紙引述其中一名委員會成員的說法,有四個線索看來「特別有希望」。線索一:有位「一百二十一歲的老人」是孫中山共和政府的高官,他說他清楚知道化石在哪裡。線索二:西北甘肅省有位「老教授」在訪問日本期間,曾在東京軍事法庭檔案中,找到一個美軍公開的證詞。線索三:一位來自北京的劉先生,說自己認識一位「老革命」,他曾擁有一顆頭骨。線索四:另一個北京男子說,他父親曾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有天他從醫院帶了顆頭顱回家,將它埋在鄰居的院子裡。
這些線索全都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