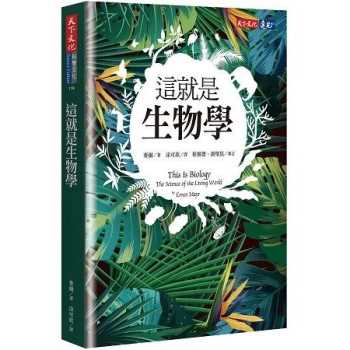生命是什麼?
原始洪荒時期的人類居住在大自然中,每天以採集者、狩獵者或畜牧者的身分接觸著動植物;而無論是老者或嬰兒、生產中的婦女或戰鬥中的勇士,死亡屢見不鮮。「生命是什麼?」這樣亙古不變的問題,必定也曾縈繞在我們老祖先的腦海中。
或許最初的人類對「生物體的生命」和自然界中「無生命物體的靈魂」並沒有清楚的區別。大部分原始人類相信,一座高山、一池清泉、一棵樹木、一隻動物或一個人,內部皆有靈魂寄居其中。這種相信靈魂到處存在的觀點(泛靈論)最後雖然式微,但人類對「生命體內有些東西使之有別於無生命物質,且這些東西會在死亡的剎那離開身體」的信仰,卻仍十分強烈。在古希臘文明中,存在於人體內的這種神祕東西稱為「氣息」。後來則稱為「靈魂」,特別是在基督教中。
到了笛卡兒和科學革命時代,動物也和山川、樹木一樣,失去了持有靈魂的資格,但人類可分成軀體和靈魂的二元論觀念,卻還持續普遍的根植在一般大眾心中,並一直延續至今。死亡對二元論者來說,是一道格外難解的謎題,為什麼靈魂會突然消失或離開身軀?它又去到何方?是臻至涅盤,還是回到天堂?一直要到達爾文發展出經由天擇篩選,使生物得以演化的學說後,死亡才算有了科學和理性的解釋。生物學家魏斯曼是達爾文的忠實信徒,他在十九世紀末首次解釋:快速的世代更替提供了全新的基因型,使生物能用一勞永逸的方式應付變化中的環境。魏斯曼有關死亡的論文,為死亡意義的探求和了解開展新紀元。
然而,當生物學家和哲學家言及「生命」時,他們所說的生命,並不是意指相對於死亡的那種生命,而是相對於無生命物質的那種生命。闡釋生命這種實體的特質,已成為生物學家的主要目標,但問題是「生命」好像暗示了有某些東西存在,那可能是一些物質,也可能是一些力量。於是幾世紀來,哲學家和生物學家嘗試認清這些生命物質或生命力量,但都徒勞無功。現實上,「生命」一詞只是將抽象的存活過程具體化,並不存在有獨立的實體。我們可以用科學的方式探討存活的過程,卻無法研究抽象的「生命」;我們可以描述、甚至嘗試定義「存活」是什麼,我們可以界定存活和不存活(無生命);事實上,我們還可解釋存活是一些無生命的巨分子作用下的產物。生命是什麼?我們又如何解釋生命過程?自十六世紀以來就一直是熱烈討論的議題。情形大致如此:有一派陣營認為,生物和無生命物質並沒有什麼區別,支持這一論點的人,有時被稱為機械論者,後來改稱為物理論者。另外一派稱為生機論的反對陣營,則宣稱生物體具有一些特質,是無法在無生命物質中找到的,因此生物的理論和觀念是不能完全簡化為物理和化學定理的。在某些時期及某些學術機構中,物理論似乎取得優勢,但在其他時期及其他地點,生機論者似乎又占上風,到了二十世紀,我們已能清楚看出,這兩派陣營的說法並非完全正確,但也非全盤皆錯。
物理論者在「沒有抽象的生命物質存在」以及「生命在分子層面可用物理化學定理解釋」上的堅持是正確的。僅管如此,生機論者強力論述:「生物和無生命物質是不同的,生物有許多自發性的特徵,尤其是從歷史演進(演化)中獲得的遺傳程式,是無生命物質所沒有的,生物體具有多層秩序系統,這和無生命世界所發現的任何事物都不一樣。」這也很合理。若將物理論和生機論這兩大哲學思想去蕪存菁,並融合兩者的最佳原理後,所形成的思想學說稱為「有機生物論」(Organicism),這正是主導今日生物學的新思典範。
有機生物論
大約在1920年以前,生機論在生物學觀念中的可信度已經完全消失,生理學家老霍登(J. S. Haldane)曾為這一情形做了注解,他說:「生物學家幾乎已一致揚棄生機論,不再把它當做公認的信仰。」老霍登同時也指出,純機械式的詮釋無法說明生命協調統合的現象,而讓老霍登當時苦思的統合現象,就是遵循一定程序進展的胚胎發生現象。在揭示生機論和機械論的無效後,老霍登認為我們必須根據所有生命現象都傾向有協調的特性,找尋出一個不同的生物學理論基礎。
因此生機論的衰亡並沒有導致機械論的勝利,而是造就了一個全新的解釋系統。這個新的典範接受分子層次是完全可以物理化學機制來解釋的想法,但也同時相信,物理化學機制在愈高整合層次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小:組織系統會有一些突現的特徵來取代或附加在機械性的機制上;生命最特殊的性質並非來自組成元件,而是組成元件的組織。這類觀點現在通稱為「有機生物論」,著重高度複雜秩序系統的特徵和生物演化遺傳程式的歷史特性。里特爾(W. E. Ritter)在1919年創造「有機生物論」一詞根據他的說法,一個整體與其組件之間的關係,不僅包括整體的存在需仰賴各組件間的次序協調和相互依存,還含有整體對其組件的絕對控制。斯馬茨(J. C. Smuts)則解釋他的整體性觀點為:「一個完整個體並不單純,而是複合的,是由多個零件組成的。自然的整體(例如生物個體)亦是複雜或複合的,由彼此具有活躍交互關係的許多零件組成。這些零件本身也可以是一個較小的整體,例如生物體內的細胞。」後來其他生物學家把斯馬茨的這段敘述精簡為「整體大於各組成的總和」。
於是在1920年代後,整體論(Holism)和有機生物論成為意義相等、可交換使用的詞彙。起初「整體論」一詞較常被使用,而其形容詞「整體的」(holistic)更是到現在依然仍耳熟能詳。但整體論並不是一個嚴謹的生物學術語,就像波耳指出,許多無生命系統也具有整體的特性。生物學界現在已改用較嚴格的有機生物論一詞,並將「遺傳程式為重要特質」的認識,納入這個新典範中。
有機生物論者對物理論中機械式論點的反對,遠不如對化約論思想的反對來得強。物理論者稱他們的解釋為機械論的解釋,此點可算是名副其實,但在此之外,他們的解釋也常帶有化約式的色彩。化約論認為,只要將事物化約成較小的組成,表列整理後,並判定每一個組成的功能,原則上就可算是解決了這道問題,因為有了對組成的了解後,再去解釋組織中較高層次的每一個觀察現象,將會是一件簡易的工作。
但有機生物論者卻證明這樣的陳述並不正確,化約論無法說明生物體較高組織中才突現的特徵。有趣的是,大多數機械論者也承認純化約解釋的不足,例如美國哲學家納格爾(Ernst Nagel)就曾坦言:「物理及化學的解釋在目前大部分的生物研究中付之闕如,許多成功的生物理論都不含有物理及化學性質。」納格爾雖插入了「目前」一詞挽回化約論的顏面,但很明顯的,有一些生物學觀念,像是領域、展示(炫耀)、獵食者恫嚇等,永遠無法在不喪失其生物學意義下,簡化為化學和物理名詞。倡導整體論的先驅,例如羅梭和老霍登,都曾有力的反駁化約論方法,並令人信服的證實了整體式角度是如何適用於行為和發生現象。但他們在解釋真正整體現象的本質時卻失敗了,他們無法說明「整體」的特性,或各組成統合成整體時的過程。里特爾、斯馬茨和其他早期的整體論支持者,對他們自己的解釋也同樣似懂非懂,還有些形上學的思想在內。事實上,斯馬茨的用語中還有些帶有目的論的味道呢。
不過,諾維克夫(Alex Novikoff)則詳細說明了為什麼生物體的解釋必須是整體性的:「某一層次的整體,只是更高層次的組件。組件和整體都是物質實體,而各組件互動所造成的統合現象,則是各組件特性整合的結果。由於整體論排斥化約思想,因此反對將生物比喻為一個由各式獨立零件(物理化學單元)組成的機器,而這些零件就像可以從任一台引擎取出來的活塞,還能描述其功能與性質,不管它們是從什麼系統中取出的。」相對的,由於生物系統中的每個組件間都有交互作用,因此光描述一個分離組件,無法傳達整個系統的性質。真正控制整個系統的,是組件間的組織。
生命世界從細胞,到組織、器官、器官系統,以及完整的生物體,每一階層都存在組件的整合現象,這種整合可在生化層面、發生層面和個體行為層面中清楚看到。所有整體論者皆一致同意,沒有任何系統可完全以分離組件的特性來解釋清楚。有機生物論的基礎建立在生物體具有組織的這項事實上,生物體並不只是由一堆性狀和分子堆砌而成,生物體的功能是由性狀和分子間的組織、互助關係、交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等特性所完成的。
(摘錄自本書第1章)
原始洪荒時期的人類居住在大自然中,每天以採集者、狩獵者或畜牧者的身分接觸著動植物;而無論是老者或嬰兒、生產中的婦女或戰鬥中的勇士,死亡屢見不鮮。「生命是什麼?」這樣亙古不變的問題,必定也曾縈繞在我們老祖先的腦海中。
或許最初的人類對「生物體的生命」和自然界中「無生命物體的靈魂」並沒有清楚的區別。大部分原始人類相信,一座高山、一池清泉、一棵樹木、一隻動物或一個人,內部皆有靈魂寄居其中。這種相信靈魂到處存在的觀點(泛靈論)最後雖然式微,但人類對「生命體內有些東西使之有別於無生命物質,且這些東西會在死亡的剎那離開身體」的信仰,卻仍十分強烈。在古希臘文明中,存在於人體內的這種神祕東西稱為「氣息」。後來則稱為「靈魂」,特別是在基督教中。
到了笛卡兒和科學革命時代,動物也和山川、樹木一樣,失去了持有靈魂的資格,但人類可分成軀體和靈魂的二元論觀念,卻還持續普遍的根植在一般大眾心中,並一直延續至今。死亡對二元論者來說,是一道格外難解的謎題,為什麼靈魂會突然消失或離開身軀?它又去到何方?是臻至涅盤,還是回到天堂?一直要到達爾文發展出經由天擇篩選,使生物得以演化的學說後,死亡才算有了科學和理性的解釋。生物學家魏斯曼是達爾文的忠實信徒,他在十九世紀末首次解釋:快速的世代更替提供了全新的基因型,使生物能用一勞永逸的方式應付變化中的環境。魏斯曼有關死亡的論文,為死亡意義的探求和了解開展新紀元。
然而,當生物學家和哲學家言及「生命」時,他們所說的生命,並不是意指相對於死亡的那種生命,而是相對於無生命物質的那種生命。闡釋生命這種實體的特質,已成為生物學家的主要目標,但問題是「生命」好像暗示了有某些東西存在,那可能是一些物質,也可能是一些力量。於是幾世紀來,哲學家和生物學家嘗試認清這些生命物質或生命力量,但都徒勞無功。現實上,「生命」一詞只是將抽象的存活過程具體化,並不存在有獨立的實體。我們可以用科學的方式探討存活的過程,卻無法研究抽象的「生命」;我們可以描述、甚至嘗試定義「存活」是什麼,我們可以界定存活和不存活(無生命);事實上,我們還可解釋存活是一些無生命的巨分子作用下的產物。生命是什麼?我們又如何解釋生命過程?自十六世紀以來就一直是熱烈討論的議題。情形大致如此:有一派陣營認為,生物和無生命物質並沒有什麼區別,支持這一論點的人,有時被稱為機械論者,後來改稱為物理論者。另外一派稱為生機論的反對陣營,則宣稱生物體具有一些特質,是無法在無生命物質中找到的,因此生物的理論和觀念是不能完全簡化為物理和化學定理的。在某些時期及某些學術機構中,物理論似乎取得優勢,但在其他時期及其他地點,生機論者似乎又占上風,到了二十世紀,我們已能清楚看出,這兩派陣營的說法並非完全正確,但也非全盤皆錯。
物理論者在「沒有抽象的生命物質存在」以及「生命在分子層面可用物理化學定理解釋」上的堅持是正確的。僅管如此,生機論者強力論述:「生物和無生命物質是不同的,生物有許多自發性的特徵,尤其是從歷史演進(演化)中獲得的遺傳程式,是無生命物質所沒有的,生物體具有多層秩序系統,這和無生命世界所發現的任何事物都不一樣。」這也很合理。若將物理論和生機論這兩大哲學思想去蕪存菁,並融合兩者的最佳原理後,所形成的思想學說稱為「有機生物論」(Organicism),這正是主導今日生物學的新思典範。
有機生物論
大約在1920年以前,生機論在生物學觀念中的可信度已經完全消失,生理學家老霍登(J. S. Haldane)曾為這一情形做了注解,他說:「生物學家幾乎已一致揚棄生機論,不再把它當做公認的信仰。」老霍登同時也指出,純機械式的詮釋無法說明生命協調統合的現象,而讓老霍登當時苦思的統合現象,就是遵循一定程序進展的胚胎發生現象。在揭示生機論和機械論的無效後,老霍登認為我們必須根據所有生命現象都傾向有協調的特性,找尋出一個不同的生物學理論基礎。
因此生機論的衰亡並沒有導致機械論的勝利,而是造就了一個全新的解釋系統。這個新的典範接受分子層次是完全可以物理化學機制來解釋的想法,但也同時相信,物理化學機制在愈高整合層次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小:組織系統會有一些突現的特徵來取代或附加在機械性的機制上;生命最特殊的性質並非來自組成元件,而是組成元件的組織。這類觀點現在通稱為「有機生物論」,著重高度複雜秩序系統的特徵和生物演化遺傳程式的歷史特性。里特爾(W. E. Ritter)在1919年創造「有機生物論」一詞根據他的說法,一個整體與其組件之間的關係,不僅包括整體的存在需仰賴各組件間的次序協調和相互依存,還含有整體對其組件的絕對控制。斯馬茨(J. C. Smuts)則解釋他的整體性觀點為:「一個完整個體並不單純,而是複合的,是由多個零件組成的。自然的整體(例如生物個體)亦是複雜或複合的,由彼此具有活躍交互關係的許多零件組成。這些零件本身也可以是一個較小的整體,例如生物體內的細胞。」後來其他生物學家把斯馬茨的這段敘述精簡為「整體大於各組成的總和」。
於是在1920年代後,整體論(Holism)和有機生物論成為意義相等、可交換使用的詞彙。起初「整體論」一詞較常被使用,而其形容詞「整體的」(holistic)更是到現在依然仍耳熟能詳。但整體論並不是一個嚴謹的生物學術語,就像波耳指出,許多無生命系統也具有整體的特性。生物學界現在已改用較嚴格的有機生物論一詞,並將「遺傳程式為重要特質」的認識,納入這個新典範中。
有機生物論者對物理論中機械式論點的反對,遠不如對化約論思想的反對來得強。物理論者稱他們的解釋為機械論的解釋,此點可算是名副其實,但在此之外,他們的解釋也常帶有化約式的色彩。化約論認為,只要將事物化約成較小的組成,表列整理後,並判定每一個組成的功能,原則上就可算是解決了這道問題,因為有了對組成的了解後,再去解釋組織中較高層次的每一個觀察現象,將會是一件簡易的工作。
但有機生物論者卻證明這樣的陳述並不正確,化約論無法說明生物體較高組織中才突現的特徵。有趣的是,大多數機械論者也承認純化約解釋的不足,例如美國哲學家納格爾(Ernst Nagel)就曾坦言:「物理及化學的解釋在目前大部分的生物研究中付之闕如,許多成功的生物理論都不含有物理及化學性質。」納格爾雖插入了「目前」一詞挽回化約論的顏面,但很明顯的,有一些生物學觀念,像是領域、展示(炫耀)、獵食者恫嚇等,永遠無法在不喪失其生物學意義下,簡化為化學和物理名詞。倡導整體論的先驅,例如羅梭和老霍登,都曾有力的反駁化約論方法,並令人信服的證實了整體式角度是如何適用於行為和發生現象。但他們在解釋真正整體現象的本質時卻失敗了,他們無法說明「整體」的特性,或各組成統合成整體時的過程。里特爾、斯馬茨和其他早期的整體論支持者,對他們自己的解釋也同樣似懂非懂,還有些形上學的思想在內。事實上,斯馬茨的用語中還有些帶有目的論的味道呢。
不過,諾維克夫(Alex Novikoff)則詳細說明了為什麼生物體的解釋必須是整體性的:「某一層次的整體,只是更高層次的組件。組件和整體都是物質實體,而各組件互動所造成的統合現象,則是各組件特性整合的結果。由於整體論排斥化約思想,因此反對將生物比喻為一個由各式獨立零件(物理化學單元)組成的機器,而這些零件就像可以從任一台引擎取出來的活塞,還能描述其功能與性質,不管它們是從什麼系統中取出的。」相對的,由於生物系統中的每個組件間都有交互作用,因此光描述一個分離組件,無法傳達整個系統的性質。真正控制整個系統的,是組件間的組織。
生命世界從細胞,到組織、器官、器官系統,以及完整的生物體,每一階層都存在組件的整合現象,這種整合可在生化層面、發生層面和個體行為層面中清楚看到。所有整體論者皆一致同意,沒有任何系統可完全以分離組件的特性來解釋清楚。有機生物論的基礎建立在生物體具有組織的這項事實上,生物體並不只是由一堆性狀和分子堆砌而成,生物體的功能是由性狀和分子間的組織、互助關係、交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等特性所完成的。
(摘錄自本書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