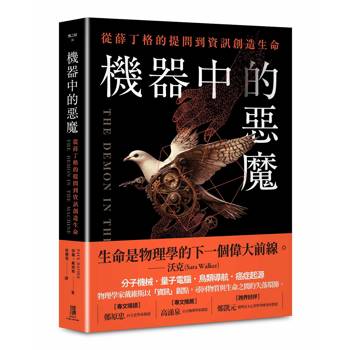第四章
達爾文主義2.0
「除了演化論,生物學中的一切都毫無意義。」
——多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1]
「大自然,充滿了腥牙血爪。」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在達爾文時代初期寫下了這段耐人尋味的話語。可以理解的是,當時的科學家和詩人慣於對天擇的殘酷性詳加描述,這體現在身體適應的軍備競賽中,無論是鯊魚鋒利的牙齒,還是烏龜堅硬的防禦殼甲。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很容易理解演化如何選擇更大的翅膀、更長的腿、更敏銳的視力等等。但身體——生命的硬體——只是故事的一半。與身體同樣重要的另一部分——事實上是更加重要的,是資訊的變化模式、命令和控制系統,它們構成了生命的軟體。演化對生物軟體的作用,就如同對硬體的作用;由於資訊是看不見的,所以我們不容易注意到它。我們也沒有注意到分流和處理所有資訊的微型惡魔,但它們近乎完美的熱力學表現,是數十億年演化完善的結果。[2]
這與電腦業有類似之處。三十年前,個人電腦處理速度緩慢又攜帶不便。滑鼠、彩色螢幕和小型電池等創新,使得電腦變得更有效率和便捷,因此銷量爆增。於是資本主義版本的天擇導致了電腦數量的大幅成長。但除了硬體創新之外,電腦軟體取得了更令人矚目的進步。例如Photoshop 或PowerPoint 的早期版本,與目前版本相比簡直無法相提並論。最重要的是,電腦的速度大幅提升,成本卻大幅下降。軟體改進對產品成功的貢獻至少與硬體改進一樣大。
達爾文理論發表後的一個世紀,生命的資訊故事才進入演化的論述。如今,生物資訊領域已成為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產業,累積了驚人的數據量,也充斥著誇大其詞的言論。在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個完整的人類基因組序列在2003 年公佈,此事被譽為改變了生物學、尤其是醫學領域的重大事件。儘管這項里程碑帶來的成就重要性不容小覷,但人們很快就發現,擁有完整的基因組細節還遠遠不足以「解釋生命」。
當達爾文的演化論在20 世紀中期與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結合,形成所謂的「現代演化綜論」(modern synthesis),這個故事看起來似乎簡單到令人誤解。DNA 是一個實體的物體;複製它一定會產生隨機的錯誤,因此提供了天擇可以運作其中的基因變異機制。一旦列出基因及其編碼的蛋白質功能清單,其餘的就只是細節了。
大約二十年前,這種簡單的演化觀點開始站不住腳。從一份蛋白質清單到功能性的三維構造的道路非常漫長,而且如果沒有「組裝說明」,基因組計畫提供的蛋白質「零件清單」就毫無用處。即使在今天,也沒有人能夠根據基因組序列,預測生物體的實際樣子,更不用說基因組序列的隨機變化會如何轉化為表現型的變化。
基因只有當它們被表達(即被打開)時才會產生影響,而真正的生物資訊故事就是從這裡開始的,也就是基因控制和管理的領域。這一個新興學科被稱為表觀遺傳學,它比孤立的遺傳學更豐富和微妙。越來越多驅動生物資訊模式和資訊流組織的表觀遺傳因素被發現。現在,達爾文主義正在進一步完善和擴展,我將其稱為「達爾文主義2.0」,它為生物學中資訊的力量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並引發了演化論的重大修正。
電氣怪
「遺傳不僅僅與基因有關。」——雅布隆卡(Eva Jablonka)[3]
「來自太空!雙頭扁蟲震驚了科學家!」[4]2017 年6 月,英國一份網路刊物如此宣稱。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國際太空站中出現的怪物,也難免提到了「困惑的科學家」。怪物並沒有入侵太空站;牠們的出現是為了進行一項實驗,該實驗旨在觀察低等扁蟲在被砍掉頭部和尾部後,如何進入軌道。事實證明,牠們應付得很好。到頭來,每十五隻中就有一隻長出了兩顆頭,取代了原本失去的那顆。[5]
太空扁蟲只是表觀遺傳學領域蓬勃發展的一個相當戲劇性的例子。廣義來說,表觀遺傳學是研究生物體基因之外的形態決定因素(見BOX 9)。這種雙頭蟲從基因上與牠們更常見的近親完全相同,但看起來就像是不同的物種。事實上,雙頭扁蟲會繁殖,並生出更多的雙頭扁蟲,難怪科學家感到困惑不已。發現這個案例的首席科學家是塔夫茨大學的萊文,他恰好是我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研究小組的合作者。
為了將扁蟲放進本文的脈絡中,請回想一下上一章中的胚胎發育(形態發生),儘管實際機制令人費解,但它仍是一個生動的例子,說明了資訊的力量如何控制和塑造生物體的形態。那時我的解釋是,構建和操作生物體所需的資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系統打開或關閉基因的能力,以及在遺傳指令轉譯後影響蛋白質的能力。目前我們仍然不太清楚這種透過化學途徑調節資訊流的規則,其中牽涉到甲基、組織蛋白的尾巴和小分子RNA 等分子(見BOX 9),以及將這種基因轉換組合、與大量不斷變化的化學模式結合起來的規則。因此,表觀遺傳學開啟了更廣大的組合方式和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界。我提到過,有種稱為形態發生素的特殊分子,它的擴散方式在控制發育的動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事實證明,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幾年裡,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另一種物理機制在形態發生中可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它被稱為電轉導(electro-transduction),與電力引起的生物體形態變化有關。
達爾文主義2.0
「除了演化論,生物學中的一切都毫無意義。」
——多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1]
「大自然,充滿了腥牙血爪。」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在達爾文時代初期寫下了這段耐人尋味的話語。可以理解的是,當時的科學家和詩人慣於對天擇的殘酷性詳加描述,這體現在身體適應的軍備競賽中,無論是鯊魚鋒利的牙齒,還是烏龜堅硬的防禦殼甲。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很容易理解演化如何選擇更大的翅膀、更長的腿、更敏銳的視力等等。但身體——生命的硬體——只是故事的一半。與身體同樣重要的另一部分——事實上是更加重要的,是資訊的變化模式、命令和控制系統,它們構成了生命的軟體。演化對生物軟體的作用,就如同對硬體的作用;由於資訊是看不見的,所以我們不容易注意到它。我們也沒有注意到分流和處理所有資訊的微型惡魔,但它們近乎完美的熱力學表現,是數十億年演化完善的結果。[2]
這與電腦業有類似之處。三十年前,個人電腦處理速度緩慢又攜帶不便。滑鼠、彩色螢幕和小型電池等創新,使得電腦變得更有效率和便捷,因此銷量爆增。於是資本主義版本的天擇導致了電腦數量的大幅成長。但除了硬體創新之外,電腦軟體取得了更令人矚目的進步。例如Photoshop 或PowerPoint 的早期版本,與目前版本相比簡直無法相提並論。最重要的是,電腦的速度大幅提升,成本卻大幅下降。軟體改進對產品成功的貢獻至少與硬體改進一樣大。
達爾文理論發表後的一個世紀,生命的資訊故事才進入演化的論述。如今,生物資訊領域已成為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產業,累積了驚人的數據量,也充斥著誇大其詞的言論。在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個完整的人類基因組序列在2003 年公佈,此事被譽為改變了生物學、尤其是醫學領域的重大事件。儘管這項里程碑帶來的成就重要性不容小覷,但人們很快就發現,擁有完整的基因組細節還遠遠不足以「解釋生命」。
當達爾文的演化論在20 世紀中期與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結合,形成所謂的「現代演化綜論」(modern synthesis),這個故事看起來似乎簡單到令人誤解。DNA 是一個實體的物體;複製它一定會產生隨機的錯誤,因此提供了天擇可以運作其中的基因變異機制。一旦列出基因及其編碼的蛋白質功能清單,其餘的就只是細節了。
大約二十年前,這種簡單的演化觀點開始站不住腳。從一份蛋白質清單到功能性的三維構造的道路非常漫長,而且如果沒有「組裝說明」,基因組計畫提供的蛋白質「零件清單」就毫無用處。即使在今天,也沒有人能夠根據基因組序列,預測生物體的實際樣子,更不用說基因組序列的隨機變化會如何轉化為表現型的變化。
基因只有當它們被表達(即被打開)時才會產生影響,而真正的生物資訊故事就是從這裡開始的,也就是基因控制和管理的領域。這一個新興學科被稱為表觀遺傳學,它比孤立的遺傳學更豐富和微妙。越來越多驅動生物資訊模式和資訊流組織的表觀遺傳因素被發現。現在,達爾文主義正在進一步完善和擴展,我將其稱為「達爾文主義2.0」,它為生物學中資訊的力量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並引發了演化論的重大修正。
電氣怪
「遺傳不僅僅與基因有關。」——雅布隆卡(Eva Jablonka)[3]
「來自太空!雙頭扁蟲震驚了科學家!」[4]2017 年6 月,英國一份網路刊物如此宣稱。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國際太空站中出現的怪物,也難免提到了「困惑的科學家」。怪物並沒有入侵太空站;牠們的出現是為了進行一項實驗,該實驗旨在觀察低等扁蟲在被砍掉頭部和尾部後,如何進入軌道。事實證明,牠們應付得很好。到頭來,每十五隻中就有一隻長出了兩顆頭,取代了原本失去的那顆。[5]
太空扁蟲只是表觀遺傳學領域蓬勃發展的一個相當戲劇性的例子。廣義來說,表觀遺傳學是研究生物體基因之外的形態決定因素(見BOX 9)。這種雙頭蟲從基因上與牠們更常見的近親完全相同,但看起來就像是不同的物種。事實上,雙頭扁蟲會繁殖,並生出更多的雙頭扁蟲,難怪科學家感到困惑不已。發現這個案例的首席科學家是塔夫茨大學的萊文,他恰好是我們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研究小組的合作者。
為了將扁蟲放進本文的脈絡中,請回想一下上一章中的胚胎發育(形態發生),儘管實際機制令人費解,但它仍是一個生動的例子,說明了資訊的力量如何控制和塑造生物體的形態。那時我的解釋是,構建和操作生物體所需的資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系統打開或關閉基因的能力,以及在遺傳指令轉譯後影響蛋白質的能力。目前我們仍然不太清楚這種透過化學途徑調節資訊流的規則,其中牽涉到甲基、組織蛋白的尾巴和小分子RNA 等分子(見BOX 9),以及將這種基因轉換組合、與大量不斷變化的化學模式結合起來的規則。因此,表觀遺傳學開啟了更廣大的組合方式和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界。我提到過,有種稱為形態發生素的特殊分子,它的擴散方式在控制發育的動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事實證明,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過去的幾年裡,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另一種物理機制在形態發生中可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它被稱為電轉導(electro-transduction),與電力引起的生物體形態變化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