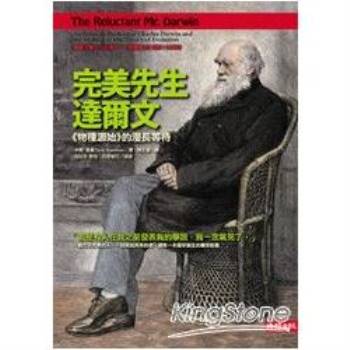導讀:達爾文為什麼不會是咱們的孩子?
──程延年自然科學博物館資深研究員、成功大學地球科學所教授
E=MC2的雷射炫光,打在台北東區一○一的高樓壁面,全球同步歡呼慶賀的景象依稀猶存。場景一換,「物競、天擇、適應、存活」八字箴言,不似數學程式的簡約動人,卻是演化生物學的核心概念。瘋完愛因斯坦,瘋達爾文!
達爾文的熱潮方興未已
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是達爾文的二百歲生日。十九世紀的西方,兩位巨人因緣際會,在同一天降生(一八○九年二月十二日)。林肯廢止黑奴制度,開啟了人類心靈的解放,也是自由真諦的原動力量;而達爾文解脫生物學於超自然論與自然神學論的桎梏,發掘生命的「自然汰擇」大力。這誠然都是人類最罕見的心靈!同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正是《物種源始》這本曠世鉅作發表問市一五○年的日子。二月十二日當天,我正在北臺灣的基隆,為摯友許醫師籌備多年的精緻化石博物館開幕而共襄盛舉。博物館的橫匾書寫:達爾文。同一天,位於倫敦的英國自然史博物館盛大揭幕達爾文特展,名為:Darwin: Big Idea, Big Exhibition。迎接這個世紀盛事,全球平均每個星期就會上市出版一本達爾文/演化論的專書,讓我們目不暇給。
達爾文為什麼不會是咱們的孩子?教育的核心訓練與價值使然!這本書的作者既非生物學家,也非演化學家,更不具學府訓練的科學背景,他如何寫出這本精采的專書?他僅是一位自由撰稿作家呢!達爾文呢?進入愛丁堡研讀醫學,轉到劍橋學習神學;浪跡天涯近五年,「頓悟開竅」,創生了演化理論的核心概念與機制。在我們制式教育的菁英主義試鍊下,莘莘學子訓練成為考試的機器,而不是思考的機制,學習的「單扇」窄門,從我們那個年代的物理學,移化到醫學,到電腦資訊,到分子生物,到基因工程,到.. ,孩子們戴著鋼盔往前衝,撞到南牆不回頭。當我的孩子早熟地棄守資優班及聯考大關,以小留學生身分遠赴英倫,進到「九年級班」,我猛然覺醒:他們的教育體系有萬扇門,配了萬把鑰匙;教育,在摸索、試探取對了錀匙,進對了高門。開啟殿門,始見百官之富,宗廟之美。頂尖的華裔科學家許靖華教授曾經撰寫:為什麼牛頓不是中國人?他以兩大支系的文字起源及演變,針對以科學描繪、精準述說為訴求的西方文字,探究其思維模式之深意。這裡,我試圖以教育體系中思辨能力的培育,以及邏輯思考、理性辯駁、質疑傳統權威等核心議題,加以釐清並歸結之。
浮光掠影導讀
像是莎士比亞的大劇《哈姆雷特》,或者但丁的《神曲》,本書作者以編年、斷代的時間軸為經,以序列的事件中人物與事蹟為緯,編織、浮現出這位科學史和思想史中的巨人,以及這一本曠世傑作的精髓內涵,潑墨渲染,成其大器。以「引子」揭開了序幕,引領出七幕劇的精采戲碼。
小獵犬號探險航行四年九個月又五天,總計一千七百多個日子,真是足夠了!序曲以「凱旋歸故里」拉開了布幕。「真是足夠了」有兩層深義:一是茫茫大海中,孤寂、顛簸、風吹雨打、千辛萬苦,軀體上及生理上瀕臨極限,真正是受夠了;而心靈上則因周遊列國而大開眼界,驚艷、震撼、衝擊備至,真是足夠了──足夠豐富,足夠啟迪變革了!
第一幕(1837-1839),固有的架構瓦解了。這正是浪跡天涯返家之後,一個嶄新的頭腦、一個全新的思維,徹頭徹尾的變革,從蛹繭中羽化而登仙。維多利亞時代,整個社會主流的信仰、價值觀、科學核心認知與哲學思維,在達爾文歷經愛丁堡與劍橋的洗禮,歷經航程中五年敏銳的觀察、細膩的筆記、邏輯的推理思考,一切固有的架構似乎一夕之間全部崩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浴火重生的鳳凰,在迷霧中若隱若現。字裡行間,我們幾乎可以想像到那一顆年輕心靈的澎湃、激情、恐懼與不安。
第三幕(1846-1851),延怠發表,專注實驗。達爾文鎖起了天大祕密,天機無可洩露,轉而養起了成群的鴿子,玩賞起成堆的奇特小傢伙:藤壺(現生的與化石的標本)。為什麼?這可是歷史的懸案,卻也是最精采的自我沉寂、自我檢視、自我突破的關鍵時期。那正是解碼大自然「最神祕中的神祕」的一把鑰匙。所有藤壺個體之間的差異,群體系譜關係的隸屬,與分類系統的釐清建構,達爾文觸摸到了最底層、最內裡的神經,一幹就是八年的歲月,沉迷其中。他最終完成了四卷的藤壺分類圖鑑,獲得了英國皇家學會金質獎章的殊榮!藤壺,這群歸屬於節肢動物的不起眼小傢伙,在演化生物學的體系中,可是立下了大功勞。
第二幕(1842-1844),幾維鳥的一顆大蛋。達爾文開始抽絲剝繭,將所有近五年的毛片影像剪接、整理──準備要編織一齣好的劇本,說一場好的故事。他移居「唐屋」,離群索居,沉靜的空氣中,瀰漫著糾結、喧鬧雜陳的心思。依偎著親愛的終身伴侶艾瑪,仰仗著魚雁的往返,與維多利亞社群中頭腦最頂尖的一群菁英神交。一個偉大的演化思維體系,悄然茁生,很少人知道那將會震撼整個世界爾後的一百五十個年頭!從飼養、選種的「人擇」,推演到大自然中的「自然汰擇」(注:Natural Selection 。我一直以為慣用的「天擇」,約定成俗,是極不精準的譯名。天啊!怎麼會將「自然」譯成「天」呢?大自然中的選擇,有兩個關鍵步驟,一是淘汰不適者、二是較適應者存活。簡言之,Selection ,汰擇是也。因而,我一直譯成「自然汰擇」。),近二百多頁的初稿,一八四四年受孕、懷胎、成形,卻封存在保險櫃中,一鎖十五年,不見天日,為什麼?
第四幕(1848-1857),遠東寄來的雁鴨。高潮迭起,那一位際遇真可說是不幸的華萊士登場了,他攪亂了一池春水!亞馬遜的四年,東南亞蠻荒的流浪,靠著獵捕、販賣標本維生;卻也同時觀察、思索、註記、頓悟─孤寂,是成就偉大心靈的溫床。達爾文在「唐屋」困戰於藤壺的八年期間,在遙遠的東方孤島上,另一個偉大的心靈形影相隨,思索著同樣神祕未解的議題:變異、適應、地理分布、選擇、共同後裔……。當維多利亞的菁英們,萊爾、赫胥利、胡克紛紛登門拜訪達爾文的同時,華萊士只能跟他獵捕的雁鴨標本對話─其中一隻,打包妥當,就要寄給地球另一端的達爾文。達爾文警覺到遙遠的另一個心靈的浮現與威脅;而華萊士呢?正在為生活溫飽而「困戰求存」呢!
第五幕(1858-1859),令人厭煩的大卷冊。科學史上,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封短信(並附上了論文手稿),不但幾乎擊潰達爾文,同時也極可能改寫科學史,終於在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八日輾轉寄到了達爾文的手上!在科學的現實領域中,可真是理性與感性的雜陳;是協同合作與競爭奮戰的並行;是掠食者與獵物之間的較勁。這裡有寬容大度與諄諄教誨,也有掠奪邀功爭寵和堅齒利爪的血腥,不堪聞問。它終究是一個縮影、一個具體而微的小世界。達爾文心靈上的震驚可想而知。封存了近廿年的偉大創見,可能一夕成為泡影?復加愛子病危的折磨,達爾文立時求助於摯友萊爾與胡克,他們即刻介入了這一椿歷史懸案。直到半個世紀之後,華萊士在自傳中才娓娓道出未能共享盛名,僅僅坐上第二把交椅的情懷。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在林奈學會上,宣讀達爾文與華萊士手稿論文,是「菁英領導群」喬出來的一場戲碼。達爾文立時面臨放棄撰寫大書的初衷偉業,改而寫一帖精簡版的「摘要」─那就是最後成形的《論物種源始》第一版。這部演化生物學的聖經寶典,終於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的近午時刻問市了。當時正啜飲著下午茶的大主教妻子,聽聞這件事後,說了兩句話:「啊,最好那不是真的。唉,如果是真的,最好不要有太多人知道!」實情總是不盡如人意─《物種源始》修訂了六個版本,譯成多國文字,流傳百世,歷久而彌新─它,正是一場科學革命「典範轉移」的正型模式。
第六幕(1860 年以後),最適的概念。達爾文的演化論,不受青睞長達半個世紀。挑戰者眾,多半無功而退。兩個核心議題是:演化,可曾真正發生過?自然汰擇可真是主要的機制?顯然,演化論不是要挑戰上帝,而是要洞悉自然運作的真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之後一個半世紀,針對解碼大自然奧祕,有諸多的信仰體系瀰漫著─常民的、宗教的、科學的、形而上的、哲學的。達爾文式演化論同樣歷經多次的蛻變,嫁接了孟德爾式遺傳思維、古生物學的化石證據、分子生物學基因的洞悉,以至於最新胚胎學、發育學的崛起─所稱「演化發育生物學,Evo-Devo」的幽靈重現。演化論如虎添翼,翱翔天際。
第七幕終曲(1876-1882),最終的甲蟲隱喻。大劇接近了尾聲,達爾文也心身俱疲,打了一場還分不清勝負的大戰役,戰場尚待清理。持續永不歇止的工作,是達爾文的鎮靜劑;科學追尋,是達爾文終其一生的信仰。達爾文難以捉摸的個性,更加怪異了。或者較精準地說:一顆超越時空的偉大心靈,對當世之人更加陌生,他自己也對塵世間的「當世」更加難理解。達爾文持續研究食蟲植物,研究蘭花品種,研究起蚯蚓。他從不退休,只因為他幸運地,從未有一個可以引退的正職工作。誠然,達爾文的生命,不是「職業」,不是「事業」所可以框架的,那可是最崇高「志業」的實踐,至死不渝。達爾文在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日迫西山時分死去,走完了七十三年曲折迷離的一生。肉身軀體葬於西敏寺,與萊爾、牛頓、喬叟為鄰;而靈魂,卻四處飛揚、跨越時空,生生世世。
怎麼樣才能成為達爾文?
這本譯書,字裡行間像是音符般,跳躍在現實場景的推移與虛幻心靈的發掘、揣摹,深深撥動了讀者的心弦。譯者字字句句斟酌,誠屬高妙。信達雅兼顧,譯文允為箇中高手。要怎麼讀引言 凱旋歸故里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科學與社會的發展歷史上地位獨特。雖然他的名字家喻戶曉,但不表示他的想法也是如此(只有一項例外);雖然他在科學界的地位崇高,深具代表性,但不表示人們真的瞭解他。假如科學界要發行紙鈔,面額最小、發行量最大的鈔票上頭印的肯定是達爾文。他的臉還滿適合放在上面的──一張親切但木然的臉,就像一元美鈔上根據吉爾伯.史都華(Gilbert Stuart)的肖像畫所刻印的美國總統華盛頓頭像。而且達爾文也跟華盛頓一樣,高深莫測、緊張壓抑才是他們的真性情。每個人或多或少都知道達爾文是誰,曉得他做過什麼事、說過什麼話,而且大部分人都曉得達爾文提出了「演化論」,可惜這是個含糊不精確的說法,雖不算錯,但卻遺漏了達爾文學說剛提出時創意十足、挑戰傳統、驚世駭俗的論點。
既被視為英雄也是妖魔,達爾文自然與哥白尼、克卜勒、牛頓、林奈、萊爾(Charles Lyell)、孟德爾、愛因斯坦、居禮夫人、波耳、海森堡、魏格納(Alfred Wegener)、哈伯(Edwin Hubble)、華生與克立克等人有所不同。達爾文之所以會那麼有名,部分是由於「達爾文主義」與「達爾文派」等浮泛的詞彙受到濫用,將達爾文的想法簡化如商標,但其實他的想法並沒有那麼容易化繁為簡。忘了「達爾文主義」吧!那根本是子虛烏有。除非你武斷地決定什麼算這個「門派」的想法、什麼又不算,但開山祖師達爾文自己可從沒這樣做過。那麼,什麼叫達爾文派?嗯.. 迷上外型華麗精緻的家鴿的人,大概就是達爾文派的吧!因為老祖宗達爾文自己就曾對鴿舍裡各色的球胸鴿、扇尾鴿等愛不釋手;喜歡單獨在住家附近散步好幾個小時的人也可以稱為達爾文派;甚至你將會看到,沒來由地反覆作嘔就是非常典型的達爾文作風。會這麼說是因為筆者想強調,達爾文並沒有發起某種運動或創立某個宗派,他從來沒有將科學原理編成教條,然後冠上自己的姓名,奉為圭臬。他是個喜歡躲在鄉下老窩的生物學家,寫書表達自己的見解。有時候他會犯錯,有時候他的想法前後不一;有時候他鑽研小細節,有時候他探索大問題。沒錯,他大部分發表的作品都有個共同的主題─所有生命一貫反映出演化的過程。但是他用包羅萬象的觀點來詳述這個主題,其中有些觀點環環相扣,至今對於生物學仍有價值;有些則不然。對於他的想法,逐一檢視會比全盤視為一體來得好。
前面提過的大科學家克卜勒,其理論在當時產生的衝擊與達爾文的狀況最為相似。達爾文延續了由克卜勒起頭的革命,否定人類位居宇宙的中心位置;達爾文將此認知從天文學延伸到生物學。他在早期的筆記本中抱怨:「人們常讚嘆﹃智慧人類﹄的出現。」達爾文對此並不那麼感興趣,反而接著寫道:「世上出現具有其他感官的昆蟲(insects with other senses)才值得讚嘆。」從這樣在當時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言論可以看出,達爾文從一開始沉思物種起源時就否定人類自認的半神地位,認為人類與其他物種一樣,在過去的歷史中飽經掙扎與改變。他不是人道主義者(雖然他總是很有人情味),讓他驚嘆的不是智人的大腦,而是蜜蜂定向與建築的本能。
筆者說達爾文「延續」而非「完成」克卜勒對抗人類本位說的革命,那是因為這場革命還在進行。許多人,甚至是宣稱接受達爾文演化論的人(不管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個理論),並不認同他著作中的所有內蘊。他有一個比演化更深層的想法,這就是他稱為「自然汰擇」(natural selection,或譯為天擇)的概念,認為這是演化發生的主要機制。根據達爾文的看法(至今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生物學驗證),自然汰擇是一種沒有目的但卻有效的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各個平等,不知道未來,不講求目標,只有結果;唯一的價值標準是成功存活與繁衍後代。生物從漫無目的的變異開始,經過自然的挑選、增殖,創造出井井有條、層次分明的生物圈。產生更多後代與生存競爭是其背後的驅動力,生物對環境的適應、生物的複雜性與變異則是其產物與副產物。這背後隱含的隨機性與創世論互相衝突,因為創世論主張世上生物的能力(包括人類的能力)、歷史、特定的棲息地,以及生物間的相互關係都反映出神的旨意,這讓支持創世論的人因此對自然汰擇的想法感到厭惡與恐懼。
這群人士在反對演化思潮的路上並不寂寞,近幾年來大可以感到欣慰,因為達爾文在一八五九年提出的觀點一直受到抵抗(至少在美國如此)。創世論的支持者在各州議會與當地學校董事會持續循政治途徑提出挑戰,但是大多沒有成功。重要的法院判決不支持他們(像是一九八七年的美國最高法院裁決路易斯安那州的反演化論法案違憲﹝愛德華(Edwards)對簿阿基拉德(Aguillard)﹞,還有二○○五年的基茲米勒﹝Kitzmiller﹞對簿多佛﹝Dover﹞),但是這反映一項事實:大部分民眾對此議題的立場遊移不定。在現代的美國社會中,大多數民眾對生物學的知識,仍停留在演化論未提出前的狀態。
你也許曾聽過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還是四○%,甚至更多?)不接受演化論。這裡有幾個數據是四五%、四七%和四四%。二○○四年十一月,蓋洛普民調中心完成一千多份電話訪問後,發現有四五%的受訪者同意以下陳述:在最近約一萬年內上帝創造了人類,而人類一開始的模樣就跟現在差不了多少(也就是同意創世論)。蓋洛普在做電訪時也提供另一項選擇:上帝引導人類從較原始的狀態發展了幾百萬年,結果有三八%的人同意(也就是同意有神論的演化論)。民調中只有十三% 的人同意人類不經上帝的指引,從其他生命形態發展而來(也就是同意唯物論的演化論)。剩下的人不做回應(也就是:「煩死了,我正在看電視!」的意思)。
這些民調結果中,最惹人注目的地方不在於有那麼多人反對演化論,而是過了一個世代後,六個相似的取樣呈現幾乎一模一樣的結果。蓋洛普在一九八二年也曾做了相同的民調,發現有四四%的受訪者同意是上帝而非演化創造了人類。到了一九九九年,數據更高達四七%,數字從未低於四四%。假如民調可信,將近半數美國人對物種起源的認知完全不受達爾文學說的影響。這幾年來,則有介於三七%與四○%的受訪者選擇「上帝引導演化」,也就是有神論的演化論─那與達爾文學說完全是兩碼子事。兩樣加總起來,介於八一%至八七%之間的美國人反對達爾文的人類演化觀點。
並非只有蓋洛普的調查反映這個現象。在更近一點的時間,沛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二○○五年七月做了一項調查發現,(兩千名受訪的美國人中有)四二%同意「物種一出現就是目前的模樣」,另外有十八%的人選擇有神論的演化論,認為至少人類的演化過程一定是在「神的旨意下」進行。沛尤的民調數據中,反對達爾文學說的人比蓋洛普民調少一些,只有六○%的美國人持反對意見,而非百分之八十幾。
也許那些民調不足以採信,也許在英國、瑞典或印度,數據會截然不同。也許是美國人混雜著懷疑論與基督教信仰的心態,也就是導致一九二五年斯科普斯審判案(the Scopes trial)的同一種心態,繼續促使許多美國人民寧可透過《聖經》而非科學來學習生物學。也許人類演化的問題會造成誤解,而且太過敏感;或許蓋洛普與沛尤應該要問:上帝創造的樹袋鼠是否一開始就是現在的模樣。或許.. 誰曉得呢?筆者並非要提出任何確鑿的解釋,來說明這種針對立論穩固的科學發現的極端懷疑心態及刻意唱反調。坦白說,筆者也很困惑,但是蓋洛普的民調,加上在美國公立學校教導演化論屢次造成對簿公堂,不只證明了達爾文的重要性歷久不衰,他與教育和政治氛圍也密切相關。
容筆者插些題外話:筆者是繞了一圈才開始接觸這個主題。筆者不是生物學家,也不是歷史學家,而且沒有任何學院背景的科學訓練。儘管如此,過去二十五年來筆者主要以科學記者為業,靠自學(換句話說,就是靠閱讀,特別是科學期刊)與不斷向專家請教來學習演化生物學與生態學。這些年來,筆者有許多時間在野外與生物學家共處,這種機會殊為難得。筆者因為受雜誌委託或寫書所需的研究,長途跋涉穿過熱帶叢林、溯河而上的足跡遍及蒙古與亞馬遜河流域,橫跨赤道上的熱帶大草原,尋找偏僻的島嶼,以及和全世界最聰明、最刻苦耐勞的野外生物學家在荒野間探險。這些經驗除了(緩慢地)增進筆者對某些生態系與物種的瞭解,以及對一些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基礎概念的瞭解,同時也讓筆者見識到,野外生物學家整體而言都是一群優秀的專業人士──聰明、熱情、耐煩、直爽、身心俱強。有的人欣賞士兵、外科醫生、消防隊員、天文物理學家、醫療佈道者或牛仔,筆者則欣賞野外生物學家。
筆者之所以研究達爾文,有一部分是因為他也是一位野外生物學家,他曾在奉派繪製南美洲海岸線航海圖的英國海軍戰艦小獵犬號(Beagle)上待了四年九個月零五天,那是他生命中的一段關鍵時期。那一趟航行從一八三一年開始到一八三六年結束,達爾文當時二十多歲,正是適合極力體驗艱苦與吸收新知、拓展眼界的年齡。小獵犬號的船員各司其職,年輕的達爾文便用船後拖曳的魚網收集浮游生物的標本,並且登岸深入內陸做進一步的採集與觀察。他從一開始毫無經驗,慢慢變成一位做事有條不紊而且觀察力敏銳的科學家。達爾文到過巴西、烏拉圭、阿根廷、智利、祕魯、紐西蘭、澳洲、南非與一些海上小島,包括維德角、亞速爾群島、大溪地、模里西斯、聖赫勒拿島與加拉巴哥群島。然而,一八三六年十月二日小獵犬號在英格蘭西南方的費爾茅斯(Falmouth)靠岸後,他就再也沒離開過英國。他當野外生物學家的漫遊生涯結束了,不僅是凱旋榮歸,而且至少有段時間樂於維持現狀。與他同時期的生物學家(像是華萊士﹝Alfred Ru
──程延年自然科學博物館資深研究員、成功大學地球科學所教授
E=MC2的雷射炫光,打在台北東區一○一的高樓壁面,全球同步歡呼慶賀的景象依稀猶存。場景一換,「物競、天擇、適應、存活」八字箴言,不似數學程式的簡約動人,卻是演化生物學的核心概念。瘋完愛因斯坦,瘋達爾文!
達爾文的熱潮方興未已
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是達爾文的二百歲生日。十九世紀的西方,兩位巨人因緣際會,在同一天降生(一八○九年二月十二日)。林肯廢止黑奴制度,開啟了人類心靈的解放,也是自由真諦的原動力量;而達爾文解脫生物學於超自然論與自然神學論的桎梏,發掘生命的「自然汰擇」大力。這誠然都是人類最罕見的心靈!同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正是《物種源始》這本曠世鉅作發表問市一五○年的日子。二月十二日當天,我正在北臺灣的基隆,為摯友許醫師籌備多年的精緻化石博物館開幕而共襄盛舉。博物館的橫匾書寫:達爾文。同一天,位於倫敦的英國自然史博物館盛大揭幕達爾文特展,名為:Darwin: Big Idea, Big Exhibition。迎接這個世紀盛事,全球平均每個星期就會上市出版一本達爾文/演化論的專書,讓我們目不暇給。
達爾文為什麼不會是咱們的孩子?教育的核心訓練與價值使然!這本書的作者既非生物學家,也非演化學家,更不具學府訓練的科學背景,他如何寫出這本精采的專書?他僅是一位自由撰稿作家呢!達爾文呢?進入愛丁堡研讀醫學,轉到劍橋學習神學;浪跡天涯近五年,「頓悟開竅」,創生了演化理論的核心概念與機制。在我們制式教育的菁英主義試鍊下,莘莘學子訓練成為考試的機器,而不是思考的機制,學習的「單扇」窄門,從我們那個年代的物理學,移化到醫學,到電腦資訊,到分子生物,到基因工程,到.. ,孩子們戴著鋼盔往前衝,撞到南牆不回頭。當我的孩子早熟地棄守資優班及聯考大關,以小留學生身分遠赴英倫,進到「九年級班」,我猛然覺醒:他們的教育體系有萬扇門,配了萬把鑰匙;教育,在摸索、試探取對了錀匙,進對了高門。開啟殿門,始見百官之富,宗廟之美。頂尖的華裔科學家許靖華教授曾經撰寫:為什麼牛頓不是中國人?他以兩大支系的文字起源及演變,針對以科學描繪、精準述說為訴求的西方文字,探究其思維模式之深意。這裡,我試圖以教育體系中思辨能力的培育,以及邏輯思考、理性辯駁、質疑傳統權威等核心議題,加以釐清並歸結之。
浮光掠影導讀
像是莎士比亞的大劇《哈姆雷特》,或者但丁的《神曲》,本書作者以編年、斷代的時間軸為經,以序列的事件中人物與事蹟為緯,編織、浮現出這位科學史和思想史中的巨人,以及這一本曠世傑作的精髓內涵,潑墨渲染,成其大器。以「引子」揭開了序幕,引領出七幕劇的精采戲碼。
小獵犬號探險航行四年九個月又五天,總計一千七百多個日子,真是足夠了!序曲以「凱旋歸故里」拉開了布幕。「真是足夠了」有兩層深義:一是茫茫大海中,孤寂、顛簸、風吹雨打、千辛萬苦,軀體上及生理上瀕臨極限,真正是受夠了;而心靈上則因周遊列國而大開眼界,驚艷、震撼、衝擊備至,真是足夠了──足夠豐富,足夠啟迪變革了!
第一幕(1837-1839),固有的架構瓦解了。這正是浪跡天涯返家之後,一個嶄新的頭腦、一個全新的思維,徹頭徹尾的變革,從蛹繭中羽化而登仙。維多利亞時代,整個社會主流的信仰、價值觀、科學核心認知與哲學思維,在達爾文歷經愛丁堡與劍橋的洗禮,歷經航程中五年敏銳的觀察、細膩的筆記、邏輯的推理思考,一切固有的架構似乎一夕之間全部崩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浴火重生的鳳凰,在迷霧中若隱若現。字裡行間,我們幾乎可以想像到那一顆年輕心靈的澎湃、激情、恐懼與不安。
第三幕(1846-1851),延怠發表,專注實驗。達爾文鎖起了天大祕密,天機無可洩露,轉而養起了成群的鴿子,玩賞起成堆的奇特小傢伙:藤壺(現生的與化石的標本)。為什麼?這可是歷史的懸案,卻也是最精采的自我沉寂、自我檢視、自我突破的關鍵時期。那正是解碼大自然「最神祕中的神祕」的一把鑰匙。所有藤壺個體之間的差異,群體系譜關係的隸屬,與分類系統的釐清建構,達爾文觸摸到了最底層、最內裡的神經,一幹就是八年的歲月,沉迷其中。他最終完成了四卷的藤壺分類圖鑑,獲得了英國皇家學會金質獎章的殊榮!藤壺,這群歸屬於節肢動物的不起眼小傢伙,在演化生物學的體系中,可是立下了大功勞。
第二幕(1842-1844),幾維鳥的一顆大蛋。達爾文開始抽絲剝繭,將所有近五年的毛片影像剪接、整理──準備要編織一齣好的劇本,說一場好的故事。他移居「唐屋」,離群索居,沉靜的空氣中,瀰漫著糾結、喧鬧雜陳的心思。依偎著親愛的終身伴侶艾瑪,仰仗著魚雁的往返,與維多利亞社群中頭腦最頂尖的一群菁英神交。一個偉大的演化思維體系,悄然茁生,很少人知道那將會震撼整個世界爾後的一百五十個年頭!從飼養、選種的「人擇」,推演到大自然中的「自然汰擇」(注:Natural Selection 。我一直以為慣用的「天擇」,約定成俗,是極不精準的譯名。天啊!怎麼會將「自然」譯成「天」呢?大自然中的選擇,有兩個關鍵步驟,一是淘汰不適者、二是較適應者存活。簡言之,Selection ,汰擇是也。因而,我一直譯成「自然汰擇」。),近二百多頁的初稿,一八四四年受孕、懷胎、成形,卻封存在保險櫃中,一鎖十五年,不見天日,為什麼?
第四幕(1848-1857),遠東寄來的雁鴨。高潮迭起,那一位際遇真可說是不幸的華萊士登場了,他攪亂了一池春水!亞馬遜的四年,東南亞蠻荒的流浪,靠著獵捕、販賣標本維生;卻也同時觀察、思索、註記、頓悟─孤寂,是成就偉大心靈的溫床。達爾文在「唐屋」困戰於藤壺的八年期間,在遙遠的東方孤島上,另一個偉大的心靈形影相隨,思索著同樣神祕未解的議題:變異、適應、地理分布、選擇、共同後裔……。當維多利亞的菁英們,萊爾、赫胥利、胡克紛紛登門拜訪達爾文的同時,華萊士只能跟他獵捕的雁鴨標本對話─其中一隻,打包妥當,就要寄給地球另一端的達爾文。達爾文警覺到遙遠的另一個心靈的浮現與威脅;而華萊士呢?正在為生活溫飽而「困戰求存」呢!
第五幕(1858-1859),令人厭煩的大卷冊。科學史上,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封短信(並附上了論文手稿),不但幾乎擊潰達爾文,同時也極可能改寫科學史,終於在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八日輾轉寄到了達爾文的手上!在科學的現實領域中,可真是理性與感性的雜陳;是協同合作與競爭奮戰的並行;是掠食者與獵物之間的較勁。這裡有寬容大度與諄諄教誨,也有掠奪邀功爭寵和堅齒利爪的血腥,不堪聞問。它終究是一個縮影、一個具體而微的小世界。達爾文心靈上的震驚可想而知。封存了近廿年的偉大創見,可能一夕成為泡影?復加愛子病危的折磨,達爾文立時求助於摯友萊爾與胡克,他們即刻介入了這一椿歷史懸案。直到半個世紀之後,華萊士在自傳中才娓娓道出未能共享盛名,僅僅坐上第二把交椅的情懷。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在林奈學會上,宣讀達爾文與華萊士手稿論文,是「菁英領導群」喬出來的一場戲碼。達爾文立時面臨放棄撰寫大書的初衷偉業,改而寫一帖精簡版的「摘要」─那就是最後成形的《論物種源始》第一版。這部演化生物學的聖經寶典,終於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的近午時刻問市了。當時正啜飲著下午茶的大主教妻子,聽聞這件事後,說了兩句話:「啊,最好那不是真的。唉,如果是真的,最好不要有太多人知道!」實情總是不盡如人意─《物種源始》修訂了六個版本,譯成多國文字,流傳百世,歷久而彌新─它,正是一場科學革命「典範轉移」的正型模式。
第六幕(1860 年以後),最適的概念。達爾文的演化論,不受青睞長達半個世紀。挑戰者眾,多半無功而退。兩個核心議題是:演化,可曾真正發生過?自然汰擇可真是主要的機制?顯然,演化論不是要挑戰上帝,而是要洞悉自然運作的真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之後一個半世紀,針對解碼大自然奧祕,有諸多的信仰體系瀰漫著─常民的、宗教的、科學的、形而上的、哲學的。達爾文式演化論同樣歷經多次的蛻變,嫁接了孟德爾式遺傳思維、古生物學的化石證據、分子生物學基因的洞悉,以至於最新胚胎學、發育學的崛起─所稱「演化發育生物學,Evo-Devo」的幽靈重現。演化論如虎添翼,翱翔天際。
第七幕終曲(1876-1882),最終的甲蟲隱喻。大劇接近了尾聲,達爾文也心身俱疲,打了一場還分不清勝負的大戰役,戰場尚待清理。持續永不歇止的工作,是達爾文的鎮靜劑;科學追尋,是達爾文終其一生的信仰。達爾文難以捉摸的個性,更加怪異了。或者較精準地說:一顆超越時空的偉大心靈,對當世之人更加陌生,他自己也對塵世間的「當世」更加難理解。達爾文持續研究食蟲植物,研究蘭花品種,研究起蚯蚓。他從不退休,只因為他幸運地,從未有一個可以引退的正職工作。誠然,達爾文的生命,不是「職業」,不是「事業」所可以框架的,那可是最崇高「志業」的實踐,至死不渝。達爾文在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日迫西山時分死去,走完了七十三年曲折迷離的一生。肉身軀體葬於西敏寺,與萊爾、牛頓、喬叟為鄰;而靈魂,卻四處飛揚、跨越時空,生生世世。
怎麼樣才能成為達爾文?
這本譯書,字裡行間像是音符般,跳躍在現實場景的推移與虛幻心靈的發掘、揣摹,深深撥動了讀者的心弦。譯者字字句句斟酌,誠屬高妙。信達雅兼顧,譯文允為箇中高手。要怎麼讀引言 凱旋歸故里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科學與社會的發展歷史上地位獨特。雖然他的名字家喻戶曉,但不表示他的想法也是如此(只有一項例外);雖然他在科學界的地位崇高,深具代表性,但不表示人們真的瞭解他。假如科學界要發行紙鈔,面額最小、發行量最大的鈔票上頭印的肯定是達爾文。他的臉還滿適合放在上面的──一張親切但木然的臉,就像一元美鈔上根據吉爾伯.史都華(Gilbert Stuart)的肖像畫所刻印的美國總統華盛頓頭像。而且達爾文也跟華盛頓一樣,高深莫測、緊張壓抑才是他們的真性情。每個人或多或少都知道達爾文是誰,曉得他做過什麼事、說過什麼話,而且大部分人都曉得達爾文提出了「演化論」,可惜這是個含糊不精確的說法,雖不算錯,但卻遺漏了達爾文學說剛提出時創意十足、挑戰傳統、驚世駭俗的論點。
既被視為英雄也是妖魔,達爾文自然與哥白尼、克卜勒、牛頓、林奈、萊爾(Charles Lyell)、孟德爾、愛因斯坦、居禮夫人、波耳、海森堡、魏格納(Alfred Wegener)、哈伯(Edwin Hubble)、華生與克立克等人有所不同。達爾文之所以會那麼有名,部分是由於「達爾文主義」與「達爾文派」等浮泛的詞彙受到濫用,將達爾文的想法簡化如商標,但其實他的想法並沒有那麼容易化繁為簡。忘了「達爾文主義」吧!那根本是子虛烏有。除非你武斷地決定什麼算這個「門派」的想法、什麼又不算,但開山祖師達爾文自己可從沒這樣做過。那麼,什麼叫達爾文派?嗯.. 迷上外型華麗精緻的家鴿的人,大概就是達爾文派的吧!因為老祖宗達爾文自己就曾對鴿舍裡各色的球胸鴿、扇尾鴿等愛不釋手;喜歡單獨在住家附近散步好幾個小時的人也可以稱為達爾文派;甚至你將會看到,沒來由地反覆作嘔就是非常典型的達爾文作風。會這麼說是因為筆者想強調,達爾文並沒有發起某種運動或創立某個宗派,他從來沒有將科學原理編成教條,然後冠上自己的姓名,奉為圭臬。他是個喜歡躲在鄉下老窩的生物學家,寫書表達自己的見解。有時候他會犯錯,有時候他的想法前後不一;有時候他鑽研小細節,有時候他探索大問題。沒錯,他大部分發表的作品都有個共同的主題─所有生命一貫反映出演化的過程。但是他用包羅萬象的觀點來詳述這個主題,其中有些觀點環環相扣,至今對於生物學仍有價值;有些則不然。對於他的想法,逐一檢視會比全盤視為一體來得好。
前面提過的大科學家克卜勒,其理論在當時產生的衝擊與達爾文的狀況最為相似。達爾文延續了由克卜勒起頭的革命,否定人類位居宇宙的中心位置;達爾文將此認知從天文學延伸到生物學。他在早期的筆記本中抱怨:「人們常讚嘆﹃智慧人類﹄的出現。」達爾文對此並不那麼感興趣,反而接著寫道:「世上出現具有其他感官的昆蟲(insects with other senses)才值得讚嘆。」從這樣在當時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言論可以看出,達爾文從一開始沉思物種起源時就否定人類自認的半神地位,認為人類與其他物種一樣,在過去的歷史中飽經掙扎與改變。他不是人道主義者(雖然他總是很有人情味),讓他驚嘆的不是智人的大腦,而是蜜蜂定向與建築的本能。
筆者說達爾文「延續」而非「完成」克卜勒對抗人類本位說的革命,那是因為這場革命還在進行。許多人,甚至是宣稱接受達爾文演化論的人(不管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個理論),並不認同他著作中的所有內蘊。他有一個比演化更深層的想法,這就是他稱為「自然汰擇」(natural selection,或譯為天擇)的概念,認為這是演化發生的主要機制。根據達爾文的看法(至今經歷了一百五十年的生物學驗證),自然汰擇是一種沒有目的但卻有效的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各個平等,不知道未來,不講求目標,只有結果;唯一的價值標準是成功存活與繁衍後代。生物從漫無目的的變異開始,經過自然的挑選、增殖,創造出井井有條、層次分明的生物圈。產生更多後代與生存競爭是其背後的驅動力,生物對環境的適應、生物的複雜性與變異則是其產物與副產物。這背後隱含的隨機性與創世論互相衝突,因為創世論主張世上生物的能力(包括人類的能力)、歷史、特定的棲息地,以及生物間的相互關係都反映出神的旨意,這讓支持創世論的人因此對自然汰擇的想法感到厭惡與恐懼。
這群人士在反對演化思潮的路上並不寂寞,近幾年來大可以感到欣慰,因為達爾文在一八五九年提出的觀點一直受到抵抗(至少在美國如此)。創世論的支持者在各州議會與當地學校董事會持續循政治途徑提出挑戰,但是大多沒有成功。重要的法院判決不支持他們(像是一九八七年的美國最高法院裁決路易斯安那州的反演化論法案違憲﹝愛德華(Edwards)對簿阿基拉德(Aguillard)﹞,還有二○○五年的基茲米勒﹝Kitzmiller﹞對簿多佛﹝Dover﹞),但是這反映一項事實:大部分民眾對此議題的立場遊移不定。在現代的美國社會中,大多數民眾對生物學的知識,仍停留在演化論未提出前的狀態。
你也許曾聽過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還是四○%,甚至更多?)不接受演化論。這裡有幾個數據是四五%、四七%和四四%。二○○四年十一月,蓋洛普民調中心完成一千多份電話訪問後,發現有四五%的受訪者同意以下陳述:在最近約一萬年內上帝創造了人類,而人類一開始的模樣就跟現在差不了多少(也就是同意創世論)。蓋洛普在做電訪時也提供另一項選擇:上帝引導人類從較原始的狀態發展了幾百萬年,結果有三八%的人同意(也就是同意有神論的演化論)。民調中只有十三% 的人同意人類不經上帝的指引,從其他生命形態發展而來(也就是同意唯物論的演化論)。剩下的人不做回應(也就是:「煩死了,我正在看電視!」的意思)。
這些民調結果中,最惹人注目的地方不在於有那麼多人反對演化論,而是過了一個世代後,六個相似的取樣呈現幾乎一模一樣的結果。蓋洛普在一九八二年也曾做了相同的民調,發現有四四%的受訪者同意是上帝而非演化創造了人類。到了一九九九年,數據更高達四七%,數字從未低於四四%。假如民調可信,將近半數美國人對物種起源的認知完全不受達爾文學說的影響。這幾年來,則有介於三七%與四○%的受訪者選擇「上帝引導演化」,也就是有神論的演化論─那與達爾文學說完全是兩碼子事。兩樣加總起來,介於八一%至八七%之間的美國人反對達爾文的人類演化觀點。
並非只有蓋洛普的調查反映這個現象。在更近一點的時間,沛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二○○五年七月做了一項調查發現,(兩千名受訪的美國人中有)四二%同意「物種一出現就是目前的模樣」,另外有十八%的人選擇有神論的演化論,認為至少人類的演化過程一定是在「神的旨意下」進行。沛尤的民調數據中,反對達爾文學說的人比蓋洛普民調少一些,只有六○%的美國人持反對意見,而非百分之八十幾。
也許那些民調不足以採信,也許在英國、瑞典或印度,數據會截然不同。也許是美國人混雜著懷疑論與基督教信仰的心態,也就是導致一九二五年斯科普斯審判案(the Scopes trial)的同一種心態,繼續促使許多美國人民寧可透過《聖經》而非科學來學習生物學。也許人類演化的問題會造成誤解,而且太過敏感;或許蓋洛普與沛尤應該要問:上帝創造的樹袋鼠是否一開始就是現在的模樣。或許.. 誰曉得呢?筆者並非要提出任何確鑿的解釋,來說明這種針對立論穩固的科學發現的極端懷疑心態及刻意唱反調。坦白說,筆者也很困惑,但是蓋洛普的民調,加上在美國公立學校教導演化論屢次造成對簿公堂,不只證明了達爾文的重要性歷久不衰,他與教育和政治氛圍也密切相關。
容筆者插些題外話:筆者是繞了一圈才開始接觸這個主題。筆者不是生物學家,也不是歷史學家,而且沒有任何學院背景的科學訓練。儘管如此,過去二十五年來筆者主要以科學記者為業,靠自學(換句話說,就是靠閱讀,特別是科學期刊)與不斷向專家請教來學習演化生物學與生態學。這些年來,筆者有許多時間在野外與生物學家共處,這種機會殊為難得。筆者因為受雜誌委託或寫書所需的研究,長途跋涉穿過熱帶叢林、溯河而上的足跡遍及蒙古與亞馬遜河流域,橫跨赤道上的熱帶大草原,尋找偏僻的島嶼,以及和全世界最聰明、最刻苦耐勞的野外生物學家在荒野間探險。這些經驗除了(緩慢地)增進筆者對某些生態系與物種的瞭解,以及對一些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基礎概念的瞭解,同時也讓筆者見識到,野外生物學家整體而言都是一群優秀的專業人士──聰明、熱情、耐煩、直爽、身心俱強。有的人欣賞士兵、外科醫生、消防隊員、天文物理學家、醫療佈道者或牛仔,筆者則欣賞野外生物學家。
筆者之所以研究達爾文,有一部分是因為他也是一位野外生物學家,他曾在奉派繪製南美洲海岸線航海圖的英國海軍戰艦小獵犬號(Beagle)上待了四年九個月零五天,那是他生命中的一段關鍵時期。那一趟航行從一八三一年開始到一八三六年結束,達爾文當時二十多歲,正是適合極力體驗艱苦與吸收新知、拓展眼界的年齡。小獵犬號的船員各司其職,年輕的達爾文便用船後拖曳的魚網收集浮游生物的標本,並且登岸深入內陸做進一步的採集與觀察。他從一開始毫無經驗,慢慢變成一位做事有條不紊而且觀察力敏銳的科學家。達爾文到過巴西、烏拉圭、阿根廷、智利、祕魯、紐西蘭、澳洲、南非與一些海上小島,包括維德角、亞速爾群島、大溪地、模里西斯、聖赫勒拿島與加拉巴哥群島。然而,一八三六年十月二日小獵犬號在英格蘭西南方的費爾茅斯(Falmouth)靠岸後,他就再也沒離開過英國。他當野外生物學家的漫遊生涯結束了,不僅是凱旋榮歸,而且至少有段時間樂於維持現狀。與他同時期的生物學家(像是華萊士﹝Alfred 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