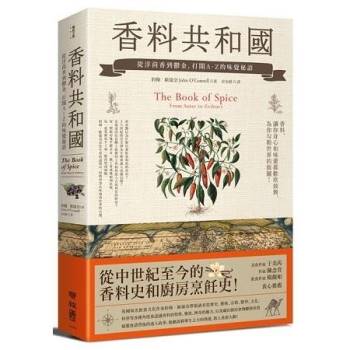芫荽(Coriander)
Coriandrum sativum
臭蟲是否肆虐,憑一個線索就可知道,那就是氣味。這種寄生蟲聚在一起,如果遭到驚擾,就會散發出「警報費洛蒙」互相警示,並且散開,結果就是如焚燒橡膠那樣可怕的氣味,讓普林尼想到一種鮮綠色的細莖植物,生有繖狀花序粉、藍或白色的小花。普林尼知道它可治癌症和瘧疾;萬一被神話中以螞蟻為食,生有雞腳的雙頭蛇(amphisbaena)──「彷彿由一張嘴噴出毒藥還不夠似的」咬了,也可服芫荽作為解藥 。那使人厭惡的氣味表示那株植物的果實尚未成熟:一旦成熟,氣味就消失了。
普林尼把這植物命名為coriandrum,來自拉丁文的coris(蟲),不過它也有其他的名字──在美國和中南美洲叫cilantro,在印度叫dhana,在中國叫香菜。反正它是芫荽屬的1年生植物,原生於南歐和地中海沿岸,但也能耐熱和乾旱,因此在世界各地都能栽植,尤其是在俄羅斯、印度、摩洛哥和澳洲。
人類使用芫荽已有很長的歷史,《出埃及記》、希臘邁錫尼文明時期克諾索斯(Knossos)的泥版殘片上就已提及芫荽子,埃及圖坦卡門法老的墓裡也發現了實物。儘管它們是進口而來,因此十分昂貴,但在埃及卻當作藥物大量使用。 《愛柏斯紙草紀事》就推薦以芫荽子作為止痛劑,不過它也建議用啤酒泡沫和半個洋蔥當作「防死的藥物」,因此可靠與否不得而知。
安德魯‧道比說,芫荽「如今似乎是典型的印度香料,也是常見的東南亞香草植物」,不過這種印象是錯的。它一直到西元前三世紀才大量引進印度;可能是阿育王由波斯進口, 因為阿育王「對於移植香草和藥草十分自豪」。芫荽的根和葉(有皺邊就像洋香菜一樣)及種子(黃褐色,有稜紋,有兩個分離的果瓣)都可食用,但似乎只有泰國才這樣做。其葉片尖銳,似柑橘類,種子甘甜,帶燒灼的柑橘味。 芫荽子應在磨成粉之後立即使用,不然風味很快就會消失。
芫荽子在塞浦路斯和希臘特別受歡迎,加在香腸中別具風味,若以檸檬醃汁浸泡,再加入青橄欖,有一種堅果般脆的口感。塞浦路斯招牌菜醃豬肉(afelia),就很依賴芫荽子的味道;希臘捲心菜沙拉(lahanosalata)亦然。水裡撒下芫荽子、丁香、肉桂和月桂葉煮醃豬腿,就讓人想起耶誕節的味道,至少我覺得如此。
就像葛縷子的種子一樣,黑麥麵包也會加入芫荽子。丹‧雷帕德(Dan Lepard)的《手工麵包》(The Handmade Loaf,2004) 就有一道絕佳的芫荽味黑麥麵包,味道和俄羅斯、烏克蘭傳統小吃店提供的差不多。芫荽子讓麵包「略帶苦味,就像柑橘的白瓤」,不過雷帕德承認,這是後天養成的口味 。
……
如今芫荽子依舊用來釀酒,主要是比利時式的上層發酵(top-fermented,發酵過程酵母會移動至液面)白啤酒,如豪格登白啤酒(Hoegaarden):「通常是在煮鍋煮沸最後5-20分鐘時,每桶加入2.11至8.3盎斯的芫荽。」煮沸時間短是為了確保香氣不會揮發。通常會把芫荽子配合柑橘皮使用。
就像葫蘆巴和薑黃一樣,芫荽子一向都是印度咖哩粉中的平價成份。不過它比較溫和而且可以配合其他成份,十分低調。它最重要的特質就是能調和不同的風味。它很可能是藉著南印酸豆湯(sambar)粉,而被引入英印族群版本的咖哩粉,因為芫荽是這種豆湯主要的香料。但在烹飪最後常加的黎巴嫩香料粉塔克利亞(taklia),和中東各地常用的巴哈拉特(baharat )(見〈混合香料總覽〉)中,它也舉足輕重。
參見: 葫蘆巴、薑黃。
孜然(Cumin)
Cumimum cyminum
就影響和普及這兩方面來看,1生小型草本植物小茴香的乾燥種子小茴香子,別稱孜然,是最重要的香料之一。它有強烈且持久的檸檬和紅糖香味,在許多國家市售和自製的咖哩粉中,都是主要成份,如波斯的阿德魏(advieh)、阿富汗的恰馬薩拉、中東的巴哈拉特、印度的格蘭馬薩拉,和北非的醃漬醬(chermoula,摩洛哥青醬)等混合香料。在歐洲,它的主要用途則只限於印度甜酸醬和德國酸菜,不過萊頓(Leyden)和高達(Gouda)等荷蘭起司也有添加孜然,另外如果以阿爾薩斯的芒斯特(Munster)起司配麵包,也會撒一點在上面食用。
伊麗莎白‧大衛告訴我們說,孜然溫韾的芳香「瀰漫著北非和埃及的露天市場,讓摩洛哥的燒烤羊肉串有它獨特的風味,也出現在地中海東部種種蔬菜、肉類和米飯的菜色中。」乾煎孜然可以帶出它堅果的香味,並緩和磨成粉會有的苦味。
孜然如果加在肉類,和羊肉最搭調;如果配蔬菜,則與胡蘿蔔相合(比如摩洛哥經典的生胡蘿蔔、大蒜和孜然沙拉),更教人吃驚的是,它和甜菜根也很速配:《河邊小屋每日青菜食譜!》(2011)的作者休‧芬姆利-威丁史塔(Hugh Fearnley-Whittingstal)就步古老食譜阿皮基烏斯《烹飪技法》的後塵,用甜菜根、胡桃和孜然的天然組合,達到了泥土甜美和溫暖的完美平衡。該不該加鷹嘴豆泥,大家莫衷一是,其討論的熱烈程度唯有鷹嘴豆泥是由阿拉伯人抑或猶太人發明差堪比擬。
……
孜然在埃及土生土長,是使用在葬禮塗香膏儀式中的諸多香料之一。在伊朗、土耳其、印度(舉世最大的香料生產及消費國)、中國、日本、美國和如索馬利亞和蘇丹等非洲國家都有栽植。它生有紫白色的花朵和嬌弱的莖,因此匐匍蔓延。它毛茸茸的錐形種子長3-6毫米,有成對或分開的心皮(carpels)。它們的長得很像葛縷子的種子,因此造成各種烹飪和字源的混亂──印度文兩者都用jeera表示,德文則用kummel代表葛縷子和孜然味的酒。更細緻的伊朗黑孜然Bunium bulbocastanum常被誤認為黑種草(nigella)。孜然需要像打穀那樣脫粒;泰奧弗拉斯托斯說,這種植物「在播種時一定要詛咒和虐待,收成才會漂亮且豐富」。如果做得恰當,孜然就會生出「比任何植物都多的果實」。
……
普林尼對孜然從不厭煩──在其他調味料顯得平淡之時,「永遠都歡迎」加一點孜然。在古代的羅馬,到處都可看得到孜然:磨成糊好加在麵包上,或者和鹽混合,製成孜然鹽,迄今在北非依舊流行。
阿皮基烏斯把孜然用在上百道食譜裡,包括搭配牡蠣和貝類的醬汁,這或許讓你以為它很昂貴,但其實它賤如塵土;比胡椒便宜。古希臘把守財奴稱為 kyminopristes,字面上的意思是「劈開小茴香子的人」。據說古羅馬哲學家皇帝馬可‧奧里略(著有《沉思錄》)因為節儉小氣,而被取了「孜然」這個綽號。不過在德國,孜然代表的是忠實:新娘在婚禮上捧著孜然、鹽和蒔蘿,表示發誓忠實於丈夫。
Coriandrum sativum
臭蟲是否肆虐,憑一個線索就可知道,那就是氣味。這種寄生蟲聚在一起,如果遭到驚擾,就會散發出「警報費洛蒙」互相警示,並且散開,結果就是如焚燒橡膠那樣可怕的氣味,讓普林尼想到一種鮮綠色的細莖植物,生有繖狀花序粉、藍或白色的小花。普林尼知道它可治癌症和瘧疾;萬一被神話中以螞蟻為食,生有雞腳的雙頭蛇(amphisbaena)──「彷彿由一張嘴噴出毒藥還不夠似的」咬了,也可服芫荽作為解藥 。那使人厭惡的氣味表示那株植物的果實尚未成熟:一旦成熟,氣味就消失了。
普林尼把這植物命名為coriandrum,來自拉丁文的coris(蟲),不過它也有其他的名字──在美國和中南美洲叫cilantro,在印度叫dhana,在中國叫香菜。反正它是芫荽屬的1年生植物,原生於南歐和地中海沿岸,但也能耐熱和乾旱,因此在世界各地都能栽植,尤其是在俄羅斯、印度、摩洛哥和澳洲。
人類使用芫荽已有很長的歷史,《出埃及記》、希臘邁錫尼文明時期克諾索斯(Knossos)的泥版殘片上就已提及芫荽子,埃及圖坦卡門法老的墓裡也發現了實物。儘管它們是進口而來,因此十分昂貴,但在埃及卻當作藥物大量使用。 《愛柏斯紙草紀事》就推薦以芫荽子作為止痛劑,不過它也建議用啤酒泡沫和半個洋蔥當作「防死的藥物」,因此可靠與否不得而知。
安德魯‧道比說,芫荽「如今似乎是典型的印度香料,也是常見的東南亞香草植物」,不過這種印象是錯的。它一直到西元前三世紀才大量引進印度;可能是阿育王由波斯進口, 因為阿育王「對於移植香草和藥草十分自豪」。芫荽的根和葉(有皺邊就像洋香菜一樣)及種子(黃褐色,有稜紋,有兩個分離的果瓣)都可食用,但似乎只有泰國才這樣做。其葉片尖銳,似柑橘類,種子甘甜,帶燒灼的柑橘味。 芫荽子應在磨成粉之後立即使用,不然風味很快就會消失。
芫荽子在塞浦路斯和希臘特別受歡迎,加在香腸中別具風味,若以檸檬醃汁浸泡,再加入青橄欖,有一種堅果般脆的口感。塞浦路斯招牌菜醃豬肉(afelia),就很依賴芫荽子的味道;希臘捲心菜沙拉(lahanosalata)亦然。水裡撒下芫荽子、丁香、肉桂和月桂葉煮醃豬腿,就讓人想起耶誕節的味道,至少我覺得如此。
就像葛縷子的種子一樣,黑麥麵包也會加入芫荽子。丹‧雷帕德(Dan Lepard)的《手工麵包》(The Handmade Loaf,2004) 就有一道絕佳的芫荽味黑麥麵包,味道和俄羅斯、烏克蘭傳統小吃店提供的差不多。芫荽子讓麵包「略帶苦味,就像柑橘的白瓤」,不過雷帕德承認,這是後天養成的口味 。
……
如今芫荽子依舊用來釀酒,主要是比利時式的上層發酵(top-fermented,發酵過程酵母會移動至液面)白啤酒,如豪格登白啤酒(Hoegaarden):「通常是在煮鍋煮沸最後5-20分鐘時,每桶加入2.11至8.3盎斯的芫荽。」煮沸時間短是為了確保香氣不會揮發。通常會把芫荽子配合柑橘皮使用。
就像葫蘆巴和薑黃一樣,芫荽子一向都是印度咖哩粉中的平價成份。不過它比較溫和而且可以配合其他成份,十分低調。它最重要的特質就是能調和不同的風味。它很可能是藉著南印酸豆湯(sambar)粉,而被引入英印族群版本的咖哩粉,因為芫荽是這種豆湯主要的香料。但在烹飪最後常加的黎巴嫩香料粉塔克利亞(taklia),和中東各地常用的巴哈拉特(baharat )(見〈混合香料總覽〉)中,它也舉足輕重。
參見: 葫蘆巴、薑黃。
孜然(Cumin)
Cumimum cyminum
就影響和普及這兩方面來看,1生小型草本植物小茴香的乾燥種子小茴香子,別稱孜然,是最重要的香料之一。它有強烈且持久的檸檬和紅糖香味,在許多國家市售和自製的咖哩粉中,都是主要成份,如波斯的阿德魏(advieh)、阿富汗的恰馬薩拉、中東的巴哈拉特、印度的格蘭馬薩拉,和北非的醃漬醬(chermoula,摩洛哥青醬)等混合香料。在歐洲,它的主要用途則只限於印度甜酸醬和德國酸菜,不過萊頓(Leyden)和高達(Gouda)等荷蘭起司也有添加孜然,另外如果以阿爾薩斯的芒斯特(Munster)起司配麵包,也會撒一點在上面食用。
伊麗莎白‧大衛告訴我們說,孜然溫韾的芳香「瀰漫著北非和埃及的露天市場,讓摩洛哥的燒烤羊肉串有它獨特的風味,也出現在地中海東部種種蔬菜、肉類和米飯的菜色中。」乾煎孜然可以帶出它堅果的香味,並緩和磨成粉會有的苦味。
孜然如果加在肉類,和羊肉最搭調;如果配蔬菜,則與胡蘿蔔相合(比如摩洛哥經典的生胡蘿蔔、大蒜和孜然沙拉),更教人吃驚的是,它和甜菜根也很速配:《河邊小屋每日青菜食譜!》(2011)的作者休‧芬姆利-威丁史塔(Hugh Fearnley-Whittingstal)就步古老食譜阿皮基烏斯《烹飪技法》的後塵,用甜菜根、胡桃和孜然的天然組合,達到了泥土甜美和溫暖的完美平衡。該不該加鷹嘴豆泥,大家莫衷一是,其討論的熱烈程度唯有鷹嘴豆泥是由阿拉伯人抑或猶太人發明差堪比擬。
……
孜然在埃及土生土長,是使用在葬禮塗香膏儀式中的諸多香料之一。在伊朗、土耳其、印度(舉世最大的香料生產及消費國)、中國、日本、美國和如索馬利亞和蘇丹等非洲國家都有栽植。它生有紫白色的花朵和嬌弱的莖,因此匐匍蔓延。它毛茸茸的錐形種子長3-6毫米,有成對或分開的心皮(carpels)。它們的長得很像葛縷子的種子,因此造成各種烹飪和字源的混亂──印度文兩者都用jeera表示,德文則用kummel代表葛縷子和孜然味的酒。更細緻的伊朗黑孜然Bunium bulbocastanum常被誤認為黑種草(nigella)。孜然需要像打穀那樣脫粒;泰奧弗拉斯托斯說,這種植物「在播種時一定要詛咒和虐待,收成才會漂亮且豐富」。如果做得恰當,孜然就會生出「比任何植物都多的果實」。
……
普林尼對孜然從不厭煩──在其他調味料顯得平淡之時,「永遠都歡迎」加一點孜然。在古代的羅馬,到處都可看得到孜然:磨成糊好加在麵包上,或者和鹽混合,製成孜然鹽,迄今在北非依舊流行。
阿皮基烏斯把孜然用在上百道食譜裡,包括搭配牡蠣和貝類的醬汁,這或許讓你以為它很昂貴,但其實它賤如塵土;比胡椒便宜。古希臘把守財奴稱為 kyminopristes,字面上的意思是「劈開小茴香子的人」。據說古羅馬哲學家皇帝馬可‧奧里略(著有《沉思錄》)因為節儉小氣,而被取了「孜然」這個綽號。不過在德國,孜然代表的是忠實:新娘在婚禮上捧著孜然、鹽和蒔蘿,表示發誓忠實於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