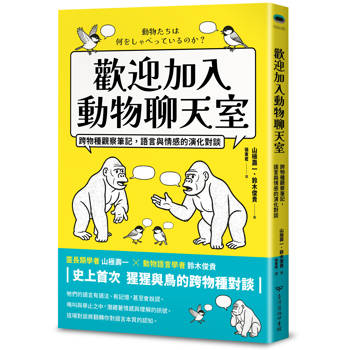前言
本書是變成鳥的研究者與變成大猩猩(金剛猩猩)的研究者,討論語言的演化及未來的記錄。
所謂變成鳥的研究者,是指負責寫這篇前言的我(鈴木俊貴)。以白頰山雀這種小鳥為對象,花了十七年以上的時間調查牠們叫聲的意思及扮演的角色。而且一年裡有長達八個月的時間窩在長野縣的森林裡,從日出到日落都在觀察牠們。為了要確認牠們叫聲的意思而對牠們錄音,並且進行各種各樣的分析和實驗。
在持續這樣的生活之間,我開始能夠想像白頰山雀在思考些什麼、又是怎麼看世界。現在則是連在空中有老鷹在飛,或是地上有蛇在爬,都是由白頰山雀告訴我。因為只要聽牠們的叫聲,我馬上就能懂牠們的意思。
所謂成為大猩猩的研究者,則是我的對談對象山極壽一先生※。知道他是誰的人應該很不少。他曾經擔任過京都大學的校長,也是研究大猩猩的世界性權威。
山極先生從二十幾歲時就加入大猩猩群,花了很長的年月研究牠們的行為與生態、社會結構。正如他已經出版的許多著書中也能明顯看出來的,在非洲的熱帶雨林中研究體型比人類還大的大猩猩,絕對不是件簡單的事情。既不像日本這樣被保障著有安全又方便的生活,也有必要習慣外國的文化與習俗。然後最重要的,應該是和大猩猩之間的距離感吧。為了要與大猩猩群做密切接觸、近距離進行觀察,察知牠們在想什麼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同時,也有必要讓大猩猩們理解研究者對牠們來說並不危險。這應該是跟白頰山雀的研究最大的差異吧。
縱然如此,我還是和山極先生有著共鳴。雖然在實現這場對談之前我沒有過跟他見面的機會,不過我讀過好幾本山極先生的書,並從其中感覺到他為了想要了解牠們的世界而讓自己成為對象動物的那種姿態和我出奇的相似。
讓我確信這個印象正確無誤的,是在山極先生的最終講義(退休前的最後一場演講)。那是於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線上舉辦的。雖然他是從京都大學的校長位置退休,卻完全沒有提到大學營運的事情,只是從頭到尾都在述說大猩猩的各種樣貌,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山極先生一定是由於知道大猩猩的世界、成為大猩猩,才會有說不完的事情想要傳達給人類社會。我也是研究白頰山雀,認識了牠們豐饒的世界,才有許多逐漸看清楚的事情。
二○二○年九月十二日。我造訪了位於京都市北區山中的總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山極先生在從京都大學退休後,到這個研究所擔任所長。我稍微有點緊張的進入所長室,跟山極先生打招呼的時候,他笑咪咪的跟我說:「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您呢。」然後在我剛開始絮絮說明我的研究內容時,他稱讚我:「鳥類竟然有文法,真是了不起的發現!」
我自己本身是隨著白頰山雀的研究逐漸有了進展之後開始對語言的演化產生興趣,並且也注意到類人猿的叫聲研究,山極先生也同樣是對語言的起源感到興趣,而知道了白頰山雀的研究。雖然我們是研究白頰山雀及大猩猩這兩種在外觀上完全不同的動物的兩個人,卻透過「語言」這個關鍵字而串連在一起。
對談是從分享白頰山雀與大猩猩的世界開始。白頰山雀的叫聲也存在著單字與文法、包含大猩猩在內的類人猿,隱藏著解讀人類語言的起源的線索等,對談十分的熱烈。在我忘我的講著自己喜歡的白頰山雀的事情的過程中,我的緊張完全消失,熱切的訴說在研究中注意到的事情以及新的學問的可能性。言語跟骨骼等不同,不會以化石的方式留下來。也因此雖然要解明演化的途徑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但是對於熟知為我們近緣種動物的類人猿的山極先生的言語演化論,我有著非常多「原來如此啊」很同感的部分。
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本書的最後一場對談後,我突然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不論在身分、年齡、研究資歷都跟我有極大差距的山極先生,從頭到尾都很一致的以和我對等的態度進行議論。這應該是山極先生除了尊重我的想法以外,也將他本身的主張傳達給我所致吧。
據說大猩猩的社會關係是不會想要贏過、壓倒對方。重視著對等關係來對待我的山極先生,真的就是位很像大猩猩的人。搞不好山極先生也覺得話多的我就像是白頰山雀般的人呢。
雖然當初是把對談的主題訂為動物們的語言,但是對談的內容卻逐漸擴大,延伸到了現代社會的問題,以及應該視為目標的未來樣貌。於是這本書不光只是介紹動物研究的最先端而已,也成為想要以語言當成關鍵字,從鳥類及大猩猩的立場來俯瞰人類社會的獨特書籍。假如這本書能夠成為讓大家思考語言是什麼、人類究竟是什麼樣的動物,以及真正的豐饒是什麼等等的契機,就是我們的榮幸。
鈴木俊貴
本書是變成鳥的研究者與變成大猩猩(金剛猩猩)的研究者,討論語言的演化及未來的記錄。
所謂變成鳥的研究者,是指負責寫這篇前言的我(鈴木俊貴)。以白頰山雀這種小鳥為對象,花了十七年以上的時間調查牠們叫聲的意思及扮演的角色。而且一年裡有長達八個月的時間窩在長野縣的森林裡,從日出到日落都在觀察牠們。為了要確認牠們叫聲的意思而對牠們錄音,並且進行各種各樣的分析和實驗。
在持續這樣的生活之間,我開始能夠想像白頰山雀在思考些什麼、又是怎麼看世界。現在則是連在空中有老鷹在飛,或是地上有蛇在爬,都是由白頰山雀告訴我。因為只要聽牠們的叫聲,我馬上就能懂牠們的意思。
所謂成為大猩猩的研究者,則是我的對談對象山極壽一先生※。知道他是誰的人應該很不少。他曾經擔任過京都大學的校長,也是研究大猩猩的世界性權威。
山極先生從二十幾歲時就加入大猩猩群,花了很長的年月研究牠們的行為與生態、社會結構。正如他已經出版的許多著書中也能明顯看出來的,在非洲的熱帶雨林中研究體型比人類還大的大猩猩,絕對不是件簡單的事情。既不像日本這樣被保障著有安全又方便的生活,也有必要習慣外國的文化與習俗。然後最重要的,應該是和大猩猩之間的距離感吧。為了要與大猩猩群做密切接觸、近距離進行觀察,察知牠們在想什麼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同時,也有必要讓大猩猩們理解研究者對牠們來說並不危險。這應該是跟白頰山雀的研究最大的差異吧。
縱然如此,我還是和山極先生有著共鳴。雖然在實現這場對談之前我沒有過跟他見面的機會,不過我讀過好幾本山極先生的書,並從其中感覺到他為了想要了解牠們的世界而讓自己成為對象動物的那種姿態和我出奇的相似。
讓我確信這個印象正確無誤的,是在山極先生的最終講義(退休前的最後一場演講)。那是於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線上舉辦的。雖然他是從京都大學的校長位置退休,卻完全沒有提到大學營運的事情,只是從頭到尾都在述說大猩猩的各種樣貌,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山極先生一定是由於知道大猩猩的世界、成為大猩猩,才會有說不完的事情想要傳達給人類社會。我也是研究白頰山雀,認識了牠們豐饒的世界,才有許多逐漸看清楚的事情。
二○二○年九月十二日。我造訪了位於京都市北區山中的總合地球環境學研究所。山極先生在從京都大學退休後,到這個研究所擔任所長。我稍微有點緊張的進入所長室,跟山極先生打招呼的時候,他笑咪咪的跟我說:「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您呢。」然後在我剛開始絮絮說明我的研究內容時,他稱讚我:「鳥類竟然有文法,真是了不起的發現!」
我自己本身是隨著白頰山雀的研究逐漸有了進展之後開始對語言的演化產生興趣,並且也注意到類人猿的叫聲研究,山極先生也同樣是對語言的起源感到興趣,而知道了白頰山雀的研究。雖然我們是研究白頰山雀及大猩猩這兩種在外觀上完全不同的動物的兩個人,卻透過「語言」這個關鍵字而串連在一起。
對談是從分享白頰山雀與大猩猩的世界開始。白頰山雀的叫聲也存在著單字與文法、包含大猩猩在內的類人猿,隱藏著解讀人類語言的起源的線索等,對談十分的熱烈。在我忘我的講著自己喜歡的白頰山雀的事情的過程中,我的緊張完全消失,熱切的訴說在研究中注意到的事情以及新的學問的可能性。言語跟骨骼等不同,不會以化石的方式留下來。也因此雖然要解明演化的途徑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但是對於熟知為我們近緣種動物的類人猿的山極先生的言語演化論,我有著非常多「原來如此啊」很同感的部分。
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本書的最後一場對談後,我突然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不論在身分、年齡、研究資歷都跟我有極大差距的山極先生,從頭到尾都很一致的以和我對等的態度進行議論。這應該是山極先生除了尊重我的想法以外,也將他本身的主張傳達給我所致吧。
據說大猩猩的社會關係是不會想要贏過、壓倒對方。重視著對等關係來對待我的山極先生,真的就是位很像大猩猩的人。搞不好山極先生也覺得話多的我就像是白頰山雀般的人呢。
雖然當初是把對談的主題訂為動物們的語言,但是對談的內容卻逐漸擴大,延伸到了現代社會的問題,以及應該視為目標的未來樣貌。於是這本書不光只是介紹動物研究的最先端而已,也成為想要以語言當成關鍵字,從鳥類及大猩猩的立場來俯瞰人類社會的獨特書籍。假如這本書能夠成為讓大家思考語言是什麼、人類究竟是什麼樣的動物,以及真正的豐饒是什麼等等的契機,就是我們的榮幸。
鈴木俊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