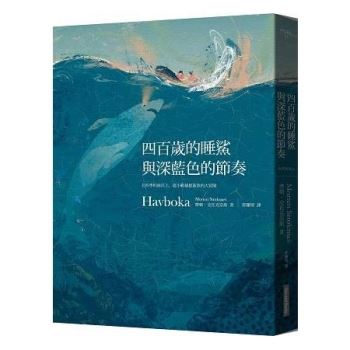1
三十五億年。從最初,最原始的生物形式在海中長成,到雨果.艾斯約德(Hugo Aasjord)在這個七月下旬的某個週六晚上打電話給我,中間相隔了這麼久的時間。那時,我正在奧斯陸(Oslo)市中心一場晚宴上,周遭人聲鼎沸。
「你看過下禮拜的天氣預報沒有?」他問道。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在等著一種特殊的天氣;這種天氣沒有陽光,並不溫暖,且必須持續有雨。我們所需要的,就是位於博德(Bodø)與羅浮敦群島(Lofoten,即挪威西岸峽灣〔Vestfjorden〕)之間海域的風勢;這是相當不容易的。我們心平氣和地等待著西岸峽灣的風勢平息下來。數週來,我一直關注天氣預報。預報指出會有強風或清爽的微風,但幾乎不曾出現過微風、和風或無風。最後,我幾乎忘記要跟他一起去冒險了。我選擇到奧斯陸慵懶地度假,享受暖熱的白晝與輕柔的夜晚,反而忘了察看天氣預報。
現在,我聽到雨果的聲音;他很討厭講電話,除非有重要的事情才會打電話來。我知道:長期以來的警報,終於要成真了。
「我明天就訂機票,週一下午抵達博德。」我回答道。
「很好,到時候見。」他「嗶」一聲掛斷電話。
我坐在前往博德的飛機上,透過窗戶,望見海面。思緒不斷飛馳。二十億年前,也許,除了幾個遠離彼此的小島以外,整個地球都被水所覆蓋著。至今,海水仍佔有地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積。有人曾寫過一篇文章,表示:這顆行星根本不該叫作「地球」,明明就該叫作「海球」。
直到我們抵達賀爾格蘭(Helgeland) 海岸為止,山岳、森林與荒野不斷地在我下方延展。到了那兒,地形景觀驟變成峽灣與擴張、膨脹的大海,直到海天之隔幻化成一道閃閃發亮、與鳥羽顏色極其相似的灰色,溶解在地平線上。每次我遠離奧斯陸、一路往北旅行時,總有同樣的感覺:從內陸、蟻垤、樹叢、河川、淡水湖和汩汩作響的沼澤裡解脫出來。來到奔放、一望無際的海邊,就像大航海時代傳遍五大洋,傳遍馬賽、利物浦、新加坡或蒙地維德亞(Montevideo)等港口的老歌那樣,富有韻律、像搖籃一樣規律地震顫著。甲板上的所有人試圖抓握住索具,或揚帆,或調帆,或縮帆。
上過岸的水手,猶如不安分的訪客。或許他們再也沒機會出海;然而,他們的言談與姿勢在在都顯示他們只是進行短期拜訪。他們永遠擺脫不了對大海的渴望。大海對他們的呼喚,必將得到含糊的答案。
我的高曾祖父在離開瑞典內陸、穿越峽谷與高山、開始向西行進時,想必也感受到了這股神祕的吸引力。他就像鮭魚一般,先沿著大河逆流而上,再順流而下,直到抵達大海為止。據說,他這趟旅程沒有任何目的,只想親眼見到大海。然而,他完全沒有回到出生地的打算。也許,他就是無法忍受在瑞典山區貧瘠的高原上,赤裸上身耕作、終其一生的想法。他終於抵達海岸;這一點就可看出,他不只個性剛強,更是個敢於行動的夢想家。他在此建立了家園,然後成為一艘貨輪上的船員。那艘船沉入太平洋海底的某處,船上所有人悉數溺斃。從海底來的人,彷彿就必須回到海裡去。這一切似乎證明了,他一直深知自己屬於那裡。無論如何,只要我一想到他,腦中就浮現這些念頭。
造就亞瑟.蘭波(Arthur Rimbaud)詩篇的,就是大海。大海使他的語言變得更加寬廣,使他創作出〈醉舟〉(Le Bateau ivre,一八七一年)一詩,引領他與其詩篇進入現代。詩中的第一人稱「我」,就是一艘想要無須操舵就能順著大河而下,直達海岸,來到公海,體驗自由之海的老舊貨輪。這艘貨輪陷入狂風暴雨之中,沉入海底,成為大海的一部分:「從此,我沉浸於詩之/海洋,如注入了星星和乳汁,/吞噬著蔚藍色的詩句;/那裡偶爾有沉醉的浮屍;/漂過,如船之殘骸,帶著蒼白的愉悅。」
在機上,我試圖重新建構自己記憶中〈醉舟〉的段落。洶湧的浪濤,彷彿一群歇斯底里的牲畜,衝擊著岩礁。海底,巨鯨利維坦就在漂搖的成串海草間腐爛著,將這條醉舟吸向自己,牢牢用觸角抓住。從暗黑的漩渦之上,這艘船可以聽見抹香鯨發情求歡的聲音。它看到被海蝨和可怕的海蛇、吟詠的金黃魚群、通電流的半月、黑黝黝的海馬圍繞著的爛醉如泥的沉船 ──人們只能相信,他們親眼見過這些東西⋯⋯
船身,使人目眩;她體驗到大海使人恐懼、解放的力量,連續不斷的波濤與浪花,直至進入一陣昏沉、麻木的狀態。就在此時,她開始想念陸地,想回到那個孩提時期所形塑,陰暗、沉靜的池塘。
蘭波十六歲寫下這首詩時,從未真正見過大海。
2
雨果住在史提根(Steigen)縣的天使島(Engeløya)上;我必須從博德搭乘北行的雙體快艇,穿越各群島與懸掛在峽灣口一個又一個飽經風霜的小村落,才能抵達該島。兩個小時的航程後,小艇抵達柏格島(Bogøy),一座橋連接起這個小村落與天使島。雨果正站在碼頭上,通知我一個好消息:我們很可能有釣餌了。一頭蘇格蘭高地牛三天前才被宰殺,殘肢與牛雜碎還放在戶外,隨時都可以去撿走。但當我們開車過橋到天使島時開始下雨,所以要等到第二天才能處理。我們在雨果偌大的獨棟房前停下來,他的獨棟房有著塔樓式的尖頂,地下室有畫廊,朝西方還可看到挪威西岸峽灣的景致。
來到雨果的莊園時,你很快就感覺到自己彷彿進入了海盜的營區之中。那些能夠沿著海岸、很可能是在掠奪之行時蒐集到的東西堆積在車庫旁邊,其他物品則擺在遠處面對迴廊的通道旁,活像展覽品或戰利品。他在海裡找到了許多寶貝,像是一艘舊船的舷,還有幾個陳舊的大錨。有個屬於一艘在挪威西岸峽灣史柯洛瓦(Skrova)島外海沉沒的英國拖網漁船的推進器,就像展覽品一樣擺在院子裡。庫房裡吊著一塊他從海裡打撈上來的俄語招牌。雨果本來相信,這塊招牌屬於一艘俄國船艦;結果發現那其實來自阿爾漢格爾斯克區(Arkhangelsk)以外,某個選區的選舉看板。除了主要庫房以外,雨果還蓋了另外兩間庫房,以及一座馬廄,裡面養著兩匹昔德蘭群島小馬,名叫盧娜(Luna)與韋斯勒格洛帕(Veslegloppa)。庫房裡面與旁邊,總是停放著各式小艇。本來還有一艘船艉低矮、像是隨時想航入地中海里維耶拉(Rivieraen)海岸的紅木色小遊艇;不過,他已把它賣掉了。
雨果一生從沒吃過炸魚條,而他也完全不打算品嘗一下這種食品。喝完由新採異株蕁麻、歐當歸和扁豆煮成的湯,還有品嘗完手工駝鹿肉香腸,一杯葡萄酒下肚之後,我們一起下樓,來到畫廊。雨果的油畫,大致上都非常抽象;但挪威北部人都傾向於將這種油畫解讀為大海與海岸的具體風景畫,把它們解讀為對自身居住環境的描繪。原因顯而易見,這些油畫都閃動著北極圈以北海面特有的光芒,特別是在冬季時。雨果繪畫的特點就是在暗黑(順便一說其實一點都不昏暗)的冬季清冷時光裡,那道好認的極地藍。即使畫中予人某種迷霧感,甚至撕裂感,光線仍然充滿整幅畫的視野。天幕的顏色被賦予某種深度與濃縮的光輝,而北極光則隨時能灼燒起來,帶來即興的迷幻效果。
他正在繪製的幾幅畫,取材位於天使島外側的迪爾特(Dietl) 加農砲陣地,德國人就在該地興建二戰時北歐最大、最昂貴的軍用基地。包括德國士兵與俄軍戰俘在內,總共有一萬人被安置在該處。他們在此建立挪威北部最大的城鎮之一,蓋起電影院、醫院、士兵與低階軍官營房、餐廳,甚至妓院,還從德國與波蘭運來妓女。整個街區充滿著雷達設備、氣象觀測站,以及啟用最先進科技的指揮中心。本來的目的是加農砲火要能涵括整個挪威西部的峽灣,射程達數十公里。後方的碉堡,更有數層樓之深。即使數以百計的俄軍戰俘死於強制勞動,雨果還是覺得這塊區域相當寧靜、平和。他在畫中,只將加農砲描繪成小小的立方體。
幾年前,雨果曾經展示過一隻抹上香膏防腐的死貓。這隻貓躲在路旁遠處老舊畜舍的牆縫裡,垂死著。在得知雨果即將於佛羅倫斯雙年展展出這隻貓後,《諾爾蘭日報》(Avisa Nordland)就曾質問:「一隻死貓,能算是藝術嗎?」
雨果的成長歷程,遍及西部峽灣的兩岸;他如果不是生活在海邊,就是在海上。他成為德國明斯特(Münster)頗負盛名的藝術學院最年輕的新生以後,才搬到當地就讀,這也是他一生當中,唯一一次長期定居在內陸。當時的街道上仍有許多戰後歸鄉的傷員,有人臉部毀容,有些撐著拐杖,有些斷了手臂,或者必須以輪椅代步。他和許多態度激進、樂於對越戰高談闊論的德國年輕人一起學習,但二戰則完全是不可談的禁忌。他喜歡坐火車朝漢堡北行,因為旅程上每向北經過一座城市,空氣就越來越新鮮,帶著一絲海水的味道。
他在取得證明其具備油畫、平面藝術與雕刻古典技巧的文憑後,才返回挪威。此外,他還多獲得了一項特質:他的身上,還殘留著一九七○年代德國青年學生的極端氣息。不過雨果的思想從未特別極端,所以這與政治無關;即使他戴著粗框眼鏡、留著小鬍子與黑色長髮,這也和他的個人風格沒什麼關係。這主要與如何做事、如何生活,一種不依循守舊的態度有關。此外,他還有一個惡習:每天下午五點整,定時收看德語的《德瑞克》(Derrick)影集。你要是膽敢在那時打攪他⋯⋯嗯,保證會有你受的!
在雨果帶我參觀過他的新作品以後,我們就上到小屋的閣樓。從那兒,我們得以眺望天使島那草木繁茂、欣欣向榮的內側。這是一個柔和的夏夜;露珠歇落在草地上與朝南的黑土上,寂靜覆蓋著沉睡中的大地。就連耳語也傳播到遠處。
我們周邊有許多由樺樹、花楸、柳樹與山楊樹所組成的落葉林。我走到房屋正面那外觀類似船橋樓甲板的露台上;樹梢間,一切其實相當不平靜。整座森林充滿著花粉,冒著葉綠素。我聽見鷸科、杓鷸與山鷸的叫聲;一片鳥鳴聲此起彼落,使耳朵需要多花點時間,才能區分彼此。黑琴雞咯咯叫著;畫眉呱呱啼著;杜鵑則發出咕咕聲。磧鶸鳴囀,麻雀與山雀啁啾著。杓鷸常發出不勝憂鬱、孤寂的口哨聲;但牠們也可能突然變換節奏,轉變成某種類似友善的機槍聲。其中一隻鳥的叫聲,聽來就像撞擊桌面的硬幣,是如此的乾涸。
一隻短耳鴞低空飛過;那對長長的翅膀,使牠不穩地顫動著。雪白的峽灣泛著光。在島上泛黑的山區地表,積雪尚未完全融化;山區的海拔頗高,高到這些年來共有三架軍機發生過撞山事故。其中兩架是一九七○年代初期的星座式戰鬥機,以及一九九九年的一架德製龍捲風式機;那架龍捲風式機在博爾灘(Bøsanda)一帶墜毀,所幸兩名飛行員已經彈射出來。在天使島與小丘島(Lundøya)之間,史嘉格斯塔海峽(Skagstadsundet)海域作業、正在手釣黑鱈的小漁船,將兩人救起。
鳥類生態,就是天使島與西部峽灣另一端史柯洛瓦島最主要的差異;只有海鳥會在那兒出現。雨果和梅特(Mette)正試圖在史柯洛瓦島上維持住一座魚肝油與漁產加工廠,名字就叫作艾斯約德(Aasjord)漁產加工廠。一如店名所暗示,這家加工廠一開始由雨果的家族所經營,但不幸在數十年後宣告倒閉,並於八○年代轉賣給他人。在雨果與梅特將加工廠買回時,廠房狀況已大不如前。現在,加工廠已經過局部重建,而且雨果和梅特對加工廠的未來可是有著長遠規劃的。
天使島是個農業聚落,島上的一切,包括居民的心態,都與史柯洛瓦島這種孤懸外海的漁業聚落大相逕庭。小島外,水深達數百公尺。位於史柯洛瓦島上的艾斯約德漁產加工廠,就是我們捕鯊計畫的基地。
回到小屋內,雨果講述著一個詭異、對他而言卻不特別奇怪的故事。我不知道這故事是怎麼發生的,然而,雨果有一項特殊技能,就是由某個事物能讓他想起另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他說道有那麼一次,他領養了一頭剛出生的公羊,公羊的主人表示這頭羊生來有缺陷,本來想將牠殺掉。雨果覺得這頭羊很可憐,就把牠領回家。他們把公羊養在廚房裡,準備在秋天時將牠宰殺。幾個星期後,雨果又在店裡遇見這位農夫,他隨口跟農夫說,這頭公羊形單影隻真是怪可憐的。結果,這農夫回去又給了他另一頭公羊。
經年累月下來,這兩頭公羊被他們養得相當肥壯 ── 牠們早已難以駕馭。沒多久,牠們就對社區內的孩童與犬隻構成了危險;於是,雨果把牠們送上小艇,野放到一處孤島上。牠們在孤島上,總有牧草可以啃食吧!
這兩頭公羊越長越肥,越長越壯;然而,牠們可是十足的忘恩負義。當雨果接近荒島時,牠們竟朝他游來;羊毛一浸水,變得又濕又重,牠們很可能溺斃,他不得不出手相救。一個美好的夏日,他登上荒島,本想散散心,享受閒暇時光,未曾預想到會有危險;不意其中一頭公羊竟在他即將下船之際,直接朝他衝來。故事的尾聲,他拉起毛衣袖口,向我展示上臂一道又深又長的傷痕。
不久後,這兩頭公羊就被屠宰了。全家人對牠們原有的同情心,至此蕩然無存。牠們的毛皮,至今還懸掛在小屋裡的一根枝條上。
兩年前像這樣的一個晚上,雨果首次提及格陵蘭鯊(håkjerringer,又稱睡鯊)。雨果的父親從八歲起就開始參與捕鯨活動,親眼見過格陵蘭鯊從海底游出、大口吞食鯨脂,而捕鯨船的船員則邊划動船身、邊在船邊抽取鯨油。他描述船員如何對一頭緊追不放的格陵蘭鯊賞了一魚叉,再設下防護網,才用起重機將牠舉起。儘管當時牠已被捕鯨叉貫穿背部倒掛著,處於瀕死狀態,但躺在甲板上的新鮮鯨肉還是被牠狼吞虎嚥地大嚼起來。
這頭格陵蘭鯊掙扎了許久才死去。牠可以躺在甲板上好幾個小時,一直盯著穿梭於甲板上的船員,嚇唬著那些強悍、老練的漁夫。雨果的父親也不忘告訴他,某個風光秀麗的夏日,他們沿著挪威西岸峽灣駕駛快速號(Hurtig)漁船時,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一個漁夫為了消暑跳下海游泳,這時一頭格陵蘭鯊突然在他數公尺遠的地方衝出海面,那個漁夫嚇得瞬間游回船上,讓其他船員樂不可支。
這類故事引燃了雨果的想像,四十年來在他體內不斷地發酵、沸騰著。每當他描述格陵蘭鯊時,眼睛閃動著奇異的光芒,口吻激動異常。他從未忘記這些在孩提時代就聽過的故事。雨果見過絕大多數的海底生物與魚類;然而,他從未親眼見過格陵蘭鯊。
我也沒親眼見過格陵蘭鯊。這個意念,從直覺上完全讓我上鉤了,雨果無須大費周章,說服我加入獵鯊活動。我也在海邊長大,從孩提時代就開始釣魚。當獵物上鉤時,我總期待著從海底衝出的會是何種生物,這種感覺很吸引人。
海平面下真是別有洞天,藏著許多我根本一無所知的生物。我在書中見過許多海底已知物種的圖片,那不僅僅是「引人入勝」可以形容的:海底的生命,遠比陸地上的生物精彩、富麗得多。令人驚異不已的生物在水中到處悠游,幾乎就在我們的鼻子下方徜徉著;然而我們卻看不見牠們、感覺不到牠們,只能憑空猜想水面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從那時起,海洋對我的吸引力堪稱無可磨滅。許多我們小時候覺得神祕、好玩又刺激的事物,都在我們的青少年時期一一失去吸引力;然而,海洋卻變得越來越寬廣、越來越深厚越來越神祕。或許,這和隔代遺傳也脫不了關係,這是一項跨越數個世代的特質,而我就從那葬身海底的高曾祖父身上,傳承了這項特質。
雨果的捕鯊計畫,也自有其吸引力,這是我當時並未能意識到,甚至現在也還未能看得清楚,是在我眼界以外的體驗 ── 猶如燈塔旋轉式的探照燈,用光束將黑夜劈開。
當我毫不猶疑地回答他「走,我們出海捕鯊去!」的同時,其實還有許多應該要做的事情。
三十五億年。從最初,最原始的生物形式在海中長成,到雨果.艾斯約德(Hugo Aasjord)在這個七月下旬的某個週六晚上打電話給我,中間相隔了這麼久的時間。那時,我正在奧斯陸(Oslo)市中心一場晚宴上,周遭人聲鼎沸。
「你看過下禮拜的天氣預報沒有?」他問道。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在等著一種特殊的天氣;這種天氣沒有陽光,並不溫暖,且必須持續有雨。我們所需要的,就是位於博德(Bodø)與羅浮敦群島(Lofoten,即挪威西岸峽灣〔Vestfjorden〕)之間海域的風勢;這是相當不容易的。我們心平氣和地等待著西岸峽灣的風勢平息下來。數週來,我一直關注天氣預報。預報指出會有強風或清爽的微風,但幾乎不曾出現過微風、和風或無風。最後,我幾乎忘記要跟他一起去冒險了。我選擇到奧斯陸慵懶地度假,享受暖熱的白晝與輕柔的夜晚,反而忘了察看天氣預報。
現在,我聽到雨果的聲音;他很討厭講電話,除非有重要的事情才會打電話來。我知道:長期以來的警報,終於要成真了。
「我明天就訂機票,週一下午抵達博德。」我回答道。
「很好,到時候見。」他「嗶」一聲掛斷電話。
我坐在前往博德的飛機上,透過窗戶,望見海面。思緒不斷飛馳。二十億年前,也許,除了幾個遠離彼此的小島以外,整個地球都被水所覆蓋著。至今,海水仍佔有地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積。有人曾寫過一篇文章,表示:這顆行星根本不該叫作「地球」,明明就該叫作「海球」。
直到我們抵達賀爾格蘭(Helgeland) 海岸為止,山岳、森林與荒野不斷地在我下方延展。到了那兒,地形景觀驟變成峽灣與擴張、膨脹的大海,直到海天之隔幻化成一道閃閃發亮、與鳥羽顏色極其相似的灰色,溶解在地平線上。每次我遠離奧斯陸、一路往北旅行時,總有同樣的感覺:從內陸、蟻垤、樹叢、河川、淡水湖和汩汩作響的沼澤裡解脫出來。來到奔放、一望無際的海邊,就像大航海時代傳遍五大洋,傳遍馬賽、利物浦、新加坡或蒙地維德亞(Montevideo)等港口的老歌那樣,富有韻律、像搖籃一樣規律地震顫著。甲板上的所有人試圖抓握住索具,或揚帆,或調帆,或縮帆。
上過岸的水手,猶如不安分的訪客。或許他們再也沒機會出海;然而,他們的言談與姿勢在在都顯示他們只是進行短期拜訪。他們永遠擺脫不了對大海的渴望。大海對他們的呼喚,必將得到含糊的答案。
我的高曾祖父在離開瑞典內陸、穿越峽谷與高山、開始向西行進時,想必也感受到了這股神祕的吸引力。他就像鮭魚一般,先沿著大河逆流而上,再順流而下,直到抵達大海為止。據說,他這趟旅程沒有任何目的,只想親眼見到大海。然而,他完全沒有回到出生地的打算。也許,他就是無法忍受在瑞典山區貧瘠的高原上,赤裸上身耕作、終其一生的想法。他終於抵達海岸;這一點就可看出,他不只個性剛強,更是個敢於行動的夢想家。他在此建立了家園,然後成為一艘貨輪上的船員。那艘船沉入太平洋海底的某處,船上所有人悉數溺斃。從海底來的人,彷彿就必須回到海裡去。這一切似乎證明了,他一直深知自己屬於那裡。無論如何,只要我一想到他,腦中就浮現這些念頭。
造就亞瑟.蘭波(Arthur Rimbaud)詩篇的,就是大海。大海使他的語言變得更加寬廣,使他創作出〈醉舟〉(Le Bateau ivre,一八七一年)一詩,引領他與其詩篇進入現代。詩中的第一人稱「我」,就是一艘想要無須操舵就能順著大河而下,直達海岸,來到公海,體驗自由之海的老舊貨輪。這艘貨輪陷入狂風暴雨之中,沉入海底,成為大海的一部分:「從此,我沉浸於詩之/海洋,如注入了星星和乳汁,/吞噬著蔚藍色的詩句;/那裡偶爾有沉醉的浮屍;/漂過,如船之殘骸,帶著蒼白的愉悅。」
在機上,我試圖重新建構自己記憶中〈醉舟〉的段落。洶湧的浪濤,彷彿一群歇斯底里的牲畜,衝擊著岩礁。海底,巨鯨利維坦就在漂搖的成串海草間腐爛著,將這條醉舟吸向自己,牢牢用觸角抓住。從暗黑的漩渦之上,這艘船可以聽見抹香鯨發情求歡的聲音。它看到被海蝨和可怕的海蛇、吟詠的金黃魚群、通電流的半月、黑黝黝的海馬圍繞著的爛醉如泥的沉船 ──人們只能相信,他們親眼見過這些東西⋯⋯
船身,使人目眩;她體驗到大海使人恐懼、解放的力量,連續不斷的波濤與浪花,直至進入一陣昏沉、麻木的狀態。就在此時,她開始想念陸地,想回到那個孩提時期所形塑,陰暗、沉靜的池塘。
蘭波十六歲寫下這首詩時,從未真正見過大海。
2
雨果住在史提根(Steigen)縣的天使島(Engeløya)上;我必須從博德搭乘北行的雙體快艇,穿越各群島與懸掛在峽灣口一個又一個飽經風霜的小村落,才能抵達該島。兩個小時的航程後,小艇抵達柏格島(Bogøy),一座橋連接起這個小村落與天使島。雨果正站在碼頭上,通知我一個好消息:我們很可能有釣餌了。一頭蘇格蘭高地牛三天前才被宰殺,殘肢與牛雜碎還放在戶外,隨時都可以去撿走。但當我們開車過橋到天使島時開始下雨,所以要等到第二天才能處理。我們在雨果偌大的獨棟房前停下來,他的獨棟房有著塔樓式的尖頂,地下室有畫廊,朝西方還可看到挪威西岸峽灣的景致。
來到雨果的莊園時,你很快就感覺到自己彷彿進入了海盜的營區之中。那些能夠沿著海岸、很可能是在掠奪之行時蒐集到的東西堆積在車庫旁邊,其他物品則擺在遠處面對迴廊的通道旁,活像展覽品或戰利品。他在海裡找到了許多寶貝,像是一艘舊船的舷,還有幾個陳舊的大錨。有個屬於一艘在挪威西岸峽灣史柯洛瓦(Skrova)島外海沉沒的英國拖網漁船的推進器,就像展覽品一樣擺在院子裡。庫房裡吊著一塊他從海裡打撈上來的俄語招牌。雨果本來相信,這塊招牌屬於一艘俄國船艦;結果發現那其實來自阿爾漢格爾斯克區(Arkhangelsk)以外,某個選區的選舉看板。除了主要庫房以外,雨果還蓋了另外兩間庫房,以及一座馬廄,裡面養著兩匹昔德蘭群島小馬,名叫盧娜(Luna)與韋斯勒格洛帕(Veslegloppa)。庫房裡面與旁邊,總是停放著各式小艇。本來還有一艘船艉低矮、像是隨時想航入地中海里維耶拉(Rivieraen)海岸的紅木色小遊艇;不過,他已把它賣掉了。
雨果一生從沒吃過炸魚條,而他也完全不打算品嘗一下這種食品。喝完由新採異株蕁麻、歐當歸和扁豆煮成的湯,還有品嘗完手工駝鹿肉香腸,一杯葡萄酒下肚之後,我們一起下樓,來到畫廊。雨果的油畫,大致上都非常抽象;但挪威北部人都傾向於將這種油畫解讀為大海與海岸的具體風景畫,把它們解讀為對自身居住環境的描繪。原因顯而易見,這些油畫都閃動著北極圈以北海面特有的光芒,特別是在冬季時。雨果繪畫的特點就是在暗黑(順便一說其實一點都不昏暗)的冬季清冷時光裡,那道好認的極地藍。即使畫中予人某種迷霧感,甚至撕裂感,光線仍然充滿整幅畫的視野。天幕的顏色被賦予某種深度與濃縮的光輝,而北極光則隨時能灼燒起來,帶來即興的迷幻效果。
他正在繪製的幾幅畫,取材位於天使島外側的迪爾特(Dietl) 加農砲陣地,德國人就在該地興建二戰時北歐最大、最昂貴的軍用基地。包括德國士兵與俄軍戰俘在內,總共有一萬人被安置在該處。他們在此建立挪威北部最大的城鎮之一,蓋起電影院、醫院、士兵與低階軍官營房、餐廳,甚至妓院,還從德國與波蘭運來妓女。整個街區充滿著雷達設備、氣象觀測站,以及啟用最先進科技的指揮中心。本來的目的是加農砲火要能涵括整個挪威西部的峽灣,射程達數十公里。後方的碉堡,更有數層樓之深。即使數以百計的俄軍戰俘死於強制勞動,雨果還是覺得這塊區域相當寧靜、平和。他在畫中,只將加農砲描繪成小小的立方體。
幾年前,雨果曾經展示過一隻抹上香膏防腐的死貓。這隻貓躲在路旁遠處老舊畜舍的牆縫裡,垂死著。在得知雨果即將於佛羅倫斯雙年展展出這隻貓後,《諾爾蘭日報》(Avisa Nordland)就曾質問:「一隻死貓,能算是藝術嗎?」
雨果的成長歷程,遍及西部峽灣的兩岸;他如果不是生活在海邊,就是在海上。他成為德國明斯特(Münster)頗負盛名的藝術學院最年輕的新生以後,才搬到當地就讀,這也是他一生當中,唯一一次長期定居在內陸。當時的街道上仍有許多戰後歸鄉的傷員,有人臉部毀容,有些撐著拐杖,有些斷了手臂,或者必須以輪椅代步。他和許多態度激進、樂於對越戰高談闊論的德國年輕人一起學習,但二戰則完全是不可談的禁忌。他喜歡坐火車朝漢堡北行,因為旅程上每向北經過一座城市,空氣就越來越新鮮,帶著一絲海水的味道。
他在取得證明其具備油畫、平面藝術與雕刻古典技巧的文憑後,才返回挪威。此外,他還多獲得了一項特質:他的身上,還殘留著一九七○年代德國青年學生的極端氣息。不過雨果的思想從未特別極端,所以這與政治無關;即使他戴著粗框眼鏡、留著小鬍子與黑色長髮,這也和他的個人風格沒什麼關係。這主要與如何做事、如何生活,一種不依循守舊的態度有關。此外,他還有一個惡習:每天下午五點整,定時收看德語的《德瑞克》(Derrick)影集。你要是膽敢在那時打攪他⋯⋯嗯,保證會有你受的!
在雨果帶我參觀過他的新作品以後,我們就上到小屋的閣樓。從那兒,我們得以眺望天使島那草木繁茂、欣欣向榮的內側。這是一個柔和的夏夜;露珠歇落在草地上與朝南的黑土上,寂靜覆蓋著沉睡中的大地。就連耳語也傳播到遠處。
我們周邊有許多由樺樹、花楸、柳樹與山楊樹所組成的落葉林。我走到房屋正面那外觀類似船橋樓甲板的露台上;樹梢間,一切其實相當不平靜。整座森林充滿著花粉,冒著葉綠素。我聽見鷸科、杓鷸與山鷸的叫聲;一片鳥鳴聲此起彼落,使耳朵需要多花點時間,才能區分彼此。黑琴雞咯咯叫著;畫眉呱呱啼著;杜鵑則發出咕咕聲。磧鶸鳴囀,麻雀與山雀啁啾著。杓鷸常發出不勝憂鬱、孤寂的口哨聲;但牠們也可能突然變換節奏,轉變成某種類似友善的機槍聲。其中一隻鳥的叫聲,聽來就像撞擊桌面的硬幣,是如此的乾涸。
一隻短耳鴞低空飛過;那對長長的翅膀,使牠不穩地顫動著。雪白的峽灣泛著光。在島上泛黑的山區地表,積雪尚未完全融化;山區的海拔頗高,高到這些年來共有三架軍機發生過撞山事故。其中兩架是一九七○年代初期的星座式戰鬥機,以及一九九九年的一架德製龍捲風式機;那架龍捲風式機在博爾灘(Bøsanda)一帶墜毀,所幸兩名飛行員已經彈射出來。在天使島與小丘島(Lundøya)之間,史嘉格斯塔海峽(Skagstadsundet)海域作業、正在手釣黑鱈的小漁船,將兩人救起。
鳥類生態,就是天使島與西部峽灣另一端史柯洛瓦島最主要的差異;只有海鳥會在那兒出現。雨果和梅特(Mette)正試圖在史柯洛瓦島上維持住一座魚肝油與漁產加工廠,名字就叫作艾斯約德(Aasjord)漁產加工廠。一如店名所暗示,這家加工廠一開始由雨果的家族所經營,但不幸在數十年後宣告倒閉,並於八○年代轉賣給他人。在雨果與梅特將加工廠買回時,廠房狀況已大不如前。現在,加工廠已經過局部重建,而且雨果和梅特對加工廠的未來可是有著長遠規劃的。
天使島是個農業聚落,島上的一切,包括居民的心態,都與史柯洛瓦島這種孤懸外海的漁業聚落大相逕庭。小島外,水深達數百公尺。位於史柯洛瓦島上的艾斯約德漁產加工廠,就是我們捕鯊計畫的基地。
回到小屋內,雨果講述著一個詭異、對他而言卻不特別奇怪的故事。我不知道這故事是怎麼發生的,然而,雨果有一項特殊技能,就是由某個事物能讓他想起另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他說道有那麼一次,他領養了一頭剛出生的公羊,公羊的主人表示這頭羊生來有缺陷,本來想將牠殺掉。雨果覺得這頭羊很可憐,就把牠領回家。他們把公羊養在廚房裡,準備在秋天時將牠宰殺。幾個星期後,雨果又在店裡遇見這位農夫,他隨口跟農夫說,這頭公羊形單影隻真是怪可憐的。結果,這農夫回去又給了他另一頭公羊。
經年累月下來,這兩頭公羊被他們養得相當肥壯 ── 牠們早已難以駕馭。沒多久,牠們就對社區內的孩童與犬隻構成了危險;於是,雨果把牠們送上小艇,野放到一處孤島上。牠們在孤島上,總有牧草可以啃食吧!
這兩頭公羊越長越肥,越長越壯;然而,牠們可是十足的忘恩負義。當雨果接近荒島時,牠們竟朝他游來;羊毛一浸水,變得又濕又重,牠們很可能溺斃,他不得不出手相救。一個美好的夏日,他登上荒島,本想散散心,享受閒暇時光,未曾預想到會有危險;不意其中一頭公羊竟在他即將下船之際,直接朝他衝來。故事的尾聲,他拉起毛衣袖口,向我展示上臂一道又深又長的傷痕。
不久後,這兩頭公羊就被屠宰了。全家人對牠們原有的同情心,至此蕩然無存。牠們的毛皮,至今還懸掛在小屋裡的一根枝條上。
兩年前像這樣的一個晚上,雨果首次提及格陵蘭鯊(håkjerringer,又稱睡鯊)。雨果的父親從八歲起就開始參與捕鯨活動,親眼見過格陵蘭鯊從海底游出、大口吞食鯨脂,而捕鯨船的船員則邊划動船身、邊在船邊抽取鯨油。他描述船員如何對一頭緊追不放的格陵蘭鯊賞了一魚叉,再設下防護網,才用起重機將牠舉起。儘管當時牠已被捕鯨叉貫穿背部倒掛著,處於瀕死狀態,但躺在甲板上的新鮮鯨肉還是被牠狼吞虎嚥地大嚼起來。
這頭格陵蘭鯊掙扎了許久才死去。牠可以躺在甲板上好幾個小時,一直盯著穿梭於甲板上的船員,嚇唬著那些強悍、老練的漁夫。雨果的父親也不忘告訴他,某個風光秀麗的夏日,他們沿著挪威西岸峽灣駕駛快速號(Hurtig)漁船時,發生過這麼一件事:一個漁夫為了消暑跳下海游泳,這時一頭格陵蘭鯊突然在他數公尺遠的地方衝出海面,那個漁夫嚇得瞬間游回船上,讓其他船員樂不可支。
這類故事引燃了雨果的想像,四十年來在他體內不斷地發酵、沸騰著。每當他描述格陵蘭鯊時,眼睛閃動著奇異的光芒,口吻激動異常。他從未忘記這些在孩提時代就聽過的故事。雨果見過絕大多數的海底生物與魚類;然而,他從未親眼見過格陵蘭鯊。
我也沒親眼見過格陵蘭鯊。這個意念,從直覺上完全讓我上鉤了,雨果無須大費周章,說服我加入獵鯊活動。我也在海邊長大,從孩提時代就開始釣魚。當獵物上鉤時,我總期待著從海底衝出的會是何種生物,這種感覺很吸引人。
海平面下真是別有洞天,藏著許多我根本一無所知的生物。我在書中見過許多海底已知物種的圖片,那不僅僅是「引人入勝」可以形容的:海底的生命,遠比陸地上的生物精彩、富麗得多。令人驚異不已的生物在水中到處悠游,幾乎就在我們的鼻子下方徜徉著;然而我們卻看不見牠們、感覺不到牠們,只能憑空猜想水面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從那時起,海洋對我的吸引力堪稱無可磨滅。許多我們小時候覺得神祕、好玩又刺激的事物,都在我們的青少年時期一一失去吸引力;然而,海洋卻變得越來越寬廣、越來越深厚越來越神祕。或許,這和隔代遺傳也脫不了關係,這是一項跨越數個世代的特質,而我就從那葬身海底的高曾祖父身上,傳承了這項特質。
雨果的捕鯊計畫,也自有其吸引力,這是我當時並未能意識到,甚至現在也還未能看得清楚,是在我眼界以外的體驗 ── 猶如燈塔旋轉式的探照燈,用光束將黑夜劈開。
當我毫不猶疑地回答他「走,我們出海捕鯊去!」的同時,其實還有許多應該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