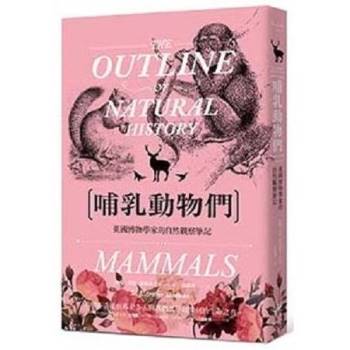不眠不休的實驗家
要了解猿猴,我們必須認清一件事,就是牠們擁有一顆不凡的大腦。猿猴的腦部已經發展到很高程度,當我們看進一隻活力充沛猴兒的雙眼,總覺得自己似乎能看見萬千思緒正在牠心中輪轉。猿猴總是靜不下來,而這正是因為牠們具有高度智能,所以才會如此。美國心理學家桑代克教授(Edward L. Thorndike)如是說:「看看一隻貓或一隻狗,牠們會做的事情相較之下十分有限,而且就算長時間閒散也不覺無聊。「看看一隻猿猴,你就發現牠會做的事情多到不勝枚舉,一切事物對牠都有吸引力,牠常只是因為好動而活動。」
只要猿猴們感覺到身邊有未解之謎,就永遠無法停下手來,這個實際的現象讓我們明白桑代克教授所言不虛。作家及詩人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筆下,那隻貓鼬李奇─蒂奇─塔威(Riki-Tiki-Tavi)的故事就是如此,牠終生的志願就是要探索新知,但比起貓鼬,這特質其實還更符合猿猴呢!就算要說猿猴們對這世界存有一顆好奇之心,也絕不為過。
桑代克教授所研究的猴子裡,某隻有回恰巧碰到一根突出的鐵絲,導致它不斷抖顫,這現象可讓這位猴老兄興致大發,此後幾日每天都要將相同把戲玩上幾百回。當然啦,牠這麼做也不會得到任何物質成果,但僅僅是讓這根鐵絲嗡嗡震顫就足以使牠樂此不疲。
猿猴動作之快常令人驚異,一但牠們腦子裡出現了什麼主意,即刻就會起而行之;總在人類還來不及察覺牠們企圖時,牠們就已得手收兵。說到對於因果關係的認知(例如某種聲音與某種事件之間的關聯),猿猴的學習速度可是動物界中翹楚。倫敦動物園裡有隻著名黑猩猩,名叫莎莉(Sally),曾受訓學習一項技能:當訓練師給出一個數字,牠就要挑出同樣數量的稻草交給訓練師。莎莉很快就學會了一到五的數字,當牠聽到訓練師說「五」「四」或「三」,牠總能拿出數量正確的稻草,因此得到獎賞。不過,或許是因為牠太缺乏定力,要教牠計算超過五的數字就困難重重。當牠聽到大於五的指令時,時常會把手中一根稻草對折,用拇指和其他手指握著,這樣露出的兩端看起來就像兩根而非一根稻草。這個對折稻草的行為很可能是牠用來省時的聰明巧思,就算這樣做無法讓牠獲得獎勵,牠還是十分愛用這招。美國動物學家霍姆斯教授(Samuel J. Holmes)養了一隻名叫「麗茲」(Lizzie)的印度僧帽猴,這種猴子是住在直布羅陀那些獼猴的遠房親戚,而牠的能力與其極限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課題。牠的籠子前方是一排直柱,讓牠可以將手臂整個伸出來。有一回,科學家放了顆蘋果在一塊板子上,麗茲無法直接拿到蘋果,但這塊板子卻有個把手可供抓取;麗茲一看,馬上伸手抓起把手,拉近板子,然後抓住蘋果。整個過程中,牠的動作沒有片刻遲疑,但這或許是因為這類猴子天生就習於將長滿水果的樹枝拉近身前,藉此讓自己能摘到果實。又有一回,科學家在一個凡士林空瓶中放了顆花生,用瓶塞封口後交給麗茲,麗茲也是立刻就用牙齒把瓶塞拉開,算是發揚牠「見到新東西就咬」的本能;但在這之後,牠卻怎樣都學不會把瓶子反過來以倒出花生。這個有趣例子清楚呈現牠們心智能力的侷限性。雖然麗茲最後還是能從瓶中拿出花生,且之後每次重複這個實驗牠都能更快做到這一步,但牠就是無法掌握「讓花生掉出瓶子」的原理何在。牠能逐漸減去過程中那些無用的動作,因此在現象上出現某種進步,但這只是一種低等級的學習。如果麗茲能運用更高的智能來學習,牠就能學會直接將瓶子倒過來。
在迷籠實驗 (puzzle box)中,受試動物必須以特定程序操縱機關,才能解開眼前障礙。猿猴在這種實驗中善於學習的程度遠遠超出貓或狗,這與牠們靈巧操作事物的能力有關。牠們會一再嘗試,去除錯誤的部分,於是其最後表現比起麗茲與凡士林瓶奮戰的經驗(麗茲的行為實在稱不上是在「做實驗」)能夠更勝一籌。某隻猿猴在間隔八個月後重新接受同一組迷籠實驗,結果牠仍然能夠迅捷嫻熟的解開機關,展現出極強記憶力。某些猿猴能學會從迷宮(例如英國漢普頓宮花園裡的迷宮)裡頭自己找出路,這種技藝背後可能代表牠們能記得路徑的轉向或彎曲之處。有一篇記載值得一讀:某次實驗中,兩隻獼猴已經走到迷宮出口前最後一彎,這時牠們卻開始大聲咂嘴,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好像是在說「咱們這回幹得不錯,獎品就在眼前啦!」紅松鼠
紅松鼠在大不列顛十分常見。由於森林不斷遭砍伐,牠們已在一個世紀前被逐出蘇格蘭;現在許多地方人們又重新將牠引進,因這生物不但美麗,生活習性也很可愛。年復一年,牠們數量逐漸增長,直到在某些森林地區已被視為害蟲,必須採取手段加以消滅。我們不必沉湎於這些恩怨,若要真正了解野生動物的生活,人類必須學著以牠們的眼光看事物,而非停留於自身視野。
且看,紅松鼠活得多快活!當我們看見牠在樹幹上跑上跑下,從樹後探出頭窺看我們,直待我們走近,牠就竄上枝幹末梢,輕輕一躍跳上另一棵樹,然後消失在黝暗的松樹頂上,這整個過程對牠似乎都樂趣無窮。當牠端坐大樹腳下,尾巴立於身後,靈巧前掌執著一片傘蕈,優雅的小口小口咬,這畫面看來又是何等美好!牠有時愛在圓木或平石上用餐,瞧牠坐在那,明亮雙眼觀四面,全身都在留神周圍,將冷杉毬果鱗片一片片剝下來吃裡面種子,技術嫻熟。只要一點風吹草動,牠馬上拋下吃了一半的毬果與杯盤狼藉的餐桌,一閃身已經上了附近樹梢。
有時,母松鼠會小心翼翼用口啣著孩子穿越草地,從一片樹林遷移到另一片,這景象極其可人,但卻難得一見。牠要將孩子一個一個從舊有舒適窩巢(也是小孩出生、哺乳的地方)搬到較為隱密、或是附近食物較多的新家。牠必須來回好幾趟,這次「潛逃」才算成功。母松鼠一胎通常生兩到三隻,小松鼠若能順利長大,隔年春天就能自己成家立業;難怪牠們可能在林中數大成患。應當注意到,松鼠父母給小孩的教育可不少,包括體操技巧和森林生活基礎知識。松鼠主食為松果種子、橡實、山毛櫸果實和榛子,但在春天也會咬下落葉松嫩芽來吃,或是將幼樹頂端樹皮環狀啃掉一圈,啜飲底下往下流的甜美樹汁。然而,一但樹皮遭咬穿、底下幼嫩木質被啃壞,幼樹從根部往上輸送水分(除了從土壤中吸收的水分,還包括樹木生長不可或缺的鹽分)的管道就被阻絕,於是環狀傷口以上的部分都會死亡。
若機會允許,松鼠也和其他囓齒動物一樣會開葷;牠會吃林鴿(Wood pigeon)的雛鳥與鳥蛋,這樣牠就算欠了林地主人一屁股債,也多少還了些給農人。不幸的是,牠也會掠奪鳴禽類窩巢。入秋後,松鼠開始積存堅果、橡實等食物,牠會在自己最愛那棵樹腳下挖洞棲身,把一部分存糧藏於此,在天氣陰雨或霜雪凜冽時充飢。牠不會一覺睡過冬季,但常在洞中一待就是兩三天;有時看來昏昏沉沉,但不具真正的冬眠習性。
其他存糧被分做好幾份,埋在平坦地或河岸上不同地方,通常離洞穴有段距離。這些糧窟表面被精心掩蓋,讓人懷疑松鼠本人以後是否還找得到。蘑菇與傘蕈也在採集行列,但不會被埋起來,因為這些東西碰到潮濕土壤很快就腐爛。松鼠會把它們搬到樹上,緊緊塞入樹幹裂縫中或叉型枝椏間,如此可保乾燥新鮮。由此可見,松鼠在儲物時可不是盲目亂塞,而會動動腦子。
松鼠覓食的態度很揮霍,「為了五、六顆堅果可以摧毀整叢灌木」。有人曾目睹兩隻松鼠在櫸木矮林中忙幹活,牠們攀到極細枝幹末端,用兩條後腿把自己掛在上面,伸手摘下一顆顆堅果,其中許多都掉落地上白白浪費、等著腐爛。松鼠常這樣邊工作邊玩,連續好幾個小時不疲倦。
一名美國觀察家看見灰松鼠──英國產的紅松鼠的近親,現在在英格蘭某些地區已對紅松鼠產生排擠效果──將堅果用口含著,一顆顆搬下樹來,在地上刨出約兩吋深的洞,放入堅果,用前掌往下緊壓,再以土壤覆蓋,最後還拉青草遮蓋。這不禁讓人懷疑;儲物處掩藏得如此巧妙,就算是埋東西的松鼠本人,稍後回來也未必找得到。然而,此人同樣也見過一群松鼠在冬日兩吋厚積雪上來回奔跑,每過一會兒,其中一隻就會突然急剎車,在原地往下挖掘,「挖出一顆堅果,下手處極其精準、毫無誤差」。如此看來,松鼠並非表面上那般樂天無憂,牠知道自己能憑敏銳嗅覺找到存放食物的無數地點。有件趣事值得一提,北歐人相信馴鹿能「用蹄聞嗅」,因為牠們總能準確刨開積雪找到糧食;但這說法是錯的,馴鹿用來聞味道的仍是鼻子。松鼠身上有種異常迷人的特質,牠身軀嬌小卻不令人覺得像侏儒,蓬鬆大尾與身體構成美感上的平衡,表層毛髮呈現賞心悅目的鮮豔棕紅,連牠瞅著人的警戒眼神都那麼討人喜歡。牠剝出堅果核仁的用餐禮儀無懈可擊,如老麥吉利維(William MacGillivray) 所觀察到的「甚至會先去掉果仁外層薄膜再進食」。這些動作令觀者不禁屏息,不知是該更敬佩牠的優雅或是膽量。
夏天,如果我們驚起一隻正享用堅果或傘蕈的松鼠,牠會連續幾跳橫越空地,動作之快讓人完全看不清過程,只見牠如履平地一溜煙上了樹,在另一側枝頭現身,朝我們觀望。如果我們又靠近,牠就會跑到一根樹枝末端,隨即身子已經在另一棵樹上。若有必要,牠可以把身體緊貼樹幹動也不動,維持許久。當牠睡覺時,尾巴就是蓋在身上的毯子。
人類對於松鼠扒光樹皮或吃光樹頂新芽的行徑感到厭惡,這也無可厚非。除了人類以外,這動人生物的天敵並不多,即使白鼬或鷹隼面對幼年松鼠都未必佔得到便宜。安全感讓松鼠更能發揮那喜氣洋洋的性情,鮮少有其他生物能如此強烈呈現「生命之樂」的意象。牠們讓人想起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的詩句:
「牠們不因自己處境而勞苦、呻吟……
在這世上沒有一個可敬,也沒有一個不樂 。」
迷籠實驗:必須觸動特定機關才能把籠子打開的實驗。前文提及的美國心理學家桑代克,就是以「迷籠中的貓」實驗著名。
老麥吉利維(1796-1852):蘇格蘭博物學家與鳥類學家。有兩個兒子,長子約翰是個博物學家(1822-1867,主要活躍在澳大利亞),另一個兒子保羅(1834-1895)也是個出過《亞伯丁植物誌》的科學家。
沃爾特.惠特曼(1819-1892):美國詩人與作家,人文主義者,被稱為美國的自由詩體之父,重要作品為詩集《草葉集》(Leaves of Grass)。
譯注:出自The Beast一詩,為惠特曼代表作《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第三十二節。
要了解猿猴,我們必須認清一件事,就是牠們擁有一顆不凡的大腦。猿猴的腦部已經發展到很高程度,當我們看進一隻活力充沛猴兒的雙眼,總覺得自己似乎能看見萬千思緒正在牠心中輪轉。猿猴總是靜不下來,而這正是因為牠們具有高度智能,所以才會如此。美國心理學家桑代克教授(Edward L. Thorndike)如是說:「看看一隻貓或一隻狗,牠們會做的事情相較之下十分有限,而且就算長時間閒散也不覺無聊。「看看一隻猿猴,你就發現牠會做的事情多到不勝枚舉,一切事物對牠都有吸引力,牠常只是因為好動而活動。」
只要猿猴們感覺到身邊有未解之謎,就永遠無法停下手來,這個實際的現象讓我們明白桑代克教授所言不虛。作家及詩人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筆下,那隻貓鼬李奇─蒂奇─塔威(Riki-Tiki-Tavi)的故事就是如此,牠終生的志願就是要探索新知,但比起貓鼬,這特質其實還更符合猿猴呢!就算要說猿猴們對這世界存有一顆好奇之心,也絕不為過。
桑代克教授所研究的猴子裡,某隻有回恰巧碰到一根突出的鐵絲,導致它不斷抖顫,這現象可讓這位猴老兄興致大發,此後幾日每天都要將相同把戲玩上幾百回。當然啦,牠這麼做也不會得到任何物質成果,但僅僅是讓這根鐵絲嗡嗡震顫就足以使牠樂此不疲。
猿猴動作之快常令人驚異,一但牠們腦子裡出現了什麼主意,即刻就會起而行之;總在人類還來不及察覺牠們企圖時,牠們就已得手收兵。說到對於因果關係的認知(例如某種聲音與某種事件之間的關聯),猿猴的學習速度可是動物界中翹楚。倫敦動物園裡有隻著名黑猩猩,名叫莎莉(Sally),曾受訓學習一項技能:當訓練師給出一個數字,牠就要挑出同樣數量的稻草交給訓練師。莎莉很快就學會了一到五的數字,當牠聽到訓練師說「五」「四」或「三」,牠總能拿出數量正確的稻草,因此得到獎賞。不過,或許是因為牠太缺乏定力,要教牠計算超過五的數字就困難重重。當牠聽到大於五的指令時,時常會把手中一根稻草對折,用拇指和其他手指握著,這樣露出的兩端看起來就像兩根而非一根稻草。這個對折稻草的行為很可能是牠用來省時的聰明巧思,就算這樣做無法讓牠獲得獎勵,牠還是十分愛用這招。美國動物學家霍姆斯教授(Samuel J. Holmes)養了一隻名叫「麗茲」(Lizzie)的印度僧帽猴,這種猴子是住在直布羅陀那些獼猴的遠房親戚,而牠的能力與其極限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課題。牠的籠子前方是一排直柱,讓牠可以將手臂整個伸出來。有一回,科學家放了顆蘋果在一塊板子上,麗茲無法直接拿到蘋果,但這塊板子卻有個把手可供抓取;麗茲一看,馬上伸手抓起把手,拉近板子,然後抓住蘋果。整個過程中,牠的動作沒有片刻遲疑,但這或許是因為這類猴子天生就習於將長滿水果的樹枝拉近身前,藉此讓自己能摘到果實。又有一回,科學家在一個凡士林空瓶中放了顆花生,用瓶塞封口後交給麗茲,麗茲也是立刻就用牙齒把瓶塞拉開,算是發揚牠「見到新東西就咬」的本能;但在這之後,牠卻怎樣都學不會把瓶子反過來以倒出花生。這個有趣例子清楚呈現牠們心智能力的侷限性。雖然麗茲最後還是能從瓶中拿出花生,且之後每次重複這個實驗牠都能更快做到這一步,但牠就是無法掌握「讓花生掉出瓶子」的原理何在。牠能逐漸減去過程中那些無用的動作,因此在現象上出現某種進步,但這只是一種低等級的學習。如果麗茲能運用更高的智能來學習,牠就能學會直接將瓶子倒過來。
在迷籠實驗 (puzzle box)中,受試動物必須以特定程序操縱機關,才能解開眼前障礙。猿猴在這種實驗中善於學習的程度遠遠超出貓或狗,這與牠們靈巧操作事物的能力有關。牠們會一再嘗試,去除錯誤的部分,於是其最後表現比起麗茲與凡士林瓶奮戰的經驗(麗茲的行為實在稱不上是在「做實驗」)能夠更勝一籌。某隻猿猴在間隔八個月後重新接受同一組迷籠實驗,結果牠仍然能夠迅捷嫻熟的解開機關,展現出極強記憶力。某些猿猴能學會從迷宮(例如英國漢普頓宮花園裡的迷宮)裡頭自己找出路,這種技藝背後可能代表牠們能記得路徑的轉向或彎曲之處。有一篇記載值得一讀:某次實驗中,兩隻獼猴已經走到迷宮出口前最後一彎,這時牠們卻開始大聲咂嘴,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好像是在說「咱們這回幹得不錯,獎品就在眼前啦!」紅松鼠
紅松鼠在大不列顛十分常見。由於森林不斷遭砍伐,牠們已在一個世紀前被逐出蘇格蘭;現在許多地方人們又重新將牠引進,因這生物不但美麗,生活習性也很可愛。年復一年,牠們數量逐漸增長,直到在某些森林地區已被視為害蟲,必須採取手段加以消滅。我們不必沉湎於這些恩怨,若要真正了解野生動物的生活,人類必須學著以牠們的眼光看事物,而非停留於自身視野。
且看,紅松鼠活得多快活!當我們看見牠在樹幹上跑上跑下,從樹後探出頭窺看我們,直待我們走近,牠就竄上枝幹末梢,輕輕一躍跳上另一棵樹,然後消失在黝暗的松樹頂上,這整個過程對牠似乎都樂趣無窮。當牠端坐大樹腳下,尾巴立於身後,靈巧前掌執著一片傘蕈,優雅的小口小口咬,這畫面看來又是何等美好!牠有時愛在圓木或平石上用餐,瞧牠坐在那,明亮雙眼觀四面,全身都在留神周圍,將冷杉毬果鱗片一片片剝下來吃裡面種子,技術嫻熟。只要一點風吹草動,牠馬上拋下吃了一半的毬果與杯盤狼藉的餐桌,一閃身已經上了附近樹梢。
有時,母松鼠會小心翼翼用口啣著孩子穿越草地,從一片樹林遷移到另一片,這景象極其可人,但卻難得一見。牠要將孩子一個一個從舊有舒適窩巢(也是小孩出生、哺乳的地方)搬到較為隱密、或是附近食物較多的新家。牠必須來回好幾趟,這次「潛逃」才算成功。母松鼠一胎通常生兩到三隻,小松鼠若能順利長大,隔年春天就能自己成家立業;難怪牠們可能在林中數大成患。應當注意到,松鼠父母給小孩的教育可不少,包括體操技巧和森林生活基礎知識。松鼠主食為松果種子、橡實、山毛櫸果實和榛子,但在春天也會咬下落葉松嫩芽來吃,或是將幼樹頂端樹皮環狀啃掉一圈,啜飲底下往下流的甜美樹汁。然而,一但樹皮遭咬穿、底下幼嫩木質被啃壞,幼樹從根部往上輸送水分(除了從土壤中吸收的水分,還包括樹木生長不可或缺的鹽分)的管道就被阻絕,於是環狀傷口以上的部分都會死亡。
若機會允許,松鼠也和其他囓齒動物一樣會開葷;牠會吃林鴿(Wood pigeon)的雛鳥與鳥蛋,這樣牠就算欠了林地主人一屁股債,也多少還了些給農人。不幸的是,牠也會掠奪鳴禽類窩巢。入秋後,松鼠開始積存堅果、橡實等食物,牠會在自己最愛那棵樹腳下挖洞棲身,把一部分存糧藏於此,在天氣陰雨或霜雪凜冽時充飢。牠不會一覺睡過冬季,但常在洞中一待就是兩三天;有時看來昏昏沉沉,但不具真正的冬眠習性。
其他存糧被分做好幾份,埋在平坦地或河岸上不同地方,通常離洞穴有段距離。這些糧窟表面被精心掩蓋,讓人懷疑松鼠本人以後是否還找得到。蘑菇與傘蕈也在採集行列,但不會被埋起來,因為這些東西碰到潮濕土壤很快就腐爛。松鼠會把它們搬到樹上,緊緊塞入樹幹裂縫中或叉型枝椏間,如此可保乾燥新鮮。由此可見,松鼠在儲物時可不是盲目亂塞,而會動動腦子。
松鼠覓食的態度很揮霍,「為了五、六顆堅果可以摧毀整叢灌木」。有人曾目睹兩隻松鼠在櫸木矮林中忙幹活,牠們攀到極細枝幹末端,用兩條後腿把自己掛在上面,伸手摘下一顆顆堅果,其中許多都掉落地上白白浪費、等著腐爛。松鼠常這樣邊工作邊玩,連續好幾個小時不疲倦。
一名美國觀察家看見灰松鼠──英國產的紅松鼠的近親,現在在英格蘭某些地區已對紅松鼠產生排擠效果──將堅果用口含著,一顆顆搬下樹來,在地上刨出約兩吋深的洞,放入堅果,用前掌往下緊壓,再以土壤覆蓋,最後還拉青草遮蓋。這不禁讓人懷疑;儲物處掩藏得如此巧妙,就算是埋東西的松鼠本人,稍後回來也未必找得到。然而,此人同樣也見過一群松鼠在冬日兩吋厚積雪上來回奔跑,每過一會兒,其中一隻就會突然急剎車,在原地往下挖掘,「挖出一顆堅果,下手處極其精準、毫無誤差」。如此看來,松鼠並非表面上那般樂天無憂,牠知道自己能憑敏銳嗅覺找到存放食物的無數地點。有件趣事值得一提,北歐人相信馴鹿能「用蹄聞嗅」,因為牠們總能準確刨開積雪找到糧食;但這說法是錯的,馴鹿用來聞味道的仍是鼻子。松鼠身上有種異常迷人的特質,牠身軀嬌小卻不令人覺得像侏儒,蓬鬆大尾與身體構成美感上的平衡,表層毛髮呈現賞心悅目的鮮豔棕紅,連牠瞅著人的警戒眼神都那麼討人喜歡。牠剝出堅果核仁的用餐禮儀無懈可擊,如老麥吉利維(William MacGillivray) 所觀察到的「甚至會先去掉果仁外層薄膜再進食」。這些動作令觀者不禁屏息,不知是該更敬佩牠的優雅或是膽量。
夏天,如果我們驚起一隻正享用堅果或傘蕈的松鼠,牠會連續幾跳橫越空地,動作之快讓人完全看不清過程,只見牠如履平地一溜煙上了樹,在另一側枝頭現身,朝我們觀望。如果我們又靠近,牠就會跑到一根樹枝末端,隨即身子已經在另一棵樹上。若有必要,牠可以把身體緊貼樹幹動也不動,維持許久。當牠睡覺時,尾巴就是蓋在身上的毯子。
人類對於松鼠扒光樹皮或吃光樹頂新芽的行徑感到厭惡,這也無可厚非。除了人類以外,這動人生物的天敵並不多,即使白鼬或鷹隼面對幼年松鼠都未必佔得到便宜。安全感讓松鼠更能發揮那喜氣洋洋的性情,鮮少有其他生物能如此強烈呈現「生命之樂」的意象。牠們讓人想起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的詩句:
「牠們不因自己處境而勞苦、呻吟……
在這世上沒有一個可敬,也沒有一個不樂 。」
迷籠實驗:必須觸動特定機關才能把籠子打開的實驗。前文提及的美國心理學家桑代克,就是以「迷籠中的貓」實驗著名。
老麥吉利維(1796-1852):蘇格蘭博物學家與鳥類學家。有兩個兒子,長子約翰是個博物學家(1822-1867,主要活躍在澳大利亞),另一個兒子保羅(1834-1895)也是個出過《亞伯丁植物誌》的科學家。
沃爾特.惠特曼(1819-1892):美國詩人與作家,人文主義者,被稱為美國的自由詩體之父,重要作品為詩集《草葉集》(Leaves of Grass)。
譯注:出自The Beast一詩,為惠特曼代表作《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第三十二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