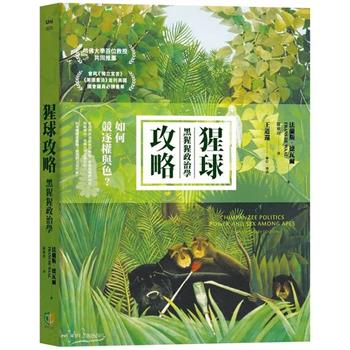廿五週年紀念版前言
一本書能夠常銷二十五年,表示它的題材有歷久不衰的魅力。政治是這樣的題材。我們自己精通政治,因此我們立即就能認出它的運作──即使它發生在人文世界之外。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 1902-1978)對政治下過一個著名的定義:政治是決定「誰在何時、使用何種方式、得到什麼東西」的社會過程。要是接受這個定義,那麼黑猩猩也從事政治活動,毫無疑問。對人類及其近親,那個過程都涉及威嚇、結盟、孤立戰術,因此有必要使用一套通用的術語。
對一些人,本書這樣的書提供了貶低政治人物的論證;對其他人,本書可用來提升猩猩的地位。我們或許該為政治人物洩洩氣,特別是在他們流露躊躇滿志的時刻。本書用來達到這個目的,歷有年所。例如本書法文版出版商將密特朗、席哈克的相片放在封面,中間有一隻黑猩猩,分別與兩人握著手!我不覺得這很逗趣。拿黑猩猩嘲笑人類,表示我們其實並不認真看待黑猩猩,這與我想傳達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馳。我更感興趣的是另一個角度:人類近親的行為為人的本性提供了重要線索。除了搞政治,黑猩猩還有許多行為類似人類,從工具技術到社群間的戰爭。事實上,為了定義我們在靈長類中的地位,大體相似的背景成為越來越難以克服的問題。
發現的世紀
柏拉圖把人定義為世上唯一「沒有羽毛的兩足動物」,立刻遭到第歐根尼駁斥。第歐根尼拿了一隻拔了毛的雞到課堂,以證明自己的論點。從那時起,人就為了什麼東西可以證明人的獨特性而絞盡腦汁。例如製造工具一度被認為是非凡的本領,甚至有一本書的書名就叫做《人是唯一的工具製造者》(Man the Tool Maker)。後來,珍古德發現野生黑猩猩會用特製的樹枝插入蟻丘釣白蟻。另一個獨特性主張是語言,被定義為符號溝通(象徵溝通)。可是語言學家一聽說黑猩猩學會了手語,就把符號這一要件改成語法,繼續強調語言是人類最獨特的能力。人類在宇宙中的獨特地位成了一再棄守的宣稱和不斷移動的目標。愈了解黑猩猩,他們看起來就愈像我們,正如他們的基因組告訴我們的。對黑猩猩行為的知識從廿世紀初開始累積,開路先鋒是幾位實驗室科學家。根據柯勒(Wolfgang Köhler)的描述,黑猩猩也有靈光一閃的時刻。他將香蕉放在黑猩猩拿不到的地方,但是棍子、紙箱隨手可得。黑猩猩幾經嘗試,一再失敗,就在附近坐下,結果突然想出辦法。學界至今仍將這種靈機一動的時刻稱為「柯勒瞬間」。耶基斯(Robert Yerkes)記錄了黑猩猩的性情;雷迪吉納—柯茲(N. N. Ladygina-Kohts)在莫斯科的家裡養了一隻幼年黑猩猩,她效法達爾文,詳細比較了黑猩猩與自己兒子的表情。
人也到黑猩猩的自然棲息地觀察他們,但在當年,科學界認為野外研究是不科學的;只有實驗室的實驗才能提供科學所需的控制。這兩種研究途徑之間的緊張關係至今猶存,儘管黑猩猩研究史已成為展示場,證明實驗室和田野的交流互動能產生豐富的成果。下一波研究方向出現於1930年代,有些人進入田野觀察猩猩,例如尼森(Henry Nissen)在幾內亞花了三個月記錄黑猩猩的覓食習性。他們是第一批認真的野生黑猩猩研究者。不過兩個長期研究計畫要到1960年代才開始。珍古德在坦尚尼亞坦干依喀湖東岸的岡貝溪保留區(Gombe Stream Reserve)設立研究站,同時日本京都大學博士生西田利貞(1941-2011)在岡貝以南170公里處的馬哈勒山脈(Mahale Mountains)建立了研究站。
這些田野研究動搖了黑猩猩是愛好和平的素食者形象,揭露了牠們驚人的社會複雜性。過去我們認為人類是靈長類中唯一的肉食物種,但是研究人員觀察到黑猩猩會捕捉猴子、撕扯開、生吞活剝。原先以為黑猩猩除了母親與幼年子女的聯繫之外,別無其他社會聯繫,田野研究者卻發現,生活在森林特定範圍內的所有個體,會經常聚在一起,儼然一個社會群體。另一方面,相鄰近地區的個體並不互動,若有互動,表現的往往是敵意。科學家開始使用「社群」(community)一詞,避免「群體」(group),因為黑猩猩很少大量聚在一起,而是分成經常變動的小「幫派」(party),在森林裡活動──這個系統稱為「分裂-融合」。
還有一個關於人類獨特性的主張也放棄了,我們發現自己並非唯一會殺害同類的物種。黑猩猩社群之間會為了爭奪地盤而進行殊死鬥爭,這個發現深深影響了戰後針對人類侵略性起源的辯論。
1970年代,第二波有深遠影響的黑猩猩研究問世,這次是圈養的黑猩猩。這些研究發現,黑猩猩的認知能力比我們過去所想像的還接近人類。蓋洛普(Gordon Gallup)證明黑猩猩能夠辨認自己的鏡中影像,表示他們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識,這是人、猿與其他靈長類的區別。曼佐(Emil Menzel)把知道某件物品藏在何處的一隻黑猩猩與其他一無所知的同類放在一起,結果他發現,黑猩猩不但懂得彼此學習,也會彼此欺騙。大約在這個時候,荷蘭的阿納姆動物園建立了世上最大的戶外黑猩猩圈養區,我就是在那裡開始觀察黑猩猩,成果之一便是本書,於1982年首次出版。
歷史書寫
我在1979年到1980年撰寫本書,年方三十,是個初出茅蘆的科學家,天不怕、地不怕。至少,我那時是這麼想。我樂意跟隨自己的直覺與信念,不管它們會不會招致爭議。別忘了,當時若把「動物」和「認知」放在同一個句子中,都會教人不順眼。我的同事大部分都不願意談論動物的意圖或動物會計畫行動,因為會受到擬人化的批評。倒不是他們非要否定動物有內心世界不可,他們只是遵循行為學派的教條:既然不可能知道動物的想法和感受,談了也是白談。我還記得,自己站在金屬架上,居高臨下面對黑猩猩的夜間籠舍,忍著臭氣一站就是幾個小時,手裡握著建築物裡唯一的話筒,和我的教授范侯夫(Jan Van Hooff, 1936-)通話,想說服他接受我的另一個瘋狂臆測。雖然他總是支持我,仍比我謹慎。就是在這些討論中,他和我開始把這個黑猩猩社群的動態比喻為「政治」,起先只是開玩笑吧。
對這本書的另一個主要影響,是一般大眾。多年來,我向動物園的團體訪客演講,包括律師、家長、大學生、心理治療師、警校學生、賞鳥愛好者,等等。對於想寫科普的人,他們可是最好的諮商對象。遊客對於某些當紅的學術議題意興闌珊,卻對我已開始視為理所當然的基礎靈長類心理學,一聽就懂而且著迷。我發現,我的故事,唯一的講述方法是讓每一隻黑猩猩都成為有血有肉的個體,描述真實事件,而不是科學家喜歡的抽象通則。這個覺悟受益於先前的經驗。來到阿納姆前,我在烏特勒支大學完成了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我研究的是長尾獼猴(或稱爪哇獼猴)。我觀察的是雄猴之間的階級變化,1975年出版了第一篇科學論文──《受傷的領袖:人工豢養的爪哇獼猴的敵對關係結構的自發性短暫變化》。我論文的封面插圖,想表達的是爪哇獼猴的權力遊戲非常複雜──在插圖裡,猴子也是棋子。我發現,一涉及社會戲劇與謀略,動物行為學家那套形式化的紀錄根本派不上用場。我們收集數據的標準方法,目標是計算事件的發生次數。電腦程式分析數據,為攻擊事件、理毛頻率、或任何其他我們感興趣的行為,做出工整的摘要。
無法量化或繪成圖表的東西,就可能被視為「逸文軼事」,晾在一旁。逸文軼事是難以概化的獨特事件。可是,難道這就是某些科學家對它們嗤之以鼻的理由?且讓我舉一個人類的例子:伍華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最後的日子》(The Final Days)一書描寫了尼克森失去權力後的反應:「尼克森很哀傷,斷斷續續地啜泣……不過就是一起單純的竊盜事件,怎麼會演變成這個樣子?……他雙膝跪地……俯在地上以拳重捶地毯,放聲哭喊:『我做了什麼?究竟發生什麼事?』」
尼克森是唯一一位請辭下台的美國總統,所以這個故事只能是逸文軼事。可是,它的意義難道會因此而微不足道?我必須承認,我就是喜愛稀罕而獨特的事件。本書裡就有一個類似的故事,我的一隻黑猩猩在類似的情況下,也像尼克森那樣的發脾氣(只是不用言語)。先前的研究經驗教給我的是,為了分析、理解這種事件,我必須寫日記,記錄事情的發展,每個個體捲入的經過,牠們的處境(與過去相比)又有什麼特殊之處。我不要只是計算、平均黑猩猩的行為,我要把歷史書寫注入我的計畫中。
我想寫通俗讀物,是因為我一向愛讀為大眾寫的動物書、科學書。許多學者似乎不明白這類讀物的重要。吸引學生進入某個領域的,正是這類讀物,它們為那一領域提供了平易近人的面貌。繼本書之後,我寫了好幾本科普書,談巴諾布猿、談猩猩猴子的和解行為,甚至談道德、文化的起源。由於我還負責帶領一個活躍的研究團隊,我過著一種雙重生活。白天,我們從事科學研究;晚上與週末,我寫作科普書。這些書讓我討論較大的議題,其中有一些在科學文獻中幾乎提都不能提。
本書避免直接拿人類的政治與黑猩猩政治做比較──不過我會偶爾拋出一些線索。譬如說,我並沒有點出年長雄性的權力,例如野倫,和年長的政治人物極為相像。每個國家都有錢尼與甘迺迪(Ted Kennedy, 1932-2009)之類的人物,在幕後操控大局。這些老練的政客雖然已過巔峰,往往能利用年輕政客的鉤心鬥角,攫取極大權力。我也沒有明白指出,角逐大位的雄性為了拍雌性馬屁,會為她們理毛、逗弄她們的小寶寶,多像在選舉期間抱起嬰兒親吻的人類政治人物!諸如此類的相似之處太多了,非言語溝通方式也一樣,像是威嚇、降低聲量,但是我全都不提。在我看來,它們顯而易見,我樂意留給讀者自行發現。
1982年,《黑猩猩政治學》由倫敦的強納森開普(Jonathon Cape)出版社出版,並未招致什麼爭議。(註一)它受到一般大眾與學界的歡迎,而非攻擊。然而,隨著時間流逝,本書成為某些人所謂的「經典」,實在太不敢當。本書的成功之處,在於那群猩猩的故事教人一看就明白,而且有時出人意料。以後見之明,本書受到熱烈歡迎,不難理解,因為書中的潛台詞與1980年代的時代精神契合;當時,大眾對動物的看法正在迅速改變。認知心理學在美國興起,我一無所知,我不知道我並不孤獨,其他人也在探索這一新的知識領域。這一情況證明了科學發展從來不是完全獨立的。因此,格里芬(Donald Griffin)的《動物有意識嗎?》(The Question of Animal Awareness, 1976)並沒有讓我驚訝,就像本書顯然也沒有讓大多數靈長類學者大吃一驚。
本書的目標讀者是一般大眾,但是老師與企業顧問也會利用本書,在美國甚至上了國會菜鳥議員的推薦書單。二十五年來,對本書的興趣仍未消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和我判斷,製作一本廿五週年紀念版可能會受到新讀者的歡迎,因為他們對人與黑猩猩的關係不但有興趣,而且求知若渴。廿五週年紀念版的底本是1998年修訂版,並收錄了未在原書發表的彩色照片,還更新了一些黑猩猩要角的資訊。
為了說明我的研究產生的睿見,我喜歡以島嶼的生物地理學做比喻。生態複雜度會與動植物物種的數量成正比,這是很容易的概念。不過,島嶼上的物種數量,通常比距它們最近的大陸少。島嶼生態相對單純,因此自然學者得以發展可適用於複雜系統的點子,達爾文、威爾森(Edward O. Wilson)都是典範。同理,阿納姆動物園的黑猩猩島住著一群數量不多的黑猩猩,生活條件比赤道雨林單純多了。請想像一下,要是社群中雄性的數量多了兩倍──野生黑猩猩社群便是──或者黑猩猩能夠自由出入島嶼,結果會怎樣?我可能就無法理解在眼前上演的社會戲劇。我像一個島嶼自然史家,因為東西少,看到的反而多。然而,我揭露的通則不只適用於孤島上的黑猩猩,也適用於每個地方的權力鬥爭。
結果就是本書,以直截了當的筆法鋪陳阿納姆黑猩猩經歷的一切,沒有摻雜「人類在相同的情況下會怎麼做」的提示。這麼一來,敘事焦點一直是我們的近親,讀者的心思可以集中在牠們的行為上。但是,在辦公室、在美國華府政治走廊、或者在大學各學系中,任何人只要環顧四周,一定會注意到社會動態本質上都一樣。到處都是同樣的遊戲:刺探與挑戰、結盟、破壞他人結盟,以及為了加強語氣而拍桌。權力意志是人性通相。人自演化伊始,就在玩馬基維利權術,本書點明的演化關聯,應該沒人感到意外才是。
一本書能夠常銷二十五年,表示它的題材有歷久不衰的魅力。政治是這樣的題材。我們自己精通政治,因此我們立即就能認出它的運作──即使它發生在人文世界之外。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 1902-1978)對政治下過一個著名的定義:政治是決定「誰在何時、使用何種方式、得到什麼東西」的社會過程。要是接受這個定義,那麼黑猩猩也從事政治活動,毫無疑問。對人類及其近親,那個過程都涉及威嚇、結盟、孤立戰術,因此有必要使用一套通用的術語。
對一些人,本書這樣的書提供了貶低政治人物的論證;對其他人,本書可用來提升猩猩的地位。我們或許該為政治人物洩洩氣,特別是在他們流露躊躇滿志的時刻。本書用來達到這個目的,歷有年所。例如本書法文版出版商將密特朗、席哈克的相片放在封面,中間有一隻黑猩猩,分別與兩人握著手!我不覺得這很逗趣。拿黑猩猩嘲笑人類,表示我們其實並不認真看待黑猩猩,這與我想傳達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馳。我更感興趣的是另一個角度:人類近親的行為為人的本性提供了重要線索。除了搞政治,黑猩猩還有許多行為類似人類,從工具技術到社群間的戰爭。事實上,為了定義我們在靈長類中的地位,大體相似的背景成為越來越難以克服的問題。
發現的世紀
柏拉圖把人定義為世上唯一「沒有羽毛的兩足動物」,立刻遭到第歐根尼駁斥。第歐根尼拿了一隻拔了毛的雞到課堂,以證明自己的論點。從那時起,人就為了什麼東西可以證明人的獨特性而絞盡腦汁。例如製造工具一度被認為是非凡的本領,甚至有一本書的書名就叫做《人是唯一的工具製造者》(Man the Tool Maker)。後來,珍古德發現野生黑猩猩會用特製的樹枝插入蟻丘釣白蟻。另一個獨特性主張是語言,被定義為符號溝通(象徵溝通)。可是語言學家一聽說黑猩猩學會了手語,就把符號這一要件改成語法,繼續強調語言是人類最獨特的能力。人類在宇宙中的獨特地位成了一再棄守的宣稱和不斷移動的目標。愈了解黑猩猩,他們看起來就愈像我們,正如他們的基因組告訴我們的。對黑猩猩行為的知識從廿世紀初開始累積,開路先鋒是幾位實驗室科學家。根據柯勒(Wolfgang Köhler)的描述,黑猩猩也有靈光一閃的時刻。他將香蕉放在黑猩猩拿不到的地方,但是棍子、紙箱隨手可得。黑猩猩幾經嘗試,一再失敗,就在附近坐下,結果突然想出辦法。學界至今仍將這種靈機一動的時刻稱為「柯勒瞬間」。耶基斯(Robert Yerkes)記錄了黑猩猩的性情;雷迪吉納—柯茲(N. N. Ladygina-Kohts)在莫斯科的家裡養了一隻幼年黑猩猩,她效法達爾文,詳細比較了黑猩猩與自己兒子的表情。
人也到黑猩猩的自然棲息地觀察他們,但在當年,科學界認為野外研究是不科學的;只有實驗室的實驗才能提供科學所需的控制。這兩種研究途徑之間的緊張關係至今猶存,儘管黑猩猩研究史已成為展示場,證明實驗室和田野的交流互動能產生豐富的成果。下一波研究方向出現於1930年代,有些人進入田野觀察猩猩,例如尼森(Henry Nissen)在幾內亞花了三個月記錄黑猩猩的覓食習性。他們是第一批認真的野生黑猩猩研究者。不過兩個長期研究計畫要到1960年代才開始。珍古德在坦尚尼亞坦干依喀湖東岸的岡貝溪保留區(Gombe Stream Reserve)設立研究站,同時日本京都大學博士生西田利貞(1941-2011)在岡貝以南170公里處的馬哈勒山脈(Mahale Mountains)建立了研究站。
這些田野研究動搖了黑猩猩是愛好和平的素食者形象,揭露了牠們驚人的社會複雜性。過去我們認為人類是靈長類中唯一的肉食物種,但是研究人員觀察到黑猩猩會捕捉猴子、撕扯開、生吞活剝。原先以為黑猩猩除了母親與幼年子女的聯繫之外,別無其他社會聯繫,田野研究者卻發現,生活在森林特定範圍內的所有個體,會經常聚在一起,儼然一個社會群體。另一方面,相鄰近地區的個體並不互動,若有互動,表現的往往是敵意。科學家開始使用「社群」(community)一詞,避免「群體」(group),因為黑猩猩很少大量聚在一起,而是分成經常變動的小「幫派」(party),在森林裡活動──這個系統稱為「分裂-融合」。
還有一個關於人類獨特性的主張也放棄了,我們發現自己並非唯一會殺害同類的物種。黑猩猩社群之間會為了爭奪地盤而進行殊死鬥爭,這個發現深深影響了戰後針對人類侵略性起源的辯論。
1970年代,第二波有深遠影響的黑猩猩研究問世,這次是圈養的黑猩猩。這些研究發現,黑猩猩的認知能力比我們過去所想像的還接近人類。蓋洛普(Gordon Gallup)證明黑猩猩能夠辨認自己的鏡中影像,表示他們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識,這是人、猿與其他靈長類的區別。曼佐(Emil Menzel)把知道某件物品藏在何處的一隻黑猩猩與其他一無所知的同類放在一起,結果他發現,黑猩猩不但懂得彼此學習,也會彼此欺騙。大約在這個時候,荷蘭的阿納姆動物園建立了世上最大的戶外黑猩猩圈養區,我就是在那裡開始觀察黑猩猩,成果之一便是本書,於1982年首次出版。
歷史書寫
我在1979年到1980年撰寫本書,年方三十,是個初出茅蘆的科學家,天不怕、地不怕。至少,我那時是這麼想。我樂意跟隨自己的直覺與信念,不管它們會不會招致爭議。別忘了,當時若把「動物」和「認知」放在同一個句子中,都會教人不順眼。我的同事大部分都不願意談論動物的意圖或動物會計畫行動,因為會受到擬人化的批評。倒不是他們非要否定動物有內心世界不可,他們只是遵循行為學派的教條:既然不可能知道動物的想法和感受,談了也是白談。我還記得,自己站在金屬架上,居高臨下面對黑猩猩的夜間籠舍,忍著臭氣一站就是幾個小時,手裡握著建築物裡唯一的話筒,和我的教授范侯夫(Jan Van Hooff, 1936-)通話,想說服他接受我的另一個瘋狂臆測。雖然他總是支持我,仍比我謹慎。就是在這些討論中,他和我開始把這個黑猩猩社群的動態比喻為「政治」,起先只是開玩笑吧。
對這本書的另一個主要影響,是一般大眾。多年來,我向動物園的團體訪客演講,包括律師、家長、大學生、心理治療師、警校學生、賞鳥愛好者,等等。對於想寫科普的人,他們可是最好的諮商對象。遊客對於某些當紅的學術議題意興闌珊,卻對我已開始視為理所當然的基礎靈長類心理學,一聽就懂而且著迷。我發現,我的故事,唯一的講述方法是讓每一隻黑猩猩都成為有血有肉的個體,描述真實事件,而不是科學家喜歡的抽象通則。這個覺悟受益於先前的經驗。來到阿納姆前,我在烏特勒支大學完成了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我研究的是長尾獼猴(或稱爪哇獼猴)。我觀察的是雄猴之間的階級變化,1975年出版了第一篇科學論文──《受傷的領袖:人工豢養的爪哇獼猴的敵對關係結構的自發性短暫變化》。我論文的封面插圖,想表達的是爪哇獼猴的權力遊戲非常複雜──在插圖裡,猴子也是棋子。我發現,一涉及社會戲劇與謀略,動物行為學家那套形式化的紀錄根本派不上用場。我們收集數據的標準方法,目標是計算事件的發生次數。電腦程式分析數據,為攻擊事件、理毛頻率、或任何其他我們感興趣的行為,做出工整的摘要。
無法量化或繪成圖表的東西,就可能被視為「逸文軼事」,晾在一旁。逸文軼事是難以概化的獨特事件。可是,難道這就是某些科學家對它們嗤之以鼻的理由?且讓我舉一個人類的例子:伍華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最後的日子》(The Final Days)一書描寫了尼克森失去權力後的反應:「尼克森很哀傷,斷斷續續地啜泣……不過就是一起單純的竊盜事件,怎麼會演變成這個樣子?……他雙膝跪地……俯在地上以拳重捶地毯,放聲哭喊:『我做了什麼?究竟發生什麼事?』」
尼克森是唯一一位請辭下台的美國總統,所以這個故事只能是逸文軼事。可是,它的意義難道會因此而微不足道?我必須承認,我就是喜愛稀罕而獨特的事件。本書裡就有一個類似的故事,我的一隻黑猩猩在類似的情況下,也像尼克森那樣的發脾氣(只是不用言語)。先前的研究經驗教給我的是,為了分析、理解這種事件,我必須寫日記,記錄事情的發展,每個個體捲入的經過,牠們的處境(與過去相比)又有什麼特殊之處。我不要只是計算、平均黑猩猩的行為,我要把歷史書寫注入我的計畫中。
我想寫通俗讀物,是因為我一向愛讀為大眾寫的動物書、科學書。許多學者似乎不明白這類讀物的重要。吸引學生進入某個領域的,正是這類讀物,它們為那一領域提供了平易近人的面貌。繼本書之後,我寫了好幾本科普書,談巴諾布猿、談猩猩猴子的和解行為,甚至談道德、文化的起源。由於我還負責帶領一個活躍的研究團隊,我過著一種雙重生活。白天,我們從事科學研究;晚上與週末,我寫作科普書。這些書讓我討論較大的議題,其中有一些在科學文獻中幾乎提都不能提。
本書避免直接拿人類的政治與黑猩猩政治做比較──不過我會偶爾拋出一些線索。譬如說,我並沒有點出年長雄性的權力,例如野倫,和年長的政治人物極為相像。每個國家都有錢尼與甘迺迪(Ted Kennedy, 1932-2009)之類的人物,在幕後操控大局。這些老練的政客雖然已過巔峰,往往能利用年輕政客的鉤心鬥角,攫取極大權力。我也沒有明白指出,角逐大位的雄性為了拍雌性馬屁,會為她們理毛、逗弄她們的小寶寶,多像在選舉期間抱起嬰兒親吻的人類政治人物!諸如此類的相似之處太多了,非言語溝通方式也一樣,像是威嚇、降低聲量,但是我全都不提。在我看來,它們顯而易見,我樂意留給讀者自行發現。
1982年,《黑猩猩政治學》由倫敦的強納森開普(Jonathon Cape)出版社出版,並未招致什麼爭議。(註一)它受到一般大眾與學界的歡迎,而非攻擊。然而,隨著時間流逝,本書成為某些人所謂的「經典」,實在太不敢當。本書的成功之處,在於那群猩猩的故事教人一看就明白,而且有時出人意料。以後見之明,本書受到熱烈歡迎,不難理解,因為書中的潛台詞與1980年代的時代精神契合;當時,大眾對動物的看法正在迅速改變。認知心理學在美國興起,我一無所知,我不知道我並不孤獨,其他人也在探索這一新的知識領域。這一情況證明了科學發展從來不是完全獨立的。因此,格里芬(Donald Griffin)的《動物有意識嗎?》(The Question of Animal Awareness, 1976)並沒有讓我驚訝,就像本書顯然也沒有讓大多數靈長類學者大吃一驚。
本書的目標讀者是一般大眾,但是老師與企業顧問也會利用本書,在美國甚至上了國會菜鳥議員的推薦書單。二十五年來,對本書的興趣仍未消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和我判斷,製作一本廿五週年紀念版可能會受到新讀者的歡迎,因為他們對人與黑猩猩的關係不但有興趣,而且求知若渴。廿五週年紀念版的底本是1998年修訂版,並收錄了未在原書發表的彩色照片,還更新了一些黑猩猩要角的資訊。
為了說明我的研究產生的睿見,我喜歡以島嶼的生物地理學做比喻。生態複雜度會與動植物物種的數量成正比,這是很容易的概念。不過,島嶼上的物種數量,通常比距它們最近的大陸少。島嶼生態相對單純,因此自然學者得以發展可適用於複雜系統的點子,達爾文、威爾森(Edward O. Wilson)都是典範。同理,阿納姆動物園的黑猩猩島住著一群數量不多的黑猩猩,生活條件比赤道雨林單純多了。請想像一下,要是社群中雄性的數量多了兩倍──野生黑猩猩社群便是──或者黑猩猩能夠自由出入島嶼,結果會怎樣?我可能就無法理解在眼前上演的社會戲劇。我像一個島嶼自然史家,因為東西少,看到的反而多。然而,我揭露的通則不只適用於孤島上的黑猩猩,也適用於每個地方的權力鬥爭。
結果就是本書,以直截了當的筆法鋪陳阿納姆黑猩猩經歷的一切,沒有摻雜「人類在相同的情況下會怎麼做」的提示。這麼一來,敘事焦點一直是我們的近親,讀者的心思可以集中在牠們的行為上。但是,在辦公室、在美國華府政治走廊、或者在大學各學系中,任何人只要環顧四周,一定會注意到社會動態本質上都一樣。到處都是同樣的遊戲:刺探與挑戰、結盟、破壞他人結盟,以及為了加強語氣而拍桌。權力意志是人性通相。人自演化伊始,就在玩馬基維利權術,本書點明的演化關聯,應該沒人感到意外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