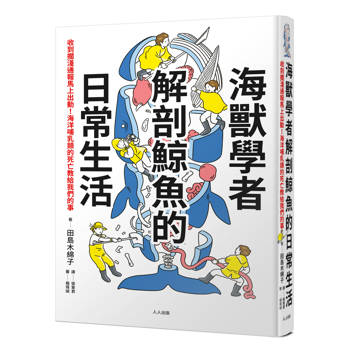擱淺是突發事件
在我的研究室中,每星期三會全體出動進行博物館的業務。所謂博物館的業務,就是跟標本相關的各種作業,包含標本的製作、整理與典藏。即使是跟個人研究無關的標本,在博物館中需要保管、典藏的標本也是極為大量,這類的工作都是在星期三,全員一起出動進行。
在其他的日子,個人可以自由專注在自己的研究或業務上。就我個人而言,除了標本製作與管理、研究以外,還要花時間撰寫論文或準備要提交給行政單位的文件、創建各種資料庫等等。期間還要出席會議,與參觀標本的訪客接觸往來,也經常接受媒體採訪。
然而只要一通電話,這種日常就會徹底改變,也就是擱淺的通報。所謂擱淺,就像在「前言」中提到鯨豚之類的海洋哺乳類被拍打上岸的現象(詳見第三章)。
擱淺是無法預測的。在收到通報之前,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在哪裡、哪種海洋哺乳類會擱淺。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有齣連續劇的主題曲《突然發生的愛情故事》非常流行。「突發的擱淺」亦如是。
每當同事裡有人不小心說出:「最近都沒有關於擱淺的聯絡呢!」很不可思議地電話就會響,真是烏鴉嘴。
由於擱淺調查就是在和時間賽跑,因此一旦收到擱淺的報告,所有的作業就得即刻中斷,馬上開始著手處理。
海洋哺乳類經常是以屍體的狀態漂流到岸邊,時間過得越久,個體的腐敗程度就越高,病理解剖也變得越困難。此外,更加惱人的是以屍體方式漂到海邊或擱淺後死亡的海洋哺乳類,根據當地政府單位的判斷,將其視為大型垃圾處裡掉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對不關心的人來說,被拍打上岸的鯨豚通常都是只會發出惡臭的討厭東西而已。但是正如前述,屍體充滿了很多極有價值的資訊。透過盡可能的採集、調查和研究,獲得的線索不僅可以闡明擱淺的原因,也能讓我們瞭解目前為止還不清楚的生物基本資訊等等。因此我們會在鯨豚屍體被當成大型垃圾處裡掉之前,趕赴現場進行調查,做好各項安排。
首先,根據打電話來的人是誰,最初應對也會有很大的差異。電話另一端什麼樣的人都有,雖然大多數是發生擱淺海岸當地政府單位的職員、博物館或水族館的工作人員等,不過有時候也會接到正好去海岸而發現擱淺個體,直接跟我們聯絡的一般民眾。無論如何,假如對方對擱淺有相當程度的知識或經驗,事情就能夠順利進行。
特別當對方是博物館或水族館的工作人員時更是如此。光是透過電話交談,就可以大致了解是哪個物種,以什麼樣的狀態被打到海灘上,現在是什麼樣的狀況等等。
即使電話那頭是一般民眾,會直接跟科博聯絡的人,很有可能對擱淺多少有點認知與關心。因此就算不知道被拍打上岸的個體是哪個物種,也能夠問到個體大略的尺寸、背鰭有無、頭部外觀特徵等等,如果可以,還能夠請對方幫忙拍攝個體照片用電子郵件傳送給我們。這樣就已經能夠獲得相當多的資訊。
最需要小心應對的是當地政府單位。經常發現動物擱淺的地區是另一回事,但假如是第一次經歷這種事情的地區,為了不讓擱淺個體被當成大型垃圾處理,就必須做很詳細的說明,請求對方配合我們的調查活動。
除了做自我介紹以外,我也會說明博物館長年進行擱淺個體的調查活動,能從這種研究中能夠學習到什麼,為什麼得要進行調查等等。假如很幸運地獲得當地的理解,並從照片中辨識出物種,了解現狀到某種程度之後,我腦袋裡的「擱淺算盤」就會立刻開始撥算個不停。換句話說,就是開始估價,準備編列預算。
同一時間,從列出能夠到現場進行調查的人員名單(不僅是科博的工作人員,還會利用全國的聯絡網詢問有經驗的人),到準備調查工作及工作服、搬運方法、飛機或是租車、安排住宿等,都必須要立即判斷並且採取行動。出發前的準備有如戰場。我經常是在早上接到電話,當天晚上就住進調查現場附近的住宿設施。不過最近可以使用博物館的車,出門變得更加方便。
在我剛開始進行這項活動的時候,搭乘電車前往現場是理所當然的。2001年3月,單單一個星期就有12頭史氏中喙鯨在日本海沿岸擱淺的時候,也是揹著塞滿調查工具的大背包,雙手提著沉重的工具箱和水桶,感覺自己的手指快要斷了,還要轉乘客滿的電車前往目的地。
不僅對我們來說很辛苦,也對周圍的乘客帶來很大的困擾。我在移動的時候都只能不停地說:「對不起、對不起。」雖然也經常會搭乘夜間巴士或臥鋪列車移動,光是不用帶著行李走來走去,就讓我有如身處天堂了。
調查結束後溫泉設施的異味騷動
現場的擱淺調查也是與氣味的戰鬥。
被拍打上岸的鯨豚屍體,分分秒秒不停地腐敗。如果是剛死沒多久的個體,大概只是像在家裡清理魚的那種魚腥味,或是有點內臟的氣味。但若是已經腐敗相當嚴重的個體,那就會有一種非常強烈、可怕的氣味。
儘管說著:「好臭、好臭!」但是一旦在解剖過程中接觸到腐敗個體,大家都是一丘之貉。氣味附著到全身上上下下,我們也同樣成為氣味的源頭。簡直就像是被喪屍咬了之後,就會成為喪屍那樣。
因此一旦開始調查,基本上幾乎不可能中途離開現場。為了防止感染,必須要戴口罩和手套,事前準備好包含食物的所有必要物品,唯一躲不掉的就是上廁所。
由於現場不能上野戰廁所,必須借用附近的公共廁所。當然,要先脫下沾有肉片和血液的雨衣、雨鞋、手套等,並且留意不要讓氣味沾到周圍去。雖然如此,還是經常沒注意到解剖時飛散到臉上或頭髮上的血漬,在走進公共廁所時嚇到人。
此外,即使是調查結束要回去的時候,異味問題也持續存在。雖然開博物館的車回去就不成問題,不過要是調查地點距離遙遠,可能就要留宿旅館。在這種情況下,處理氣味的對策遠比上廁所更令人頭痛。
進入飯店之前,把雨衣等裝進密閉度很高的袋子裡,換掉衣服、徹底洗手、擦掉飛濺到臉上的各種飛沫、用除菌消臭劑噴頭髮噴到讓人覺得:「不然到底是還想怎樣!」
縱使如此,還是沒辦法完全去除氣味。因此在辦理入住手續的時候,為了能夠分散氣味,需要一個個分開,在不同的時間點進入飯店。搭乘電梯的時候也是比照辦理。
調查結束要搭飛機回去的時候更是困難。假如不換衣服就這樣搭飛機,絕對會因為異味引起騷動而讓飛機無法起飛。不過話說回來,辦理登機手續的時候應該就直接出局了吧!那個氣味就是這麼臭。
究竟要怎麼搭飛機回去?就是在去機場之前,先到當地的溫泉設施把氣味跟髒污給洗掉。其實在這邊也是會出亂子的。
跟在旅館辦理入住手續一樣,要先做好除臭對策才去櫃台辦理手續,前往女性專用的浴池。但是所謂的溫泉設施,在更衣室中也是瀰漫著蒸氣,沾染在我們身體上的氣味,便會隨著蒸氣在更衣室中擴散。
因此在周圍的人注意到之前,就算在更衣室中也一定要分散各處,迅速找個地方把衣物脫掉,移動到盥洗區。即使如此,仍然很常引發異味騷動。感覺到異味的人,首先會開始檢查寄物櫃或垃圾桶。可能是在確認有沒有嬰兒的尿布或嘔吐物,接下來則會將廁所門一扇扇打開檢查內部。
有時候也會請設施的工作人員進來把窗戶關緊,以免異味從外部飄進來。雖然我很想說:「哎呀,那樣會造成反效果……。」不過這樣就會被發現我們才是異味的來源而將我們趕出去,這樣就沒辦法搭飛機了。於是只能在心裡默念:「抱歉抱歉,請原諒我們。」同時慌慌張張地前往浴室盥洗。
在一遍遍重複這樣的經驗之後,我學會如何極其迅速,幾乎是瞬間移動般從更衣室走到浴室,動作小到可以不讓氣味傳播到周圍去呢。
我問過男性工作人員有沒有遇過同樣的問題,他們卻說在男性浴場從來沒有發生過異味騷動。這真是讓人驚訝,難道氣味的感官是男女有別嗎?還是那並非嗅覺的問題,而是耐受度的差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