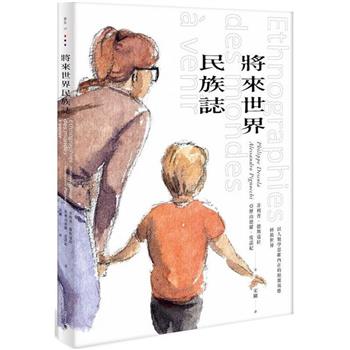5
裂解自然主義領土
嘗試從目前在荒地聖母鎮發生的事件中總結幾點觀察
亞歷山德羅・皮諾紀:你剛剛說的,關於薩拉雅庫的寓居地與寓居人關係的翻轉,當然跟現在在荒地聖母防衛區發生的事件相呼應。正如一位防衛區住民所言39:「最近幾年是樹籬田在用我們的身體來捍衛它的完整性40」。在雙方友善共處的關係當中,是樹籬田同意讓防衛區人寓居。他們相對於它,透過因為它而在人之間、以及與非人之間構織的多重變動連結,是處於一種存有論意義上的依賴形式之中的。而且,這正是在2012年和2018年的兩次驅離行動當中,幫助拯救了防衛區的原因所在。國家不曾預料到佔領民眾捍衛他們生命環境的決心。就跟在本地原生抗爭當中一樣,他們捍衛的不是自然、生物多樣性或是別的這類抽象的概念,而是已經慢慢變成了構成他們自己所是的一團關係叢結。所以他們才能夠堅持到願意賭上他們的生命41。
在現場,我相信自己從來不曾聽到用「自然」來談論防衛區和其中各種不同的環境。這並不是說各位住民禁止自己使用這一字眼,因為他們看了太多菲利普・德斯寇拉的書,而只不過是因為這個詞完全失去了有效性。同樣,把森林、草地或是池塘當成是待開發的純資源,或是要保護的空間,也會是件很詭異的事。很顯然,這些生命環境和生活於其中的非人,都是這個集體完整意義上的成員,彼此之間理應善待對方,一起分享這塊共同的領土42。防衛區的一個住民,在一段拍他勞動的影片中解釋說43:「森林的利益優先於我們的」。防衛區的集體當然很開心有木材去搭建他們的樑柱,但是在選擇要砍伐的樹木時,則是森林的可再生性問題優先於人對木材的需求。當然了,森林的利益是什麼,需要人去想像發展,但是有一些指標還是相對明確的。比如說,當你知道一棵樹平均要到150歲之後,保有的生物多樣性才會達到最高程度,而由ONF(國家林業局)管理的森林是永遠也不會達到這樣的年歲,那你就可以想到採納森林的視角,就必須首先轉換時間尺度44。在這片領土上組織生活的決定,特別是生產活動的決定,就不再是由經濟邏輯引導,而是由集體認定的可欲狀態,這個「集體」就是要盡可能納入樹籬田和它的非人住民。
這麼做,我們並沒有變成泛靈主義者,但的確是超越了自然主義,在走向某種別的、混雜的狀態。注意力機制在轉化,限定重要與否的界線在移動,使用的概念術語在更新。Baptiste Morizot,還有別的一些人,在致力於陪伴這次的概念更新。根據他的觀點,並不是要像泛靈主義那樣,努力賦予植物和動物一種與人相似的內在性,而是要同時承認它們的親近性與他異性,將它們主體化但又不要擬人化,堅持尋找對它們來說最「適切」的「關懷」45。
菲利普・德斯寇拉:我的確認為,即使是在聖母荒地的樹籬田,也很難跳出經過自然主義社會化而形成的慣習,突然開始在夜裡夢見蠑螈在抱怨濕地的縮減,或是把菌菇中毒認定為野豬精靈的報復所為。但話說回來,我在防衛區短短的停留期間,的確讓我很驚訝的是,接待我的人相對於非人存有,已經發展出了一種,除非是在某些農人或是一些一生都在與植物和動物親密互動的專業生態學者身上,非常少見的注意力機制。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對一個環境特性極為敏銳的觀察力──構成環境的植被、植被為這種或那種動物提供的保護、植栽不同朝向的效果,等等──同時又對環境的每一個成分有種緊密的親切感──這棵樹的位置對它的生長是好還是壞、那頭羊有多任性、那片穀物過於向北迎風,等等。對每一個動物和植物個體的關注讓人可以看到它在所屬的跨物種集體當中如何行動,它又是怎麼受這個集體的影響。而依照防衛區眾多住民的城裡人出身判斷,這一類注意力很可能一開始完全不是自發的,它是一點一點,因為對保衛這個地方免受外部侵擾有了全面的認同,而逐步形成的。地方認同也許,在開始時,是來自於對一個共同敵手的抵抗,但是這不足以讓人愛上一個地方,人還必須要對一切構成其特性的東西加以注意,而這在事後又會反過來,證明自己戰鬥所為是對的。
亞歷山德羅:防衛區當然並沒有發明這些與非人相連結的方式。就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所有人每天都會有一些屬於別的宇宙論系統的直覺,我們每個人也都會採取與之相應的一些做法。任何一個小的養殖業者都會與他養的動物和他領土裡的某些非人存有連結起一些社會關係,特別是情感關係。但是總體來說,那都是在反向上的自然主義大潮中,這裡或那裡,冒出來的一些孤立的時刻。小畜牧業主,在某一個時刻,必然會被經濟法則逼迫,將自己養的動物看作是物資。在防衛區裡很特別的,主要是因為它的規模,就是這種相對於自然主義的偏離,會在一個相對寬廣的人與非人的集體層次,透過習俗、實踐、觀念和共同價值,穩定下來並且制度化。那真的是另外一個世界的草圖,而且還帶著意料之中的所有的變奏與對立。比如説,素食主義者和養殖業者之間,人跟非人所建立的關係類型就差別很大。但是他們卻有著一個共通的宇宙觀基礎,那就是超越自然主義的利用關係和對非人開放的社會關係場域。反過來,在群組裡穩定下來的便會進一步深入到行為和敏感度之中。而這正是防衛區裡最令人稱奇的事情之一:這些與領土和別的存有相關聯的方式,一點一點被人接受,甚至包括那些一開始對生命並沒有什麼特別敏感的人。你談到了你遇到過的防衛區人,對生命發展出了一種特別的敏感。但說到底,最有趣的可能恰恰是,他們還是屬於少數。住在或者是待過防衛區的絕大多數的人,並沒有特別對鳥、對花、對蠑螈有什麼興趣。但是從你在這樣的一片領土裡待過一段時間開始,沉浸在組織了那裡不同集體生活的那些明裡和暗中的結構之後,就會自發地採納在那裡被視為有效的宇宙觀特徵,尤其是對實用主義的排斥。慢慢地,對生命體的敏感開始發展,包括那些本來最無動於衷的人。在所有別的地方,制度性的結構都在把我們拉向相反的方向:小畜牧業者,事業擴大,就得學會將他的動物物化,才不會發瘋。巡山員,厭惡了僱用他的機構那套管理邏輯,就得辭職或是壓抑自己對樹的熱愛。在防衛區裡,就連最為都會的行動者也都會在某天早上,被一隻知更鳥或是一頭蜥蜴顯而易見的內心世界驚喜到,或者至少是不可能把圍繞自己的那些非人存有看作是要保護的自然或是生產物資。
菲利普:如果有一個民族誌調查去理解在什麼條件下、通過什麼樣的過程、在多長的時間之後,一些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知識與精神環境完全處於無所不在的自然主義籠罩之下的人,能夠發生這樣的轉變,將會是非常珍貴的材料。如果能夠理解在一個新環境中的社會化,如何讓人可以採納新加入的群體的價值,也會很有意思;而加入這個群體,就是因為預感到這些價值更符合一些自己先前未必清楚意識到的深層期待。這個問題跟阿秋瓦小孩上學那個是並列的:一個城市出身的防衛區人,一開始對蠑螈、野豬很不熟悉,他是怎麼釋放出那些先前被自然主義一再壓制的非標準推論的?是在交談之間,在對日常生活的事件加以敘述之後?一些隨著情境不斷強化的深切的信念,因為突然有了別人所說的話語而終於能夠得到表達?是在面對某些非常具體的選擇時機,像是要挑選砍伐這棵或是那棵樹的時候?
亞歷山德羅:我不知道防衛區的各位住民是不是認同我們剛剛所說的一切……就跟任何話題一樣,意見很可能分歧很大。我想,有的人會說,認為只要在防衛區住過就能夠走出自然主義是太過誇大;別的人會說,他們早在來防衛區生活之前就很清楚意識到自然主義的局限;還有的人會說,既然在這塊領土上是要嘗試與國家對抗,提出「別的東西」,那麼對實用主義加以質疑就很正常。
但是很多人很可能會認為,與非人的一種新的關係的出現,是跟居住在一片抗爭中的領土上這件事密切相關的,因為必須每天盡力對抗國家、對抗資本主義霸權(前者成了後者的武裝擔保,不管其形式是一個機場規劃還是集約農業,就像我們今天這樣)。在與樹籬田明顯的情感連結和(在司法抗爭中與保育物種;在土地佔領行動中與牛群、羊群和栽種植物)特別的聯盟之外,我認為,在這樣的情境下,人可以自發地辨識出一個共同的壓迫者、一個人與非人要一同戰鬥的敵人:就會覺得自己跟所有那些受到同樣的經濟與政治詭計威脅的存有是一條戰線的。我相信,這當中有一種,無論是對正在進行的社會抗爭與生態抗爭的關係重組,還是在脫離自然主義的方式上,都要一般性許多的經驗。
裂解自然主義領土
嘗試從目前在荒地聖母鎮發生的事件中總結幾點觀察
亞歷山德羅・皮諾紀:你剛剛說的,關於薩拉雅庫的寓居地與寓居人關係的翻轉,當然跟現在在荒地聖母防衛區發生的事件相呼應。正如一位防衛區住民所言39:「最近幾年是樹籬田在用我們的身體來捍衛它的完整性40」。在雙方友善共處的關係當中,是樹籬田同意讓防衛區人寓居。他們相對於它,透過因為它而在人之間、以及與非人之間構織的多重變動連結,是處於一種存有論意義上的依賴形式之中的。而且,這正是在2012年和2018年的兩次驅離行動當中,幫助拯救了防衛區的原因所在。國家不曾預料到佔領民眾捍衛他們生命環境的決心。就跟在本地原生抗爭當中一樣,他們捍衛的不是自然、生物多樣性或是別的這類抽象的概念,而是已經慢慢變成了構成他們自己所是的一團關係叢結。所以他們才能夠堅持到願意賭上他們的生命41。
在現場,我相信自己從來不曾聽到用「自然」來談論防衛區和其中各種不同的環境。這並不是說各位住民禁止自己使用這一字眼,因為他們看了太多菲利普・德斯寇拉的書,而只不過是因為這個詞完全失去了有效性。同樣,把森林、草地或是池塘當成是待開發的純資源,或是要保護的空間,也會是件很詭異的事。很顯然,這些生命環境和生活於其中的非人,都是這個集體完整意義上的成員,彼此之間理應善待對方,一起分享這塊共同的領土42。防衛區的一個住民,在一段拍他勞動的影片中解釋說43:「森林的利益優先於我們的」。防衛區的集體當然很開心有木材去搭建他們的樑柱,但是在選擇要砍伐的樹木時,則是森林的可再生性問題優先於人對木材的需求。當然了,森林的利益是什麼,需要人去想像發展,但是有一些指標還是相對明確的。比如說,當你知道一棵樹平均要到150歲之後,保有的生物多樣性才會達到最高程度,而由ONF(國家林業局)管理的森林是永遠也不會達到這樣的年歲,那你就可以想到採納森林的視角,就必須首先轉換時間尺度44。在這片領土上組織生活的決定,特別是生產活動的決定,就不再是由經濟邏輯引導,而是由集體認定的可欲狀態,這個「集體」就是要盡可能納入樹籬田和它的非人住民。
這麼做,我們並沒有變成泛靈主義者,但的確是超越了自然主義,在走向某種別的、混雜的狀態。注意力機制在轉化,限定重要與否的界線在移動,使用的概念術語在更新。Baptiste Morizot,還有別的一些人,在致力於陪伴這次的概念更新。根據他的觀點,並不是要像泛靈主義那樣,努力賦予植物和動物一種與人相似的內在性,而是要同時承認它們的親近性與他異性,將它們主體化但又不要擬人化,堅持尋找對它們來說最「適切」的「關懷」45。
菲利普・德斯寇拉:我的確認為,即使是在聖母荒地的樹籬田,也很難跳出經過自然主義社會化而形成的慣習,突然開始在夜裡夢見蠑螈在抱怨濕地的縮減,或是把菌菇中毒認定為野豬精靈的報復所為。但話說回來,我在防衛區短短的停留期間,的確讓我很驚訝的是,接待我的人相對於非人存有,已經發展出了一種,除非是在某些農人或是一些一生都在與植物和動物親密互動的專業生態學者身上,非常少見的注意力機制。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對一個環境特性極為敏銳的觀察力──構成環境的植被、植被為這種或那種動物提供的保護、植栽不同朝向的效果,等等──同時又對環境的每一個成分有種緊密的親切感──這棵樹的位置對它的生長是好還是壞、那頭羊有多任性、那片穀物過於向北迎風,等等。對每一個動物和植物個體的關注讓人可以看到它在所屬的跨物種集體當中如何行動,它又是怎麼受這個集體的影響。而依照防衛區眾多住民的城裡人出身判斷,這一類注意力很可能一開始完全不是自發的,它是一點一點,因為對保衛這個地方免受外部侵擾有了全面的認同,而逐步形成的。地方認同也許,在開始時,是來自於對一個共同敵手的抵抗,但是這不足以讓人愛上一個地方,人還必須要對一切構成其特性的東西加以注意,而這在事後又會反過來,證明自己戰鬥所為是對的。
亞歷山德羅:防衛區當然並沒有發明這些與非人相連結的方式。就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所有人每天都會有一些屬於別的宇宙論系統的直覺,我們每個人也都會採取與之相應的一些做法。任何一個小的養殖業者都會與他養的動物和他領土裡的某些非人存有連結起一些社會關係,特別是情感關係。但是總體來說,那都是在反向上的自然主義大潮中,這裡或那裡,冒出來的一些孤立的時刻。小畜牧業主,在某一個時刻,必然會被經濟法則逼迫,將自己養的動物看作是物資。在防衛區裡很特別的,主要是因為它的規模,就是這種相對於自然主義的偏離,會在一個相對寬廣的人與非人的集體層次,透過習俗、實踐、觀念和共同價值,穩定下來並且制度化。那真的是另外一個世界的草圖,而且還帶著意料之中的所有的變奏與對立。比如説,素食主義者和養殖業者之間,人跟非人所建立的關係類型就差別很大。但是他們卻有著一個共通的宇宙觀基礎,那就是超越自然主義的利用關係和對非人開放的社會關係場域。反過來,在群組裡穩定下來的便會進一步深入到行為和敏感度之中。而這正是防衛區裡最令人稱奇的事情之一:這些與領土和別的存有相關聯的方式,一點一點被人接受,甚至包括那些一開始對生命並沒有什麼特別敏感的人。你談到了你遇到過的防衛區人,對生命發展出了一種特別的敏感。但說到底,最有趣的可能恰恰是,他們還是屬於少數。住在或者是待過防衛區的絕大多數的人,並沒有特別對鳥、對花、對蠑螈有什麼興趣。但是從你在這樣的一片領土裡待過一段時間開始,沉浸在組織了那裡不同集體生活的那些明裡和暗中的結構之後,就會自發地採納在那裡被視為有效的宇宙觀特徵,尤其是對實用主義的排斥。慢慢地,對生命體的敏感開始發展,包括那些本來最無動於衷的人。在所有別的地方,制度性的結構都在把我們拉向相反的方向:小畜牧業者,事業擴大,就得學會將他的動物物化,才不會發瘋。巡山員,厭惡了僱用他的機構那套管理邏輯,就得辭職或是壓抑自己對樹的熱愛。在防衛區裡,就連最為都會的行動者也都會在某天早上,被一隻知更鳥或是一頭蜥蜴顯而易見的內心世界驚喜到,或者至少是不可能把圍繞自己的那些非人存有看作是要保護的自然或是生產物資。
菲利普:如果有一個民族誌調查去理解在什麼條件下、通過什麼樣的過程、在多長的時間之後,一些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知識與精神環境完全處於無所不在的自然主義籠罩之下的人,能夠發生這樣的轉變,將會是非常珍貴的材料。如果能夠理解在一個新環境中的社會化,如何讓人可以採納新加入的群體的價值,也會很有意思;而加入這個群體,就是因為預感到這些價值更符合一些自己先前未必清楚意識到的深層期待。這個問題跟阿秋瓦小孩上學那個是並列的:一個城市出身的防衛區人,一開始對蠑螈、野豬很不熟悉,他是怎麼釋放出那些先前被自然主義一再壓制的非標準推論的?是在交談之間,在對日常生活的事件加以敘述之後?一些隨著情境不斷強化的深切的信念,因為突然有了別人所說的話語而終於能夠得到表達?是在面對某些非常具體的選擇時機,像是要挑選砍伐這棵或是那棵樹的時候?
亞歷山德羅:我不知道防衛區的各位住民是不是認同我們剛剛所說的一切……就跟任何話題一樣,意見很可能分歧很大。我想,有的人會說,認為只要在防衛區住過就能夠走出自然主義是太過誇大;別的人會說,他們早在來防衛區生活之前就很清楚意識到自然主義的局限;還有的人會說,既然在這塊領土上是要嘗試與國家對抗,提出「別的東西」,那麼對實用主義加以質疑就很正常。
但是很多人很可能會認為,與非人的一種新的關係的出現,是跟居住在一片抗爭中的領土上這件事密切相關的,因為必須每天盡力對抗國家、對抗資本主義霸權(前者成了後者的武裝擔保,不管其形式是一個機場規劃還是集約農業,就像我們今天這樣)。在與樹籬田明顯的情感連結和(在司法抗爭中與保育物種;在土地佔領行動中與牛群、羊群和栽種植物)特別的聯盟之外,我認為,在這樣的情境下,人可以自發地辨識出一個共同的壓迫者、一個人與非人要一同戰鬥的敵人:就會覺得自己跟所有那些受到同樣的經濟與政治詭計威脅的存有是一條戰線的。我相信,這當中有一種,無論是對正在進行的社會抗爭與生態抗爭的關係重組,還是在脫離自然主義的方式上,都要一般性許多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