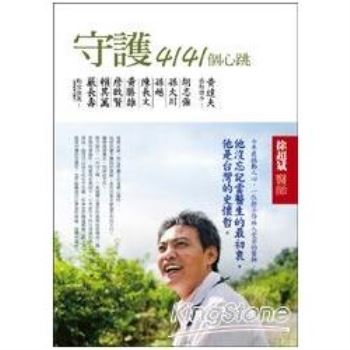醫護就是一個團隊
我第一次學會打針就是在內科病房內。頭一回是由一位交情深厚的學長帶著我,他邊打針邊教我步驟和技巧。一開始我沒抓到訣竅,連續打了六位病人都宣告失敗。那個時候,我因擔心病患會受不了疼痛,又怕被他們責罵,只要病患連打兩針都打不上,我立刻向資深的護士求援,並且在旁邊仔細觀察她們的技巧,幸好我笑話、點子超多,為人也極好相處,所以沒多久就與護理人員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係,也因為這層關係,許多醫師叫不動的護士,我卻輕易就可以求得幫忙,甚至有些護士會在我忙不過來時主動前來協助。
正因為如此,我當醫生十餘年來,不論再怎麼忙、遇到再難處理的病患,我從未對護理人員咆哮、責難,所以,每當我看到一些大牌醫生,脾氣來時,對護士怒罵、丟病歷或摔器械,心中總是不解,醫護本是一體。要拯救病人,並不是一個拿著手術刀的醫生就能完成,護士、助手等人的協助,都對病人的生死起著關鍵的作用。醫生與護士應該屬於同一個團隊,共同為病人的健康努力打拚。
隨著我打針的技巧逐漸成熟,我求助護士的次數越來越少,到後來,她們請我幫忙的機會反而多了。
破天荒
有一位中年婦女,我印象很深刻。我不記得她得了什麼病,只記得她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住院治療。有一次她住院時剛好輪到我值班,那次她的靜脈留置針,我一針就順利打上了,此後她住院時,都會對病房護士指名:「我的血管很不好打,請你幫我找那個長得黑黑的山地醫生來替我打針。」護士一聽,立刻明白她要找的人是我。但有時儘管護士對她說明我已下班,今天的值班醫師打針技術也很好,她還是堅決要指定我。那時我心想,病患選擇主治醫師診療及開刀時有所聞,但竟然有人會指定實習醫師打針,這恐怕是破天荒吧。
當時,醫院每個月都會安排教授級醫師查房,查房前,所有大大小小的醫生就在護理站等待,時間一到,一大群醫師就浩浩蕩蕩地到病房做床邊臨床教學。其實,我一向不太喜歡這樣的學習方式,每次教授遇到特殊的案例要年輕醫師視診或觸診時,看著同學們爭先恐後地上前審視或觸摸病灶,我總不由自主地想,換作我是病人,被一大群人圍觀,已經夠難受了,還要被當成教材般任人觸摸,真是情何以堪。
所以,每當這個時候,我通常會躲在後頭,只要沒被教授注意到,我能不碰病患就儘量不碰,以免病患尷尬,但事後我又常懊悔,我會不會因此比其他同學少學了一些東西?我會不會因此比其他同學少了一些實務上的實習,然而我卻始終改不了這種習慣,總是讓它一再發生。(待續)
最震撼的醫學教育
在實習生涯中,我最難忘,也影響我最深的是皮膚科及婦產科,兩科的主任分別由醫學院及附設醫院院長兼任。説來奇怪,我與兩位院長似乎特別投緣,兩人對我都很親切。
皮膚科的胡院長,是留美的皮膚科專家,記得我大五時,曾因指導教授的引介,在院長室召見過我,所以每次跟他的門診,他總會問我:「將來要走那一科啊?有沒有興趣來皮膚科?」那時候總是看到他隨身帶著一本附有圖譜的原文書籍。看見病患身上長出不明的疹子,他毫不避嫌,當場就會翻書對照。當時我深感震撼,堂堂一個留學美國的皮膚病專家,居然還如此謙卑到在病人面前翻閱書籍。
在往後的行醫日子裡,我也養成隨身攜帶必要書籍的習慣,但因為我並非名醫,怕病患對我失去信任,我不敢在病人面前翻書。每每遇到未曾見過的現象或難以解釋的病情,我都會利用時間跑回休息室對相關疾病的診斷及治療猛翻書本。
為病人奮戰到最後一刻
當天下午,我剛好要跟陳院長開一台子宮頸癌的刀,然而,那天手術非常不順利,病人的腹腔一直冒出大量的鮮血,我們邊輸血邊開刀,不知過了多久,我抬頭望望牆上的時鐘,竟然已經下午五點多了,其他同學們大概都高高興興地打包東西回家了吧。當我這樣想時,麻醉科醫師大喊:「病患血壓急速下降,出現心室震顫,準備電擊。」我們退到一旁,騰出急救的空間,經過一番處理後,病人總算回復正常心跳、血壓。
後來,陳院長接著說:「我們繼續。」於是我們的手術持續進行,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病患腹腔中的血還是止不住,眼見病人的搶救機會越來越渺茫,我看著年近八十歲的陳院長,站立多時又汗流滿面,但他卻為了病人,依然奮戰到最後一刻,我的心底滿是感動,也深刻覺得,只要患者有一絲一毫活下去的機會,身為醫師的我們,就絶對不能放棄。
但晚間八點多,病患卻撐不下去了,手術也只能無奈的到此為止。我看見院長頹然脫下手術袍,他紅著眼眶,滿臉哀悽地走出開刀房向家屬宣布惡耗。那一晚,我九點才回到家,在實習的最後一天,我依然學習到身為醫生最寶貴的一課。
醫師就是要有這樣的肩膀和擔當
多年以後,我決定離開醫院,回鄉服務,在奇美醫院急診室最後一天當班時,那天急診室也是忙成一團,傷患來來去去,與我一起上班的住院醫師,可能消受不了大量湧入的病患,每當檢傷護士推病人到診區時,立刻大聲抱怨檢傷護士:「別再推床進來了,這裡嚴重塞車了。」我見狀,馬上出言制止:「沒關係,推過來,我來處理。」
原本,我應該下午五點就可以交班回台東了,但我依舊放不下心,一直到將觀察室的病人逐一再次檢視,交給下一班的主治醫師接手為止。那一天,我離開醫院時恰巧也接近晚間九點。
臨走前,我告訴那位大發脾氣的住院醫師:「將來有一天,你也會成為獨當一面的主治醫師。你千萬要記得,在醫院裡,護理人員是協助你治療病人的最佳幫手,你和護士、助手們是一個團隊,團隊就必須合作,才能用最精準的診治、最快的速度把病人從死神手中搶回來,所以無論你再忙,心情再壞,或遇到多麼無法掌握的狀況,你都不能把氣出在護士身上,更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診治病人。當一個主治醫師,就是要有這樣的肩膀和擔當。」(待續)
視病猶親
有一位八十幾歲的老阿嬤,因跌倒導致股骨頸骨折,我一面為她輸血和做止痛治療(大腿骨骨折,大約會流失一千五百毫升的血液,這對老人家的身體是極大的負荷),一面向家屬解釋病情並詢問他們開刀的意願。
我告訴他們:「病人年紀這麼大了,手術不可能讓病人恢復行走的能力,只是要讓病人至少可以坐起來吃喝拉撒,若不開刀,病人只能躺著生活,那三個月後老人家可能會因反覆的肺炎和泌尿道感染而死亡,當然,年齡那麼大,開刀的風險也高,病人也可能捱不過麻醉和手術的壓力。」
如果她是我阿嬤,我會選擇開刀
十幾位家屬七嘴八舌討論很久,沒有一個人願意負起責任決定是不是要開刀。我擔心等久了病人情況有變,看著他們猶豫不決,無法下決定,我突然靈機一動,找了幾位較年輕的家屬對他們說:「我知道一時要你們馬上做決定相當困難,因為要考慮的因素很多,但我可以告訴你們,如果她是我阿嬤,我會選擇開刀。」沒多久,他們立刻就簽了手術同意書。
當時我的感觸非常深刻。或許一般民眾不像醫生擁有醫學常識,所以面對一些醫療情況常常會不知所措,但其實只要我們醫護人員能設身處地,多以同理心,將心比比地站在他們的立場,多為他們設想一點或多做一點,即使只是簡單幾句話的提醒、叮嚀或建議,我相信對病人的幫助都很大,尤其在心理層面上,畢竟醫療不只是醫治身體上的病痛,也應該包括安撫病人的心、家屬的心。只是很可惜,這一點在我們的醫療體系內,似乎總是做的不夠多,或者往往被忽略了。
還有一位從台南鄉下送來到院前死亡的老先生,經過急救後,病人暫時恢復生命徵象,但我判斷病患因缺氧時間過長,恐怕撐不過二十四小時,偏偏那時全院的加護病房都滿床,問遍台南縣市,也沒有一家醫院的加護病房有空位,好不容易問到高雄一家中小型醫院有空床可以轉過去,但我搜尋家屬只找到一位老阿嬤。
我決定要為他們與醫師周旋到底
我問老阿嬤有沒有其他年輕的家屬可以幫忙,老太太搖搖頭說:「我們家小孩都在外地工作,沒有辦法聯絡上。」我看著這位鄉下的老阿嬤,心想她可能半個字都不認得,甚至連高雄在哪裡可能都不知道。如果老先生轉過去沒多久就過世,她又得找救護車把病人送回家。我心中盤算著:她付得起救護車的錢嗎?她認得從高雄回到家的路嗎?看到老阿嬤驚惶失措的表情,我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公、外婆,於是我決定要為他們與加護醫學部的醫師周旋到底。
電話那頭,加護病房的醫師不斷以不符合加床原則為理由拒絕再收病人,無論我怎麼說,不管動之以情,或者威脅利誘,他始終都不為所動,最後我對他說:「我實在不忍心看著這位年老阿嬤來回奔波,而且她的老伴活下來的機會也不大。別再跟我說什麼加床原則了,你捫心自問,如果這是你自己的家屬,他們是你的阿嬤、阿公,你收是不收?」聽到我這句話,他才回答:「好吧,好吧,我挪床看看。」(待續)
死亡的味道
二○○○年底,我在奇美醫院升任完全可以獨當一面的主治醫師,當時是我行醫生涯中經驗技術最好,直覺也最靈敏的時期。有天早晨,我與前一班的主治醫師對留置病患逐一交班,來到一位老太太的病床前,同事正講述她的病情時,我望見病人黯淡的眼神和憔悴不堪的身體,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奇特的感覺,立刻脫口而出:「趕快找一張加護病床,把病人收治進去。」
同事用疑惑的語氣問:「可是,病人的生命徵象很穩定,為什麼要進加護病房?」我回應:「因為,我在這個病人身上聞到『死亡的味道』。」住院醫師雖然有點懷疑,但他還是照做了,只可惜在進加護病房的隔天,這名病患就過世了。
另一個午夜的急診室,病人來來去去,紛亂不已,在吵雜聲中,我發現一位剛被檢傷護士推進診區的病患,雖然意識清楚且心跳、血壓正常,但一直嚷著要大小便。這個場景觸動了我的敏感神經,那股奇特的感覺又浮現我腦中,於是我馬上要求診區護士,將病患推至急救區準備插管急救。
那時病人什麼檢查都還沒做,護士小姐一臉茫然,直問:「為什麼?」我一時不知如何解釋,只好回說:「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個病人情況危急,必須趕快緊急處理。」大約半小時後,病人的病情瞬間急轉直下,所幸先前有預做急救準備,雖然最後的結果讓我們覺得遺憾,因為病患仍宣告不治,但至少我們確實盡力做了我們當初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我覺得你當醫生太可惜了!
有天傍晚,我與一位當骨科主治醫師的好兄弟在樓梯間抽菸閒聊,他對我說:「我很少碰過像你這樣用鼻子就可以馬上嗅出病人病情的醫生。我覺得你當醫生實在太可惜了。」
其實我能擁有嗅出「死亡味道」的敏銳直覺,這項看來傲人的特殊能力,也許有部分是上天特別賦予,但絕大部分其實是要感謝那些難以計數、病情又千變萬化的眾多病人,是他們累積了我看診時做各種判斷與治療方法的豐富經驗,是他們訓練了我的醫學專業。(待續)
只有kuisan了解我們的病痛
七年前,我回鄉看診,經歷七年的辛勤耕耘,我當年懷抱的夢想已逐一實現,現在的衛生所不論在各項軟硬體都有長足的進步,更獲取廣大民眾的信賴。在即將服務期滿的前夕,我回首七年來的點點滴滴,忍不住問自己,我真的做到了鄉親對健康的期待與需求嗎?鄉親對醫療的真正需要又是什麼?
其實,現今的成就,只是當年我夢想中遠大藍圖的初步規劃。那時候,我甚至想過,在完成這些計劃後,未來若有機會,希望能引進更先進的醫療儀器和更完整精實的醫療團隊,進駐這個數十年來最偏遠的醫療荒漠。
然而,我心裡也很明白,在講究成本效益的現代社會,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有誰願意將大把鈔票挹注在這個人口不到萬人的偏遠山區,又有多少的優秀醫師願意降纡尊貴,忍受微薄的薪資來到這個窮鄉僻壤?對一般人來說,這不但不符合投資報酬率,也不啻浪費醫療資源。雖然明明知道這樣的願望可能永遠無法實現,然而我依然朝著這個夢想前進,而且堅持不放棄。
上週五早晨,近一年來三不五時就跑來衛生所的朱老伯又來診間報到,他說自己上腹部疼痛。扶他躺上診療床,做完觸診後。我直覺懷疑他是肝臟出了問題,於是替他安排腹部超音波檢查,掃瞄結果發現他的肝臟部位果然有不正常的影像,可惜衛生所現有的超音波儀器解析度不甚佳,在沒有十足把握的情況下,只好請老伯伯到醫院做進一步且更精密的檢查。
沒想到朱伯伯用著非常無奈的眼神對我說:「主任,我一大把年紀了,生活不方便,又沒有交通工具,身邊也缺乏親人照料。如果我的病況,衛生所沒辦法治療,我也不想再耗費時間到醫院接受折磨,我寧願死了算了。」
我腦袋瞬間轟地一聲響。這是多麼熟悉的語氣啊!
事實上,這些年來,每當遇到衛生所無法處理的病患而必須轉介到醫院時,許多病人礙於經濟或生活的因素,常常會回我類似的話。我當然知道他們絕非自暴自棄,也不是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只是長期處在醫療資源缺乏的現實,又處於社會與經濟的弱勢,早讓他們對生活養成聽天由命的豁達性格。
這並非出自於天性,而是在現實環境逼迫下,所不得不做的選擇。所以每回聽到這樣的回答,我除了搖頭深深嘆息之外,也想問上帝,難道窮苦人家就沒有生病的權利?而人世間的公平正義又在哪裡?
前些日子,我與部落裡一位常年旅居在外的老朋友閒聊,他向我提起有一回他休假返家時,正好聽到村辦公處的廣播聲響:「各位村民,今天村莊有巡迴醫療,要看病的民眾請趕快到衛生室來。」接著他就看到一大群老人家蜂擁而出,邊走邊說:「kuisan(日語,意指醫生)來了,我們趕緊去看病。」
但沒多久,又看見原班人馬垂頭喪氣走回來。他好奇地問:「你們不是去看診嗎?怎麼那麼快就看完了?」老人家回答:「不是我們的kuisan(這裡指我),所以我們就折回來了。」他納悶地問:「不是一樣都是醫生嗎?有什麼不同?」老人家堅定地搖頭說:「當然不一樣,只有kuisan才了解我們的病痛。」
昨天在新化村做巡迴醫療時,巧遇了許久未見的雲婆,我原本擔心她會因失智症而忘了我,但令人驚喜的是,經過我稍加提醒,她的眼神立刻亮了起來,還歡欣地說:「是你呀。」我與她寒暄了幾句,接著問她:「好久不見,最近身體好嗎?還有沒有繼續吃藥?」
她低頭說:「沒有啊,又沒有人幫我取藥。」離去前,我心疼地握著她的手。
晚間回到家,我一遍遍回想那一雙雙充滿無奈與渴望的眼眸,我終於漸漸明白一件事,比起高度專業的醫療團隊,偏遠地區的民眾更需要的是願意跋山涉水,傾聽他們心聲的醫生。相較於先進的醫療技術,部落鄉親更需要的是心靈可以依賴,以及託付病體的安定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