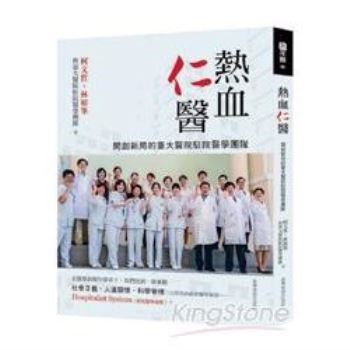代序 人因有夢想而偉大
柯文哲(臺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
二○○九年八月,我被叫進院長室,長官們只是輕描淡寫要我去開設「急診後送病房」,就這樣我開始從事一件和我過去二十年完全不同調的工作。我自從第四年住院醫師以後,就專任於外科加護病房之工作,器官捐贈移植、ECMO(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葉克膜體外維生系統)、人工器官、外科重症一直是我過去二十年主要的臨床工作,結果現在要開始處理以內科慢性病為主的一群病人,算是人生經歷的大轉彎。
回首過去三年多負責臺大醫院急診後送病房,簡而言之就是不斷的面對新問題,不斷的解決,然後又出現新的問題,再找新方法去解決新的問題,如此不斷的重覆。
本病房因為病人情況特別嚴重複雜,自始就沒有住院醫師、實習醫師的編制,改由主治醫師直接負責第一線的照護工作。過去一百年臺大醫院的主治醫師高高在上,病房雜務自有總醫師率領眾住院醫師打點一切,這個病房卻只有主治醫師率領專科護理師處理一切臨床工作。
法律上規定不可以的,當然是不可以的。但是法律上沒規定的,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主治醫師和專科護理師的分工,始終受制於這個困擾,幾年下來,我才知道法律不是為開創者制定的,而是為追隨者制定的,因為一定要有第一個人做了第一件事之後,人們才會驚覺:以前怎麼沒有相關的規定?沒有住院醫師,當然假日、夜間的值班就要主治醫師負責了。但是外面醫院視為當然的事情,在這家百年老店的臺大醫院就變成了「百年創舉」。
「創舉」已經有些困難,但前面加上了「百年」這兩個字就顯得更沉重,怎麼辦?只好讓它再沉重一點!當主任的我也自己下來值夜班,讓看似創舉的事情變得比較能被大家接受。
既然是新創事業,所以每天上工都不知今天要冒出那些煩人的新問題。既然是「急診後送病房」,當然病人從急診而來,但是到底是急診的哪些病人?沒有規則,總要訂些規則好讓彼此遵守,但是規則之外,總要有例外好讓大家方便。於是日常之中有規範,規範之中有例外,例外之中又有默契。日子就是這樣在摸索之中匍匐前進,尋找一個平衡點。
急診有一五○名等著住院的病人,可是明明全醫院各病房加起來有二五○張空床,但是追問起來又都有理由:這張空床是明天預定要住院的,後天的手術也已排定了;這張空床是下午病人突然想回家才空出來的;這張空床的病人去開刀了,今晚住加護病房,可是明天就會轉回來……。於是要設「公床管理」解決全院床位調度之問題。規則有了,但是電話加筆記本無法運作這個複雜規則之下產生的大量資訊,於是連夜寫出一個網路訂床系統,再貼心的增加一個簡訊通知系統,告知訂床者:恭喜,你要的床有了。當然如果沒有消息,就是壞消息:你訂了,但是沒有你要的床。
既然外科系的骨科、耳鼻喉科、泌尿科平時不處理內科問題,但是偶有各種嚴重內科疾病的病人(洗腎、中風、心衰竭……),需要這些外科醫師開刀,只好開辦「共同照護」(combined care)的雙主治醫師制度,內科醫師和外科醫師共同處理一名需要手術的嚴重內科病人。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績效、責任如何劃分?又是一連串的磨合。
臺大醫院接管金山醫院,我們要讓金山之民眾有感:醫學中心的臺大醫院來服務金山地區的鄉親了!所以金山分院轉總院住院的病人,就不應讓他們一樣在急診候床等住院,要讓他們可以直接安排轉院住院。但是怎麼辦?那就設一個分院病人轉總院住院的單一熱線窗口,併入「公床管理系統」且有第一優先權。接著金山要開辦住院業務,各科部都不想派住院醫師支援這個業務,深怕尾大不掉被拖下水,以後無法脫身,怎麼辦?我們不是有可以執行第一線照護的專科護理師嗎?那就先派去支援,只要臺大醫療體系某個分院某個部門缺人力,我們都可去應急,於是我們成了「人力派遣公司」。
看著每月的報表,怎麼周轉率一直下降?雖然我們都是收治各科不想要的病人,但是各科不想要的病人,種類卻會改變!以前是病況較複雜嚴重的病人,但是院方強調績效的前提下,低優先順序的病人不再是複雜嚴重的病人,而是「鐵床」的病人,就是一旦住院,不易恢復到可以出院的程度,但也不會變壞到會死亡的程度!也就是說一旦住院就會住到天荒地老的病人,在本病房越來越多,此時才驚察臺大醫院這個全國醫療最後一線的陣地,卻一直沒有建立下轉的管道,只有轉院進來的,卻沒有轉院出去的機制。連帶的中期照護、居家護理、居家安寧、轉診基層診所,這些好像都不完整?單向轉診的結果,就好像水庫被淤砂漸漸填滿,而失去了水庫的功能,於是建立「下轉機制」又變成了新的課題。
聖嚴法師的名言:「面對它、處理它、接受它、放下它。」這很像我們過去三年的寫照。我們總是面對新問題,想出方法處理它,解決之後,趕快空出雙手,因為又有新的問題要交到你的手中。我常開玩笑說:只要活得夠久,以後一定會遇到更慘的事情。而我們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最常遇到別人的反應是「以前都不是這樣!」我也常回答:「對啊!不變的只有化石,而我們不是化石」。每天在跌跌撞撞中度過,並不覺得日子有何不同?但是現在回首過去三年,卻驚覺「天啊!我們怎麼做了那麼多事?」不過還好,這個世界因為有我們,而變得更好,而不是變得更差。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本病房開辦三年,離職率奇低,雖然人才招募困難,但撐過試用期留下來就不會再走。這個單位最大的特色就是「新」,主治醫師是新的,護理長也是新的,護理師將近一半剛從學校畢業,專科護理師是訓練之後直接上任的新人。也許因為「新」,所以對「新事物、新制度」的接受度也特別高。
通常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的紛擾,我每次都說用人是用他的優點,不是用他的缺點,所以缺點能改正,就改正,不能改正就容忍它,只要不干擾大局就行。我每每告誡大家:「裝也要裝得一副相親相愛的樣子」,所以在這家歷史包袱頗重的百年老店,這個病房算是內耗最低的單位。大家雖然疲累,但也以改正台灣醫界亂象危局的角色自居,以熱情去追求理想的實現。
醫療糾紛是臺灣醫界這幾年最熱門的議題,但在這個人員充滿熱情、理想的單位,雖然我們收治最困難的病人,處理最複雜的病情,卻鮮少有醫療爭議事件。我相信人與人之間是互相的,我們有熱情、理想,別人也會回報以感謝、諒解。在這個多變的十倍速時代,預測未來是件困難的事,我們當然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不過,我希望以後的歷史,記載我們過去三年的努力,會這樣寫著:曾有一群充滿熱情與理想的醫護人員,為解決台灣醫界的問題而努力不懈,他們實踐了「人因有夢想而偉大」這句話。
楔子
駐院醫學科在臺大醫院之出現
柯文哲 (部主任)
二○○九年八月,健保局公布一項全國有關急診的資料:急診超長暫留病人的數目和比例,臺大醫院都是全國各醫院第一名;而從急診住院的病人比例,臺大醫院則是全國最低的。
雖然急診暫留人數太多已是陳年問題,但是又上了報紙總是要處理一下。於是有一天我被叫進院長室,院長一派輕鬆的說:你就負責開設一個急診後送病房吧。我還搞不清楚狀況就接下這個任務,但是事後多方打聽下,心情卻是越來越沉重。原來所謂專收急診病人住院的「急診後送病房」,以前已試辦過兩次,都不了了之的失敗收場。
內科主任帶著似笑非笑的表情說:「有時早上收了三個病人住院,下午就死掉兩個,當醫師的,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處理的。」外科主任好心的說:「你又不是急診,又不是內科,不要『假會』了。」
最後我直接去急診暫留實際觀察,到底都是些什麼樣的病人會堆在急診暫留區而無法住院?急診主治醫師解釋道:會在急診暫留超過三天以上而不能住院,沒錢沒勢應是基本條件,有辦法的早就自謀生路找門路住院去了。不過即使沒錢沒勢,如果得的病相對單純,還是會立刻收住院。例如急性心肌梗塞,依照醫院評鑑規定,到急診九○分鐘內需要接受心導管手術,一旦作了心導管手術,當然會立刻住院,不會留在急診。例如骨折,就算當晚沒有住院,第二天一早也會收住院準備開刀去了。
急性病人都不會在急診長期暫留而無法住院,但是如果是糖尿病二十年,已經腎衰竭洗腎五年多了,最近三年已有明顯心衰竭,這次是中風來急診,這種很多科(內分泌、腎內、心內、神經)都可收住院的,反而保證無法住院,他不能住院的理由是因為他的病太多太嚴重了。最後還有一群很難住院的病人,生命末期特別是已簽DNR(放棄急救同意書)的病人。
通常總醫師收一個簽DNR的病人住院,會被主治醫師罵:我們病房又不是在B3(註:臺大醫院往生室在地下三樓)!簽了DNR而不能住院,病人本人很不滿意,「我都快死了,你們也不醫治!」病人的家屬也很不滿意,「這個病人都快死了,你們也不優先處理!」至於在急診暫留被留置於這臨終病人兩側觀察的病人也很不滿意,因為他有病痛在急診暫留觀察,旁邊被擺了一個呼吸困難的臨終病人,其家屬肅穆的氣氛甚至呼天搶地的哭聲,結果生理的病痛還未解決,旁邊一個臨終病人帶來更多的心理壓力,所以也很不滿意。
最後急診的醫護人員也很不滿意,因為已經夠煩夠忙了,這臨終病人的家屬不是一直來報告病況,就是又來了一批家屬要求解釋病情。醫生心想:同樣的病情我已解釋好幾遍了,怎還有人要我再解釋一遍?雖然是同一個病人,但他可有一批一批不同的親友來看他。所以DNR病人暫留在急診,病人、家屬(親友)、其他病友、醫護人員通通不滿意,總之這是一個全輸的局面。
所以,低社經地位、病情太多太複雜、DNR,正是這群急診超長暫留病人的特色。我問:那麼為何沒人出面處理呢?急診主治醫師略帶挑釁的說:等你來處理啊!我那不信邪的脾氣又犯了,「好啊!那我來處理!」
經過一星期的考察和思索,我報告院長:「如果我們今天宣稱建立急診後送病房,是要替臺大醫院擦屁股,只是要解決急診超長暫留的病人,那麼我們只會找到衛生紙,不會找到人才。就算勉強去做,也是撐不久,一定會重蹈覆轍而失敗收場。所以是否我們反向思考,把這個病房當作試驗病房,採用全新的方法來試試看?因為重複過去失敗的方法不會成功的。」我說的新方法新制度,就是Hospitalist system(駐院科醫師制度)。
開啟Hospitalist的契機
我第一次讀到Hospitalist這個字是在《台灣醫界》雜誌,一篇介紹美國Hospitalist的文章。後來我去敏盛醫院當急重症醫療顧問時,敏盛的小老闆楊弘仁(臺大低我九屆的學弟)說:我有一個「十年百大」的夢想,要在十年內建立一百家醫院。當然所謂建立一百家醫院,不是從打地基開始蓋醫院,而是接管一百家醫院的經營權,就像目前看到的麥當勞、統一超商這些連鎖加盟店一樣,大家用同樣的標誌、操作流程等等。醫院和科部的關係則像是百貨公司和專櫃的關係,醫院大一些,裡面的專櫃就多一些,但這也不一定,因為同一專櫃在該百貨公司所占的面積,也可有不同。不過為了管理方便,專櫃的種類不宜太多。
同樣的道理,最理想情形是三○○─五○○床的醫院,裡面只有幾個科部,包括一個涵蓋該地區的糖尿病照護網,兩個CV中心(Cerebrovascular 腦血管,Cardiovascular 心血管),因為這兩類疾病的治療,需要很多加護病房床位,因有大量的加護病房床位,所以兼做外傷和各種內科急症。
就台灣十大死因之統計,雖然癌症占死亡人數的第一名(二十八%),但是我們計畫中的醫院,雖然裡面的科部(專櫃)只處理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糖尿病、肺炎、事故傷害等五個主要疾病,它們卻占全部死亡人數的三四.四%,還多於癌症。況且癌症只是一個泛稱,從腦癌、大腸癌到皮膚癌,根本跨過好幾個科部,也就是一家癌症醫院,事實上所有的科部都需要,根本就是綜合醫院。反之,我們設定的醫院就組織而言所需的科部包括神經內外科、心臟內外科、急診、一般內科就夠了,相對單純很多。
就運作而言,一家醫院只須分成三個部門:門診部(包括門診、急診)、住院部(包括一般病房、加護病房)、手術部(凡是需要醫師個人技術的都包括在內,包括手術、心導管、內視鏡……等)。而其中負責住院病人照顧的就是住院部的Hospitalist。如果我們可以接受加護病房有專責醫師,為何不能接受普通病房有專責醫師?傳統上,一位醫師要兼顧門診、手術及住院病人照護,不如予以分工使其各自專精。若能整合良好,效率及結果當可更加改善。不過後來我因擔任臺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不再去敏盛醫院兼任,這個計劃始終未實際試驗。此時要開辦急診後送病房,我就想到這個制度或可試用。
從5C病房開始
二○○九年十月,急診後送病房在5C病房開始,三名主治醫師,六名專科護理師,加上一些研究助理就上線了。病人全部來自急診,依照暫留時間最久的依序住院。
一開始的5C病人有兩個特色:
一、 非癌症安寧病人。癌症的安寧病人會住家醫科的安寧病房,但非癌症的安寧病人則主要住本病房。
二、 多重疾病。一個病人有很多科可以收住院,反而不易被收住院,而多住到本病房。
5C病房則有以下特色:
一、「新」:
這個病房一切都新,主持人的我已經二十年沒在普通病房工作過,主治醫師是新的,護理長也是新的,護理師一半是當年畢業的,一半是其他病房調來拼湊而成的,專科護理師訓練一個月就匆忙上線。但也因為全是新人,沒有歷史包袱,推行新制度反而容易。一開始我就戲稱它是「深圳病房」,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是「深圳」,而台灣醫界改革創新的起點就在「5C病房」。
我們高度使用電子科技,揚棄以前的病房白板、醫師值班表、護理師值班表及到處張貼的公告,改用一個網路電子螢幕來取代。
我們在病房裡設立一個門診,出院病人一個月內有任何問題可以打熱線電話來諮詢,若有需要,直接回到病房門診,由主治醫師診治。這個設計縮短了住院日,因為病人比較有自信心提早出院,因為有問題,可電話詢問,必要時,每日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都可回到病房門診尋求醫療;這個設計也減少了三十日內再入院比率,因為有問題可立刻處理,不會因延誤而使病情惡化到需要再次住院。甚至因為有需要才回病房門診就醫,所以也減少了出院的門診追蹤次數。
我們減少上班日和非上班日的人力差別,一般病房在上班日和非上班日醫師人力相差很多,我們只略微減少,所以非上班日的入出院作業幾乎不受影響,也大幅提升了病床周轉率。以前我的老師朱樹勳常開玩笑的說:「臺大醫院上班時間是國家醫院,下班時間就變成地區醫院」。我們雖然無法做到全年一致,但是必要的檢查和治療,差不多不受假日影響,當然同仁在非上班日工作的比例就比其他單位高很多了。
照護品質一致是我們非常強調的,所以不允許有所謂個別主治醫師專有的處方,所有的檢查治療均予以標準模式化(俗稱罐頭處方),如此效率提高,安全性也提高。因為大多變異只會增加人員的失誤。
二、 不斷的反省改進:
歐美試行良好的制度,常常移植到中國人社會就走樣而失去效用,其中之一就是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
併發症甚至死亡的病例,若能好好檢討,找出原因,予以改進,當能避免以後再發生,這是很有意義的。但是檢討要有效,必須大家開誠布公講實話,對事不對人,確實檢討才有用。如果被檢討的人抱著心理防衛機制,檢討的人或者怕得罪人而避重就輕;或者挾怨報復而無的放矢。最後大家以鄉愿的態度面對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行禮如儀甚至粉飾太平。若是團體之文化如此,還不如不要開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因為我們有較佳的企業文化,每週針對不預期急救和轉加護病房的病例作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只要發生了,一定追究:如果重來一遍,在系統上可作哪些改進,防止它再發生。三年下來,差不多病房作業的漏洞都補救了。我們收治臺大醫院最嚴重的病人,竟然已十五個月沒有不預期急救,過去七個月只有一個病人轉加護病房。長期不斷的反省作系統性的改進,已經建構一個病人安全的病房。
三、 以「人」為本:
從當見習醫師起,就一直被教導要看「病人」,不是看「病」。但是或許老師身教不好吧!只看到「器官」,沒看到「人」;只看到「病」,沒看到「病人」,仍然是臺灣醫界的普遍現象,醫療糾紛層出不窮也就不足為奇。
因此我們在病房公佈欄公告各個醫師的每日查房時間,讓家屬不至於因白等而浪費時間。平日沒用的隔離室,遇有二人房、三人房的病人臨終時,便把他移到隔離室,讓病人有較舒適的空間,家屬可較私密地和病人作最後的相處,也不干擾同病室其他病人。
只是一個挪床的動作,雖對病房工作人員增加一些負擔,卻能給病人、家屬留下一個感動的感激。目前醫病關係緊張,醫療糾紛已是醫療從業人員的夢靨,防衛性醫療也跟著盛行。這種互相防範、互相牽制的醫病關係,只會造成惡性循環。但在這個病房處處以病人為中心的文化下,在不知不覺之中扭轉了醫病關係緊張的現象,所以病房開辦三年以來,收治最麻煩的病人,卻幾乎沒有被投訴過。
這也增加我對人性的信心,我們對別人好,別人是否一定也對我們好?答案是不一定,但是九九.五%應該是肯定的,但我們不應為了那少數的○.五%而放棄了九九.五%,我堅信人與人之間始終是可以儘量作到「互愛、互信、互諒」的。
柯文哲(臺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
二○○九年八月,我被叫進院長室,長官們只是輕描淡寫要我去開設「急診後送病房」,就這樣我開始從事一件和我過去二十年完全不同調的工作。我自從第四年住院醫師以後,就專任於外科加護病房之工作,器官捐贈移植、ECMO(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葉克膜體外維生系統)、人工器官、外科重症一直是我過去二十年主要的臨床工作,結果現在要開始處理以內科慢性病為主的一群病人,算是人生經歷的大轉彎。
回首過去三年多負責臺大醫院急診後送病房,簡而言之就是不斷的面對新問題,不斷的解決,然後又出現新的問題,再找新方法去解決新的問題,如此不斷的重覆。
本病房因為病人情況特別嚴重複雜,自始就沒有住院醫師、實習醫師的編制,改由主治醫師直接負責第一線的照護工作。過去一百年臺大醫院的主治醫師高高在上,病房雜務自有總醫師率領眾住院醫師打點一切,這個病房卻只有主治醫師率領專科護理師處理一切臨床工作。
法律上規定不可以的,當然是不可以的。但是法律上沒規定的,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主治醫師和專科護理師的分工,始終受制於這個困擾,幾年下來,我才知道法律不是為開創者制定的,而是為追隨者制定的,因為一定要有第一個人做了第一件事之後,人們才會驚覺:以前怎麼沒有相關的規定?沒有住院醫師,當然假日、夜間的值班就要主治醫師負責了。但是外面醫院視為當然的事情,在這家百年老店的臺大醫院就變成了「百年創舉」。
「創舉」已經有些困難,但前面加上了「百年」這兩個字就顯得更沉重,怎麼辦?只好讓它再沉重一點!當主任的我也自己下來值夜班,讓看似創舉的事情變得比較能被大家接受。
既然是新創事業,所以每天上工都不知今天要冒出那些煩人的新問題。既然是「急診後送病房」,當然病人從急診而來,但是到底是急診的哪些病人?沒有規則,總要訂些規則好讓彼此遵守,但是規則之外,總要有例外好讓大家方便。於是日常之中有規範,規範之中有例外,例外之中又有默契。日子就是這樣在摸索之中匍匐前進,尋找一個平衡點。
急診有一五○名等著住院的病人,可是明明全醫院各病房加起來有二五○張空床,但是追問起來又都有理由:這張空床是明天預定要住院的,後天的手術也已排定了;這張空床是下午病人突然想回家才空出來的;這張空床的病人去開刀了,今晚住加護病房,可是明天就會轉回來……。於是要設「公床管理」解決全院床位調度之問題。規則有了,但是電話加筆記本無法運作這個複雜規則之下產生的大量資訊,於是連夜寫出一個網路訂床系統,再貼心的增加一個簡訊通知系統,告知訂床者:恭喜,你要的床有了。當然如果沒有消息,就是壞消息:你訂了,但是沒有你要的床。
既然外科系的骨科、耳鼻喉科、泌尿科平時不處理內科問題,但是偶有各種嚴重內科疾病的病人(洗腎、中風、心衰竭……),需要這些外科醫師開刀,只好開辦「共同照護」(combined care)的雙主治醫師制度,內科醫師和外科醫師共同處理一名需要手術的嚴重內科病人。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績效、責任如何劃分?又是一連串的磨合。
臺大醫院接管金山醫院,我們要讓金山之民眾有感:醫學中心的臺大醫院來服務金山地區的鄉親了!所以金山分院轉總院住院的病人,就不應讓他們一樣在急診候床等住院,要讓他們可以直接安排轉院住院。但是怎麼辦?那就設一個分院病人轉總院住院的單一熱線窗口,併入「公床管理系統」且有第一優先權。接著金山要開辦住院業務,各科部都不想派住院醫師支援這個業務,深怕尾大不掉被拖下水,以後無法脫身,怎麼辦?我們不是有可以執行第一線照護的專科護理師嗎?那就先派去支援,只要臺大醫療體系某個分院某個部門缺人力,我們都可去應急,於是我們成了「人力派遣公司」。
看著每月的報表,怎麼周轉率一直下降?雖然我們都是收治各科不想要的病人,但是各科不想要的病人,種類卻會改變!以前是病況較複雜嚴重的病人,但是院方強調績效的前提下,低優先順序的病人不再是複雜嚴重的病人,而是「鐵床」的病人,就是一旦住院,不易恢復到可以出院的程度,但也不會變壞到會死亡的程度!也就是說一旦住院就會住到天荒地老的病人,在本病房越來越多,此時才驚察臺大醫院這個全國醫療最後一線的陣地,卻一直沒有建立下轉的管道,只有轉院進來的,卻沒有轉院出去的機制。連帶的中期照護、居家護理、居家安寧、轉診基層診所,這些好像都不完整?單向轉診的結果,就好像水庫被淤砂漸漸填滿,而失去了水庫的功能,於是建立「下轉機制」又變成了新的課題。
聖嚴法師的名言:「面對它、處理它、接受它、放下它。」這很像我們過去三年的寫照。我們總是面對新問題,想出方法處理它,解決之後,趕快空出雙手,因為又有新的問題要交到你的手中。我常開玩笑說:只要活得夠久,以後一定會遇到更慘的事情。而我們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最常遇到別人的反應是「以前都不是這樣!」我也常回答:「對啊!不變的只有化石,而我們不是化石」。每天在跌跌撞撞中度過,並不覺得日子有何不同?但是現在回首過去三年,卻驚覺「天啊!我們怎麼做了那麼多事?」不過還好,這個世界因為有我們,而變得更好,而不是變得更差。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本病房開辦三年,離職率奇低,雖然人才招募困難,但撐過試用期留下來就不會再走。這個單位最大的特色就是「新」,主治醫師是新的,護理長也是新的,護理師將近一半剛從學校畢業,專科護理師是訓練之後直接上任的新人。也許因為「新」,所以對「新事物、新制度」的接受度也特別高。
通常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的紛擾,我每次都說用人是用他的優點,不是用他的缺點,所以缺點能改正,就改正,不能改正就容忍它,只要不干擾大局就行。我每每告誡大家:「裝也要裝得一副相親相愛的樣子」,所以在這家歷史包袱頗重的百年老店,這個病房算是內耗最低的單位。大家雖然疲累,但也以改正台灣醫界亂象危局的角色自居,以熱情去追求理想的實現。
醫療糾紛是臺灣醫界這幾年最熱門的議題,但在這個人員充滿熱情、理想的單位,雖然我們收治最困難的病人,處理最複雜的病情,卻鮮少有醫療爭議事件。我相信人與人之間是互相的,我們有熱情、理想,別人也會回報以感謝、諒解。在這個多變的十倍速時代,預測未來是件困難的事,我們當然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不過,我希望以後的歷史,記載我們過去三年的努力,會這樣寫著:曾有一群充滿熱情與理想的醫護人員,為解決台灣醫界的問題而努力不懈,他們實踐了「人因有夢想而偉大」這句話。
楔子
駐院醫學科在臺大醫院之出現
柯文哲 (部主任)
二○○九年八月,健保局公布一項全國有關急診的資料:急診超長暫留病人的數目和比例,臺大醫院都是全國各醫院第一名;而從急診住院的病人比例,臺大醫院則是全國最低的。
雖然急診暫留人數太多已是陳年問題,但是又上了報紙總是要處理一下。於是有一天我被叫進院長室,院長一派輕鬆的說:你就負責開設一個急診後送病房吧。我還搞不清楚狀況就接下這個任務,但是事後多方打聽下,心情卻是越來越沉重。原來所謂專收急診病人住院的「急診後送病房」,以前已試辦過兩次,都不了了之的失敗收場。
內科主任帶著似笑非笑的表情說:「有時早上收了三個病人住院,下午就死掉兩個,當醫師的,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處理的。」外科主任好心的說:「你又不是急診,又不是內科,不要『假會』了。」
最後我直接去急診暫留實際觀察,到底都是些什麼樣的病人會堆在急診暫留區而無法住院?急診主治醫師解釋道:會在急診暫留超過三天以上而不能住院,沒錢沒勢應是基本條件,有辦法的早就自謀生路找門路住院去了。不過即使沒錢沒勢,如果得的病相對單純,還是會立刻收住院。例如急性心肌梗塞,依照醫院評鑑規定,到急診九○分鐘內需要接受心導管手術,一旦作了心導管手術,當然會立刻住院,不會留在急診。例如骨折,就算當晚沒有住院,第二天一早也會收住院準備開刀去了。
急性病人都不會在急診長期暫留而無法住院,但是如果是糖尿病二十年,已經腎衰竭洗腎五年多了,最近三年已有明顯心衰竭,這次是中風來急診,這種很多科(內分泌、腎內、心內、神經)都可收住院的,反而保證無法住院,他不能住院的理由是因為他的病太多太嚴重了。最後還有一群很難住院的病人,生命末期特別是已簽DNR(放棄急救同意書)的病人。
通常總醫師收一個簽DNR的病人住院,會被主治醫師罵:我們病房又不是在B3(註:臺大醫院往生室在地下三樓)!簽了DNR而不能住院,病人本人很不滿意,「我都快死了,你們也不醫治!」病人的家屬也很不滿意,「這個病人都快死了,你們也不優先處理!」至於在急診暫留被留置於這臨終病人兩側觀察的病人也很不滿意,因為他有病痛在急診暫留觀察,旁邊被擺了一個呼吸困難的臨終病人,其家屬肅穆的氣氛甚至呼天搶地的哭聲,結果生理的病痛還未解決,旁邊一個臨終病人帶來更多的心理壓力,所以也很不滿意。
最後急診的醫護人員也很不滿意,因為已經夠煩夠忙了,這臨終病人的家屬不是一直來報告病況,就是又來了一批家屬要求解釋病情。醫生心想:同樣的病情我已解釋好幾遍了,怎還有人要我再解釋一遍?雖然是同一個病人,但他可有一批一批不同的親友來看他。所以DNR病人暫留在急診,病人、家屬(親友)、其他病友、醫護人員通通不滿意,總之這是一個全輸的局面。
所以,低社經地位、病情太多太複雜、DNR,正是這群急診超長暫留病人的特色。我問:那麼為何沒人出面處理呢?急診主治醫師略帶挑釁的說:等你來處理啊!我那不信邪的脾氣又犯了,「好啊!那我來處理!」
經過一星期的考察和思索,我報告院長:「如果我們今天宣稱建立急診後送病房,是要替臺大醫院擦屁股,只是要解決急診超長暫留的病人,那麼我們只會找到衛生紙,不會找到人才。就算勉強去做,也是撐不久,一定會重蹈覆轍而失敗收場。所以是否我們反向思考,把這個病房當作試驗病房,採用全新的方法來試試看?因為重複過去失敗的方法不會成功的。」我說的新方法新制度,就是Hospitalist system(駐院科醫師制度)。
開啟Hospitalist的契機
我第一次讀到Hospitalist這個字是在《台灣醫界》雜誌,一篇介紹美國Hospitalist的文章。後來我去敏盛醫院當急重症醫療顧問時,敏盛的小老闆楊弘仁(臺大低我九屆的學弟)說:我有一個「十年百大」的夢想,要在十年內建立一百家醫院。當然所謂建立一百家醫院,不是從打地基開始蓋醫院,而是接管一百家醫院的經營權,就像目前看到的麥當勞、統一超商這些連鎖加盟店一樣,大家用同樣的標誌、操作流程等等。醫院和科部的關係則像是百貨公司和專櫃的關係,醫院大一些,裡面的專櫃就多一些,但這也不一定,因為同一專櫃在該百貨公司所占的面積,也可有不同。不過為了管理方便,專櫃的種類不宜太多。
同樣的道理,最理想情形是三○○─五○○床的醫院,裡面只有幾個科部,包括一個涵蓋該地區的糖尿病照護網,兩個CV中心(Cerebrovascular 腦血管,Cardiovascular 心血管),因為這兩類疾病的治療,需要很多加護病房床位,因有大量的加護病房床位,所以兼做外傷和各種內科急症。
就台灣十大死因之統計,雖然癌症占死亡人數的第一名(二十八%),但是我們計畫中的醫院,雖然裡面的科部(專櫃)只處理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糖尿病、肺炎、事故傷害等五個主要疾病,它們卻占全部死亡人數的三四.四%,還多於癌症。況且癌症只是一個泛稱,從腦癌、大腸癌到皮膚癌,根本跨過好幾個科部,也就是一家癌症醫院,事實上所有的科部都需要,根本就是綜合醫院。反之,我們設定的醫院就組織而言所需的科部包括神經內外科、心臟內外科、急診、一般內科就夠了,相對單純很多。
就運作而言,一家醫院只須分成三個部門:門診部(包括門診、急診)、住院部(包括一般病房、加護病房)、手術部(凡是需要醫師個人技術的都包括在內,包括手術、心導管、內視鏡……等)。而其中負責住院病人照顧的就是住院部的Hospitalist。如果我們可以接受加護病房有專責醫師,為何不能接受普通病房有專責醫師?傳統上,一位醫師要兼顧門診、手術及住院病人照護,不如予以分工使其各自專精。若能整合良好,效率及結果當可更加改善。不過後來我因擔任臺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不再去敏盛醫院兼任,這個計劃始終未實際試驗。此時要開辦急診後送病房,我就想到這個制度或可試用。
從5C病房開始
二○○九年十月,急診後送病房在5C病房開始,三名主治醫師,六名專科護理師,加上一些研究助理就上線了。病人全部來自急診,依照暫留時間最久的依序住院。
一開始的5C病人有兩個特色:
一、 非癌症安寧病人。癌症的安寧病人會住家醫科的安寧病房,但非癌症的安寧病人則主要住本病房。
二、 多重疾病。一個病人有很多科可以收住院,反而不易被收住院,而多住到本病房。
5C病房則有以下特色:
一、「新」:
這個病房一切都新,主持人的我已經二十年沒在普通病房工作過,主治醫師是新的,護理長也是新的,護理師一半是當年畢業的,一半是其他病房調來拼湊而成的,專科護理師訓練一個月就匆忙上線。但也因為全是新人,沒有歷史包袱,推行新制度反而容易。一開始我就戲稱它是「深圳病房」,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是「深圳」,而台灣醫界改革創新的起點就在「5C病房」。
我們高度使用電子科技,揚棄以前的病房白板、醫師值班表、護理師值班表及到處張貼的公告,改用一個網路電子螢幕來取代。
我們在病房裡設立一個門診,出院病人一個月內有任何問題可以打熱線電話來諮詢,若有需要,直接回到病房門診,由主治醫師診治。這個設計縮短了住院日,因為病人比較有自信心提早出院,因為有問題,可電話詢問,必要時,每日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都可回到病房門診尋求醫療;這個設計也減少了三十日內再入院比率,因為有問題可立刻處理,不會因延誤而使病情惡化到需要再次住院。甚至因為有需要才回病房門診就醫,所以也減少了出院的門診追蹤次數。
我們減少上班日和非上班日的人力差別,一般病房在上班日和非上班日醫師人力相差很多,我們只略微減少,所以非上班日的入出院作業幾乎不受影響,也大幅提升了病床周轉率。以前我的老師朱樹勳常開玩笑的說:「臺大醫院上班時間是國家醫院,下班時間就變成地區醫院」。我們雖然無法做到全年一致,但是必要的檢查和治療,差不多不受假日影響,當然同仁在非上班日工作的比例就比其他單位高很多了。
照護品質一致是我們非常強調的,所以不允許有所謂個別主治醫師專有的處方,所有的檢查治療均予以標準模式化(俗稱罐頭處方),如此效率提高,安全性也提高。因為大多變異只會增加人員的失誤。
二、 不斷的反省改進:
歐美試行良好的制度,常常移植到中國人社會就走樣而失去效用,其中之一就是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
併發症甚至死亡的病例,若能好好檢討,找出原因,予以改進,當能避免以後再發生,這是很有意義的。但是檢討要有效,必須大家開誠布公講實話,對事不對人,確實檢討才有用。如果被檢討的人抱著心理防衛機制,檢討的人或者怕得罪人而避重就輕;或者挾怨報復而無的放矢。最後大家以鄉愿的態度面對死亡及併發症討論會,行禮如儀甚至粉飾太平。若是團體之文化如此,還不如不要開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因為我們有較佳的企業文化,每週針對不預期急救和轉加護病房的病例作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只要發生了,一定追究:如果重來一遍,在系統上可作哪些改進,防止它再發生。三年下來,差不多病房作業的漏洞都補救了。我們收治臺大醫院最嚴重的病人,竟然已十五個月沒有不預期急救,過去七個月只有一個病人轉加護病房。長期不斷的反省作系統性的改進,已經建構一個病人安全的病房。
三、 以「人」為本:
從當見習醫師起,就一直被教導要看「病人」,不是看「病」。但是或許老師身教不好吧!只看到「器官」,沒看到「人」;只看到「病」,沒看到「病人」,仍然是臺灣醫界的普遍現象,醫療糾紛層出不窮也就不足為奇。
因此我們在病房公佈欄公告各個醫師的每日查房時間,讓家屬不至於因白等而浪費時間。平日沒用的隔離室,遇有二人房、三人房的病人臨終時,便把他移到隔離室,讓病人有較舒適的空間,家屬可較私密地和病人作最後的相處,也不干擾同病室其他病人。
只是一個挪床的動作,雖對病房工作人員增加一些負擔,卻能給病人、家屬留下一個感動的感激。目前醫病關係緊張,醫療糾紛已是醫療從業人員的夢靨,防衛性醫療也跟著盛行。這種互相防範、互相牽制的醫病關係,只會造成惡性循環。但在這個病房處處以病人為中心的文化下,在不知不覺之中扭轉了醫病關係緊張的現象,所以病房開辦三年以來,收治最麻煩的病人,卻幾乎沒有被投訴過。
這也增加我對人性的信心,我們對別人好,別人是否一定也對我們好?答案是不一定,但是九九.五%應該是肯定的,但我們不應為了那少數的○.五%而放棄了九九.五%,我堅信人與人之間始終是可以儘量作到「互愛、互信、互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