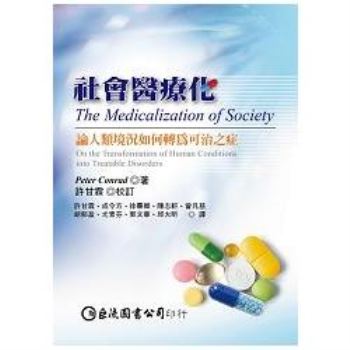第一章 醫療化:脈絡、特徵、與變化
我在1970年代開始教授醫療社會學,當時的健康與病痛(health and illness)領域,與我們在21世紀初所見有相當大的差異。當時課堂裡並未提及目前常見的疾病,以現今最盛行的疾病為例,諸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厭食症(anorexia)、慢性疲勞症候群(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CFS)、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恐慌症(panic disorder)、胎兒酒精症候群(fetal alcohol syndrome)、經前症候群(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嬰兒猝死症(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SIDS)等。當時醫療專業普遍未將肥胖和酒癮看成疾病, 也沒有提及愛滋病和諸如波斯灣戰爭症候群(Gulf War Syndrome)、多重化學物質敏感症(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y disorder)這類有爭議的病痛;利他能(Ritalin)也僅適用於相當少數的兒童, 鎮定劑普遍作為某些特定問題的處方, 人體生長激素(hGH)、威而鋼,以及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pute inhibitors, SSRIs)之類的抗憂鬱劑則尚未出現。
過去三十年間,醫學專業人員指出幾種現已看成病痛或失調(illness or disorder)而眾所周知的問題。我在本書處理幾種與某些行為、精神狀態或身體狀況相關,目前已有醫學診斷和醫療處置的病痛或「症候群」(syndromes)。顯然這類被界定為醫療問題的生命困擾
(life problems)已大量增加。這意味著出現某種新興的醫療問題?還是醫學更能及早辨識及處理既存的問題?或是整個生命中的種種困擾已取得醫學診斷,而且得透過醫學治療,即使證明這些問題醫療本質的證據依然曖昧不明?
我的興趣不在於判定任何特定問題是否真的是醫療問題,這不是我的專業領域,且已超出本書處理的範圍。我感興趣的是這種醫療管轄權限(medical jurisdiction)擴張的社會基礎,以及之所以如此發展的社會意涵。我們可以檢視人類生命困擾的醫療化脈絡,並進一步檢視其是否「真的是」醫療問題。然而,什麼是真正的醫療問題,主要的看法可能來自關注此問題的人,或是在相關領域中有權力將困擾定義成醫學問題的人。就這層意義來說,社會學工坊的素材,是命名的可行性(viability of the designation),而非診斷的效力(validity of the diagnosis)。
過去五十年來,醫學與醫學概念不斷擴張,並已造成廣泛的影響。舉兩個常見的指標來說,美國醫療保健的支出占國民生產毛額(GNP)的比例從1950年的4.5%增為2006年的16%,而醫師數從1970年的每十萬人口148位醫師增長為2003年的每十萬人口281位醫師(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2005: Exhibit 5-7)。在此期間,平均每十萬人口醫師數幾乎翻倍增長,醫療產能(medical capacity)也因此大幅增長。相同期間內,醫療管轄權限進一步擴大,將先前不認為屬於醫學領域的新困擾納入管轄範圍。
「醫療化」(medicalization)一詞描述的,是將非醫學問題透過病痛(illness)和失調(disorder)的術語,界定為醫學問題進而治療的過程。有些分析家認為「醫療管轄權限的擴展是20世紀後半葉西方最具影響力的轉型之一」(Clarke et al., 2003: 161)。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生命倫理學家及醫師等等,花了近四十年描繪醫療化的現象(Ballard and Elston, 2005)。這些分析家聚焦於醫療化的具體案例,檢視其起源、範圍,以及對社會、醫學、病患和文化的衝擊(Conrad, 1992; Bartholomew, 2000; Lock, 2001)。雖然有些分析家僅
單純檢視醫療化的發展,但大多數則對這個社會轉型抱持批判或懷疑的觀點。
本章將檢視幾個關於醫療化和社會控制的議題。重點將放在醫療化的實質性和概念性爭議,而非文獻總結。因而我並無打算提供一個全面的回顧。更完整的醫療化回顧請見我在別處的著作(Conrad,1992;2000)。
1.1 醫療化的特徵
社會學家的醫療化研究始於1960年代後期。第一波研究聚焦於「偏差行為」(deviance)的醫療化(Pitts, 1968; Conrad, 1975),但很快地,這個概念被認為可以應用在已處於醫療管轄範圍內的廣泛人類困擾問題(Freidson, 1970; Zola, 1972; Illich, 1976)。為了估計醫療
化研究著作的數目,我以「醫療化」(medicalization)為關鍵字搜尋幾個資料庫。
雖然搜尋結果僅是概略指標(見表1.1),但至少對這個主題的關注和相關著作的數目,提供一個大致概念。僅就社會學來說有數十篇醫療化的個案, 相對應的文獻可以籠統稱為「醫療化命題」(medicalization thesis)(Ballard and Elston, 2005),或甚至是「醫療化理論」(medicalization theory)(Williams and Calnan, 1996)。
表1.1 搜尋醫療化(2005/8/25, 2014/11/11)*
譯註: *原書搜尋日期為2005/8/25;2014/11/11為譯者增補。
** Newspaper Abstracts無法搜尋,以Google News替代。
醫療化也受到社會科學外其他領域的關注。《醫學文獻在線檢索》(Medline)的搜尋可以找到大量論文,而別具意義的是《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0年有一期醫療化專題,《公共科學圖書館醫學期刊》(PLoS Medicine)在2006年也有一期大幅討論
「販賣疾病」(disease mongering)。2003年美國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有一整個場次檢視醫療化(Kass etal., 2003)。新聞報導較少關注醫療化,但過去幾年來熱門新聞中提到醫療化的總數增加了。比如說,2005年《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分五集刊行題為〈突然病了〉(Suddenly Sick)的系列報導,聚焦於病痛分類的提倡和醫療化(Kelleher and Wilson, 2005)。顯然,對醫療化的興趣和研究隨著醫療化本身的增加而成長。
醫療化的關鍵是定義(definition)。亦即,以醫學詞彙來定義、使用醫學措辭來描述、採用醫學架構來理解,或用醫療介入來「處置」某種困擾問題。雖然包括作者自己在內的多數作者都對醫療化抱持批判立場,但重要的是切記:醫療化描述的是某種過程。因此我們可以檢視癲癇的醫療化,而多數人都會同意這「真的」是種醫學失調;同樣我們也可以檢視酒癮、愛滋病、停經、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或勃起功能障礙的醫療化。雖然「將⋯⋯醫療化」(medicalize)就字面意義來說是「使⋯⋯變成醫療的」(to make medical),在分析上側重於過度醫療化(overmedicalization)及其種種後果,但過度醫療化的預設並非醫療化視角的既有元素。考察醫療化的重點在於:被看作是病痛或疾病的某種實體(entity)就事實而言(ipso facto)不是醫療問題,或者應該說,它是因為需要而被界定為醫療問題。雖然醫療專業對於身體或大部分精神相關疾病,有優先發言的權力(Zola, 1972),但對多數生命困擾的醫療化案例來說,某些行動者的積極介入則是必要的(Conrad, 1992; Conrad and Schneider, 1992)。
許多早期的研究都認為醫師是理解醫療化的關鍵。Illich(1976)使用了一個吸睛但誤導的措辭─「醫學帝國主義」(medi c a limperialism)。然而,很快便釐清的是,醫療化的複雜性,甚於醫師和醫療專業對新生命困擾的納編。以酒癮為例,醫療化主要是由某個社會運動所達成(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而醫師對於酒癮作為疾病的觀點來說,實際上是後進的採納者(Conrad and Schneider, 1992)。時至今日,醫療專業或個別醫師可能僅是最低限度涉入酒癮的管理, 而實際的醫療處置對醫療化來說並非必需的(Conrad, 1992; Appleton, 1995)。
雖然醫療化主要伴隨偏差或「正常生命事件」發生,卻已在我們社會裡闢出一條寬闊地帶,將廣泛的人類生命領域包圍起來。偏差的醫療化中,比較有名的例子包括酒癮、精神病、鴉片成癮、飲食障礙、性/別差異(sex and gender difference)、性功能障礙、學習障
礙, 以及兒童虐待和性虐待。醫療化也產生大量的新分類(c a t egor i e s),從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到經前症候群(PMS)、創傷後壓力症(PTSD),以至於慢性疲勞症候群(CFS)等。曾經被界定為不道德、有罪或是犯罪的行為,如今已被賦予醫學意義,行為的意涵從壞(badness)轉變成生病(sickness)。有些尋常的生命歷程也醫療化了,包括焦慮和心情、月經、生育控制、不孕、分娩、停經、老化及死亡。醫學分類的增加意味著醫療化的增長(見第六章),但這種增長不完全是醫學殖民(medical colonization)或衛道精神(moralentrepreneurship)的後果。Arthur Barsky與Jonathan Boros指出,公眾對輕微症狀的容忍度降低,促成一種「身體不適的漸進醫療化,不舒服的身體狀態和原先獨立的癥候重新歸類為疾病」(1995: 1931)。社會運動、病患團體和個別病患向來也是醫療化的重要倡議者(Broom and Woodward, 1996),而近年來像製藥公司這類企業和身為消費者的潛在病患,在醫療化當中也開始扮演更顯著的角色。醫療化不須是全面的(total),因而可以有不同程度的醫療化。有些案例中的症狀可能並未以醫療方式處理,可能是因存在相競的定義,或是先前定義的殘餘模糊了圖像。有些諸如死亡、分娩和嚴重精神病之類的症狀,幾乎完全醫療化,但其他像鴉片成癮和停經之類的則沒有那麼完全。而像性成癮或配偶虐待,則以最低限度的醫療介入。雖然我們無法明確瞭解哪些因素普遍影響醫療化的程度,但醫療專業的支持、新病因的發現、治療的可得性和獲利、醫療保險是否給付,以及倡議或挑戰醫學定義之個人或團體的存在,在特定案例中似乎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還有對醫療化的約制,包括相競的醫學定義、醫療照護成本、缺少醫療專業的支持、限制保險給付範圍等等。醫學分類可以在朝向完全醫療化或遠離完全醫療化的連續線上移動。
醫學分類也可以擴展或限縮。醫療化程度的向度之一,便是醫學分類的伸縮性(elasticity)。「相較之下,有些醫學分類嚴格而慎重,有些則能擴展而納入許多其他問題」(Conrad, 1992: 221)。比如說,阿茲海默症(Alzheimer disease, AD)曾經是定義模糊的疾患,但若是將「年齡」這個判準移除(Fox, 1989),它與老年失智症(seniledementia)之間便不再有分別。阿茲海默症改變定義後,納入60歲以上老年失智症,結果病例數顯著增加,讓阿茲海默症成為美國前五大死因之一(參見Bond, 1992)。這種由於診斷擴展而來的醫療化,將於第三章檢視。
醫療化是雙向的, 亦即同時存在醫療化及「去醫療化」(demedicalization),但醫療管轄權限的擴展是上個世紀的潮流。去醫療化的認定在於該問題必須不再以醫學詞彙來定義,醫療手段也不再被看成恰當的介入方式。自慰(masturbation)是個經典的例子,19
世紀時被視為是且適於醫學介入(Engelhardt, 1974),但到了20世紀中期時則不再視為需要醫學介入。身心障礙的去醫療化脈絡則有點不同:身心障礙運動(disability movement)倡議去醫療化,並以近用(access)和公民權重新框構這個問題而取得部分成功(Oliver1996)。
去醫療化最顯著的例子是1970年代正式去醫療化的同性戀,我在第五章將檢視其重新醫療化的可能。相反地,分娩在近幾年歷經了從「自然產」、產房、護理助產士,以及其他許多變化的劇烈轉型,卻未曾去醫療化。分娩依然被界定為醫療事件,醫療人員仍全程參與。助產士協助的居家分娩在定義上接近去醫療化,但仍少見。總的來說,至今能夠用來檢視去醫療化的案例很少。
醫療化的評論者一向關注醫療化將日常生活各面向轉為病態,而窄化了原先被認為可接受的範圍。醫療化也將問題根源聚焦於個人而非社會環境,因此要求對個體的醫療介入,而不是更多集體的或社會的解決方案。此外,藉著擴展醫療管轄權限,醫療化增加了對人類行為的醫療社會控制(medical social control)程度。早期的評論者警告,醫療社會控制將可能取代其他形式的社會控制(Pitts, 1968; Zola, 1972),這種情況雖然尚未發生,但仍可以說醫療社會控制正持續擴張。儘管有關醫療社會控制的定義很多,我還是主張「最大的社會控制權力,來自於擁有界定特定行為、人和事物的權威」(Conrad and Schneider, 1992: 8)。因此,總的來說,主要爭議還是與定義有關,亦即讓一套(醫學)定義在精神和實務上落實的權力。更多新近的評論者強調醫療化如何增加藥廠和生技公司的獲利和市場(Moynihan and Cassels, 2005)。這些趨勢會在後面的章節討論。而醫療化的社會影響,則在第八章有更完整的討論。
我在1970年代開始教授醫療社會學,當時的健康與病痛(health and illness)領域,與我們在21世紀初所見有相當大的差異。當時課堂裡並未提及目前常見的疾病,以現今最盛行的疾病為例,諸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厭食症(anorexia)、慢性疲勞症候群(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CFS)、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恐慌症(panic disorder)、胎兒酒精症候群(fetal alcohol syndrome)、經前症候群(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嬰兒猝死症(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SIDS)等。當時醫療專業普遍未將肥胖和酒癮看成疾病, 也沒有提及愛滋病和諸如波斯灣戰爭症候群(Gulf War Syndrome)、多重化學物質敏感症(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y disorder)這類有爭議的病痛;利他能(Ritalin)也僅適用於相當少數的兒童, 鎮定劑普遍作為某些特定問題的處方, 人體生長激素(hGH)、威而鋼,以及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pute inhibitors, SSRIs)之類的抗憂鬱劑則尚未出現。
過去三十年間,醫學專業人員指出幾種現已看成病痛或失調(illness or disorder)而眾所周知的問題。我在本書處理幾種與某些行為、精神狀態或身體狀況相關,目前已有醫學診斷和醫療處置的病痛或「症候群」(syndromes)。顯然這類被界定為醫療問題的生命困擾
(life problems)已大量增加。這意味著出現某種新興的醫療問題?還是醫學更能及早辨識及處理既存的問題?或是整個生命中的種種困擾已取得醫學診斷,而且得透過醫學治療,即使證明這些問題醫療本質的證據依然曖昧不明?
我的興趣不在於判定任何特定問題是否真的是醫療問題,這不是我的專業領域,且已超出本書處理的範圍。我感興趣的是這種醫療管轄權限(medical jurisdiction)擴張的社會基礎,以及之所以如此發展的社會意涵。我們可以檢視人類生命困擾的醫療化脈絡,並進一步檢視其是否「真的是」醫療問題。然而,什麼是真正的醫療問題,主要的看法可能來自關注此問題的人,或是在相關領域中有權力將困擾定義成醫學問題的人。就這層意義來說,社會學工坊的素材,是命名的可行性(viability of the designation),而非診斷的效力(validity of the diagnosis)。
過去五十年來,醫學與醫學概念不斷擴張,並已造成廣泛的影響。舉兩個常見的指標來說,美國醫療保健的支出占國民生產毛額(GNP)的比例從1950年的4.5%增為2006年的16%,而醫師數從1970年的每十萬人口148位醫師增長為2003年的每十萬人口281位醫師(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2005: Exhibit 5-7)。在此期間,平均每十萬人口醫師數幾乎翻倍增長,醫療產能(medical capacity)也因此大幅增長。相同期間內,醫療管轄權限進一步擴大,將先前不認為屬於醫學領域的新困擾納入管轄範圍。
「醫療化」(medicalization)一詞描述的,是將非醫學問題透過病痛(illness)和失調(disorder)的術語,界定為醫學問題進而治療的過程。有些分析家認為「醫療管轄權限的擴展是20世紀後半葉西方最具影響力的轉型之一」(Clarke et al., 2003: 161)。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生命倫理學家及醫師等等,花了近四十年描繪醫療化的現象(Ballard and Elston, 2005)。這些分析家聚焦於醫療化的具體案例,檢視其起源、範圍,以及對社會、醫學、病患和文化的衝擊(Conrad, 1992; Bartholomew, 2000; Lock, 2001)。雖然有些分析家僅
單純檢視醫療化的發展,但大多數則對這個社會轉型抱持批判或懷疑的觀點。
本章將檢視幾個關於醫療化和社會控制的議題。重點將放在醫療化的實質性和概念性爭議,而非文獻總結。因而我並無打算提供一個全面的回顧。更完整的醫療化回顧請見我在別處的著作(Conrad,1992;2000)。
1.1 醫療化的特徵
社會學家的醫療化研究始於1960年代後期。第一波研究聚焦於「偏差行為」(deviance)的醫療化(Pitts, 1968; Conrad, 1975),但很快地,這個概念被認為可以應用在已處於醫療管轄範圍內的廣泛人類困擾問題(Freidson, 1970; Zola, 1972; Illich, 1976)。為了估計醫療
化研究著作的數目,我以「醫療化」(medicalization)為關鍵字搜尋幾個資料庫。
雖然搜尋結果僅是概略指標(見表1.1),但至少對這個主題的關注和相關著作的數目,提供一個大致概念。僅就社會學來說有數十篇醫療化的個案, 相對應的文獻可以籠統稱為「醫療化命題」(medicalization thesis)(Ballard and Elston, 2005),或甚至是「醫療化理論」(medicalization theory)(Williams and Calnan, 1996)。
表1.1 搜尋醫療化(2005/8/25, 2014/11/11)*
譯註: *原書搜尋日期為2005/8/25;2014/11/11為譯者增補。
** Newspaper Abstracts無法搜尋,以Google News替代。
醫療化也受到社會科學外其他領域的關注。《醫學文獻在線檢索》(Medline)的搜尋可以找到大量論文,而別具意義的是《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0年有一期醫療化專題,《公共科學圖書館醫學期刊》(PLoS Medicine)在2006年也有一期大幅討論
「販賣疾病」(disease mongering)。2003年美國總統生命倫理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有一整個場次檢視醫療化(Kass etal., 2003)。新聞報導較少關注醫療化,但過去幾年來熱門新聞中提到醫療化的總數增加了。比如說,2005年《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分五集刊行題為〈突然病了〉(Suddenly Sick)的系列報導,聚焦於病痛分類的提倡和醫療化(Kelleher and Wilson, 2005)。顯然,對醫療化的興趣和研究隨著醫療化本身的增加而成長。
醫療化的關鍵是定義(definition)。亦即,以醫學詞彙來定義、使用醫學措辭來描述、採用醫學架構來理解,或用醫療介入來「處置」某種困擾問題。雖然包括作者自己在內的多數作者都對醫療化抱持批判立場,但重要的是切記:醫療化描述的是某種過程。因此我們可以檢視癲癇的醫療化,而多數人都會同意這「真的」是種醫學失調;同樣我們也可以檢視酒癮、愛滋病、停經、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或勃起功能障礙的醫療化。雖然「將⋯⋯醫療化」(medicalize)就字面意義來說是「使⋯⋯變成醫療的」(to make medical),在分析上側重於過度醫療化(overmedicalization)及其種種後果,但過度醫療化的預設並非醫療化視角的既有元素。考察醫療化的重點在於:被看作是病痛或疾病的某種實體(entity)就事實而言(ipso facto)不是醫療問題,或者應該說,它是因為需要而被界定為醫療問題。雖然醫療專業對於身體或大部分精神相關疾病,有優先發言的權力(Zola, 1972),但對多數生命困擾的醫療化案例來說,某些行動者的積極介入則是必要的(Conrad, 1992; Conrad and Schneider, 1992)。
許多早期的研究都認為醫師是理解醫療化的關鍵。Illich(1976)使用了一個吸睛但誤導的措辭─「醫學帝國主義」(medi c a limperialism)。然而,很快便釐清的是,醫療化的複雜性,甚於醫師和醫療專業對新生命困擾的納編。以酒癮為例,醫療化主要是由某個社會運動所達成(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而醫師對於酒癮作為疾病的觀點來說,實際上是後進的採納者(Conrad and Schneider, 1992)。時至今日,醫療專業或個別醫師可能僅是最低限度涉入酒癮的管理, 而實際的醫療處置對醫療化來說並非必需的(Conrad, 1992; Appleton, 1995)。
雖然醫療化主要伴隨偏差或「正常生命事件」發生,卻已在我們社會裡闢出一條寬闊地帶,將廣泛的人類生命領域包圍起來。偏差的醫療化中,比較有名的例子包括酒癮、精神病、鴉片成癮、飲食障礙、性/別差異(sex and gender difference)、性功能障礙、學習障
礙, 以及兒童虐待和性虐待。醫療化也產生大量的新分類(c a t egor i e s),從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到經前症候群(PMS)、創傷後壓力症(PTSD),以至於慢性疲勞症候群(CFS)等。曾經被界定為不道德、有罪或是犯罪的行為,如今已被賦予醫學意義,行為的意涵從壞(badness)轉變成生病(sickness)。有些尋常的生命歷程也醫療化了,包括焦慮和心情、月經、生育控制、不孕、分娩、停經、老化及死亡。醫學分類的增加意味著醫療化的增長(見第六章),但這種增長不完全是醫學殖民(medical colonization)或衛道精神(moralentrepreneurship)的後果。Arthur Barsky與Jonathan Boros指出,公眾對輕微症狀的容忍度降低,促成一種「身體不適的漸進醫療化,不舒服的身體狀態和原先獨立的癥候重新歸類為疾病」(1995: 1931)。社會運動、病患團體和個別病患向來也是醫療化的重要倡議者(Broom and Woodward, 1996),而近年來像製藥公司這類企業和身為消費者的潛在病患,在醫療化當中也開始扮演更顯著的角色。醫療化不須是全面的(total),因而可以有不同程度的醫療化。有些案例中的症狀可能並未以醫療方式處理,可能是因存在相競的定義,或是先前定義的殘餘模糊了圖像。有些諸如死亡、分娩和嚴重精神病之類的症狀,幾乎完全醫療化,但其他像鴉片成癮和停經之類的則沒有那麼完全。而像性成癮或配偶虐待,則以最低限度的醫療介入。雖然我們無法明確瞭解哪些因素普遍影響醫療化的程度,但醫療專業的支持、新病因的發現、治療的可得性和獲利、醫療保險是否給付,以及倡議或挑戰醫學定義之個人或團體的存在,在特定案例中似乎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還有對醫療化的約制,包括相競的醫學定義、醫療照護成本、缺少醫療專業的支持、限制保險給付範圍等等。醫學分類可以在朝向完全醫療化或遠離完全醫療化的連續線上移動。
醫學分類也可以擴展或限縮。醫療化程度的向度之一,便是醫學分類的伸縮性(elasticity)。「相較之下,有些醫學分類嚴格而慎重,有些則能擴展而納入許多其他問題」(Conrad, 1992: 221)。比如說,阿茲海默症(Alzheimer disease, AD)曾經是定義模糊的疾患,但若是將「年齡」這個判準移除(Fox, 1989),它與老年失智症(seniledementia)之間便不再有分別。阿茲海默症改變定義後,納入60歲以上老年失智症,結果病例數顯著增加,讓阿茲海默症成為美國前五大死因之一(參見Bond, 1992)。這種由於診斷擴展而來的醫療化,將於第三章檢視。
醫療化是雙向的, 亦即同時存在醫療化及「去醫療化」(demedicalization),但醫療管轄權限的擴展是上個世紀的潮流。去醫療化的認定在於該問題必須不再以醫學詞彙來定義,醫療手段也不再被看成恰當的介入方式。自慰(masturbation)是個經典的例子,19
世紀時被視為是且適於醫學介入(Engelhardt, 1974),但到了20世紀中期時則不再視為需要醫學介入。身心障礙的去醫療化脈絡則有點不同:身心障礙運動(disability movement)倡議去醫療化,並以近用(access)和公民權重新框構這個問題而取得部分成功(Oliver1996)。
去醫療化最顯著的例子是1970年代正式去醫療化的同性戀,我在第五章將檢視其重新醫療化的可能。相反地,分娩在近幾年歷經了從「自然產」、產房、護理助產士,以及其他許多變化的劇烈轉型,卻未曾去醫療化。分娩依然被界定為醫療事件,醫療人員仍全程參與。助產士協助的居家分娩在定義上接近去醫療化,但仍少見。總的來說,至今能夠用來檢視去醫療化的案例很少。
醫療化的評論者一向關注醫療化將日常生活各面向轉為病態,而窄化了原先被認為可接受的範圍。醫療化也將問題根源聚焦於個人而非社會環境,因此要求對個體的醫療介入,而不是更多集體的或社會的解決方案。此外,藉著擴展醫療管轄權限,醫療化增加了對人類行為的醫療社會控制(medical social control)程度。早期的評論者警告,醫療社會控制將可能取代其他形式的社會控制(Pitts, 1968; Zola, 1972),這種情況雖然尚未發生,但仍可以說醫療社會控制正持續擴張。儘管有關醫療社會控制的定義很多,我還是主張「最大的社會控制權力,來自於擁有界定特定行為、人和事物的權威」(Conrad and Schneider, 1992: 8)。因此,總的來說,主要爭議還是與定義有關,亦即讓一套(醫學)定義在精神和實務上落實的權力。更多新近的評論者強調醫療化如何增加藥廠和生技公司的獲利和市場(Moynihan and Cassels, 2005)。這些趨勢會在後面的章節討論。而醫療化的社會影響,則在第八章有更完整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