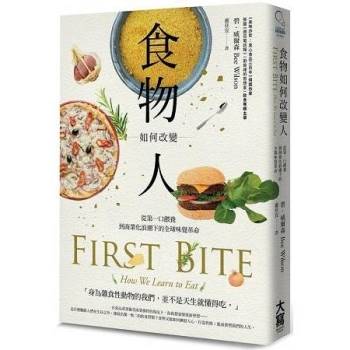第一章 喜歡和不喜歡的食物(節錄)
味覺遲鈍者易受到「飲食環境」影響
你所偏好的口味,影響你的飲食是否健康其中最重要的事,並非在你是否帶有厭惡球芽甘藍的基因;而是你所遺傳的口味傾向,與身處的食物環境之間的互動情況。一旦將食物環境納入考量,在現今充滿垃圾食物的環境下,成為味覺遲鈍者比成為味覺靈敏者,反而會引起更大的健康風險。目前已有幾項研究發現,味覺遲鈍的成年人和小孩容易擁有較高的身體質量指數(BMI)。這個理論認為味覺遲鈍者因為沒有嘗過強度一致的某些味道,因此不論食物的好或壞,更容易受到周遭環境的影響。他們比味覺靈敏者更容易知道自己喜歡的食物。在一個有益健康的食物環境裡,他們比較容易養成口味清淡的健康飲食。在提供蔬菜時,味覺遲鈍者較不會像味覺靈敏者因為味道太苦而摒棄不吃。不過,若是他們學會愛上錯誤的食物,這些味覺遲鈍者會發現他們自己就像紐約市的小孩那樣──六歲之前就過度肥胖。
所以,不、你不能單憑基因上的缺陷,就責怪自己不喜歡球芽甘藍。如果每個人第一小口所嘗到的球芽甘藍,是知名主廚奧托倫吉用自己所種植的球芽甘藍,撒上爆香的大蒜和檸檬皮,在熱煱裡快炒,直到菜葉的邊緣出現微微的焦黃;也許這會在所有蔬菜料理中,成為最受歡迎的一道菜。也許你的父母都很厭惡球芽甘藍,而且無意使你也討厭這種青菜,或者可能太強烈地強迫你吃下它。我知道某個具有PROP嘗味能力的超級味覺者,就曾發生這樣的事:有人說他可能永遠不能享受球芽甘藍的滋味,儘管他沒有挑剔不吃綠花椰菜,因為某年的聖誕節,當他被父母強迫將他最討厭的球芽甘藍切成四段,然後沒有咀嚼就吞下肚,這感覺就像吞下很苦的藥丸。也許,你實際上從未嘗過球芽甘藍,因為你「知道」你不會喜歡這種青菜,而且在我們的生活中,喜歡這種青菜的小孩是被認為有點奇怪的。當美食作家米歇爾.休姆斯(Michele Humes)從香港回到美國的時候,他花了一段時間才讓自己接受「孩子不應該喜歡蔬菜」的觀念。我們喜歡和不喜歡的食物與分子、基因無關。當報紙的頭條新聞出現像是「揭發真相:肥胖基因」的標題時,對於關注醫療健康版面熱門話題的人來說,這是一件壞消息。但對於我們其他人來說,它‧可能是一則‧很棒的‧消息。這意味著我們的飲食習慣並不是最終固定的版本,而是開放且可修改的;只要我們願意給自己一點機會。我們並不是生來就討厭有苦味的綠色蔬菜;我們其實是被環境影響而不喜歡這些蔬菜。喜愛的口味可能會一致,但不是完全絕對的,這是我們對不喜歡蔬菜但喜歡垃圾食物的孩子們的期望(不可否認地,就目前來看很渺茫),不過環境是可以改變的,儘管我們無法擺脫基因的問題。
我們學習「喜歡上食物」的主要方法很簡單,就是試著去品嘗它們。「單純曝光」(mere exposure)這個術語是在一九六八年由心理學家羅伯特.札永克(Robert Zajonc)所發明創造。札永克的論點是我們對人事物的偏好是受到熟悉程度的影響;相反的,恐懼則是出自於新的人事物。札永克早期所做的一些實驗包括在實驗對象的面前,以非常短的時間顯示各種複雜的形狀。稍後當實驗對象被要求從一排顯示過的形狀中,挑出自己最喜歡的形狀時,他們所偏愛的是已經看過數次的形狀。札永克表示,就算我們喜歡布利(Brie)乳酪勝於卡門貝爾(Camembert)乳酪,也有類似的力量在起作用;這種對食物的渴望表示先前嘗過的經驗發揮了作用。我們也許喜歡一種或其他更多的乳酪,但不見得能說出它們的差別。後來,札永克觀察到這個「單純曝光」效應,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身上都能起作用。
我們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我們也喜歡自己所知道的,這是大家都懂的事。如果你問年幼的孩童,他們最討厭的食物是什麼,答案往往會是他們從未真正嘗過的東西,通常是蔬菜。但你換角度想想,對一個成年人來說,這聽起來怪不怪?──你可能不知道你所討厭東西的味道。「快去嘗嘗看──你可能會喜歡它!」我發現在餐桌上這樣的鼓勵、催促,對我自己無效。但對一個小孩來說,說出「我不喜歡它──我從來沒吃過它!」卻沒有什麼好矛盾的。由羅素.霍班(Russel Hoban)所創作的童書《弗朗西絲的麵包與果醬》(Bread and Jam for Frances),故事內容即是關於這種兩難的情況。故事的主角弗朗西絲(一隻年輕的獾)除了麵包及果醬,不想吃任何食物。牠的父親問說:「如果你甚至連嘗都不嘗,你怎麼知道自己會喜歡吃些什麼?」最後,牠的父母只好讓步,只給牠麵包和果醬。牠很開心,但是一段時間過去,當家人正在吃東西時,牠總是被排除在外,這令牠十分傷心,而且牠渴望吃各種不同的食物。有一天傍晚,弗朗西絲流著眼淚向父母懇求一些義大利麵和肉丸子。牠的父母露出驚訝的表情,因為牠們不認為牠會喜歡義大利麵。因此牠回答說:「如果你甚至連嘗都不讓我嘗嘗看,你怎麼知道我會喜歡吃些什麼?」
如果「喜歡」是熟悉程度高所導致的結果,套用這個邏輯,起先孩子喜歡吃的食物範疇一定比成年人少;因為他們還沒嘗過許多不同種類的食物。當父母將這個暫時性的警惕解讀為永久性時,將會產生問題,而這是很容易犯的錯誤。食物偏好養成的關鍵期,是在學走路的幼兒期間:即從一歲到三歲。但是這段期間恰巧是孩子成長階段中最令人抓狂,且故意不願嘗試新事物的時候。所有孩子「都」得到了恐新症(對新鮮的事物有恐懼感),其中只是程度多寡的差別;孩子們害怕新的食物,通常是新的蔬菜,但對蛋白質食物,如魚和肉,孩子們也會感到恐懼。這種症狀在兩歲至六歲期間達到高峰。它可能是從我們的老祖先在野生環境中覓食,為了免受毒物侵害所演變而來的安全機制。不幸的是,現在它會導致孩子遠離他們本來必須學會喜歡上的──在身體發育期間所需的食物:蔬菜和蛋白質;而反過來投身蛋糕、白麵及甜甜圈的懷抱,以獲得安慰。
就像名稱所暗示的,恐新症並非只是食物吃起來不喜歡、不順口的感受:它是在要品嘗東西(或嘗試新事物)時,莫名從內心油然而生的恐懼感。在許多情況下,恐新症可以簡單地透過餵食孩子食物數次(通常最多十五次),直到他們意識到「自己並沒有遭受到任何不利的後果」才被克服。看吧!吃蕃茄不會有什麼事!你看,你還是好好的啊!漸漸地,厭惡感就會減輕,直到有一天情況整個大翻轉,幾乎很奇妙地變得熱愛上它。對於每樣新食物,就得反覆不斷地這麼做(餵食);喜歡哈密瓜的孩子,並不能保證他們也會喜歡西瓜。要在孩子身上施展「單純曝光」效應的最大問題點,在於剛開始時,必須說服他們試著去品嘗那樣食物。讓孩子試著去吃綠花椰菜幾次談何容易?說比做還簡單!任何曾試著去餵食頑固又倔強幼童的父母都知道:最善意的策略往往事與願違。典型的「把青菜吃完,你就可以吃糖果」這個作法很危險,因為這會使孩子更不喜歡那樣蔬菜。心理學家把這稱作過度酬賞效果(overjustification effect)。當完成一個活動才給予一項報酬,則會減少該活動的價值。這麼一來,孩子會更愛糖果,因為糖果已經變成獎賞的代名詞。
有鑑於恐新症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患有恐新症的孩子認為吃了陌生的食物就會對自己造成傷害,所以自己這樣堅持不吃是有助益的。因此如果讓患有此症狀的孩子親眼見證某人吃了那樣陌生的食物,仍舊安然無事,那麼他們就更能享受這項經驗。
那時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就是運用了這個方法,來讓我的女兒不對綠色蔬菜感到恐懼;我所想到的點子是把她最愛的娃娃帶到餐桌上,和我們一起共餐。在這麼做之前,我已經試了好幾個方法,但都徒勞無功。這個娃娃(一個臉髒兮兮的男寶寶)坐在餐桌前並且開始「吃著」四季豆,同時欣喜若狂地發出「哦」、「耶」的聲音(有時說:我吃了)。這感覺很蹩腳,但是有一天,我的女兒懇求我給她一些娃娃也吃的四季豆,而且從此之後就愛上它們了。另一個成功的策略是將可怕的新食物,與一個熟悉的食物做結合。當新的食物是與我們所熟悉的調味料一起端上桌時,孩子和成年人願意嘗鮮的可能將會更高,例如淋上一層蕃茄醬,進而使新食物給人足夠的安全感,而想嘗嘗看。食物心理學家約翰.普雷史考特(John Prescott)曾寫道:大量的蕃茄醬將可以促使多數孩子去嘗試一大盤自己所厭惡的食物。
大多數的孩子要一直到了六歲或七歲,才會度過嚴重恐懼新食物的階段。到了這個年齡,會被為兒童發展的正常階段。在克服恐新症後,他們可能轉而變成對新鮮事物充滿強烈的興趣:對於新口味表露出過於浮誇的喜悅,看起來很像是在炫耀。我最大的孩子(不喜歡巧克力的那個)就是表現得像這樣。他喜歡的食物反覆無常地變來變去;一開始他可能吃得很開心,但到了後來就厭倦那道菜了!他厭惡清淡的料理,抱怨著我晚餐總是煮一樣的菜,並且像男人般喜歡再加上味道濃郁的佐料。當他八歲時,我們母子兩人一起作伴去了羅馬。在一家以內臟料理聞名的餐廳裡,他從菜單中點了一道名為「羊心、羊雜拌朝鮮薊」的菜。上菜後,他也吃得津津有味。然而,就一個值得關注的未成年孩子來說,對新食物的恐懼(或者混合多樣食材的食物,還是奇怪、辛辣的食物,抑或是食材簡樸但味道不對的食物)是永遠無法被克服(接受)的。而這個總比例是高的:據估計,有多達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在飲食上患有嚴重的「恐新症」。我們常拿愛挑剔的小孩來開玩笑或者一笑置之。本章一開始提到的那個愛吃玉米片的男孩被當作家族中的異類,但不管怎樣作為一個漫畫人物,總還是勝過一個悲劇主角。
但是成年人以一個恐新症的患者在日常過活,可不是玩笑。我曾遇過男性及女性友人悄悄地向我坦承,他們沒辦法吃下任何蔬菜。其中一個女性朋友說,他覺得只有把冷凍的約克夏布丁加熱後吃下,才會感到安全;更重要的是,他酗酒的母親為他料理三餐。即使到現在,他看到蔬菜都會覺得噁心。這個朋友並不笨,他瞭解吃蔬菜是有益健康的。他曾經自己辦到(吃過青菜),但促使他有這種行為的根源已深埋在過去的記憶中。
飲食上有不少限制,除了對健康造成影響之外,也可能帶來社交上的窘境。恐新症患者要在陌生環境用餐,總是充滿了潛在的尷尬。我提到的另一個患有恐新症的女性友人,曾說過每當朋友邀她一塊在外用餐,她就不得不提前打電話到餐廳,確認餐廳在準備她的普通漢堡時,是完完全全沒有添加任何調味料的。雖然她慢慢訓練自己喜歡吃一些水果,但是還是完全不吃任何蔬菜。當我問她為什麼那麼不喜歡蔬菜?她苦笑地說:「我想大概在我三歲時,我媽受夠我那麼挑食,所以她決定讓我只吃自己喜歡的食物。」對小孩來說,很自然地除了加工肉品、洋芋片,她對其他食物別無所求。我們所偏愛的口味代表著個性中的某個面向(或者基因)──抱持這個看法會招來危險的後果。如果你認為孩子天生就有一些喜歡和不喜歡的食物(就像瞳孔的顏色固定不變),你可能不想嘗試去改變他們,因為這麼做有什麼意義?在一本二〇一三年的期刊中,有篇標題為「為什麼他們不喜歡那樣食物?遇到這種狀況,我可以做任何事嗎?」的文章,營養師訪談了六十對澳洲父母,詢問他們有關孩子食物好惡的問題。他們發現雙親有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往往會認為很少有家長能夠影響到孩子們喜好的口味,因為孩子剛生下來時很難像大人這樣,直接咀嚼、吞嚥食物。
有健康飲食習慣的孩子,其父母親則有非常不同的見解。他們談論到自家孩子喜好的口味是不可能「食古不化」的。贊成這個看法的其中一位媽媽說,這可以透過「教育」孩子們的味蕾來辦到,只要讓他們接觸到很多不同的食物就行。相較於孩子有不健康飲食習慣,或患有恐新症的父母,孩子有健康飲食習慣的雙親則抱持著更為強烈的信念,認為他們有能力去影響孩子對食物的喜好,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所付諸的行動對孩子是有影響的,這類父母總是竭盡所能去建立一個能夠讓孩子充分發展有益健康,就像是理想的「均衡飲食」的食物環境。相反的,孩子有不健康飲食習慣的父母,則認為自己無能為力。所以聽起來,他們或多或少都放棄了!
味覺遲鈍者易受到「飲食環境」影響
你所偏好的口味,影響你的飲食是否健康其中最重要的事,並非在你是否帶有厭惡球芽甘藍的基因;而是你所遺傳的口味傾向,與身處的食物環境之間的互動情況。一旦將食物環境納入考量,在現今充滿垃圾食物的環境下,成為味覺遲鈍者比成為味覺靈敏者,反而會引起更大的健康風險。目前已有幾項研究發現,味覺遲鈍的成年人和小孩容易擁有較高的身體質量指數(BMI)。這個理論認為味覺遲鈍者因為沒有嘗過強度一致的某些味道,因此不論食物的好或壞,更容易受到周遭環境的影響。他們比味覺靈敏者更容易知道自己喜歡的食物。在一個有益健康的食物環境裡,他們比較容易養成口味清淡的健康飲食。在提供蔬菜時,味覺遲鈍者較不會像味覺靈敏者因為味道太苦而摒棄不吃。不過,若是他們學會愛上錯誤的食物,這些味覺遲鈍者會發現他們自己就像紐約市的小孩那樣──六歲之前就過度肥胖。
所以,不、你不能單憑基因上的缺陷,就責怪自己不喜歡球芽甘藍。如果每個人第一小口所嘗到的球芽甘藍,是知名主廚奧托倫吉用自己所種植的球芽甘藍,撒上爆香的大蒜和檸檬皮,在熱煱裡快炒,直到菜葉的邊緣出現微微的焦黃;也許這會在所有蔬菜料理中,成為最受歡迎的一道菜。也許你的父母都很厭惡球芽甘藍,而且無意使你也討厭這種青菜,或者可能太強烈地強迫你吃下它。我知道某個具有PROP嘗味能力的超級味覺者,就曾發生這樣的事:有人說他可能永遠不能享受球芽甘藍的滋味,儘管他沒有挑剔不吃綠花椰菜,因為某年的聖誕節,當他被父母強迫將他最討厭的球芽甘藍切成四段,然後沒有咀嚼就吞下肚,這感覺就像吞下很苦的藥丸。也許,你實際上從未嘗過球芽甘藍,因為你「知道」你不會喜歡這種青菜,而且在我們的生活中,喜歡這種青菜的小孩是被認為有點奇怪的。當美食作家米歇爾.休姆斯(Michele Humes)從香港回到美國的時候,他花了一段時間才讓自己接受「孩子不應該喜歡蔬菜」的觀念。我們喜歡和不喜歡的食物與分子、基因無關。當報紙的頭條新聞出現像是「揭發真相:肥胖基因」的標題時,對於關注醫療健康版面熱門話題的人來說,這是一件壞消息。但對於我們其他人來說,它‧可能是一則‧很棒的‧消息。這意味著我們的飲食習慣並不是最終固定的版本,而是開放且可修改的;只要我們願意給自己一點機會。我們並不是生來就討厭有苦味的綠色蔬菜;我們其實是被環境影響而不喜歡這些蔬菜。喜愛的口味可能會一致,但不是完全絕對的,這是我們對不喜歡蔬菜但喜歡垃圾食物的孩子們的期望(不可否認地,就目前來看很渺茫),不過環境是可以改變的,儘管我們無法擺脫基因的問題。
我們學習「喜歡上食物」的主要方法很簡單,就是試著去品嘗它們。「單純曝光」(mere exposure)這個術語是在一九六八年由心理學家羅伯特.札永克(Robert Zajonc)所發明創造。札永克的論點是我們對人事物的偏好是受到熟悉程度的影響;相反的,恐懼則是出自於新的人事物。札永克早期所做的一些實驗包括在實驗對象的面前,以非常短的時間顯示各種複雜的形狀。稍後當實驗對象被要求從一排顯示過的形狀中,挑出自己最喜歡的形狀時,他們所偏愛的是已經看過數次的形狀。札永克表示,就算我們喜歡布利(Brie)乳酪勝於卡門貝爾(Camembert)乳酪,也有類似的力量在起作用;這種對食物的渴望表示先前嘗過的經驗發揮了作用。我們也許喜歡一種或其他更多的乳酪,但不見得能說出它們的差別。後來,札永克觀察到這個「單純曝光」效應,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身上都能起作用。
我們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我們也喜歡自己所知道的,這是大家都懂的事。如果你問年幼的孩童,他們最討厭的食物是什麼,答案往往會是他們從未真正嘗過的東西,通常是蔬菜。但你換角度想想,對一個成年人來說,這聽起來怪不怪?──你可能不知道你所討厭東西的味道。「快去嘗嘗看──你可能會喜歡它!」我發現在餐桌上這樣的鼓勵、催促,對我自己無效。但對一個小孩來說,說出「我不喜歡它──我從來沒吃過它!」卻沒有什麼好矛盾的。由羅素.霍班(Russel Hoban)所創作的童書《弗朗西絲的麵包與果醬》(Bread and Jam for Frances),故事內容即是關於這種兩難的情況。故事的主角弗朗西絲(一隻年輕的獾)除了麵包及果醬,不想吃任何食物。牠的父親問說:「如果你甚至連嘗都不嘗,你怎麼知道自己會喜歡吃些什麼?」最後,牠的父母只好讓步,只給牠麵包和果醬。牠很開心,但是一段時間過去,當家人正在吃東西時,牠總是被排除在外,這令牠十分傷心,而且牠渴望吃各種不同的食物。有一天傍晚,弗朗西絲流著眼淚向父母懇求一些義大利麵和肉丸子。牠的父母露出驚訝的表情,因為牠們不認為牠會喜歡義大利麵。因此牠回答說:「如果你甚至連嘗都不讓我嘗嘗看,你怎麼知道我會喜歡吃些什麼?」
如果「喜歡」是熟悉程度高所導致的結果,套用這個邏輯,起先孩子喜歡吃的食物範疇一定比成年人少;因為他們還沒嘗過許多不同種類的食物。當父母將這個暫時性的警惕解讀為永久性時,將會產生問題,而這是很容易犯的錯誤。食物偏好養成的關鍵期,是在學走路的幼兒期間:即從一歲到三歲。但是這段期間恰巧是孩子成長階段中最令人抓狂,且故意不願嘗試新事物的時候。所有孩子「都」得到了恐新症(對新鮮的事物有恐懼感),其中只是程度多寡的差別;孩子們害怕新的食物,通常是新的蔬菜,但對蛋白質食物,如魚和肉,孩子們也會感到恐懼。這種症狀在兩歲至六歲期間達到高峰。它可能是從我們的老祖先在野生環境中覓食,為了免受毒物侵害所演變而來的安全機制。不幸的是,現在它會導致孩子遠離他們本來必須學會喜歡上的──在身體發育期間所需的食物:蔬菜和蛋白質;而反過來投身蛋糕、白麵及甜甜圈的懷抱,以獲得安慰。
就像名稱所暗示的,恐新症並非只是食物吃起來不喜歡、不順口的感受:它是在要品嘗東西(或嘗試新事物)時,莫名從內心油然而生的恐懼感。在許多情況下,恐新症可以簡單地透過餵食孩子食物數次(通常最多十五次),直到他們意識到「自己並沒有遭受到任何不利的後果」才被克服。看吧!吃蕃茄不會有什麼事!你看,你還是好好的啊!漸漸地,厭惡感就會減輕,直到有一天情況整個大翻轉,幾乎很奇妙地變得熱愛上它。對於每樣新食物,就得反覆不斷地這麼做(餵食);喜歡哈密瓜的孩子,並不能保證他們也會喜歡西瓜。要在孩子身上施展「單純曝光」效應的最大問題點,在於剛開始時,必須說服他們試著去品嘗那樣食物。讓孩子試著去吃綠花椰菜幾次談何容易?說比做還簡單!任何曾試著去餵食頑固又倔強幼童的父母都知道:最善意的策略往往事與願違。典型的「把青菜吃完,你就可以吃糖果」這個作法很危險,因為這會使孩子更不喜歡那樣蔬菜。心理學家把這稱作過度酬賞效果(overjustification effect)。當完成一個活動才給予一項報酬,則會減少該活動的價值。這麼一來,孩子會更愛糖果,因為糖果已經變成獎賞的代名詞。
有鑑於恐新症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患有恐新症的孩子認為吃了陌生的食物就會對自己造成傷害,所以自己這樣堅持不吃是有助益的。因此如果讓患有此症狀的孩子親眼見證某人吃了那樣陌生的食物,仍舊安然無事,那麼他們就更能享受這項經驗。
那時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就是運用了這個方法,來讓我的女兒不對綠色蔬菜感到恐懼;我所想到的點子是把她最愛的娃娃帶到餐桌上,和我們一起共餐。在這麼做之前,我已經試了好幾個方法,但都徒勞無功。這個娃娃(一個臉髒兮兮的男寶寶)坐在餐桌前並且開始「吃著」四季豆,同時欣喜若狂地發出「哦」、「耶」的聲音(有時說:我吃了)。這感覺很蹩腳,但是有一天,我的女兒懇求我給她一些娃娃也吃的四季豆,而且從此之後就愛上它們了。另一個成功的策略是將可怕的新食物,與一個熟悉的食物做結合。當新的食物是與我們所熟悉的調味料一起端上桌時,孩子和成年人願意嘗鮮的可能將會更高,例如淋上一層蕃茄醬,進而使新食物給人足夠的安全感,而想嘗嘗看。食物心理學家約翰.普雷史考特(John Prescott)曾寫道:大量的蕃茄醬將可以促使多數孩子去嘗試一大盤自己所厭惡的食物。
大多數的孩子要一直到了六歲或七歲,才會度過嚴重恐懼新食物的階段。到了這個年齡,會被為兒童發展的正常階段。在克服恐新症後,他們可能轉而變成對新鮮事物充滿強烈的興趣:對於新口味表露出過於浮誇的喜悅,看起來很像是在炫耀。我最大的孩子(不喜歡巧克力的那個)就是表現得像這樣。他喜歡的食物反覆無常地變來變去;一開始他可能吃得很開心,但到了後來就厭倦那道菜了!他厭惡清淡的料理,抱怨著我晚餐總是煮一樣的菜,並且像男人般喜歡再加上味道濃郁的佐料。當他八歲時,我們母子兩人一起作伴去了羅馬。在一家以內臟料理聞名的餐廳裡,他從菜單中點了一道名為「羊心、羊雜拌朝鮮薊」的菜。上菜後,他也吃得津津有味。然而,就一個值得關注的未成年孩子來說,對新食物的恐懼(或者混合多樣食材的食物,還是奇怪、辛辣的食物,抑或是食材簡樸但味道不對的食物)是永遠無法被克服(接受)的。而這個總比例是高的:據估計,有多達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在飲食上患有嚴重的「恐新症」。我們常拿愛挑剔的小孩來開玩笑或者一笑置之。本章一開始提到的那個愛吃玉米片的男孩被當作家族中的異類,但不管怎樣作為一個漫畫人物,總還是勝過一個悲劇主角。
但是成年人以一個恐新症的患者在日常過活,可不是玩笑。我曾遇過男性及女性友人悄悄地向我坦承,他們沒辦法吃下任何蔬菜。其中一個女性朋友說,他覺得只有把冷凍的約克夏布丁加熱後吃下,才會感到安全;更重要的是,他酗酒的母親為他料理三餐。即使到現在,他看到蔬菜都會覺得噁心。這個朋友並不笨,他瞭解吃蔬菜是有益健康的。他曾經自己辦到(吃過青菜),但促使他有這種行為的根源已深埋在過去的記憶中。
飲食上有不少限制,除了對健康造成影響之外,也可能帶來社交上的窘境。恐新症患者要在陌生環境用餐,總是充滿了潛在的尷尬。我提到的另一個患有恐新症的女性友人,曾說過每當朋友邀她一塊在外用餐,她就不得不提前打電話到餐廳,確認餐廳在準備她的普通漢堡時,是完完全全沒有添加任何調味料的。雖然她慢慢訓練自己喜歡吃一些水果,但是還是完全不吃任何蔬菜。當我問她為什麼那麼不喜歡蔬菜?她苦笑地說:「我想大概在我三歲時,我媽受夠我那麼挑食,所以她決定讓我只吃自己喜歡的食物。」對小孩來說,很自然地除了加工肉品、洋芋片,她對其他食物別無所求。我們所偏愛的口味代表著個性中的某個面向(或者基因)──抱持這個看法會招來危險的後果。如果你認為孩子天生就有一些喜歡和不喜歡的食物(就像瞳孔的顏色固定不變),你可能不想嘗試去改變他們,因為這麼做有什麼意義?在一本二〇一三年的期刊中,有篇標題為「為什麼他們不喜歡那樣食物?遇到這種狀況,我可以做任何事嗎?」的文章,營養師訪談了六十對澳洲父母,詢問他們有關孩子食物好惡的問題。他們發現雙親有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往往會認為很少有家長能夠影響到孩子們喜好的口味,因為孩子剛生下來時很難像大人這樣,直接咀嚼、吞嚥食物。
有健康飲食習慣的孩子,其父母親則有非常不同的見解。他們談論到自家孩子喜好的口味是不可能「食古不化」的。贊成這個看法的其中一位媽媽說,這可以透過「教育」孩子們的味蕾來辦到,只要讓他們接觸到很多不同的食物就行。相較於孩子有不健康飲食習慣,或患有恐新症的父母,孩子有健康飲食習慣的雙親則抱持著更為強烈的信念,認為他們有能力去影響孩子對食物的喜好,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所付諸的行動對孩子是有影響的,這類父母總是竭盡所能去建立一個能夠讓孩子充分發展有益健康,就像是理想的「均衡飲食」的食物環境。相反的,孩子有不健康飲食習慣的父母,則認為自己無能為力。所以聽起來,他們或多或少都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