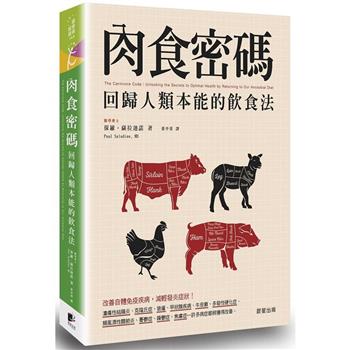第一部
第一章 人類的始源
印第安納瓊斯的考古冒險
食用動物在人類演化上約有至少 5-600 萬年的歷史,從遠古時期開始, 就已是我們人類跟早期人類(pre-humans)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我 們之前,靈長類動物已歷經 6,000 萬年左右的演化過程,而在那段時期中, 靈長類的腦基本上穩定地保持在約 350 立方公分(cc)的大小,再依據個 體體型略有出入。這項研究表示,在這 60 萬年之間,光靠吃水果跟樹葉, 並沒有為我們的靈長類先祖們帶來腦體積的成長。
一般認為,約 600 萬年前,由於構造板塊移動造成棲息環境變遷,我 們遙遠的先祖從樹上爬了下來,並進入了東北非開闊的草原—人類動物 譜系就此從黑猩猩中旁枝而出。我們譜系最古老的化石可以回溯到約 420 第一章 人類的始源 29 萬年前的北肯亞。這個族群稱作南方古猿屬(Australopithesus),其出土 化石中包含了一組女性的遺骸,由於考古過程中每晚在營區裡播放著同名 的披頭四(Beatles)歌曲,她就被暱稱為「露西(Lucy)」。露西顯然已 像人類一樣站立著行走,不過,她的腦體積僅比她的黑猩猩祖先稍微大一 點點而已。觀察露西跟其他相近時期出土的骸骨,我們得以回溯人類遠親 的大腦體積發展的進程,並見證一段有趣的故事。
我們先祖的腦體積在露西的時代之後,逐漸地成長。而在約 200 萬年 之後,一件非常驚人的事發生了:它們成長地速率突然開始激增。體積持 續增長著,並在約 40,000 年前達到 1,600cc 的頂峰。這項腦尺寸的增加也 對應到新皮質(我們腦部外層的部分)複雜度以及智慧的成長—這兩項 要素都為溝通能力和複雜的群體行為帶來進步,例如:更有組織性的打獵 行動。更大的腦也代表更聰明的人們,而更聰明的人們就能更成功地進行 團體獵捕行動。
這項腦尺寸的急遽改變引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在 200 萬年前,究竟 是發生什麼神奇的事件,讓我們的先祖們變聰明了呢?沒有人能確切知道, 但在考古學紀錄上,有兩道關鍵的線索。250 萬年前,隨著巧人(Homo Habilis)的出現,也是我們開始見到第一批石器與捕獵動物的證據。這個 時期的動物遺骸化石上,顯示了武器在骨頭上造成的傷痕,以及最早期屠 宰行為的切割痕跡。[ 註 1,2,3] 在此時間點前,像是在露西時代,也就是 400 - 500 萬年前,已有證據顯示我們的祖先們就有在食用動物,但從 200 萬年 前開始,我們似乎從拾荒者演化成為獵人的角色。
作為拾荒者,我們只能取得動物的某些部分,例如,骨髓和大腦,這 些因為被骨骼組織覆蓋,而倖免於其他動物食用的部分。[ 註 4,5] 然而,當我 們能組織團體,並用石器來獵捕動物時,我們也就突然間獲得了享有完整 獵捕物的權利。這也代表我們可以取得內臟(腹部)器官,脂肪,以及肌 肉。我相信就是食用了動物的這些部分,以及攝取了它們獨特的微量營養 素(micronutrient)以及豐沛的熱量,才得以讓我們的腦成長超越初期巧人 的增長,並且成為今日的人類。將動物從鼻到尾吃光光才讓我們成為人類!從拾荒者到獵人的轉變,顯然是我們人類演化上十分關鍵的時刻。
有些人則主張,是烹飪才使得人腦體積有所增長,但許多科學家都同 意,我們跟火炙熱的愛情故事一直要到 50 萬年之前,也就是人腦開始急速 成長的 150 萬年之後,才開始譜寫。[ 註 6]
右圖中,你可以看到我們祖先腦的尺寸在這百萬年間成長的歷程。在 大約 400 萬年前,你會看到露西跟她南方古猿支系。她的腦尺寸跟一顆小 型葡萄柚差不多大。然而,介於露西跟巧人的時代之間,人腦增長為一棵 中型大小的葡萄柚了:大概 500cc 左右。接著,在 250 萬年前,隨著石器 與獵捕行為的降臨,我們祖先的大腦開始更加快速的增大。事實上,它們 在接下來的 100 萬年間,增長為原先的兩倍大。根據化石紀錄顯示,我們 的腦尺寸在約 4 萬年前,達到最大值,也就是 1600cc,在那之後,我們的 腦微微地縮小了。這個圖表帶給我們的訊息是,我們祖先大腦尺寸增長速 率最重要的轉捩點,與石器和獵捕行為的出現相符。我們人類之所以是今 天的樣子,是因為我們食用動物。
就跟我們下一章會看到的一樣,我們飲食習慣急遽改變的時間點, 正好與我們大腦逐漸萎縮的時間點相對應。那就是我們開始少吃動物,並 多吃植物的時期。很顯然,食用動物從一開始就在我們的演化過程扮演 重大角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研究員,凱薩琳.彌爾頓(Katherine Milton)在她的論文〈源自動物之食物在人類演化中扮演的關鍵角色〉(The Critical Role Played by Animal Source Foods in Human Evolution)中寫道: 「若非日常慣例攝取源自動物的食物,人類是極不可能在作為大型、活動力高且高度社會化的靈長類,且繼續相同演化路徑之時,同時演化出如此不尋常、巨大且複雜之腦部的。在人類演化持續進行的過程中,不論是對於巨大腦部快速擴張的年輕孩童而言,還是成年人類的高新陳代謝率以及營養需求,以上各方面都會因為肉類這種高密度、高品質的食物而受益。」[註7]
我們到底曾經吃多少肉?
我們的祖先不是同時既吃植物,也吃動物嗎?我們不是除了狩獵,也有採集嗎?問得好!當我開始挖掘人類學文獻時,我也問了自己一模一樣的問題。謝天謝地,這裡的確有一台類似「時光機」的東西,可以幫助我們來回答這像疑問。
為了判斷我們前人的飲食中,究竟有多大部分是以動物為食,我們可以在他們的骨骼化石中進行氮-15測定。衡量這種同位素的值,得以讓研究人員從蛋白質的來源中推測出動物在食物鏈中究竟處於哪個位置。草食性動物(herbivores)的氮-15值通常介於百分之3-7,肉食性動物則是介於百分之6-12,而雜食性動物的氮-15值則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當分析早期現代人類與尼安德塔人的樣本時,他們分別呈現了百分之12與13.5的氮-15值測定結果,這甚至比鬣狗和狼的測定值還要來得更高。
對於這樣的結果,我們該下什麼樣的結論呢?這些極高的氮-15同位素值測定結果暗示著,在40,000年前,智人以及同時並存的尼安德塔人都是高營養級(trophic,譯注:在食物鏈中所佔的位置)的肉食動物。他們從像是長毛象一類的大型哺乳類動物身上獲取大部分的蛋白質,而非從植物來源獲取。誰要來跟我一起享用長毛象的肋眼排呀?
同樣的模式也展現在更早期的化石紀錄上,在南方古猿屬的時期,原始人似乎演化出了兩支支系,其中一支成為了巧人,而另一支則是被稱作巴蘭猿人(Paranthropus),並在後來絕種了。
就像骨骼中的氮-15值,牙齒化石中的鍶(strontium)、鋇(barium)以及鈣(calcium)值也可以被用來推斷我們老祖宗的飲食習慣。研究比較了這些元素的比例,得到一些線索暗示:南方古猿屬混合食用植物和動物,而巧人的食物組成則是有高比例的動物食物,[註8]這個演化上的改變剛好跟歷史上大腦的急速成長互相呼應。另一方面,巴蘭猿似乎比較高度依賴植物作為食物,而這個偏好可能就是他們走下坡的原因。
人類是脂肪獵人
關於這一點的數據相當清楚,並持續地在留存下來化石的氮測定中一再被重現。而從能量效率(energy efficiency)的角度來看,狩獵大型動物較為合理。假若投入相當的能量,採集植物或是追蹤小型動物在熱量和營養方面帶來的報償較少。在最近關於原住民族的一些研究中,我們觀察到相似的模式,並清楚地看見他們也偏好動物大於植物作為食物。[註9.10]舉例來說,維爾雅墨・史岱凡松(Vilhjalmur Stefansson,譯注:南極探險家、民族學家)在他對愛斯基摩人的研究中,撰寫道: 「愛斯基摩人的狀況與我們更不同之處在於蔬菜。在麥肯錫地區(Mackenzie district,譯注:位於紐西蘭的行政區)只有三種狀況下會吃蔬菜:最主要吃蔬菜的原因,跟大部分的愛斯基摩人一樣,就是因為饑荒......」[註11]
但我們的老祖宗狩獵並非不挑對象。他們還會尋找脂肪含量最高的動物。由於體重關係,較大的動物會含有比較多的脂肪,而為了生存需要,脂肪是我們所追求最主要的巨量營養素(macronutrient)。蛋白質在動物世界中來源廣泛,但脂肪相較之下則稀少許多。
許多人類學家在研究生活型態迥異的原住民族時,都發現了他們對於對脂肪與較肥胖動物的偏好。在史貝司(Speth)的著作《大型獵物狩獵的古人類學和人類學》(The Paleoanthropology of and Archaeology of Bug Game Hunting)中,他陳述道: 「......脂肪,而非蛋白質,在獵人的決策中扮演了顯著的角色,用以決定該殺哪頭動物(公還是母),哪些部位該帶走、哪些又該留下。」[註12]
對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的龔人(!Kung,譯注:非洲南部桑人的其中一支)來說:
「肥胖的動物極受喜愛,而所有的龔人總是迫切渴求著動物脂肪。」[註13]
而就詹姆斯灣(James Bay)的克里族(Cree)來說,他則描述道: 「克里族認為脂肪是所有動物身上最重要的部分。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認為熊比其他動物更加有價值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牠們身上的體脂肪。」[註14]
而澳洲阿納姆地(Arnhem)的雍古人(Yolngu)也有類似的觀點: 「沒有脂肪的動物可能因此不被接受是食物。」[註15]
為什麼我們的祖先們和較近代的原住民族們都這麼積極地想獲得脂肪呢?最根本上來上,可能是因為熱量含量。同樣重量的脂肪,能夠提供比等量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高兩倍的熱量。此外,脂肪對人類的新陳代謝來說,是一種特別有價值且必須的食物。如果我們把自己想像成汽車的話,就會需要燃料來驅使我們的新陳代謝引擎,那麼一來,蛋白質就不會是我們想放進加油箱的燃料。為了要求最高的效能,脂肪或是碳水化合物對我們的新陳代謝引擎來說更加有效率。我們的身體會優先將蛋白質作為建構組元(building blocks)使用,而非作為能源。雖然我們可以透過糖質新生作用(gluconeogenesis),來將蛋白質轉化為能量使用,但這仍舊不太能作為我們主要的能量來源。
讓我們現在來是試想一下:我已經想到能讓時光機運作的辦法,並且跟你一起回到了過去。讓把時間設置到50,000年前,到一個智人(我們的親戚)和尼安德塔人共存的時代兜兜風吧。我希望你把你的裹腰部纏好,才不至於讓我們顯得太顯眼。我還希望你懂製作長矛的方法,因為很快地,我們的肚子就會餓了。好了,那我們現在應該要去找一些會讓你拉肚子的苦葉子來吃呢,還是要挖一些有超多纖維而且難吃得要死的植物根來吃呢?還是,要不要來狩獵一些大型獵物?牠們可以提供我們更多的能量,也可以讓我們接下來幾天,甚至幾週都有食物可以吃喔。
這是個很簡單的抉擇,而對我們的老祖宗們而言也是如此。忘掉樹葉跟超多纖維的植物根吧,我們要去狩獵啦!而一旦狩獵成功,我們就可以吃好幾天長毛象或是水牛大餐了。就如同我們在穩定同位素測定研究中看到的一樣,我們所採取的手段與老祖宗們所做的不謀而合。我很高興他們作出了明智的抉擇,且想出了解決方案,因為我認為,如果不是因為如此,人類這個物種是沒辦法生存至今的。
這本書進行到這個階段,我想要來跟你分享我的肉食密碼假說:我相信,在我們的演化過程中,我們的祖先狩獵是有優先順序的,並且只有在食物難尋或是挨餓的情況下,才會以植物作為食物。我的假說建立在以下這幾項因素上:
1. 人類學數據——包括腦尺寸,來自骨骼以及牙齒可靠的同位素測定數據,以及上述的原住民族案例。
2. 投入相同能量,從動物身上所能獲取的能量遠大於植物。
3. 動物作為食物極度優越的營養含量(我們之後會在第八章繼續談這個)
我並不是在暗指我們的祖先從來沒有食用植物,但根據動物在熱量和營養學的優越地位,他們偏愛食用動物。如果在無法取得動物作為食物的情況下,我們可能會改吃植物作為備胎選項,不過,植物似乎沒有在我們祖先的飲食中佔有任何重要地位。
花一小段時間,讓我在上一段提出的這個論點好好在你心底沈澱一下。「人類是雜食性動物」這個觀點在現在已經被視為理所當然,但這究竟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們仔細思考這一點、更深入挖掘,並拿我們自己跟其他雜食性跟肉食性動物相互比較、觀察,便能得到一些深具啟發的領悟。
第一章 人類的始源
印第安納瓊斯的考古冒險
食用動物在人類演化上約有至少 5-600 萬年的歷史,從遠古時期開始, 就已是我們人類跟早期人類(pre-humans)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我 們之前,靈長類動物已歷經 6,000 萬年左右的演化過程,而在那段時期中, 靈長類的腦基本上穩定地保持在約 350 立方公分(cc)的大小,再依據個 體體型略有出入。這項研究表示,在這 60 萬年之間,光靠吃水果跟樹葉, 並沒有為我們的靈長類先祖們帶來腦體積的成長。
一般認為,約 600 萬年前,由於構造板塊移動造成棲息環境變遷,我 們遙遠的先祖從樹上爬了下來,並進入了東北非開闊的草原—人類動物 譜系就此從黑猩猩中旁枝而出。我們譜系最古老的化石可以回溯到約 420 第一章 人類的始源 29 萬年前的北肯亞。這個族群稱作南方古猿屬(Australopithesus),其出土 化石中包含了一組女性的遺骸,由於考古過程中每晚在營區裡播放著同名 的披頭四(Beatles)歌曲,她就被暱稱為「露西(Lucy)」。露西顯然已 像人類一樣站立著行走,不過,她的腦體積僅比她的黑猩猩祖先稍微大一 點點而已。觀察露西跟其他相近時期出土的骸骨,我們得以回溯人類遠親 的大腦體積發展的進程,並見證一段有趣的故事。
我們先祖的腦體積在露西的時代之後,逐漸地成長。而在約 200 萬年 之後,一件非常驚人的事發生了:它們成長地速率突然開始激增。體積持 續增長著,並在約 40,000 年前達到 1,600cc 的頂峰。這項腦尺寸的增加也 對應到新皮質(我們腦部外層的部分)複雜度以及智慧的成長—這兩項 要素都為溝通能力和複雜的群體行為帶來進步,例如:更有組織性的打獵 行動。更大的腦也代表更聰明的人們,而更聰明的人們就能更成功地進行 團體獵捕行動。
這項腦尺寸的急遽改變引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在 200 萬年前,究竟 是發生什麼神奇的事件,讓我們的先祖們變聰明了呢?沒有人能確切知道, 但在考古學紀錄上,有兩道關鍵的線索。250 萬年前,隨著巧人(Homo Habilis)的出現,也是我們開始見到第一批石器與捕獵動物的證據。這個 時期的動物遺骸化石上,顯示了武器在骨頭上造成的傷痕,以及最早期屠 宰行為的切割痕跡。[ 註 1,2,3] 在此時間點前,像是在露西時代,也就是 400 - 500 萬年前,已有證據顯示我們的祖先們就有在食用動物,但從 200 萬年 前開始,我們似乎從拾荒者演化成為獵人的角色。
作為拾荒者,我們只能取得動物的某些部分,例如,骨髓和大腦,這 些因為被骨骼組織覆蓋,而倖免於其他動物食用的部分。[ 註 4,5] 然而,當我 們能組織團體,並用石器來獵捕動物時,我們也就突然間獲得了享有完整 獵捕物的權利。這也代表我們可以取得內臟(腹部)器官,脂肪,以及肌 肉。我相信就是食用了動物的這些部分,以及攝取了它們獨特的微量營養 素(micronutrient)以及豐沛的熱量,才得以讓我們的腦成長超越初期巧人 的增長,並且成為今日的人類。將動物從鼻到尾吃光光才讓我們成為人類!從拾荒者到獵人的轉變,顯然是我們人類演化上十分關鍵的時刻。
有些人則主張,是烹飪才使得人腦體積有所增長,但許多科學家都同 意,我們跟火炙熱的愛情故事一直要到 50 萬年之前,也就是人腦開始急速 成長的 150 萬年之後,才開始譜寫。[ 註 6]
右圖中,你可以看到我們祖先腦的尺寸在這百萬年間成長的歷程。在 大約 400 萬年前,你會看到露西跟她南方古猿支系。她的腦尺寸跟一顆小 型葡萄柚差不多大。然而,介於露西跟巧人的時代之間,人腦增長為一棵 中型大小的葡萄柚了:大概 500cc 左右。接著,在 250 萬年前,隨著石器 與獵捕行為的降臨,我們祖先的大腦開始更加快速的增大。事實上,它們 在接下來的 100 萬年間,增長為原先的兩倍大。根據化石紀錄顯示,我們 的腦尺寸在約 4 萬年前,達到最大值,也就是 1600cc,在那之後,我們的 腦微微地縮小了。這個圖表帶給我們的訊息是,我們祖先大腦尺寸增長速 率最重要的轉捩點,與石器和獵捕行為的出現相符。我們人類之所以是今 天的樣子,是因為我們食用動物。
就跟我們下一章會看到的一樣,我們飲食習慣急遽改變的時間點, 正好與我們大腦逐漸萎縮的時間點相對應。那就是我們開始少吃動物,並 多吃植物的時期。很顯然,食用動物從一開始就在我們的演化過程扮演 重大角色。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研究員,凱薩琳.彌爾頓(Katherine Milton)在她的論文〈源自動物之食物在人類演化中扮演的關鍵角色〉(The Critical Role Played by Animal Source Foods in Human Evolution)中寫道: 「若非日常慣例攝取源自動物的食物,人類是極不可能在作為大型、活動力高且高度社會化的靈長類,且繼續相同演化路徑之時,同時演化出如此不尋常、巨大且複雜之腦部的。在人類演化持續進行的過程中,不論是對於巨大腦部快速擴張的年輕孩童而言,還是成年人類的高新陳代謝率以及營養需求,以上各方面都會因為肉類這種高密度、高品質的食物而受益。」[註7]
我們到底曾經吃多少肉?
我們的祖先不是同時既吃植物,也吃動物嗎?我們不是除了狩獵,也有採集嗎?問得好!當我開始挖掘人類學文獻時,我也問了自己一模一樣的問題。謝天謝地,這裡的確有一台類似「時光機」的東西,可以幫助我們來回答這像疑問。
為了判斷我們前人的飲食中,究竟有多大部分是以動物為食,我們可以在他們的骨骼化石中進行氮-15測定。衡量這種同位素的值,得以讓研究人員從蛋白質的來源中推測出動物在食物鏈中究竟處於哪個位置。草食性動物(herbivores)的氮-15值通常介於百分之3-7,肉食性動物則是介於百分之6-12,而雜食性動物的氮-15值則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當分析早期現代人類與尼安德塔人的樣本時,他們分別呈現了百分之12與13.5的氮-15值測定結果,這甚至比鬣狗和狼的測定值還要來得更高。
對於這樣的結果,我們該下什麼樣的結論呢?這些極高的氮-15同位素值測定結果暗示著,在40,000年前,智人以及同時並存的尼安德塔人都是高營養級(trophic,譯注:在食物鏈中所佔的位置)的肉食動物。他們從像是長毛象一類的大型哺乳類動物身上獲取大部分的蛋白質,而非從植物來源獲取。誰要來跟我一起享用長毛象的肋眼排呀?
同樣的模式也展現在更早期的化石紀錄上,在南方古猿屬的時期,原始人似乎演化出了兩支支系,其中一支成為了巧人,而另一支則是被稱作巴蘭猿人(Paranthropus),並在後來絕種了。
就像骨骼中的氮-15值,牙齒化石中的鍶(strontium)、鋇(barium)以及鈣(calcium)值也可以被用來推斷我們老祖宗的飲食習慣。研究比較了這些元素的比例,得到一些線索暗示:南方古猿屬混合食用植物和動物,而巧人的食物組成則是有高比例的動物食物,[註8]這個演化上的改變剛好跟歷史上大腦的急速成長互相呼應。另一方面,巴蘭猿似乎比較高度依賴植物作為食物,而這個偏好可能就是他們走下坡的原因。
人類是脂肪獵人
關於這一點的數據相當清楚,並持續地在留存下來化石的氮測定中一再被重現。而從能量效率(energy efficiency)的角度來看,狩獵大型動物較為合理。假若投入相當的能量,採集植物或是追蹤小型動物在熱量和營養方面帶來的報償較少。在最近關於原住民族的一些研究中,我們觀察到相似的模式,並清楚地看見他們也偏好動物大於植物作為食物。[註9.10]舉例來說,維爾雅墨・史岱凡松(Vilhjalmur Stefansson,譯注:南極探險家、民族學家)在他對愛斯基摩人的研究中,撰寫道: 「愛斯基摩人的狀況與我們更不同之處在於蔬菜。在麥肯錫地區(Mackenzie district,譯注:位於紐西蘭的行政區)只有三種狀況下會吃蔬菜:最主要吃蔬菜的原因,跟大部分的愛斯基摩人一樣,就是因為饑荒......」[註11]
但我們的老祖宗狩獵並非不挑對象。他們還會尋找脂肪含量最高的動物。由於體重關係,較大的動物會含有比較多的脂肪,而為了生存需要,脂肪是我們所追求最主要的巨量營養素(macronutrient)。蛋白質在動物世界中來源廣泛,但脂肪相較之下則稀少許多。
許多人類學家在研究生活型態迥異的原住民族時,都發現了他們對於對脂肪與較肥胖動物的偏好。在史貝司(Speth)的著作《大型獵物狩獵的古人類學和人類學》(The Paleoanthropology of and Archaeology of Bug Game Hunting)中,他陳述道: 「......脂肪,而非蛋白質,在獵人的決策中扮演了顯著的角色,用以決定該殺哪頭動物(公還是母),哪些部位該帶走、哪些又該留下。」[註12]
對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的龔人(!Kung,譯注:非洲南部桑人的其中一支)來說:
「肥胖的動物極受喜愛,而所有的龔人總是迫切渴求著動物脂肪。」[註13]
而就詹姆斯灣(James Bay)的克里族(Cree)來說,他則描述道: 「克里族認為脂肪是所有動物身上最重要的部分。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認為熊比其他動物更加有價值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牠們身上的體脂肪。」[註14]
而澳洲阿納姆地(Arnhem)的雍古人(Yolngu)也有類似的觀點: 「沒有脂肪的動物可能因此不被接受是食物。」[註15]
為什麼我們的祖先們和較近代的原住民族們都這麼積極地想獲得脂肪呢?最根本上來上,可能是因為熱量含量。同樣重量的脂肪,能夠提供比等量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高兩倍的熱量。此外,脂肪對人類的新陳代謝來說,是一種特別有價值且必須的食物。如果我們把自己想像成汽車的話,就會需要燃料來驅使我們的新陳代謝引擎,那麼一來,蛋白質就不會是我們想放進加油箱的燃料。為了要求最高的效能,脂肪或是碳水化合物對我們的新陳代謝引擎來說更加有效率。我們的身體會優先將蛋白質作為建構組元(building blocks)使用,而非作為能源。雖然我們可以透過糖質新生作用(gluconeogenesis),來將蛋白質轉化為能量使用,但這仍舊不太能作為我們主要的能量來源。
讓我們現在來是試想一下:我已經想到能讓時光機運作的辦法,並且跟你一起回到了過去。讓把時間設置到50,000年前,到一個智人(我們的親戚)和尼安德塔人共存的時代兜兜風吧。我希望你把你的裹腰部纏好,才不至於讓我們顯得太顯眼。我還希望你懂製作長矛的方法,因為很快地,我們的肚子就會餓了。好了,那我們現在應該要去找一些會讓你拉肚子的苦葉子來吃呢,還是要挖一些有超多纖維而且難吃得要死的植物根來吃呢?還是,要不要來狩獵一些大型獵物?牠們可以提供我們更多的能量,也可以讓我們接下來幾天,甚至幾週都有食物可以吃喔。
這是個很簡單的抉擇,而對我們的老祖宗們而言也是如此。忘掉樹葉跟超多纖維的植物根吧,我們要去狩獵啦!而一旦狩獵成功,我們就可以吃好幾天長毛象或是水牛大餐了。就如同我們在穩定同位素測定研究中看到的一樣,我們所採取的手段與老祖宗們所做的不謀而合。我很高興他們作出了明智的抉擇,且想出了解決方案,因為我認為,如果不是因為如此,人類這個物種是沒辦法生存至今的。
這本書進行到這個階段,我想要來跟你分享我的肉食密碼假說:我相信,在我們的演化過程中,我們的祖先狩獵是有優先順序的,並且只有在食物難尋或是挨餓的情況下,才會以植物作為食物。我的假說建立在以下這幾項因素上:
1. 人類學數據——包括腦尺寸,來自骨骼以及牙齒可靠的同位素測定數據,以及上述的原住民族案例。
2. 投入相同能量,從動物身上所能獲取的能量遠大於植物。
3. 動物作為食物極度優越的營養含量(我們之後會在第八章繼續談這個)
我並不是在暗指我們的祖先從來沒有食用植物,但根據動物在熱量和營養學的優越地位,他們偏愛食用動物。如果在無法取得動物作為食物的情況下,我們可能會改吃植物作為備胎選項,不過,植物似乎沒有在我們祖先的飲食中佔有任何重要地位。
花一小段時間,讓我在上一段提出的這個論點好好在你心底沈澱一下。「人類是雜食性動物」這個觀點在現在已經被視為理所當然,但這究竟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們仔細思考這一點、更深入挖掘,並拿我們自己跟其他雜食性跟肉食性動物相互比較、觀察,便能得到一些深具啟發的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