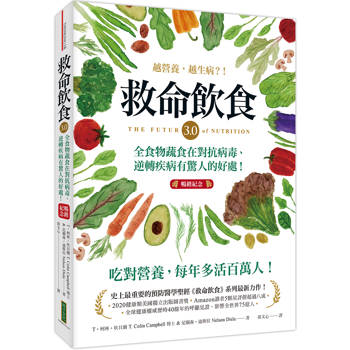【精采內容】
◎如果我轉變飲食時有這本書就好了!
霍華.李曼(Howard F. Lyman),《紅色牧人的綠色旅程》作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蒙大拿州的一個大型酪農場長大,從未懷疑過我們所生產食物的價值和品質─我相信農場出產的肉品和牛乳是未來健康的關鍵。因此,當我要決定未來的職業時,這樣的成長背景也影響了我的決定。雖然農業並不賺錢,但我相信不斷成長的世界人口會讓農業有利可圖。
在決定成為食物製造者之後,要掌握更多農業知識的下一步就是取得大學學位,所以我進入蒙大拿州立大學,取得農業生產的學士學位,準備好以暴風席捲糧食生產界。
不過,我很快就注意到一個問題:有數百萬的生產者,但銷售對象卻只有寥寥幾個買家。
我的農場必須做到更大規模,否則就會被淘汰,所以我把規模做大:後來控制幾千畝的農作物並擁有幾千頭的牲口。大學課程讓我知道如何支配生產過程:化學物質可以控制草料生長,工廠化的飼育場可以養肥待宰的牲口,大型設備可以種植和採收穀物。
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我開始注意到土壤品質下降、我們的動物從有價值的夥伴變成數字,但我實在太忙了,沒有空細想這些問題。我當時想,如果這些問題很重要,大學應該會教才對。同時,我的個人生活也變得很忙碌:我結婚了,並且生了五個小孩。
***
然後,一切都變了。我的腰部以下失去感覺,醫師診斷出我有脊椎腫瘤。開刀之前,醫師告訴我,如果腫瘤是長在脊柱內,術後可以走路的機率是百萬分之一,這讓我很擔心。手術前一夜,好多事情繚繞在心頭, 其中包括土壤品質下降,還有我和動物們的關係。我下定決心,無論手術結果如何,都要努力修正這些問題。
結果,腫瘤的確在脊髓內,但我排除萬難走出了醫院─這對我而言是個奇蹟。經過這件事之後,在漫長的復原期間,我並未忘記關於土壤或動物的事情。
手術後,我的身體沒辦法負荷勞動,而閱讀是排遣時光的好方法。那時候,我第一次注意到康乃爾大學的研究學者─柯林.坎貝爾博士。不過,在人生的那個階段,坎貝爾博士的書對我而言實在是遙不可及。
在恢復期間,我發現自己的農牧方式對環境的傷害很大,因此決定成為有機農夫。然而,當我告訴銀行業務員這個計畫時,他笑著表示,除非是透過當地化學經銷商,否則銀行不會借我任何一毛錢 !
無法改變農牧方式,再加上債務的重擔,讓我的眼前只剩下兩個選擇:繼續傳統的農業方式,或者把我的事業結束變現─我選擇後者。
後來,我競選國會長期職務失敗,便擔任華盛頓特區一家小型家庭農場組織的遊說者。對於來自蒙大拿鄉村的小鎮男孩而言,在政府大樓做事真是令我大開眼界。親眼見到國會運作,跟從談論公民議題的書籍上讀到這些事,是非常不一樣的。
***
在華盛頓時,我的飲食方式跟在農場的時候差不多,但是體能活動卻減少許多,所以我胖得跟可以抓去宰的豬差不多。我知道自己必須做出大改變,否則早晚會心臟病發作。
此時,我想起了坎貝爾博士的書,決定在不動聲色的情況下改變飲食習慣。因此,我為那些肉品和乳品製造者工作,卻同時也是一位蔬食者,但隨著時間過去,我減掉的體重已逾四十五公斤。
差不多那個時候,英國出現一種新興疾病:狂牛症。狂牛症的症狀和我在農場裡集中飼養的牛隻身上看到的問題很類似,而且病因來自使用動物廢棄物餵食牛隻,這是大部分美國集中飼養場常見的做法。這不僅對畜牧業來說是很大的問題,現在連食用遭感染肉品的人類也會生病。這個問題可能會讓畜牧業損失好幾十億美元,而畜牧業為了捍衛自己的生意,花多少錢都願意。
科學的基礎是真理,但美國人的飲食卻建立在許多謬誤上,我們幾乎無法分辨真理與謬誤。
農牧企業絕對不想說清楚狀況,美國消費者也不想知道他們相信的事實其實不是事實。他們一貫的把戲是顛覆科學並依靠從眾心理,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要從眾。
我為「超越肉類(Beyond Beef)活動」工作時,第一次在辦公室見到坎貝爾博士。我們兩個都是農場小孩,維繫融洽的情誼至今。
這次見面之後,歐普拉決定要做一集關於狂牛症的節目。我是少數針對這個問題向大眾發表意見的人,所以被邀請上節目。數百萬名觀眾引頸期盼,畜牧業則惴惴不安。他們推派的代表是我在國會曾經共事過且熟識的一位遊說者,但他在節目中代表畜牧業的表現很差。歐普拉在節目的最後表示她再也不會吃漢堡了─這對畜牧業人士而言是多大的災難啊 ! 整個畜牧業亂成一團……
當畜牧業回過神來,有些人決定要控告我和歐普拉,求償數百萬美元,以阻止媒體報導狂牛症。這樣的訴訟持續了好幾年,但每次都是我們勝訴。
我們的答辯根據是坎貝爾博士和中國營養研究。由於畜牧業人士沒辦法從連結動物性蛋白質和癌症的研究中找出任何缺點,就沒辦法根據事實進行訴訟。我們在陪審團眼中占了上風,不僅是因為言論自由權,也因為我們的言論是建立在科學和真理的基礎之上。
***
在坎貝爾博士的新作《救命飲食3.0》中,我們可以找到相同的證據, 來證明食品業和醫藥業如何結合既得的政府利益,來抹殺植物性飲食的益處。我讀這本書時不斷在想,如果我從攝取動物性食物逐漸轉變成素食者的時候,手邊有這本書,過渡期將會容易許多。
能夠讀到真正的天才科學家闡述的事實,是我的榮幸。柯林.坎貝爾博士惠我良多,我認為他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營養不良是元凶
解決辦法不是更多或更好的藥物,而是了解並處理許多疾病背後的主要元凶:營養不良。
「營養不良」是我深思熟慮後使用的詞彙。雖然這個字通常特指熱量不足或者缺乏某些必要營養素,「營養不良」字面上的意義(營養不好)也適用於過量的飲食型態,這樣的飲食型態使大部分美國人面臨更大的威脅。這包括許多生活貧困的美國人。美國社會中最窮困的人,通常會攝取單糖含量高、油脂過多的食物,因為這些食物比較便宜,但這兩點都會造成肥胖,還有更高的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風險。回溯幾十年前的研究,包括數十年前指標性的弗萊明罕心臟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都指出心臟病與許多危險因子有關,包括血膽固醇偏高和高血壓,都是營養不良的症狀。甚至,綜合國際和移民研究結果來看,「飲食」這個環境因素不但重要,甚至還是對心臟病風險影響最大的因素。
早在六十年前的驗證性實驗研究就已經證實這件事: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八年間,萊斯特.莫里森(Lester Morrison)醫師把一群心臟病患分成對照組與實驗組。他要實驗組的病人減少攝取脂肪和飲食膽固醇,從原本八○~一六○公克的脂肪和二○○~一八○○毫克的飲食膽固醇,降至二○~二五公克的脂肪和五○~七○毫克的飲食膽固醇。十二年後,對照組所有病人都去世了,而有三八%實驗組病人仍然存活。更近期的研究顯示,假使飲食改變能夠更完整,而不只是遵循莫里森設計的低脂方案(比如在他的研究中病人還是可以吃少量的瘦肉),存活率就可以從三八%更進一步提高到九○%。因此,研究結果不言而喻:我們吃的東西對心臟病的結果影響極大。類似的證據包括國際相關性研究、移民研究和實驗性實驗室動物研究,都證實飲食與癌症、糖尿病、肥胖、腎臟病,以及許多疾病之間有相似的關聯。
整合這些研究,再加上我們先前看到的對於營養不良潛在影響的保守估計,顯示心臟病、癌症、中風和醫療疏失(假設對藥物和其他醫療措施的需求減少,疏失的機會也會減少)導致的大量死亡,可以藉由良好的營養而預防,然後我們就會看到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過去列的重大死因有所改變。
光是美國,每年就有百萬性命因為不必要的疾病而流逝。如果有最適合「成長空間」這個詞的情境,大概就是這件事了;只要攝取正確的營養,因為不必要的疾病而喪生或早逝的生命,就都有救了,而巨大的經濟負擔則可以轉向資助能夠改善社區健康的計畫和政策。
如證據顯示,如果我的評估正確,為什麼這麼多人不把營養當作解決方法呢?我父親因為第二次心臟病發作而喪命,但莫里森明明早在許久之前就做了研究,為什麼我父親和許多人都沒有聽過這項研究呢?為什麼營養學沒有納入心臟科醫師、腫瘤科醫師及其他各階層醫療人員的培訓和實務中?心臟病是我們的頭號殺手,為什麼我們對於學習心臟病發生率極低的其他文化飲食型態興趣缺缺?為什麼我們持續低估營養的重要性,卻將大把的時間和資源投注在侵入性醫療處置和救急的藥物上?
有兩個基本的觀察結果有助於回答這些問題。首先,社會主流文化敘事告訴我們,營養不良和生病只有部分的關聯性。人們相信這件事的程度取決於疾病(例如,比較多人會說營養對心臟病的影響大過於癌症),但是一般而言,我們的社會不認為營養不良是大部分疾病的主因,當然也不會把營養當作最好的治療方式。即使我們在某些情況下承認營養扮演的角色,往往只是次要的。
舉例而言,有時候你可能會聽到別人建議你要吃好一點,降低遺傳疾病發病的風險。營養能做到的遠比降低風險更多,甚至能夠消除疾病,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勝過基因決定論,但接受這個概念的人還不多。我們只是空口說白話,建議攝取「對心臟好的飲食」之類的,但往往只是很粗淺的討論,而且總是與其他生活方式選擇(例如運動)連結在一起。
然而,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也對於營養很困惑。這是第二項基本觀察結果:主流文化敘事告訴我們,即使癌症跟健康密切相關,我們還是不確定最健康的飲食應該是什麼樣子。
在本章剩餘的部分,以及接下來的兩章,我把重點放在第一項觀察結果:營養(不良)未被完全視為疾病和健康的決定因素。第二點,也就是對於營養的困惑,影響我們對營養的看法和運用方式,則會在本書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著墨。現在必須重申,全食物蔬食飲食(Whole-Foods Plant-Based Diet,)的飲食生活方式具有爭議,是因為它觸犯到社會的兩種主流敘事。
◎只重視「營養素」的危機
對於飲食營養,到目前為止我們都不太謹慎,反而深陷在簡化式思維的窠臼中。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都只針對個別營養素來描述食物維持健康和預防疾病的能力。雖然在某些情況下,關於個別營養素的資訊會有幫助,但這種方法本身有以管窺天的風險。
儘管我們理智上接受全食物的複雜度,簡化論卻已經變成常態,導致關於營養個別活動的實驗性和探查性研究往往直接忽略這種複雜度。我們持續研究個別營養素,彷彿它們分離出來時的活動,和在全食物中的活動都一樣,事實上,它們在兩種情境中有極大的差異(甚至,分離出來而經由補充品攝取的營養素,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傷害)。
這是幾十年來研究食物和健康的核心模式,只著重於在食物中「獨立」作用的營養素。
從一九四○年代早期到二○○二年的食物攝取飲食指南,都是根據建議個別營養素的每日營養素攝取量(RDAs)。二○○二年,飲食建議擴增為包含個別營養素的「安全」攝取量範圍。同樣地,食品標示和健康宣言一直以來也都強調個別營養素的重要性。這樣的概念甚至滲透到大眾的認知中,塑造了我們對特定食物的評價。
我們被告知胡蘿蔔中的β-胡蘿蔔素對視力好,柑橘類的維生素C可以預防感冒,牛乳可以提供維生素D和鈣質,維持骨骼和牙齒強健。成長過程中,我被逼著要多吃肝臟!「這是很好的鐵質來源耶!你不想要貧血吧?」如果你和大部分人一樣,聽到「鉀離子」時想到的食物會是香蕉,那麼相同的邏輯也會發生在其他方面。你可能還聽說過,吃太多菠菜會因為菠菜所含的草酸鹽太多,而降低鈣質的吸收,或者馬鈴薯所含的碳水化合物會升高肥胖和糖尿病的風險,又或者,大豆所含的雌激素會造成乳癌。你可能聽說過,富含脂肪的堅果會增加心臟病的風險;不過就堅果這件事而言,你很可能也聽過相反的說法。
也許該來為困擾我們的一大堆流行病火上加油了?
你可能認為這些營養方面的細節沒什麼大不了,但我們怎麼詮釋這些細節,都會影響到我們的信念和行為,所以非常重要。想想你自己的人生吧!如果你持續告訴自己「我不夠好」,會造成什麼結果?這樣能夠培養信心、自尊並讓你頓悟嗎?當然沒辦法,遍及整個社會並塑造我們信念和行為的說法,也是如此。如果我們關於「健康營養」的說法都只是片段、互相矛盾、斷章取義,又怎麼能期待達到健康的結果?古英文中,health這個字的字根來自古英文字hǣlth,意思是「整體」(whole),但我們對健康飲食的概念卻只連結到一堆亂七八糟、片段的營養事實,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不是。
既然如此,照目前的情況看來,我們對於營養和健康的看法並不相容。我們只把重點放在簡化式營養, 刻意忽略了健康的整體性,只要我們不認為營養應該針對健康的整體性,這些看法就會持續不相容。你能想像,為剛中風過的病人開立醫囑,要他每天吃番茄,或更糟的,每天吃茄紅素補充品嗎?當然,沒有醫師光靠這些建議就能了事,也只有絕望的病人才會欣然接受這樣的建議,否則病人會懷疑醫師沒有說出全盤實情(然而也真的如此)。
◎如果我轉變飲食時有這本書就好了!
霍華.李曼(Howard F. Lyman),《紅色牧人的綠色旅程》作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蒙大拿州的一個大型酪農場長大,從未懷疑過我們所生產食物的價值和品質─我相信農場出產的肉品和牛乳是未來健康的關鍵。因此,當我要決定未來的職業時,這樣的成長背景也影響了我的決定。雖然農業並不賺錢,但我相信不斷成長的世界人口會讓農業有利可圖。
在決定成為食物製造者之後,要掌握更多農業知識的下一步就是取得大學學位,所以我進入蒙大拿州立大學,取得農業生產的學士學位,準備好以暴風席捲糧食生產界。
不過,我很快就注意到一個問題:有數百萬的生產者,但銷售對象卻只有寥寥幾個買家。
我的農場必須做到更大規模,否則就會被淘汰,所以我把規模做大:後來控制幾千畝的農作物並擁有幾千頭的牲口。大學課程讓我知道如何支配生產過程:化學物質可以控制草料生長,工廠化的飼育場可以養肥待宰的牲口,大型設備可以種植和採收穀物。
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我開始注意到土壤品質下降、我們的動物從有價值的夥伴變成數字,但我實在太忙了,沒有空細想這些問題。我當時想,如果這些問題很重要,大學應該會教才對。同時,我的個人生活也變得很忙碌:我結婚了,並且生了五個小孩。
***
然後,一切都變了。我的腰部以下失去感覺,醫師診斷出我有脊椎腫瘤。開刀之前,醫師告訴我,如果腫瘤是長在脊柱內,術後可以走路的機率是百萬分之一,這讓我很擔心。手術前一夜,好多事情繚繞在心頭, 其中包括土壤品質下降,還有我和動物們的關係。我下定決心,無論手術結果如何,都要努力修正這些問題。
結果,腫瘤的確在脊髓內,但我排除萬難走出了醫院─這對我而言是個奇蹟。經過這件事之後,在漫長的復原期間,我並未忘記關於土壤或動物的事情。
手術後,我的身體沒辦法負荷勞動,而閱讀是排遣時光的好方法。那時候,我第一次注意到康乃爾大學的研究學者─柯林.坎貝爾博士。不過,在人生的那個階段,坎貝爾博士的書對我而言實在是遙不可及。
在恢復期間,我發現自己的農牧方式對環境的傷害很大,因此決定成為有機農夫。然而,當我告訴銀行業務員這個計畫時,他笑著表示,除非是透過當地化學經銷商,否則銀行不會借我任何一毛錢 !
無法改變農牧方式,再加上債務的重擔,讓我的眼前只剩下兩個選擇:繼續傳統的農業方式,或者把我的事業結束變現─我選擇後者。
後來,我競選國會長期職務失敗,便擔任華盛頓特區一家小型家庭農場組織的遊說者。對於來自蒙大拿鄉村的小鎮男孩而言,在政府大樓做事真是令我大開眼界。親眼見到國會運作,跟從談論公民議題的書籍上讀到這些事,是非常不一樣的。
***
在華盛頓時,我的飲食方式跟在農場的時候差不多,但是體能活動卻減少許多,所以我胖得跟可以抓去宰的豬差不多。我知道自己必須做出大改變,否則早晚會心臟病發作。
此時,我想起了坎貝爾博士的書,決定在不動聲色的情況下改變飲食習慣。因此,我為那些肉品和乳品製造者工作,卻同時也是一位蔬食者,但隨著時間過去,我減掉的體重已逾四十五公斤。
差不多那個時候,英國出現一種新興疾病:狂牛症。狂牛症的症狀和我在農場裡集中飼養的牛隻身上看到的問題很類似,而且病因來自使用動物廢棄物餵食牛隻,這是大部分美國集中飼養場常見的做法。這不僅對畜牧業來說是很大的問題,現在連食用遭感染肉品的人類也會生病。這個問題可能會讓畜牧業損失好幾十億美元,而畜牧業為了捍衛自己的生意,花多少錢都願意。
科學的基礎是真理,但美國人的飲食卻建立在許多謬誤上,我們幾乎無法分辨真理與謬誤。
農牧企業絕對不想說清楚狀況,美國消費者也不想知道他們相信的事實其實不是事實。他們一貫的把戲是顛覆科學並依靠從眾心理,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要從眾。
我為「超越肉類(Beyond Beef)活動」工作時,第一次在辦公室見到坎貝爾博士。我們兩個都是農場小孩,維繫融洽的情誼至今。
這次見面之後,歐普拉決定要做一集關於狂牛症的節目。我是少數針對這個問題向大眾發表意見的人,所以被邀請上節目。數百萬名觀眾引頸期盼,畜牧業則惴惴不安。他們推派的代表是我在國會曾經共事過且熟識的一位遊說者,但他在節目中代表畜牧業的表現很差。歐普拉在節目的最後表示她再也不會吃漢堡了─這對畜牧業人士而言是多大的災難啊 ! 整個畜牧業亂成一團……
當畜牧業回過神來,有些人決定要控告我和歐普拉,求償數百萬美元,以阻止媒體報導狂牛症。這樣的訴訟持續了好幾年,但每次都是我們勝訴。
我們的答辯根據是坎貝爾博士和中國營養研究。由於畜牧業人士沒辦法從連結動物性蛋白質和癌症的研究中找出任何缺點,就沒辦法根據事實進行訴訟。我們在陪審團眼中占了上風,不僅是因為言論自由權,也因為我們的言論是建立在科學和真理的基礎之上。
***
在坎貝爾博士的新作《救命飲食3.0》中,我們可以找到相同的證據, 來證明食品業和醫藥業如何結合既得的政府利益,來抹殺植物性飲食的益處。我讀這本書時不斷在想,如果我從攝取動物性食物逐漸轉變成素食者的時候,手邊有這本書,過渡期將會容易許多。
能夠讀到真正的天才科學家闡述的事實,是我的榮幸。柯林.坎貝爾博士惠我良多,我認為他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營養不良是元凶
解決辦法不是更多或更好的藥物,而是了解並處理許多疾病背後的主要元凶:營養不良。
「營養不良」是我深思熟慮後使用的詞彙。雖然這個字通常特指熱量不足或者缺乏某些必要營養素,「營養不良」字面上的意義(營養不好)也適用於過量的飲食型態,這樣的飲食型態使大部分美國人面臨更大的威脅。這包括許多生活貧困的美國人。美國社會中最窮困的人,通常會攝取單糖含量高、油脂過多的食物,因為這些食物比較便宜,但這兩點都會造成肥胖,還有更高的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風險。回溯幾十年前的研究,包括數十年前指標性的弗萊明罕心臟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都指出心臟病與許多危險因子有關,包括血膽固醇偏高和高血壓,都是營養不良的症狀。甚至,綜合國際和移民研究結果來看,「飲食」這個環境因素不但重要,甚至還是對心臟病風險影響最大的因素。
早在六十年前的驗證性實驗研究就已經證實這件事: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八年間,萊斯特.莫里森(Lester Morrison)醫師把一群心臟病患分成對照組與實驗組。他要實驗組的病人減少攝取脂肪和飲食膽固醇,從原本八○~一六○公克的脂肪和二○○~一八○○毫克的飲食膽固醇,降至二○~二五公克的脂肪和五○~七○毫克的飲食膽固醇。十二年後,對照組所有病人都去世了,而有三八%實驗組病人仍然存活。更近期的研究顯示,假使飲食改變能夠更完整,而不只是遵循莫里森設計的低脂方案(比如在他的研究中病人還是可以吃少量的瘦肉),存活率就可以從三八%更進一步提高到九○%。因此,研究結果不言而喻:我們吃的東西對心臟病的結果影響極大。類似的證據包括國際相關性研究、移民研究和實驗性實驗室動物研究,都證實飲食與癌症、糖尿病、肥胖、腎臟病,以及許多疾病之間有相似的關聯。
整合這些研究,再加上我們先前看到的對於營養不良潛在影響的保守估計,顯示心臟病、癌症、中風和醫療疏失(假設對藥物和其他醫療措施的需求減少,疏失的機會也會減少)導致的大量死亡,可以藉由良好的營養而預防,然後我們就會看到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過去列的重大死因有所改變。
光是美國,每年就有百萬性命因為不必要的疾病而流逝。如果有最適合「成長空間」這個詞的情境,大概就是這件事了;只要攝取正確的營養,因為不必要的疾病而喪生或早逝的生命,就都有救了,而巨大的經濟負擔則可以轉向資助能夠改善社區健康的計畫和政策。
如證據顯示,如果我的評估正確,為什麼這麼多人不把營養當作解決方法呢?我父親因為第二次心臟病發作而喪命,但莫里森明明早在許久之前就做了研究,為什麼我父親和許多人都沒有聽過這項研究呢?為什麼營養學沒有納入心臟科醫師、腫瘤科醫師及其他各階層醫療人員的培訓和實務中?心臟病是我們的頭號殺手,為什麼我們對於學習心臟病發生率極低的其他文化飲食型態興趣缺缺?為什麼我們持續低估營養的重要性,卻將大把的時間和資源投注在侵入性醫療處置和救急的藥物上?
有兩個基本的觀察結果有助於回答這些問題。首先,社會主流文化敘事告訴我們,營養不良和生病只有部分的關聯性。人們相信這件事的程度取決於疾病(例如,比較多人會說營養對心臟病的影響大過於癌症),但是一般而言,我們的社會不認為營養不良是大部分疾病的主因,當然也不會把營養當作最好的治療方式。即使我們在某些情況下承認營養扮演的角色,往往只是次要的。
舉例而言,有時候你可能會聽到別人建議你要吃好一點,降低遺傳疾病發病的風險。營養能做到的遠比降低風險更多,甚至能夠消除疾病,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勝過基因決定論,但接受這個概念的人還不多。我們只是空口說白話,建議攝取「對心臟好的飲食」之類的,但往往只是很粗淺的討論,而且總是與其他生活方式選擇(例如運動)連結在一起。
然而,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也對於營養很困惑。這是第二項基本觀察結果:主流文化敘事告訴我們,即使癌症跟健康密切相關,我們還是不確定最健康的飲食應該是什麼樣子。
在本章剩餘的部分,以及接下來的兩章,我把重點放在第一項觀察結果:營養(不良)未被完全視為疾病和健康的決定因素。第二點,也就是對於營養的困惑,影響我們對營養的看法和運用方式,則會在本書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著墨。現在必須重申,全食物蔬食飲食(Whole-Foods Plant-Based Diet,)的飲食生活方式具有爭議,是因為它觸犯到社會的兩種主流敘事。
◎只重視「營養素」的危機
對於飲食營養,到目前為止我們都不太謹慎,反而深陷在簡化式思維的窠臼中。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都只針對個別營養素來描述食物維持健康和預防疾病的能力。雖然在某些情況下,關於個別營養素的資訊會有幫助,但這種方法本身有以管窺天的風險。
儘管我們理智上接受全食物的複雜度,簡化論卻已經變成常態,導致關於營養個別活動的實驗性和探查性研究往往直接忽略這種複雜度。我們持續研究個別營養素,彷彿它們分離出來時的活動,和在全食物中的活動都一樣,事實上,它們在兩種情境中有極大的差異(甚至,分離出來而經由補充品攝取的營養素,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傷害)。
這是幾十年來研究食物和健康的核心模式,只著重於在食物中「獨立」作用的營養素。
從一九四○年代早期到二○○二年的食物攝取飲食指南,都是根據建議個別營養素的每日營養素攝取量(RDAs)。二○○二年,飲食建議擴增為包含個別營養素的「安全」攝取量範圍。同樣地,食品標示和健康宣言一直以來也都強調個別營養素的重要性。這樣的概念甚至滲透到大眾的認知中,塑造了我們對特定食物的評價。
我們被告知胡蘿蔔中的β-胡蘿蔔素對視力好,柑橘類的維生素C可以預防感冒,牛乳可以提供維生素D和鈣質,維持骨骼和牙齒強健。成長過程中,我被逼著要多吃肝臟!「這是很好的鐵質來源耶!你不想要貧血吧?」如果你和大部分人一樣,聽到「鉀離子」時想到的食物會是香蕉,那麼相同的邏輯也會發生在其他方面。你可能還聽說過,吃太多菠菜會因為菠菜所含的草酸鹽太多,而降低鈣質的吸收,或者馬鈴薯所含的碳水化合物會升高肥胖和糖尿病的風險,又或者,大豆所含的雌激素會造成乳癌。你可能聽說過,富含脂肪的堅果會增加心臟病的風險;不過就堅果這件事而言,你很可能也聽過相反的說法。
也許該來為困擾我們的一大堆流行病火上加油了?
你可能認為這些營養方面的細節沒什麼大不了,但我們怎麼詮釋這些細節,都會影響到我們的信念和行為,所以非常重要。想想你自己的人生吧!如果你持續告訴自己「我不夠好」,會造成什麼結果?這樣能夠培養信心、自尊並讓你頓悟嗎?當然沒辦法,遍及整個社會並塑造我們信念和行為的說法,也是如此。如果我們關於「健康營養」的說法都只是片段、互相矛盾、斷章取義,又怎麼能期待達到健康的結果?古英文中,health這個字的字根來自古英文字hǣlth,意思是「整體」(whole),但我們對健康飲食的概念卻只連結到一堆亂七八糟、片段的營養事實,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不是。
既然如此,照目前的情況看來,我們對於營養和健康的看法並不相容。我們只把重點放在簡化式營養, 刻意忽略了健康的整體性,只要我們不認為營養應該針對健康的整體性,這些看法就會持續不相容。你能想像,為剛中風過的病人開立醫囑,要他每天吃番茄,或更糟的,每天吃茄紅素補充品嗎?當然,沒有醫師光靠這些建議就能了事,也只有絕望的病人才會欣然接受這樣的建議,否則病人會懷疑醫師沒有說出全盤實情(然而也真的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