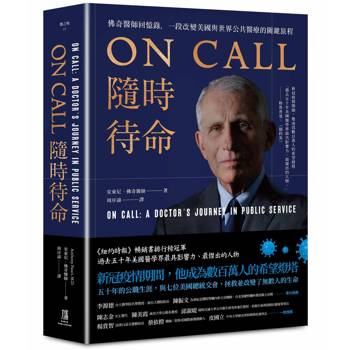近距離接觸的痛苦
隨著我們有對愛滋病患研究有興趣的消息在醫界廣為人知,連恩、馬蘇爾和我很快就有了病人加入我們的新計畫。1982年2月中旬,華盛頓特區正遭逢一場迫使聯邦政府關閉的暴風雪。我冒著風雪沿著威斯康辛大道,開車到國家衛生院貝塞斯達院區,坐在自己位於國家衛生院驗臨床中心的免疫調控實驗室辦公室中。電話響了,是NIAID所長,也是我的行政上司克勞斯(Richard Krause)醫師的特別助理懷特斯卡弗(Jack Whitescarver)醫師。一位私人醫師與懷特斯卡弗聯繫,希望將患有這種疾病的一名病人轉介到國家衛生院。
我記下這名病患的聯絡方式,並安排馬蘇爾和他見面。根據病人病史,馬蘇爾發現病人隆納(Ronald Rinaldi,我更改了病人的真實姓名以保護他的個人隱私)有個身體健康的同卵雙胞胎,因此從健康兄弟那裡進行骨髓移植的可能性立刻顯現出來。現在回想起來,這樣的想法有點天真,因為我們很快就得知導致這種疾病的原因,而大量湧入的愛滋病患讓我們應接不暇。
在過去的十年裡,我已經習慣於治療——通常也能治癒——患有發炎性疾病的重症患者;我的病人很少死亡。那是一段令人振奮的歲月,身為醫生,我一直為自己感到自豪。
此景不再。
我認為,從1982年起到80年代末期的那幾年,是我醫療生涯中的「暗黑年代」。這場疫情的肆虐讓我無法完全脫離工作,甚至影響了我的個人生活。1981年春天,我和一名交往多年的年輕女子結婚。但我們關係中長期存在的矛盾,加上我將大量時間投注在應對肆虐的愛滋病上(不幸的是,疫情在我們新婚後幾個月裡爆發),使得我們無法維繫這段婚姻。我們在結婚兩週年前後分居,並在一年後和平地離婚。
除了照顧重症病患之外,我幾乎沒有時間做任何其他事情。他們所承受的苦痛、苦難和恐懼令人難以想像。在照顧大量病危且通常驚恐萬分的病患時,身為醫生和醫療照護者所承受的強烈情緒壓力和挫折,都是筆墨難以形容的。跟著連恩、馬蘇爾和我一起併肩作戰的,還有一群才華洋溢而且認真的護士、研究員、住院醫生和其他專業的醫療人員,他們共同分擔了責任。沒有他們,我們永遠無法為患者提供他們需要的卓越照護。
我們不知道導致這種疾病的病因,我們的確也沒有治癒它的方法。這種感覺就好像是在大量出血的傷口貼上一個OK繃。我們有藥物可以治療機會性感染,但當一種感染剛被治癒,其他感染又會快速出現,並且最終導致死亡。儘管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病情還是肆無忌憚地展開。我們患者的中位存活期(medium survival)是九到十個月,也就是說當中有一半的人會在這段時間內死亡。任何一天在我們臨床中心十一樓的病房裡就有十幾位這樣的病人。我接受了多年訓練成為一位治療者;但在這段期間,沒有一個人被我治癒。在這種經驗中,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我們見證了這些相當年輕的病人,在經歷難以想像的磨難時,所展現出的勇氣和尊嚴,這激勵了我們。我們的病人在死亡或被送往臨終關懷機構之前,通常會在這裡住上一段時間,因此我們這些醫生和護士有機會好好認識他們。看著他們受苦,最終失去他們,讓我們感到無比沉重。我那些醫生同事和朋友也是如此,他們在紐約市、洛杉磯、舊金山以及其他大城市照顧著越來越多的愛滋病患,也有同樣的感受。我們經常藉由電話和互相拜訪對方的醫療中心交流經驗,發現我們的經歷完全一致。直到今天,我仍會想起當時病房中病患緊抓住我的場景,那些場景過了四十多年,今天依然在我心中激盪不已。在許許多多的回憶中,我常常想起其中一幕。
我們幾乎嘗試了所有可行的方法,包括骨髓移植和多次的淋巴球注射,但我們的第一個病人隆納的病情,最終在沒有適當治療方法下逐漸惡化。儘管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保持樂觀的態度。他的免疫系統幾乎全遭到摧毀,他成為許多種機會性感染的獵物。其中一個麻煩的感染是會攻擊多重器官系統的巨細胞病毒,它會攻擊腸道和視網膜,導致病人的視力受損。我們一直在嘗試治療隆納的巨細胞病毒感染,像是使用阿昔洛韋(acyclovir)等現有藥物;然而,唯一能阻止疾病進展的方法就是重建病患的免疫系統,並同時直接治療巨細胞病毒感染。但我們無法重建他的免疫系統。從他雙胞胎兄弟那裡取得的淋巴球注射以及骨髓移植都失效了。
隆納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傢伙,連恩和我都很期待在一天兩次的正式巡房時與他交談。我會走進病房,站在他的床邊。看到我,他會說:「佛奇醫生,您一切都好嗎?很高興見到您。」然而有一天晚間巡房時,連恩和我走進病房;我走到隆納的床邊,對他微笑。他直視著我問說:「是誰在那裡?」
這就像是有人把一根釘子插進我的胸口。隆納完全失明了。儘管他有在接受治療,但那顯然是無效的。從早上進行巡房到晚間再次走進病房的這段期間當中,巨細胞病毒吞噬了隆納視網膜上影響視覺的關鍵部分。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緒,與連恩一起,就這毀滅性的結果安慰隆納。不過他告訴我們,幾週之前他就已經逐漸失去視力,他早已預料會發生這種情況。而後,我們離開隆納的病房,繼續完成當天的巡房。我回到自己位在病房走廊盡頭的角落辦公室,在團隊看不見的地方,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我不只深受震撼,也感到悲痛;我深感挫折和憤怒。隆納不久後去世了。這只是其中一個故事。
當時我無法完全理解,但對我們來說,在這個病房裡還有成百上千個類似的遭遇。
我以前也體驗過悲傷的滋味。在我二十四歲的時候,我的母親因癌症而去世,我知道失去一個摯愛的人是什麼感覺。但與之相比,我們現在經歷的失落相差了好幾倍。它是長期而且無所不在的。我踏入醫學領域,是因為我想為人們服務;而身為一名醫生,我的任務是治癒病人,去找到解決方案,將他們從即將面臨的災難中拉回。這是我很擅長的事。我是個天性樂觀的人,但現在一波又一波,往往是二、三十歲的男性病患被宣判死刑,而我受到的訓練和性格,都無法阻擋這種可怕而無法避免的結果。我當時的心情只能以無助來形容,就好像我們身處戰場,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作戰――這個敵人正逐漸超越我們。但是我們團隊裡的醫生、護士和醫護人員不能放棄。職業倦怠不是一項選擇。病人需要我們;儘管我們無法治癒他們,我們仍然可以為他們提供我們所擁有的東西――臨床技能、同理心和優質的照護。我們必須堅持下去,而我們做到了。除了偶爾難以控制的悲傷,像是得知隆納失明的時候;在病房工作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日復一日的拋開失落的情緒,才得以堅持下去。
我認為這些感覺只能被壓抑一段時間。時至今日,當我回想起那段時光的情景,眼淚仍不由自主地湧了出來。我讀過關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的文章,我相信在這個特定領域,我有這樣的症狀。而我並不孤單。透過與許多當年在愛滋病前線工作的同事交談,我知道他們也曾有過類似的感受。但是,與病人以及他們的家人經歷的苦難相比,我們的遭遇根本算不得什麼。
...
擴大戰場
2001年1月20日,我在電視上觀看小布希 (George W. Bush) 總統就職典禮轉播時,想起我初次遇見這位第四十三任總統時的情景。將近十二年前,他和他的父親在1989年一起來國家衛生院參訪。當我帶領他們參觀我們的實驗室和病房時,我將布希一家介紹給幾位病人,小布希似乎對於愛滋病這個議題真的很感興趣。
每當一個新任總統宣誓就職時,我都想知道同樣的一件事--這位新總統將如何看待全球愛滋病毒/愛滋病疫情 假若有機會,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和NIAID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就像柯林頓政府時期一樣,我並不需要等待太久就知道答案了。
新上任的HHS部長湯普森 (Tommy Thompson) 是威斯康辛州在職時間最長的州長 (1987年至2001年),在接掌這個職務之前,他並沒有全球衛生方面的經歷。但他對於愛滋病毒以及其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影響非常感興趣。2001年4月3日,我應邀向湯普森和他的幹部做簡報,而後到他的辦公室與他進一步地交談。湯普森告訴我,他從新政府和國會一些人那裡聽說許多關於我的事,他希望我成為他關於愛滋病的顧問。他提到他和國務卿鮑威爾 (Colin Powell) 將領導一個國際愛滋病的行政工作團隊。
我很高興和訝異事情飛快地進展,兩天之後,也就是2001年4月5日,我第一次被邀請到戰情室參加會議。戰室事是一個戒備森嚴的會議室(需要將你的手機留在門外),它位於白宮西翼一樓,面對著海軍食堂。會議由埃德森 (Gary Edson) 主持,他是國家安全顧問萊斯 (Condoleezza Rice)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的副手。湯普森的國際事務聯絡人斯泰格 (Bill Steiger) 被指派制定一份將做為國際愛滋病計畫框架的白皮書,他們希望我就此提供意見。在埃德森、我和HHS以及白宮的其他人員進行反覆多次修改草稿之後,我們將最終的成果提供給湯普森和鮑威爾,以便在即將舉行的總統簡報會上使用。
早在西元2000年,就有人討論過創建一個程序的可能性,讓世界上已開發國家共同支援那些愛滋病毒/愛滋病最嚴重的非洲南部國家。這理念在全球許多有影響力的人士發起和倡議之下促成後來的「全球基金」 (Global Fund),其中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Kofi Annan) 與著名的總體經濟學家薩克斯 (Jeffrey Sachs) 等。2001年3月底,在義大利陶爾米納的一個國際聚會 (2001年7月八大工業國高峰會G8的會前會) 上,這個議題又再次被提出,並促成一份白皮書。
針對這份白皮書的相關討論中,我強調自己長期以來強烈的感受,我認為美國有道德責任,在國際衛生上發揮領導作用調動資源。在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協助開發中國家減緩和防止傳染病擴散也符合我們的自身利益。愛滋病毒/愛滋病、瘧疾和結核病等它他傳染病的威脅會影響非洲和世界其它地區的穩定性。此外,美國大多數的結核病病例是來自境外出生的人口。更重要的是,應該支援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發展永續的衛生基礎設施,以便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去應對未來的公共衛生挑戰。
2001年春天,白宮的工作人員經過討論之後認為,建立某種形式的多邊全球基金是無可避免的事。有鑑於我們很可能是最主要的捐款者,總統認為美國應該主導如何組織和管理這個基金。2001年5月11日,在剛結束與奈及利亞總統奧巴桑喬 (Olusegun Obasanjo) 和安南的會晤之後,總統在玫瑰園的公開演說中,清楚地表達了這個想法。他總結了愛滋病毒/愛滋病對於整個非洲大陸和全世界的影響,並告訴觀眾美國展現領導力和分擔責任有多麼重要,並讚揚迄今國際之間的努力。總統隨後承諾撥款兩億美元支持一個嶄新的全球性基金。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湯普森邀請我參加他和國務卿鮑威爾率領的美國聯合國大會愛滋病毒/愛滋病特別會議代表團;該會議於2001年6月25日至27日在紐約市舉行。在聯合國大會的大廳之中,我坐在國務卿鮑威爾和湯普森旁的位子,身邊是來自世界各國的元首、大使以及衛生部長。我不禁回想起整整二十年前,連恩、馬蘇爾和我在國家衛生院臨床中心接納第一批愛滋病患十,這種疾病還沒有正式的名字,也沒有受到特別的關注。現因為美國和其他國家對於聯合國對抗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防治的全球基金 (United Nation’s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簡稱全球基金) 一致達成在財政支援上的承諾,我見證到對於全球愛滋病疫情災難的全新態度和承諾。世界其它地區的政府高層終於正視愛滋病毒/愛滋病的問題。
安南針對設立這個基金的必要性發表了精彩演講。國務卿鮑威爾的演講也同樣具有說服力,講稿大部分取材自我們的白皮書。他提出在往後幾年裡他經常強調的一個問題--愛滋病除了是個嚴重的衛生問題,在非洲南部某些國家以及世界其他貧窮國家也是國家和全球的安全問題。
在六個月之後,全球基金於2002年1月28日正式成立。於此同時,一些無法預料的戲劇性事件徹底顛覆了全球對於於愛滋病的關注。
...
改變世界的九一一
我搭乘的全美航空班機大約在早上八點降落在紐約拉瓜地亞機場。我跳上一輛計程車前往曼哈頓中城,參加一個慈善基金會的董事會,我是其中一位董事。當我從皇后區的機場出發前往市區時,我被紐約市的天際線在蔚藍天空的襯托之下呈現的美景所震攝。當我們從東三十四街的中城隧道出來的時候,我看到遠處往市中心的方向有一團濃煙。
那天是2001年9月11日。
當我從西五十二街一棟大樓第十九樓的電梯出來時,我的董事會同事們不像往常一樣聚集在咖啡和糕點附近,而是專注在會議室裡的寬螢幕電視前。他們告訴我,有一架小型飛機偏離了航線,撞上世界貿易中心北塔大約第九十五層。當我看到電視畫面上由大樓升起的煙霧時,我猜想這就是我剛剛在計程車上看到的煙霧。就在我們討論一架小型的商用飛機因為偏離航線而撞上曼哈頓下城的摩天大樓是多麼不尋常時,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在早上九點三分,一架無疑是全尺寸的商用噴射客機撞上了南塔的南面。電視攝影機捕捉到一個巨大的火球非要到紐約市天際的那一瞬間。我們全部衝到窗邊,看看是否可以看到市中心的景象,但是因為窗戶的角度和大樓的位置,我們無法看到任何景象。我們像數千萬其他人一樣,目瞪口呆地盯著電視,看著兩座塔樓冒出濃煙。顯然美國正遭受攻擊,我們和其他看到這一幕的人一樣,感到非常的震驚。我們並不確定是誰在攻擊我們,或著為什麼。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們的世界和過去不樣了。
我趕緊打電話告訴跟克莉絲汀報平安,接著打電話給我在貝塞斯達的辦公室。我的同事告訴我,湯普森想和我通話。在過去幾個月裡,我和他已經逐漸熟識並且親近,我們討論了HHS在防禦生化武器物上應做的準備和應變措施。他打電話詢問我HHS在當下可以幫上什麼忙。「湯普森,我其實正在紐約市距離雙子星大樓大約五十個街區,」我說。
他回答說:「你覺得你能到現場並向我回報那裡的現況嗎?」
「我會盡力而為。」
事情越來越糟糕。上午九點三十七分,美國航空七十七號班機墜毀在華盛頓特區近郊五角大廈的西邊,新聞轉播在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廈之間來回切換報導。上午十點剛過,根據傳言,我們得知另一架正在前往國會大廈或白宮的聯合航空九十三號班機,墜毀在賓州薩默塞特郡的一片空地。劫機者被一群勇敢的乘客制伏,在與劫機者搏鬥的過程中導致飛機的墜毀。
這讓我的焦慮更為加深。我意識到,幾個小時之前我才和三個躺在床上睡覺的女兒吻別,現在他們正坐在學校的教室裡。國家主教堂學院位於國家大教堂的園區,座落在市內海拔最高處,俯瞰著華盛頓特區。我不確定有多少架飛機參與這次的攻擊行動,我擔心國家大教堂會成為另一個襲擊的目標。我不斷絕望地試圖打電話到克里斯汀在國家衛生院的辦公室。然而此時,所有的電話線路都已經卡住。這也代表我無法聯繫到目前住在曼哈頓東六十八街的父親。但因為他很少(可能從不)去市中心,我幾乎可以確定他沒事。
後來我得知克莉絲汀和女兒們都很為我擔心,因為他們知道我正在曼哈頓,而且因為女兒們可以從教室看到窗外五角大廈瀰漫著煙霧,整個攻擊事件對他們來說太真實了。
當天的慘狀持續發生,電視上轉播著人們為了躲避身後的火焰,從塔樓高樓層跳出窗外的畫面。在所有與九一一事件相關的悲劇之中,那些無辜的人跳樓致死的景象帶給我沉重的打擊,讓我永生難忘。就在那一刻,那些散播暴行的人,讓我的恐懼轉變為深沉的憤怒。
接下來在上午九點五十九分和十點二十八分,發生了讓人難以置信的打擊,南北雙塔在全世界數十億的人們的目睹下,在電視上徹底崩塌。這讓房間內所有的人感到無助,並陷入深深的沮喪之中。
我覺得自己至少需要試著履行對湯普森的承諾,到市中心的案發現場看一下。我一走到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二街,很快就發現我不可能搭乘計程車、公車或任何其他的交通工具到任何地方。所有的交通完全封閉,我決定步行前往。我碰巧遇到一位紐約市警官,他和一群警察正聚集在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二街的轉角。我跟他解釋湯普森部長要求我前往現場,並向他回報。他滿臉疑惑的看著我,好似我瘋了一樣,接著說,「誰是湯普森部長?老兄,我們只允許警察、救護車和消防員進去。 」
我別無選擇,只好返回基金會總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我不斷試圖打電話回我的辦公室,但無濟於事。奇蹟似地,我終於打通了,我的助理告訴我,湯普森部長要我立刻返回華盛頓。接下來將會有一場高層會議,規劃如何因應在飛機襲擊之後,可能發生的生物恐怖攻擊,他要我在場。
所有的航班都停止了,但我必須在當天晚上返回華盛頓。雖然機會很渺茫,但唯一的可能就是搭乘美國鐵路 (Amtrak)。我和另一位基金會董事杜克大學校長基歐漢(Nan Keohane)一起前往位於第七大道和西三十二街的賓夕法尼亞車站。因為步行是唯一可以到達那裡的方法,我們開始往南走,穿過看起來很不真實的曼哈頓中城。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情景,街上幾乎沒有任何車輛。就這樣我們穿過百老匯中間的時代廣場。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覺,讓我想起過去看過的一些電影之中,紐約市的街道在經歷致命的災難之後,一片空蕩蕩的樣子。我們步行了三十五分鐘到達賓州車站時,我很幸運地搭上了當天晚上南向前往華盛頓特區的火車。
當火車駛出隧道前往第一站紐瓦克時,從火車上可以清楚看到世貿中心遺址散發的煙霧和光芒,我看到現場突然爆出一團濃煙、灰塵和光芒。我以為可能又有另外一架飛機撞擊了另一棟建築物。我真的無法相信發生了什麼事。整趟前往華盛頓的旅程之中,我麻木地坐在座位上,不敢確定回家會將面對什麼樣的狀況。我一回去就聽說,我看到那一團噴發的煙霧和灰塵,是因為四十七樓層的世貿七號大樓(簡稱七號塔)倒塌所造成的。 它沒有遭到飛機撞擊,但因為南北雙塔爆炸、起火災和倒塌,跟著燃燒起來。
從聯合車站搭乘計程車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幾乎每個主要的路口都有警察駐守。雷根國家機場及杜勒斯國際機場無限期關閉。計程車上的廣播報導,聯邦調查局聲稱,仍有幾個恐怖分子集團潛伏在美國境內,計劃進一步進行攻擊,而華盛頓特區首當其衝。當我走進家門之後,無法停止擁抱我的女兒們。那天晚上,克莉絲汀和我躺在床上,聽著F-16 戰鬥機以戰鬥模式在城市上空飛行的聲音,它們準備就緒,以攔截任何進一步的攻擊。
第二天,湯普森告訴我,政府在籌備防範未來可能發生的生物恐怖攻擊,HHS將會是其中一個主導機構,他要求我成為他在這個任務中的負責人。那一瞬間,愛滋病毒/愛滋病幾乎從美國政府、甚至全國人的視線之中消失了,至少現在是如此。接下來的幾天,我參加了幾場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擴增策略主任法肯拉思 (Richard Falkenrath) 在白宮主持的最高機密會議。會議的目的在製定因應生物恐怖攻擊的短期和長期計畫。
與會者的普遍看法是,這樣的攻擊是無可避免的,而所有可能用來對付我們的生化物質中,氣溶膠天花病毒被認為是最主要的威脅。在歷史上,天花是一種藉由人與人之間傳播的致命疾病。眾所周知,叛逃的蘇聯官員聲稱,冷戰期間蘇聯儲存了大量的天花病毒以及其他致命的傳染源,以備在蘇聯與西方同盟國之間爆發衝突時當作生化武器使用。蘇聯解散之後的混亂之中,是否有任何庫存生物武器庫存落入蓋達組織或其他激進派伊斯蘭組織的手中,至今仍不明確。無論機會有多渺茫,白宮仍然非常慎重地評估恐怖分子已經掌握這些生化武器的可能性。
HHS位於漢弗萊大樓的華盛頓總部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會議。會議討論的基本主題是,因應這種新的生化恐怖威脅,我們需要發展診斷、治療和疫苗等因應對策。NIAID被指派為主導這項任務的機構。我們將負責規劃和協調研究方向,交由所方贊助者和承包商執行。當國家遭受另一波的衝擊襲擊時,這項任務變得更加緊迫。
隨著我們有對愛滋病患研究有興趣的消息在醫界廣為人知,連恩、馬蘇爾和我很快就有了病人加入我們的新計畫。1982年2月中旬,華盛頓特區正遭逢一場迫使聯邦政府關閉的暴風雪。我冒著風雪沿著威斯康辛大道,開車到國家衛生院貝塞斯達院區,坐在自己位於國家衛生院驗臨床中心的免疫調控實驗室辦公室中。電話響了,是NIAID所長,也是我的行政上司克勞斯(Richard Krause)醫師的特別助理懷特斯卡弗(Jack Whitescarver)醫師。一位私人醫師與懷特斯卡弗聯繫,希望將患有這種疾病的一名病人轉介到國家衛生院。
我記下這名病患的聯絡方式,並安排馬蘇爾和他見面。根據病人病史,馬蘇爾發現病人隆納(Ronald Rinaldi,我更改了病人的真實姓名以保護他的個人隱私)有個身體健康的同卵雙胞胎,因此從健康兄弟那裡進行骨髓移植的可能性立刻顯現出來。現在回想起來,這樣的想法有點天真,因為我們很快就得知導致這種疾病的原因,而大量湧入的愛滋病患讓我們應接不暇。
在過去的十年裡,我已經習慣於治療——通常也能治癒——患有發炎性疾病的重症患者;我的病人很少死亡。那是一段令人振奮的歲月,身為醫生,我一直為自己感到自豪。
此景不再。
我認為,從1982年起到80年代末期的那幾年,是我醫療生涯中的「暗黑年代」。這場疫情的肆虐讓我無法完全脫離工作,甚至影響了我的個人生活。1981年春天,我和一名交往多年的年輕女子結婚。但我們關係中長期存在的矛盾,加上我將大量時間投注在應對肆虐的愛滋病上(不幸的是,疫情在我們新婚後幾個月裡爆發),使得我們無法維繫這段婚姻。我們在結婚兩週年前後分居,並在一年後和平地離婚。
除了照顧重症病患之外,我幾乎沒有時間做任何其他事情。他們所承受的苦痛、苦難和恐懼令人難以想像。在照顧大量病危且通常驚恐萬分的病患時,身為醫生和醫療照護者所承受的強烈情緒壓力和挫折,都是筆墨難以形容的。跟著連恩、馬蘇爾和我一起併肩作戰的,還有一群才華洋溢而且認真的護士、研究員、住院醫生和其他專業的醫療人員,他們共同分擔了責任。沒有他們,我們永遠無法為患者提供他們需要的卓越照護。
我們不知道導致這種疾病的病因,我們的確也沒有治癒它的方法。這種感覺就好像是在大量出血的傷口貼上一個OK繃。我們有藥物可以治療機會性感染,但當一種感染剛被治癒,其他感染又會快速出現,並且最終導致死亡。儘管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病情還是肆無忌憚地展開。我們患者的中位存活期(medium survival)是九到十個月,也就是說當中有一半的人會在這段時間內死亡。任何一天在我們臨床中心十一樓的病房裡就有十幾位這樣的病人。我接受了多年訓練成為一位治療者;但在這段期間,沒有一個人被我治癒。在這種經驗中,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我們見證了這些相當年輕的病人,在經歷難以想像的磨難時,所展現出的勇氣和尊嚴,這激勵了我們。我們的病人在死亡或被送往臨終關懷機構之前,通常會在這裡住上一段時間,因此我們這些醫生和護士有機會好好認識他們。看著他們受苦,最終失去他們,讓我們感到無比沉重。我那些醫生同事和朋友也是如此,他們在紐約市、洛杉磯、舊金山以及其他大城市照顧著越來越多的愛滋病患,也有同樣的感受。我們經常藉由電話和互相拜訪對方的醫療中心交流經驗,發現我們的經歷完全一致。直到今天,我仍會想起當時病房中病患緊抓住我的場景,那些場景過了四十多年,今天依然在我心中激盪不已。在許許多多的回憶中,我常常想起其中一幕。
我們幾乎嘗試了所有可行的方法,包括骨髓移植和多次的淋巴球注射,但我們的第一個病人隆納的病情,最終在沒有適當治療方法下逐漸惡化。儘管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保持樂觀的態度。他的免疫系統幾乎全遭到摧毀,他成為許多種機會性感染的獵物。其中一個麻煩的感染是會攻擊多重器官系統的巨細胞病毒,它會攻擊腸道和視網膜,導致病人的視力受損。我們一直在嘗試治療隆納的巨細胞病毒感染,像是使用阿昔洛韋(acyclovir)等現有藥物;然而,唯一能阻止疾病進展的方法就是重建病患的免疫系統,並同時直接治療巨細胞病毒感染。但我們無法重建他的免疫系統。從他雙胞胎兄弟那裡取得的淋巴球注射以及骨髓移植都失效了。
隆納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傢伙,連恩和我都很期待在一天兩次的正式巡房時與他交談。我會走進病房,站在他的床邊。看到我,他會說:「佛奇醫生,您一切都好嗎?很高興見到您。」然而有一天晚間巡房時,連恩和我走進病房;我走到隆納的床邊,對他微笑。他直視著我問說:「是誰在那裡?」
這就像是有人把一根釘子插進我的胸口。隆納完全失明了。儘管他有在接受治療,但那顯然是無效的。從早上進行巡房到晚間再次走進病房的這段期間當中,巨細胞病毒吞噬了隆納視網膜上影響視覺的關鍵部分。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緒,與連恩一起,就這毀滅性的結果安慰隆納。不過他告訴我們,幾週之前他就已經逐漸失去視力,他早已預料會發生這種情況。而後,我們離開隆納的病房,繼續完成當天的巡房。我回到自己位在病房走廊盡頭的角落辦公室,在團隊看不見的地方,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我不只深受震撼,也感到悲痛;我深感挫折和憤怒。隆納不久後去世了。這只是其中一個故事。
當時我無法完全理解,但對我們來說,在這個病房裡還有成百上千個類似的遭遇。
我以前也體驗過悲傷的滋味。在我二十四歲的時候,我的母親因癌症而去世,我知道失去一個摯愛的人是什麼感覺。但與之相比,我們現在經歷的失落相差了好幾倍。它是長期而且無所不在的。我踏入醫學領域,是因為我想為人們服務;而身為一名醫生,我的任務是治癒病人,去找到解決方案,將他們從即將面臨的災難中拉回。這是我很擅長的事。我是個天性樂觀的人,但現在一波又一波,往往是二、三十歲的男性病患被宣判死刑,而我受到的訓練和性格,都無法阻擋這種可怕而無法避免的結果。我當時的心情只能以無助來形容,就好像我們身處戰場,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作戰――這個敵人正逐漸超越我們。但是我們團隊裡的醫生、護士和醫護人員不能放棄。職業倦怠不是一項選擇。病人需要我們;儘管我們無法治癒他們,我們仍然可以為他們提供我們所擁有的東西――臨床技能、同理心和優質的照護。我們必須堅持下去,而我們做到了。除了偶爾難以控制的悲傷,像是得知隆納失明的時候;在病房工作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日復一日的拋開失落的情緒,才得以堅持下去。
我認為這些感覺只能被壓抑一段時間。時至今日,當我回想起那段時光的情景,眼淚仍不由自主地湧了出來。我讀過關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的文章,我相信在這個特定領域,我有這樣的症狀。而我並不孤單。透過與許多當年在愛滋病前線工作的同事交談,我知道他們也曾有過類似的感受。但是,與病人以及他們的家人經歷的苦難相比,我們的遭遇根本算不得什麼。
...
擴大戰場
2001年1月20日,我在電視上觀看小布希 (George W. Bush) 總統就職典禮轉播時,想起我初次遇見這位第四十三任總統時的情景。將近十二年前,他和他的父親在1989年一起來國家衛生院參訪。當我帶領他們參觀我們的實驗室和病房時,我將布希一家介紹給幾位病人,小布希似乎對於愛滋病這個議題真的很感興趣。
每當一個新任總統宣誓就職時,我都想知道同樣的一件事--這位新總統將如何看待全球愛滋病毒/愛滋病疫情 假若有機會,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和NIAID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就像柯林頓政府時期一樣,我並不需要等待太久就知道答案了。
新上任的HHS部長湯普森 (Tommy Thompson) 是威斯康辛州在職時間最長的州長 (1987年至2001年),在接掌這個職務之前,他並沒有全球衛生方面的經歷。但他對於愛滋病毒以及其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影響非常感興趣。2001年4月3日,我應邀向湯普森和他的幹部做簡報,而後到他的辦公室與他進一步地交談。湯普森告訴我,他從新政府和國會一些人那裡聽說許多關於我的事,他希望我成為他關於愛滋病的顧問。他提到他和國務卿鮑威爾 (Colin Powell) 將領導一個國際愛滋病的行政工作團隊。
我很高興和訝異事情飛快地進展,兩天之後,也就是2001年4月5日,我第一次被邀請到戰情室參加會議。戰室事是一個戒備森嚴的會議室(需要將你的手機留在門外),它位於白宮西翼一樓,面對著海軍食堂。會議由埃德森 (Gary Edson) 主持,他是國家安全顧問萊斯 (Condoleezza Rice)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的副手。湯普森的國際事務聯絡人斯泰格 (Bill Steiger) 被指派制定一份將做為國際愛滋病計畫框架的白皮書,他們希望我就此提供意見。在埃德森、我和HHS以及白宮的其他人員進行反覆多次修改草稿之後,我們將最終的成果提供給湯普森和鮑威爾,以便在即將舉行的總統簡報會上使用。
早在西元2000年,就有人討論過創建一個程序的可能性,讓世界上已開發國家共同支援那些愛滋病毒/愛滋病最嚴重的非洲南部國家。這理念在全球許多有影響力的人士發起和倡議之下促成後來的「全球基金」 (Global Fund),其中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Kofi Annan) 與著名的總體經濟學家薩克斯 (Jeffrey Sachs) 等。2001年3月底,在義大利陶爾米納的一個國際聚會 (2001年7月八大工業國高峰會G8的會前會) 上,這個議題又再次被提出,並促成一份白皮書。
針對這份白皮書的相關討論中,我強調自己長期以來強烈的感受,我認為美國有道德責任,在國際衛生上發揮領導作用調動資源。在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協助開發中國家減緩和防止傳染病擴散也符合我們的自身利益。愛滋病毒/愛滋病、瘧疾和結核病等它他傳染病的威脅會影響非洲和世界其它地區的穩定性。此外,美國大多數的結核病病例是來自境外出生的人口。更重要的是,應該支援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發展永續的衛生基礎設施,以便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去應對未來的公共衛生挑戰。
2001年春天,白宮的工作人員經過討論之後認為,建立某種形式的多邊全球基金是無可避免的事。有鑑於我們很可能是最主要的捐款者,總統認為美國應該主導如何組織和管理這個基金。2001年5月11日,在剛結束與奈及利亞總統奧巴桑喬 (Olusegun Obasanjo) 和安南的會晤之後,總統在玫瑰園的公開演說中,清楚地表達了這個想法。他總結了愛滋病毒/愛滋病對於整個非洲大陸和全世界的影響,並告訴觀眾美國展現領導力和分擔責任有多麼重要,並讚揚迄今國際之間的努力。總統隨後承諾撥款兩億美元支持一個嶄新的全球性基金。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湯普森邀請我參加他和國務卿鮑威爾率領的美國聯合國大會愛滋病毒/愛滋病特別會議代表團;該會議於2001年6月25日至27日在紐約市舉行。在聯合國大會的大廳之中,我坐在國務卿鮑威爾和湯普森旁的位子,身邊是來自世界各國的元首、大使以及衛生部長。我不禁回想起整整二十年前,連恩、馬蘇爾和我在國家衛生院臨床中心接納第一批愛滋病患十,這種疾病還沒有正式的名字,也沒有受到特別的關注。現因為美國和其他國家對於聯合國對抗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防治的全球基金 (United Nation’s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簡稱全球基金) 一致達成在財政支援上的承諾,我見證到對於全球愛滋病疫情災難的全新態度和承諾。世界其它地區的政府高層終於正視愛滋病毒/愛滋病的問題。
安南針對設立這個基金的必要性發表了精彩演講。國務卿鮑威爾的演講也同樣具有說服力,講稿大部分取材自我們的白皮書。他提出在往後幾年裡他經常強調的一個問題--愛滋病除了是個嚴重的衛生問題,在非洲南部某些國家以及世界其他貧窮國家也是國家和全球的安全問題。
在六個月之後,全球基金於2002年1月28日正式成立。於此同時,一些無法預料的戲劇性事件徹底顛覆了全球對於於愛滋病的關注。
...
改變世界的九一一
我搭乘的全美航空班機大約在早上八點降落在紐約拉瓜地亞機場。我跳上一輛計程車前往曼哈頓中城,參加一個慈善基金會的董事會,我是其中一位董事。當我從皇后區的機場出發前往市區時,我被紐約市的天際線在蔚藍天空的襯托之下呈現的美景所震攝。當我們從東三十四街的中城隧道出來的時候,我看到遠處往市中心的方向有一團濃煙。
那天是2001年9月11日。
當我從西五十二街一棟大樓第十九樓的電梯出來時,我的董事會同事們不像往常一樣聚集在咖啡和糕點附近,而是專注在會議室裡的寬螢幕電視前。他們告訴我,有一架小型飛機偏離了航線,撞上世界貿易中心北塔大約第九十五層。當我看到電視畫面上由大樓升起的煙霧時,我猜想這就是我剛剛在計程車上看到的煙霧。就在我們討論一架小型的商用飛機因為偏離航線而撞上曼哈頓下城的摩天大樓是多麼不尋常時,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在早上九點三分,一架無疑是全尺寸的商用噴射客機撞上了南塔的南面。電視攝影機捕捉到一個巨大的火球非要到紐約市天際的那一瞬間。我們全部衝到窗邊,看看是否可以看到市中心的景象,但是因為窗戶的角度和大樓的位置,我們無法看到任何景象。我們像數千萬其他人一樣,目瞪口呆地盯著電視,看著兩座塔樓冒出濃煙。顯然美國正遭受攻擊,我們和其他看到這一幕的人一樣,感到非常的震驚。我們並不確定是誰在攻擊我們,或著為什麼。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們的世界和過去不樣了。
我趕緊打電話告訴跟克莉絲汀報平安,接著打電話給我在貝塞斯達的辦公室。我的同事告訴我,湯普森想和我通話。在過去幾個月裡,我和他已經逐漸熟識並且親近,我們討論了HHS在防禦生化武器物上應做的準備和應變措施。他打電話詢問我HHS在當下可以幫上什麼忙。「湯普森,我其實正在紐約市距離雙子星大樓大約五十個街區,」我說。
他回答說:「你覺得你能到現場並向我回報那裡的現況嗎?」
「我會盡力而為。」
事情越來越糟糕。上午九點三十七分,美國航空七十七號班機墜毀在華盛頓特區近郊五角大廈的西邊,新聞轉播在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廈之間來回切換報導。上午十點剛過,根據傳言,我們得知另一架正在前往國會大廈或白宮的聯合航空九十三號班機,墜毀在賓州薩默塞特郡的一片空地。劫機者被一群勇敢的乘客制伏,在與劫機者搏鬥的過程中導致飛機的墜毀。
這讓我的焦慮更為加深。我意識到,幾個小時之前我才和三個躺在床上睡覺的女兒吻別,現在他們正坐在學校的教室裡。國家主教堂學院位於國家大教堂的園區,座落在市內海拔最高處,俯瞰著華盛頓特區。我不確定有多少架飛機參與這次的攻擊行動,我擔心國家大教堂會成為另一個襲擊的目標。我不斷絕望地試圖打電話到克里斯汀在國家衛生院的辦公室。然而此時,所有的電話線路都已經卡住。這也代表我無法聯繫到目前住在曼哈頓東六十八街的父親。但因為他很少(可能從不)去市中心,我幾乎可以確定他沒事。
後來我得知克莉絲汀和女兒們都很為我擔心,因為他們知道我正在曼哈頓,而且因為女兒們可以從教室看到窗外五角大廈瀰漫著煙霧,整個攻擊事件對他們來說太真實了。
當天的慘狀持續發生,電視上轉播著人們為了躲避身後的火焰,從塔樓高樓層跳出窗外的畫面。在所有與九一一事件相關的悲劇之中,那些無辜的人跳樓致死的景象帶給我沉重的打擊,讓我永生難忘。就在那一刻,那些散播暴行的人,讓我的恐懼轉變為深沉的憤怒。
接下來在上午九點五十九分和十點二十八分,發生了讓人難以置信的打擊,南北雙塔在全世界數十億的人們的目睹下,在電視上徹底崩塌。這讓房間內所有的人感到無助,並陷入深深的沮喪之中。
我覺得自己至少需要試著履行對湯普森的承諾,到市中心的案發現場看一下。我一走到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二街,很快就發現我不可能搭乘計程車、公車或任何其他的交通工具到任何地方。所有的交通完全封閉,我決定步行前往。我碰巧遇到一位紐約市警官,他和一群警察正聚集在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二街的轉角。我跟他解釋湯普森部長要求我前往現場,並向他回報。他滿臉疑惑的看著我,好似我瘋了一樣,接著說,「誰是湯普森部長?老兄,我們只允許警察、救護車和消防員進去。 」
我別無選擇,只好返回基金會總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我不斷試圖打電話回我的辦公室,但無濟於事。奇蹟似地,我終於打通了,我的助理告訴我,湯普森部長要我立刻返回華盛頓。接下來將會有一場高層會議,規劃如何因應在飛機襲擊之後,可能發生的生物恐怖攻擊,他要我在場。
所有的航班都停止了,但我必須在當天晚上返回華盛頓。雖然機會很渺茫,但唯一的可能就是搭乘美國鐵路 (Amtrak)。我和另一位基金會董事杜克大學校長基歐漢(Nan Keohane)一起前往位於第七大道和西三十二街的賓夕法尼亞車站。因為步行是唯一可以到達那裡的方法,我們開始往南走,穿過看起來很不真實的曼哈頓中城。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情景,街上幾乎沒有任何車輛。就這樣我們穿過百老匯中間的時代廣場。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覺,讓我想起過去看過的一些電影之中,紐約市的街道在經歷致命的災難之後,一片空蕩蕩的樣子。我們步行了三十五分鐘到達賓州車站時,我很幸運地搭上了當天晚上南向前往華盛頓特區的火車。
當火車駛出隧道前往第一站紐瓦克時,從火車上可以清楚看到世貿中心遺址散發的煙霧和光芒,我看到現場突然爆出一團濃煙、灰塵和光芒。我以為可能又有另外一架飛機撞擊了另一棟建築物。我真的無法相信發生了什麼事。整趟前往華盛頓的旅程之中,我麻木地坐在座位上,不敢確定回家會將面對什麼樣的狀況。我一回去就聽說,我看到那一團噴發的煙霧和灰塵,是因為四十七樓層的世貿七號大樓(簡稱七號塔)倒塌所造成的。 它沒有遭到飛機撞擊,但因為南北雙塔爆炸、起火災和倒塌,跟著燃燒起來。
從聯合車站搭乘計程車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幾乎每個主要的路口都有警察駐守。雷根國家機場及杜勒斯國際機場無限期關閉。計程車上的廣播報導,聯邦調查局聲稱,仍有幾個恐怖分子集團潛伏在美國境內,計劃進一步進行攻擊,而華盛頓特區首當其衝。當我走進家門之後,無法停止擁抱我的女兒們。那天晚上,克莉絲汀和我躺在床上,聽著F-16 戰鬥機以戰鬥模式在城市上空飛行的聲音,它們準備就緒,以攔截任何進一步的攻擊。
第二天,湯普森告訴我,政府在籌備防範未來可能發生的生物恐怖攻擊,HHS將會是其中一個主導機構,他要求我成為他在這個任務中的負責人。那一瞬間,愛滋病毒/愛滋病幾乎從美國政府、甚至全國人的視線之中消失了,至少現在是如此。接下來的幾天,我參加了幾場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擴增策略主任法肯拉思 (Richard Falkenrath) 在白宮主持的最高機密會議。會議的目的在製定因應生物恐怖攻擊的短期和長期計畫。
與會者的普遍看法是,這樣的攻擊是無可避免的,而所有可能用來對付我們的生化物質中,氣溶膠天花病毒被認為是最主要的威脅。在歷史上,天花是一種藉由人與人之間傳播的致命疾病。眾所周知,叛逃的蘇聯官員聲稱,冷戰期間蘇聯儲存了大量的天花病毒以及其他致命的傳染源,以備在蘇聯與西方同盟國之間爆發衝突時當作生化武器使用。蘇聯解散之後的混亂之中,是否有任何庫存生物武器庫存落入蓋達組織或其他激進派伊斯蘭組織的手中,至今仍不明確。無論機會有多渺茫,白宮仍然非常慎重地評估恐怖分子已經掌握這些生化武器的可能性。
HHS位於漢弗萊大樓的華盛頓總部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會議。會議討論的基本主題是,因應這種新的生化恐怖威脅,我們需要發展診斷、治療和疫苗等因應對策。NIAID被指派為主導這項任務的機構。我們將負責規劃和協調研究方向,交由所方贊助者和承包商執行。當國家遭受另一波的衝擊襲擊時,這項任務變得更加緊迫。